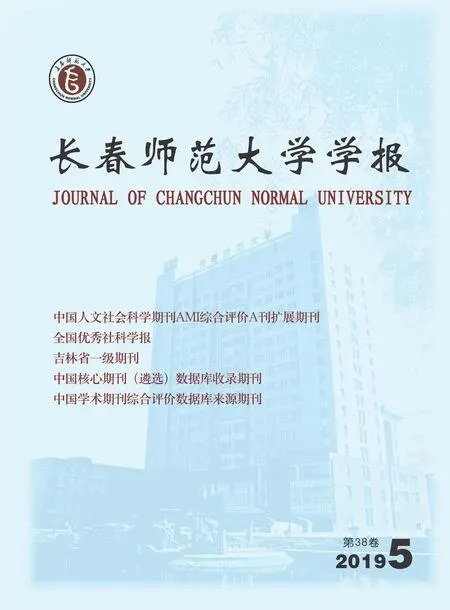博弈论视角下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语用策略
陈 洁
(广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话语”研究起源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20世纪70年代传入我国。历经几十年的蓬勃发展,话语研究已经成为横跨人文社科多个领域的术语。2008年有学者从西方话语分析的局限性和中国文化传播的需求两个方面指出中国话语研究文化转向的必要性,提出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话语学体系”,既要反映中华文化的优点与现实,又要胸怀世界[1]。2008年后,我国的话语研究路径逐渐由语言层面拓展到文化领域,呈现出“从微观的话语内部走向宏观的话语秩序、话语文化和话语文明;从个体或群体话语走向国家话语;从国内话语走向国际话语;从国家形象的话语建构研究走向国家软实力建设研究”的趋势[2]。在众多研究问题当中,中国国家话语已成为学术研究热点,并正在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
一、国家话语建构:一种国家战略
国家话语是“国家话语权利实施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一种国家传播现象及信息形态,是一种以传播国家信息,塑造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解决国际国内问题为目的的国家传播行为。其传播主体、动机、目的、信息以及传播对象、传播媒介、传播机制、传播方式和方法以及传播功能,都是以国家为核心的。”[3]中国国家话语体现了当今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艺术、体育、教育、法律、宗教、科学等各个方面的文明和文化[1]。
中国在经济崛起之后,需要拓展国际话语空间,需要输出国家价值,需要在全球提高国家话语能力,这是一种学术思维、一种政治文化思维、一种文化和文明思维[4]。
2012年6月,李长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用中国的理论研究和话语体系解读中国实践、中国道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2013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2013年12月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加强国家话语体系建设,增强国家话语权,“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在中共第十九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报告中强调,要“加强中外人文交流,以我为主,兼收并蓄,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对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语用策略研究,一方面对中国国家话语体系研究有积极的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另一方面,对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与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系,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提高国家软实力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
二、博弈论:新的研究视角
目前国际流行的话语研究方法论主要有三种:其一,语篇方法论,将言语的形式和语篇作为研究对象;其二,语篇功能方法论,将言语与语境两者作为研究对象;其三,语境构建方法论,将语篇和语境两者作为研究对象,但强调语篇对语境的构建作用。
这些方法割裂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容易使研究产生片面、脱离实际的结论,甚至导致文化冲突。在当今文化多元的世界,这样的研究方法会抑制其他文化的学术发展,阻碍学术创新。
有学者提出了话语研究的中国模式:整体、全面地分析评价话语,理性与经验、客观与主观相结合,兼顾本土和全球价值,既要使用西方实证研究方法,也要结合中华文化和本国的语境。可以多元、灵活地使用来自不同学术传统的研究工具、研究程序、手段、计策、范畴、标准等。经济学、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心理学等相关的理念都可以被借用来进行话语研究[5]。
在经济学中应用广泛的博弈论,作为人类行为研究的一种分析工具,成为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共同选择。它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统一场”理论。其中,“社会”可以作宽泛的理解,既包括人类个人组成的社会,也包括其他各种参与人组成的群体(如公司、国家、动物、植物、计算机等)。博弈论不像经济学或政治学等学科,采用不同的、就事论事的框架来对各种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如完全竞争、垄断、寡头、国际贸易、税收、选举、遏制、动物行为等。博弈论先提出在原理上适用一切互动的情形的方法,然后考察这些方法在具体应用上会产生何种结果[6]。
“博弈论理解的概念是最适合于稳定的、由大量局中人参与的现实环境,因此,在用以解释语言现象时,博弈论工具可能最为有效”[7]。博弈论运用于语言研究也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8]
Stalnaker将格赖斯对意义的哲学研究与诚信信息交换的博弈论分析相类比[9]。Parikh将不完全信息的信号博弈引入语用分析[10]。Allott指出经典博弈论运用于交际分析的模式都基于某些强式假设,而关联理论原则证明了这些假设的不可靠性。他认为交际博弈存在多均衡解,而交际博弈方并非先验式地清楚应该遵从其中哪一项[11]。
现有的将博弈论用于语言的研究主要有两个路径:一是将经典博弈论模型用于话语交际的分析;二是将演化博弈用于语言发展与进化的研究。
博弈论假设人是理性的,而现实中人们的行为不可能完全理性。整个社会科学的目的不仅是要预测人是如何行为的,还要分析社会制度的优劣,评价各种政策和方案。如果假定人不理性,那人和社会的弊端都可以归结到人的问题,人类就没有办法进步了。从长期看来人是理性的,否则无法生存[12]。
国家话语建构的行为是符合理性人假设的。国家作为话语建构的主体,其根本目的通过话语建构传播国家的文化、理念和政策,通过协调实现国内国外的合作共赢。而国家话语建构博弈的另一方参与人——各国公民,都是长期理性的,共同希望世界和平、生活富足、安居乐业。因此,将博弈论应用于国家话语建构的研究是切实可行的。
三、中国国家话语建构的语用策略
话语构建的互动行为可以视作一个博弈(game);话语构建博弈的参与人(player)是国家或企业或个人;参与人是博弈的决策主体,参与人行动的目的是使自己的效用(payoff)最大化;战略(strategy)是参与人的一个相机行动计划(contingent action plan),即参与人在什么情况下要采取什么行动。
我们认为,国家话语建构博弈是一种不完全信息(incomplete information)的动态博弈,即一方参与人对另一方的偏好(preference)、效用(payoff)、战略(strategy)的了解不充分,且博弈中参与人轮流行动。本研究另辟蹊径,使用不完全信息下的动态博弈的一些理论和模型,结合中国的国情、中华文化和学术传统进行分析,讨论在具体的环境中采用什么样的语用策略(pragmatic strategy)可以使话语达到最大化的效用。
(一)内涵稳定策略,建立和积累优良的政府声誉
国家话语建构的过程当中,双方参与人(国家与国家之间或国家与公民间)都不能完全了解对方的类型和策略。因此,这是典型的双方信息不完全情况下的重复博弈。
那么,不完全信息如何影响人们在重复博弈中的行为?1982年,克雷普斯(Kreps)、米尔格罗姆(Milgrom)、罗伯茨(Roberts)、威尔逊(Wilson)提出了KMRW声誉模型进行解释。KMRW定理认为,在博弈双方互相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只要博弈重复的次数足够多,每个人有足够的耐心,参与人就有积极性在博弈的早期建立一个“合作”的声誉。
声誉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我们第一次见到一个人,或初到一个国家,都会对这个人或者国家有一个先验的判断。随着了解的深入,我们会不断地自我修正,形成对其长期声誉的后验判断。贝叶斯法则通过所观测到的信息修正先验概率,得到后验概率的规则。
国家无论处理国内事务,还是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其声誉都是非常重要的。重视信誉的政府能够得到本国人民的信任,从而在国际事务上更好地参与合作和竞争。因此,在建构国家话语时,应采用表述内涵的稳定和一致性策略,不可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以期建立和积累良好的政府声誉。
以中国在外交领域的国家话语为例,中国正在不断地融入世界,中国的外交战略和外交理念的表述几经变迁。从解放初期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冷战结束后的“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从21世纪初期“中国的和平崛起”“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到当今的“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历来追求和睦、爱好和平、倡导和谐,造就了中华民族独树一帜的“和”文化。我国外交战略表述虽然在形式上不断发生变化,但其“和为贵”的价值内涵从未改变,并被赋予了新的时代价值。
这样的国家话语表述为我国建立和积累了“和平”“和谐”“发展”的优良政府声誉,增强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战略互信,对中国的复兴和世界和平发展有着积极的贡献。
在国际关系中,政府的声誉非常重要。但是,一个国家建立和积累何种声誉,是由需要处理的问题来决定的。我国对“南海问题”的表述也体现了国家话语中的内涵稳定性。习近平在多个场合阐述了中国在南海问题的坚定立场,强调“南海诸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仲裁庭仲裁是非法无效的,中国不接受,不承认”,面对外部势力的干涉,“中国人民不信邪也不怕邪,不惹事也不怕事”,“中国坚定维护在南海的主权和相关权利,坚定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坚持通过同有关当事国直接协商谈判和平解决争议”[13]。通过这些话语,中国政府建立了强硬的声誉,坚持和平解决问题,但也不害怕别人的挑衅。在领土问题上的强硬声誉,长期看来对解决其他地区潜在的领土争议问题是有利的。
(二)承诺策略,增强许诺的可信性
我们在生活中常见一些语言上的“威胁”和“许诺”,比如:“你要是不答应我,我就会……”,这是一种“威胁”(threat)性的言语;“你要是答应我,我就会……”,这是一种“许诺”(promise)性的声明。实质上,这些言语声明都是希望以此来影响对方的行动。
当博弈的一方发出威胁,接到威胁的一方就要判断这一威胁是否可信,比如:热恋中的人威胁对方,如果分手就不活了;有领土争端的一方宣称,如果对方不让步,就要使用武力,等。在动态博弈中如何排除不可置信的威胁,获得事前最优和事后最优动态一致的纳什均衡呢?博弈论中使用逆向归纳(backward induction)把不可置信威胁和许诺排除,从而对参与人的行为作出合理的预测。
在博弈论中,如果某个参与人采取某种行动,使原先事后不可置信的威胁变成一个事后可置信的威胁、事前最优和事后最优相一致,则这种行动被称为承诺(commitment)。承诺不同于上文提到的许诺。“许诺”和“威胁”是言辞上的表现,“承诺”指的是一种行动。只有通过承诺,才能排除不可置信的威胁和许诺,实现帕累托最优。
在我国古代的婚姻关系中,结婚后男方可以通过“一纸休书”离婚,女方会担心嫁过去之后男方不遵守诺言而始乱终弃。为了使许诺可以置信,男方通过送昂贵的“彩礼”、举办成本很高的婚礼,来对婚姻做出“承诺”:如果男方结婚后写休书的话,无法拿回彩礼,婚礼的成本越高,其承诺的作用越大,其许诺的可信性就越高。承诺行动的实质是限制自己的选择范围,通过限制己方的选择可以使己方的许诺或威胁变得可信。
我们以“一带一路”的相关话语表述为例,来说明中国国家话语建构中如何体现了承诺这一策略。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演讲,表示“为了使欧亚各国经济联系更加紧密、相互合作更加深入、发展空间更加广阔,我们可以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14]
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的题为《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强调“中国愿同东盟国家加强海上合作,使用好中国政府设立的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国愿通过扩大同东盟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同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实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15]
可以看到这些话语表述是一种“许诺”。对话语的接受者,即欧亚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国家、东盟各国而言,该倡议充满了吸引力。但是,这些许诺的可信性仍然需要耐心分析和观望。
在这之后的几年中,我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对“一带一路”作了重要的表述,不仅在言语上作出“许诺”,更在行动上作出真金白银的投入,以“承诺”增加“许诺”的可信性。关于“一带一路”的表述,既有“承诺”,又有“许诺”,在“承诺”的基础上做出“许诺”。以下三个例子来源于习近平总书记有关“一带一路”的论述。
例1: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已经迈出实质性一步。中国还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等有关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16]。
例2:“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文件已经制定,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筹建工作迈出实质性步伐,丝路基金已经顺利启动,一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项目已在稳步推进[17]。
例3:2014年至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已经为“一带一路”建设参与国的9个项目提供17亿美元贷款,“丝路基金”投资达40亿美元,中国同中东欧“16+1”金融控股公司正式成立[18]。
亚投行的建立、丝路基金的投入、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可见的经济活力,都是“承诺”行为及其话语表述,证明“一带一路”建设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举措,给地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17]。其他的国家和人民作为话语接受者,通过中国的承诺行为和承诺话语,剔除了事前许诺的不可置信性,选择与中国建立合作,这是对博弈双方都有利的帕累托最优。
由此可见,在国家话语建构的过程中,我们不能只有许诺,更需要使用承诺,承诺会使许诺的可信性进一步增强,有利于中国建立“言必信,行必果”的良好政府声誉。
(三)主动发送信号策略,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信息不对称是人类生活的基本特点之一。博弈中一方拥有的但是不被另一方所知道的信息被称为非对称信息(asymmetric information)。日常生活中,由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很多有利的交易无法实现。比如,一个产品质量很好的信息,卖家知道,而买家不知道。由于担心产品质量不好,买家怕自己上当受骗,选择不交易。这样一来,好的东西无法被卖出去。这种事前(ex ante)利用信息优势损害另一方的行为称之为“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
逆向选择会造成“劣胜优汰”。比如:二手车市场上,因为有坏车的存在,无法分辨质量优劣的消费者选择不购买,从而造成了好车不能成交[19];人们因为无法判断乞丐是真还是假,选择都不帮助,假乞丐使真乞丐得不到救济,等。
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减少信息的不对称性促成合作,具有私人信息的一方会主动向缺乏信息的一方来传递信息。但是,缺乏信息的一方如何才会相信对方主动传递来的信息是真实的呢?经济学家使用信号传递模型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Spence研究了劳动力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发现雇员有动机通过文凭等教育水平来向雇主传递自己的能力高这一信息,以此来克服信息不对称性。文凭之所以能够传递信息,是因为不同的人接受教育的成本是不一样的。简单地说,越好的大学,上学越痛苦,成本越高;越好的大学,让高能力和低能力人受痛苦的差别越大[20]。
再举一个例子,A品牌冰箱在销售时提供终身保修,而B品牌只有三年保修,那么对消费者来说,“终身保修”就是有效的信号,向消费者传递了“产品质量好”的信息,因为终身保修对质量不过硬的厂家来说是难以模仿的。
在劳动力市场上名牌大学毕业生通过文凭向雇主传递了有效的信号,因为其接受教育的成本高,痛苦程度大,名牌大学不容易考,市场上的其他雇员无法模仿。“名牌大学文凭”这个信号产生了分离均衡,将“自己是一个能力高的人”这个信息传递给雇主,使对方相信和接受。
国家话语的建构正需要解决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我们的国家正在蓬勃发展,也存在着不少问题。这些信息都是我方信息,他国并不知晓。在全球语境下,我们作为有私人信息的一方,想要有效地融入世界,促进合作和共同发展,必须向世界传递我们的信息。国家话语建构就是要通过语言向外界传递信号,这些信号必须是不可被模仿的,是有效的。这样才能够有效地将我们的信息传递出去,并得到话语接受者的信任。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实质上就是在国家话语建构的博弈中,通过话语建构向外界传递信号,减少信息不对称的影响,“让世界认识一个立体多彩的中国”。这些信号必须是有效的、不可被模仿的、让世界接受和认同的。
这些信号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是中国发展的基本国情,是中国人民真实的生活现状,是中国人民纯良质朴的情感,是中国人民积极向上、追求美好的价值观,是中国人勇敢创造、不怕困难的精神,是中国面对问题勇于承认、敢于接受挑战的自信,是中国坚持走自己道路的骨气和底气。这些是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接受中国的有效信号。
2017年1月1日一个《四川遂宁救护车隧道遇堵,众车纷纷让路》的短视频引爆网络,成为海外曝光率最高的中国社会新闻之一。视频中,当救护车行驶到遂宁城区的观音湖下穿隧道时,遭遇节日高峰堵车。救护车司机拉响警报后,社会车辆主动靠边,两车道的中间留出一辆车的宽度,使病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了救治。视频中没有露脸的“小人物们”默默做了救命的“大事”。关注这条新闻的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对许多发达国家的人民来说,这可能是一种非常自然的行为,但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这件事却又不简单,它体现了中国社会秩序的进步,真实地向世界展现了当下中国人互助、真诚的生活。这样的视频、这样的叙事,向全世界展示了真实动人的中国小事,获得了世界人民的认同。
《舌尖上的中国》是近年来炙手可热的美食纪录片,不仅在国内创下收视奇迹,在海外也颇受关注。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一季》以每集4万美金的价格出口海外,如今已经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和播放,2018年《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再次登上电视荧幕。为什么介绍中国美食的纪录片会获得来自多种文化的认同?其话语的表述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
以食物为载体,讲述的是中国人故事,展现的是食物和人物背后的中国哲学和文化传承。这样的多模态叙事将多元而真实的信号传递到世界各地,分享人类共同珍视的情感和文化,真正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见到真实的中国。
我们的国家正处在高速发展的时期,国家话语建构应该执行主动发送信号的策略,把真实的信号发送给博弈的另一方,增加信息的透明性,对内塑造社会的价值观和社会规范,对外塑造文明负责任的国家形象。
四、结语
语用策略是语言使用者为了达到交际目的对语言结构和形式做出的选择,它对语言交际的成败十分重要。本文将国家话语建构视为一种博弈,从博弈论的角度讨论了中国国家话语建构中的语用策略,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战略意义。本研究提出的国家话语体系建构策略,为如何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精神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