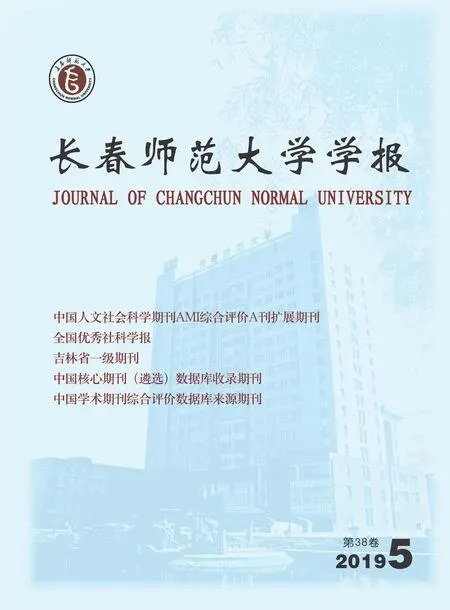关于聊城“辱母案”的伦理思考
韩 茜
(苏州科技大学 教育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在山东聊城“辱母案”的审判中,被告人于欢被判无期徒刑,因为其杀死了极端侮辱自己母亲的讨债人。这一判决在社会舆论之中引起轩然大波。对于这一案件,如果以简单的描述——于欢杀死了人为根据,那么法院判处其无期徒刑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当案件发生的详细过程公布于众后,案件的判处结果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讨论。因为从伦理角度看,在于欢母亲遭受欺辱的情况下,于欢做出这样一个举动是合乎情理的。可以看出,法律的判决并不符合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法律和伦理思想之间出现了冲突。本文就以这一案件引起的伦理问题进行探讨。
一、案件分析
根据最高法出台的《关于公布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的若干规定》要求,对于进入失信执行人名单的当事人,银行不得向其发放贷款。于欢母亲苏银霞被列入这个名单,无法进行合法贷款。为偿还债务,苏银霞向吴学占借贷非法的高利息贷款。2016年4月13日,吴学占对苏银霞进行暴力催债。催债过程中,于欢与其母亲苏银霞受到凌辱。在打斗过程中,于欢持水果刀致催债人之一杜志浩死亡。
2017年2月17日,聊城市中级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法院认为,讨债人限制了苏银霞母子的人身自由,但杜志浩等人并未使用工具。在已出警的情况下,于欢不存在防卫的紧迫性,因而以故意伤害罪对于欢进行定罪。对此判决,社会舆论将这一案件推到了全民关注的位置,并引发关于法律公正性的讨论。为此,我们有必要从法律与伦理平衡的角度对其进行思辨。
二、案件中各主要当事人的行为性质及影响
(一)催债人角度
聊城“辱母案”中,催债人的行为具有一定的攻击性。攻击性行为是指违背社会主流规范,有意、有目的地对他人精神、肉体造成损害的行为[1]。杜志浩等人的行为违反了社会道德准则,违背了社会伦理标准。从伦理角度来说,催债人的行为是不道德的,是恶的。从法律角度看,催债人的行为已构成非法拘禁罪和侮辱罪。另外,此案还涉及民间高利贷、涉黑等案件。杜志浩等人的催债行为无论从伦理道德还是法律方面来说都是不正当的,不仅对于欢母子的身心造成了伤害,也对社会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二)于欢母子角度
于欢母亲的借高利贷行为是整件事的源头,但不是事件恶化的决定性因素。本案中,被告人的母亲在自己眼前遭受持续的极端侮辱。依此背景,多数民众同情杀死辱母者的被告人于欢。但司法机关判定于欢属故意伤害不属正当防卫,并处以无期徒刑。客观地说,于欢伤人并致死,确实触犯法律,即使死者做出过违反伦理和法律的行为,其生命和生存权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所以从法律角度而言,于欢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一定的代价。
这个案件最核心的争论点是如何量刑。于欢的行为属于防卫行为,这一点从伦理和法律上都是成立的,但争议在于其是否防卫过当。于欢的行为是否属于防卫过当,取决于他当时面临的客观环境和主观环境。客观环境是于欢母子受控制于杜志浩等人,并遭受暴力催债行为;主观环境主要指于欢的心理状态。首先是恐惧心理[5]。不可预知、不可控制的事情比那些人们自认为能够控制的事情让人更有压力。面对施暴者的长时间控制,于欢无法预知他们是否还会做出其他不好的事情。加之他和母亲明显处于弱势一方,内心会产生一种恐惧心态。其次是愤怒心理[5]。心理学上认为,一次尖刻的侮辱会引起大多数人的愤怒。在此案件中,杜志浩等人对于欢母亲的凌辱行为引起了于欢内心的愤怒,进而引发了他的攻击行为。再次是于欢对母亲的爱[6]。从人性本能来说,人对母亲的生养之恩始终抱有一种感激之情。并且在长时期共同生活中,子女会对母亲产生浓浓的依赖和关爱之情。自古以来,我国以“孝”为传统美德,“百善孝为先”。汉文化价值观有这样一个公理性基础:被生育的人一定要顺从、孝顺、赡养生育自己的人,这是不用论证也没必要论证的道德根基。所以,于欢于情于理都会做出奋不顾身地保护自己的母亲的行为。
(三)民警角度
依媒体报道,民警的处理方式只是一句话:“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因而,部分舆论把矛头指向执法民警,指责其不作为。后经调查,当时案发地派出所接警后,民警朱秀明带领两名辅警出警,对现场讨债人员进行了口头制止和警告。由于现场人员众多,民警朱秀明没有采取其它强制措施,而是打电话请求增援,有不得已而为之的客观原因。虽然其处理方式确实存在一定失误,但很明显不完全属于不作为行为。从另一方面讲,在场的警察主观意识上无法预见之后发生的于欢伤人事件,他们无法预知本来处于弱势的被追债方突然成为伤人的一方。从这一点来说,民警的处理方式是不妥当的。当然,公众强烈的舆论指责也给负责对民警进行问责的相关部门造成了一定压力。
媒体报道使这一案件的审判处于群众监督审视之下。人民群众渴求科学执法、公正执法,但不可避免的是,人民群众习惯于从感性、伦理道德角度考虑司法的合理性,法律审判又是基于尊重客观事实、规则并理性地给予审理结果的一种方式。从这一案件来看,人民的诉求和法律的审判或多或少存在着不一致性。如何兼顾法律与人伦情理的共同需求,是当代寻求社会和法律的进步需要思考并解决的问题。
三、案件中体现的法律与伦理的冲突
(一)制度的正义——法治
一个普遍适用的法律体系应该是符合正义的,能满足绝大多数人的合法需求。罗尔斯说:“形式正义的观念和有规则的、公平的行政管理的公共规则被运用到法律制度中时,它们就成为法律规则”[3]。也就是说,法治要在两个方面有所体现:一是法律规则要有形式正义的观念,二是法律制度要有规矩地公正地执行。罗尔斯把执法过程中要遵守的法则称为“法治的准则”,主要有四条[4]:
第一条是“应该意味着能够”。此准则的特征为:(1)法治要求人们去做或不去做的行为应该是人们能够遵守去做或者不去做的行为;(2)立法者和法官在立法和发布法律命令的时候是真诚的,他们相信明文规定的法律是能够执行的;(3)法律制度应该把不执行的可能性看作一种抗辩,或者至少看作一种缓刑。
第二条是“类似情况类似处理”。这一准则要求执法过程中对所有规则的解释和案件中各种层次的说明具有一致性,司法者和执法者对所有的公民要给予公平和平等的对待。
第三条是“法无明文不为罪”。按照罗尔斯的解释,这一条准则包含两个方面:(1)法律要对民众进行公开的解释和说明,不能有模棱两可的嫌疑;(2)法规在其表述和含义两方面都应该是普遍的,而不是针对特定的个人。
第四条是“界定自然正义观念的准则”。法治要求执法的整个过程都要遵守恰当的规则。法官办案过程必须是独立和公正的,审判必须是公平和公开的。
以上准则明确了法治所需要的公平和自由,法治的目的也在于实现每个人的公平和自由。以这些准则来反思聊城“辱母案”的审判问题:二审前,此案子的公开性不够明显,如果不是网络平台的广泛传播,它的曝光度和受关注度不会这么强。
(二)朴素正义
此案件引起了强烈的社会愤慨,原因在于社会公众的朴素正义观念与司法实践结果之间的巨大落差。此案件中,公众以“当事人”的方式代入性思考,“如果我是他,面对自己的母亲遭人凌辱的情况,我可能也会做出和于欢一样的行为”。这种带有朴素正义的心态,促使普通民众在道德情感上认同于欢的做法。
这种朴素的正义基于人的本性——怜悯或同情[2]。亚当·斯密认为,无论人们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情。怜悯或同情是我们看到或逼真地想象到他人的不幸遭遇时所产生的感情[7]。因为我们没有亲身经历别人的事情,对他人的感受也没有直观的了解,所以我们会倾向于设身处地地想象别人的感受。
法治的追求与公众对法治的诉求存在交集,也存在差异。交集是对正义的追求,差异决定了二者的矛盾。法治实践严格遵循法理的规定,即审判、量刑等过程都客观、严谨地按照法律条文所表达的去执行,从而使人们产生了法律教条化等质疑。而公众有着朴素正义观念,往往从感性角度考量一些不合法的行为,认为很多时候不需要死守法律的条条框框,而可以凭一颗善良正义的心进行判断。其实,法治的真正实现和公众对法治的期待并不完全冲突。要想达到这两者的统一,就要做到法则正义和朴素正义的统一,让法治合情合理。
四、实现法则正义和朴素正义的辩证统一的途径
(一)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公平正义是普遍的,在实践过程中不可以为了一部分人的正义而牺牲另一部分人的正义。在“辱母案”中,舆论一致指责法律审判的不公正,乃是出于对于欢的同情,因为于欢及其母亲被催债人限制人身自由且对方人多势众。但是他们忽视了即使于欢是无意的,他也伤害了几个人的生命并且导致一个人死亡的事实。社会之所以会出现质疑审判结果的声音,就在于对于欢行为的法律审判被公众不自觉地完全当作伦理、道德、人性问题看待,所以他们作出的判断是缺乏理性的,忽视了客观存在的法律正义。
(二)明确媒介的道德尺度
在“辱母案”中,我们可以发现媒介对案件情节的传播或多或少地影响着这一案件的审判过程。这一案件之所以能引起广泛关注,最开始就是由于网络媒介的传播。从积极方面来说,有效的传播使这一案件的审判更具公开性,确保司法程序接受人们的监督,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公平正义的实现。从消极方面来说,某些传播媒介所传播的不实、虚假消息对这一案件的舆论发展方向及社会产生了不良影响。因此,社会应该对媒介所应遵循的道德尺度给予明确、严格规定。首先,媒介传播的内容必须是真实的。一方面,传播媒介有保证传播内容真实的责任;另一方面,媒介的可靠传播一旦促成了真实、善良的道德环境,自然会对整个社会带来良好的道德影响。其次,媒介的传播内容必须是健康的。这一健康的伦理意义是指要有益于人的身心发展和精神完善,要有益于锤炼人们向上的精神品格。最后,媒介的传播内容必须是科学的,主要包括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破除迷信、布局权威等等。
(三)完善执法程序的正义性
法律是以国家意志的方式指导人们行为的准则,法是正义的重要评价尺度。从前文列举的法治准则来看,立法精神、立法原意中都体现着法律对正义的追求。所以,法律在维护社会秩序的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常常发现法律存在局限性。在司法实践过程中,某些案件的争议点也表明法律是不完备的。“辱母案”反映出来的法理正义与朴素正义的冲突给了我们以下启示:在执法过程中,执法人员既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穷尽法理,按法律规定执法;也要讲情理,做到情与理的辩证统一。所谓“理”,可以狭义地理解为法理;所谓“情”,既包含与执法有关的情节、情况,也包含当事人在特定场合的心情、感情等等,同时要适当考虑广大人民群众的诉求[1]。当然,这并不是承认或者认为舆论可以影响审判量刑的结果,只是要求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合法合理地灵活运用法律条文的相关规定。
五、结语
聊城“辱母案”引起的关于法律与伦理关系的思考,反映出法理的应用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总之,法律与伦理并不是完全对立的,在实践过程中应当保持一种对立统一关系,这样才能更有效地发挥各自的社会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