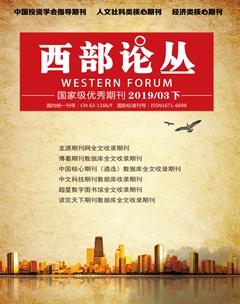英国学派世界社会视角下中国应对人道主义干预的对策
刘波
摘 要:英国学派世界社会理论强调正义的优先秩序。当前国际关系更趋复杂多变,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也日趋规范化和硬化。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积极有为,“义利共举”,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概念,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我国在人道主义干预领域的积极有为做法,与英国学派世界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相一致。
关键词:英国学派 世界社会 国际社会
英国学派世界社会理论强调正义的优先秩序。当前国际关系更趋复杂多变,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也日趋规范化和硬化。 2011年,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外交资源,开展大规模撤侨行动,在12天内,将3.6万多名中国公民和2100名来自12个国家的外国人, 海、陆、空联动,成功撤离利比亚,充分体现出中国外交“以人为本”,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本文基于英国学派世界社会中的人道主义干预理论基础,探索中国在国际压力之下如何既维护国家利益又有益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如何更加有效地选择“介入”关键点;如何在回应国际诉求、推动国际合作与实现中国战略利益之间选择“平衡点”。
一、英国学派世界社会的概念
世界社会主要指分享共同的身份和文化。布尔说的世界社会(世界秩序),指的是支撑整个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或主要目标的人类活动的格局或布局。[1]他认为世界秩序同国际秩序有些不一样。整个人类的秩序比国家间的秩序范围更广、更重要、更基本、而且认为前者在道义上优于后者。可以看出布尔的世界主义倾向。个人是属于世界社会的一部分,个人的利益应该服从于世界社会的整体利益,但同时作为世界社会中的国家应该充分保障个人的权利利益。如果国家不能够很好的保护好国内民众的基本人权,那么国家的合法性将受到严重质疑,国际社会的干预就此产生。可见,布尔后期的学术思想偏向于正义领域的研究。
布赞通过阐述世界社会的概念,重建国际社会和世界社会之间的关系,发展一种对英国学派理论的结构性解释,这种解释对之前的国际社会元素有一定的颠覆性,但本质上还是一种规范性理论,其研究方法也是多元的,因此,布赞的世界社会可以被看作一种高度成熟的国际社会。
二、世界社会视角下我国应对人道主义干预思路分析
近年来,中国国际关系领域积极有为,“义利共举”,并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概念,展现了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创造性”介入国际事务。我国在人道主义干预领域的积极有为做法,与英国学派世界社会理论的核心观点相一致。英国学派世界社会理论的核心就是人道主义干预,强调秩序的优先选择。我国积极参加世界维和行动,为人类和平事业贡献越来越大的力量。尤其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核心概念的提出,与世界社会理论强调人类命运一体的核心观点,有某种关联性。基于世界社会有关正义和秩序之间的相互联系关系,我国在应对人道主义干预方面应采取以下战略举措。
首先,積极回应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审慎选择“介入”关键点。随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变化和地位提升,中国应该从维护本国国家利益出发,积极回应国际社会人道主义干预相关规范,从发展中国家的视角来丰富和完善人道主义干预体系,引导其朝着有利于国际公平正义的方向发展。中国在坚持长期对外援助和国际维和一贯方针政策基础上,应以“一带一路”倡议为突破点,重点布局经济社会文化层面,帮助受援国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主动实施国际人权保护上的预防战略和根源治理。基于此,积极有为的“创造性介入”不失为一种新战略。
其次,积极回应人道主义干预和“保护的责任”,形成中国的话语主张。自2005年在联合国首脑大会上达成初步共识,“保护的责任”作为一种规范性要素迅速扩散。中国政府一贯赞成《联合国宪章》有关尊重人权与基本自由以及为促进人权而进行国际合作的原则。中国作为2005年“保护的责任”签字国,应履行签字责任,积极参与知识的传播与重新塑造,推动预防、治理和能力建设。无论是达尔富尔危机,还是利比亚干预,都表明国际社会对中国担负起更多的国际社会责任的国际诉求更加强烈,中国应对人道主义干预应该更加积极、主动,既不能为西方的不合法干预埋下伏笔,同时又要在回应国际诉求、推动国际合作和实现中国战略利益之间选择好平衡点。具体而言,对于“保护的责任”,课题组建议中国政府采取“逐案处理”原则:
强调根源治理和早期预防。针对西方国家强调的“作出反应”的责任核心主张,中国要突出强调早期预防在“保护的责任”原则中的核心作用,在制度设计层面上,形成以“回应解决问题”为核心的动态平衡结构。 注重结构分层和根源治理,密切关注人权灾难背后的经济资源匮乏、贫穷落后、社会治理失效和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等深层次因素,加强与国际社会在发展援助方面的合作,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国际援助”治理体系完善。需要突出当事国政府在履行人权保护方面的首要责任。主权国家应该担当起本国民众基本人权保护的最主要“责任”,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作用是辅助性的。人权本质上是属于国家主权范畴内的事务,人权主要通过国内立法、司法保障等措施加以保护和救济,外部世界无法代替当事国政府推动当地人权事业发展。人权问题进入国际法领域后,一国政府应当主动承担人权保护的首要责任,国际社会的人权保护只是维护一国人权的重要手段,并不是唯一和首要手段。
关注“保护的责任”区域层面的治理安排与实践。“保护的责任”不仅需要联合国在全球层面的治理安排与实践,更是需要各区域根据自身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性制定区域层面富有特色的治理安排与实践。中国应在国际社会就“保护的责任”在区域层面的治理展开讨论,设置相关区域治理主题,就早期预警和冲突预防,拟定完善相关区域治理协调机制。如果当事国政府已经不具备履行国内基本人权的保护责任时,在联合国行动框架内,在确定能够产生较大积极效果的情况下,优先采取非暴力手段,即外交谈判、政治协商、经济制裁、武器禁运或其他非武力方式。就具体的“介入”时间点,人道主义灾难形成的早期抑或萌芽期,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落实到保护当事国民众的人权。在非武力制裁过程中,要动态监测、评估和调整相关措施,避免加重当地人民的人权苦难。此外,要研究推动非武力制裁的具体规范措施和约束机制,确保不会被一些西方大国滥用。假如当事国因为自身人权救济能力有限,“不愿或不能主动履行‘保护的责任”,主动同意外部力量协助“介入”,那么应首先取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同意基础上,部署联合国维和人员对当事国国内民众人权进行保护。 在介入前,就维和部队的组成人员构成、实施经费、保障措施等,要进行风险评估和预警,进一步调整和严格限定介入的规范和约束性指标。就维和的具体介入时间点,安理会要根据具体情况,科学判断,审慎处理。如果联合国的力量不足以维护当地局势稳定和人权保障,那么联合国安理会在取得当事国同意基础上,授权某些国际组织,甚至某国承担“保护的责任”,但是这种局面的前提条件是:联合国安理会合法授权;取得当事国同意;如不及时快速拯救,当事国人权面临更大规模的侵害;排除干预“利益方”介入;干预取得效果后,及时撤离。在此过程中,要确保干预不会被滥用,尤其要反对借“保护的责任”口号,强行推动“政权更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