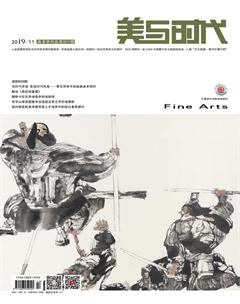美术馆里的陌生人:谈美术馆的公共教育
宣文陵
摘 要:美术馆的公共教育部门是美术馆的第四职能部门,是连接美术馆与观众之间的重要桥梁部门,也是美术馆的窗口部门,是人类完成社会自我教育的重要一环。然而国内文博系统的美术馆与博物馆更多是将观众当成陌生人、客人一般对待,提供、传达、灌输一些知识给观众。不同的观众对于知识获取的需求也是不同的,所以需要美术馆像对待顾客一样地对待观众,了解观众的需求,分年龄段地策划、设置公共教育活动以期获得观众的“好评”。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以实践为基础,从观众的角度出发,为我们提供了良好的公共教育案例。
关键词:美术馆;高校;公共教育;观众;陌生人
前些天,笔者在地铁上遇到几个外地游客在跟本地居民请教,来南京旅游可以去哪些博物馆或者美术馆参观。在很多年前,这样的情况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如今美术馆之旅已经慢慢进入普通观众的日常生活。一直以来,美术馆以“展示、保存、研究”三大功能广为人知,而对于普通参观者而言,只有在展示环节可以和美术馆发生关系。整体来说,观众是处于美术馆体系之外的,在很多时候,他们是身处于美术馆之中的陌生人。
美国博物馆学会(史密森尼学会)高级社会学家扎哈瓦·多林将博物馆(包括美术馆)对参观者的态度分成三类:一是陌生人,即博物馆方对参观者完全不理不睬,以自身的展示为主要目的;二是客人,博物馆方对参观者负有一点的教育义务,展示的同时也解释,以期传授给参观者相关的知识;三是顾客,即像对待顾客一样对待参观者,设身处地考虑他们的需求。时至今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博物馆开始考虑观众的观展体验,将参观者奉为客人,比如说配备相应的讲解,做一些浅层次的导览,甚至针对展览设置一些相应的公共教育活动等。[1]
在英语中,有“be my guest”的说法,意思是让来人能够放松下来、不要太拘束,而这句英文在翻译成中文的时候,往往被译成“像在自己家一样”。在中文语境中,这显然是更亲密的关系,但也仅仅是“像”,而不可能是真正在自己家一样随意,作为客人的参观者到了美术馆也是如此。我们很容易就会注意到,这两种对待观众的方式,都有一个主体调性在其中若隐若现,即将美术馆这一机构当成主体,而且是唯一的主体,与此同时,观众就自然而然地成为客体,居于次要位置。
与此相对,将参观者当成顾客,看似是一种买卖的关系,好像彼此的关系更为疏远了,实际上是更现代的思维方式和处理方法。“顾客”乃是一种比喻,它建立在市场经济、理性时代的商业逻辑之上。在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里,每个人都是理性人,在顾客和商人之间,隐含着一种契约精神,这种精神包含着顾客对商品的知情权,商人对顾客了解商品上要尽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义务。举个例子,你去购买一件衣服,你不会不了解它的材质、产地、价格、质量等等,在理想型的商业体系里,这些围绕着商品的所有知识你都有权获得,而且保证获得的是真实数据,商家不应该有所隐瞒。因此,在将参观者比喻为顾客的时候,美术馆和参观者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双主体的,而且这两个主体都是成熟的、理性的。这是长久以来,美术馆作为绝对主体常常会忽略的问题。
作为博物馆(包括美术馆)的参观者,我们经常会在馆内看到这样的标语“办公区域,参观者(游客)止步”。这个标语给人的感觉是:我(作为参观者)与馆方实际上是隔绝的,而馆方是更加优势的一方,我是劣势的一方。这种天然的类似于“等级”的观念,有其历史原因,也有其现实根源。历史上,美术馆的主要功能并不包括对观众敞开怀抱这一项。而现实中的原因是,参观者是处于知识的劣势地位的。由于知识的不匹配所形成的权力的不对等是普遍的,比如:教室中最有权威的是老师,学生天然就要受到老师的管束;在医院里,最有权威的是医生,病人必然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无论是手术还是用药。这种无所不在的权力,在当下社会中是十分普遍的。但这种权力关系格局明显带有非现代性,它是背负着历史的沉渣走过来的,在一个强调独立、平等、公正、自由、民主的社会里,这种权力格局迟早是要打破的。因此,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就变得尤为重要。
众所周知,公共教育是美术馆的第四职能。对于“普及艺术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让所有观众在参观展览、接受美的熏陶的时候得到精神上的升华并对文化有深刻的理解”[2],美术馆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这些都要在公共教育上有所体现。
说到公共教育,有一个经典场景就会出现在大家的脑海中:在美术馆展示的作品面前临摹的观众和在馆内席地而坐聆听讲解或现场临摹的中小学生[3]。此类场景曾经似乎是西方博物馆的专属,而现在国内的各大美术馆、博物馆不乏这样的场景出现。但是这样的场景多半出于中小学的课堂教育或是艺术培训机构的手笔,美术馆作为展示方,可以提供这样培训的场馆却很少。
虽然现如今的美术馆日益重视公共教育,但是對于公共教育重视程度和可能的边界都没有足够的认识。公共教育是美术馆直面观众的最重要的一环,也是作为机构的主体和观众这一主体直接交互的窗口。因此对于公共教育的理解,就牵涉到主体碰撞的方方面面的问题。作为一名美术馆公共教育活动的从业人员,笔者有深刻的体会。
作为一所公立美术馆、高校美术馆,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立足于南京艺术学院本身,又面向南京乃至全国的群体,以国际视野在公共教育上一直认真钻研。自创馆以来,公共教育的问题就摆在了全馆工作人员面前,如何利用现当代艺术的特性服务于大众,是其关注点之一。而作为执行团队,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负责具体的事务。
一般来说,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活动有三种类型:第一,服务于展览的公共教育活动;第二,独立于展览的公共教育项目;第三,为了公共教育而举办的展览。①
第一,服务于展览的公共教育活动。以往,观众从进入美术馆开始,就只能通过观看作品来与美术馆建立关联。然而与传统艺术作品不同,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展出的多半是现当代主题的艺术作品,观众是否有此类作品的观看经验和知识储备成为了进入此类场馆的门槛。服务于展览的公共教育项目依托于学术性的展览,活动基于深化展览主题的需要,通过一系列切合展览主题的讲座和学术性讨论进一步对展览进行梳理,增进观众对于展览的理解。教育部门的主要工作是首先认识到哪些当代艺术概念是比较难让公众了解和接受的,细化目标人群,对普通观众展开艺术通识性教育讲座以及体验型艺术实践活动。另外,面向艺术家、相关艺术从业者,艺术院校专业师生开展学术性讨论以及创作交流工作坊等活动。以此,将展览的内核逐一呈现给观众。
第二,独立于展览的公共教育项目。我们的成长是在不断的教育中得以完善的,从家庭教育到学校教育,而进入社会之后,还会有社会化的自我教育完整我们的人生。公立性质的美术馆和博物馆则肩负社会教育的重任。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本着大文化、泛艺术的教育理念,针对不同人群因材、因人施教,设置了丰富的独立于展览的公共教育项目。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美术馆现场项目,现场项目包含戏剧、肢体、实验音乐等艺术表演形式,在美术馆进行现场教学和演绎。由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是依托于南京艺术学院的公立美术馆,除了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外,还有不局限于美术的泛艺术学科受众,在这些表演艺术中,观众通过声音、律动、感官、肢体等沉浸在艺术环境中,体会了艺术的博大与宽容。而针对低龄儿童所设计的肢体课程让孩子们从小就拥抱和感知艺术带给人的喜悦。肢体剧场定期邀请国内外舞蹈艺术家及其团队驻留美术馆展开教学工作坊、环境编创、圆桌讨论以及现场表演等活动。面向零基础的公众开设的体验性教学工作坊和针对校内师生以及专业舞者策划开设专门性学习课程。(专业与公众的分层教育)
公共教育部考虑到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所能接受到的资讯满足不了知识爆炸时代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求,开设了通识性课程,包括文学、哲学、心理学、人类学系列讲座,请来了江苏省乃至全国各领域的学者、教授用深入浅出的方式分享不同学科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与运用,以期提供给观众观看展览以及了解世界的窗口。
大多数的观众是主动走进美术馆的,但是有一些群体却从来没有走进过美术馆,他们对于美术馆的了解或许只在书本或者电视里,所以针对弱势群体、特殊群体、低收入人群的教育活动就显得非常有意义。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多次举办特殊儿童的专场公共教育导览以及实践活动,带领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儿童参观美术馆并为其设置专门课程,并与偏远地区的学校建立联系,提供力所能及的艺术普及教育支援。艺术并不是某些人和阶级的专享,艺术理应遍地开花。
第三,为了公共教育而举办的展览。这一直以来是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的特色活动。以展览的形式去做公共教育活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美术馆以展览为主的格局,进一步扩大了公共教育的可能性。这类展览一般针对的是少年儿童或是对于现当代艺术缺乏了解的成年观众,所选择的题材以插画、服装设计、流行元素更加充足的艺术作品为主。配合这些展览,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会邀请相应的艺术家和适龄群体面对面交流,通过艺术家的展示、分享和授课,观众们可以直接接触到艺术创作本身。
在进行这么多公共教育项目之后,作为一名从业人员,笔者以为,公共教育项目一定要做到有针对性,不能无的放矢,尤其是要注意区分年龄段。不同群体有不同的诉求,我们需要使用他们能够懂得的语言去言说。
只有在照顾到参观者主体的多样性之后,才能进一步和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和互动。在当前的情形下,美术馆在公共教育上做的还远远不够,而笔者以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意识到参观者的主体性,还有一种美术馆中心主义。正如青年批评家蓝庆伟在《美术馆的秩序》一书中所说的:“我们无论谈美术馆的参观,还是美术馆的公共教育,往往会犯一种美术馆主体性的错误,即思考的基点为美术馆——美术馆兼具的功能很多,但如果从观众的角度出发,美術馆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服务机构,这种服务集收藏、研究、教育、展览为一体。”②因此,美术馆应该进一步去除自身的中心主义,而我们也欣然看到许多地方在提倡一种参与式美术馆,这是美术馆“去中心化”的尝试。美术馆各个部门之间的职能也应该慢慢融合,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彼此区隔。但对于长久以来形成以学术研究、展览为中心的美术馆来说,要想突出公共教育和打破这种中心主义,显然并非一朝一夕之功。
注释:
①具体公共教育活动项目请参看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官方微信 公众号“AMNUA 视野”。
参考文献:
[1]陈怡倩.从“参观”到“参与”:谈西方公共艺术教育[J].贵州大学学报:艺术版,2018(2):139.
[2]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全国美术馆优秀公共教育案例选编[M].北京:东方出版社,2019:4.
[3][4]蓝庆伟.美术馆的秩序[M].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27;130.
作者单位:
南京艺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