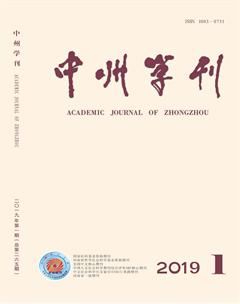宋代巫祝卜相的文化水平及数量
摘 要:巫祝普遍拥有相当高的智商,其中也有士人参加。就其职业本身而言,做法事需要书写上报神灵的奏章,很多巫师主导的民俗宗教或秘密宗教也有经文著作,敬神作法活动中经常有文字出现,还有巫祝自己的法术文字体系符箓,他们绝非“愚夫愚妇”。卜相类职业群体拥有较高的知识技能,文化水平远过巫师,他们将传统的占卜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可谓对历史文化作出了一大贡献。风水学的大普及,使宋代成为堪舆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占卜算命同样需要足够的文化基础,如果仅以会读写为标准,相士卦师基本都能做到。巫祝卜相作为一个民间不可或缺的职业参与人数广泛存在,数量巨大,有文化者全国50万余人。
关键词:宋代;巫祝卜相;文化水平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9)01-0123-08
中古代社会人神之间的媒介是巫祝(或称巫医)卜相,即借助鬼神为人驱邪、治病、算命、选定住宅墓穴等的专业人员,本文包括与巫等同的庙祝及官方常与巫术并列的“妖术”。他们在宋代活动范围广泛,正如李觏说:“今也巫医卜相之类,肩相摩,毂相击也。或托淫邪之鬼,或用亡验之方,或轻言天地之数,或自许人伦之鉴,迂怪矫妄,猎取财物,人之信之若司命焉。”①古人将巫祝卜相统称为一类,也大致可分为巫祝、卜相两类,有关研究侧重于巫觋,学术界已有颇多成果。②但在发达的宋代文化背景下,他们的文化水平(读、写或算)如何,人数是多少,均不在以往学界的研究范围之内。对巫觋文化水平偶有提及者,则贬之为“愚夫愚妇”。巫觋文化水平虽属宋代正统文化的边缘,却与主流社会密切相关,对现代学术研究而言,則事关重大,不得不专题予以探讨。
一、宋代巫祝的文化水平
对于古代巫祝,有学者认为他们的文化水平不高:“中国古代巫觋发展到宋代,群体成员中已经比较少见知识分子的身影,主要由来自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构成。他们文化素质不高,大多为文盲或半文盲的所谓‘愚夫愚妇。正如《夷坚志》记临安王法师云:‘临安涌金门里王法师者,平日奉行天心法,为人主行章醮,戴星冠,批法衣,而非道士也。民俗以其比真黄冠,费谢已减三之一,故多用之。每使邻人李生书写章奏青词。(洪迈:《夷坚志》支戊卷六《王法师》)这个王法师,似乎是一个打着道士旗号的民间巫觋,自己识字不多,连‘书写章奏青词也要他人代笔,宋代巫觋的形象和素质在此暴露无遗。”③其实,这里有偏见与误解:一是王法师为真巫师、假道士,而青词是产生于唐朝的道士通神文字,即道教举行斋醮时献给上天的奏章祝文,为形式工整和文字华丽的骈俪体,这需要很高的文化水平,显然不是巫师的专长;二是有关事例除此以外极为罕见,不能以此个别代表一般而得出巫医“大多为文盲或半文盲的所谓‘愚夫愚妇”的结论。其实,宋代巫祝还是有一定文化水平的。
第一,首先要肯定的是,巫祝普遍拥有较高的智商,“民之精爽不贰,齐肃聪明者,神或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使制神之处位,为之牲器”④。必须精力充沛、谦恭庄重、聪明智慧的人,才能担任巫师。古人还说:“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⑤巫医成为有恒心恒志的样板,由此也可知掌握这种知识、技能的高难度。在宋代,他们在官方的地位虽下降,但在民间至少是能言善辩的有见识和有口才者,为人推崇:“里能言者,宗以为巫。”⑥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有些人由于这种或那种原因,由于天赋才能的高低,被人们认为具有极大的超自然力量,从而逐渐从一般人中分出来。”⑦复杂的专业技术知识相应地都有稳定的职业教育体系。就宋代而言,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师傅教授,“医巫祝卜百工之技,莫不有师”⑧,“夫巫医药师百工之人,其术贱,其能小,犹且莫不有师”⑨。具体情况,如北宋知洪州夏竦曾揭露的那样:洪州的巫觋,“所居画魑魅,陈幡帜,鸣击鼓角,谓之神坛。婴孺襁褓,已令寄育,字曰‘坛留、‘坛保之类,及其稍长,则传习妖法,驱为童隶”⑩。可谓是“从娃娃抓起”,浸淫教养一二十年。其二是世代相传。如东京城北的祅庙,“京师人畏其威灵,甚重之”,“其庙祝姓史名世爽,自云家世为祝累代矣”,“乃能世继其职踰二百年,斯亦异矣”。另如池州英济王祠的祠祝周氏,自唐文宗开成年间执掌祠事,累代相继,到北宋其子孙分为八家,“悉为祝也”。 B11 有师长长期传授的专业文化,属于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本身性质决定,这个职业群体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巫祝队伍中有士人参加。陆游晚年曾自言:“我悔不学农。力耕泥水中。二月始穑事。十月毕农功。我悔不学医。早读黄帝书。名方手自缉。上药如山储。不然去从戎。白首捍塞壖。最下作巫祝。为国祈丰年。犹胜业文辞。志在斗升禄。” B12 认为士人可以作巫祝。他们虽然经常在某些时期遭到官府的打击(主要是针对其过分行为),但在宋代社会中还是一个正当职业,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社会地位仅次于儒者。袁采即云:“如不能为儒,则巫医、僧道、农圃、商贾、伎术,凡可以养生而不辱先者,皆可为也。” B13 属于“可以养生而不辱先者”的、能赚钱养家有体面的职业,位居僧道、商人之前。如此看来,其从业者包括士人也就可以理解了。具体例子不少,如衢州刘枢干,“本一书生。少年游京师,曾处沈元用给事馆第,遇异僧过而相之,识其功名无成,而眸子碧色,堪入鬼道,欣然授以卦影妙术,勉而受之。又一客为传天心正法,亦姑受之。其进取之气方锐,所怀盖不在此。及离乱而还,蒱博饮酒,穷悴日甚,乃习持正法,治妖魅著声” B14 。沅州的一座村寺中,有“僧行者十数辈。寺侧某秀才,善妖术,能制其命” B15 。既云秀才,该巫师定是读书识字人。蜀州杨望才,字希吕,“自为儿童,所见已异。尝从同学生借钱,预言其笥中所携数,启之而信。既长,遂以术闻”,每逢朝廷举行省试,他“必先为一诗示人,语秘不可晓。迨揭榜,则魁者姓名必委曲见于诗。或全榜百余人,豫书而缄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级高下,无有不合”。 B16 根据他少年时曾“从同学生借钱”,且有表字,可见曾上学读书,所以不但会写大标语,还会写诗。
第三,巫祝做法事需要书写上报神灵的奏章。如福州侯官张德隆知县家,有一婢女“为祟所凭扰”,“招里巫文法师视之”,无效后又“邀商日宣法师同梁绲治之。梁先行,诘问曰:‘汝曾在谁人家作过?谢曰:‘固有之,只是过公宅门不得,有秽迹神兵一千万数,罗列遮护,岂敢正眼觑着?盖梁氏素事此神甚严敬也”,“梁亦与商共议,具状其故,移牒东岳收管,婢即时顿醒”。 B17 所谓商法师、梁法师与文法师一样,其实都是供奉有“秽迹神兵”的里巫。他们依靠的是神,所有法事必须向东岳等神书写状子报告情况、请求裁决。岳州崇阳县有“村巫周狗师者,能行禁祷小术,而嗜食狗肉,以是得名。最工于致雨,其法以纸钱十数束,猪头鸡鸭之供,乘昏夜诣湫洞有水源处,而用大竹插纸钱入水,谓之刺泉。凡以旱来请者,命列姓及田畴亩步,具于疏内,不移日,雨必降,唯名在祷疏者得雨,它或隔一塍越一堑,虽本出泉处,其旱自若” B18 。祷疏之类的文字至关重要,需要精心书写,错了就失灵。
第四,巫术及巫师主导的秘密宗教,不少也有经文著作。如鄱阳官宦之后阎黻,“习行五雷术,而为人儇薄,少诚敬”。因累造祸患,担心遭报应,“招王仙坛杨道士醮谢。杨盖素行雷法者,语之曰:‘此法中神祇威猛,吾羽流清净,犹常常戒惕,岂君尘俗辈所应用心!凡所传文书之类宜以付我,不然,将获大戾。黻惧而从之,且上章谢罪,缴纳法式,誓不复敢行”。 B19 既有所研习的文书,又会上章谢罪,有文化无疑。荆南官府搜捕一巫师时,“叱从卒缚诸柱,命以随行杖乱箠,凡神像经文等悉发之” B20 。这些经文,自是巫术的来源,必须研读不已。秘密流传民间的弥勒教、摩尼教等,则有系统的经书文献。宋仁宗时恩州兵变首领王则為宣武军为小校时,参加弥勒教,与当地信徒一样,“相与习《五龙》、《滴泪》等经及图谶诸书” B21 。政和四年(1115)的诏书披露:“河北州县传习妖教甚多,虽加之重辟,终不悛革。闻别有经文,互相传习鼓惑致此,虽非天文、图谶之书,亦宜立法禁戢。仰所收之家经州县投纳,守令类聚缴申尚书省。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当官弃毁。应有似此不根经文,非藏经所载,准此。” B22 妖教传教、研习的经文,或手抄,或版印。宣和六年(1124)有臣僚报告:“比者纷然传出一种邪说,或曰《五公符》,或曰《五符经》,言辞诡诞不经,甚大可畏。臣窃意以谓其书不可留在人间。”朝廷随即颁旨:“令刑部遍下诸路州军,多出文榜,分明晓谕。应有《五公符》,自今降指挥到,限一季于所在官司首纳,当时实时焚毁,特与免罪。如限满不首,并依条断罪施行。仍仰州县官严切觉察。诏限一季首纳,限满不首,依谶书法断罪,许人告,赏钱一百贯。余依已降指挥。” B23 这些秘密宗教,主要靠文字游戏传播。明教即摩尼教信徒,“所念经文及绘画佛像,号曰《讫恩经》、《证明经》、《太子下生经》、《父母经》、《图经》、《文缘经》、《七时偈》、《日光偈》、《月光偈》、《平文策》、《汉赞策》、《证明赞》、《广大忏》、《妙水佛帧》、《先意佛帧》、《夷数佛帧》、《善恶帧》、《太子帧》、《四天王帧》。已上等经佛号,即于道释经藏并无明文记载,皆是妄诞妖怪之言,多引‘尔时明尊之事,与道释经文不同。至于字音,又难辨认。委是狂妄之人伪造言辞,诳愚惑众” B24 。这些颇具中国特色、民间特色的经文,显然是教徒编撰的,既是传教文字,至少大小头目能读懂。摩尼教在传教以及教务活动中,有“传习魔教,诈作诵经,男女混杂”,有“布置官属,掌簿掌印,出牒陛差,无异官府”,有“假作御书,诳惑观听,以此欺诈,多取民财”等等, B25 都离不开文字。从洪州巫师“神其异像,图绘岁增,邪箓妖符,传写日伙” B26 看,抄写图文的巫师以及信徒越来越多,可知他们也会识字写字。至于将佛经中“是法平等,无有高下”一句,改变断句:“则以‘无字连上句,大抵多如此解释。” B27 这就成了著名的“是法平等无,有高下”的“革命”口号。此类文人的伎俩,证明他们会读书。
第五,巫祝敬神作法的活动中,经常有文字出现。如宁乡巫师书写仇人的八字等施巫术:“朱书年命,埋状屋下,更相诅咒。” B28 具体案例如广西化州有一村巫,“能禁人生魂,使之即病。适与邻人争田,石龙县宰知其名,将杀之。既严捕入狱,即觉头痛甚,疑而思之。宰固健吏,不为沮止,帕首坐狱户自鞫讯,不胜痛,始承伏云:‘囚来时收系知县生魂于法院,盛之以缶,煮之以汤,申之以符,见在法坐。宰即押巫出城三十里,抵其居,视之而信。下著姓名、生年日月” B29 。知县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是他写的,至少具备基本的文化水平。巫师刘道昌“梦道士持一卷书置其袖,曰:‘谨秘此,行之可济人,虽父兄勿示也。戒饬甚至。既寤,书在袖间,顿觉神思洒落,视其文,盖符咒之术。还家即绘事真武象,为人治病行醮” B30 。靠着识字,才得以通过秘籍学习符咒之术,并以此为业,自学成为巫师。温州薛季宣家有病人,“命巫沈安之治鬼”期间,“与论鬼神之事”,“又语沄问学,曰:‘当读睿智、显谟两先生文集”。 B31 巫师竟然能与大儒薛季宣谈论高深的鬼神和经籍问题,有文化是肯定的。延平人张抚干“有术使鬼神,钟士显病疟,折简求药,张不与药,不答简,但书‘押字于简板上” B32 。作为同乡,向其写信求药,前提是知道张抚干识字且应回信。虔州知州刘彝,为打击改造巫医,“乃集医作《正俗方》,专论伤寒之疾。尽籍管下巫师,得三千七百余人,勒之各授方一本,以医为业” B33 。地方官知道这些巫觋具有一定的医药基础,而且识字,才向其分发医书。福州有村妇患病,“招村巫马氏子施法考验。巫着绯衣,集邻里仆童数十辈,如驱傩队结束。绕李向所游处山下,鸣金击鼓,立大旗,书四字曰:‘青阳大展” B34 。招摇旗帜上的大字表明他们识字。北宋湖州新市有朱将军庙得到重修,请太史章写碑记:“皤然老叟杖藜过门,出其旧录以示余日。”“余为览之,嫌其文词之鄙俚,姑易其语而书之壁间。” B35 所谓“文词之鄙俚”的文献,显然不是出于士人,而是出自朱将军庙的庙祝。
巫祝有文化最典型的事例,就是扶乩。宋代盛行紫姑神信仰,其基本神性就是通过写诗词占卜。洪迈指出:“紫姑仙之名,古所未有,至唐乃稍见之。近世但以箕插笔,使两人扶之,或书字于沙中,不过如是。有以木手作黑字者,固已甚异。” B36 这种完全依赖现场书写文字的神秘游戏,从唐代才开始出现,至宋朝大为盛行,可谓宋代民间文化水平提高的体现。好奇的苏轼曾亲自前往,考察体验:“予往观之,则衣草木,为妇人,而置箸手中,二小童子扶焉。以箸画字曰:‘妾,寿阳人也,姓何氏,名媚,字丽卿。自幼知读书属文,为伶人妇。”“公少留而为赋诗,且舞以娱公。诗数十篇,敏捷立成,皆有妙思,杂以嘲笑。” B37 所作诗词都是出口成章,所反映的艺术性、思想性连苏轼都惊讶,文化水平之高可以想见。朱熹曾对学生“论及请紫姑神吟诗之事,曰:‘亦有请得正身出见,其家小女子见,不知此是何物。且如衢州有一个人事一个神,只录所问事目于纸,而封之祠前。少间开封,而纸中自有答语。这个不知是如何” B38 。理学家谢良佐明确指出:“又如紫姑神,不识字底把着写不得,不信底把着写不得。” B39 另一理学家陈淳进一步言:“世之扶鹤下仙者亦如此,识字人扶得,不识字人扶不得。能文人扶,则诗语清新;不能文人扶,则诗语拙嫩。问事而扶鹤人知事意,则写得出;不知事意则写不出。与吟咏做文章,则无不通;问未来事则全不应。亦可自见。此非因本人之知而有假托,盖鬼神幽阴,乃藉人之精神发挥,随人知识所至耳。” B40 从本文角度而言,不过都是巫祝操纵的表演,反映的是巫师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才情。例如有位精通扶乩者,出身于儒生:“余干冕山士人陈氏子文叔,少习儒业,从里人许子推受迎致箕神之术,诙奇谲怪,殊骇听闻。凡来求文词者,落纸辄千言,笔不停缀,所谈皆出人意表。淳熙戊戌,有曹延者乞诗,延赋性淳朴。立书二十八字云:‘混然天性本天成,何必拘拘守意城。识破鸢飞鱼跃事,自知万物不离诚。语脉暗含其旨,他所作尽然。” B41 证实了谢良佐的判断。
第六,巫祝有自己的文化知识体系。正如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内部有“行头”“门徒知识”, B42 其中包括法术文字体系。对巫祝来说,“文字是一种巫术工具,通过这种工具获得占有某个事物和击退地方的力量” B43 。最常见的是巫祝所书画的符箓,符箓术起源于东汉的巫师,后来又经过道教的改造,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字表达体系。符箓是符和箓的合称,通常多由两个以上小字组合而成的复文,以及云篆、灵符、宝符、符图等几种形式组成,以汉字的奇异变形、重新组合为主要形式和特点,“与汉字的‘六书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B44 。这些巫教内部的文字,广大民众包括士人只能认识其中的个别文字和偏旁部首,整体是懵懂的。这也正是巫祝的意图:一是为了秘而不宣,二是为显示神秘,有意避开正常的汉字。巫术不为世俗所知所理解,正是其神秘之处。但无论如何,这种另类文字也是一种文化,是巫文化的主要成分之一。既然符箓的基本要素是汉字,不识字者也不会书画和辨认符箓。
以上事实说明,宋代巫祝绝非“愚夫愚妇”,并不是“大多为文盲或半文盲”,应该说大多不是文盲,至多属于半文盲。
二、宋代卜相的文化水平
卜相即卜相卦师,所从事的是术数文化。术数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命、卜、相三术,基础是阴阳五行、天干地支、河图洛书、太玄甲子数等“天道”的学问,为中华古代神秘文化的主干内容,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星占、卜筮、六壬、奇门遁甲、相命、拆字、起课、堪舆、择日等等。从业者想要多挣钱,就需要较高的文化水平。
测字(又称相字、拆字)的前提,是善于说文解字。不但要识字,而且要精于六书、字体结构、《周易》等。如有“测字圣手”之誉的四川人谢石,宣和年间在汴京“以术得名。善相字,使人书一字,即知人之用意,以卜吉凶,其应如响,遂得荣显”。典型事例如:“始石居市邸,人有失金带者,书一‘庚字以问石,石曰:‘汝有所失乎?必金带也。然我知其人三日内始出。果如期出。鲁公知而召之焉,书一‘公字。石曰:‘公师位极人臣,福寿若此,不必問所问吉凶。但表某微术者,公师当少年时尝更名尔。鲁公笑而颔之。吾最晚生,盖不知此,然虽伯氏枢府为长,且亦不知也。太上皇闻而密俾之,尝为书一‘朝字,命示之。石曰:‘此非人臣也。我见其人则言事。询何自知,石曰:‘大家天宁节以十月十日生,此朝字十月十日也,岂非至尊乎?上喜,乃召见。石有问辄中,且令中官索东宫书一字来,乃以‘太字进。又问石,石曰:‘此天子也。左右为大惧。上询谓何,石曰:‘太字点微横,此必太子也。他日移置诸上,岂非天字耶?上以金带赐之。” B45 其对文字精确的认识和巧妙的解读,称之为另类“文字学家”,恐不为过。南宋理学家刘爚指出:“相字知吉凶,古无此法,而今有之。” B46 可见这类拆字游戏与扶乩作诗一样,也是在宋代文化水平提高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有文化的卜相创造并从事的职业技术。
堪舆即风水术,需仰观天象,俯察地理,为世人的住宅、坟墓选择地点和时间。宋代是堪舆术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宫廷还是民间都虔诚信奉,因而其学非常普及。例如“江西有风水之学,往往人能道之” B47 。如江西人廖瑀,士人出身,精通儒家五经,“天赋聪敏,博学强记,好奇幻之术,谙天文地理。年十五,通五经,人称‘廖五经。宋初,以茂异荐不第,精研父三传堪舆术。卜居金精山,自称金精山人。著有《怀玉经》”。另有江西宁都人赖文俊,“字太素,宋时人。精地理,人呼赖布衣。著《催官篇》以天星阐龙穴砂水秘,至今传诵”。 B48 有风水术的研究专著流传于世,至清朝尚广为传播。两浙风水师陈忠厚,也是儒生出身,“少孤,举进士不偶,贫甚,无以养其母,慨然取家藏地理书学焉。且历求一时名人以为师,莫不妙尽其长,而机圆智独,又自得于象数之外。操以渉世,其术遂显”,“学于其门者,必皆心同之人乎?今江淮闽浙间,由指授以显者,著录逾四十人,而踵继者未止”。 B49 由不得志的士人而为显赫的风水大家。宋代堪舆名家和著作因而大为增多,《古今图书集成》中列入堪舆名流列传者共115人,其中秦2人、汉1人、晋3人、隋2人、唐33人,元1人、明30人,而两宋则多达43人,占总数的37.4%。 B50 古代堪舆史上两大流派——形势派和理气派,在宋代也最终形成。这些都是宋代风水师们高水平文化素质的产物。
更高深的是六壬學,为古代天文星象应用学的一种,以天人合一、天人相应的理论为指导,以天道对应人道,以时空信息包含万物运转的规律来推算人事,是天文数术之首。宋孝宗时,“日者”蒋坚“其学精于六壬,为士大夫所称道”。 B51 有着令士大夫赞赏的高深学问。刘辰翁载道:“颇有言近年樵谷星术者,问谁氏,曰:‘永丰李仁卿子也。家故儒,识今古。” B52 文化功底也是传统的儒学、史学。
占卜算命,同样需要足够的文化基础。如刘得升,“初业儒,略通《易经》大衍之数。后遇异人,教以算法,可逆知未来之事。其数积至百千万亿无涯涘,特凡人鲜能工之,惟儒者精专而识其要,故能不失万一于掌握中,言事未尝不效也”。他是儒生出身,又掌握了奇特的精算术,以儒学的底子和“精专而识其要”的功力,融会贯通,成为一方名家;算命者饶某“本书生”,建安卜者吴唐佐“本儒生,通易象,兼以篆系断之而然也”。 B53 严州人邵南,“颇涉书记,好读《天文》、《五行志》,邃于遁甲,占筮如神” B54 。遁甲以天干为三奇六仪,分置九宫,而以甲统之,根据其加临吉凶以为趋避,有雄厚文史基础者才能掌握。温州一位隐者,“居于瑞安之陶山,所处深寂,以耕稼种植自供。易筮如神,每岁一下山卖卦,卦直千钱,率十卦即止,尽买岁中所用之物以归。好事者或赍金帛,经月邀伺,然出未十里,卦已满数,不复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书生,读书不成,决意往从学。值其出,再拜于涂,便追随入山,为执奴仆之役。稍稍白所求,隐者亦为说大概,又举是岁所占十卦,使演其义。王疲精竭虑,似若有得,彼殊不以为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进也。遣出山。然王之学,固已绝人矣” B55 。书生王浪仙半途改行学算卦,尽管天分不足,但技艺仍强于众卦师,由此可知那位隐士的文化水平要高明的多,也可知只有较好的文化水平才能有较高的占卜技艺。乐平湖口人汪经,“自七岁知专志读书,性亦开敏,意将来必成伟器。未几,有一道人至,疎眉秀目,颀然而长,衣冠褎博,自称曰梅溪子,姓宇文氏,梓潼人,精于太乙数,且善圆梦”,“父呼之前,道人一见,即摩其顶曰:‘真吾弟子也。出书一编与之:‘他日藉此翱游公卿间,不可谓之无所遇也。坐顷之,一笑告去,不复再来。汪父虽甚嗟异,然期厥子以学问荣家,不令留意。累年后,经为俗故所撄,浸废学,方阅其书,了然贯通,不假指教,遂用此技成家”。 B56
另有不少卦师虽不详出身,但颇有文采。如张风子,“绍兴中来鄱阳,止于申氏客邸,每旦出卖相,晚辄醉归”,“好歌《满庭芳》,词曰:‘咄哉牛儿,心壮力壮,几人能可牵系。为爱原上,娇嫩草萋萋。只管侵青逐翠,奔走后、岂顾群迷?争知道,山遥水远,回首到家迟。牧童,能有智,长绳牢把,短稍高携。任从它入泥,入水无为。我自心调步稳,青松下、横笛长吹。当归处,人牛不见,正是月明时。皆云其所作也,留岁余乃去”。 B57 显然善于填词。刘克庄在《赠徐相师》中提到:“许负遗书果是非,子凭何处说精微。”“半头布袋挑诗卷,也道游方卖术归。” B58 卖相术之余,诗书不离身,可见其嗜读诗集。元丰年间,开封西门外荒郊中,“得一王翁焉,于乡社间能书画操筭,但久年风疾,不能履耳”。前来相求者支付数十贯,才为之卜算,结果据说非常准确,令人感叹:“其卜祝之精,有如此者。” B59 卜算之外,还善于书画、数学。狄青之孙狄偁,因家道衰落,“得费孝先《分定书》,卖卜于都市。芗林向伯共子諲,自致仕起贰版曹,偁为写卦影,作乘巨舟泛澄江,舟中载歌舞妇女,上列旗帜,导从之属甚盛。岸侧一长竿,竿首幡脚猎猎从风靡。诗云:‘水畔幡竿险,分符得异恩。潮回波似镜,聊以寄君身。向读之甚喜” B60 。不仅识字,还会写诗。
如果仅以识字写字为标准,相士卦师基本都能达到,举例如下。绍兴十年(1140)常州秋试,有术士预言:“今岁解元,姓名字中须带草木口。”众人以为:“人名姓犯此三者固多,岂不或中。”“及榜出,乃李荐为首。荐字信可,姓中有木,名中有草,字中有口。” B61 不管是否准确,至少识字。开封相国寺一相士,“以技显,其肆如市,大抵多举子询扣得失”。曾对一位考生说:“君气色极佳,吾阅人多矣,无如君相,便当巍峩擢第。”随即提笔,“大书纸粘于壁云:‘今岁状元是丁湜。” B62 居于临安中瓦的夏巨源,“亦精于卜筮”,“每来卜者,一卦率五百钱。绍熙三年冬,禹之自贑倅受代造朝,其子价侍行。既至,检点勑告文书,遗其一。虽遣仆还家访寻,终不能自释。乃同诣夏肆。夏书纸上曰:‘事在千里外。继书一‘食字,一‘尧字,合而读之,则‘饶字也”。 B63 显然,识字只是其最基本的职业要求,尤其他们多与士子考生以及官员打交道,对其所学不能不熟悉。
要之,卜相类职业群体,一般拥有高端的知识技能,文化水平远过巫师。他们的文化贡献是发展了传统的占卜学。例如宋代占卜方式比以前增多,创行了一些新的占卜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星禽,相传系北宋初司天监王处讷所创;二是揣骨,相传系宋太宗时一瞎眼相士所创;三是卦影,相传为宋仁宗时成都人费孝先所创。《古今图书集成·博物汇编·艺术典》辟有“卜筮部名流列传”“星命部名流列传”“相术部名流列传”“术数部名流列传”,唐代入传者仅20人,宋代则多达39人。《宋史·艺文志》新开辟了“蓍龟类”,专门著录占卜书籍35部。至今尽人皆知的《麻衣相书》,相传即是北宋麻衣道者或陈抟所著。 B64 由此可知,宋代卜相把占卜学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顶峰,与宋代文化的发达完全一致,也是宋代文化发展的表现之一。
三、宋代巫祝卜相数量估测
上述情况,建立在巫祝卜相盛行的基础之上,同时也促进着这一风气的兴盛,拥有相当大一批从业人员,包括士大夫在内的民众,几乎人人笃信鬼神。巫师的职业也是合法的。宋孝宗时,“绍兴府诸县自旧以来,将小民百工技艺、师巫、渔猎、短趁杂作,琐细估纽家业,以凭科敷官物,差募充役” B65 。巫师身份与百工一样。有的甚至拥有官府颁发的“执照”:宋孝宗时,“广南诸郡创鬻沙弥、师巫二帖以滋财用,缘此乡民怠惰者为僧,奸滑者则因是为妖术” B66 。其职业合法受保护。连朝廷事务中也出现巫师:宣和元年(1119),礼制局言:“崇德车载太卜令一员,画辟恶兽于旗。《记》曰‘前巫而后史,《传》曰‘桃弧棘矢,以供御往事。请以巫易太卜,弧矢易辟恶兽。从之。” B67 一度恢复了仪仗车前巫师的序列。更有甚者,在靖康元年(1126)闰十一月,金兵攻打京城、国家危亡之际,朝廷竟然病急乱投医,听信巫师救国:“妖人郭京用六甲法,尽令守御人下城,大启宣化门出攻金人,兵大败。京托言下城作法,引余兵遁去。金兵登城,众皆披靡。” B68 正如笔者早先说过的那样:“在宋代,佛教的寺院远多于道教的宫观,而神祠又远多于寺院。就其影响而言,宋人不信佛、道者甚多,但上自皇帝,下至百姓,无一不信奉神祠。” B69 至少可以肯定,宋代巫祝队伍非常庞大,不亚于佛教僧尼。
“信巫不信醫”是宋代各地普遍存在的习俗,因而巫祝遍布全国城乡,以南方广大地区最为密集。例如荆湖路:“荆楚之俗尚鬼,病者不药而巫。” B70 四川:“蜀民尚淫祀,病不疗治,听于巫觋。” B71 二广:“民间尚有巫师作为淫祀,假托神语,鼓惑愚众,二广之民信向尤甚。” B72 巫祝作为一个民间不可或缺的职业广泛存在,数额巨大。“村巫社觋”一词,就意味着每一村落都有巫祝存在。如福建福州“每一乡率巫妪十数家” B73 ,一乡十余家,一县百余家,一州则是千余家了。汀州“人多为巫” B74 。镇江龙王庙密布:“江城无小大,咸有庙祝。” B75 宋仁宗时,江西洪州(今江西南昌)发生大范围的瘟疫,但“江西之俗尚鬼信巫,每有疾病,未尝亲药饵也”。长官夏竦“遂下令捕为巫者杖之,其着闻者黥隶他州,一岁部内共治一千九百余家”。 B76 宋神宗时,虔州(今江西赣州)更多:“俗尚巫鬼,不事医药。”知州刘彝“著《正俗方》以训,斥淫巫三千七百家,使以医易巫,俗遂变”。 B77 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用的是“淫巫”一词,与“淫祠”指正祠(即载入祀典、官方承认的祠庙)以外、非法泛滥的私设祠庙一样,“淫巫”指非法的巫祝。按《元丰九域志》载该州98130户,则是“淫巫”占总户数的3.8%,若加上合法的巫祝,至少有4000户,占总户数的百分比会超过4%。粗看起来数量很大,其实平均到虔州10县中,每县不过400户、每村不过一二户而已。江西10州军,其他9州军总户数为1189006户, B78 若以2%计,则为23780户,江西路巫祝总约27780余户。这是世代相传的职业,一般都是全家靠作巫师为生,如“巫家丘氏世事邹法主,其家盛时,神极灵异。人有祷之者,能作人语,指其祸福,感应如响,家遂稍康。自后兄弟析居,神亦不复语。今其子孙尚以巫祝,相传不绝” B79 。除了男巫、女巫外,还有“童巫”,如“群国乞膏雨,童巫叫蜥赐” B80 。以一家至少2个巫师计,江西巫师约有55500余人。南方地区其余13路平均按4万计,为52万余人。加上江西数字南方总共575000余人。北方地区巫风虽然不如南方浓烈,但仍有大量巫祝。仅以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最发达的京师开封为例,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诏令:“毁京师淫祠一千三十八区。” B81 一次下令拆毁的民间淫祠就有1000余处,以每处巫祝一人计也有1000余人,另有大量合法祠庙如祆庙等等,加上巫师,估计巫祝不少于2000人。北方地区9路,巫祝平均每路按1万人计,为9万人,加上京师2000人,合计92000人。加上南方地区的575000余,全国约667000余人。
卜相人员也颇具规模。李觏曾说:“今也巫医卜相之类,肩相摩,毂相击也。” B82 是将卜相与巫祝混为一体的。其后的王安石说得具体明确:卜者“抵今为尤蕃,举天下而籍之,是自名者,盖数万不啻,而汴不与焉。举汴而籍之,盖亦以万计。予尝视汴之术士,善挟奇而以动人者,大抵宫庐服舆食饮之华,封君不如也。其出也,或召焉,问之,某人也,朝贵人也;其归也,或赐焉,问之,某人也,朝贵人也。坐其庐旁,历其人之往来,肩相切,踵相籍,穷一朝暮,则已错不可计” B83 。他估计开封人数“以万计”。
综计全国巫祝卜相共约727000余人。北宋中期的刘敞对此有个估计:“今庶人而得祭天地,旅山川,祀非其鬼,卿大夫不得立宗庙,可谓治神乎?庶人服侯服,食侯食,居侯居,男不耕女不蚕,起而相随,以事神为俗,无父子之亲,无君臣之节,下者乃为巫祝,略计天下,常百万人,可谓治民乎?” B84 他认为全国约有巫祝100万人,比我们估计的数据多出不少。还需要指出的是,这70余万巫祝卜相未必全部识字,不乏仅靠口耳相传掌握一点技术者和盲瞽、蒙人混事者。巫祝的文化水平普遍低于卜相,以巫祝三分之一不识字计、卜相五分之一不识字计,北宋末期全国约有444000余巫祝、48000余卜相,约50万个有文化的巫祝卜相。
四、结语
宋代巫祝卜相是个非同寻常的职业,本身需要掌握较高的专业技术,无论是家传还是师授、自学,都应有初步的文化水平。我们已经看到,他们拥有不同程度的文化知识,尤其是卜相者,文化水平相当高,他们发展了传统的占卜学并多有创新,在中国文化史上有一席之地。宋代诸州主管教育的官职为助教,然而,“夫市井巫、医、祝、卜技艺之流,孰不以助教自名” B85 。巫医卜祝昂昂然以教官自居,自称助教,固然是妄自尊大,未尝不是其文化底气的彰显。因而,约50万有文化的巫祝卜相,得以拥有更强的能力广泛活动在宋代各个层面的人群及各种事务中,对社会发挥着不同程度、不同性质的影响,深刻地融入、左右着人们生活,是宋代历史和文化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社会史的一个重要内容。
注释
① B82 李觏:《李觏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139页。
②仅巫医及民间信仰方面的学术专著,就有韩森:《变迁之神:南宋时期的民间信仰》,包伟民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刘黎明:《宋代民间巫术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王章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宋代巫觋信仰研究》,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皮庆生:《宋代民众祠神信仰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方燕:《巫文化视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中华书局,2008年;李小红:《宋代社会中的巫觋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等等。
③李小红:《宋代社会中的巫觋研究》,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第93页。
④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189页。
⑤孔子著,杨伯峻、杨逢彬注译:《论语·子路第十三》,岳麓书社,2000年,第124页。
⑥曾枣庄、刘琳主编,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全宋文》(第五册)卷二〇三,释遵式:《金圆集》卷下《野庙志》,巴蜀书社,1989年,第505页。
⑦J.G.弗雷泽:《金枝——巫术与宗教之研究》,汪培基、徐育新、张泽石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78页。
⑧程俱:《北山集》卷一五《汉儒授经图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0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1页。
⑨罗从彦:《豫章文集》卷一六《附录下》,李侗:《见罗先生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8页。
⑩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华书局,2004年,第2341页。
B11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四《祅庙庙祝及英济王祠祠祝累代相继》,中华书局,2002年,第110页。
B12 陆游:《陆游集》,中华书局,1976年,第1681页。
B13 袁采:《袁氏世范》,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5页。
B14 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三《刘枢干得法》,中华书局,2006年,第1484页(以下版本略)。
B15 洪迈:《夷坚志·丁志》卷四《沅州秀才》,第567页。
B16 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三《杨抽马》,第386页。
B17 洪迈:《夷坚志·支癸》卷四《张知县婢祟》,第1252—1253页。
B18 洪迈:《夷坚志·支乙》卷三《周狗师》,第816页。
B19 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六《阎义方家雷》,第837—838页。
B20 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二〇《荆南妖巫》,第532页。
B21 B67 B68 B71 B77 B81 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9770、3495、434、9216、10729、385页。
B22 B23 B24 B65 B66 B72 徐松辑:《宋会要辑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317、8330、8325、6288—6289、8348、8318页。
B25 B2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宋辽金元史研究室点校:《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536、545页。
B26 夏竦:《文庄集》卷一五《洪州请断妖巫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84页。
B27 庄绰:《鸡肋编》,中华书局,1983年,第12页。
B29 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四《化州妖凶巫》,第1498页。
B30 洪迈:《夷坚志·丁志》卷二《刘道昌》,第551页。
B31 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一《九圣奇鬼》,第364、365、368页。
B32 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一六《张抚干》,第322页。
B33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三《广南人多北于瘴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8页。
B34 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三《李氏红蛇》,第986页。
B35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二七〇九,太史章:《朱将军庙记》,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51页,引《同治湖州府志》卷五三《朱将军庙记》。
B36 洪迈:《夷坚志·三志壬》卷三《沈承务紫姑》,第1486页。
B37 苏轼:《苏轼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912—913页。
B38 B7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56、3028页。
B39 谢良佐:《上蔡语录》卷一,《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9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74页。
B40 陈淳:《北溪字义》,中华书局,1983年,第56页。
B41 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一〇《蓬莱紫霞真人》,第1463页。
B42 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二《彭师鬼孽》,第1399页。
B43 恩斯特·卡西尔著,黄龙宝、周振选译:《神話思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261页。
B44 刘黎明:《宋代民间巫术研究》,巴蜀书社,2004年,第116页。
B45 蔡绦:《铁围山丛谈》,中华书局,1983年,第43页。
B46 刘爚:《云庄集》卷五《赠相字郭道人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98页。
B47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79页。
B48 黄永纶、杨锡龄等纂修:《道光宁都直隶州志》卷二六《方伎志》,中国方志丛书,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第2108页。
B49 邹浩:《道乡集》卷二七《送陈忠厚秀才还姑苏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2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0页。
B50 張邦炜:《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05页。
B51 洪迈:《夷坚志·支甲》卷一〇《蒋坚食牛》,第788页。
B52 刘辰翁:《刘辰翁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87页。
B53 王庭珪:《卢溪集》卷三六《送刘得升序》,卷三七《增饶子序》《送卜者吴唐佐序》,《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3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68、269、271页。
B54 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三《邵南神术》,第25页。
B55 洪迈:《夷坚志·丁志》卷一《王浪仙》,第538页。
B56 洪迈:《夷坚志·三志辛》卷五《梅溪子》,第1421页。
B57 洪迈:《夷坚志·丙志》卷一八《张风子》,第513页。
B58 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05页。
B59 章炳文:《搜神秘览》,“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42页。
B60 洪迈:《夷坚志·甲志》卷一三《狄偁卦影》,第109页。
B61 洪迈:《夷坚志·乙志》卷一四《常州解元》,第301页。
B62 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七《丁湜科名》,第1026页。
B63 洪迈:《夷坚志·支丁》卷五《夏巨源》,第1003页。
B64 杨晓红:《宋代占卜与宋代社会》,《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B69 程民生:《论宋代神祠宗教》,《世界宗教研究》1992年第2期。
B70 蔡戡:《定斋集》卷一《荐鄂州通判刘清之状》,《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8页。
B73 梁克家:《淳熙三山志》,中华书局,1990年,第7877页。
B75 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南京出版社,2009年,第1098页。
B76 B85 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B78 王存:《元丰九域志》,中华书局,1984年,第249—258页。
B79 鲁应龙:《闲窗括异志》,“全宋笔记”,大象出版社,2017年,第38页。
B80 强至:《祠部集》卷二《苦雨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页。
B83 王安石:《王文公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386—387页。
B84 刘敞:《公是集》卷三八《重黎绝地天通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5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26页。
The Cultural Level and Number of Wu Zhu and Buxiang in Song Dynasty
Cheng Minsheng
Abstract:Wu Zhu generally has a fairly high intelligence quotient, among which there are also scholars. As far as the profession is concerned, Wu Zhu needs to write to report the gods when doing religious ceremonies. Many folk religious or secret religions led by wizards also have scriptures. There are often words in the practice of worshipping gods, and there are witches wishing their own spell-writing system. They are by no means "ignorant men and women". The professional groups of Buxiang have higher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their cultural level is far beyond the wizards. They have developed the traditional divination to an unprecedented peak, which has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history and culture. The popularity of Feng Shui made Song Dynasty become the heyda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geomantic omen. Divination and fortune-telling also require a sufficient cultural foundation. If only using reading and writingas the standard, physiognomists and divinators can basically do it. As a folk indispensable profession, the number of people involved in Wu Zhu and Buxiang is widespread and huge, and among them, there are more than 500,000 literate people in the whole country.
Key words:Song Dynasty; Wu Zhu and Buxiang; cultural lev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