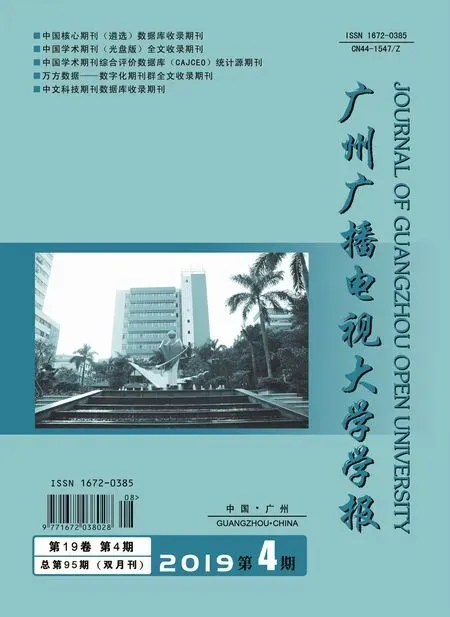论《九月寓言》的乡土流浪主题
吴雨婷
(长沙理工大学,湖南 长沙 410076)
作为当代文坛具有持续创造力和独特风格的作家之一,从80年代的《古船》到近几年的《你在高原》和《独药师》,张炜的创作始终在追寻知识分子精神的立足点,并对现代社会的现实逻辑和文化本质进行着执着的质疑与探索。《九月寓言》出版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社会经济和思想意识转型的背景下,在功利主义和消费潮流渐起中,张炜仍坚持“抵挡整个文学潮流的雄心”[1]。《九月寓言》体现着乡土叙事在世纪末的变迁,展现了对现代城市及其为代表的世俗利益观的反抗,和对乡土败落的浪漫挽歌,其中体现的超越性精神及其自身的局限性昭示着生命内在的活力,表达了张炜对乡土乃至人类内在命运的追索和探寻。
一、乡土流浪主题的形成
不管怎样变迁,地域一直是承载乡土作家的大地梦想之处,同样是胶东半岛,迥异于莫言,张炜抒写的是对野地的赞歌,对昔时自然的追忆,他迫切地希望“融入野地”,“城市是一片被肆意修饰过的野地,我终将告别它。我想寻找一个原来,一个真实”[2]。不可否认张炜的创作中确实有一定道德意识,结合时代背景,这种道德意识在对野地的塑造中逐步展现,他始终追求作家创作的某种纯洁度,坚持“把这个时代思想和创作界的一切喧嚣作为腐殖,全面地营养自己,从中孕育和培植独立的生长”[3]的精神取向,他“拒绝道德堕落,拒绝不加约束的泛滥的现代科技理性对人性的侵蚀”[4]。张炜的《九月寓言》包括之前的创作都是站立于乡土中国,城市自然而然具有了“他者”属性,是“失范的科技理性和物质欲望”[5]的象征,而他专注于挖掘乡土中国的精神根基,并将乡土精神活力终极的来源称为“野地”,张炜强调“融入野地”的这个过程,却又没有给“野地”赋予充实的内涵,而是放大了“野地”的目的性与符号性意义,从这个层面看,最终目的的模糊性和绝对性,对被神化野地的空洞迷恋,使“融入野地”的整个过程处于一定程度的非理性氛围中,无法真正达成对乡土的回归,而是呈现出持续徘徊的状态,这就形成了一种乡土流浪的主题特征。
形成乡土流浪主题的根源在于融入野地的精神焦虑与混乱。90年代产生了多元化的文化语境,并且这种多元化的文化语境本身是混乱、急遽出现又马上被颠覆的,在这种文化场域中,张炜对现代文明虽然有着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中又包含着某种理性的认同,《九月寓言》对工区和“工人捡鸡儿”的塑造就体现了这种态度的内在矛盾。张炜具有家园情节[6],怀念曾经故乡的自然环境,并将这种怀念升华为对野地的呼唤,但在小说中这种呼唤消解了对乡土的批判色彩,转而形成一种退守,这种退守有些不知何去何从的意味,因为乡土世界的愚昧、麻木、落后、狭隘和保守,使他的回望的视线无处立足,所以他渴望存在另一片带有理想色彩的乡土领域,迫切地命名“野地”这样一个元乡土概念来瓦解他的价值困惑,“当我还一时无法表述‘野地’这个概念时,我就想到了融入”[7],事实上从始至终张炜并没有对“野地”的具体内涵给出实在的界定,他焦灼的融入一直只能在乡土徘徊,这种徘徊深层上反映了在退守复古与投奔现代性之间滑动的时代思潮,在这种思想立场的指导下,小说中形成了一种乡土流浪的主题意蕴。这种乡土流浪主题,从宏观上来看,是九十年代乡土作家在“对传统与现实、城市与乡村在历史层面上的冲突时,保持了大体的理性精神”,“一旦这种冲突转移到情感层面,他们便体现出前瞻与恋旧意识的交混”[8]的困境。
《九月寓言》讲述的是奔走与停留之间的故事,一群人流浪来到此地,“整个小村都是从远处迁移过来的,不知经历了多少艰难困苦,也不知饿死了多少人,这是后代必须牢记的一次大迁移”[9],他们“停吧停吧”的声音被外乡人误解而形成䱓鲅小村,虽然小村整体的流浪告一段落,但流浪的心理却作为一种潜意识沉淀在村人心中,文中反复渲染小村人夜间串门,在田野中游荡、追逐、嬉戏、奔跑,这种奔走形成一种贯穿始终的流浪的隐喻,最终小村在工区的炮声中坍塌、消失,而村民们开始了新的流浪。
二、乡土流浪主题的具体体现
《九月寓言》的乡土流浪主题在小说中,主要通过两个部分具体体现,一个部分是外在性的乡土流浪故事。闪婆和露筋为了爱情在九月的田野间漂泊,但却充满爱情的甜蜜,住在洞穴中饱食秋天丰盛的果实,在自然中他们的生命力得到旺盛滋长,他们这过去的爱情故事是充满了浪漫色彩的民间传说,当他们来到小村,住进了温暖的泥屋后,他们的生命力却开始衰竭,田野给他们的灵气、活力、智慧在他们停止奔跑时丧失殆尽,于是露筋死去,“小村失去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个流浪汉,一个懒惰的天才”[10],虽然闪婆和露筋的流浪随着定居在䱓鲅小村而停止,但他们的儿子欢业却在宿命里继承了他们的流浪命运,在帮助小豆时杀死了金友而被迫出走荒野,他在野地中也找到了爱情。《九月寓言》的文本主要可以划为四个部分,即现时的小村故事,过去的小村传奇,现时的民间口述故事以及未来肥和挺芳重回小村遗迹的叙述内容,其中现时的民间口述故事指的是闪婆和金祥在寒冷冬季里热腾腾的忆苦,独眼义士死前的回忆,这些故事也都是外在性的乡土流浪故事的展现。
具体体现乡土流浪主题的另一部分是内在性的意象,这些意象指向乡土流浪在精神上的内在品质,文中的“红色”的存在感尤为突出,交织着热烈与焦虑的复杂情绪,《九月寓言》红色意象包括“红色的马”和“火红的地瓜”。“红色的马”这个极具有诗意的意象是张炜非常喜欢用的。张炜是由诗人转向小说创作,他的作品中的意象具有浓郁的诗学内涵,正如杨义所说“叙事作品存在着与诗互借和互通之处,意象这种诗学的闪光点介入叙事作品,是可以增加叙事过程的诗化程度和审美浓度的。不过,叙事借助意象不是为了在行文中直接做诗,它彬彬有礼地接受诗的影响,却在接受过程中使这种诗学要素入乡随俗,改变了它原来的表现。”[11]《九月寓言》中的䱓鲅小村有三宝,金祥用命换来的鏊子烤出的黑煎饼,红小兵用祖传酿酒法酿出的酒,俊俏的赶鹦。秃头工程师初次见到赶鹦时“他明白了,从此整座村庄都将退隐到云雾中去,而面前这个姑娘却会从云雾中走出来。她是这个小村落的魂魄,是它的化身”[12],赶鹦是夜间青年奔跑的带领者,她有着长腿细腰不瘦削而健壮饱满的身体,她是通过夜间奔跑保持内在的活力,她带领着肥、争年、龙眼等一批青年人在祖辈停止流浪后,以奔跑的姿态完成对大地的回归,在她身上始终有着某种东西在燃烧,这些火焰有力地吸引着村人,虽然秃头工程师对她的占有与背叛一度阻碍了这种回归与火焰,她一度迷失在黑暗而生疏的矿道里,她也曾迷茫地喃喃自语“看不到边的野地,我去哪儿啊?……”[13],但最终她还是在火海浴火重生成红色宝驹。赶鹦形象中的红色马意象暗喻小村以及小村人颠沛流离的精神特质以及一种宿命。
从地里挖出的火红的地瓜是䱓鲅小村人们的主食,让他们饱腹又带给他们痛苦“瓜干烧胃”,身体中燃烧的地瓜让他们在夜里燥热难耐,青年们夜间串门在田野释放着燥热的能量,男人们狠狠地抽打着自己的女人。肥在母亲死去之后一个人在夜间游荡,太累了而躺下时被描述为一块红扑扑温吞吞沾满泥土的地瓜,肥失去了最后的亲人,可以理解为失去了与大地的最后的联系,这为她对小村的背叛埋下了伏笔,失根的她如离开土地的地瓜,于是无可避免地被代表工区与现代性的挺芳吸引,她随着挺芳离去,却终究没被工区接纳,没有融入现代城市,而是失魂落魄的返回故土,但小村早已消失在时间中,只剩下沉淀在九月荒芜里的磨盘,在倒叙的故事的最开始,挺芳“望着茫茫夜色中动摇的枯草,一片断墙瓦砾,明白他心爱的肥再也找不到家了。”[14]在他们视角的叙述中,多次提到回来再也找不到原来的小村的感慨、悲伤,无处可归,这暗喻了他们无可避免地陷入一场更大的心灵的流浪中。
《九月寓言》的乡土流浪主题以丰富充实的表现形式存在,从表面的流浪故事到深度性的意象。这样的乡土流浪主题产生于逃避,逃避现代性的堕落、世俗的痛苦与纷扰,希望寻得心灵的自由与安定,由此引发还乡的追求,但这种还乡的过程却是失败和重复的混合体。还乡在中国当代文学中由来已久,80年代汪曾祺《大淖记事》、《受戒》等一系列书写故乡的小说,还有文化寻根小说,本质上都是在寻找精神皈依,而这种寻找是还乡性的、回归性的。张炜的还乡希望的不是返回乡土,而是更进一步、更远一些返回“野地”,但由于他对“野地”内涵的理解还未达到深层次,使得还乡成为一种无着落的流浪,从而产生了一段失落性的距离。
《九月寓言》中还有一对重要的意象“䱓鲅小村”和工区,小村的土地是肥沃的,其下丰富的矿藏是小村的灵气之源,土壤中生长的地瓜养育着一代代小村人,从这个角度看,小村意象仿佛象征的是乡土的丰厚文化精神蕴藏,工区的建立和对矿产的开掘看起来是现代性堕落对乡土精神的消耗、毁坏,其实不然,小村是建在土地之上的,因此小村意象需从土地意象中拆除出来,小村不是乌托邦[15]。土地连接广袤的野地,在《九月寓言》中更升华为某种精神根基的象征,并不会因为工区在这里的开采而消失,小村本身才是与工区相对的意象,工区的机器声、炮声打破了小村的宁静,改变了小村人的生活方式,小村人不再甘于吃苦涩烧胃的瓜干,他们想吃美味的黑面肉馅饼,去大澡堂洗去身上的泥土,不再赤足而是有黑胶鞋穿,虽然代表工区的秃头工程师、语言学家伤害了小村纯洁的爱情,但正是因为工区,小村人有了对外面世界的渴望,工区最后毁灭的并不是小村本身,而是他们的停滞。张炜的主要目的并不是揭示文明与愚昧的冲突,而是给予寓言式的警告:工业文明在摧毁归乡之路,土地才是人的根,野地才能给人以真正的生命力,是人们强烈活力的产生根源,失去地人只能不停的奔走,而永无宁日。《九月寓言》从肥重返䱓鲅小村开始文本叙述,那时小村已变成一片荒芜,肥虽然感到痛苦和失落但也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这种“轻松”既是属于肥的也是属于张炜的,因为张炜对小村的态度是尴尬的,在与工区的对比中,张炜明显倾向䱓鲅小村,他将小村的陋习风俗描写得充满诗意,潜藏着某种同情的情绪,但是从叙述中可以看出,张炜也明白这样的小村是没有未来的,它无法成为归乡情感的寄托点,无法安抚现代人日益破碎的精神。那么野地能否成为归乡情感的寄托点呢?这点在张炜那里是悖论的存在,《九月寓言》中露筋的儿子欢业出逃,走向了野地的流浪人群,在丰饶的秋季“黑斑老头明显地胖了。老婆婆们怀中的鸡一个接一个下蛋,有两个女人嚷着要生娃了”,但是欢业却日益消瘦患上怪病,他说“这病只有让那个小村的烟火熏一熏才会好哩”[16],小村排斥欢业,野地象征的流浪人群也不是欢业的归宿,由此发现,欢业的处境意味着还乡问题被悬置。
三、结语
在九十年代文学发展中,小说有滑向市场的取向,“昔日它强大的思想载力和精神含量,正是由于这种变化而日益稀少”[17]。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张炜坚持的纯文学道路中“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越来越让位于文化坚守”甚至是“退守”[18],但他创作中的对于道德精神领域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九月寓言》以䱓鲅小村为象征,展现了对人与野地关系的探索,从凝滞与流变中探寻文化出路,外在性的故事和内在性的意象共同构成《九月寓言》的乡土流浪主题书写,显示了张炜在经济发展泛滥下的人文精神立场,对乡土败落的一曲挽歌,虽然夹杂着乡土文学中对工业文明普遍的敌视,但对野地的呼唤仍体现了他对人的本质以及人文精神的执着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