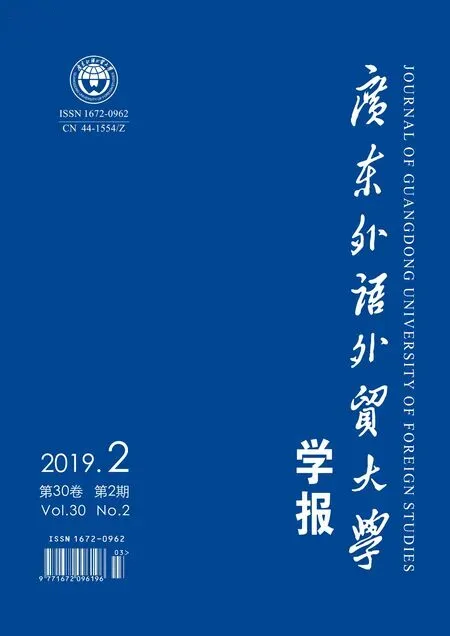长篇小说《困兽记》版本校释
罗敏月 张 均
(1.广东花城出版社, 广州 510000; 2.中山大学 中文系, 广州 510275)
沙汀“三记”之《困兽记》以演剧为线索,描述抗战时期大后方一群知识分子的挣扎与苦闷,其主要版本包括:重庆新地出版社1945年初版、上海新群出版社1946年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选集本。其中,1963年、1984年两版改动较大。就修改幅度而言,《困兽记》可谓“三记”之最,几乎每章、每段甚至每句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从修改内容上看,广涉人物、语言、细节、心理等多方面,异文材料多且丰富,颇具研究价值。大体而言,《困兽记》版本变迁主要因于出版审核制度、“新的人民的文艺”规范及主体艺术诉求等因素的变动,可谓是左翼马克思主义写作范式与《讲话》以后所形成的“新的人民的文艺”之新范式之间冲突与调适的范例。
一、政治修辞的重新调整
《困兽记》初版于1945年,是一部在左翼马克思主义写作范式影响下完成的长篇小说。与五四启蒙主义侧重于文化层面的思想批判不同,左翼写作则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将批判焦点转移到制度层面。与之相应,五四文学的批判对象可能是不确定的思想上的“无物之阵”,左翼写作则明确聚焦于现时代的政治经济权力结构之上。因此,《困兽记》最初的写作与出版,必然在其时代氛围中显得“敏感”。抗战时期,国统区不少作品被冠以“宣传共产党”“攻击政府”之名而被查禁,当政者以此手段来禁止与其执政理念相违背的思想传播,因国民党出版审核制度的影响,作家如果直接揭露、批判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问题就不免危险。在此压力之下,《困兽记》初版关于政党政治的表述就相当含糊、暧昧。及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作修改,这层“禁忌”不复存在,其暧昧的政党政治就变得明晰。对此,沙汀表示:“《困兽记》改得多,因为这本书矛头直指国民党县党部,初版时未改动那些含糊其辞的文句”,“写它时,由于牵涉到当时的国民党,牵涉到它假抗日、真反共的反动政策,因而难度也大,这本书中不少地方都写得含糊,这才得以出版”(王锦厚,2011)。而在修改中,含混模糊之处变得明确。如初版第17页:“‘老实讲吧,’田畴忽然插进来问,‘据你看,他们会不会闹翻呵!’他问得热忱而又执拗。正如一般关心这同一问题的有心人一样。仿佛这是一个重大艰险的问题,若果不能尽善解决,一切便都无从提起。因此,当他道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空气立刻变来很严肃了”。1963年版第16页改为:“‘老实讲吧,’田畴忽然插进来问,‘据你看这个大局会不会就这样好起来呵?’他主要指的是国民党对共产党闹摩擦,神气显得很热忱而又执拗。因为前几个月的反共逆流,虽然已经被击退了,但都担心反动派还会滋事。无疑这是一个重大问题,它直接牵涉到我们整个民族的发展前途。因此,当他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空气立刻变得很严肃了。而且全都情不自禁的瞟眼看了茶馆四周的动静”。显然,1963年版将初版含混的“大局”指明为国民党对共产党闹摩擦,并称国民党为“反动派”,直接批评其反共政策影响整个民族的发展。
与此相关是有关抗战材料的增补。《困兽记》初版抗战背景不大明显,修改中则屡作强调。如初版第91页:“他十分痛切的体察到,作为一个男子,而且,生在这样的时会(选集本改为:一个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孩子们对于他的阻碍太可怕了”,把“时会”改为“一个民族存亡的历史关头”,强调了抗日背景;再如初版第314页:“可是,当一听到他念到,‘一俟聘定专家,当即迅与办理,以利桑梓’等等话语的时候,大家就再也难于忍耐,谁都不肯听下去了”。1963年版第285页改为:“可是,当一听他念到,‘一俟聘定专家,当即迅与审查,以利抗战’等等鬼话的时候,大家的忍耐毕尽到了尽头,谁都不肯听下去了。而且忘记了一切禁忌”,把演剧目的由“以利桑梓”改为“以利抗战”,也是对抗战背景的强调。其次,在对章桐的修改中融入了不少抗战材料,如初版3-4页:“章桐是个小个子青年,瘦削,精悍,耸着半头未上过油脂的黑发。他在十分诙谐的诉说着回家以后的遭际。若果没有接二连三的老母病危的电信,他不会回来的,可是他就在翌晨,他才弄明白,自己这一回上了这个使人啼笑皆非的呆当(1963年版:已经溜到解放区去了。因为他所属的那一部分川军正和八路军防地接近,彼此常有来往。而他这回的确碰上了一个使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刚才到家的一天,他就有点怀疑,因为他的母亲正和从前一样健康,只是瘦了一点,老了一点,但他相信了她的已经复原的解释。他走了一两个月的路,她的复原是可能的;然而,他的妹妹,终于向他告了密了(1963年版:把秘密透露了)”。到选集本305-306页,这段被增写为:
到家不久,可以说刚一再街上露面,他便被热烈的欢迎所包围了。不仅是他的同事,那些在“七·七”事变后跟他一道搞过“救亡运动”的人们,便是一些素无交往的各色人等,也怀抱着不同的动机,沾着他探询前线的情况和他对战争前途的看法。……今天宴请他的同事也都大体得到了满足,对抗战增强了信心。而他本人,则正在用他惯有的诙谐语调、措词向他们诉说着他回家以来的遭遇感受,不时发出苦笑,用手掌往后抹了一抹马偕乱糟糟的头发;虽然这一抹的功效太有限了。这倒千真万确,若果没有接二连三的老母病危的电报,他是不会回来的。而且已经溜到延安学习去了。……然而,就在昨天他妹妹终于把真情透露了,全是他大舅出的主意。
此处改动幅度颇大,1963年版指明了章桐所去之地为解放区,选集本则增补了章桐回到家乡以后人们对他的热烈反响,并向他询问前线情况及对战争的看法。此外,还增加了对八路军积极抗战的正面描述,增补了章桐前往延安学习的材料。这些修改既能更好地突出章桐英勇形象,也能从侧面强化抗战叙事。又如初版第12页:“章桐是在形容着前线吃食的菲薄,但又立刻加以限制,说这菲薄不仅不使人觉得困苦,反而提高了吃的兴致,因而有时一碗白饭竟也等于一种异味”。1963年版第12页改为:“章桐正在用一种赞扬口气叙述着前线的日常生活。但他所说的情况,绝大部分都是八路军地区的。因为他见过不少,也听过不少,而更为重要的是,他向往这种生活,而且希望大家从它得到鼓舞”。此处改动把初版中含蓄的前线生活明确为八路军地区的日常生活,并指出章桐的向往与赞美之情。这些相关抗战材料的增补,一方面明确了小说故事背景,另一方面更显现出章桐“走出去”的光明形象。此外,借章桐之口来抒发对八路军的赞美之辞,无疑也与新中国成立后“新的人民的文艺”之于党的历史的神圣叙述相适应。所谓“新的人民的文艺”,是新中国成立后周扬根据《讲话》与新形势所提出的新的文艺要求,它承续左翼文艺却又有较大发展。承续在于它继承了左翼文艺的政治经济学视野,发展在于它更强调对“新英雄人物”及其所从属的“新社会”的叙事形构。
出于这种“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需要,作者还把小说中人物去向或愿景均改为“到延安去”。如初版第417页:“他从他的朋友看出了自己的不行,而且徒然的感觉到,他也有一条和他相同的出路:到前线去!”1963年版把“到前线去”改为:“到延安去!到抗战的最前线去!”这两处都把初版中“上前线”改为“到延安去”;又如初版第14页:“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个孕妇的英勇经历”,1963年版14页改为:“他们最感兴趣的是一个叫作小邬的女同志,随后跑到延安去了”;再如初版第393页:“‘随便你怎样说,怎样好啦!到成都,重庆,都行!再不然我们就直接到恩施去找老黄。只要是你愿意,找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1963年版第351页改为:“‘随便你怎样说,怎样好啦!到成都,到重庆,都行!再不然我们直接到延安去找小邬。只要你愿意,就是天涯海角我都没有问题!’”。这些修改多次把人物去向改为“到延安去”,多少反映了初版写作时作家不便表达的心理(沙汀写作“三记”之前曾在延安实地生活并写作),但更多是“新的人民的文艺”的规约所致,故略显干瘪且有一定说教意味。这可算是“新的人民的文艺”逐步内化于作者创作思想的生动体现。
二、人物塑造之修改
《困兽记》最大改动是对人物塑造方法进行调整。小说主要刻画抗战时期大后方苦闷挣扎的知识分子群像,因有作者真实体验为基础,初版对人物的内心描写尤见逼真极致。而在新中国成立后,传统左翼文学对人物极致的白描刻画笔法一定程度上让位于“新的人民的文艺”的叙事成规。为此,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做出调适,这首先体现在拔高牛祚这一象征出路意义的人物之上。
作者在《困兽记》题记中写道:“我另外穿插了两个人,一个勇敢地走出去了,一个则一直勤勤恳恳地固守着岗位。若果说一部作品必得向读者指出一条道路,这点穿插,也许可以担当起这个任务罢了”(沙汀,1950:4)。《淘金记》曾被批判写得过于黑暗,同样,《困兽记》整体色调也灰暗阴郁,但较之前者它还是刻画了两个象征出路与光明的人物——积极出走的章桐和乐观留守的牛祚。在修改中,作者对他们均作出不少改动,一定程度上美化了象征出路意义的人物牛祚。当然,这多少含有作者个人情感因素在内。牛祚原型是作者“素所尊重,交情又最深的老友马之祥”(沙汀,1987:135),“此公在安县教育界很有威信,的确也是一位很有特色的知识分子。20年代末期,他曾是安县发展党组织的对象之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过安县人民政府的文教科长”(沙汀,1998:342),沙汀对其极为欣赏。但主要应是出于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适应。“新的人民的文艺”要求文艺作品能够鼓励读者向往新的社会与人生,故作品不宜写得过于消极灰暗,为此,沙汀从三个方面对牛祚进行修改。
首先,增补牛祚的苦难经历,突出其坚毅品质。譬如初版第10页:“这人叫做牛祚。白面黄须,三角眼,素以明达干练(1963年版改为:耿介正直,改同选集本)获得普遍的尊敬。加之口齿幽默锋利,时有警语,因而更加使得一批年青爱戴。他常被誉为老青年,在座的人,几乎大半全是他的学生。他已经教了二十多年书了”。1963年版此处增加:“这中间他经历过不少事变,碰过不少钉子,但是人世间的一切艰辛并没有叫他完全消沉下去,便在日常谈话中间,也都经常流露出他对现状的愤懑”。此处增补“他经历过不少的事变,碰过不少钉子”,强化了牛祚曲折苦难的生活经历,并以“没有叫他完全消沉下去”来突出他豁达坚毅的品质。第二处修改是初版第101页:“虽然时常同情别人,体恤别人,尤其是青年人,老教师(1963年版改为:牛祚)却挺不喜欢别人向他诉苦。他只有几亩薄田,一座(1963年版改为:几间)破屋,但却有着七八口人的负担;半生来的挫折更不算少。他失过恋,受过政治上的迫害,因为贫困,他在大学三年级上便不能不辍了学,抛弃了他的工程师的梦想(1963年版改为:他父亲是为打抱不平被恶霸干掉的;他兄弟在广州起义后失踪了;母亲哥哥则是活活给气死的!因为贫困,他在大学一年级上便不能不辍了学,抛弃了他的工业救国的梦想),但他却从不会同任何人诉说过他的苦衷(1963年版改为:诉过苦)”。对比可知,初版关于牛祚挫折的描述是“失恋”“受政治迫害”,以及因贫困在大学三年级不得不辍学;而1963年版则改为“父亲被恶霸干掉”“兄弟在广州起义后失踪”“母亲哥哥被活活气死”,刚上大学一年级便因贫困而不得不辍学。如此处理不仅使牛祚挫折经历更为痛苦心酸,而且更能使牛祚苦难成长历程与革命史发生更深关联。
其次,突出牛祚为他人着想的善良品性。譬如初版第28页:“大家意外高兴的哄笑起来,而牛祚实在没办法说下去了。这并非因为大家笑得过于厉害,或者怕过分得罪了人,实则是他由此感到了一种更深更广的怅惘(1963年版改为:苦闷;选集本改为:忧愤)”。1963年版此处增加:“而且从内心深处来说,归根到底,他也并不愿意挫折他们对待生活的积极态度”。在初版里,只是写到牛祚面对现实产生了深广的怅惘,修改中,作者则增补了牛祚虽然内心苦闷但并不愿意打击人们对生活的积极态度,由此体现了他心性温纯、替他人着想的善良品性。又如初版第358页:“他忘记了他对牛祚素来的尊敬,跳起来就走掉了”。1963年版第321页增加:“牛祚不以为然的皱皱眉头。他一向是了解章桐的,他对章桐最近两年的经历和思想变化也知道得最多,但也奇怪,这个青年人一下会这样不冷静,完全忘记了他一向对这个所谓大后方的看法。而且他还想起老医生刚才向他透露过的消息,很为他的学生担心。‘我看他也该走得了!’他自言自语的叹息说,决定很快找章桐谈一谈”。这处修改增补了他对自己学生章桐的担心与关心,两者均更好地表现了牛祚替他人着想的善良品性。
另外,作者还增强了牛祚沉着踏实、睿智豁达的品行。如初版第160页:“于是牛祚开始从从容容铺叙了一番目前许多事只有逆来顺受的理由。然而,这却是多余的,因为单凭他的深沉的设问,以及暗示,田畴便已经醒悟了。‘好了吧!’他切断他说,‘我认输就是了!……’‘这还不够!以后凡是什么事,要多用点脑筋才对呢!’牛祚纠正的说”。1963年版第150—151页改为:
于是,凭着他那份有关全县政治社会情况的丰富知识,牛祚开始从从容容铺叙了一番他对整个事件的看法以及各种设想。然而,这却是多余的,因为(选集本改为:只是没有提说一句他为章桐作的安排,那位仁兄恐怕还没有资格为所欲为!然而,)单是那些深沉的设问,以及提示,田畴便已经醒悟了。“好了吧!”他切断牛祚说,“我认输就是了!……”“不要忙着认输!我还有点补充:大局已经没有春天紧了……(选集本此处增加:那位仁兄恐怕也还没资格为所欲为。)”“这点我倒知道!”“知道就好!不过以后凡是什么事,不要一股冲呵!”牛祚柔声的叹息说。
此处着重写出了牛祚对整个政治社会情况十分了解,使牛祚显得更为沉着冷静,对前景充满希望。又如初版第298页:“‘要是能够安于平凡也好’(1963年版改为:‘能够像牛老师那样认认真真教书,也好!’),他痛苦的加上说,勾下了头”。初版第410页:“十二月中旬的一天下午,大家草草结束了课程,接着就放学了,一齐了无生气的守在准备室等晚饭吃”。1963年版增加:“只有牛祚在聚精会神批改文卷。正如他的性格、情趣以及土头土脑的装束一样,他对功课照样还是那么热心,没有多少改变。”两处修改均表现了牛祚工作的踏实、认真。前者通过旁人赞美话语,从侧面突出了牛祚工作热真;后者增补了牛祚结束课程后留在办公室聚精会神批改作文的情节,直接描写其对工作充满着热忱。这些改动也是作者逐步转向“新的人民的文艺”的生动体现。
此外,作者还对小说中劳动人民的描写进行了部分修改,以适应“新的人民的文艺”之于正面人物的肯定性的叙述要求。其中,以对田畴家佣人“王妈”的修改最为典型。与初版相比,1963年版明显有美化意图。譬如初版第63页:“这姨娘(1963年版改为:王妈)也是田畴的脾气所能容忍的人物之一(1963年版此处增加:身材瘦小,但却硬朗,地道的庄稼人)。她没有亲属,她的唯一的儿子,出门当兵十多年了(1963年版改为:因为同一批地主娃娃在打猎中引起一场斗殴,十多年前,逃跑出去当兵去了)。她从未讨过工价,而当去年那当兵的忽然从湖南寄回证件以后,她还继续把按期领到的优待谷借给主人使用,说是这个年景,只要大家混得过便算万幸(选集本此处增加:她对这家拖儿带女的小学教师非常同情)。她的缺点是(1963年版改为:王妈)行动迂缓,性情固执,老是钉住一件事唠唠叨叨不休(1963年版此处增加:又很自信,凡是自己以为正当的事从不让步)”。修改后,首先点明王妈是“地道的庄稼人”这一劳动人民的身份,明确其阶级属性;其次删去了描写王妈缺点的字眼;另外,还增加了她自信兼具正义心与同情心的优点。在遣词造句上,也下意识地美化了她的形象。
《困兽记》主要描写知识分子,王妈毕竟不是主要人物,作者对她的陈述并不算多,但从1963年版中所增加的对其美好、善良品格的描述中足以窥视,作者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对“新的人民的文艺”的适应与调整。沙汀属于左翼作家,深得左翼传统批判精神之精髓,即便是对下层人物也时常赋予灰暗、麻木的色彩,但《讲话》明确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毛泽东,1968:828),“颂歌”即成为“新的人民的文艺”描写人民之间新的准则,沙汀的修改折射出了他对新的文学规范的接近。
三、重构情感故事
“五四”作品普遍注重个体感性心理描写,沙汀曾师承鲁迅,对人物心理刻画之功力尤为深厚。《困兽记》初版有很多关于人物个人情感的叙述,尤其是对吴媚、孟瑜、田畴三者之间复杂爱情描写非常细腻,直见人物内心深处的隐秘与挣扎。其中知识分子感情上的纠结与抗战时期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的焦虑心境,尤能显出“困兽”之蕴含。然而私人化感情往往是“比较孤立、本身缺乏社会性含义的题材”(林岗,1998:218),并无助于政治意识形态的表现传达,与“新的人民的文艺”也不太吻合,故在修改中,初版强烈而复杂的人物情感相对被弱化。作者对吴媚、田畴、孟瑜之间三角恋的情感纠葛作了删减,尤其对小说人物关于爱情的心理感受、回忆及其情态动作等描述删改颇大。
在三者中,吴媚感情关系最为复杂。她作为第三者介入了田畴与孟瑜之间的夫妻关系,同时在与丈夫的关系之中又被小妾介入。作者对吴媚与丈夫的情感关系作了修改,如初版第281页有这么一段话在1963年版中被删去:“她之动摇,固然由于娘家并非久留之所,父母原和她不投机,他们的窘况,更是叫她难受。但是最主要的,是她被娘姨的传言迷惑住了,认为她的回去不能算作示弱,因为他已经特别派人来请她。”此处描述吴媚与丈夫吵架后赌气较量的复杂心理。此时吴媚已爱上田畴,对于丈夫并非纯粹爱情关系,更多是失宠后对另一女人的报复、斗气与屈辱感:最初觉得回去就是示弱,但后来觉得娘家亦非久留之地,且传闻丈夫已派人来请自己,回去也不算示弱。修改删去此段,则把吴媚犹豫纠结的复杂心理简化了。另外,对吴媚与田畴的情感也大有改动。如初版第321-322页:“随着皮鞋声音的临近,吴媚确乎是出来了。当一听到他的拜访的时候,她开始感到惊异,这是她不会想到过的,更猜不透他是抱了什么目的而来”,“她一时曾推测他是为了演剧来的,但也立刻被推翻了。这不仅因为早已没有人提及它,假期也快完了,大家决定不会有这份闲情。此外一个推测,虽然使她马上陷入一种甜蜜道德感情的混乱,但她又尽力排拒它,想出种种理由来向自己正名,这个是毫无根据,不可靠的。正如一个正经绅士,会非礼非法,闯进一个良家女子的闺房一样的古怪。然而,末了,她却始终只能相信它了:他是受了孟瑜,她的知心朋友的怂恿来解释的”,“因此,吴媚,不仅对于孟瑜那天的态度抱着好感,她还谴责自己的狭小,负气”,“于是,稍稍打扮了一下,她就走出寝室去了”。1963年版第291页对这段文字大为删减:
随着皮鞋声的临近,吴媚确乎是出来了。当她听到田畴的拜访的时候,她开始感到惊异,随即作出各种各样的推测;但却始终猜不透他是抱了什么目的来的。只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不可能是一种通常访问。最后,抱着一种复杂、微妙的紧张心情,她出来接待他了。因为从内心深处说,她也多么强烈的期望着这个会见!
此处改动幅度极大,初版通过系列细腻心理刻画,精确地描绘出了吴媚此时此刻焦急期盼又忐忑不安的复杂心绪,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她处于三角恋关系中痛苦矛盾的心境。修改版则简单很多,对人物内心隐衷挣扎的描写大量删除,仅以“随即作出各种各样的推测”一语带过。复杂而微妙的爱情心理状态被简单化、规范化了。这种修改,显然与三角恋爱在“新的人民的文艺”中的不合时宜有关。但从艺术层面上而言,心理描写最能深入而真实地呈现人物性格特征,删去对人物内心感受的刻画,无疑对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及真实性有所削弱。
田畴作为知识分子“困兽”的代表,是这场三角关系中唯一男性,作者对他的改动也不少。譬如初版第236页:“从此以后,他们没有再提吴媚的事,但都显得有点沉闷不安。而且彼此又全明白,他们之所以避开它不谈,只是因为担心他们的沉闷不安,将会转化成暴风雨,不是互相争吵一场,便会对于吴媚爆发出无所顾忌的怨诟。甚至彼此会同意于一个和她决裂的行动。然而,当其吃过早饭,向大门走了一转,又回来翻了翻书,然后用了极大的忍耐,在阶沿和她相对的坐了一会之后,他就再也受不住了;但是,一个蓦然而来的念头仍然解救了一场争吵”。1963年版改为:“从此以后,他们没有再提到吴媚的事,但都显得有点沉闷”,“吃过早饭,他有意回避似的跑去逛田坝去了;但他随又转回来了,坐在堂屋里乱翻阅书籍;最后,他偷偷看了孟瑜一眼,接着乒的一声把书放在桌子上面”。以上所写是孩子已成为田畴夫妇生活的累赘,他们本期待吴媚来领养他们的孩子,结果吴媚失约,田畴因此心情颇是复杂:埋怨吴媚轻率爽约,内心不无压抑、愤怒,但吴媚始终是其内心最深刻的思念与隐痛,在忍耐极致至快崩溃的时刻,还是按捺住内心情绪,缓解了一场争吵。修改后,作者把这种复杂心理纠葛简化了,而个中人物压抑的撕裂感也被大大弱化。对孟瑜的情感修改也不少见。如初版第405-406页:“孟瑜于是收住眼泪,也立刻站起来了;悬心的期待着那个默默站在那里的田畴的次一动作。她哀怨的苦笑了,她看见他延颈望了一会,接着就转过身来,踽踽凉凉的踏上了回转家里的去路。当他从她面前走过的时候,他连看也没有看她一眼,他的注意,似乎沉到某个深渊处所去了。孟瑜把脸迈开,让他走过去了,于是低低的垂下头,无声无息的跟在他身后。陆续跟上来的是孩子们和王妈”。1963年版第361页改为:“孟瑜一直没有张声。而且,当田畴踽踽凉凉从她面前走过的时候,她还充满恨意的叹口气,回避开脸。她痛恨他对她的欺骗,甚至感到无法再同他一道生活了。但是,当她想起他的神色,他的痛苦和他的脆弱的时候,却又不禁心头一软,渗出一种无法克制的怜惜之情。最后,经过王妈的劝慰、恳求,孩子们又一直闪着可怜无告的眼色,不肯回家,她也终于从田坎上站起来了”。初版中孟瑜情感显得更为柔弱而细腻,内心完全受田畴态度所影响纠结。修改后人物情感被弱化,改叙得较为抑制,由“哀怨的苦笑”“无声无息的”跟在田畴身后可怜的怨妇形象被改为“一直没有张声”、痛恨他对自己的欺骗、“从田坎上站起来”的女性形象,人物变得相对独立坚强。
无论是吴媚、田畴还是孟瑜,初版主要以传统左翼文学“如实写来”的笔法为之,尤其是人物心理刻画极其细腻且深刻真实。然而在“新的人民的文艺”里,“爱情”成了小资产阶级情调,故其删减势不可逆。但从艺术层面而言,这种删减无疑使人物复杂纠结的内心活动相对单一化了,间接削弱了人物性格的内在矛盾性及其真实性。尤其小说中两性之间的纠葛情感实也是知识分子苦闷之外现,所谓“困兽”之压抑困顿的生存状态一定程度上也是通过人物爱情纠结来传达的,但删减后对初版“困兽”的压抑无望感亦有所冲淡,其艺术性必然有所降低。
以上所述,是《困兽记》版本变迁之主体面貌。恰如研究者所言,文本生产“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源于一个复杂的生产过程,受到多种不同层面社会结构力量的制约”(大卫·克罗图、威廉·霍伊尼斯,2009:40),《困兽记》版本变迁正是这种“复杂的生产过程”的例证。其初版延续了左联时期以茅盾为代表的左翼马克思主义写作范式,但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不同版次的修改中,则呈现了朝向“新的人民的文艺”靠近的努力,如增补政党政治及抗战材料,调整人物性格塑造、重构情感故事等,皆因此故。就艺术层面而论,其有关人性、人情的复杂呈现,有关人物性格真实性的发掘,都不免有所削弱。这种版本变迁,是左翼文学传统在新中国文学环境中自我调整的代表性案例,透露出当代文学内部不同文学传统之间相互冲突与调适的文学史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