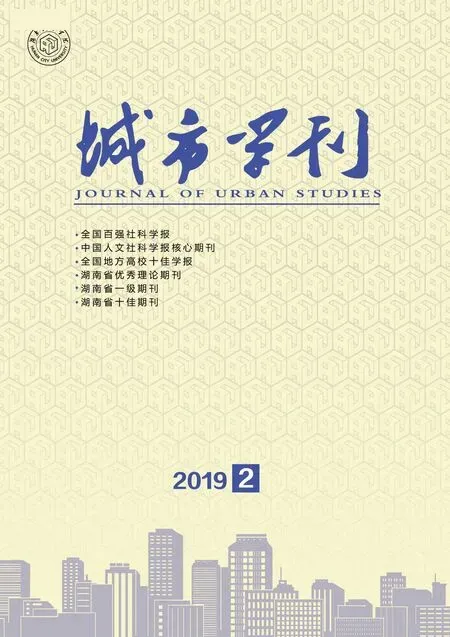女性身体的焦虑与释放——《山乡巨变》的另一种解读
杨厚均,张诗颖
女性身体的焦虑与释放——《山乡巨变》的另一种解读
杨厚均,张诗颖
(湖南理工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作为“十七年”革命文学经典之一,《山乡巨变》看似回避身体的文学叙述里,暗含着女性的身体焦虑,存在着一个女性的身体焦虑与主流意识形态既冲突又和谐的复杂关系。这样的一种叙事态度,体现了《山乡巨变》文本意义的丰富性。
《山乡巨变》;女性身体焦虑;焦虑释放
《山乡巨变》作为“十七年”文学经典之一,以“茶子花”般的浪漫抒情风格显示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作为《山乡巨变》中亮丽风景的女性形象,始终是研究者关注的对象。小说以农业合作化的宏大叙事为背景,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女性形象图,如以邓秀梅、盛淑君为代表的新型乡村女性,[1]以张桂贞、盛佳秀为代表的徘徊在进步与落后之间的农村妇女,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中老年妇女群……她们向我们展现了女性在合作化运动中的自觉与自信,用实际行动践行妇女“半边天”的社会主义新理念。但当我们对这些女性形象作更细致更深入的探究时,我们又惊讶地发现,她们并不是像我们之前理解的那样“单纯”,在她们身上我们隐隐能感觉到一种与她们身体相关联的深深的焦虑,与此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她们总是自觉不自觉地通过各种合法的途径来替换或者释放这样一种焦虑。由此,我们可以窥见作者在女性体察的真实性、细致性与浪漫性之间纠结、调和的良苦用心,而这恰是《山乡巨变》文本的丰富性所在。
一、三种身体焦虑
性、生育与劳作,是人类生存最基本的几个方面,最终都凭借身体来实现。就女性而言,这三个方面面临的局面可能较之男性更为尴尬,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女子的性往往是不“合法”的,是压抑的,与此相关的身体特征同样也是被遮蔽的,生育更是被指认为女性的“当然”职责,其独有的身体体验根本无法获得男性关注更不用说认同,而劳作,在一个“夫唱妇随”的社会结构里,男性的劳作才是主体,女性的劳作以及劳作中的身体遭遇同样是被忽略的。也因此,女性身体上的焦虑也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新中国的理想是男女平等,是女性全面解放,因此,在新中国想象的各类文学文本里,新的女性总是健康的,阳光的,充满朝气的,她们像男性一样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当中,她们在性、生育与劳作方面的身体差异也往往被有意无意地“过滤”。应该说,这也是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在女性形象塑造的出发点。然而,即使是浪漫的周立波,以其对家乡女性的熟谙,常常能触及到某些“真实”的方面,女性在这三个方面的性别体验或者说身体焦虑在他的笔端依然随处可见。
(一)性的焦虑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从社会生活到文学作品,女性的性欲都处于被压抑的状态。尽管孔子在《礼记》中讲过:“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定程度上肯定了男女之性对于人基本生活的重要性,但是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性”在主流社会中永远是不可明说的秘密,这就更不用说在地位上从属于所“依附”的男人、行为上统治于以男性为主宰的文化话语的女性之性欲了,它们只能以一种潜伏的状态而存在。虽然在“五四”文化革命后有过一段艰难地浮出历史地表的岁月,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受主流意识形态与阶级话语的制约,性欲被指认为反动阶级的情调,欲望的公开通常与“堕落”“放荡”“淫秽”联系在一起。为了传达新的道德与风尚、表现革命的纯洁性,要求作家在进行社会主义文学创作时,回避革命者的性与身体。但是这样的要求带有一种理想化的色彩,实际情况是“食、色,性也。”一味地回避,只会走向空洞与虚无。优秀的作家在创作时,潜意识中就会想要表现这种人性的冲动,这就很容易形成作者笔下的焦虑。一直以来《山乡巨变》以唯美的文本与单纯的女性形象为学界公认,但在唯美与单纯的背后也隐藏着作者对女性性焦虑的体认。
《山乡巨变》中的女性普遍存在性的焦虑,她们年轻的身体语言总是如此美好而又不安,暗示着对爱情(在隐性的层面常常是性)的憧憬与渴望。盛淑君是这类女性中的典型。作者对盛淑君身体的展示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越来越丰富,她的身体焦虑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充分的表达。盛淑君的身体散发出一种原生美与劳动美,她的体态首先是符合新时期对女子身体健美的新期待。她的第一次出场便显示出作者对她的身体的“偏爱”:在水井边打水的她与乡间的草垛、炊烟、池塘、茶子花融为一体,伴着鸟啼,出现在入乡干部邓秀梅的眼中。接着,作者通过“辫子弯弯”“丰满的鼓起的胸脯”“脸颊涨的通红”“脸颊丰满”“黑黑的大眼睛”等词汇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健康的充满朝气的能承担起未来社会主义建设重任的新女性形象,然而从这些与身体相关的词语里,我们又不难发现一个发育成熟女子膨胀的身体欲望。下面的这段描写也许更为“露骨”,在邓秀梅与盛淑君深夜长谈之后,作者有这样一段关于女性的身体描写:“两个年轻的女子,体质都好,身上又盖了两铺被子,睡了一阵,都热醒了,盛淑君把她两条壮实的手臂搁在被窝外,一直到天光……”对此,有人作了这样的解释:“看似不经意的生活化描写,却在一句‘燥热的身体’中投射出青春的激情和欲望。”[2]很显然,这里的“青春的激情和欲望”不能不与性的萌动与焦虑相关联。和同时期的其他合作化小说不同,《山乡巨变》有较多的关于女性的外貌描写,外貌是身体的一部分。小说写盛淑君,多次提到她两条弯弯辫子。弯弯的辫子其实是姣好而充满活力的身材体态的曲折表达,没有好的身材和健康的身体,何来弯弯的长辫?我们看看下面两处对盛淑君辫子的描写:一次写她熟睡时,“两条黑浸浸的长长的粗辫子,分离在两处,一条鬈曲地躺在枕头上,一条随便地拖在被窝上。”另一次是在她和心仪的陈大春见面时,因羞于面见陈大春而逃跑,这时“两条大辫子在背后不停地摆动。”而面对陈大春的质问与责骂时,“盛淑君不停地卷着辫子尖,卷起又放开,放开又卷起,没有作声”。辫子在盛淑君熟睡时呈现出来的自由放松状态与在男性面前的躁动和被紧张的摆弄,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身体的欲望与内心的焦虑。
其实,在合作化小说中,写未婚的正面新女性似乎都会写到她们的辫子,比如《创业史》中的改霞就有长长的辫子。不同在于,不同的作者在辫子面前会有不同的态度和立场。以《创业史》为例,改霞的长辫至少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借梁三老汉的视角出现的,改霞和梁三老汉的女儿秀兰同学,改霞的母亲是寡妇,她自己又是解除了包办婚约的,保守的梁三老汉自然是看不惯,所以当改霞经过梁家向梁三老汉打听秀兰上学没有时,梁三老汉“厌恶地眯缝着老眼,盯着那提着书兜、吊着两条长辫的背影”,虽然同样是两条辫子,(注意,这里是“长辫”[3]而不是《山乡巨变》的因身体曲线而致的“弯弯”的辫子)在这里,身体的意义并不明显。第二次出现倒是和《山乡巨变》有些类似,是两个女性在一起的场景中出现的,改霞和秀兰,两个年轻女子一起嬉闹:“两个女学生在河边草滩上跑起圈子来了。改霞笑得跑不动了,只好蹲下来。立刻,她觉得两条辫根子被小伙子一般有力的手扭住了。”事情的起因是改霞笑话秀兰偷偷想念男朋友,应该来说,如果要写改霞的欲望冲动,在这里是顺理成章的,“长辫子”可以发挥其身体的作用,但这里,两条辫子只是通过改霞自己的感觉呈现的,而不是被看到的,尤其是两条“辫根子”的表述,并没有写出辫子的形态,与身体关联的长度或者形状是缺席的。因此,这里的辫子并不具备身体的意义。第三次是通过不正经的孙水嘴来呈现的,孙水嘴一直想打改霞的主意,和改霞套近乎,改霞匆匆离开,这时孙水嘴还不死心,看着改霞的背影放低了声音赞叹了一句:“嗬,好大辫子!”这里的“大辫子”终于是与身体相关了,但因为是孙水嘴的不正经言说,这种意义便连同孙水嘴一起成为被否定的对象。和《创业史》的“辫子”比较起来,《山乡巨变》“弯弯辫子”的身体意义便非常明显了。
除了盛淑君,性的焦虑在别的女性身上也有体现。事实上,前述文本其实也或多或少体现了邓秀梅的身体焦虑,“体质好”“热醒了”,是写盛淑君的,也是写邓秀梅,邓秀梅为了工作,和年青的丈夫长期两地分居,性的焦虑也确在情理之中。小说的另一个女性张桂贞,不满于刘雨生只顾外面的工作全然不问家中冷暖而心生怨气提出离婚,“我一天到黑,总是孤孤单单地,守在屋里,米桶是空的,水缸是空的,心也是空的。”对于张桂贞来说,空的米桶与水缸是一个隐喻,“心也是空的”也只是可以明说的方面,我们从刘雨生的工作与张桂贞的诉说中看到,在这段婚姻中,两人心意不通,刘雨生无法满足张桂贞的需求,就更不用说夫妻生活的方面了,这就造成了张桂贞性的焦虑。当张桂贞想要发泄这种焦虑找刘雨生吵架的时候,刘雨生根本没有给她吵架的机会,这就导致焦虑在心中一步步扩大,最终走向离婚。与此同时,我们从菊咬筋夫妻俩的相里手骂中,从盛佳秀面对刘雨生时的欲靠近又羞涩的肢体语言中,从邻居家堂客看到青年男女亲昵的光景,招呼自己男人来看“好得点启发,对自己也来那么一下子”的召唤中,都发现作者在写作时不经意流露出的对女性性焦虑的体认。
斯蒂芬·茨威格在他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中曾写道:“凡是受到压抑的东西,总要到处为自己寻找迂回曲折的出路。所以,说到底,迂腐地不给予任何关于性的启蒙和不准许与异性无拘无束相处的那一代人,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享有高度恋爱自由的青年一代好色得多。因为只有不给予的东西才会使人产生强烈的欲望;只有遭到禁止的东西才会使人如痴若狂地想得到它;耳闻目睹得愈是少,在梦幻中想得愈是多;一个人的肉体接触空气、光线、太阳愈是少,性欲积郁得愈是多。”[4]这说明,越是禁欲的时代,欲望的积压以及由此导致的表达和发泄的冲动就越是凶猛。[2]144在十七年合作化叙事中,女性自我生命体验的私密性与合作化要求的女性身体的社会性呈现出一种分裂的状态,这就导致女性存在普遍的性焦虑。
(二)生育的焦虑
“生育”是属于女性的特殊生命体验,它包括分娩与养育孩子两方面。波伏娃认为,虽然男女两性都承载着繁衍物种的责任,但男性在完成生育职责时,其个体性是得到保持的。而女性在生育过程中却经历着个体性与异己性的斗争。[5]这种“斗争”就很容易使女性产生身体焦虑。
《山乡巨变》中女性的生育焦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分娩的痛苦及其后遗症,二是养育孩子的艰难。李月辉与其妻子伉俪情深,但是不能掩盖李嫂一直饱受生育焦虑的困扰这一事实。虽说李嫂在作品中出场的次数不多,但几乎她的每次出场都笼罩在她曾经遭受的生育的痛苦之中,她的身体饱受生育的摧残。从李月辉口中我们得知,李嫂十四岁过门,接连生了四胎。中国古代中医就提倡“欲不可早”:“女虽十四而天葵至,必二十而嫁。”[6]十四岁时,身体尚未发育成熟,便要开始孕育胎儿,对母体伤害极大,“今未笄之女,天葵始至,已近男色,阴气早泄,未完而伤,未实而动,是以交而不孕,孕而不育,育而子脆不寿。”[6]46因此李嫂生了四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两个,丧子之痛使其坐月子时忧伤过度,坏了身体,内心的焦虑外在为身体的焦虑一触即发,得了“扯猪栏疯”的症候,外加李嫂性格上喜欢与人怄气、发火,之后又染上了肺炎,这是身体焦虑进一步加重的表现,李月辉甚至还担忧她不是一个长命人。
“十七年”合作化叙事中,妇女在政治、经济、法律意义上确实实现了解放,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与义务,但是另一方面,“女性在家庭中所出演的却仍是极为经典、传统的角色:扶老携幼、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甚或是含辛茹苦、忍辱负重。”[7]是以女性看似获得了解放,实则面临更大的压力。《山乡巨变》中的妇女在参与公共事务时,很难摆脱孩子的束缚:清溪乡第一任妇女主任便是一个典型,军属的身份加上一本正经的性格使她在一众女性中脱颖而出成为妇女主任,但是她在工作上总是受那还未断奶的孩子的拖累,参加会议总是迟到不说,还要分心照看孩子“她把她带来的吃奶的孩子放在桌子上,由他满桌爬。……一眼看钟,他就要拿。妇女主任大声喝止,吓得他哭起来了。主任只得把他抱起来,敞开胸口,把奶子塞在小小的、嚎哭的咀里。”另一个妇女会上,谢庆元堂客给孩子喂奶时,被孩子咬得哎呦直叫,“孩子被一推一打,大哭起来。这位妈妈只得又把另一个奶头塞进他的哭着的小咀里……”被孩子咬了一口的疼痛激发了在场妇女们带孩子时感受到的多种不适,深感受孩子拖累之不便。这样的遭遇只是清溪乡哺乳期妇女参与公共事务时的一个缩影,合作化运动的紧迫性要求妇女们积极参与各项事务,但是养育孩子的现实需求又使妇女们束手束脚,她们参与合作化运动的同时也要照看孩子,孩子饿了、哭了,她们要喂奶给予安慰,孩子该睡觉了,她们得抱着孩子哼起催眠曲……反观男性,参与公共事务中的男性多是独身出现,没有出现照看孩子的情况,养育孩子的责任似乎全部落到了女性肩上,男女平权也没能把女性从传统的女性角色中拉出来。当参加合作化运动的时代要求与传统观念的伦理要求相冲突,妇女们的生育焦虑就显现出来了。
(三)劳作的焦虑
建国后,广大女性从家庭走向社会,从家庭妇女变成参与社会主义事业建设的新女性。在我国广大的乡土世界里,妇女多是通过参加劳动获得与男性同等的政治、经济地位。据相关统计,妇女参加劳动的比例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化开展呈上升趋势:1950年,农村妇女参加劳动的只占妇女劳动力的20%-40%,到1957年,农村适龄妇女中有70%参加了劳动,到1958-1959年有90%的妇女参加了劳动。[8]但是妇女全面参加社会劳动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这在《山乡巨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劳动身体,不仅仍具有政治身体钢铁般的意志,还有着新的典型特征,那就是参与社会生产建设中所体现的具有劳动生产能力和具有新社会思想、以及阳刚味十足的性格。”[9]“铁姑娘”成为新的时代风尚。然而,在周立波笔下,我们却不难看到女性身体在高强度劳动中的艰难与不适。“老单”王菊生为了超过互助组,带着妻女没日没夜地将塘泥运到田里,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使得王嫂身体吃不消又只能顺从丈夫的指派,最终“菊咬堂客上好一挑黑泥巴,才搁到肩上,忽然觉得远处的汽灯好像在飘动,接着眼前一阵黑,扁担一滑,她栽倒了,连人带担子滚进烂泥里。”这个消息传到爱护堂客的李月辉的耳朵里,他推己及人,想到了所有的妇女“她们是有特殊情况的,要生儿育女,每个月还有几天照例的阻碍,叫她们和男子一样地霸蛮是不行的。”在向朱明书记反映情况,遭到批评后,他坚持自己的主张“这事不小啊,这是关系妇女健康的大事”。“李月辉不断地诉说女性身体健康的大事,是立足于身体的底层,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层面。”[10]作者借李月辉之口,抒发对合作化运动中妇女身体焦虑的认同,“女性的身体必然不适应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而产生强烈生理反应。”[10]28“十七年”作品中塑造的“铁姑娘”形象,在性格、外貌、能力的追求上皆向男性靠拢,社会生产力的需要促成这一审美风向标的形成,有一定合理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铁姑娘,被抹灭了女子的个性、和女人身体所承载的意义符号所指。”[9]16
上了年纪的婆婆子虽说不用参与高强度合作化劳动,但是积年的体力劳动已经损耗了她们的身体,她们目前的身体状况预示着那些年轻妇女的明天。通过邓秀梅的眼睛,我们看到陈先晋妻子的脸晒得黑黑的,但有点不一定健康的虚胖,即面部浮肿,从医学层面判断,应是长年累月的操持导致肝肾功能受损而出现的症状。“疾病是通过身体说出的话,是一种用来戏剧性地表达内心情状的语言,是一种自我表达。”[11]陈妈的身体焦虑便显现在那微黑浮肿的脸上。在催促儿子赶紧找对象时她也提到了自己的身体状况“我呢,也是一年比一年差池。”“我不懂得什么叫悲观喜观,我只晓得,体子一天不如一天了。”同一次对话,陈妈两次提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到一年不如一年,是对自身身体焦虑的强调,儿子正处于谈婚论嫁的年纪却满心思在别处,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催促着陈妈拉回儿子在别处的心思。
二、焦虑的释放
弗洛伊德认为,“作为一种感觉,焦虑的一个尤为明显的特征是不愉快”[12]而焦虑的释放就是使这种“不愉快”的状态得以缓解,正如作者对女性身体焦虑的体认是以一种隐蔽的方式适当地呈现出来,在“十七年”话语体系下,这种焦虑的释放同样需要找到合理的途径。合理与否,往往决定了焦虑释放所表现出或积极或消极的两种不同的后果。《山乡巨变》中女性身体焦虑的释放也呈现出积极或消极两个走向。当然并不是所有女性的身体焦虑都得到了释放。
(一)政治转移
当“十七年”文学中的个人情感、性别、性行为被诸如阶级、民族、国家等话语所压抑,女性身体的焦虑只能以一种隐蔽的方式表达,而一旦找到某个与主流话语相契合的突破口,身体焦虑则有可能得以尽情的宣泄。盛淑君的身体焦虑一开始是无意识的,潜在的,后来因团支书陈大春的出现而被进一步激活。绕有意味的是,陈大春同时又激活了盛淑君的政治激情。她将对陈大春的期待转移到参与清溪乡的政治事务中,这是走近陈大春并且得到他认可的最好的途径,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盛淑君的身体焦虑得以合理释放。在“山里”这一节中,发生了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盛淑君的入团申请得到了组织的批准,由团支书兼暗恋对象告诉她这个消息意义非凡,表面上是盛淑君近段时间的表现得到了组织的认可,实际上是盛淑君得到了曾经一直否定自己的陈大春的认可,得到了进入陈大春世界的许可证;第二件事情则是两人在内心的期待与巧合的碰撞中终于炙热的拥抱与亲吻,“情感的交流,加上身体的徒然的接触,使得他们的关系起了一个重大的质的突变,男性的庄严和少女的矜持,通通让位给一种不由自主的火热的放纵,一种对于对方的无条件的倾倒了。”“风吹得她额头上的散发轻微地飘动。月映得她脸颊苍白。她闭了眼睛,尽情地享受这种又惊又喜的、梦里似的、颤栗的幸福和狂欢”。在这身体的亲密接触中,盛淑君身体的性焦虑得到了一次狂欢式的释放。即使后来陈大春被派到厂里,两人不好相见,盛淑君也能很好地安置自己内心的情愫,当然,这也得益于陈大春临走前的一番“嘱咐”:“是团员,就应该遵守纪律,服从调配,叫你留在哪里工作,死也要留在这里,你还是这个自由主义的派头,当初何必入团呢?”自此之后,她再不会因为羞于见陈大春便躲,更不会在他人拿陈大春调侃她时羞红了脸。人前发言的盛淑君,干脆利落地将编好的辫子甩到背后,双辫不再承载其它语言。继任妇女主任的盛淑君,处理政治事务更加繁忙,田间劳动也更加卖力,凡事都要抢在前头,不愿落后于男子。伴侣不在身边,她只能继续将对对方的感情转移到各项政治事务中,在奔波与繁忙中发泄出来。
在《山乡巨变》中,妇女们生育的焦虑与劳作的焦虑等焦虑的释放同样是在主流话语的框架中实现的。妇女在公共劳动中打破既有的传统角色分工,但是妇女并没有完全从家庭中解放出来,嗷嗷待哺的孩子成为她们参与公共劳动最主要的拖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妇女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的困难,作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新生事物的公共食堂、托儿所和缝纫组应运而生,使妇女从私人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13]《山乡巨变》中关于托儿所的叙事正是试图借这样一种主流政治话语来缓解女性生育的身体焦虑。妇女外出劳动时将孩子放在托儿站托管,“摆脱了孩子拖累的堂客们一个个掮着耙头来到一丘圆畈眼子的田边。”托儿站的成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妇女们的生育焦虑。而至于劳作的身体焦虑,也是在上级政策的调整中得以解决:“来了例假可以请假,生产队还特意增设了一个女队长,为的是我们妇女有一些话,不方便跟男人家去讲。”“那天会上决定了,上级又有指示:你们干轻活。”领导的调整是上级指示的结果:1961年中央出台了《中央转发全国妇联党组关于农村妇女劳动保护政策和农村托儿所组织问题的两个报告附件1》,针对妇女劳动力面临的实际情况,提出:“男女劳动力可以做到合理安排,妇女可以不做引起闭经,子宫下垂、流产等用力过猛过大的重劳动。”“要做好经期保护,主要是要做到经期不下冷水、深水、不做重活。”[14]这样一种对上级主流话语的精心“利用”,正凸现出周立波女性叙事的在合作化小说中的独特性。
(二)婚姻重组
无论是张桂贞不能忍受刘雨生忽视自己的需求而选择离婚转而嫁给符贱庚,还是盛佳秀被丈夫抛弃一直隐忍却又按捺不住对刘雨生的倾心,这里面都内在着性的焦虑。“性,就像共生作用一样,是宇宙现象的一个表征,即混合配对的原则。只要两个发展、适应良好的生物(或系统、物体),彼此相互结合后,再次反映、发展,并重新界定彼此、重新适应环境,便有新的东西出现。”[15]两位女性的婚姻重组便暗含这一原则。拜伦曾经说过,爱情是男人生命的一部分,却是女人的全部。换言之,男人的婚姻只是其命运的一部份,而女人的婚姻也许就是女人命运的全部。
符贱庚虽说口碑不好,但是他对于桂贞来说却是一名合格的丈夫,结婚后的符贱庚追求上进并且将生活的重心放在家庭的经营上,满足妻子的各种生活需求,两性关系的完满重组使张桂贞性的焦虑得到释放,进而在行动、思想上都发生着变化:符贱庚进厂后,她开始自己挑水、砍柴、煮饭和种菜,积极参加田间劳动,虽然田间的太阳晒黑了她的面庞,但是在周立波眼里这样的张桂贞更加生动妩媚,他借谢庆元之眼将张桂贞的身段、脸庞、头发、眉毛、眼睛、酒窝、衣着等仔仔细细打量了一遍,而这样的张桂贞在与刘雨生的婚姻续存期间是没有出现过的。龚子元事件败露之后,她对亲哥张桂秋的一番说教让我们发现张桂贞内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靠近:“如今又不像是旧社会。原谅我做老妹的劈句直话,你和龚子元实在也太那个了,信了他的话,社也不入。受点虚惊也是应该的。”由此我们几乎可以推断,当初张桂贞与刘雨生的不合,并不完全是思想上的分歧,更多地是身体上的焦虑,而一旦身体上的焦虑得以缓解,思想上的进步其实并不是多大的问题,只是有些遗憾的是,这种身体焦虑的缓解并不是在张桂贞和刘雨生之间完成的。如果说,张桂贞是在和一个之前口碑并不很好的男人的身体释放之后得以进步的话,盛佳秀则是在与一个政治上优秀的男人的身体释放后获得进步的,她们二人给人一种殊途同归的感觉。盛佳秀与刘雨生的重组也使她压抑许久的身体焦虑得到释放,在进步的刘雨生面前,她获得尽情释放自己身体的“资本”,她不用将自己伪装起来,她的女性身体以及与此相关联的小女人的情态在刘雨生面前展示得淋淋尽致。因为刘雨生,她变得年轻多了,更加注重容貌打扮,而这种身体焦虑的释放,最终也促成了她思想行为上的上进:她参加会议也比以前更积极了。身体上的释放与思想上的进步由此达致和谐。(其实,作为问题男性的符贱庚也存在着性的焦虑,也在焦虑释放后,完成了“华丽”转身,这是另外一个值得研究的话题。)
(三)言语暴力
当身体的焦虑无法通过政治转移和婚姻重组来释放的话,又会出现怎样的情况呢?
相里手骂是《山乡巨变》极有特色的一个章节。王菊生与其妻子假装为入不入社的问题吵架,目的是为了阻止工作组的干部到他家里来做工作。问题是,本是夫妻合作的一出写好台本的戏,却在演出中,渐入佳境,几乎失控,作为女人的王嫂对丈夫的谩骂越来越不堪入耳:“我肏你王家里祖宗三代。打了我,你会烂手烂脚,捞不到好死的,你会爸死,崽死,封门死绝,你这个遭红炮子穿的,剁鲁刀子的。”很显然,王嫂已经是假戏真做了。
为什么会这样?作为男人的王菊生为人吝啬,却是作田的一把好手,从早到晚手脚不停,不仅自己一心扑在田上,连带着妻女也要跟着一块儿劳动,毫无体恤。他与刘雨生在某些方面有些相似之处,他们的心思永远在外面而不在妻子身上。男强女弱的夫妻关系使王嫂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事实上,王嫂连自己的名姓都没有,相里手骂给了她一个“合法”释放身体的一个出口:一个“肏”字打头阵更让人值得玩味,“肏”本是方言词汇,意指两性行为,它的字形表示出这是男性的动作,辅以干脆、急促、暴烈的发音十分合适。[16]这样一种粗鄙的性词汇出现在女性尤其是南方女性的口中,是耐人寻味的。作为女人的内在的不满与焦虑,借其男人给予的相里手骂的“合法”途径得以尽情宣泄。得到释放的菊嫂,再次出现在读者面前时,已经换了衣服、梳好了头发,坐在灶屋门口补袜子,面对丈夫的忿恨斥责,一改往日的小心拘谨,她面带笑容,还与王菊生开起玩笑“我是泼妇,你呢?你是孙悟空,会七十二变。”王嫂通过一番暴力言语释放了自己的身体焦虑。
言语暴力虽说是消极的焦虑释放途径之一,在《山乡巨变》中出现的次数不多,但同样堪称典型。
三、小结
《山乡巨变》一直被认定为纯洁的文本,然而,单纯的后面,其实隐藏着女性的身体焦虑。《山乡巨变》中女性的身体焦虑与革命、集体的关系存在一个既冲突又合作的复杂关系,当身体的焦虑通过合理的途径进行释放、转移,女性的身体与革命、集体便达到了和谐与互相包容的状态。“女性的身体体验在男权文化中历来是一个被遮蔽的存在,而女性也被迫对此话题保持沉默。”[17]而女性主义主张打破这一传统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压制,它们思考着发生在女性身体上的一切,她们以身体为主题,以身体为表达工具,成为想要摆脱男权文化压抑的内在声音。[18]《山乡巨变》当然不是典型一个女性主义的文本,作者对女性身体焦虑的表达也许是不自觉的,但在客观上却避免了当时革命叙事的简单化处理方式,增添了《山乡巨变》文本的丰富性,尤其是,一个男性作家,在那样一个政治话语时代,却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的关于女性形象的文本,不能不是一个颇有意思的话题。
[1] 南帆. 性别、女权主义与阶级话语[J]. 当代作家评论, 2017(8): 4-16.
[2] 李蓉. 限度和自由——论“十七年文学”情爱叙事的间接呈现[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12): 144-149.
[3] 柳青. 创业史[M]. 陕西: 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1. (以下《创业史》原文引用出处均同此)
[4]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M]. 舒昌善, 等, 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1: 84.
[5]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29-30.
[6] 褚氏遗书[M]. 卢祥之, 注.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2: 46.
[7] 戴锦华. 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 西安: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2: 14-15.
[8] 董丽敏. 性别、语境与书写的政治[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2: 4.
[9] 崔文苑.“十七年”小说中女性身体叙事的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1.
[10] 戴黄. 论周立波小说的“女性化”倾向[D]. 岳阳: 湖南理工学院, 2017.
[11] 苏珊·桑塔格. 疾病的隐喻[M]. 程巍,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3: 41.
[12] 弗洛伊德文集(第4卷)抑制、症状与焦虑[M]. 车博, 编.杨韶刚, 高申春, 译.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8: 240.
[13] 王尧, 汤虹,任茹文,等. 文学与历史的双重见证[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08: 162.
[14] 中国妇女管理干部学院. 中国妇女运动文献资料汇编: 第2册(1949-1983)[M]. 北京: 中国妇女出版社, 1988: 1.
[15] 林恩·马古利斯, 多里昂·萨根. 小宇宙细菌主演的地球生命史[M].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7: 153.
[16] 韩少功. 马桥词典[M]. 安徽: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6: 110.
[17] 陶东风. 文化研究:第21辑[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99.
[18] 王文新. 观念的艺术表达[M]// 艺术学教育丛书. 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6: 67-73.
Anxiety and Release of the Female Body: Another Interpretation of
YANG Houjun, ZHANG Shiyi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Yueyang, Hunan 414006, China)
The novel titled, as one of the revolutionary literary classics of the seventeen years since liberation of China was published, the female body anxiety is implied in literary narration that seems to avoid the body, there is a complex relationship between female body anxiety and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which is both conflicting and harmonious. Such a narrative attitude reflects the richness of the meaning of the text.
; female body anxiety; release anxiety
2018-07-22
湖南省教育厅创新平台开放基金项目(16K038)
杨厚均(1964-),男,湖南汨罗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张诗颖(1995-),女,湖南长沙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I 206
A
10.3969/j. issn. 2096-059X.2019.02.013
2096-059X(2019)02–0076–007
(责任编校:彭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