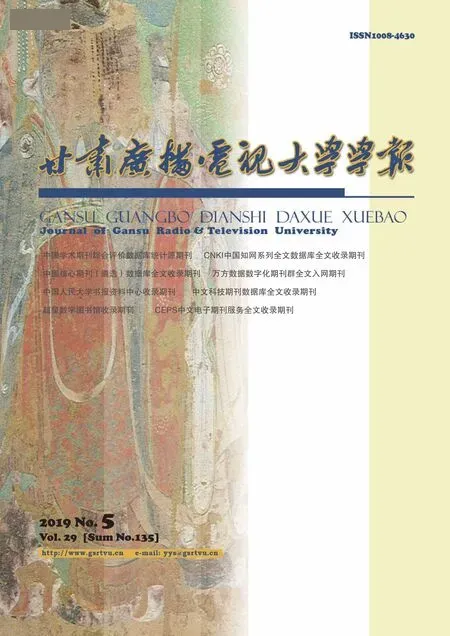论林纾古文文体论对《文心雕龙》的祖述
王 婷
(复旦大学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上海200433)
林纾乃清末民初颇有成就之学者,虽以译书享誉文坛,但其兢兢于古文数十年,“用力颇深,探索颇苦”[1],可谓能跻于古作者之林也。《春觉斋论文》便是他任教京师大学堂时的课堂讲稿。该书以《流别论》一章专论文体,凡十五类,分别为骚、赋、颂赞、铭箴、诔碑、哀吊、传记、论说、诏策、檄移、章表、书记、赠序、杂记、序跋。所言之文体,在弥伦群言的基础上对《文心雕龙》思想绍述的痕迹显而易见。当然,林纾并非一味承袭前人,亦不乏个人创见。“夫方有殊音,故文不同体。”[2]1220《春觉斋论文》虽无《文心雕龙》之体大虑周,但实可视为继彦和之后,一部系统的分体文学史。林琴南对文体做专门考究,是眼见古文江河日下应势而为,亦是为捍卫道统,保存国故。
一
齐梁时期,儒、道、佛、玄思想并立,然“道虚无,佛唯心,玄清谈,只有儒家学说带有一定的唯物色彩,能够与实际生活相联系”[3]。彦和以儒家之道匡正时弊,与讹滥文风相抗衡,他“从文学之浮靡推及当时士大夫风尚之颓废与时政之隳弛,实怀亡国之惧,故其论文必注重作者之品格高下与政治之得失”[4]。至清末民初,世道不古,文亦下衰,所苦英俊之士,“不省中国四千年绍继之绝学”,更有甚者,“以挦撦为能,以饾饤为富”[5]615,“割裂古字,填写古字,用以骇众,且持‘古文宜从小学入手’之论”,“此等鼠目寸光,亦足啸引徒类,谬称盟主”[6]146,所作雕刻文字,博而寡要,无涉川之用,其失之也愈远。文坛风气尚且如此,且西学东渐之下,青年抨击古文不适于用,以白话为文学正宗,对古文必欲尽废之。于此种情况下,林纾不愿屈己之道而从人之志,转而以己之力,教授古文创作之法,传承圣人之教化。“中国之文敝久矣,余惧其长此而澌尽也,欲自奋以广古人之传。”[5]650在“亡国之惧”的心理下,刘勰与林纾皆选择以论文的方式明道,著书立说,以广其传。
刘勰《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可谓见识独到,“先民矩获,毕具于斯”,彦和以《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为“文之枢纽”,论述文章核心。林纾要求古文创作服之以理,动之以情,“惟理足者,言之始精”[7]6330,“文章为性情之华”[7]6529。所言之理,很大程度上就是依经典而出;所论之情,更是发抒自然,不做矫饰。从这个角度而言,二人思想的契合,更容易引发林纾对《文心雕龙》的接受。林纾的文体论创作思想秉承刘勰,要求文章创作遵循经典之道与自然之道。《流别论》更是处处体现出“以道为原,以经为宗,以圣为征”[8]的强烈观念。
文章创作原出经典,多为学者之共识,《颜氏家训》有言:“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9]既然各类文体与经典息息相通,则当以圣贤之道,经典之理寓于文中,林纾认为“凡文字不由经籍溯源而出,未有不流于杂家者”[10]。“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得其当,则六经至于今日,其为道也一。”[6]147经典旨意深远,文章创作溯源经典,深究乎先哲之用心处,正反映了林纾归本归正的立场。此外,他将道一以贯之,超越时间的限制,“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11]18,将经典所蕴含之理运用到当下社会中,使文章发挥其应有之意,琴南之用心处,可见一斑。
林纾称《文心雕龙》为“古论文之要言”[7]6330,出发点正是该著对儒家之道与经典的尊崇,故而承袭刘勰宗经的思想,将之融会贯通。不仅把文体的源头溯源于经典,如赋体,“发源之处,实沿《三百篇》而来”[7]6338,秉承诗教观念,高扬社会功用,还要求文体创作立足经史而表达,诸如颂赞之词,言“自非发源于葩经,则选词不韵;赋色于子书,则取材不精”[7]6348;史传要“转受经旨,以授于后”[7]6348;诏诰文,“非镕经铸史,持以中正之心,出以诚恳之笔,万不足以动天下”[7]6354;“学记一种,非湛深于经学儒术者,不易至也”[7]6363;又序跋文“要在平日沉酣于经史,折衷以圣贤之言,则吐词无不名贵也”[7]6364。他将评论文章的标准确定在能否使创作与经典融合,且相得益彰,如评刘向《论星孛山崩疏》曰:“更生论事,纯引经籍,及汉朝故实。”[12]128《条灾异封事》则谓:“此文难在引用经籍时,加以制断之语,如出金石,此所谓经术也。”[12]133只有符合经义的文章才能流传久远,坚实之内容,经典之雅义,方为文之正轨。
然而,若只一味代圣贤立言,文章如同木偶,便会失了生气。林纾言:“为文不专言道学,斯为活著。”[7]6537为文要有同于经典之处,也当有异乎经典处。文章要说道说经,也应“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11]2,所以林纾一方面推尊儒家之道,在宗经的基础上追求复古,所谓“词不追古,则意必循今;率意以言,违经益远”[2]1221。另一方面,他又承续并发展了刘勰的“自然之道”,将道融入生活。由此,所论之道便不再高高在上,空悬其中,而与人息息相关,如影随形,“盖道味之甘平如稻榖,且人之需道以生者,如游空气。”[5]649在抒写性灵的思想碰撞下,“傍及万品,动植皆文”[11]1,大凡眼中所见之“山林皋壤”,生平所经之琐琐屑屑,皆为“文思之奥府”。由此,文章创作便囊括了人类、自然与社会,言自然之景,诉个人之志,张扬世态人情,可谓见识深远。他评《左传》曰:“左氏之文极巧妙处,皆有自然之趣。读其文者,当看其如何部署,如何说法,与其本色风神步骤。”[7]6542显然,文章的自然之道,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而非于文法上刻意钻营,张裕钊所言之“凡天地之间之物之生而成文者,皆未尝有见其营度而位置之者也,而莫不蔚然以炳,而秩然以从”是也[2]1217。
古文创作,与道相谐。徒有华采的文章没有价值,故而林纾以充实的义理,真挚的情感修弊补罅,扭转文坛之风。他要求文体创作走经典之道与自然之道,是承袭了彦和“文之枢纽”的思想,也恰是其论文主旨的体现。
二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揭橥自己“论文叙笔”的方法是“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11]632。综观《流别论》一章,林纾绍述《文心雕龙》创作体制的痕迹显而易见,且在前十二类文体的叙述中,开篇便引用《文心雕龙》对相关文体的定义,并在刘勰阐述的基础上加以扩展生发。林纾站在清代文学的终结点上,其优势在于能够综合历代文学作品,因而能够更全面地看待文体的发生、发展与衰落过程,而其所论述的作家与作品,更是各代兼而有之,范围极广。
同刘勰一致,林纾将各类文体上溯至经典,归之淳雅,使文有根祗。又因林纾所处的时代,对各类文体的评论,可算是真正做到了“原始以表末”,以发展的眼光,叙述文体在各时代的兴衰变化,旨在“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11]632。
林纾论文体的起源,多与《文心雕龙》一致。如其论赋体,谓“然其发源之处,实沿《三百篇》而来。至《楚辞》出,局势声响,始洪大而激楚”[7]6338。语同彦和“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11]119,以《诗经》为赋体的起源,受《楚辞》的影响而发展。论吊文,《文心雕龙·哀吊》有言:“宋水郑火,行人奉辞,国灾民亡,故同吊也。”[11]214林纾曰:“古人有哭斯吊,宋水郑火皆吊以行人。”国家受灾,民不聊生,各国使节同去吊慰,斯有此体[7]6347。至于《文心雕龙》中未作具体说明的,林纾则直接点明,《文心雕龙》言“三代政暇,文翰颇疏。春秋聘繁,书介弥盛”[11]406。但林纾在书说一体中,引用姚鼐观点点明源流,言“姚惜抱谓书之为体,始于周公之告君奭,‘于是列国士大夫,或面相告语,或为书相遗,其义一也’”[7]6358,《文心雕龙·诔碑》言“自鲁庄战乘丘,始及于士;逮尼父之卒,哀公作诔”[11]188。林纾则谓:“诔之最古者,凡两见于《左传》:一为鲁庄公之诔县贲父,一为鲁哀公之诔孔子。”[7]6344以“最古”二字,点明《左传》为诔体的源头。
在阐释文体发展时,林纾基于所处时代的优势,阐述本末。其论赋的发展演变,在选取司马相如、扬雄等汉大赋进行点评后,略论齐梁小赋的弊病,转而根据时代的演变顺序,言:“宋人以赋取士,破题竟有定格,如‘蛇不难斩,君宜灼知’之类,几成笑柄。先朝馆赋,格律较严,然多以诗句命题,以水济水,声响皆劣。”[7]6339俨然乃一赋体的发展演变史。
林纾依命名而彰显文体性质,其中多征引《文心雕龙》之言,如“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7]6338。他释名主要采用训诂的方法,是对刘勰思想精准把握的一种表现。有以换字为训者,如“吊者,至也”[7]6346。“章者,明也。表者,标也”[7]6356。有因声求义者,“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7]6344。有训释后加以引申,以短语来解释单音节词者,如“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纪号封禅,树石埤岳,故曰碑也”[7]6344。“‘檄’之为言‘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7]6354这些方法,使得字义由抽象变具体,更有形象性。林纾以其深厚的古文根祗,训释名物,既有古文经学重训诂的一面,又有今文经学重视大义的一面,体现出二者的融合。
此外,林纾解释文体的含义,还着眼于当下,着眼于具体实践,以达到经世致用的目的。以史传为例:“‘传’之为言‘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7]6348史传以先哲为彝宪,“禀承圣人与经书的思想,探原道之本体,而指示人世之行事,劝戒与夺,以期符合道之本体与圣人之旨”[13]。林纾主张史传发扬经义幽深之旨,以资后世,正反映了他在儒道衰微、纲纪覆灭之时,希望以传统救传统的强烈愿望。
在《流别论》中,林纾以较大篇幅“选文以定篇”,往往与“敷理以举统”相结合,并呈现出以下特点。
第一,沿着刘勰的选文,展开论述。“刘勰盛推潘岳‘巧于叙悲’。愚按《黄门集》所登哀诔之作,颇赡于他集。”[7]6344潘岳诔文,所以见称后代也,缘事抒情,表心中之哀思,情文相谐,可谓独步当时。《文心雕龙·诏策》有言:“明帝崇学,雅诏间出。”[11]318-319林纾则谓:“东汉明帝所降诏书,不及文帝精肯,然祖义褒德,雅善说辞,亦佳笔也。”[7]6352刘勰从朝廷崇尚儒学的角度总结明帝时诏令“雅”的特点,言简意赅。林纾将文帝与明帝诏书做比对,肯定了明帝诏令文中的丽辞雅意。情之所至时,林纾亦会在引用刘勰言论后加上“确矣”等词,表示认同。如“刘勰称‘蔡邕铭思,独冠千古’,以《黄钺》之名为‘吐纳《典》、《谟》’《朱公叔之鼎斤》为碑文之体,确矣”[7]6342。蔡邕效法《尚书》,得其古雅,又能吐故纳新,便成文思之典范。
第二,选择魏晋以后的文章品评,以作补充。齐梁以后,佳作频仍,惜刘勰未能窥全貌,琴南应势而为,弥补缺憾。如其论哀辞,在细品韩愈之《哀独孤申叔文》《欧阳生哀词》后,分析了曾巩《元丰类稿》中的《王君俞哀词》、方苞《亡妻蔡氏哀词》等文,指陈其中优劣处。如论诏令,赞唐太宗《节省山陵节度诏》《答房玄龄解仆射诏》《答皇太子承乾诏》《责齐王祐诏》“似出御笔,其中或纬以深情,或震以武怒,咸真率无伪,斯皆诏敕中之极笔也”[7]6353。太宗诏令,情志疏放,风韵天成,深浅合度。又如论碑文,沿刘勰所品,继而对韩愈《平淮西碑》《南海庙碑》,苏轼《表忠观碑》及元代姚牧菴进行品评,并指出创作之大旨。林纾借前人评论论姚牧菴碑文,“张养浩称其‘才驱气驾,纵横开合,纪律惟意’,柳贯又称其‘雅奥深醇’。实则,以纵横之才气入碑版文字,终患少温纯古穆之气。”[7]6346张养浩与柳贯皆颂之,琴南却从风格入手,认为碑文但存古风而已。
第三,臧否文人才士,寄寓褒贬。“陈思王之诔文帝,数语外即陈己事,斯失体矣。”[7]6345诔文重在逝者,曹植借诔体而附己意,不免乖体。“若苏家则好论古人,荆公间亦为之,特不如苏氏之多。苏氏逞聪明,执偏见,遂开后人攻击古人之核窦。张娄东尚平允,至船山《通鉴》《宋论》一出,古人体无完肤矣。”[7]6351论说一体,贵在说理,苏轼多论说之作,然失其中正平和之气,船山亦患此弊,乖离事实,与古人相去甚远,若为此旨,不如不作,故论需谨慎为之。“子固、震川皆不长于韵语,去昌黎远甚。他若方望溪之哀蔡夫人,则文过肃穆,辞尤无味,名为哀词,实不能哀。”[7]6347曾巩、归有光逊于声韵情致之语,哀文少绵亘抑扬之姿,方苞缘题生意,作哀辞润色者少,未见其长情,徒有其名。
第四,品评趋于精细化,以指导写作为旨归。刘勰在《辨骚》中,只言“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11]40。林纾则具体分析何为“朗丽以哀志”,他列举《惜颂》与《涉江》中佳句品评。“其曰‘莫之白’,曰‘莫察’,曰‘无路’,曰‘吾莫闻’,积沓而下,不外一意,胡以读之不觉其否?由积愫莫伸,悲愤中沸,口不择言而发,惟其无可申诉故沓,惟沓乃愈见其衷情之真。若无病而呻,为此絮絮者,便不是矣”。[7]6337林纾不仅引用原文佳笔处,还字句分析屈子之情志。刘勰论颂赞,将“子云之表充国”,与班固、史岑文章归纳为“虽深浅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11]140。林纾则对前者做了深刻的分析,言“观子云《赵充国颂》,无一语不经心,亦无一语伤于纤弱,则极意摹古,由其读古书多,故发声亦洪而肃,此不能以浅率求也”[7]6340-6341。又《文心雕龙·铭箴》言:“班固燕然之勒,张昶华阴之碣,序亦盛矣。”林纾曰:“班兰台《封燕然山铭》,文至肃穆,序不以华藻为敷陈,骨节铿然,铭用《楚辞》体,实则非也。”[7]6343一方面沿着刘勰的论述,称赞序文之美盛,另一方面则从句式的角度指出铭文以楚辞体表述,是为不佳,楚辞声悲,而铭词声沈,二者合用,俨然不相协。
第五,根据所选之文确定各代的普遍风格。其论诏令,言“汉诏最为渊雅”[7]6352,“至于六朝,则纯以藻缋胜矣”,“有唐诏墨,高逾山丘,独太宗为美”“宋人制诰,初无散行文字,而四六之中,往往流出趣语”[7]6353,金人之诏“陈腐如书启”,降及明代,“明太祖起自兵间,子孙相沿,乃不究心文采”,竟有“这厮”等词,“真是伧荒说话,非诏书矣”[7]6354。寥寥数语间,各附一时代之经典作品,以阐明文体发展的轨迹,不失为一简明的诏令文风格发展小史。文随世相移,于独特之社会风气中,各有殊采,具体言之,汉以儒学为尊,上溯三代,深远典雅;六朝绮靡,尚骈俪风,徒以华彩饰之;有唐包容,壁立千仞,气象万千;宋人喜尚理趣,行文缜密;金人观点陈旧,不足言文,至明代,则直以俚俗口语出之,庄重之气全无。又“至于碑志之文,窃以为汉文肃,唐文赡,元文曼”[7]6345。碑志之文,于相异之时代自成风韵。
当然,琴南选文,亦有个人之见,“彦和称当时英杰,但有十家,太冲诸人不与焉。鄙意谓足与《两都》抗席者,良为平子之《两京》”[7]6338-6339。且左思亦可归为“辞赋之英杰”,细究其中缘由,左氏承袭班固、张衡之赋旨,“《三都》之赋,力排吴、蜀,中间贯串全魏故实,语至堂皇”[7]6339。除此,刘勰称蔡邕《杨赐碑》“骨鲠训典”是站在褒奖的角度,林纾则言:“踵效《虞书》太似,至亦袭其句法,不足用为法程。”[7]6345又刘勰盛推左雄的表议与胡广的章奏为“当时之杰笔”,林纾则运用《后汉书·左雄传》《后汉书·胡广传》中史料,论证二人之文虽在当时确实称得上独步文坛,但却太中规中矩,不必成为后人为文的法则。可见琴南论文,要学习经典之表达思想与潜言造语,推陈出新,而非一味仿其句子,踵效前人,反而失了自我。
“文章既立各体之名,即各有其界说,各有其范围。”[14]289在选文定篇的同时,林纾还阐明文体的写作方法及标准风格,即“敷理以举统”。对《文心雕龙》中的创作要求,林纾往往直接以作品为证,表明对彦和之认同。诔之为体,“论其人也,暧乎若可觌;道其可哀也,凄焉如可伤”[11]189。林纾绍承《文心雕龙》的创作要求,以潘岳的文章为例,“黄门以深情为人述哀,自能动听”,其诔武帝,“恋恩之情,溢言表矣”,其诔马汧督,“尤悲愤有余音,且琢句奇丽。”[7]6344-6345诔文对人物的描写要使人能看到逝者的音容风貌,以强烈的感染力与读者产生情感的共鸣。刘勰将哀词的对象确定为“不在黄发,必施夭昏”,即为年老与夭折之人,“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11]213。所以林纾批判归有光为御史中丞作哀辞,“年非夭礼”,是为乖体。
观其主张,肯定与否定的态度十分明显,如赋体,“虽极于雕画,苟不定以旨趣,均不足以传播于艺林,驰骋于文圃”[7]6338。林纾认为赋体当“出于颂扬”“本于讽喻”,而后者是首要的,如果文章没有寄寓之旨,即使文采彬蔚,也算不上佳作。又如箴言,他要求“陈义必高,选言必精,赋色必古,结响必骞,不必力摹古人,亦能自肖”[7]6344。依经立义,择取精到之言语,又不可步步紧趋古人字句。盖琴南笃于道而好于古,颂赞要“文既古雅,体不板滞”[7]6340,碑志则“造语必纯古,结响必坚骞,赋色必古朴”[7]6346,所谓“贵乎慎德”是也。校练名理以成文,发抒情性以成文,舍经籍不可,堆积圣贤之理,无个人风采亦不可。
此外,要掌握各类文体的创作方法,写出优秀的文章,还应处理好文体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古人之学说,各有独到之处,故其发为文学,或缘题生意,以题为主,以己为客;或言在文先,以己为主,以题为客”[14]284。林纾意识到文章要抒己意,其论诔体,要“入己之事实,当缘情而抒哀”,哀词则“既以情胜,尤以韵胜”。文章之美,在乎性情,真情流露,自生妙笔。当然,文体有主客之殊,非全为主观之作,赞体“必务括本人之生平而已”[7]6341,论说“括众意而归淳”[7]6351,即吴讷所言“解释义理而以己意述之也”[7]1623。无论是介绍他人的生平,还是阐发经书,说明道理,都要客观。而在一定情况下,还要将二者巧妙结合,“唯诏诰一门,非镕经铸史,持以中正之心,出以诚恳之笔,万不足以动天下”[7]6354。诏令文不仅要依据客观之事实,还应有作家本人真挚之血泪。
三
文体论发轫于魏晋,曹丕《典论·论文》“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2]176一语可视作文体分类之滥觞。文体分类之初,便对各类文体的风格有所界定。所谓的“体”,不仅指体裁,还包括各种体裁所具有的风格。文体不同,风格迥异,彦和所谓“各有其美,风格存焉”。
林纾论文体风格,立足刘勰主张,展开生发,并提出相应的创作方法。其中直接引用原文的如颂体,“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赞者,“约举以尽情,昭灼以送文”[7]6340。“颂者,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慎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7]6340。刘勰将颂体与赋、铭相联系,指出其内在关系。颂体纯正美善,既可如赋体般铺陈文辞,但不以繁辞胜,又应如铭体谦恭庄重,却又不能掺杂规劝警戒之语,当有“典懿”“清铄”之格调,琴南承彦和所论,以不轻佻、不纤弱的古雅之风为颂的风格特色。
林纾论檄文,对刘勰“必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的判断深表赞同,言“二语尽之矣”。若要“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11]335,则必须要以旺盛之气势与果决之言辞将事实讲述得清楚明白,所以林纾继而言“刘勰之论檄曰:‘植义扬辞,务在刚健。’愚谓本无义愤,何由能刚?不衷公道,奚得称健?”[7]6356林纾在要求檄文有激昂之情感的同时,更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表明自己态度的处世,并非要说得天花乱坠,诡谲欺诈,而要本之以道,参之以信。一理一情,正契合其论文主旨。
又如铭体,林纾先引用刘勰之言,“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后说明道:“弘润非圆滑之谓也。辞高而识远,故弘;文简而句泽,故润。”[7]6342其所言之“辞高而识远”“文简而句泽”正与刘勰“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11]173同意,只是换了种说法而已。铭体之风,乃陆机所言之“博约而温润”,显示作者美好的品德,即有褒赞之意,则要以雅正为本,彰显儒家“温柔敦厚”之旨。
作为“经国之枢机”的章表,林纾先采用刘勰语为之定调,即“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11]364的基本风格,章宜明朗,表应显耀,转而将章表与今人之奏议相联系,指出今人的奏议特点是“密”,即“粉饰补救,俾无罅隙之谓,偶举一事,上虑枢臣之斥驳,下防部议之作梗,故必再四详慎,宜质言者则出以吞吐,故作商量,宜实行者则道其艰难,曲求体谅,语语加以骑墙,篇篇符乎部式,此安得有佳章表”[7]6357。詹锳指出:“这是从反面的例证来说明‘雅义以扇其风,清文以驰其丽’的。”[15]诚然,雅正之意,清丽之辞,使人自见其中是非曲直,此乃是章表应有之风,林纾以批判的言辞说明今人奏议之弊,衡量的标准正是彦和之语。
综上所述,林纾对文体风格的论述,往往直接引用《文心雕龙》原文展开论述,且有个人之见。林纾不仅遵循刘勰的风格论,为了能让学者写出具备相应风格的文体,还在授课时,点明具体实践之法。包括为文的知识储备、叙述的侧重点、行文的章法笔法等方面。
“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11]438,下笔创作时文思跳跃飞舞,很难用恰切语言表达出来,很大程度上是没有做好积理的工作,所谓“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11]438,创作需要一定的知识储备,博观才能约取。“自六经以下,至于诸子百氏,骚人辩士论述,大抵皆以为寓理之具也。”[16]林纾很重视积理的环节,对很多文体的创作都提出了这种要求:“颂赞之词,非泽于子书,精于小学者,万不能佳。”[7]6340此种称许嘉言懿行,歌功颂德之作,以典雅纯正为贵,用词须谨慎,则应从小学中学习声韵;立意须敬慎,则应从子书中汲取义归雅正之旨。序跋则“要在平日沈酣于经史,折衷以圣贤之言,则吐词无不名贵也”[7]6364。记事之作,当“熟取《史》《汉》读之,自得制局之法”[7]6350,《文心雕龙》所谓“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11]455是也。
具备了相应的知识积累,还要注意各文体论述的要领及侧重点,夫体裁虽同,作法则殊。论檄文:“盖不斥人之罪案,不见己师之出于有名;不张己之兵威,莫望壮士之进而杀敌。且证以天时,审以人事,辨兴亡之理,论强弱之势,此檄文之要领也。”[7]6355此外,在《文微》中也不乏此类论述,如“诔载死者功德,于交谊当略言言之;祭文详交谊及死者之家世,于其生平转可略也”[7]6533。“善为传者,必寻其人轶事以为余波。”[7]6532林纾的观点,虽然不免有程式化的特点,但对于初学古文的人来说,可谓简单易行。
对于句法章法的处理,林纾往往着眼于与文体相对应的句式,如颂赞,“二体均结言于四字之句,不能自镇则近佻;不能自敛则近纤;累句相同,不自变换,则近沓;前后隔阂,不相照应,则近蹇”[7]6340。“大抵碑版文字往往宜长句者,必节为短句,不多用虚字,则句句落纸,始见凝重。”[7]6346其他如“记事之作,务取简明。凡局势之前后,宜有部署,有前后错叙,而眼目转清;有平铺直叙,而文势反窒”[7]6350。
四
“每种文体都有着一个发生发展,以及互相渗透、流变和演化的过程,每一种新文体的产生和形成,往往既是社会生活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语言发展变化、作家创作经验的日渐积累的结果。”[17]文体至清代,已趋于定型。随着文体的发展演变,刘勰所论之谐隐、祝盟等文体渐趋消亡,而新的文体也层出不穷。林纾在《文微》开篇有言“文须有体裁,有眼光,有根柢”[7]6529,文体的重要性自是不言而喻。然而,与林纾同时期的王兆芳撰《文章释》,总括一百四十三种文体,若以此为例进行教学,不免太过繁冗。诚如黄侃所言:“详夫文体多名,难于拘滞,有沿古以为号,有随宜以立称,有因旧名而质与古异,有创新号而实与古同,此唯推迹其本原,诊求其旨趣,然后不为名实玄纽所惑,而收以简驭繁之功。”[18]文类繁多,若不能整理分类,笼圈条贯,则实难发扬,故而林纾在“弥纶群言”的基础上去奢去汰,钩玄提要,在彦和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文体论。而在具体的论述中,林纾又有个人特色。
刘勰将“骚”归入“文之枢纽”,王运熙认为这“不但说明他对《楚辞》地位的尊重,而且还表明了他的一个重要的文学观念,即创作必须以经典为准则”[19]。林纾却将骚体置于文体论首位,究其原因,主要有三点。
其一,刘勰将“骚”作为“文之枢纽”,旨在建立为文所要遵循的思想观念。彦和之后,“诗骚传统”已逐渐成为文家共识,得到普遍认可。后世“拟骚体”的出现,使得“骚”作为一种文体,得到确立。林纾将“骚”体置于文体论首位,是从文体的角度,阐述文体来源、作法等,而非依据文学观念而言。
其二,从全书的结构而言,《春觉斋论文》在《述旨》中已略论为文之核心要则,林纾在《流别论》中,承袭《文心雕龙》的创作体制,分别对十五种文体进行溯源流、下定义、品文章、论写法。骚体与其他的十四种文体都是沿着这种方法论证,且各类文体大抵皆遵循论文主旨的创作原则。
其三,就文体的编排顺序来说,首列骚体,后言赋体,而从林纾对两类文体的论述来看,二者联系紧密。由此,我们不妨将骚体与赋体结合起来,以形成比对。骚体抒情,是介于诗与赋之间的文体。举凡“叙情怨,述离居,论山水,言节候”[7]6336,以兮字结尾增强声韵,发抒真情,更是要蕴含文人血泪在其间。林纾论赋时,肯定赋具备的抒情性的同时,更注重赋在劝谏讽谕方面的社会作用。所以他将柳宗元的《解崇》《征咎》《悯生》《梦归》《囚山》诸赋,归为骚体,认为这些篇章可与《九章》相媲美,言“题目甚似《涉江》《怀沙》诸作。当日若去赋字,但以‘解崇’等目标题,亦无不可。或且泥于《九章》《九辩》,故例不能足成九篇,故以赋名,亦未可定”[7]6481,柳宗元与屈原文章皆因真情而成至文。又认为庾信《哀江南赋》“不名为赋,当视之为亡国大夫之血泪”[7]6339,将此抒情性强的文章排除出赋的行列。“夫宛转偯隐,赋之职也。儒家之赋,意存谏诫。”[2]1256林纾论赋,注重社会功用。诚如刘大杰所言:“由《楚辞》到汉赋,是诗的成分减少,散文的成分加多,抒情的个人成分几乎完全消灭。”[20]林纾将骚体和赋体分别放在前两位,旨在由这两类文体表明区别及发展变化。
“兵燹之余,百物荡尽,田荒不治,蓬蒿没人,一二文士,转徙无所。”[2]1198于清末民初之时代下,琴南论文体发展,总是充斥有古今之感,盖于残破之社会境况中,欲借古文,用为“主文谲谏”之资也,又无奈于古文创作之颓势,以今昔对比,寄希望于归正返本。其论赋的发展演变后,感慨道:“今日科举一变,乃并此区区者亦绝响矣。”[7]6339是以馆赋虽步步循规,适时科举废除,竟连此墨守成规之作亦不复存在。“天子、诸侯所谓‘令德’、‘记功’者,晚近文人集中恒不多见。大抵无德可称而亦称之。”[7]6342铭箴初为记功颂德之作,然人心不古之时,世人以西方新道德为道德,有又何可称述之?“古之奏议取直,今之奏议取密。直者,任气摅忠,以所言达其所蕴,凡德不聪,佥壬在侧,乱萌政弊,一施匡正,一加弹劾,不能以格式拘,亦不必以忌讳避。至于密之为言,则粉饰补救,俾无罅隙之谓。”[7]6357琴南比对古今奏议文体,透过今人奏议敷设文辞,博取欢心的特点,亦可窥见社会之腐败。又如论碑体,林纾赞蔡邕《郭有道碑》“脍炙人口,由其气韵至高,似鼎彝出于三代,不必极雕镌之良,而古色斑斓,望之即知非晚近之物”[7]6345。蔡邕碑文,正是符合其温纯古穆的要求。观蔡中郎之文,与近人碑文相较,相去远甚,故碑文有古色之风,乃文之上乘也。大抵今人之文,多为无关痛痒之言。
文与世变相因,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章。“六朝之际,虽文与笔分,然士之不工修词者鲜矣。”[2]1278六朝追求词采华美,刘勰铺采摛文,骈俪华美,析理周致深切。而林纾正处于古文渐趋没落之时,面对清末民初特殊的政治局面与文化之凋敝,西学东渐下,报馆多章又多喜掺杂西方新名词,去经甚远。大道不行,这种深层次的心理动因更推动着林纾坚定地走着对经典的承续之路。为求文论有更广大受众,林纾摒弃艰深,选择更为通俗的表达方式,即便是才疏力薄之人,初识古文,也不会觉得困难。又因《春觉斋论文》原本就是课堂讲义,若以艰涩之语发之,则学生必昏昏然不知所指陈。诚如琴南所言:“盖讲义者,教普通之人,知古文义法,非先为奇古之文,使人不可得解,用以自炫其奇也……讲义之体,虽用白话可也。总之,以悟人之神,且导人之程途,以明白为上。”[6]178无论二人以何种表述方式述之,皆旨在由学文转而习道、悟道,协调文章“质”与“文”,“经义”与“翰藻”之间的关系,使文章在依经立义的同时,抒发情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