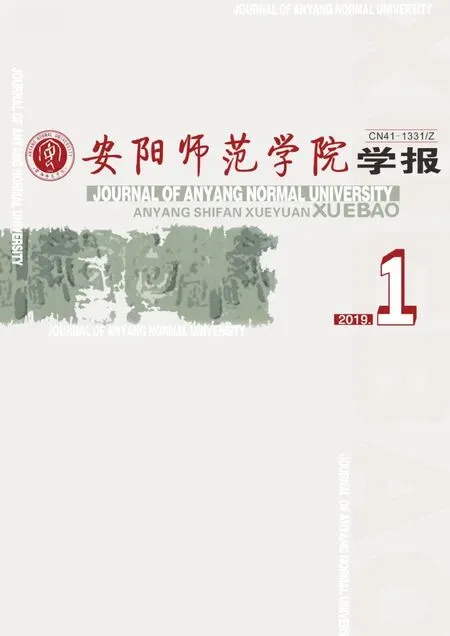墨家“用夏政”说辨析
刘书刚
(重庆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重庆 400044)
在先秦思想史的演进序列里,很多时候,墨家都扮演了一个儒家批判者的角色,其兼爱之说、薄葬之论、非乐之谈,都与儒家存在着明显的分歧;《非儒》等篇目的存在,更直接证明,墨家在展开其思想时,将儒家视为最主要的论辩对象。孔子有“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的说法,将有周一代的典章制度、礼乐文明视为典范,以兴复“周道”为旨归,成为儒家一派的思想特色。而据《淮南子·要略》篇所言:“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家正是不满于儒家的诸多主张,于是另辟蹊径,选择了“夏政”作为取法对象。自此之后,在论及墨家思想渊源之时,认为墨家效法“夏政”以与儒家之“从周”针锋相对,成为一个几乎可以算是常识的观点。
然而,如果仔细分析墨家思想,会发现以“用夏政”来对其核心观念进行总结,存在着许多的龃龉不合之处,也会掩盖墨家思想的一些特质,对此,汪中已经有所质疑,但所论较为简略。注汪中在《述学·墨子后序》中说:“墨子质实,未尝援人以自重。其则古昔,称先王,言尧舜禹汤文武者六,言禹汤文武者四,言文王者三,而未尝专及禹。墨子固非儒而不非周也,又不言其学之出于禹也。……然则谓墨子背周而从夏者,非也。”本文即试图在仔细分析墨家思想的基础之上,对墨家“用夏政”一说,做出详细辨析。
一、儒家的“从周”之义
认定墨家“法夏”,主要是突出其与儒家之“从周”取径不同而成分庭抗礼之势,因此,不妨先考察“从周”在儒家思想中的位置,进而反观“法夏”对于墨学而言是否有着类似的功用。自孔子开始,儒家就对周文化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在他看来,周代之治承接于唐虞夏商之后,能够更进一步,在政教体制、道德风化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至为全备的境界,“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周礼是在借鉴前朝得失、总结过往经验基础之上的伟大制作,自然成为孔子应对衰乱之世时取法的对象,其政治主张也一直以回归周制、恢复周礼为目标。当然,孔子并不要求一仍周礼之旧,在新的情形下,一些变更仍是必要的。比如他说:“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复古与从今之间的选择,需要具体考量。在描述理想政治时,他也说应当“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都可见其复古而不泥古。不过,即便有所改变,周礼之大体却不能损伤。正是因此,“文武之道”(《论语·子张》)成为子贡对其师之学的概括,相传主持制礼作乐之事的周公,孔子也极为钦佩欣赏;孔子之后,儒家学者对于文武周公之道的尊崇,几乎全无异词。
儒家对于周代的重视,还表现于对经典的整理和解释之中。儒家以传经、解经为本务,六艺经书所涉及的历史时段,虽然始于唐虞三代,终于春秋之世,而周代却居于核心之位。经书之中,与周代相关者占据了最大的篇幅:《易》经文王推演而愈加周全,“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周易·系辞下》)《诗》据传由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汉书·艺文志》),所存商、鲁篇什实际寥寥无几;《书》以《周书》篇目最为繁夥,记言载事也尤其详备;礼书,本就是周代曲为之防、事为之制的制度仪法的载记;《春秋》“举十二公行事,绳之以文、武之道,成一王法”(《汉书·儒林传》),同样有存周之道的意图。
周代在经典之中分量尤重,这或是文献流传所致,孔子之时,夏商文献已不足征,唯周朝典籍尚属完备。不过,“《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汉书·儒林传》)儒家对于经典的重视,在于其中蕴含着可以拨乱反正、协理天下的至高之“道”。六艺经典尽管内容各有侧重,体式亦不划一,但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它们相辅相成、互补互足,共同完成对“道”的呈现,成为修齐治平的不易之法。而周代鼎盛时期的政制典章,恰恰是“道”的完美体现。在儒者相传的信念之中,周代有制礼作乐之盛事,有致天下于太平之壮举,其先王行事、制度文章,实际荟萃了古来圣王制作之精华。既能集前代之成,与周代相关的内容,在经书中份量最重,也就合乎情理。
总之,在儒家看来,周之礼乐制度作为“道”的完美实现,其中的任何一个细微关节,都是在“道”的统摄之下的精妙设计,儒家所传承的经典之中,周代占据最大的篇幅正是理所应当。这样,周代在儒家学说中所占据的位置,就相当核心,儒家对于理想社会形态的构想和设计,也正以周代为蓝本,整理旧籍、传承经典,正是为保存周制。围绕着周代的遗文旧制,儒家进行了大量的编次考订、阐释发挥等工作,儒家思想的展开,周代实为其基础。如果说墨家之“法夏”,可以与儒家之“从周”相提并论,那么首先需要追问的是,夏代对于墨家思想学说的发生和发展,是否像周代之于儒家一般,如此至关重要?“夏政”是否成为墨家所提出的诸多社会政治主张的依据?
二、墨家“法夏”说质疑
尽管在诸多观念上与儒家对立,墨家同样宣称自己的各种主张是对“先王之道”的继承。“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生者,以先王之道教也。今誉先王,是誉天下之所以生也。可誉而不誉,非仁也。’”(《墨子·耕柱》)在墨子看来,“先王之道教”实为生民之本,并不因时日久远而丧失其有效性,在列国相争、强弱相凌的战国之世,尤其有被重提的必要。
对先王之道的探寻,自然要借助于流传于世的文本,事实上,在墨家看来,先王制作这些文辞,本就有保存道术、为万世开太平的良苦用心:“古之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之也。今闻先王之遗而不为,是废先王之传也。”(《墨子·贵义》)在政衰民敝之时,不废先王之传、延续古圣之道就显得更为重要,这是拯救乱世、平定天下的必须。正是因此,《墨子》一书中大量引用《诗》《书》等前代文献,甚至保存了许多不见于儒家经典的佚文。[注]有关《墨子》征引《诗》《书》等文献的情况,可参考陈柱《墨学十论》中“墨子之经学”一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0-90页。在墨家奉为言说之“仪”的“三表”之法中,“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被置于首位,《墨子》一书的众多篇目中,圣王行事、遗训,也被当做最具权威性的资料加以引证。
对“先王之道”和“先王之书”极其重视,在这点上,墨家与儒家保持了一致。不过,这并没有使墨家与儒家一般,围绕着《诗》《书》等典籍,发展出一个庞大的经学体系,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墨家以“夏政”为基础,构建自己的理想社会图景。在《墨子》一书所征引的诸多前代文献、圣王事迹之中,夏朝并未占据一个特别显眼的位置。《墨子·贵义》篇记载墨家判断言说、行为正确与否的标准:
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为之;凡言凡动,合于三代暴王桀、纣、幽、厉者舍之。
在逻辑上,“利于天、鬼、百姓”优先于“合于三代圣王”,《墨子》诸篇,大多正是先提出墨家以为能够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的观点,再引往古圣王之遗言故事以为佐证。并且,在这种有些主题先行的征引里,所谓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之间,很难说有本质的区别,夏代的重要性并没有被突出出来。儒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对于上古帝王同样称颂不已,但对周代有特别之注意,周之文献在其整理下亦最成体系,“从周”并不是一句虚言;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如果说墨家用夏政,从《墨子》及墨家学者的著作中,实际无法找到太多关于夏朝的资料。
这与墨家的思想倾向及其使用文献资料的方式有关。较之儒家在现实与历史之间斡旋,借整理、阐释典籍以表达思想不同,墨家对于现实的关切更为急迫,传承经典的欲望并不强烈。虽然前代圣王被视作兴利除害的典范,但墨家的思想主张,却很难说是从先王行事、或前代制度中引申而来,而是针对当下的现实情境提出相应的解决措施,继而从历史文献中寻找能够充当佐证的段落。对待前代文献的这种态度,使得墨家虽然同样频繁称引《诗》《书》,却没有以这些经典文本为基础,阐释出一套完整、系统的经学体系的欲望,而是仅仅满足于在论述之时寻章摘句,引用零星片段,有些时候甚至并不顾及这些片段的前后语境、上下之文,“断章取义”较之儒家更有过之,曲解以申已意的情况十分常见。
在反映墨家核心观点的诸篇之中,如果说《明鬼》《天志》等篇,因为天、鬼信仰的由来已久,所引用的历史资料尚能证明其思想主张的话,那么《兼爱》《非攻》《非命》等尤能显现其思想独创性的篇目,其中引述的历史,就显然经过了一番曲折的解说。在证明“兼爱”之说“古者圣王行之”之时,墨子引禹、文王、武王等平治天下的故事为例,并指出自己正是通过对文献典籍的阅读知其如此,“吾非与之并世同时,亲闻其声,见其色也。以其所书于竹帛,镂于金石,琢于槃盂,传遗后世子孙者知之。”(《墨子·兼爱下》)但其所述圣王抚有四海、济养万民,与其说是在践行“兼爱”思想,不如说只是履行其身为首领的职责,其所引《诗》《书》等文献,也只是以宏阔壮丽的文字来渲染圣王功业,其中看不出“兼爱”观念存在的痕迹。总之,墨子在这里引述的历史,根本无法证明“兼爱”说早已有之。
墨家对“非命”的论证大抵相类。墨子要求“尚观于圣王之事”“尚观于先王之书”以见命之乌有,其所谓“圣王之事”,即“世未易,民未渝,在于桀纣则天下乱,在于汤武则天下治,岂可谓有命哉!”而“先王之书”,即“古之圣王发宪出令,设以为赏罚以劝贤”(《墨子·非命上》),如果有命存在,则先王立赏设罚之举措就全是多余。墨子又多引《诗》《书》,指出自古及今,相信有命者尽为“暴不肖人”,至于“圣善人”则坚决抵制这一邪说。用励精图治、赏善罚恶的事迹,来否认先王对于“命”的信仰,墨子的论证很难说逻辑顺畅,他所说的执“有命”者对命的迷信已趋于极端,在先王之中自然难以找到如此激进之人,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命”的观念已被先王彻底排斥。事实上,在证明先王非诋有命之时,墨子对文本甚至存在误解,如《仲虺之告》中汤曰:“我闻有夏人矫天命于下,帝式是憎,用爽厥师。”墨子解释道:“彼用无为有,故谓矫”,由此可见“昔者,桀执有命而行,汤为《仲虺之告》以非之。”(《非命下》)以“用无为有”解释“矫”,未必合乎文本之义,更有可能的是,汤是在指责桀扭曲、背离天命,而不是假称天命。[注]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篇,此句作“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孔颖达疏:“夏王自有所欲,诈加上天,言天道须然,不可不尔,假此以布苛虐之命于天下,以困苦下民。上天用桀无道之故,故不善之,用使商家受此为王之命,以王天下。”如依此解,则汤并不否认有天命存在。
总之,在墨家这里,思想主张与历史事件、文献之间的交相辉映远逊于儒家。急切的救世之志使其兼爱、非攻等观念都是径直为现实而发,与历史事实、文献典籍之间的兼容度难免有所欠缺,有时甚至扞格难入。虽然同样频繁征引《诗》《书》等前代文献,来证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墨家完全没有以这些典籍为基础,建立一个学术体系的欲望,在其征引中,也看不到对于夏政有特别的兴趣。因此,与儒家以复兴周道为己任、以周代文献为核心建立经学体系不同,墨家“用夏政”之说,就有些缺乏证据,所谓“夏政”,从来就不曾在墨家思想体系的构建和演生中居于核心位置。
三、墨家对“法古”逻辑的批判
墨家无法以“夏政”为基础发挥自己的思想学说、构建理想的社会图景,也许是受到了一些现实因素的限制,即,墨家学者实际并没有太多夏代资料可以依赖。孔子即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对于夏、商二代之礼,孔子之时已嫌于文献不足,不能言明其详,年世又在孔子之后的墨家,自然也没有办法依之立说。这也是《墨子》一书中征引的前代文献,大多可以在儒家经典中找到的原因,儒、墨两家,实际面对的是大致相同的学术资源。
不过,墨家不以“夏政”为自己学说的根基,也与其思想的一些特质有关。“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论语·述而》)自孔子开始,儒家就表现出对于“古”的喜好,过往的历史,不仅成为知识的重要来源,很多时候也是儒者们审视现实的立足点。于是,儒家思想就表现出“温故而知新”的特色,“述而不作”也是儒者们认同的学术路径。然而,由于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墨家更关注的是学说或政治意见在兴利除害上的有效性,是否本之先王、继自往昔,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考量。因此,墨家对儒家“述而不作”的主张,有着直接的批评。
儒家学者公孟子曰“君子不作,术而已”,墨子不以为然,并指出“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注]引文中“术”“诛”二字,皆通“述”。参见孙诒让撰,孙启治点校《墨子间诂》,中华书局,2001年第434页。(《墨子·耕柱》)苟能为善,原不必在意是述是作,是承之于古,还是创之今日。在这里,墨子尚能够对述、作一视同仁,而在《非儒》篇中,墨家的态度就要更为激烈,在列举传说中的圣人作器造物之后,墨者指出:“且其所循,人必或作之;然则其所循,皆小人道也?”(《非儒下》)有“作”方能有“循”,如果“作”为“小人道”,那么“循”同样不值一提,“较之“循”,“作”具有毋庸置疑的优先性。这种论断或许有辩争时意气相激的成分,但也合乎墨家但求有利、不问来源的基本逻辑。
所以尽管依旧频繁称道先王,墨家终究流露出一些新鲜气息,有时甚至表现出对复古思维的质疑。公孟子主张“君子必古言服,然后仁”,墨子反驳道:“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为天下之暴人;箕子、微子,为天下之圣人。此同言,而或仁不仁也。周公旦为天下之圣人,关叔为天下之暴人,此同服,或仁或不仁。然则不在古服与古言矣。”这些同时并世之人,语言、服饰亦大致类似,但其中有仁有不仁,可见仁之与否原不在口中言语、身上衣冠,模仿古言古服,终不免失之皮相。何况,“且子法周而未法夏也,子之古,非古也。”(《墨子·公孟》)[注]许多学者都用此句作为墨家“法夏”的确证,然而从前后语境来看,墨子此言不过是拆穿公孟子“法古”的逻辑漏洞,并不意味着他主张“法夏”。追溯往古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不加别择、不论是非而一味以古为尚,将无实现之可能。更进一步说,“所谓古之言服者,皆尝新矣,而古人言之服之,则非君子也?然则必服非君子之服,言非君子之言,而后仁乎?”(《墨子·非儒下》)古之言服皆尝为新,若以法古为是,则并不法古之古人,应该算是背弃仁义,自然不足为训,如此,则所谓法古,实际是一个于理不通的悖论。
在《节葬》篇中,墨家揭示了法古者的另一个困境,即古之真相难以确定。“今逮至昔者三代圣王既没,天下失义,后世之君子,或以厚葬久丧以为仁也,义也,孝子之事也;或以厚葬久丧以为非仁义,非孝子之事也。曰二子者,言则相非,行即相反,皆曰吾上祖述尧、舜、禹、汤、文、武之道者也。”两种意见彼此对立,都自称为前古圣王之道,但古人既已不能复生,也就无法确定其是非然否。因此,墨家主张与其讨论何者更符合历史真实,不如根据其现实功效进行评判,“若苟疑惑乎之二子者言,然则姑尝传而为政乎国家万民而观之。”(《墨子·节葬下》)在这种唯以功利为尚的视野中,“古”根本不具备天然的价值,如果先王之道对当下无益,那么便没有任何传之承之的必要,不妨任其湮灭消失。因此,墨家虽不曾明确反对法古,但其思想中已经蕴含了这种可能。[注]在这一点上,墨家已开法家之先河。如《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墨子俱道尧、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谓真尧、舜,尧、舜不复生,将谁使定儒、墨之诚乎?”逻辑正与墨子相同。
在“述”与“作”二者之中更侧重于“作”,其基本理由在于时移事迁,当下世界中出现的许多新情形,并非遗传自古昔的智慧能悉数解决,墨家实际上已经承认了古今之间存在着无法弥缝的差异。在出自于墨家后学之手的《墨经》和《经说》之中,世界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变化的观念得到了更加明切地确认,这也就意味着,在墨家看来,“温故”并不一定能够“知新”,“先王之道”,并不见得能解决当下的所有问题。《经下》保存了如下两条,《经说下》亦有相应之解释,今并举如下:
经:在诸其所然、未者然。说在于是推之。
说:在尧善治,自今在诸古也。自古在之今,则尧不能治也。
经:尧之义也,生于今而处于古,而异时,说在所义。
说:尧霍,或以名视人,或以实视人。举友富商也,是以名视人也;指是臛也,是以实视人也。尧之义也,是声也于今,所义之实处于古。
对这些条目逐字进行精确的解释仍然十分困难,不过,注释者大多认为,这表达了尧不能治今的观点。[注]如孙诒让云:“言尧不能治今世之天下。”“言尧之义施于当时不能及今,即经‘异时’之义。”见《墨子间诂》第364页、380页。吴毓江云:“古今异情,其所以治乱者异道。故尧善治尧之世,而不能治今之世,非尧不善,时不可也。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治无定法,期当时耳。”见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2006年,第549页。尧虽然在今日有善于治理天下的名声,但其治理天下的事实,却发生在古代,而古今异时,使尧生于今日,未必能取得同样光辉的成绩。对尧的态度如此,对“夏政”的态度也应大致相类,很难想象,墨家会以“用夏政”的方式,来回应战国之时的诸多社会政治问题。
总之,无论是强调“作”之重要以与儒家“述而不作”相对立,还是对“法古”的逻辑漏洞的揭发,还是以古今异时为理由,认为尧不能治今,都足以表明,墨家对于从过往的朝代中选择其中一个作为典范,在已有的某个政制体系基础上缘饰发挥,以治理当下之纷乱,并没有足够的兴趣。墨家更习惯的思考方式,还是直接面对眼前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所谓“用夏政”之说,不仅不符合墨家学说之事实,而且会遮蔽其思想的上述特质。
四、墨家“法夏”说的由来
如上所述,墨家“用夏政”之说,考之其书,则无其实,揆之以理,又有矛盾,那么,需要继续追问的是,这一误解墨家学术、又流传甚广的说法是如何产生的。此说最早见于《淮南子·要略》篇,在作出这一论断之后,此篇继而写道:
禹之时,天下大水。禹身执蔂臿,以为民先,剔河而道九岐,凿江而通九路,辟五湖而定东海。当此之时,烧不暇撌,濡不给扢,死陵者葬陵,死泽者葬泽,故节财、薄葬、间服生焉。
可见,将墨家与夏代联系起来的关键在于夏之始祖禹。由于生当灾难之世,禹不辞劳苦而奉行节俭,省财用而薄丧葬,这些同样是墨家为救世之弊而提出的主张。并且,禹在治水过程中表现出的苦行精神,也与墨家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的气度相吻合,所以,墨家对于禹之事迹特别津津乐道,也在情理之中。事实上,在《淮南子》之前,《庄子·天下》篇已经突出了墨家对于禹的心有戚戚:
墨子称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禹亲自操橐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胈,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禹大圣也,而形劳天下也如此。”使后世之墨者,多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谓墨。”
这一段论述,甚至都没有提到禹也有节葬之类的主张,仅仅强调其济天下之溺而劳苦不休的精神,使墨子极为钦佩,奉为仪表,而墨家一派,遂以行“禹之道”自任。但墨家与禹在行事风格上的接近,最多只是异世之间的同气相求,远远没有达到“用夏政”的地步。墨家并非在夏朝政制的基础上,推演自己的思想观念,引申自己的救世之说,即便其节用、薄葬之说,合乎禹之行迹,其兼爱、非攻、尚同等一系列更为核心的思想,显然不是在“夏政”的基础之上,阐释、发挥而来。总之,墨家即便对禹十分尊崇,其思想与夏政的关系,也远远无法与儒家之“从周”相提并论。
那么,何以《淮南子》会发明墨家“用夏政”之说,以与儒家“从周”成对峙之势?这或许与汉代流行的“三代改制”之说有关。所谓“三代改制”,指历史上的夏、商、周三代,相互承继之际,在政制上必有所改易,以救前代之弊;而三代恰成一循环,继周而兴起者,又须与夏朝保持同样的精神特质。“三代改制”之说在孔子处初见端倪,他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虽只是简单描述礼制互有损益的历史进程,并无三代往复循环之论,但已经足以成为后世儒者倡为此说的起点。
董仲舒提供了“三代改制”之说最具代表性的阐述,在《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质文》一篇中,他对交替终始的三代的正朔、服色、礼乐等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构建了一个复杂而又不失为有序的体系。其说繁复,在此也无需详述,倒是曾经向董仲舒问学的司马迁,提供了对“三代改制”的一个简明的描述,可据以了解此说之大概:
太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高祖本纪》)
三代之制循环相承,前代政制的沉疴积弊,正有赖于继承者的改弦更张。“三代改制”之说,一方面,是对以往历史朝代的政治风格的抽象概括,另一方面,也有指点新王朝前途何在、应该如何改制的意图。[注]有关“三代改制”之说,可参考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汉武帝的改制及三统说的发生”一节,见《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二,中华书局2011年,第279-292页。
看起来,“三代改制”之说与思想史、学术史上的儒、墨之争本来不应有瓜葛。然而,在其提供的循环不已的序列里,周衰文弊之后,需要以夏政之忠来矫正;而儒家学说以“从周”为特色,墨家又处处以攻讦儒家为事,且对夏代始祖大禹又倍加推崇,于是,在三代质文相替之说流行之后,人们很自然地会以为,墨家正是试图以“夏政”来纠正儒家“从周”的弊端。墨家“背周道而用夏政”的说法,很有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产生于世,并影响深远。但对于墨家学说而言,这一论断其实不无误解。
五、结语
如上所述,墨家虽然与儒家一样,屡屡引述“先王之道”以证明自家主张,但在《墨子》一书对于《诗》《书》等前代文献的大量征引中,很难说与夏代相关的条目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并且,墨家在与儒家的争辩交锋之中,对于儒家的“述而不作”提出了质疑,并特别强调了“作”的重要,对于儒家“法古”逻辑中的不通之处,也进行了犀利的揭露。这些,都决定了墨家不可能以“夏政”为核心,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的用世之心和功利色彩的流派,墨者更习惯于直接针对当下的社会政治问题,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不过,墨家对于夏代之祖大禹,表现出相当的尊崇,这主要是因为,禹在治水之时表现出的坚忍克制、俭省节用的作风,正是墨者所提倡的行事风格。而在“三代改制”之说兴起,以夏之忠救周之文的观念流行之后,作为儒家批判者的墨家,就被冠以“背周道而用夏政”的名号。这一断语,有时会导致对于墨家思想的误解,比如,会忽略其虽不废弃“述”、但更侧重于“作”的学术风格,会将其视作一个在“好古”程度上与儒家不相上下的学派。因此,墨家“用夏政”的说法,虽然早在汉代就已提出,并且流行已久,成为学者们论及墨家时屡屡提起的常识,但实际上经不起仔细检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