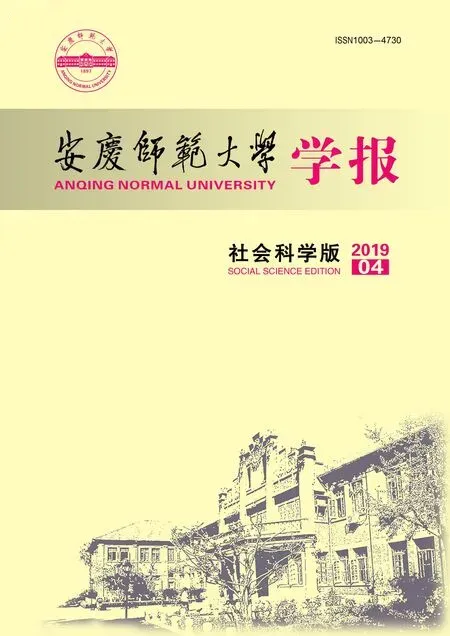李维桢对诗学辨体论的审视
张银飞
(铜陵学院文学与艺术传媒学院,安徽铜陵244061)
李维桢(1547—1626),字本宁,明“末五子”,是中晚明文坛上一位重要的领军人物,著有《大泌山房集》一百三十四卷,其诗学思想以诗学辨体理论为主。
一、诗论焦点:诗歌“咏物”“使事”伤体论
有明一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高举“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大旗,“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1]7438主张“格调”复古,“夫诗有七难,格古、调逸、气舒、句浑、音圆、思冲、情以发之,七者备而后诗昌也。”[2]446随后的明代文坛被“格调”复古派所左右,其诗学主张和诗学取向均以“格调”为诗学最高范式。在宗唐抑宋的诗学背景下,明代诗论家从不同的诗学立场、学术视角,对咏物诗以及诗歌“使事”问题作了诸多探讨,提出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诗学批评主张,这也成为明代诗学批评史上焦点问题之一。
以诗文著称,且与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交游的陆深在其诗论中认为:“大抵咏物诗体,不免要粘带,颇累气格。”[3]2151从明代复古“格调”论角度,认为咏物诗是有“粘带”之弊的,破坏了诗歌内在的审美性,不符合当时的诗学创作规范和诗学理论要求。作为“后七子”领袖、主盟文坛二十余载的王世贞,结合自身的诗歌创作体会和实践,直言不讳地指出咏物诗伤体,特别是在创作七言近体诗过程中表现最为明显。“余不喜咏物,诗至七言近体,尤绝不为之,惧伤体裁。故长夏无事,家园景物,颇成烂熳,鱼鸟亲人,亦自足怜,因戏各赋一章,合之得六十首,并旧作六首,别成一卷,老翁涂抹作儿子态,终不似也。”[3]4600-4601“诗言志”是文人士大夫对诗歌创作本质特征的共同认识,也是共同的诗学追求和诗学取向,王世贞也不例外。在创作为数不多的咏物诗时,王世贞不是从“诗言志”的高度审视和认同自己的诗学作品,而是认为其创作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戏作”,并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惧伤体裁”,尤其是七言近体咏物诗最为伤体,甚至以“老翁涂抹作儿子态”的讽刺性的话语和诙谐的言语评价自己创作咏物诗的质量和水平。胡应麟也认为:“咏物七言诗,唐自《花宫仙梵》外,绝少佳者,国初季迪《梅花》,蒙载《芳草》,海叟《白燕》,皆脍炙人口,而格调卑卑,仅可主盟元、宋。”[4]363在提及咏物诗创作时,对七言律诗创作高度繁荣的唐代也提出了批评,认为不可取的咏物诗诸多,更不言宋、元、明三朝。在胡应麟看来,仅《花宫仙梵》是符合明代诗法规范和诗学审美范式的,其他咏物七言诗,与明代复古诗派的诗学理论主张极度不符,皆是“格调”低下,由此也就顺理成章否定了七言咏物诗的艺术成就和诗学史地位,阐明不被明代复古派所接受并在诗歌创作中所践行的原因。明人宋绪对此也有独特体会,“随寓感兴者易,验物切近者难。”[5]指出诗歌创作应该随感即兴而发,仔细验物式的创作诗歌,很难创作出佳作,而咏物诗正是在“验物”范畴之内。
相较对咏物诗伤体论的认识而言,明代诗学理论家对诗歌“使事”问题的阐述就要深刻得多。朱权在《西江诗法》中明确指出:“持要铺叙正,波澜阔,用意深,琢句雅,使事当,下字切。观诗之法,亦当如此。”[3]527注意到了诗法规范下诗歌的“使事”问题,认为诗歌“使事”需建立在对诗法本体性认识的基础之上,在不破坏诗法规范的前提下,对诗歌“使事”问题提出了关切,把诗歌“使事”问题纳入诗法的范畴展开探究。黄溥在评价黄庭坚“使事”诗歌时,倍加赞赏。“山谷善使事,诗家借和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山谷《猩猩毛笔》是也。”[3]1066认为诗歌“使事”本身并无不可,其关键是诗歌“使事”的“妙法”在于用其事而不用其意,这是针对宋代诗歌多用典故之弊而提出的诗学主张,也是明代“格调”复古派在诗学领域尊唐抑宋的诗歌创作路径的必然选择。王世贞对诗歌“使事”问题论述较为全面,提出了“三欲一必”的主张。在“藩镇富强,兼所辟召,能致通显”[3]4246的唐贞元以后,诗坛出现了“取办俄顷以为捷,使事豆丁以为工”[3]4246的不良诗学“使事”取向,王世贞极力纠偏。在评价陆子渊《闻警》中“大将能挥白羽扇,君王不爱紫貂裘”的一联时,高度评价并赞赏其“使事之工,骈整含蓄,殊不易匹”[3]4288。列举诗歌“使事”的实例,阐述精妙所在,并在诸多诗论中先后提出“使事欲博”[3]4457“使事欲稳”[3]4526“使事欲切”[3]4528“使事必惬”[3]4491的“三欲一必”的主张,要求诗歌“使事”必须做到“博”“稳”“切”“惬”,足见其对诗歌“使事”问题的独特见解和领悟。胡应麟在《诗薮》中也多次对宋人在诗歌创作过程中过多“使事”提出批评,指出:“禅家借事理二障,余戏谓宋人诗,病症坐此,苏、黄好用事,而为事使,事障也”[4]39;“使事自老杜开山作祖,晚唐若李商隐深僻可笑,宋人一待坐困此道。”[4]356综观有明一代的诗论,胡应麟对宋诗“使事”批评是较为激烈的,显然受到严羽诗学思想的影响,虽较为激进,有失偏之嫌,但无可否认的是,宋代诗歌创作,在“使事”上确实存在种种弊端。对此,胡应麟进一步指出,“后之作者,鉴戒前归,遂为大忌。国朝诸公,间有用者,束而未畅。惟弇州信手匠心,天然凑泊,千秋妙解,独善斯人。观察系兴,尤得三昧,极盛之后,殆难继矣。”[4]356直指明代诗人未能解决诗歌“使事”的问题,诸多诗人均是“束而未畅”,诗歌创作不得“信手匠心”。胡应麟认识到了宋、明两朝诗歌“使事”不当从而破坏诗体问题的存在,但并未从诗学理论的高度加以剖析和解决。
综上所见,有明一代的诸多诗论家,在诗歌创作、诗法探究、诗体分析等诗学主张方面,均对诗歌“咏物”“使事”是否伤体的问题作了有益探索,但由于这些诗学理论探究是基于“格调”复古派诗学视野和诗学范畴之上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其桎梏,看到问题的所在,但未能从诗学理论构建、诗歌创作实践等方面解决这一诗学问题,构建符合诗体发展的诗学理论体系。
二、诗学立场:对诗歌“咏物”“使事”的把握
面对明代诗坛对诗歌“咏物”“使事”的批评,李维桢突破了“格调”复古派的诗学认识,从诗学辨体理论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较为全面地认识了这一问题的实质,从理论构建到创作实践均较好地把握了诗歌“咏物”“使事”伤体论问题。
李维桢在《唐诗类苑序》中,集中阐发了对咏物诗以及诗歌“使事”伤体问题的看法。那么,李维桢为何要在这篇序中凸显出对此类诗学理论的特别关注和关切呢?首先,要弄清楚《唐诗类苑》到底是一部怎样的著作?其中是否收集了大量的咏物诗以及“使事”的诗歌?“初,宋赵孟坚有分类唐诗,佚阙不完,世无刊本,之象因复有此作,凡分三十六部,以类隶诗。”[6]1752《唐诗类苑》是明人张之象所编,两百卷,收录了唐代1472位诗人的28245首诗,是编纂《全唐诗》的三大来源之一,足见其规模宏大。后被卓明卿所得,“割取初盛唐诗刊之”[6]1752。李维桢为《唐诗类苑》作序时也指出“卓征甫先版行初盛诸家百卷”[7]491。可见,李维桢为序的是卓氏百卷本的《唐诗类苑》,而不是张之象的两百卷本。“明华亭张之象始有《古诗类苑》、《唐诗类苑》两集。然亦多以人事分编,不专于咏物。其全辑咏物之诗者,实始自是编。”[6]1726卓明卿百卷本的《唐诗类苑》,确实是在张之象两百卷本的基础上所编纂,但编纂体制和编纂内容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一方面是卓明卿百卷本明显压缩了诗歌收集的范围,初盛唐之后的诗歌并未收录和编纂。另一方面,张之象的两百卷本以人事分类编次,而卓明卿百卷本则是首开诗歌主题编次的先例,辑录了大量的咏物诗,这在编纂诗歌领域中是创新的举措,是对以往诗歌编纂以类分次的一种突破。而这百卷本的《唐诗类苑》,在李维桢为之作序时,其在士林中流传范围较广,影响较为深远,从为之作序的文坛大家便可看出。“王元美、汪伯玉、屠长卿、李季常及征甫为之序,艺林以不睹全书为憾。”[7]491在明代产生如此影响的诗歌选本的序中,李维桢首次对诗歌“咏物”“使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盖闻之先进言诗者,总诸诗之体而论,以为咏物为伤体,就一诗之体而论,以使事为伤体。”[7]492从诗学辨体的角度,简明扼要地概括了“咏物”“使事”在诗歌创作中存在伤体的情况,并分析了两者的区别,认为把握不好诗歌“咏物”,可能会造成诸体皆伤局面,对诗歌“使事”问题处理不当,则会伤一诗之体。从“诸诗之体”到“一诗之体”,引出了“先进言诗者”的观点,进而指出继《三百篇》“后人为诗者,咏物征事以多为贵”[7]487的怪状。其批评的着力点是对宋诗“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不满,既不符合“格调”论的诗学规范,也不符合“格调”论的诗学审美,这一批评与《沧浪诗话》的批评思想是不谋而合的。“近代诸公乃以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且其作多务使事,不问兴致;用字必有来历,压韵必有出处,读之终篇,不知着到何在。……诗而至此,可谓一厄也。”[8]26相较李维桢的委婉批评,王世贞表现的更为直接:“余不喜咏物”。由此,李维桢结合《唐诗类苑》,进一步对诗歌“咏物”与“使事”问题全面阐述自己的诗学立场和诗学取向。
夫诗《三百篇》何者非事?何者非物?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孔子固有定论矣。然当是时,诗体与今异,试取易之卦象、爻象、书之典谟、训诰与诗之风、雅、颂而并观之,其象别几何?故咏物、使事累用之而无嫌。至汉魏六朝而后,诗始有篇,皆五言者;诗始有篇,皆七言者。汉魏古诗以不使事为贵,非汉魏之优于《三百篇》也,体故然也。六朝诗律体已具,而律法未严,不偶之句与不谐之韵往往而是,至唐而句必偶,韵必谐,法严矣。又益之排律,则势不得不使事,非唐之能超汉魏六朝而为《三百篇》也,体故然也[7]491。
宏观上,从梳理诗体源流嬗变着手,把握诗歌“咏物”“使事”在不同时代、不同诗体和不同诗法中运用的具体情况,探索到诗歌源头,直指《三百篇》中“何者非事?何者非物?”,全面论述了“咏物、使事累用之而无嫌”的根本原因在于古、今诗体和诗法的不同。正是由于诗体和诗法有别,古诗体累用“咏物”“使事”不会出现伤体的情况,并指明这一论断在孔子删诗时就有定论。这一格局,到了汉魏古诗出现后,对诗歌“咏物”“使事”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几乎与《三百篇》背道而驰,不再是“何者非事?何者非物?”,取而代之的是“以不使事为贵”。对六朝诗歌的“使事”问题,在《龚子勤诗序》中,李维桢刻意提出了尖锐批评,“夫诗自六朝而使事之体兴,铺张驰骋,排偶猥杂,大伤气骨,病在夸多,不能割爱耳。”[7]723指出律法不严的六朝律诗,“使事”之诗体虽大兴,但随之而来的是,出现了种种弊端,如“伤气骨”“病多夸”,说明诗歌“使事”的现象虽在六朝律诗中大量出现但并未达到成熟之境。这一问题,就急需在唐代予以解决。然而,唐近体诗的出现,又增加了这一问题复杂性。唐近体诗是在六朝律诗的基础上才达到“句必偶,韵必谐,法严矣”格律要求的,即到唐代律诗诗体发展成熟、诗法日臻完善,出现了“使事”不伤诗体的情况,但这一情况并不是在所有的唐诗诗体中都存在,而仅限于排律诗体之中,由“势不得不使事”达到“证事而不役事”[7]717的境界,也就不存在“伤体”之说。可见,诗歌“咏物”“使事”是否伤体,不在于诗歌创作时运用的技巧上,而在诗体与诗法的规范要求上。
除宏观把握外,李维桢在论述此类问题时,总是不断地发出“体故然也”的感慨,并从这一角度进一步探讨“近体”与“古体”在对待这一问题上的差别,指出:“故诗咏物而善使事者为尤难,非近体之难于古体也,体故然也。使事而为古选,譬之金屑,不可入目,其可以极命庶物,百出不穷者排律耳,七言古次之,五七言律次之,体故然也。”[7]491李维桢是从两个方面来阐述这一问题:一是从把握“咏物而善使事”的诗歌特点着手,不是强调近体诗难于古体诗,是由古体诗的诗体特性和本质决定的。另一方面,认为古体诗就诗体而言,在诗歌“使事”上就不如排律、七言古、五七言律,特别指出诗歌“使事”只有排律“百出不穷”。实际上就是刻意强调,最适合“使事”的诗体是排律诗。由此不难发现,李维桢在考察诗歌“咏物”“使事”伤体论的问题上,从诗学辨体理论的角度不仅否定了汉魏诗歌优于《三百篇》,而且也否定了唐咏物诗或诗歌的“使事”技巧超过汉魏六朝甚至是《三百篇》,其在把握诗体发展和流变的前提下,逐一审视这一问题,探讨存在差异的深层次原因。
在《徐茂吾诗序》中,李维桢又进一步谈到了对咏物诗的看法,“咏物诗仿于六朝,而体不称律,音韵不谐,句子不偶,未足为病。至唐人,律有定句,句有定字,职成拒制,无容逾越,离则双美,合则两伤,其体愈严,结撰愈难。”[7]758两个朝代,同一类诗歌,在创作上对诗体与诗法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李维桢全面把握了六朝与唐代在咏物诗歌创作方面存在的差异,分析了咏物诗在六朝不为病而到唐代出现种种弊端的根本原因,重点探究了唐代咏物诗在律诗这一特定诗体规范中创作的难点。阐释的诗学理论基点在诗体流变和诗法演变上,六朝咏物诗在韵律、对仗上的要求不高,达不到唐诗“离之双美”的境界,但在六朝诗体和诗法的规范下,咏物诗创作的自由度、自主性和灵活性反而较高,这无疑为咏物诗创作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诗学氛围。到了唐代,诗体空前发展,诸体皆备,诗歌体制特别是律诗的外在形态已经完善,“调”与“格”达到“职成拒制,无容逾越”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咏物诗创作来说,反而是“结撰愈难”。揭示出咏物诗创作规范是随着诗体的不断发展而变化,这对咏物诗创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在唐代近体诗的诗体规范中,如何创作咏物诗且不存在伤体的弊端?针对这一问题,从李维桢全面评价徐茂吾的咏物诗便可窥探一二。首先,咏物诗的诗体发展重在创新。“多用一律,或一物而数十篇,律且用强韵,或一韵而数百言。”[7]759实际上是肯定了徐茂吾的咏物诗创作打破了六朝和唐代咏物诗创作固有的范式,同时又达到了“缛藻艳色,炫心夺目”[7]759之境,对其创新表示了充分地肯定和认同。其次,咏物诗创作要兼顾“才”“学”“格”“调”。“六朝之才与学而得唐人之格与调”[7]759,清晰表达了李维桢创作咏物诗的诗学主张,其中是否夸大了徐茂吾创作咏物诗才能,此且不论,但却将六朝的“才”“学”与唐人的“格”“调”结合的诗学思想是有其合理之处的,符合诗歌创作规律和诗学理论要求。最后,咏物诗要达到神气兼备的境界。“错综之,变无穷靡曼之态,非一意奇骨,劲神合气完不堕外道,不缚小乘。”[7]759阐明咏物诗创作并非一味追求“奇骨”。过度盛行“奇骨”之风,是导致后世咏物诗伤体情况存在的直接原因。要改变咏物诗伤体的弊端,最有效、最直接的创作方式是“错综之,变无穷靡曼之态”,最后使咏物诗达到劲神合气、形神俱佳的审美范式,摒弃了六朝、唐代咏物诗的缺陷,又很好地把握住了咏物诗的创作精髓。
三、理论构建:“三必”的诗学境界
至此,李维桢对咏物诗以及诗歌“使事”伤体论问题的探讨并未结束,“以为使事、咏物诗家所难,而音调格律,意致风神,种种具足,殆不易也。”[7]732诗人在创作“咏物”诗及诗歌中“使事”时并不是很难,难的是要达到“音调格律,意致风神,种种具足”。受复古思潮的影响,崇唐抑宋的思想在明代诗人的心中根深蒂固,李维桢也不例外。在评价唐、宋咏物诗和诗歌“使事”优劣的问题上,李维桢一方面从诗体发展论的角度出发,认为宋诗确实逊于唐诗。“诗自《三百篇》至于唐,而体无不备矣。宋元人不能别为体,而所用体又止唐人,则其逊于唐也。”[7]495另一方面,又不完全否定宋诗,指出“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7]1450。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对宋诗加以肯定。而对于明代早中期的诗歌创作,李维桢在诗序中多次提出明代诗学历经“三变”,即一变雅俗杂糅,二变师古,三变师心。
本朝人文极盛,成弘而上,不暇远引,百年内外约有三变,当其衰也,几不知有古。德靖间二三子反之而化裁未尽,嘉隆间二三子广之而模拟遂繁,万历间二三子厌之而雅俗杂糅一变,再变觭于师古,三变觭于师心[7]537。
李维桢对明诗发展情况的把握是较为准确的,在此基础上,指出在历经“三变”后的明代诗学,依然弊端种种:
盖今之能为诗者,所在而有其法。取嘉隆以来,诸公上及三唐而止,不能求诸六朝、汉魏,安问《三百》?其材取诸诗而止,不能求诸史与子与经;其体五七言律而止,不能求诸乐府、骚雅;其人则游大人以成名或广引俦类,互相标帜,而酒人博徒、跳浪忿詈迫胁,士大夫以张其声誉,诗道之衰,莫其为甚矣[7]9。
李维桢分别从“法”“才”“体”“材”等方面来分析明代“诗道之衰”的基本事实和深层原因,并深刻地认识到在经历“三变”后的明代诗学,不管是雅俗杂糅,师古还是师心,都没有彻底改变明代诗学的颓废之势。有明一代的咏物诗和诗歌“使事”也面临着同样的迫切问题。为了改变这一诗学现状,促使明代诗学走向健康的轨道,作为复古阵营的李维桢,在纠偏“师古”与“师心”的两种极端的诗学主张的同时,结合时代背景和诗坛语境,必然会选择一种折衷的诗学路径。
在诗学辨体理论的视域下,就如何彻底解决咏物诗和诗歌“使事”伤体论的问题,李维桢整合诗学思想,构建较为合理的诗学理论,表明了诗歌创作倾向和诗学理论主张,提出了咏物诗和诗歌“使事”问题的诗学批评标准:“使事善者,必雅、必工、必自然,不则,反是而诗受伤矣。诗使事者,篇不必句有事,句不必字有事。其伤诗差小。咏物者,篇不得有无事之句,句不得多无事之字,其伤兹大。”[7]491指出诗歌“咏物”“使事”,要达到“必雅、必工、必自然”的“三必”意境。其中,“雅”是要求诗歌创作时在“咏物”“使事”上要符合传统的诗学美学审美标准和诗学审美范式,要复归“雅”“正”,不能偏离诗学传统。“工”更多的是针对诗歌创作技巧层面而言的,从各种诗体和诗法的内在要求出发,诗歌“咏物”“使事”必须符合诗体规范的特性,破坏诗歌整体的布局及诗歌营造的意境。而“自然”是对咏物诗和诗歌“使事”的最高要求,也是李维桢诗学思想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即诗歌“咏物”“使事”必须要达到无痕的境界。“雅”“工”“自然”的诗学主张,“雅”“工”皆是诗歌创作的外在要求,而“自然”是诗歌创作的内在需求,李维桢在诸多诗序中均有论及,现兹引录,以便疏解:
以情纬物,以文被质,合于自然[7]538。
本于性灵,归于自然,无二致也[7]735。
有诗而不贵自然者,善乎[7]721?
削鐻神志之间,斫轮甘苦之外,肉奏丝竹之上,要之,悉本自然,非雕缋满眼无生意者可企及也[7]727。
人力至合于天然,故巧而若拙,冲然而有余味[7]39。
淡然绝尘,莹然骇瞩,爽然掞溪之景,冷然姑射之肤,婉转流便而有余态[7]778。
自任其力之所至,自得其性之所近,自发其衷之所知,自适其景之所遇,必不啜人残渖,拾人剩馥,补人旧衲[7]23。
李维桢在创作实践上极力反对为文造情、生搬硬套,在诗歌风格上追求“冲然而有余味”“婉转流便而有余态”,在诗学理论上倡导味之不尽的“自然”之境,在对待诗歌“咏物”“使事”是否伤体问题上也秉承了这一诗学理念,坚持以“自然”为核心的“必雅、必工、必自然”的“三必”诗学思想来解决诗歌“咏物”“使事”伤体论问题。
此外,李维桢运用以“自然”为核心的“三必”诗学主张,对初、盛、中、晚唐的咏物诗和诗歌“使事”现象提出批评:“唐之律严于六朝而能用六朝之所长,初、盛时得之,故善美千古。中、晚之律自在而犯六朝之所短,雅变而为俗,工变而为率,自然变而变而为强造。”[7]491指出初、盛唐的“咏物”“使事”类的诗歌符合“三必”的诗学主张。中、晚唐不可同日而语,随之而来的是“俗”“率”“强造”。最后李维桢甚至用“诗道陵迟”[7]492加以否定,可见其对“俗”“率”“强造”诗歌的厌恶程度。在对待如何学习初、盛唐的咏物诗和诗歌“使事”问题时,李维桢认为,“咏物同其使事,同以时求之,而唐诗与时高下若妍媸也,以类求之,而唐人才识高下若苍素也。”[7]49明确提出“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改之”[7]492的学习、临摹方法,极力主张既不要一味的抛弃,也不要一味泥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