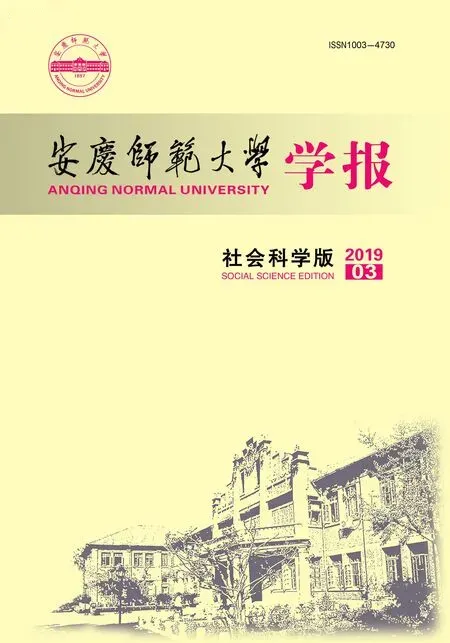“身后毁誉”:段祺瑞逝世后的社会舆论反应
刘东庆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
1936年11月2日,素有“北洋之虎”美誉,在民国政坛上叱咤一时的北洋元老段祺瑞因宿疾复发,宣告不治。他的离世正值内忧外患的社会背景下,一方面中日矛盾加深,战争一触即发,另一方面国内局势山雨欲来、危机四伏,在此敏感时刻,段祺瑞的逝世引发社会舆论的高度关注。作为一位有着广泛影响、颇受争议的政治人物,无论在生前还是身后,对段祺瑞及皖系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相关成果亦复不少。①代表文章主要有莫建来:《试论段祺瑞在北洋建军中的作用》(《历史档案》1991年第1期),张华腾:《河间、彰德会操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6期),莫建来:《评辛亥革命中的段祺瑞》(《历史档案》1993年第2期),汪朝光:《北京政治的常态和异态——关于黎元洪与段祺瑞府院之争的研究》(《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3期),胡晓:《段祺瑞武力统一政策失败原因探析》(《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杨德才:《1924年段祺瑞出山的主要原因》(《安徽史学》1993年第1期)等。关于段祺瑞逝世前后各方因应的文章有许曾会:《南京国民政府对段祺瑞去世的反应》(《平顶山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目前相关研究大多集中于段祺瑞在政坛上最为活跃的时段,对段祺瑞晚年南下及逝世前后的活动关注较少。②学术界对张之洞、孙中山、吴佩孚等人逝世后社会舆论的反应已有关注,代表性文章有桑兵:《盖棺论定“论”难定:张之洞之死的舆论反应》(《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郭辉:《“盖棺论定,尚有待于千载下焉”——孙中山逝世后的舆论反应》(《民国档案》2010年第4期),林辉锋、黄宝撰:《吴佩孚逝世后的社会舆论反应》(《学术研究》2015年第1期),等等。本文在利用报刊杂志、日记、回忆录等多种史料基础上,尝试从段祺瑞逝世后相关各方所争论的段祺瑞“个人品行”“政治作为”等层面展开论述,力求揭示立场背景、时代环境等对人物评价的影响,加深对抗战爆发前政治局势的认识。
一、“复杂多面”:段氏个人品行的舆论评价
段祺瑞素有“六不总理”的美誉,仅就个人操守而言,他在北洋诸政要中确有可圈可点之处。正如《中央日报》所言:“政治领袖刚劲之节,廉介之风,其于人民精神上之感召力最为伟大,其取得人民之同情也最易,政治上到处充满罪恶,然其罪恶之永不能湔涤者,无过于贪黩,故清勤二字,为中国政治家最要之原则。”[1]可见,在政潮迭起的北洋时代,个人操守往往超然于政治功业之上,成为评价政治人物的重要面相。
曹汝霖在段氏死后追述其一生功绩,对其人品做了高度评价。他认为:
芝老……素性刚毅,果断廉洁,不威而严。闻在小站练兵时,不离营舍,与士卒同甘共苦。每逢发饷,总由陆军部军需处员,点名发放,从未经手,更见其公而无私。余追随二十余年,见其治事之勤,待人之诚,自奉之俭,而遇事负责,令出必行,皆足为后人法。项城对段寄之以股肱,重之以姻娅,而段对项城亦忠心耿耿,惟命是听。及帝制发生,合肥即毅然隐退,屡召不至,其公私分明若此。迨项城取消帝制,应征组阁,含泪受命,其爱护项城始终不渝又若此。参战之役,力排众议,虽被黎罢免亦不顾。卒以宣布虽近欧战尾声,然仍为国增光[2]307。
曹汝霖对段氏的评价透露出其性格的几个特点,一是“素性刚毅”,二为廉洁奉公,三为敢于负责、待人真诚,四为公忠体国。曹汝霖曾长期在段祺瑞手下任职,两人关系密切,他对段祺瑞性格的评价基本反映了段氏性格中的几个特质。
对段祺瑞的评价中,“刚直”成为其最鲜明的性格特点,相关报道屡见于报端:“综段氏之一生,廉洁正直,识高力果”[3],“段芝老素有‘倔强’之称”[4],“自信甚深,刚而揽权”[5]4。各方对此种性格特质也褒贬各异,徐一士就认为:“其长处,论者多以‘刚毅木讷,廉公有威’八字推之;其短处,则每以‘刚愎’、‘负气’见少焉。(闻其老友王士珍尝以‘刚愎人用,气令智昏’规之)褒贬双方,均占得一‘刚’字,可见其性行实近于刚劲一流矣。”[6]4
有人认为正因其直拗的性格所以能力排众议,建成民国历史上若干功勋。“如对德宣战,采用汪精卫梁任公之意见,而于素日言听计从之徐又铮,则坚决排除其反对论,至于牺牲政权,再仆再起,终底于成。此其决心之坚,自信之笃,非真能谋国忠而任事勇者,断断无此毅力”[7],认为段氏是为国而“直”,为民族而“直”。
有些评论则认为段氏之“直”乃刚愎自用、固执己见而不用人言,“盖心所谓可,必欲达其目的,心所谓非,不惜尽排众议,段氏之习性然也。”[5]4黄炎培认为,段氏为人“刚方正直是其特性。‘言必信,行必果’二语,殆为先生一生服膺之所在。因是,其所言所行向适合于时需,有当于众意也。以其执之至固,而所获之果,其坚确每超越寻常。其或否也,以其一往不返之故,殆不免愈趋而愈远,故人之不满于先生者,辄加以一字曰‘愎’。”[8]冯玉祥也认为“段先生吃苦耐劳,廉洁自持”,但“刚愎自用,目不识人是其特短,如对有才有德之人不能合作,既不能合于王、冯、陆、曹,又不能合于黎、张诸贤。”[9]826段氏固执于自己的政治理念招致诸多批评。
除了刚直之外,舆论也多次述及段氏“沉默寡言”的性格特征,以论其“不能善全交谊”,费行简著有《段祺瑞》一书,书中对段氏的性格多有评论,他认为:
段氏厚重寡文,言笑不苟,颀颀硕人,岸崖甚高,虽弗逮东海之和蔼豁达,顾亦无官僚矜持之习,与人周旋,辞气亦循循有序,其接见僚属,繁文缛节,皆弗尚,如脂如韦者,段氏所弗与也。性行峭直,不喜面谀己,亦从不面谀人,平生折服项城,惟命是听,而对于帝制则极端反抗,袁氏猜防备至……段氏不轻然诺,有言必践,惟好同恶异,与人交,初若落落难合,至既得其信任,则终始倚之,不以人言易操也,为军事专家,外交非所长[5]3-4。
段祺瑞发迹于军旅,其身上具有浓厚的军人色彩,与一般政客的能言善辩不同,给人留下“沉默寡言”“不善交际”的印象,“以沉默寡言,于同人不好为世故周旋,故其时或戏加以‘大架子’之称,藉彰傲骨,亦可见其风采之一斑焉”[6]5。虽然不善与人交际,但舆论对段氏敢于负责的精神则颇为赞赏:“祺瑞自信甚坚,而任人亦最专,举事有失败,舆情有怨诟,均肯负其责任,不诿罪于下,其得僚属拥戴者盖多以此。”[10]
段氏离世次年,贾逸君著《民国名人传》一书,书中论及段氏,称:“段氏为一武人,民国以来,屡执政柄,惟刚愎执拗,政绩殊寡。然能不顾利害,言行一致,常保操守,亦有足多者。”[11]对段氏的品格给予了比较客观的评价。相较于政治上的成败得失,对个人品格的定位相对比较容易,即便如此,因个人色彩的掺入有时也加大了人物评价的难度,对段祺瑞性格中“直”的理解就反映出这一点。
二、“毁誉一身”:段氏政治作为的舆论品评
段祺瑞在民国时期即享有“三造共和”的美誉,舆论认为他“对于中华民国的关系之大,为孙中山先生及袁项城以外之第一人”[12]。段氏自追随袁世凯小站练兵开始,历经清末民初的时代更迭,屡居要津,由陆军总长到国务总理再到临时执政,经历了北洋由崛起到沉沦、由盛转衰的历史轨迹。正如费行简所言:“夫段氏以北洋军阀之巨擘,改革以来,首总戎机,历膺揆席,自项城以迄东海,为民国总统者虽已四易其人,而当国最久者无过段氏。”[5]2然而,誉满天下,谤亦随之,正因其一言一行动关全局,其功劳与过失往往透过舆论得到无限地放大,正如报纸所言:“毁誉功罪,宜盖棺而论定,顾于氏,未许执一论之。”[13]
段祺瑞曾赴德国学习军事,回国追随袁世凯小站练兵,在新军的创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凡属北洋军官,半出段氏之门”[5]6。辛亥革命爆发后,段祺瑞率军镇压,他顺势向清廷提出逊位主张,虽然袁世凯隐然操控时局走向,但段祺瑞仍被冠以“共和元勋”。舆论称:“辛亥革命,领袖北方军人,首赞共和,促成和局,功在国家。”[7]
民国建立后,段祺瑞长期担任内阁要职,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和反对袁世凯称帝方面段祺瑞的表现尤其得到舆论称赞,“民四中日交涉,氏长陆军,力主硬论,袍泽景从。冀鲁之交,明修战备,征调繁忙,英使朱尔典至以为忧,而日方怵于局势之严重,最后通牒,遂将第五项之要求除外,危机一解。此中枢纽,系于段氏之反对态度者甚大。”[7]袁世凯称帝,段祺瑞称病不出,“顾以推翻清室,曾任首倡,效忠民国,义无携二,坚持反对,不受劫持,蔡松坡之卒能成功,黎宋卿之终获正位,微段氏之力不至此。”[7]
段氏之功最为舆论所称道者,为马厂誓师与参加欧战,“马场之役,再造民国,厥功尤伟”[12]。《秦风周刊》称:“段氏为北洋宿将,实力尽在掌握,从根本上加一痛击,才能肃清辫军,再倒清室,成共和重建之功,维民国一线之命。”[3]舆论对段祺瑞力排众议,坚持加入欧战也评价甚高:“欧战之起,国人眩于德意志之兵精械足,以为胜利可操左券,主张附德者甚多,国会议员之争此者尤众。”但是段氏“力排众议,毅然决然,力持对德宣战,不可不谓为有特识也。不可不谓为公忠以体国也。非然者,则九一八之祸,或将早见于十余年前乎?”[3]
舆论总结段氏的政治过失,集中在“武力不能用在对内”和“群小足以亡国”两点[14]。一战期间,段祺瑞向日本大举借款,“旋因国内多事,移用殆尽,为世诟病”[15]。所借款项并未用作国计民生,而是借“参战军”之名义培植私人势力,致力于武力统一。舆论对此批评道:“欧战方酣,列强未暇东顾,日本之在远东,俨然成为独占势力,段氏之对国家民族,吾人虽可信其无他,当时之主张亲日,亦为势不能避。独其左右人物,即所谓安福派者,则攘利营私,未能顾及国家百年久远之计。”[3]段氏另一过失为所用非人,安福派以段祺瑞为魁首,“安福系当国,的确是外患之媒,他招致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更大的侵略”[16]。此外,安福系的政治作为也颇受舆论指摘:“安福派为国人诟病,而段氏则多方袒庇,此则其性情刚愎之处,而贻祸于国家者也。”[3]
对于段氏的过失,舆论大致采取了相对宽容的态度,认为他“数度柄政,虽治绩不及殊勋,而功远超于过”[12]。而且段氏之功绩带有“民族意义”,“无论其功业之大小,亦无论其功业之成败,必为当世讴歌,后人称诵”,“无论其当时之用心何如,事后之影响何如,时日渐移,情势稍迁,其求谅于人也易,其获誉于时也速”[1]。舆论各方亦为其过失开脱,认为与其性格有关:“其刚劲之性,不宜于纵横捭阖之政治生活。”[7]此外,段氏屡次当国,但并不长久,其原因在于“牵于时会,非有逼逐”[17],“其周旋于袁黎冯徐之间,历秉国钧,时就时去,政治上迄未能毅然有所树立,则恶劣之环境使然也。”[4]
段祺瑞逝世后,黄炎培撰有《敬悼段芝泉先生》一文,“自谓甚精彩”[18]。他认为段祺瑞作为军事人物则有余,作为政治人物则不足,“如先生者,苟终其身为军事首领,平时本其至贞之德操,至高之位望,猛虎在山,百兽震慑,一言一动,挽救国家危局而措之于安,一旦对外作战,其功名必不在卫霍下……惜乎其生在今之中国也。今之中国,苟其人系物望者,非尊之为行政首领不可”,而“中国首领,自袁世凯以来,非尽不才也,非尽无能也,只以地位过于其才能,脰绝而鼎亦覆。”同时,他认为用人不当是段氏一大缺点,“先生用人,限于其所亲信,非亲勿信,非信勿用,而又以秉性强固,勇于负责之故,凡左右所为,先生必举其所不必负之责,不当负之责而尽负之,以其一身集万矢而不辞,而先生殆矣。”[8]
段祺瑞作为北洋派代表人物,其逝世昭示着北洋势力已日薄西山,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因此难免激起舆论的悲凉之感。有舆论感慨:“北洋军人中三大首领,自袁世凯,冯国璋谢世以后,段祺瑞不能不说是鲁殿灵光的一个了。今亦溘化,如为安福系设想,似不免有‘树倒猢狲散’之概。”[19]预言段祺瑞逝世会引起北洋势力的内部分化。正因段祺瑞为北洋耆宿,享有崇高威望,“许多北籍将领,至今仰为圭臬”,段氏拥护统一的态度成为国民政府宝贵的政治资源,舆论哀叹:“段氏殂谢,在目前时局,实为一大损失。”[7]
段祺瑞逝世后,如何继承其遗志亦成为舆论讨论的焦点,有的主张政治人物要以之为鉴,“当国诸贤,念段氏之往事,知法戒之昭彰,对于国家民族之挽救,则取其长,对于用人行政之大端,则弃其短,斯则段氏千古,而后之人亦可以有功而无过矣”[3];有的大声疾呼军人以段祺瑞为榜样,振作民族精神,重塑国魂:“今国势陵夷,冀察已濒边防,段公昔日旧游之地,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感,燕赵武装同志,于段公风节,果能深体力行,振作军人之魂,挽救国族之厄,哀念老成,不忘元宿,尤当于此国家勋臣盖棺之日,益自励其民族国家之信念,坚贞其卫国守土之大节,是尤纪念段公之极大意义,不同于寻常之哀吊者矣。”[1]
三、“盖棺殊难论定”:段氏之死的舆论分野
段祺瑞逝世的消息传到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即刻从南京出发,3日晨抵达上海,由淞沪警备司令杨虎陪同,未作休息,直接前往段宅祭拜。林森谈到:“保家始能保国,保国始能保家,二者有不可分离之关系,国人固有之传统观念,视家为重,视国为轻,殊不知无国何以为家,此种传统观念,实属错误。”[20]林森在祭拜段氏之后谈论家国关系,实有深意。紧随林森之后,行政院长蒋介石派上海市长吴铁城代表行政院前往祭拜并致唁电,称:“昊天不吊,丧我元勋,木坏山颓,弥深痛悼。”[21]行政院各部长官如孔祥熙、蒋作宾、张群、何应钦等也一同发唁电追悼。11月3日,行政院会议讨论“段祺瑞褒恤办法”[22]。11月5日,国民党中央常会议决段氏死后褒扬办法,颁令:
前临时执政段祺瑞,持躬廉介,体国公忠,辛亥倡率各军,赞助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洁身隐退,力维正义,节概凛然,嗣值复辟变作,誓师马厂,迅遏逆氛,卒能重奠邦基,巩固政体,殊勋硕望,薄海同钦,兹闻在沪病逝,老成凋谢,惋悼实深,应即特予国葬,并发给治丧费一万元,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示国家笃念耆勋之至意,此令[23]。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为宣扬段氏的功绩与精神,以段氏逝世之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声势颇为浩大的宣传活动,“以段氏功在民国,特通令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一天,以志哀悼”[24]。除政府大员、社会名流陆续吊唁之外,段氏大殓当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介石特派代表吴铁城等亲自执绋送别。国民政府此举,一方面彰显对段祺瑞本人的尊重,树立自身不计前嫌的宽容形象,另一方面也有借重段祺瑞的政治影响笼络北洋势力之意。
国民政府对段氏的褒扬深刻影响了舆论的走向,一些在当时颇有影响力的大报,如《中央日报》《大公报》《益世报》等对段祺瑞逝世的报道中明显采取了“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立场,其报道大多表彰段氏功绩,对其过失或一笔带过,或隐而不提,认为“察其心迹,情有可原也”[13]。
1933年段祺瑞受蒋介石之邀,由天津南下,寓居上海,这被时人视为拒绝与日本合作、保持晚节之举。舆论对此大事渲染,《时事新报》认为:“三年之前,谋我者于关外设傀儡之外,复拟于平津树立所谓华北政权,以氏之尝负一时一方之重望而尤朴厚可使焉,酝酿拥氏,氏乃扶杖而南,遂止于上海,以修其生,此其晚年之大节,国人所不应忘而应致敬者也。”[13]《大公报》也认为:“年来外力内侵,平津形势日趋险恶,第二第三傀儡之剧,时在敌人计画制造之中,芝老垂暮之年,不辞远徙,游处沪滨,藉明其超世出尘之志,是又晚节之可嘉者也!”[4]
这些主流大报从当时国内外形势出发,营造段祺瑞逝世前忧国忧民的形象,藉此唤起国人的危机意识,诸如“忧心国事,旧疾复发”等字眼屡屡见于报端,《大公报》报道称:“芝老年龄虽高,但平时身体尚健,对于国事,尤为关怀,每日必浏览报纸,至触目惊心处,恒废报长叹,最近中日交涉日趋紧张,北方情形,更见黑暗,芝老本为有心人,目击外患日亟,国事阽危,愤恨之余,致肝火上升,旧疾复发,芝老平时对人言,恒谓国家将亡,此身何惜,已早置生死于度外,故此次旧疾复作,亦不以为意,讵知刺激太深,竟致不起。”[25]认为段祺瑞死于忧心国事,使其高大形象进一步升华。
相较于大报对段氏过失的隐而不发,一些受众相对较小的报纸的报道则相对灵活,认为段祺瑞“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特今当新逝,政府善善从长,不妨略过推功耳”[10]。有些报纸对段氏拒绝与日本合作,寓居沪上也相当赞赏,但其立足点为以段为戒,“对于国家民族之挽救,则取其长,对于用人行政之大端,则弃其短,斯则段氏千古,而后之人亦可以有功而无过矣”[3]。
日本侵略者扶持建立的伪满洲国对段祺瑞逝世也十分关注,但与关内报道的口径截然相反。《盛京时报》以《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在沪溘然逝世》为题,介绍段氏一生行迹,其褒贬之意跃然纸上。数日后,该报刊登《中国政治的特征》一文,称中国政治“第一特征便是军阀政治。军阀政治,就是暴力政治。暴力政治,就是压迫政治。中国数十年来。无论一时执政者是武人抑是文人。政治都千篇一律的是军阀政治”。在此基础上,该报声称:“北伐以前,北洋军阀所属之北洋官僚系统,尽为革命的敌人。”[26]伪满洲国另一份刊物《大同报》于11月11日发表题为《论段祺瑞及国葬》的社论,采取“先扬后抑”的手法,先赞扬段祺瑞“勋猷彪炳,声名洋溢,方其盛时,军阀政客,翕然宗之,物望攸归,悉尊前辈”,然后话锋一转,对段祺瑞“三造共和”之功,一一予以驳斥:
以言建造共和,初特藉总军师,内结巨奸之袁世凯,外联尝试之黎元洪,党恶要君,肆志攘夺,维时民智,本不足以自主,乃遽剽虚声,躐级改革,名为共和国体,实则暴民专利,卒堕袁氏彀中,遂启洪宪僭窃之机,虽能于此毅然勇退,反对决绝,后复出任艰巨,收拾残局,而自斯以往,国内分裂,军阀割据,战乱频仍,日无宁息,整理统一,终付梦想,是徒骛共和之名,致酿多数暴民专制之祸,为害之烈,不可胜言,功耶过耶,其实果安在耶?段之与袁,积年相处,而不知其奸恶之不可及,而为所舞弄,夫岂智明之所为哉?至马厂誓师,则亦不过乘时崛起,藉攘政权,而所以善其后者,卒亦未见整理统一之效,且酿成直皖之战,参战军之精华,空付虚掷,伤残国本,责有攸归,此三造共和之赫赫大功,盖仅如是焉而已,使果具有不世之略,则民国十余年间,数总阁揆,兼长军政,顾不可经文纬武,整理统一,卓著治绩之效耶,而卒未也,其能事盖可知已[27]。
对关内舆论颇为诟病的段祺瑞与日本的关系,《大同报》则大加赞赏,“其政策夙主中日合作之见地,亦堪称超越,为他人之所不及,如所实施之中日共同防敌协定,及军械参战交通铁路等等借款,皆以改善或兴造国家之有利事业,于斯不能不佩其眼光之远大,超出寻常万万也”。此外,该报渲染蒋介石与段祺瑞之间的嫌隙,蓄意挑拨,可谓用心良苦:“数年以来,蒋氏对段,猜疑防闲,无所不至,隐居津沽,犹恐有异,用尽忮心,徙之沪上,密侦环伺,不啻监守。”对于国民政府隆重的临终饰典,《大同报》认为:“矫揉作态,若深哀悼,率请国葬,示崇异数,岂欲以双手尽掩天下之耳目耶?”“使其任处津门,优游自养,或犹有余年,亦未可知,今其死也,谓有以促之盖无不可。”[27]暗示段祺瑞逝世与国民政府脱不开关系。伪满洲国舆论的报道折射出日本侵略者强烈的政治意图,正如戈公振所言:“近二十余年来,日人所办之华字报,如《顺天时报》、《盛京时报》等……借外交之后盾,为离间我国人之手段。”[28]
对于段祺瑞的评价也受个人立场与关系亲疏的影响,冯玉祥与段祺瑞之间纠葛甚多,段氏编练新军时冯即在他手下任职。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冯回师倒戈,发动政变,与奉系妥协,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执政府,后又遭到奉、晥双方排斥,就任西北边防督办。虽时过境迁,但这段复杂纠葛仍萦绕心头,冯玉祥认为:“执政再出,听张而不尊孙中山先生,信吴、贾而大杀‘三一八’之学生,使国民军不能站立于北京,致使国家正气损失殆尽。”[9]827对这段陈年旧事仍无法释怀。同属北洋遗老,曹汝霖与段祺瑞渊源颇深,在回忆录中对段祺瑞逝世前的情态细致刻画:“闻病笃自知不起,犹倚枕草遗嘱,寄望于蒋先生,拳拳为国,语不及私。尤于希望和平,培养国力,力图团结,以防共祸,更三致意焉。”[2]308可见,个人之好恶,关系之亲疏同样影响了人物评价。
四、结 语
韩愈说:“行矣且无然,盖棺事乃了”,然而对于那些动关全局的人物来说,其盖棺而论定却显得并不那么容易。以段祺瑞为例,一方面,段氏“功满天下,过满天下,毁誉丛集于一身”[3]。这种是非功过的复杂纠葛本身就给人物蒙上一层“面纱”,使其历史地位殊难评价,后世论者也莫能执一;另一方面,面临变局,时局的变化也能“障人耳目”,对论者产生影响,而后人自身所处的立场与态度,也会对时论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以历史的后见之明观之,这些品评都带有了评论者的主观色彩,而人物真正的形象却因历史的尘埃而逐渐黯淡,因此,给人物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何其难哉,真正要做到盖棺定论,“尚有待于千载下焉”更并非虚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