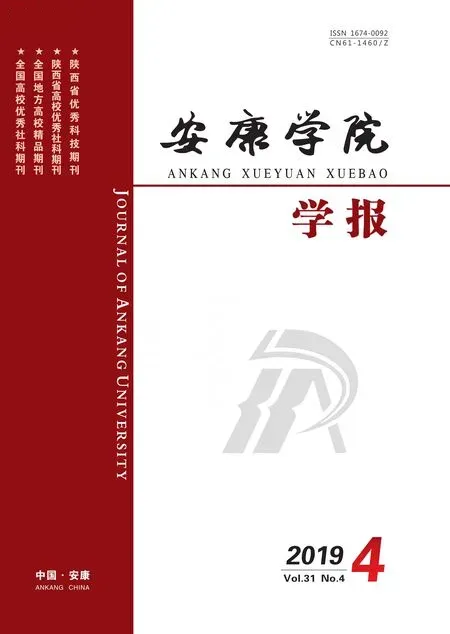守与变:桐城大师吴汝纶的文学传承与超越
张凤云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吴汝纶作为桐城派代表人物,不仅是一位著名的学者、文学家,更是一位教育家。他在教育界建树颇多,开风气之先,积极倡导引进并身体力行地传播西方文化。吴汝纶与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被称为“曾门四弟子”,是曾国藩后桐城派最重要的传播人员。很多学者认为,在四弟子中,以吴汝纶的成就最大。姜书阁曾言:“曾派中年最高而享名最盛者,莫过于俞樾、王闿运、吴汝纶三人。”[1]关爱和与之持相同的观点:“曾门四弟子中,对桐城派的发展给予较大影响的是吴汝纶。”[2]由于吴汝纶较其他人最晚去世,因此学界有时将其称为“桐城派最后一位宗师”或“桐城派—湘乡派古文家最后的大师”。同治光绪年间,西方侵略不断加剧,国家命运摇摇欲坠,新文化对旧文化的冲击、贬低,都使桐城派古文越来越步履维艰,走向穷途末路,于是吴汝纶起而守护,以重振桐城文学为己任,志在恢复气清、雅洁的文学传统,维护古文体系。
一、提倡体清气洁、清真雅正
道光二十年(1840),吴汝纶生于安徽桐城。桐城是一个文化风气浓郁的地方,文人辈出,“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已流传甚久,吴汝纶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以身为桐城人为傲,对桐城古文充满了自豪和敬仰。面对日益见衰的桐城文学,他后来在《孔叙仲文集序》中说:“汝纶窃自维念,幸生桐城,自少读姚氏书,姚氏支与流裔在天下,有振起而益侈大之者,而乡里后生,卒鲜得其近似,闻公言,则矍然而惧”[3]55。生为桐城后人,吴汝纶表达了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立言要传承桐城文学。后来很多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吴汝纶有意恢复桐城派文学的志向,如关爱和在《桐城派的中兴、改造与复归——试论曾国藩、吴汝纶的文学活动与作用》一文中从三方面说明吴汝纶对桐城派的复归与维护,并得出结论说:“吴汝纶实在是有意识地恢复以气清、体洁、语雅为特色的桐城派文”[4]。
吴汝纶《与杨伯衡论方刘二集书》中由方、刘二人的作品谈到“才、学、气”与文章的关系,提出“醇厚”优于“闳肆”的主张,从文中也可以明显看出吴汝纶的确更加倾向醇厚老确之文:
夫才,由气见者也。今之所谓才,非古之所谓才也,好驰骋之谓才……然而资力所进,于闳肆之文,尚可一二几其仿佛;至醇厚,则非极深邃之功,必不可到。然则望溪与海峰,断可识已。
夫文章之道,绚烂之后,归于老确。望溪老确矣,海峰尤绚烂也。意望溪初必能为海峰之闳肆,其后学愈精,才愈老,而气愈厚,遂成为望溪之文。海峰亦欲为望溪之醇厚,然其学不如望溪之粹,其才学不如望溪之能敛,故遂成海峰之文。[3]360
此文对方、刘的分析,说明了“才”由“气”见,但是二者都受到“学”的影响,“学”的深浅,决定着“才、气”的高低厚薄。其实在这篇文章中,吴汝纶并没有厚此薄彼,也无意让方苞、刘海峰二人之文一决高下,只是吴汝纶以此来重建一种新的文化审美方式,“学”深则气沉静,才内敛,为文醇厚老确;“学”浅则气纵横,才轻浮,行文偏于闳肆张扬。作文更高的层次是二者兼并,达到醇而能肆的境界。他曾在《与萧敬甫》中比较姚鼐和刘大櫆的诗歌,姚鼐学养深厚,作诗造诣要远高于刘,论其诗“雅洁奥衍,自是功深养到”,而刘大櫆“虽才若豪横,亦间涉俗气”,时时流露出俚俗轻浮之气。可见,他并不是反对闳肆之文,而是肯定学养深厚,然后才能醇静成熟的重要性。
此外,吴汝纶是在有意识地追求清正雅洁之文法,自方苞倡导删繁就简、清正古雅的古文宗旨后,桐城派在随后的发展中一直以行文清淡简朴、清正雅洁为文人坚守的基本原则。吴汝纶重视文学的艺术性,要求各种形式文学作品的语言文雅纯正,坚决反对俚俗鄙陋之词,认为行文采用俚俗、轻佻之语是对桐城派清正雅洁文风的极大破坏,是其万万不能接受的。后来吴汝纶借探讨严复翻译《天演论》之际,重新提出方苞传统和古文文法。
1898年,严复的译作《天演论》出版之时,向吴汝纶求序,两人就不止一次地讨论雅洁之事,吴汝纶在给严复写的信中提及:
来示谓行文欲求尔雅,有不可门阑入之字,改窜则失真,因仍则伤洁。鄙意与其伤洁,毋宁失真。凡琐屑不足道之事,不记何伤?若名之为文,而俚俗鄙浅,荐绅所不道,此则昔之只言者无不悬为戒律。曾氏所谓辞气远鄙也。[5]235
与其伤洁,毋宁失真,要求行文过程要遵循雅洁远俗,极力避免鄙浅,并教导严复化俗为雅之法。同时,他还论述了行文应重视剪裁,说:“文无剪裁,专以求尽为务,此非行远所文”[5]236,讲究文章要简洁得当。这种严格恪守桐城古文的教诲,直接影响了严复的翻译,使他在翻译过程中十分注重古雅,并提出了译文追求“信、达、雅”的准则。由此看出,吴汝纶在面对外来事物对桐城派的冲击时,仍然践行着桐城家法,坚守着桐城先人们代代传承的醇厚、雅洁的古文传统,努力保护着桐城古文的地位。
二、离异“文”“道”关系
吴汝纶在继承桐城文学的同时,并未全盘接受其传统文风,而是提出了自己独特的主张和见解,最明显的一点就是“文”“道”之关系。在吴之前,受时代风气和文学领袖主张的影响,对“文”“道”关系的解读一直在随着时代发生着变化。无论是方苞的义法说、刘大櫆的神气说、姚鼐的义理、考据、辞章说,还是曾国藩后来的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合一的理论,都始终坚持并追求着“文”“道”合一、“文”以载“道”的思想。在传统中,“文”是没有独立地位的,“文”是要为“道”服务。然而在曾国藩时期,他虽然坚持着“文道合一”的观点,但在行文中却背离了初衷,一方面重视义法,在原基础上加入经济说,要求文章发挥社会教化功能,强调文章“经世致用”的作用,更好地为封建社会所服务;另一方面,他又多次承认“文不宜说理”,提倡行文要抒发个人真情实意,有肆意纵横、酣畅淋漓之感,要发挥精神愉悦的审美功能,提出“道与文不能不离于二”,说理之文贵在严谨精当,而文学创作则追求审美艺术、奇伟瑰丽,做文与说理无法兼顾,妄想两相兼顾就会导致力不从心。然而,由于个人身份与职责,曾国藩还是比较保守,一直没有突破文以载道的樊篱。
到了吴汝纶时期,他继承了先师曾国藩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明确提出反对“文以载道”“文道合一”的文学主张,将其发展为“文道离异”。吴汝纶更加重视文学的特性,使其保持文学的艺术抒情性,将文学从原来“道”的附属品地位中独立出来。吴汝纶在《答姚叔节》中说:
通白与执事皆讲宋儒之学,此吾县前辈家法,我岂敢不心折气夺。但必欲以义理之说施之文章,则其事至难。不善为之,但堕理障。程朱之文,尚不能尽餍众心,况余人乎?方待郎学行程朱,文章韩欧,此两事也。欲并入文章之一途,志虽高而力不赴。此不佞所亲闻之达人者,今以质之左右,俾定为文之归趣,冀不入歧途也。[5]138-139
如果将义理、文章结合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方苞“学行程朱,文章韩欧”,想要达到统一,志向虽然远大,尚且是无能为力,何况我们普通人呢。在《与姚忠实》一书中,更进一步的说明了义理、考据、训诂对文章的损害:
说道说经,不易成佳文。道贵正,而文者必以奇胜。经则义疏之流畅,训诂之繁琐,考证之该博,皆于文体有妨。故善为文者,尤慎于此。退之自言执圣之权,其言道止《原性》 《原道》等三篇而已。欧阳修辨《易》论《诗》诸篇,不为绝盛之作,其他可知。[5]52
从此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汝纶又一次强调了文章不宜说道说经,“文”与“道”的行文风格是明显不同的,“文”“道”结合,必然会造成互相妨碍的后果,即使像韩愈、欧阳修这样的大家,也不能协调其中的关系,创作出绝盛之作,其他人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在“文”“道”关系上,吴汝纶坚定地向先师们提出了挑战,改变了流传甚久的文学主张,离异了原先义理、考据、辞章相辅相成的文法,突出行文以辞章为主,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吴汝纶站在一个文人的角度,提出以文人之心看古文,保存古文本身的文学特点,将古文从“道”强加的重担中解脱出来,“文”“道”分途,更加尊重文学本身的特点,强调“文”的重要性。这样大胆的主张是对传统桐城派的一次动摇和颠覆,也使得古文从说理说经向纯文学层面过渡,吴汝纶对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主张以古文载西学
桐城派作为一个文学流派,对于文学艺术的追求是不断改进、增补的,既坚守古文传统原则又充满了时代特色,它的与时俱进是桐城派长期存在并充满生命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在发展的不同时期,从方苞到吴汝纶,他们对于“文”“道”关系的解读和践行都各有所不同,在历史的大背景下,桐城派的领导者善于顺应潮流,加入了新的内容,行文主张充满了时代性。方苞生活在康雍时期,统治者推崇程朱理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此有了“学行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的行文准则,提出了“义法说”,即言有物、言有序也。姚鼐处于汉学大盛时期,文论在继承方、刘的衣钵同时又加入考据之学,来应对汉学家不断的挑战,旨在凭借考据说来开辟道路,发扬古文。到了曾国藩时期,晚清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动荡,曾在前人“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入了经济一项,即经世致用,希望能够发挥文学服务于社会的经世致用功能。到了吴汝纶时期,清王朝在欧美的入侵下愈加风雨飘摇,面对着西方坚船利炮的冲击,意识到中国要想富强,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借鉴西方教育,所以,吴汝纶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添加西学,利用古文来介绍西方知识。
清末政治危机的加深,迫使文人们重新审视传统学术的空洞无力,纷纷将眼光投向西方有用之学。传播新思想,废除旧思想;提倡新文学,废除旧文学,日渐成为学界的共识。在这种情况下,桐城古文的生存和发展,变得非常艰难。作为最后一位桐城大师,吴汝纶曾作为曾国藩、李鸿章的门僚,亲身见证了洋务运动的兴盛与失败,他眼界开阔、思想开放、善于变通,尽管作为桐城末期的中坚人物,他也并没有闭门造车、固守旧思想,将西学放在古文的对立面,而是主动向西方学习,致力于利用古文来倡导、传播实用性的西学,并希望借助西学来发展桐城古文,以改变其江河日下的困境。最有代表性的便是为严复的《天演论》作序,在这篇序文中,吴汝纶以“与天争胜”“以人持天”来概括赫胥黎的进化论思想,并以此来推介、宣传西学,而这不仅仅是因为《天演论》传播了新思想新文化,更重要的是因为严复的翻译体包含了吴汝纶的古文理想,表现了雅洁、渊茂的桐城文风。在序文中,他说:
今赫胥氏之道,未知于释氏何如,然欲侪其书于太史氏、扬氏之列,吾知其难也;即欲侪之唐宋作者,吾亦知其难也。严子一文之,而其书乃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然则文顾不重耶?[3]147
在吴汝纶看来,赫胥氏本身宣扬的道,远远比不过佛教教义,但是经由严复翻译后的《天演论》却蔚然改观,完全可以与先秦诸子相提并论,以此来凸出古文的重要性。吴汝纶将西学加诸于古文之中,在传统的内容外,拓展题材,大力引入新的思想,给陈旧的古文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使得桐城文学在新旧交替、日渐凋敝的时候,得以继续发展。
四、结语
吴汝纶作为晚清桐城派最后一位宗师,为古文的守护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既恪守醇厚雅洁,又努力变通,注入西学,从未放弃过对古文的坚持和追求,古文的创作、倡导、传播始终贯穿吴汝纶的一生。然而,就算吴汝纶等人不断对桐城古文进行协调和发展,依旧未能改变其被白话文逐渐取代的局面。欧风美雨的侵袭和新旧文化的撞击,早已使桐城文学支离破碎,古文已是明日黄花,在所难免地走到了历史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