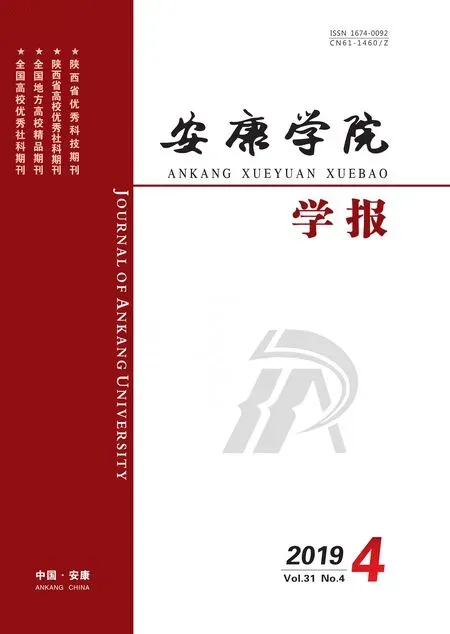论鲁迅《野草》中的复仇意识
姜汉西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野草》在阐释上一向以难解著称,其中原因除了言论和表态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外,还在于鲁迅自己极为深刻的人生体验以及对世事形势的深沉思考,也正是基于此,《野草》可供阐释的空间得到了拓展,其意蕴的丰富性和价值意义同时也得以被无限放大。在已有的研究中,大多围绕其作为鲁迅“反抗绝望”的哲学进行注解和探索,孙玉石先生八十年代初的《〈野草〉研究》以及九十年代汪晖先生的《反抗绝望—鲁迅的精神结构与〈呐喊〉 〈彷徨〉研究》是其中较有影响力的代表,他们严谨扎实的治学风格,将《野草》的内向性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同时也为后人的继续探索开辟了道路。但自新时期以来,因文化市场和文学环境的改变,导致新的批评话语和理论资源不断输入,一时间出现了西方学术话语随意介入和嵌套鲁迅研究的局面,尤其是关于《野草》的研究更是乱象百出。这种文本加流行理论的尝试固然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其方法往往是先验地从某一个基本命题出发,进而在文本中寻找支撑,最终的结果只是证明了鲁迅可以与西方的某一思想家或哲学家比肩,而作为研究对象的《野草》本体则渐隐于范式的阐述中。《野草》在创作时间上虽存在着先后的差异,但鲁迅在编《乌合丛书》时能够把这些作品辑录在一起,在一定程度上就说明了《野草》的相对独立性和系统性,而这也要求我们对于《野草》的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具有自足性的文本分析上,同时辅以严谨精密的考证推理、敏锐的文字感受能力和丰厚的人生体验阅历来对其进行更为深层次的阐释。
复仇是对过往的一次集中清理和整顿,同时还是对自我未来方向的一个追求设定,更是一种带有暗示情绪的激励和督促,一种充满了内在机制的自我调节和改变。由于复仇动机、复仇手段和复仇对象的不同,在简单的“复仇”二字背后包含了太多的关乎民族、国家和社会以及社会中的个人等多重主体的丰富内蕴。在鲁迅的《野草》中,“复仇”是一个无法忽视的关键词,在为数不多的二十几篇作品里,就有两篇直接以“复仇”为题,凸显出复仇的中心价值,更有多篇则是在文中书写复仇故事或流露出复仇的意味。可以说这样的一本《野草》是被浓浓的复仇氛围所笼罩的,其中充斥了大量的复仇气息。复仇可以是一个具象的身体行为,也可以是一个具有隐蔽性的精神活动,但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复仇,其指向的终极都有着相似的地方。《野草》中的复仇表现为不同的形式,或隐或现,或明或暗,而将它们纳入一个统一的平台和体系中加以考量,则有助于走近《野草》中自成系统的鲁迅精神,进而以此为径把握鲁迅精神整体性。同时在思想互证和文本互证的基础上,梳理出鲁迅精神的生发以及其内在性的延伸与拓展过程。
一、对立:消解“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
在鲁迅的作品里,看客是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他们大多是深处社会的底层,是被侮辱和被侵害的对象,饱尝了人世间的温情冷暖,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塑造了他们特有的性格特点和精神品质。在鲁迅的《朝花夕拾·藤野先生》里,他们就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日俄战争期间,一部分中国人给俄国人做侦探,被日军捕获后马上要枪毙了,而同时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于是鲁迅先生坦言:“但在那时那地,我的意见却变化了”[1],而这个变化正是其一生重要的转折点——从医学上救治国人身体上的痛苦到从文学上唤醒民众之觉醒的开始。而必须重申的是,这里的看客只是录影带上的形象,归国后在古老大地上所呈现的景象更加令鲁迅悲愤,《彷徨·示众》可谓是其中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作品,直接将这样一群“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的群体作为书写的主体,直击庸俗看客的病态心理和丑陋形态,其中如是写道:“刹那间,也就围满了大半圈的看客,待到增加了秃头的老头子之后,空缺已经不多,而立刻又被一个赤膊的红鼻子胖大汉补满了。这胖子过于横阔,占了两人的地位,所以续到的便只能屈在第二层,从前面的两个脖子之间伸进脑袋去……但是后面的一个抱着孩子的老妈子却想乘机挤进来了;秃头怕失了位置,连忙站直……”[2]。无孔不入的看客,实际上构成了其空虚和无聊的作证,而这也正显示出了对大众进行精神启蒙的迫切性。
看客们的围观和凝视,其实在行为本身上具有一种鉴赏的性质,那些被示众的和被杀害的个体和群体正是他们赖以进行评头论足的材料,这种鉴赏是残忍的,同时又是可怕的。在《野草》中,复仇首先就表现为对庸俗看客鉴赏过程愉悦性的阻碍,具体则是通过赤身裸体和永久的对立,在长时间的“将要拥抱,将要杀戮”中,使得看客们的心理预期得不到应有的满足,由此造成的失落感构成了复仇的意义。在《复仇》中,鲁迅毫不留情地揭示出了个体不自主和不独立,鲜血是温热的,“于是各以这温热互相蛊惑,煽动,牵引,拼命地希求偎依,接吻,拥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由此提出了国民主体性的建构问题。个体在社会中无法生存,于是只有依靠他人和集体的力量赖以维系,但是个体身上所具有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一旦借以大众数量上的优势,便获得了一种集体心理,同时他“有意识的个性将被群体的无意识人格所淹没”,从而表现为“完全受一些无意识的因素控制,并且服从于一种独特的集体逻辑”[3]。于是“路人从四面奔来,密密层层地,如槐蚕爬上墙壁,如蚂蚁要扛鲞头。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从四面奔来,而且拼命地伸长脖子,要赏鉴这拥抱或杀戮。他们已经预觉着事后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鲜味。”然而已经被看客们所包围的两个人却并没有如众人所想象的那样,“他们俩对立着,在广漠的旷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拥抱,也不杀戮,而且也不见有拥抱或杀戮之意”,于是路人们觉得无聊,喉舌干燥,并终于走散,而广漠的旷野上的两个人“以死人似的眼光,赏鉴这路人们的干枯,无血的大戮,而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4]172-173,完成了一次酣畅的复仇。
在《复仇》中,“生命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被多次叙述,而它即是“路人们”以看旷野上对立的两人的杀戮或拥抱而得到“赏鉴”满足后的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同时也是对立于旷野上的两人在赏鉴过路人们的干枯后得到的自我满足,由此实现了“戏剧的看客”转变为被“示众”的材料,而这一颇具讽刺和象征意义的转换,也正显示出了鲁迅思想中尖锐的现实批判性以及对国民性的深入思考。正如孙玉石所言:“复仇的人生哲学,是鲁迅出于改造国民性思想而对于麻木群众的一种愤激批判情绪的升华与概括。”[5]这说明《野草》的绝望已不是针对原来意义上的敌人,而就是被寄予无限同情的庸俗大众,正是由此庸众成了《野草》中绝望的中心情结,同时也正是在对他们的带有讽刺意义的批判和复仇上,消解了其“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而使得启蒙者获得了“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二、选择:“惟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
当代学人汪卫东根据自己多年的研究,将《野草》置于鲁迅生命发展的历程中加以考量,并进而提出了鲁迅生命中的“两次绝望”这一概念,第一次绝望发生在日本求学期间,主要指向的是对自身行为能力的怀疑,而第二次绝望则是以1923年的沉默为标志,于是他提出了:“《野草》,与其说是一个写作的文本,不如说是20年代中期鲁迅陷入第二次绝望时生命追问的一个过程,一次穿越致命绝望的生命行动,它伴随着情感、思想和人格的惊心动魄的挣扎与转换的过程”[6]。其实在经历了声嘶力竭的“呐喊”后的鲁迅,一方面是对启蒙对象的可启蒙性产生了动摇,认识到“非‘用刺刀割开’他们的魂灵,用净水来好好地洗一洗,这病症是医不好的”[7];另一方面是对自我的反思,正如鲁迅自己所说:“我虽然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8]。而当他真正进入《野草》写作后,在以往所形成的新的认知和重塑的精神特征上都有了较大的飞跃与提升,其中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对自我的反思与追问,或者可以称之为内向性的绝望,这种转变是长期痛苦和绝望的结果,也是无奈中的选择,但却在无意中将鲁迅的精神困境引入到了一个更深层次的探索,于是“反抗绝望”成了其精神的核心和意志的符码。他以特有的执拗切入对自我的审视,对纠缠于身的诸多矛盾进行了彻底地展示和梳理,并作出了干脆的决断,走进“惟黑暗和虚无乃是实有”的现实生活,展开了反抗绝望的实践上的努力,拒绝在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氛围下使生命消殒,其实这种选择本身就构成了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复仇行为。
《过客》是《野草》中比较特别的一篇,以一种存在主义式的戏剧展示了老翁、女孩和过客之间具有辩难性的对话。三个人在对过客的去向和未来的选择上所产生的分歧,一定程度上是可以代表书写主体的内在矛盾性的,而同时三个人也代表了现实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群所抱有的三种基本立场和态度。在过客对前方进行追问的时候,女孩心目中的野百合和野蔷薇是一种对未来的美好想象,表达出的是一种希冀和理想,这正是符合其身份和年龄的。而老翁的坟的回答,则是一种痛苦的失望和无奈,甚至是绝望,预示了必然的死亡。但他们两个人都带着极强的生命体验去给过客提供参考,并表达出自己强烈的主观认同感,无疑会对现实的真实性和客观性造成一定程度的遮蔽。而过客说:“从我还能记得的时候起,我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我接着就要走向那边去,(西指)前面!”[4]190这种近乎玄奘西行求取真经的行为选择正是反抗绝望的核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置之死地而后生。这样的一种不是以最终的胜利或希望为目的的追求,只是在朝着一个方向做出无悔的选择,在《影的告别》中同样有着一以贯之的精神血脉。
我们常说如影随形,影子从其自主性上来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傀儡,根本无法掌控自己的选择和去向。然而无论是“天堂”“地狱”还是“你们将来的黄金世界”,影子都发出了“我不愿去”的呐喊,即便是彷徨于无地,将得到“虚无”,也要与这个外在的已经厌弃的身体彻底告别,来一场具有革命意义的决断。当然影子也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影,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然而光明又会使我消失。然而我不愿意彷徨于明暗之间,我不如在黑暗里沉没”[4]166。明和暗之间是影子可以暂时栖身的场所,但终于还是给自己来了一个决断,影虽然固执地选择了诀别,但这并不是逃避,反而是独自承受了一切的黑暗与虚空,正如鲁迅自己所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9],影也以这种近乎惨烈的方式结束了自己非生非死的存在状态,与现实的一切彻底决裂,选择了“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4]177。一种选择的作出同时意味着另一种选择的放弃,正是选择的坚定和果断带来了复仇的快感,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将鲁迅反抗绝望的精神推向了极点。
三、涅槃:永不停止运行的“地火”
启蒙者是一个时代的良知,对于现实生活和当前处境具有超越性的真知灼见,固然可以成为社会中的领航者和开拓者,但其思想中的先锋性也同时会招致周身的诽谤、误解甚至是报复。因而在一种近乎“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氛围下,作为启蒙者的主体在不断的失望中终于认识到“在寂寞之世界里,虽欲得一可以对垒之真敌人,亦不易也”[10],于是就会将矛头由庸俗大众和社会环境转而指向对自我的深思,展开对自我的审视,甚至是自虐自厌式的灵魂拷问。这是一种由外而内的自在性过程,而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自我的矛盾和分裂空前集中,由此对自己的过往生命才有了回顾与整合的可能,旧的自我得到了有效地展示和分析,而新的价值立场和思想准则也在此期间酝酿并形成。
在鲁迅的“野草”时期,《复仇(其二)》同样是其中比较特别的一篇,其独特之处在于借用了西方圣经中的故事加以现代的演绎,这一点与他后来《故事新编》的创作模式和叙述方式颇有相似之处。但我们更为关注的是其中所贯穿和表达的情结以及强烈的精神诉求,“因为他自以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钉十字架”,简单的一句话交代了事情的原委,曾经给大众带来福祉和希望的耶稣,此刻被悬在虚空中,“路人都辱骂他,祭司长和文士也戏弄他,和他同钉的两个强盗也机巧他”,而且“四面都是敌意,可悲悯的,可诅咒的”。曾经的启蒙者身陷困境,遭受着难堪的侮辱,无法继续其启蒙的使命,但他并没有表现出痛苦,反而是以苦为乐,欣赏大众在其面前所呈现出的罪恶,“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悯的人们的钉杀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诅的人们要钉杀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4]174-175。耶稣通过身体的受难和精神的沉酣而接近上帝,在身体上感受痛苦、在精神上成就自我的过程中获得了人格意义上的重生,实现了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因此这里对于痛苦的承受,固然有孤独的启蒙者对于麻木大众的悲剧性思考和蔑视性复仇,但同时也转入到了启蒙者对于自我的深思与反省,将外在的求全与内在的完善臻于一体。
启蒙者与大众之间是一个传播与接受的关系,但是在《复仇(其二)》中很明显对传播和接受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而在《颓败线的颤动》中,则同样提出了启蒙者的“自食其果”后的自厌情绪。《复仇(其二)》中的耶稣,目睹着以色列人的以怨报德,在生命的最后关头尚且喊出了“以罗伊,以罗伊,拉马撒巴各大尼!”。但在垂老的女人那里,面对着来自亲人的“冷骂”和“毒笑”,只有在“无边的荒野”中“尽走”,继而“举两手尽量向天,口唇间漏出人与兽的,非人间所有,所以无词的言语”[4]206,最后“并无词的言语与沉默沉绝”,而她那如点点鱼鳞的“颤动”也终于成了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形象。很明显可以看出,老女人身躯的“颤动”是带有猛烈的反抗意味和复仇情绪的,当然其矛头指向是双面的,而更多的还是在于自我认知清醒后的无话可说,以及“欲辨已忘言”的落寞,但无语并不是虚空,无词的言语和颓败的身躯的颤动,共同构成了“暴风雨中的荒海的波涛”。一心付出的启蒙者成为了被启蒙对象眼中的敌人,也就从根本上消解了之前所有的期望和努力,于是自己就要为自己的过去承担所有的罪责,默默忍受着来自过往所招致的后果,这也就成了启蒙者最后的收获。由此启蒙者所秉持的对大众的责备进而转向自我的拷问,新我的诞生对旧我的存在构成了挑战,正像那运行不息的“地火”开始了“奔突”,继而“喷出”,并且“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得到“无可腐朽”[4]159。
四、结语
复仇是一个对过往进行清理与整合的过程,有着极为强烈的情感色彩,充满着快意与欣喜,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复仇,更为深层次的复仇还表现为由复仇所带来的对人生与世事的思考,以及由复仇所牵引出的自省自悟以及对自身价值与立场的重新认识。鲁迅的《野草》创作虽然在时间维度上并不统一,其内容和形式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复仇情绪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精神脉络,除了以上所分析过的篇目外,像《狗的驳诘》 《死火》和《墓碣文》等篇章中同样氤氲着复仇的气息。而在以复仇来对《野草》进行整体性的概而论之时,我们发现在鲁迅的思想中,其所复仇的对象并不是固定和唯一的,而这正显示出作为民族战士和思想家于一体的鲁迅思想上一个内在的变化过程,从对黑暗现实所表现出的决绝以及对生活于其中的大众的失望,再到对自我的拷问与反思,在《野草》里我们看到了鲁迅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拐点,也可以说正是借助于《野草》这个平台,鲁迅由对外在的关注开始了与自我的对话,从而正视自己存在的意义和价值,直面“虚无”和死亡,与过往彻底告别,在绝望中进行反抗绝望的斗争,为反抗而反抗,在自我的超越和解脱中“得到生命的飞扬”,并且“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