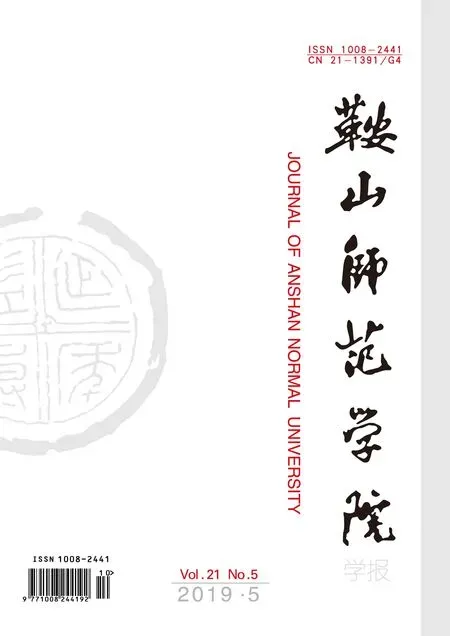论嘉靖后期辽东将官贪懦与边患
张晓明
(鞍山师范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1]。”嘉靖时期,明廷失策,纲纪不修,加之鞑靼蒙古势力寇边,辽东社会深受其害。在明廷不良政治气候影响下,辽东军政体系亦出现衰败迹象,其中以边将贪爆、怯战最为明显。
一、嘉靖时期辽东将官表现
嘉靖皇帝“御极之初,力除一切弊政,天下翕然称治[2]。”明廷任命一批为官清明、专心边务的官员为辽东督抚,以图革新军政系统中的贪暴之风,进而扭转蒙古诸部大举入寇、杀掠人畜的被动局面。正德时期,“祖宗之纪纲法度一坏于逆瑾,再坏于佞幸,又再坏于边帅,盖荡然无余矣[3]。”辽东边地官员疏于管控,蒙古部族牧区深入边内,边关连年失事。辽东将官滥杀放牧人冒领军功的行为致诸部“愤怨报复,为患不已[4]。”正德十六年(1521)七月,参将孙堂因率兵掩杀速长加等部二百余人而获功,巡按御史劾其贪不法,请有才望着经略战守。兵部以“辽东军饷不给,将领非人”,令巡抚都御史李承勋练习边事,谕辽东守臣于农隙时“责才能吏”修浚边墙、巩固墩台[5]。同时诏令“让其寇边之罪”,缓和边地民族矛盾[6]。嘉靖元年(1522)二月,户部郎中马应龙奏报应急择将领恢复边地秩序。辽东巡抚李承勋“沉毅果断,有经济大略……当表败之余,推循疮痍,措划战守,东土以宁”[7]。明廷许令辽东或进行招募或摘选卫所余丁组建新军,武将统领操练,扼守险要,广宁、开原、辽海三线防务有所改善。嘉靖十三年(1534)六月,兵部尚书以“军伍多缺,宜量地方缓急,招募土军”。明廷批准辽东招募二千人[8]。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明廷于海、盖二城附近卫所摘选舍于丁壮加之原军合六千人,每城分拨三千。五月,辽镇宁前义州城堡新增募军三千二十九名[9]。至嘉靖中期,辽东边墙东北段之抚安(铁岭市东大甸子镇)、新安(凤城市东北石城镇)、松山(开原市东南松山堡乡)、三岔河(铁岭市东南横道子乡)、靖安(尚阳堡,今开原市东清河区)、镇北(今开原市东北威远堡镇)等要冲虽有虏情,但官兵能主动出击且多有斩获之功,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边地的安全。
明朝初年,朵颜在山海关以西,古北口以东,蓟州边外驻牧;泰宁在广宁境外;福余在开原境外,辽河左右驻牧。嘉靖后期,蒙古左翼(东部蒙古)小王子打来孙部侵驻三岔河,泰宁部屡与仇杀,后避入夹墙。在明廷的招抚政策下,兀良哈三卫头目都督等官虽每岁自喜峰口入贡如常,但其活动空间与东蒙古诸部交集颇多,在蒙古势力对明廷北疆高压未除、辽东防御力量不足的情况下,朵颜、泰宁等部常偕东蒙诸部犯辽。嘉靖二十年以后,蒙古诸部多合势大犯开原、锦义等地,建州女真亦开始反侧入寇边关。辽东将官在抵御蒙古寇边时虽有斩获,但虚报战功时有发生。嘉靖二十年(1541)六月,兵部尚书张瓒等言:“今辽东开原报有虏万余,踪迹(开启衅端)颇露”,命巡官御史协同总兵官从宜抚谕之余整饬边备。辽东锦、义、宁远地方兵力单弱,宜再选所部精兵付之才将。同月,参将刘大章等与寇边蒙古人战于大康堡(锦州市北义县头道河乡)。皇帝嘉奖此战过程中,总兵李凤鸣欲掩其失仅报以大捷[10]。嘉靖二十一年(1542),“建州达贼从凤凰城入寇,杀守备李汉、指挥佟恩等,所过掳掠无算。总兵官李凤鸣、副总兵刘大章及巡抚孙禬罪俱宜治[11]。”嘉靖后期,辽东边将的贪爆怯战已成风气,明廷虽对此严加整饬但收效甚微。嘉靖二十八年(1549),明廷核查上年十二月“虏犯辽阳”时诸将功过。巡抚都御史李钰以“杀虏至万两千余人,亡失不算”等表面之功报捷,但经查“去冬虏众不满三万,我兵亦是相当。且虏雪深失道,尤易控制。乃诸将相视不发,致贼深入……”[12]巡按御史李钰解官;总兵李琦按兵纵寇,攘级冒功,被革都督职衔,以留察看;暂代副总兵、闲住游击王言闻警不趋,叆阳守备都指挥薛良弼应援逗留,指挥高勋、刘椿杀降启衅,闲住参将韩承恩、游击高大恩、备御蒋承勋等迁延后至,备御把总指挥等官李用等三人各以首功私相贸易,以上诸将均降职三级并付巡按御史逮问;曹禄等二十六人或戕弃尸或冒他级,各降一级,夺俸有差[13]。嘉靖三十一年(1552),辽东总兵李琦终因“贪饕不法”被革职,宣府总兵都督佥事赵国忠代之[14]。嘉靖三十四年(1555),赵国忠亦因“贪纵”被革职,“下按臣追赃”[15]。
二、嘉靖后期辽东将官贪懦与边患
从本质上看,辽东边将的贪懦实为执行防御政策失误的一种表现。明廷的御虏政策以驻防险要、军事弹压为基础,辅以贡贸等招抚手段。嘉靖时期,辽东边堡失修,军士困窘,蒙古诸部乘虚常年寇边。边将对近边蒙古、女真部落疏于管理和防控,亦致边地朝贡、贸易秩序混乱,激化了官方与近边诸部矛盾。蒙古侵袭边地,上至总兵下至把总未有预警亦无有效打击,使辽东边患不断升级。嘉靖二十二年(1543),蒙古连犯叆阳,刘大章副总兵等“莫能制之”,皆因其“假抚处之名,私许贸易,致虏邀杀”。建州等部“见利从恶”,“通事挟求添贡”,动辄大举寇边。边将对寇边之部未能果断采取“闭绝绝交、险剿杀”等惩处措施[16]。嘉靖二十三年(1544),东州、新安、清河、叆阳、碱场累造虏患,杀掠五百余口,抢夺马牛若干,防守将官隐而不报,受到明廷革职、降级等惩处。究其原因,为“虏酋捌卜你等以求贡为名,冀雪往年舍人寨之耻。而巡抚都御史孙禬招抚太轻,镇守总兵官赵国忠调度失策,致虏入寇[17]。”后指挥孙铣等十一人因“废弛边防”被问罪[18]。辽东将官应对蒙古、女真族近边住牧频频失策,恐惧明廷针对其剿抚不利采取的惩处措施,又贪图斩首之功,遂滥杀顺遗、虚报战功使明廷失去了对辽东边患的正确判断。嘉靖二十四年(1545),“辽东长胜堡(沈阳市西南辽中区茨榆坨镇)近边夷人百五十人窃朵颜马畜逃匿。指挥王勋、孟儒等纵之住牧墙内,会虏入寇。勋等不能御,惧得罪,乃绐,执诸逃夷尽杀之,诈为与虏战,效首级上功。总兵赵国忠、原任巡抚董珊信、副总兵郝承恩妄以捷闻[19]。”嘉靖二十五年(1546),辽东东宁卫指挥胡孝臣等“为虏盗其马畜,俱得罪,乃潜兵出塞掩杀住收熟夷二十六人,诈称对阵斩获以自饰。副总兵种继误以捷报之。抚按巡按御史张铎验首,虏多老弱妇女疑而诘之……”胡孝臣等扑杀内附部民,贪功启衅,下巡按御史逮治。同年十月,辽东总兵张凤、于敖令其中军指挥陈守节犒赏马市诸部,克减盐物,激女真部众怨愤,陈守节下令杖行,致七名女真首领死亡。女真部众遂以三千余骑攻镇虏台、岐山东空台一带,备御指挥不能抵御,纵其杀掠而去[20]。
嘉靖时期,明廷在虏患问题的处理上主要依据辽东战报做出判断,终将问题矛头直指兵力不强、战备较弱等作战方面,忽略各级将官治边、治军政策失误和能力欠缺。明廷不断下令辽东诸将,命其“整兵严备,相机出塞剿杀”,但收效甚微。嘉靖末期蒙古左翼时常突破辽东防线袭掠腹地。嘉靖二十六年(1547)正月,明廷升山东左布政使胡宗明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其任职甘肃、四川、广东、陕西期间,督军饷、平剧盗、纾民困,颇有功绩[21]。胡宗明虽尽力修缮城垣,补足兵备,但边患甚峻终不得治。同年十月,广宁城备御指挥李钺及中军都指挥陈守节诱杀把把亥等七人,诸部率众犯广宁、义州,“官军不能御,杀掠几万人”[22]。次年正月,永宁孛只郎中率众寇掠长静堡(今辽阳市唐马寨镇)一带。辽阳总兵戴廉率兵迎敌,斩首一百七十八级。“未几虏乘我不备,突入自镇静堡(今锦州市黑山县白厂门镇)至广宁界二百余里,官军死者三百九十三人,男女被虏杀者几万人。”胡宗明被降三级调外任[23]。嘉靖二十九年(1550)七月,总兵戴廉、副总兵罗文豸、游击武镗因二十六年辽阳、广宁守蒙古侵袭失事被罚谪戍边卫,广宁备御李广宁降一级守镇堡[24]。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二月,“虏自辽东海州东胜堡(今海城市新台子)入,南趋耀州堡(今营口市北)转掠海、盖、熊岳等堡,杀掳男妇六千余人,所焚劫庐舍畜产称是。”失事指挥王胤祖等二十九人于御史问罪[25]。嘉靖四十年(1561)九月,广宁把总指挥吴麃、千户郎松以兵二百防护解银,经历王钥、鲁亨至海州新台遇虏伏击,劫所赍给修边银八百两,杀钥及享,麃、松战没[26]。十二月,“虏犯辽东,攻陷盖州、熊岳驿,杀指挥杨世武等[27]。”嘉靖四十五年(1566)四月,“虏众万余自辽东西兴、西平二堡入寇,备御苟麒、把总张禄引兵御之,至高桥,陷虏伏中死[28]。”辽东军威衰弱如此,失去对蒙古诸部的震慑作用。
日益严峻的边疆政局使辽东边将的贪懦行为更为突出。嘉靖后期,蒙古、女真社会的发展与南迁势必不断冲击明廷原有的防御边界,《明世宗实录》中频现“虏贪侵袭利益”入寇辽东边堡的记载。辽东兵源补给不足,城垣修缮,多数将官难抵蒙古大举入侵。嘉靖二十五年(1546)九月,“虏七十余骑自义州、清河入寇”,锦义参将周益昌领兵迎击但并未将其驱除。次日,反被万余蒙古骑兵所围。指挥钟世威、原游击武堂兵率所部亲军赴援。辽军伤亡七十余人,斩蒙古部族首领二十五级,余部虽退,但仍徘徊于羊山一带随时可复至。辽东巡抚遂请发还戍宣、大郭游击所领游兵[29]。嘉靖二十八年(1549)九月,兀良哈三卫及花当部落导东蒙诸部寇辽东入沙河堡。备御张景福督兵出战,遇蒙古大队伏击,景福及百户成策、李松等及百余军士被杀。分守宁前左参将徐府怯敌引避,蒙古诸部得志而去。后徐府被革职回卫,夺总兵李琦、巡抚蒋应奎俸半年[30]。嘉靖三十五年(1556),辽东边外女真人寇永宁,失事参将崔钦、守备刘潮、把总汤淳下御史问罪[31]。嘉靖四十二年(1563)五月,蒙古拥众犯辽东海、金等处,大掠七百余里,杀掳二万余人。当时抚臣吉澄闻罢官报离任,代者未至。总兵吴瑛等在镇畏其众,不敢击。诸部留边内十五日始出境[32]。在岁无宁日的防守备战中,辽东边将很难保证任期内作战的成功率。主动迎敌战死、战败机率极大,在明廷复杂的考核体系下即使有所斩获,亦有可能因整体战局的失利而受到牵连。观望和权衡似乎成为边将应对边患、规避处罚的常态,当然,如遇大警被问责治罪在所难免。
三、辽东将官的贪懦与明廷政策
嘉靖即位前后(正德十六年至嘉靖二年),巡按辽东御史杨百之、巡抚辽东御史李承勋、巡抚辽东御史张琏等明确指出:军功奖惩制度僵化,失去激励辽东官兵主动御敌作用。嘉靖后期,明廷仍“以敢战立功,不以损军为罪,或打其营帐,或屠其老小,或夺其牛马,或剿其零骑,沿边丁壮有奋勇斩获首功者以新例行赏”[33]。据《明世宗实录》中武将升迁历程可知,御敌胜负为将官奖惩的首要标准:胜,且有斩获,可谓大功;谨守防区,且不受它役牵连,可功过相当;“虏”袭其境,掠夺人畜,损兵折将,轻则罚俸降职,重则革职处斩。辽东不乏猛将,辽东官兵皆不惧与蒙古、女真士兵为战。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明廷奖赏辽东开原及陕西波罗堡等处获功阵亡官军吴自武等一百四十六人,王用等十四人。同年十月,“虏酋小王子打来孙等率众数万寇辽东锦州地方”,赵国忠督诸将率兵御之,杀虏千余人[34]。嘉靖三十二年(1553),蒙古五百余骑犯辽东上榆林堡(今沈阳市大东区榆林大道东北部),副总兵岳懋、游击苏澄督兵御之。诸部遁走出塞,懋等追奔四十里及于小长山,斩获四十七级。嘉靖三十九年(1560)十一月,明廷“录辽东马根单等堡擒贼死事官军郭保儿等六百七十一名,升赏有差。”嘉靖四十二年(1563)九月,“录三十九年辽阳等处东州等堡获功官军王承爵等一百八十人,升赏有差。”“录四十年辽阳马根单等堡斩虏功,升赏官军韩禄等八十五人[35]。”明廷以军功为首的赏罚制度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官兵骁勇御敌。如广宁前屯卫人杨照,起家偏校,以战功累迁辽东总兵官。期间亦因败绩被夺或降职,但终其骁勇敢战为朝廷起用。因感知遇之恩,誓以死报。后恢复都督职衔,充总兵官,镇守辽东。杨照曾因不输贿严嵩,又与巡抚侯汝谅不睦,被革职。后于嘉靖四十二年一月两著战功,以功补过,复官叙用。八月,出塞御虏,夜行失道,中流矢而亡[36]。但是,在蒙古势力南下,诸部入侵无法预测,而辽东防御机制僵化,财力、兵力动支困窘,将官很难有效维护辖境安全。嘉靖三十一年(1552)十二月,虏犯辽东锦、义,官军斩首四十七级,各堡将士斩首八级,得虏马二百二十匹,但我军亦亡三百三十余人,伤一百二十余人。此役各卫官兵虽有斩获,但明廷仍就各将所部失亡给予了处罚。广宁中屯卫指挥使郝堂降等俸二级,夺守备吴佩等俸半年。总兵赵国忠、张齐暂无问责[37]。嘉靖十八年五月(1539),因虏寇辽东,开原参将孙继祖与守备武勋各被夺俸三月,后虏再次侵入因稍有斩获二人被准赎罪。嘉靖二十七年(1549),虏犯辽阳大肆杀掠,从巡抚、总兵至把总多获罪,原任河东游击今升参将武勋因谨守本职且辖境无碍,礼科给事中评定为功罪相当。嘉靖三十九年(1560),明廷治威宁营(开原三万卫铁场所)等堡失事罪,发分守辽阳副总兵王重禄、定辽左卫指挥同知陈可、东宁卫指挥佥事王廷兰俱戍边。更为严重的是,将官窥战功之利,报功不实,官兵以战功、首极殉情咨送,极大损伤辽东军队整体战斗力的提升。嘉靖后期,贪功惧战已成辽东军镇体系中的一块顽疾。将官“以虏入为奇货,以谋级为要津,凭藉虎威大张鸱吻,见军民获首虏者即攫为己物[38]。”嘉靖三十一年(1552)五月,时任定辽后卫左参将署都指挥佥事的武勋,因“贪酷”被巡抚御史所劾,黜为民[39]。嘉靖三十九年(1560)五月,“以辽东、延绥二镇报首功不赏,夺巡抚侯汝谅、董威及总兵杨照、李辅各俸二月,下冒功官军陈举等于巡按御史问[40]”。
明廷抽调边镇精兵入京、驻守蓟镇、应援他镇等兵制,无形中削弱了辽东防御力量,加重了辽东边患危机。辽东兵额不足,尤其是堪战精兵。嘉靖后期,兵部多次强调辽兵应还镇防御,但仍须专设援兵驻守蓟、辽之间以备蒙古诸部内犯时入关应援。若武臣应援失期“与战败同罚”。嘉靖四十年(1561)八月,兵部尚书杨博上陈守御之策:“今之九边,大率以蓟镇为重,盖腹心既安四肢自无可虑……燕河冷口一带逼近辽东,督抚官隔远调度不及,宜责之辽东兵将闻警星驰赴援不必俟调。”明廷制定宣、大、辽东等边镇应援京师,“左右夹击”来犯诸部的政策固然利于边疆防御的整体局势,但在兵力有限的前提下,辽东的防御力量势必受到削弱,武将在主观上亦以应援京师、布防重镇为要务。瓦剌、鞑靼等部在近边蒙古三卫的策应下,入寇的切入点往往随明廷布防虚实而做出调整,明廷北疆防御体系不变,辽东边堡不坚、堡军力弱的颓势亦无法扭转。嘉靖四十一年四月,蒙古土蛮部大举寇辽东,巡抚都御史吉澄言:“本镇士马单弱,城堡颓坏,不堪战守”。兵部尚书杨博建议,“岁调辽东兵四千人入卫蓟镇,今可暂免,专备辽东”[41]。在明朝政治氛围不甚清明时,辽东边将多遇敌不战确保境内“平安”。若遇敌侵袭,常通过结交权臣、构建私人关系网等方式来规避处罚乃至获取战功。倘遭大股侵袭,败绩显露,边将受罚便成为常态。嘉靖三十一年(1552)四月,把都儿辛爱部原计划袭击锦、义,但知其有备,便乘虚犯广宁前屯卫。自新兴堡(新兴营堡,又名刘彦章堡,今辽宁兴城市大寨满族乡)入,百户长禄、指挥姚大谟率堡兵二百,提调指挥刘栋、团练指挥刘启基率军舍四百余卒与之连战两日,四将俱没。备御指挥王相率亲兵四百人赴援,经过殊死搏杀,王相及麾下士死者不下三百人,余卒无几无不带伤者。指挥姚大谟、备御指挥王相等以必死之心竭力抗敌虽可谓忠烈,但参将郭世勋、守备李尚文等多观望不敢近。参将郭世勋、守备李尚文等被革职听勘,余下按臣逮问,总兵赵国忠、巡抚许宗鲁各停俸,令戴罪自效。明廷清晰认识到“虏岁入犯,各边无敢斗者”的边防境况[42]。
嘉靖后期,辽东地区边患日趋严重。除却蒙古、女真南下等外部因素,明廷内部制度僵化、军政体系衰败使明政府在御虏过程中愈显势弱。辽东将官的贪懦表面为个人的道德素养,实为军政体系运转的关键所在。军事将领贪功图利,势必失去全局战略眼光;士兵被夺战功,丧失晋升机会,敢怒而不敢言,见他人叙功定生怨愤,不利队伍合力抗敌。辽东高级将官贪占下属兵士之功,势必导致辽兵作战积极性下降。同时,为图上峰提携照顾,普通军士及将官家丁作战目的势必围绕将官所需,忽视整体战略安排,极易形成以将官为中心的利益集团,侵蚀辽东乃至明朝整体的军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