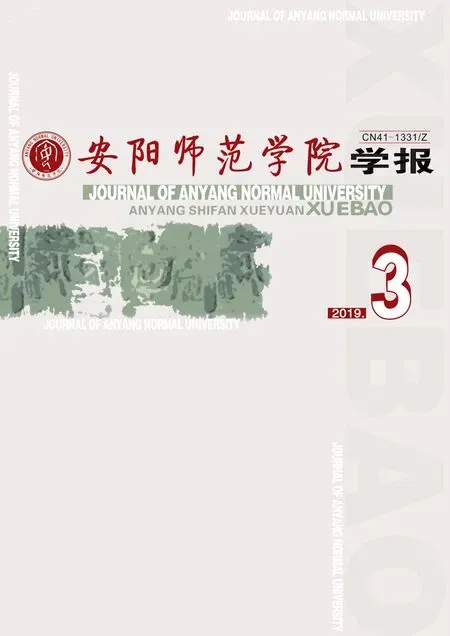中外诗人笔下的自然描写之比较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自然诗歌比较
刘诗诗
(深圳大学 人文学院,广东 深圳 518061)
在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东西方文学研究变得愈加受重视,尽管人类千差万别,但从文学领域来看,各民族都存在共同的诗心、文心,由于人类具有大体相同的生命形式和体验形式,以表现人类生命与体验为主要内容的文学一定会面临许多共同问题,因此相似性与可比性必然存在。
诗歌作为一种抒情言志的文学体裁而为中外文学家所偏爱。朱光潜在《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一文中指出:“在中国和西方一样,诗人对于自然的爱好都比较晚起,最初的诗都偏重人事,纵使偶然涉及自然,兴趣中心都不在自然……所以,自然情趣的兴起是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在中国晋宋之交,约5世纪左右;西方则起于浪漫主义运动初期,在公元18世纪左右。”[1]谈到自然情趣,中国诗人则首推陶渊明,而西方则以华兹华斯为显,二者笔下的自然诗虽皆写自然但亦各有千秋。
一、自然诗心与朴素风格
陶渊明与华兹华斯分别是中西诗坛的伟大诗人,都向往和谐美丽的自然田园生活,都具有浪漫主义情怀,因此,他们笔下都有大量描绘自然的诗歌作品。
华兹华斯作为英国 “湖畔诗派”的代表人物,其诗歌理论动摇了英国古典主义诗学的统治,华兹华斯从小就受到美丽大自然的熏陶,立志投身其中,通过潜心创作来探索人生的真谛和生命的意义。他主张亲近自然,与自然融合,修身养性,他的诗歌代表作品《延腾寺》:“这个日子又到来了,我能再一次站在这里,傍在这棵苍翠的槭树,俯览脚下,各处村舍的园地,种满果树的山坡,由于季节未到,果子未结,只见果树一片葱绿,隐没在灌木和树林之中。”[2](P81)华兹华斯摒弃了18世纪诗歌风格上古典主义的因袭与滥调,注重发展民间诗歌传统,他的诗展现了对乡村生活的赞美,诗人描写自己在喧嚣的城市中感到孤独无助,而自然的美好却能让他的心灵得到平静,诗人把自然看作心灵的向导,能给他心灵的慰藉,可以看出诗人对自然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陶渊明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同时也是田园诗的开拓者,他的田园诗以淳朴自然的语言、高远拔俗的意境,为中国诗坛开辟了新天地。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他的创作中,几乎三分之一以上的作品,包括诗与辞赋,描写了自然界的山水田园风光,花鸟草木物态。这类诗充分表现了诗人对淳朴的田园生活的渴慕与追求。《和郭主簿》(其一)中写道:“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阴,凯风因时来,回飙开我襟。”[3](P25)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夏日清凉美景,在静谧的堂前享受自然风光带给人的舒适,在自然中获得精神的自由。
两位诗人的诗歌作品都具有创新意义。陶渊明的诗歌,继承了《诗经》的传统,由《诗经》农事沿袭下来,而题材、内容、形式都较前丰富、生动、形象,在描写农村生活和田园风光上,别开生面,开创一代田园诗风,陶渊明在歌颂田园生活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华兹华斯的诗歌贯穿了自然的虔诚,从自然中去思考和探索人性的回归与人生的真谛,成为欧洲浪漫主义诗歌中响彻天际的一曲回旋的交响乐。毫无疑问,热爱自然、善于将真挚、深厚的感情倾注于描写自然的诗作中,是陶渊明与华兹华斯诗歌共同的特色,此外,两人都主张运用朴素、平淡的语言,反对绮丽雕饰的诗风,采用农村下层人民的生活题材,给读者营造了一种淡雅悠扬、返璞归真的意境。
二、蓄婉美与张扬美
由于地理环境、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因素,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人对于事物的认知是不同的,在审美观念上也是存在一定差异的。东西方文化截然不同的底蕴造就了西方崇尚外向张扬的美,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则偏好沉静而内敛的美。
一切诗歌都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湖畔派诗人基本把诗歌视为情感的表现,浪漫主义诗人似乎比常人有更丰富的情感,拜伦也曾反复强调“诗是激情的表现”。西方新古典主义者强调感情要克制,要合理,而华兹华斯的诗歌所表现的情感是强烈的,外放的,他认为情感无论是一种欲念或者是情绪,它都要真挚,诗所表达的精神是内心世界的总体,华兹华斯的自然诗歌风格是激昂的,是张扬的,表现为情感的倾吐、想象的飞腾。
华兹华斯曾经积极支持法国大革命,然而,革命的失败是他饱受重压,于是他转向到自然寻求安慰,通过这种方式来寻找心灵的出路。所以他诗歌的主要特征在于其主观性、主情性和大自然崇拜,在于尊重心灵和崇尚自由,营造一种奇特的梦幻气象,他的《序曲》就以感情为中心,张扬的情绪是诗人在诗中表达动作与情节的重要线索,作者将内心想要表达的情绪显露得淋漓尽致,丝毫无所隐藏,勇于传达自己蓄积于胸的想法而无所拘泥,这是华兹华斯诗歌所体现的一种张扬美。
中国的传统素来以含蓄内敛为主要情感倾向,因而中国得文学作品中往往会产生很多意象和想象,在不同意象和不同想象之中会产生不同的画面感。陶渊明在其著名诗歌《饮酒·其五》中写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4](P114)这首诗没有任何华丽繁绮的辞藻,诗歌的语言风格含蓄蕴藉,由语言、形象、审美意蕴三个层面组成,在平淡的外表下,饱含着炽热的思想感情和浓郁的生活气息,读来韵味隽永。诗人摆脱尘俗烦扰,从南山的美好景色中获得无限乐趣,表现了诗人热爱田园生活的真情和高尚人格。诗人从大自然中的“飞鸟、南山、夕阳、秋菊”中悟出了真意,悟出了自然的人生哲理,但他没有明确表示,只是含蓄地提出问题,让读者去思考,留给读者言已尽而意无穷的想象空间,使读者置身于境,去仔细品味思索其中之意。这不同于华兹华斯那种强烈的情感流露,诗人内心是及其平静淡然的。
三、融于自然与游离自然
中西方文学都具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写意的文学,一种是写实的文学,虽然陶渊明与华兹华斯的笔下都有大自然的景象,都醉心于大自然,但由于所处的时代、文化背景以及哲学观点的不同,二者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与心性上也有很大的区别。华兹华斯作为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它的诗更加注重写意性,更关注自然的境界,而人处于游离于自然之外的一种状态;而陶渊明的诗更注重写实性,更关注人与自然的亲密关系,陶渊明将本然的心性融于自然中,主体的消解,让其本人就成为自然的一部分,所以,其自然观有很强的实践性。
陶渊明生活在魏晋时期,玄学之风对陶渊明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陶渊明深知社会政治的黑暗、官场的腐败、人性的贪婪,他宅心空远、守拙抱朴、回归自然,投身于毫无人工雕琢的自然,不肯屈从流俗。《归园田居》(其二)中,诗人满怀激情地歌颂了美好的田园生活,炊烟缭绕的村落幽深的小巷中传来的鸡鸣犬吠,都会唤起他无限亲切的感情。更重要的是,在他的心目中,恬美宁静的乡村是与趋膻逐臭的官场相对立的一个理想天地,诗人亲身实践农庄生活,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山水田园风光相契合,此时,他并非一位诗人,而是一位从事农业生活的普通农民,也只有把自己当作农民,才能感受到田园劳作之乐。
这是“性本爱丘山”的本性使然,寄身于田园,在饮酒劳作中以求心灵的安慰,死后愿意“托体同山阿”,完全与自然融为一体,主客观融合,不分彼此,惘然于时间,惘然于空间,达到了一种“致虚极,守静笃”的精神境界。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天人合一”的思想,这一思想发源于中国古代宇宙生成论和自然世界观,古人认为天与人是相通的,人应该顺应自然,亲近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再者,我国向来是个农业国度,长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人们劳动和生活于农村,更养成对自然的依赖心理和认同意识。
而西方则长期把自然神化,认为自然景色、山水风貌是神魔的化身,自然与人不是合二为一的,不是水乳交融的,而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因此,华兹华斯笔下所描绘的自然更多的是对自然的敬畏,例如他在《丁登寺》里面写道:“我感觉到有什么在以崇高的思想之喜悦,让我心动;一种升华的意念,深深地融入某种东西,仿佛正栖居于落日的余晖,浩瀚的海洋和清新的空气,蔚蓝色的天空和人类的心灵。”[5](P27)诗人以一种强烈的语势描述着大自然中的种种,他将大自然视为一种精神,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推动着宇宙的运行,这种力量是人类所无法掌控的,这里边寄寓着诗人宗教式的感情,也赋予了深邃的哲理。这与陶渊明的纯粹赞美大自然、融于大自然的诗歌就无法相提并论了,华兹华斯是大自然出色的观察者,而陶渊明则是一名体验者。
四、情本体与理本体
中国文学是以抒情为主导的传统,即“诗”的出现,中国文学一开始即对理性保持距离;而西方文学有根深蒂固的理性传统,西方文学以理性作为抒情原则的灵魂,主张人类不仅要有情感,更要具有理性思维,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但需要理性意识的参与和评判。
中国古代山水田园诗人代表王维、孟浩然、陶渊明,他们的诗天真无痕,纯正自然,读之尤感诗意盎然,真如宛在。因为他们的诗融入了情感于其中,情感融化在意象之中,毫无雕琢之痕迹。陶渊明的诗以一种十分真实、自然的态度表现自己的生活,抒写着自己的情怀,他在《归去来兮辞》里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这既指为人,也指写诗,陶诗呈现出一种“豪华落尽见真醇”的质性情感。这种古朴平淡所内蕴的,并非一无波澜,而是内心汹涌的情感与自然交合中所达到的深刻的情感境界。纵观中国历代文学作品,“情”也是贯穿其中的重要脉络,这似乎是中国古代文学家所奉为圭臬的主导意识。
“情本体”是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李泽厚所提出的思想,情本体与文化心理结构不同,指人的道德和本能在生命中的多种多样不同比例的配置和组合,它更多的是强调通过审美的活动来塑造新的人性,以“情”为最终实在与根本。西方则主张与之相对的“理本体”的文学观念,这发源于西方哲学史,自古希腊哲学到德国古典哲学,通过理性特别是知性思辨获得真理。
因此,受西方理性思维的影响,华兹华斯始终与自然保持一定距离,在抒发情感的同时始终保持着理性,人与自然始终无法交融为一体。华兹华斯在《咏水仙》(又译为《我好似一朵流云独自漫游》)中想象自己的周围是一大片金色的水仙花,在随风嬉舞、随风飘荡,水仙虽然给了诗人受伤的心灵以慰藉,但使人并未忘却内心的烦扰,内心仍然是“人自孤寂花自摇”的状态,并没有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受西方理性分析传统的影响,华兹华斯始终强调“理性”的重要性,因此他的自然诗更多的是在探索自然,思考哲学和宗教命题,这与陶渊明自然诗的“物我交融”、“托体同山阿”的境界有显著差别。
结语
通过以上比较,陶渊明与华兹华斯两人都醉心于自然,且都运用质朴、淡雅的语言为世人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自然诗歌。但,陶渊明笔下的自然是与其本身融为一体的自然,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超然境界,人由自然孕育,又归于自然,化为自然,从而获得心灵的释放与超越。陶诗并不注重说理,而是注重将内在情感巧妙的融于作品之中,创造出一种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而华兹华斯对自然更多的是一种宗教式的崇拜,致力于表现人与自然的从属关系而非平等关系,他对自然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其作品追求对内心世界的探索,对自然寄寓一种宗教式的感情,同时赋予了深邃的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