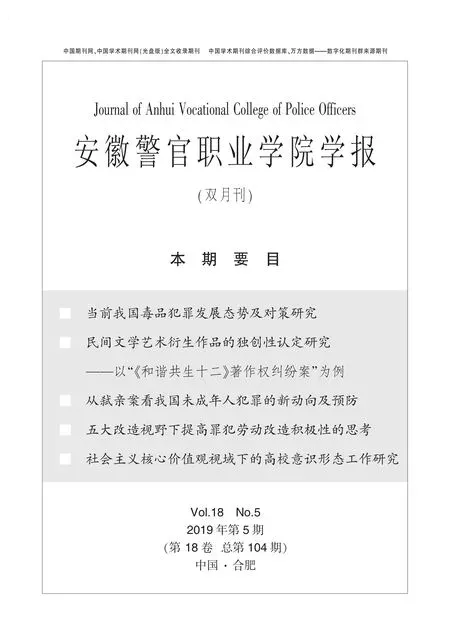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案的刑法定性分析
王 刚,王洪坤
(江苏大学 法学院,江苏 镇江 212013;江苏省泰州医药高新区人民检察院,江苏 泰州 225300)
关于“偷换商家收款二维码案”(下文简称“二维码案”)的刑法定性,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存在盗窃罪、诈骗罪和侵占罪三种分歧意见。①周铭川副教授、柏浪涛副教授持盗窃说。参见周铭川:《偷换商家支付二维码获取财物的定性分析》,载《东方法学》2017 年第2期;柏浪涛:《论诈骗罪中的“处分意识”》,载《东方法学》2017 年第2 期。 何鑫、刘梦雅等人持诈骗说,杜邈、程畅等人持三角诈骗说。 参见何鑫:《调换商品付款条形码之罪名认定》,载《中国检察官》2017 年第12 期(下);刘梦雅、张爱艳:《偷换商家支付二维码案的刑法认定》,载《中国检察官》2018 年第1 期(下);杜邈:《电子支付时代的侵犯财产犯罪新形态——基于“三角诈骗”理论的分析》,载《中国检察官》2018 年第1 期(下);程畅:《“偷换二维码案”的法律定性》,载《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8 年第1 期。 张开骏博士持侵占说。 参见张开骏:《偷换商户支付二维码侵犯商户应收款的犯罪定性》,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8 年第2 期。在规范层面,盗窃罪与诈骗罪的犯罪构成有交叉之处,侵占罪与盗窃罪的关联性较大,与诈骗罪的关系则较为疏远。 在事实层面,窃取和欺骗相结合的财产犯罪屡见不鲜。 由此,这类案件的刑法定性往往比较困难。从各方的争议焦点及论证过程来看,二维码案之定性既包含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的犯罪构成及其差异等规范问题,也涉及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及盗窃罪、诈骗罪、侵占罪的边界等理论问题,还离不开对案件事实的价值判断。 通过综合研判,本文认为二维码案应定盗窃罪。
一、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
我国传统刑法理论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是财产所有权, 具体包括权利人对财产所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1]至多扩展至其他本权。 德日刑法理论中存在本权说、占有说和中间说等诸多观点,本权说的保护范围太窄,占有说的保护范围太宽,比较而言中间说更加合理。[2]我国传统观点属于德日刑法理论中的本权说范畴, 据此观点可能导致很多财产案件的处理结论不妥当。例如,对于行为人偷回被交通管理部门扣押的违章车辆与被他人非法占有的本人财物这两种行为, 处理结论及其理由便存在不少争议。[3]本文认为中间说中的“与本权无对抗关系的占有说”较为合理,该说认为财产犯罪的保护法益既包括所有权和其他本权, 也包括作为本权前提的占有, 因而为本文所采纳并作为立论基础。 据此观点,当占有和本权发生冲突时,能够合理对抗本权的占有值得保护, 无法与本权进行合理对抗的占有则不值得保护。因此,凡是侵犯了能够合理对抗本权之占有的行为, 即有可能构成财产犯罪。 按照这种理解, 盗窃罪和诈骗罪的共性之处在于,破坏了原来的合法占有关系,建立一种新的非法占有关系,这种非法占有当然也包含对本权的侵犯。侵占罪不涉及对占有关系的破坏, 仅仅是侵犯了权利人的本权,故侵占罪的法益不包括占有,[4]这是其与盗窃罪和诈骗罪存在的明显区别。
二、诈骗罪的主要理由及其反驳
有学者认为二维码案应定诈骗罪,主要理由是:“处分行为并非诈骗罪独立的成立要件,只要具有财产处分权限的人,因受骗陷入了认识错误,并有财产减损的直接性危险时,行为人就应当构成诈骗罪,而不应当对‘诈骗’的范围作过多限制。 ”[5]诈骗罪(既遂)的客观要件表现为下述行为过程:行为人实施欺骗行为——对方产生或者继续维持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财物——行为人获得或者使第三者获得财物——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4]1000在被害人心理方面, 诈骗罪在形式上没有违反被害人意志,被害人形成了关于财物的决意,并对财物之转移有认识。 在行为特征方面,诈骗罪的被骗人(包括被害人和非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作出处分行为,被骗人对犯罪结果的实现发挥了必要的加功作用,故诈骗罪属于主动型、自损型犯罪。 基于上述认识,本文认为二维码案不构成诈骗罪,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二维码案中的犯罪行为不是欺骗行为。张明楷教授认为, 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表现为向受骗者表示虚假的事项或者传递不真实的资讯。[6]我国刑法学通说认为, 欺骗行为包括虚构事实和隐瞒真相两种方式,前者是指捏造原本不存在的事实,后者是指应当告知真相而没有告知。在二维码案中,行为人偷偷更换商家收款二维码的行为不是诈骗罪中的欺骗行为,这是因为:其一,欺骗要求行为人与被骗者之间存在意思交流, 被骗者在此过程中接受了错误信息,因而产生或者强化了错误认识。二维码案中行为人和被骗者之间没有意思交流, 不符合欺骗行为的客观特征。其二,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的结果是使被骗者在固有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一种新的错误认识或者强化了原来的错误认识, 二维码案中被害人只是消极地没有认识到事项的变化, 不属于这两种错误认识的情形,不符合欺骗行为的主观特征。
第二,二维码案中的被害人没有作出处分行为。这是一个富有争议的理论问题。理论上一般认为,是否存在处分行为是区分诈骗罪和盗窃罪的关键。[3]21处分行为以具有处分意识为主观要素,“处分意识是指处分人意识到将自己占有的财物或享有的财产性利益转移给对方占有或享有。 ”[7]诈骗罪中有被骗者的处分行为, 盗窃罪不存在规范意义上的被害人处分行为。 客观上, 处分行为是指转移财物占有的举动。 主观上, 对于被骗者基于何种心理实施处分行为,理论界存在处分意思不要说、缓和的处分意思说和严格的处分意思说之争。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处分意思不要说的观点逐渐式微。 本文赞成缓和的处分意思说, 认为被骗者需要认识到自己将财物转移给对方的事实,但无须对财物的价值、种类、数量等有具体认识,只要对处分对象有概括性认识即可。如前所述, 二维码案中顾客和商家都没有认识到二维码被更换,都没有预见到货款会转至行为人的账上,因此没有将货款转移给行为人的认识和意志, 故商家要求顾客扫描二维码以及顾客扫描二维码的行为均不属于诈骗罪中的处分行为。
第三, 二维码案也不属于三角诈骗。 有观点认为,“行为人偷换收款二维码的争议焦点不在于如何认定盗窃罪与诈骗罪, 也不在于新型的电子支付方式,而在于对‘三角诈骗’理论的态度。”[8]这种观点倾向于将二维码案定性为三角诈骗, 本文也不赞成。“传统类型的三角诈骗表现为,具有处分权限的受骗人基于认识错误处分被害人(第三者)的财产,因而使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9]因此,三角诈骗的成立条件是: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具有处分被害人财物权限或者处于可以处分被害人财物地位的受骗者因此产生错误认识或者强化了原来的错误认识, 受骗者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处分了被害人的财物, 致使被害人遭受财产损失。概言之,三角诈骗中仍然需要具备欺骗行为、 被骗者产生错误认识及作出处分行为等构成要件要素。如前文所述,二维码案中并不存在这些要素,因此不成立三角诈骗。
三、侵占罪的主要理由及其反驳
有学者认为二维码案应定侵占罪,主要理由是:行为人对非法取得的商户财产负有返还义务, 拒不返还的符合侵占罪本质;不成立盗窃罪的关键在于:支付款自始至终没有进入商户的账号, 而是直接进入了行为人的账号,商户没有占有过支付款,不符合盗窃罪侵害占有、建立新的占有的行为本质。[10]根据侵占罪的罪状表述和本质特征, 二维码案也不构成侵占罪,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二维码案不符合侵占罪的行为构造,商家应收货款也不是侵占罪的行为对象。 侵占罪是真正的不作为犯, 其成立前提是行为人先合法占有他人财物,这种占有关系的设立不具有违法性。 无论是受人委托代为保管他人财物,还是拾得他人遗忘物或取得他人埋藏物,行为人对财物的占有过程和结果都不具有违法性。 但在二维码案中,行为人对商家应收货款的“拦截”没有任何根据,其对应收货款的占有过程和结果都是非法的。《刑法》第270 条明确规定,侵占罪的对象是“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和“他人的遗忘物或埋藏物”,将商户的应收货款解释为侵占罪的对象,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此外,侵占罪以“拒不返还”为入罪条件,从刑法实质解释的立场考虑, 行为人偷换店家收款二维码并截取其应收货款后,如果返还即不构成犯罪,显然也不符合一般的社会观念。
第二, 盗窃罪中被害人对其财物的占有不以事实上的实力控制为限, 规范的占有概念已经获得较为普遍的认可。 理论上认为占有概念具有事实和规范的二重性,占有的规范性包括两层含义:一指以社会一般观念为内容的规范性视角,二是以法律、道德或社会习俗等为内容的规范性秩序。[11]现实生活中,财物所有人不可能时时刻刻对其财物进行实力性控制,不可能对其所有财物进行实力性控制,在此背景下承认缓和的、规范的占有概念是必然的结果。有学者指出:“虽然顾客的钱款并未首先进入商家账户而是直接进入行为人账户, 但是至少在顾客扫码支付的那一瞬间,无论在社会观念上还是在所有权上,该钱款都属于商家所有和占有。 ”[12]尽管这种解释并不完美,但仍然具有较大的合理性,在电子支付时代基本是可以接受的观点。从货款占有转移的角度分析,通过更换收款二维码截取商家货款的行为, 与现金交易中行为人在买方交钱、 卖方收钱的一瞬间抢走现金极为相似。在后一种情形中,基于规范的占有概念认可卖方对货款的占有是较为妥当的结论。
四、二维码案构成盗窃罪的主要理由
通说认为, 盗窃罪的客观要件是采用秘密手段窃取财物或财产性利益, 少数情况下也不排除被害人对窃取行为有认识。在被害人心理方面,盗窃罪违反被害人意志,被害人没有形成关于财物的决意,一般对财物之转移亦不知情(少数情况下知情)。 在行为构造方面,盗窃罪的被害人没有作出处分行为,行为人通过自己积极的作为手段获取了财物, 被害人对犯罪结果之实现一般没有加功作用, 故盗窃罪属于被动型、他损型犯罪。 基于这种认识,二维码案应定盗窃罪,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行为人实施了秘密窃取行为。行为人偷偷将商家的收款二维码换成自己的二维码, 使得顾客扫描该二维码后货款即转到他的账户上, 这是一种典型的“移花接木”的秘密窃取手法,本质上与盗接他人通信线路、 复制他人电信码号等盗窃行为并无二致,司法解释规定后两种行为均构成盗窃罪。
第二,被害人没有认识到其财产性利益被转移。由于二维码难以辨识,加之疏忽大意,被害人没有认识到其收款二维码被更换, 无法预见到其应收货款被秘密地转移至他人账户。
第三,被害人没有处分应收货款的行为。此处是个争议焦点, 诈骗论者认为顾客是被害人。 本文认为,顾客按照商家的指示支付货款,即获得了商品所有权。至于货款流向何处,顾客既无注意义务也无须承担责任,因而其不是被害人。商家财、物两空,是真正的被害人。但商家对货款被截取的事实没有认识,更无处分应收货款的意思和举动, 因此是典型的被动型、他损型被害人。
第四,窃取行为破坏了商家对应收货款的占有。此处是个争议焦点, 诈骗论者认为盗窃罪之成立以被害人对财物的占有为前提, 本案被害人尚未占有财物,因而不构成盗窃罪。 如前所述,这里涉及到对“占有”的理解问题。关于财产犯罪中的“占有”,刑法理论界形成了事实性说、规范性说、二重性说、折中说等观点。事实的占有概念属于事实判断,是指主体对财物事实上的控制力,该说确认的占有范围很窄。规范的占有概念属于价值判断, 是指根据社会规范将财物分配至某人的控制之下, 从而应当建立起来的一种支配关系,该说确认的占有范围很宽。事实的占有概念外延过窄, 对具体案件的处理结论也未必妥当。 例如,被害人将汽车停放在火车站的停车场,坐高铁去外地,后汽车被盗,按照这种理论认定盗窃罪存在障碍。 规范的占有概念能够克服事实的占有概念之缺陷,合理地扩展了财产犯罪的处罚范围,为本文所采纳。按照一般交易习惯,商家交付商品后即获得对顾客的债权, 顾客按照商家要求扫描二维码说明其具有支付货款的意愿, 扫描二维码后商家可以在瞬间占有货款。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基于规范的占有概念的立场, 可以认为商家已经对货款形成占有。 退一步说,即使认为商家尚未占有货款,但这种结果正是行为人的窃取行为所致, 完全可以被评价为“破换原来的占有关系、建立新的非法占有关系”。毫无疑问, 行为人的窃取行为破坏了商家对货款的占有,构成盗窃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