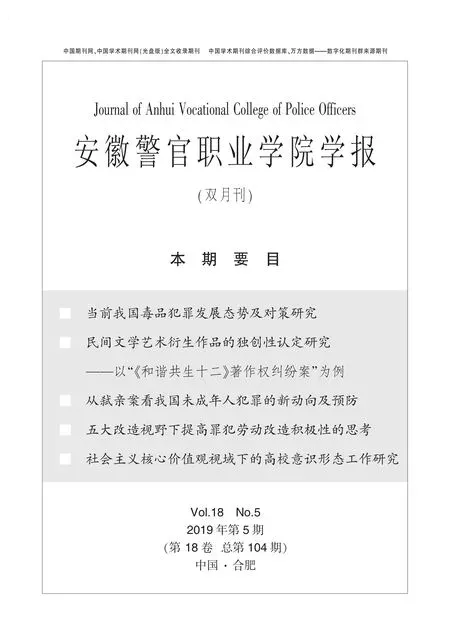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独创性认定研究
——以“《和谐共生十二》著作权纠纷案”为例
夏士园
(上海师范大学,上海 200233)
一、《和谐共生十二》著作权纠纷案案情简介和争议焦点
(一)基本案情
《和谐共生十二》著作权纠纷案是2017 年3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知识产权指导性案例,对于研究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具有指导性意义,也给司法实践中有关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纠纷处理提供有力参考。
原告洪福远从事蜡染艺术设计创作多年,《和谐共生十二》是其完成的作品,2009 年发表在《福远蜡染艺术》中,其参考了传统蜡染图案的纹样,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作,使图形更加传神,刻画了花鸟共生的场景。 洪福远对中间的铜鼓纹花也作了改变,与传统的蜡染图案不同。洪福远在2010 年8 月与邓春香签订合同将《和谐共生十二》的使用权转让给邓春香, 由邓春香拥有该作品的著作财产权。第三人今彩公司接受被告五福坊食品公司的委托,进行产品的市场形象策划设计,五福坊公司在其生产销售的贵州猪肉干等食品外包装上印了蜡染花鸟图案。
为此,洪福远认为被告侵犯其署名权,要求被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邓春香认为其著作财产权受到损害,要求赔偿其20 万。被告辩称:原告的作品与今彩设计的图案花纹, 两者都是借鉴的贵州黄平革家传统蜡染图案花纹,被告不构成侵权;五福坊使用的涉案图案在食品包装的右下角, 整体面积只占产品外包装面积很小一部分,其影响较小,赔偿20 万数额过高; 五福坊在使用今彩设计的产品外包装时尽到了合理注意义务。今彩公司辩称其2006 年完成了“四季如意”的创作,五福坊于2011 年开发有关旅游市场的礼品,选取了其中一部分图案使用,作品中的图案和原告一样都是参考的黄平革家蜡染图案,因此原告作品不符合独创性的条件,被告不构成侵权。
法院通过审理查明: 五福坊在产品手册和外包装礼盒上所使用的蜡染图案和《和谐共生十二》图案只有线条的颜色和图案的底色有细微区别, 其余都是一致的。并且第三人金彩公司辩称其于2006 年创作的“四季如意”的手绘原稿,但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予以证明。而洪福远的《和谐共生十二》在《福远蜡染艺术》中则明确注明了创作于2003 年。 故今彩公司是有接触原告作品的条件的。
因此,法院最终判决支持了原告的部分请求,包括被告五福坊公司赔偿原告邓春香经济损失10 万元;被告五福坊公司停止使用涉案《和谐共生十二》作品; 被告五福坊公司销毁涉案产品的包装盒和宣传册。 驳回原告其它诉讼请求。①参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筑知民初字第17 号民事判决。
(二)争议焦点
本案所涉的作品《和谐共生十二》是以黄平革家传统蜡染艺术图案为基础所创作的作品, 其主要的艺术表现方式与传统的蜡染艺术是相似的, 而黄平革家蜡染图案是属于公共领域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无法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因此原告的衍生作品是否能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就是本案首要的争议焦点,即原告的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问题。
对于衍生作品是否具有独创性, 需要明确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独创性的认定标准和认定方法,在此基础上, 才能准确判断衍生作品是否能够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以及被告是否构成侵权。
二、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界定
“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定义目前在我国还没有一致的观点,但是早已有学者、法院的判决书中使用了这一概念,例如管育鹰的《知识产权视野中的民间文艺保护》一书中在第一章第三节写到了“民间文艺衍生作品的著作权保护的利弊”、广西壮族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廖冰冰在《妈勒带子访太阳》 一案中,认定《妈勒带子访太阳》为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案例“《和谐共生十二》著作权纠纷”一案中,也使用了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这一概念。
顾名思义, 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是以民间文学艺术作品为基础而衍生出来的, 其与民间文学艺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国外对于衍生作品使用的是“derivative works”, 翻译过来就是派生作品的意思。 也就是说,衍生作品是以原作品为基础的,保留原作品的某些特征,在此基础上加入自己的创作,形成既和原作品有联系,又有别于原作品的新作品。在“《和谐共生十二》著作权纠纷案中”,原告洪福远借鉴了传统蜡染艺术的表达方式, 创作灵感源于黄平革家蜡染图案。但是他在此基础上补充了鸟的外形,加入了他个人的独创, 丰富了鸟的眼睛和嘴巴的线条,创造性改变鸟的脖子、羽毛,使鸟的图形更加形象、逼真,另外对中间的铜鼓纹花也进行了独创性改变,和传统的蜡染艺术图案不同。 最终的《和谐共生十二》画作是包含着传统蜡染艺术作品的特征,同时融入了作者洪福远个人的独创, 而形成的传统蜡染艺术作品的衍生作品。
三、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独创性的认定标准
(一)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独创性认定标准的理论基础
1.作品独创性的认定标准
作品独创性问题是著作权法基础理论研究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 同时也是著作权侵权认定中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对于特殊的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著作权纠纷来说也是如此。我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2 条对“作品”下了定义,从该定义来看,具有独创性是作品受到著作权法保护的必要条件,但目前我国《著作权法》中还没有关于独创性认定标准的具体规定。大多数学者持有的观点是两要件说,即作品具有独创性需要同时满足“独”和“创”两个方面,缺一不可。“独”意味着作者独立创作、源于本人,而不是抄袭他人的作品, 即使碰巧和他人的劳动成果完全相同,也符合“独”的要求。“创”要求作品中加入作者相当程度的智力创造, 可以体现作者的个性特点、独特的智力判断和选择。而对于某些特定类型的作品,例如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不仅需要具有创造性,还需要达到一定程度的创作高度,才能满足“创”的要求。在英美法系国家,对于独创性的认定要求较低,只要劳动成果中包含了作者独立的、辛勤的劳动并且有实际价值, 那么即使劳动成果不包含任何智力创造的成分,仍然是符合独创性的要求的,因此被形象地称为“额头流汗”标准。 虽然这个标准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防止自己的劳动成果被他人免费利用,但是如果一项劳动成果仅仅包括辛勤的劳动,而不包含任何智力创造成分, 例如编制一本电话号码簿,而拥有版权的话,那无疑是对事实和数据进行了垄断,将影响他人利用事实和数据进行创作,是不符合著作权法鼓励创作的基本宗旨的。 在以法德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国家, 著作权立法上更加注重作者的人格利益,保护作者精神权利,要求“独创性”不仅是独立创作, 还要有一定程度的智力创造水准。 例如《德国著作权法》规定著作权保护的是“个人的智力创作”, 这就清楚地表明作品必须包含智力创造性,而不仅仅是“额头流汗”。
2.衍生作品独创性的认定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独创性的认定标准,国际上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是认为衍生作品只需要“存在”独创性,便能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二是衍生作品必须拥有较高程度的独创性才可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形成不同观点的原因主要在于对民间文学艺术是否受保护不同,在民间文学艺术受保护的国家,对于衍生作品的独创性要求就较高,因为衍生作品是以民间文学艺术为基础而创作的,要求不高容易造成相差无几的衍生作品泛滥,无益于文化水准的提高; 而在不保护民间文学艺术的国家,认为任何人都是有权力利用民间文学艺术进行创作的,对于衍生作品的独创性就只需按照一般的作品来认定。
“在创制法的过程中,了解各种社会利益是创制法的起点……协调和取舍各种利益, 是创制法的关键。”[1]因此在研究法律问题时,利益平衡是必不可少的考量因素, 例如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是维护社会利益和个人利益, 而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是吸纳了民间文学艺术的精髓, 再加上作者的个人独创而形成的作品, 其中可能存在着和公共部分的民间文学艺术相同的部分,比如在《乌苏里船歌》一案中,虽然作者对其进行的大量的独创性改变, 但还是存在民歌的基本曲调, 因此其中必然包含着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 在认定其独创性时就需要结合两者进行考虑,以达到利益平衡。
(二)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独创性认定标准的司法实践
我国目前对于独创性的判断标准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 在有关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著作权纠纷中, 对于衍生作品的独创性认定大多选择和一般作品相同的判断标准, 即只需要具有最低程度的创造性就能获得著作权法的保护。但是,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是来源于公共领域的,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具有强烈依附性, 如果在判断衍生作品独创性时采用较低的标准, 那么创作者便很容易地就能垄断著作权,这对于公共利益来说是一种损害,而且对民间文学艺术的创造群体也是不公平的, 是不符合著作权利益平衡的立法目的的。
以蜡染案为例,法官在认定洪福远的《和谐共生十二》作品的独创性时,将涉案作品与黄平革家蜡染图案进行对比,认为其对鸟的外形、羽毛、脖子都进行了创造性的改变, 对中间的铜鼓纹花也进行了个人创作,与传统的蜡染图案有明显区别,而不只是简单的变化,因此认定其是具有独创性的,属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这样既能维护公共利益,也能够维护洪福远的个人利益,以达到著作权法的利益平衡。
四、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独创性的认定方法
在现有的独创性理论中, 创造性的高低没有明确的标准,只有通过作品的表达方式来“推定”,这是一个由形式到思想的反向认定, 需要考虑作品的细节、法律传统、产业政策和相关行业习惯。[2]因此,判断独创性问题不单单包含法律问题, 同时还需要判断复杂的事实问题。
(一)接触+实质性审查
对于侵权作品独创性的认定, 一直以来都是遵循国际上公认的公式:“接触+实质性相似”。 即如果被控侵权作品的作者有曾经接触原告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的可能性, 并且同时被控侵权的作品又与原告的作品有实质性相似的内容, 那么除非被控侵权人有合理使用等法定抗辩理由, 否则就将被认定为侵权作品。 其中“相似”的判定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涉及民间文学艺术时就更加复杂。[3]应当注意对于衍生作品相似性的认定不能泛泛地对比,要将被控侵权的作品与主张权利作品的独创性部分一一进行对比, 要先将原告的衍生作品与被告的作品进行观察比较,找出相同或相似的部分,再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比较, 观察这部分是属于公共领域还是属于原告独创性的部分。 如果是属于公共领域的因素,则被告不构成侵权;如果是属于原告独创性的部分, 就再证明被告是否有接触原告作品的可能性,如果有,则构成侵权,如果没有,则被告与原告作品相似就属于巧合,被告的作品符合独创性的要求,不构成侵权。
(二)引入专家辅助方式
在司法实践中, 一般对于作品独创性的认定都是由法官自由裁量,但是,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是属于特定的文化领域,与一般的作品不同,对于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方面,例如民歌、民族舞蹈等,法官未必能够准确判断衍生作品的独创性程度, 结果也许会有失偏颇。此时就需要专家学者作出专业的判断,给法官提供参考。 例如在王庸诉朱正本、 中央电视台、王云之著作权侵权案中,法官就参考了当事人提供的专家证人的意见,全面而科学地分析了《送同志哥上北京》与《长歌》、《十送红军》的区别,从而判断《十送红军》是否具有独创性。 但专家意见并不是独创性认定的决定因素, 最终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独创性的认定还是要由法官自由裁量。
我国一直以来是以文明古国著称, 因为我们有优秀的传统文化, 而民间文学艺术是我国璀璨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 并且随着文化软实力在当今综合国力的竞争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对于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应当引起广泛的重视。 目前,国内对于民间文学艺术衍生作品的研究比较少,也没有相关的法律保护,但是相关的纠纷却日益增多,因此对其独创性进行研究有其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