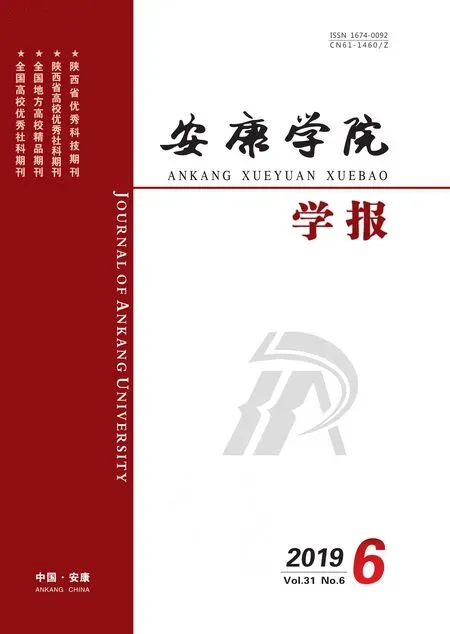生态危机下的人生悲剧
——以《无名的裘德》和《怀念狼》为例
余 珊
(安康学院 文学与传媒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自然生态是指自然界中生物的生存样态和布局结构,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生存处所及其境况。社会生态则是指人类在自我生命过程中,对生存处境的改造所形成的人工环境。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依靠自然生态结构来形成人类社会的生态结构,这种生态结构包括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处所及人口结构。人类作用于自然界,干预着自然界原有的生态结构,遂使自然界朝着紊乱及与人的对抗性方向发展。生态危机就是人化自然所导致的恶果,它体现在人类生存环境恶化、生物系统失调及人类伦理道德秩序紊乱等多方面,并最终导致了人类的悲剧。
一、《无名的裘德》与《怀念狼》中所呈现的自然生态危机
在农业社会,人类对自然界的人化局限于相对原始的顺应状态,对自然界的利用更多局限在种植、养殖、狩猎、采摘等方面。在这个阶段,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都非常有限,所有的生产生活都围绕着土地展开,生产资料与人紧密相邻。由于生活方式的趋同性,使得这一时期人们的社交网络相对单一,生活相对简单。随着生产力的持续发展,机械化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土地不再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而是转换成了资本,人力从农业生产中解放了出来。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剧烈变化,社交网络不再基于“土地”而展开,交际圈子开始流动,变得多元而复杂。人的力量被夸大,从最开始的利用自然变成了试图驾驭自然,对物质财富的追求不再是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而是为了满足更高的生活质量。农民们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资源,无法适应新的变化,他们既没有建立起新的价值理念,又无法在城市中立足,面对这样的生存困境,无所适从,到处漂泊。
在《怀念狼》中,捕狼队之所以可以盛极一时,就是因为村民与土地保持着极其紧密的关系。在村民看来,土地就是他们的家园,为他们提供生存所需,狼要共享家园,就成了他们唯一的敌人。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的力量逐渐强大,狼群被赶尽杀绝,自然生态环境变得恶劣,土地变得贫瘠,家园开始荒芜,由此衍生出来的社交关系开始瓦解。捕狼队解散,各商铺也随之关门,村民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他们无所适从,要么精神萎靡、瘫痪在床;要么神经癫狂,痛苦死去[1]。《无名的裘德》的女主人公淑处于社会的底层,生活的轨迹是从农村走向城市。她有着较高的智商,接受了一定的学校教育,拥有了相对独立的人格,曾做出过冲破传统禁锢、自由追求爱情的勇敢举动,但却始终无法明确自己的内心需求,激进的行为也被周遭环境所排斥。她脱离了农村生活,却又与城市气息格格不入,最终向传统道德做出了妥协,过上了行尸走肉的生活。
无论是《怀念狼》还是《无名的裘德》,它们都体现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农村的封闭生活被打破,面对新的生态环境,破产的农民们感觉到旧有的价值观念在被逐步摧毁,土地无法支撑起他们的生产生活。他们被迫远离土地,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试图顺应这个新的时代,构建新的社交网络,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这也就导致了自然生态危机的发生。
二、《无名的裘德》与《怀念狼》中所呈现的人类生态危机
人类技术的发展,使得人类从对自然的利用转变成对自然的改造,自然成为人类生存需要征服的对象。人类通过技术手段,把自己的意志延伸到自然界各个不同的领域,使得自然界中原有的生态不再以本来的面目呈现在人类面前。人类对大自然的肆意开采、人工水库及电站的修建、对大自然生物的广泛运用、对自然面貌的大幅度改造等一系列措施,使自然呈现出更多的人化痕迹,也使自然环境呈现出与人类生存的对立状态。一系列物种的灭绝、生物链的断裂及臭氧层的破坏等等,使自然界以“恶”的面貌呈现在人类面前,这规约着现代人的生存状态——焦虑与恐惧。生存在这个环境中的人处于无所适从的极度恍惚中,与此相应的人类社会的常态性生存,逐渐转换成一种不可捉摸的焦虑状态。这种无所适从感和焦虑感正揭示出工业社会及后工业时代带给现代社会人类秩序的紊乱。人不过是用来交易的符号,对利益的追求成了社会前进的唯一驱动力,人类的生态危机由此产生。
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作为一个独立人的存在,从未彰显过人的价值和尊严。阿拉贝拉把他看成通往锦衣玉食的阶梯,淑把他当成新女性必不可缺的一个门面,裘德对她们倾其所有,但于她们而言,裘德不是爱人、不是亲人、甚至不是人,只是一个可以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的工具。在《怀念狼》中,商州专员虽倡导建立生态保护区,但熊猫和狼于他而言,只是为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禁止捕狼令颁布时,他从未考虑猎人的生存困境,最终导致村庄变成生命的禁区;大熊猫难产死去时,他也毫不关心善后问题,最终导致专家疯癫,熊猫基地解散。
文艺复兴运动让古希腊就已经萌芽的人性得以复苏,人文主义驱赶了神性,人性得到弘扬。近代科技的发展以及启蒙运动的兴起,人的理性精神得到了张扬。人们开始推崇工具理性,人的主体化进程加快,二元对立哲学思想的形成,使得人类的中心主义思想得以建立。人类中心主义思想极力倡导人类的主体地位,它认为人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独特存在,应该不遗余力、不惜代价地追求自我价值,唯“我”才是意义的彰显。这使得人们为了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对他者的生存状态置若罔闻,这就是人类的生态危机。
三、《无名的裘德》与《怀念狼》的悲剧性
生态文学“表现的是自然与人的关系,而落点却在人类的思想、文化、经济、科技、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上。”[2]人既是自然的人也是社会的人,当自然生态出现危机时,社会生态也会出现问题。对自然的过分索取,人与人之间的恶性竞争以及道德的沦丧等等,都会导致社会环境的失衡,而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失衡将会导致异化的发生。所谓生态异化,简单来说,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即“人与自然之间的双向控制和奴役”[3]。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人类中心主义的盛行,人们把自身利益作为最高价值。为了实现最高价值,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放大,对自然的索取与征服不断加强,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加剧,最终导致了生态异化的发生。这种生态异化,从表面看是由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所导致的,但实质上是人与人之间利益冲突的结果。在《怀念狼》中,傅山与子明刚回村时,村民们争先与之攀谈,几乎全村的村民都和他们有着亲戚关系,大家一团和气。可是当子明阻拦傅山杀狼时,村民们把对狼的恐惧转变为对子明的厌恶,进而捆绑、殴打子明。当傅山再次拒绝打狼时,他们不再把他当成英雄,而是用最恶毒的话侮辱他。生态系统本就包含了人在内的所有生命,人本应从整个自然生态系统的角度去看待和解决问题,应该把维系整个生态系统的持续发展作为一切行动的根本目的,但对于雄耳川村民而言,自身利益才是衡量一切事情的根本标准。当冲突发生的时候,亲人和狼对他们而言,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可以被消灭的对象。即便狼群是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村民也与狼群为敌;即便傅山和子明是他们的同胞,彼此之间也不共戴天。人与自身分裂,自己与自己为敌,生态异化发生,最后只能自食生态异化的恶果——人性消失殆尽,兽性肆意横行,人物的悲剧命运不可逆转。
健康的生态环境应该是一个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组成的全面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每一个生命都不可或缺,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必然会出现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资本主义社会“把自然当作某种完全供人类享用的原料,其最终目的是全面控制自然”[4],而对自然的全面控制必然会走向对人的全面控制。不管是自然生态还是人类生态,为了达到控制效果,都必须消除一切不和谐的因素,树立权威观念。把生产劳动中所形成的统一观念,以民间习俗或是官方法律的形式推广到其他领域,形成了约束和控制的局面,衍生出了统治与被统治的概念,在被统治阶级进一步分化出服从与反抗这两种情况。国家意志会宣扬服从的重要性,同时对反抗者进行惩戒以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对于《怀念狼》中的雄耳川村而言,全体村民就是权威,子明和傅山就是异己者和反抗者,村民对于他们,先是拉拢,后是排斥,继而伤害,直至傅山“归顺”,子明被赶走,村庄变成了生命的禁区。生态异化的本质就是对多样性的抹杀,对全面共同体的破坏,它既表现为对他者的排斥,也表现为集团内部所形成的主奴关系。在《无名的裘德》中,裘德与淑一生被驱逐、被迫害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安于“奴”的身份,做出了一系列的反抗行为。裘德上进好学,但他属于被统治阶层,进入基督寺继续深造是超越阶级的行为,理所当然就被拒绝;淑与裘德真心相爱,自愿同居,但因为不想有法律层面的婚姻关系,于是遭人排斥,举步维艰。裘德与淑都有超越自己阶级属性的梦想,也凭借一己之力对约定俗成的观念做出了反抗,但两人最终都走向了消亡。生态环境本该是开放式的,每一个人都是联系他人和共同体的中介,他者是对于自己的补充,对他人的肯定就是对自己的、甚至是对自然界乃至整个生态环境的肯定[5]。但当生态异化发生时,共同体被破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组合,人群被简单划分成“我”与异己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服从者与反抗者,在不健康的生态环境中,后者会被排斥在社会圈之外。裘德与淑的悲剧是被排斥的悲剧,这种排斥是由具有话语权的统治阶层来执行的,但更多的排斥来源于他们的周遭环境,是“奴”对统治秩序的盲目维护,是“奴”对“奴”的残杀,是普通人之间地互相伤害。
四、《无名的裘德》与《怀念狼》的生态展望
哈代认为,所谓悲剧,就是“表现人生中这样一个处境,即这种处境不可避免地要使他的某个目标或欲望——在即将付诸实施时——以毁灭性的灾难而告终”[6]160。两部小说的主人公们都想追求自我价值,在追求价值的过程中都曾非常执着,但都无法实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无疑是悲剧的。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两部小说探讨的基本问题和终极问题都是个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主人公都无法和自然和谐相处,生态危机随处可见。但是仔细分析,两部作品的悲剧色彩还是有所不同,这源自作者不同的生态展望。
在《无名的裘德》中,基督寺具有特殊的象征意义。年幼的裘德从乡村教师菲洛特桑的口中得知了基督寺的存在,他曾多次跑到远离村庄的一座房子的房顶上去眺望。在他看来,“那是一座光明的城市,知识之树就长在那儿……那座城市,是人类的导师出现的地方,也是他们荟萃的地方,那是一座你可以叫作是用学问和宗教来守卫着的城堡……那正是于我适合的地方”[7]。在理想光环的照耀下,裘德孜孜不倦地读书,尽管他后来又要照料面包房,又要去学石匠,但依旧没有放弃过所追求的理想。直到他遭遇种种挫折,直到他所崇敬的神父亲自写信劝告他要安于工人阶级的身份,他才明白,基督寺不仅仅是由学问和宗教守护的城堡,更是一所封闭式的哥特式建筑,是维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意识形态城堡。裘德不断靠近基督寺的过程,其实是他的身份转化过程,由农民阶层转向工人阶级。但不管个人多么有才华、自我身份如何变化,基督寺都是无法逾越的鸿沟。这座古老的建筑就是一道分界线,它将完整的世界人为地割裂开来。在威塞克斯的农村环境被彻底毁灭之后,以裘德为代表的破产农民们进入了城市,于城市而言,他们格格不入。基督寺的永存就意味着一代又一代的裘德们不管怎么努力,其悲剧命运都无法逆转。
《怀念狼》中,金香玉也极具象征性。虽然小说中弥漫着作者对世态、人情、文化、文明的悲观态度,但是金香玉却始终散发着淡淡的幽香。金香玉原本就是埋藏在土里的天然玉石,老道士救了狼的命,狼衔来玉石报恩。他有金香玉的消息不胫而走,各路人士连蒙带骗,使尽手段想把宝石占为己有。金香玉越来越少,人与狼、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老道士下葬,狼群赶来送别,衔来了最后一块金香玉,最终玉石不小心被打碎,化为了尘土。外人们喜欢金香玉是因为它价值连城,老道士不断赠予却是因为玉石可以给他人带来福报。金香玉由报恩而来,由于利益引起纷争,最终又消失殆尽。狼群衔金香玉而来是为报恩,它象征着和谐的生态关系;玉石香消玉殒的过程,象征着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仅存的玉片被摔碎预示着生态异化的终结。金香玉其实完成的是一个循环,从泥土中来,回自然中去。“生态批评强调人与自然环境的互相依存的关系,是从人本主义向生存环境的转换,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关联被视为人的生存所面临的一个终极问题,人不应是人类生存活动的中心,而只是一个组成要素,与自然环境相辅相成,共同构成适应生存活动的生态体系。”[6]25在作者看来,所有的利益纷争都会消失,人与自然最终能够融为一体,生态环境可以重返和谐。
五、结语
《无名的裘德》的时代背景是科学技术大爆发的维多利亚时代,人们依然陈旧的思想观念与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剧烈的碰撞。裹挟其中的普通人目睹了农村经济的凋敝,工人阶级的破产,贫富差距的增大等等诸多社会问题,他们受苦受难,但上帝无动于衷,于是他们无所适从,随波逐流,直至消亡。作为哈代威塞克斯系列小说中乡土气息最淡的一部,它既展现了农业文明中田园牧歌式的和谐之美的荡然无存,又展现了个体与社会环境不相容所产生的恶果——生机勃发的生态环境遭到毁坏,悲剧发生的无法逆转。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发展重心从农村转向了城市,轰轰烈烈地开启了它的城市化进程。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的需求急剧增加,人的无限欲望与自然的有限供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人类能力的极速膨胀,使得自然生态和人类生态都面临严重的危机。《怀念狼》刻画了人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自我膨胀之后所产生的后果——自然资源面临枯竭,人与人之间尔虞我诈,生态系统的完整性遭到严重破坏,人即将自我埋葬。两个文本中都出现了生态异化,哈代让主人公几经挣扎,但都无果,由此展现出作者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叔本华式的悲观态度;贾平凹则是在抨击生态异化的同时提出了自我拯救的可能性——人与世间万物以伙伴关系的方式互相帮助,和谐共处,这既是作者对于生态环境的诗意想象——这种想象代表了作者对于修复生态环境的乐观态度,也是人类生态观发展的必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