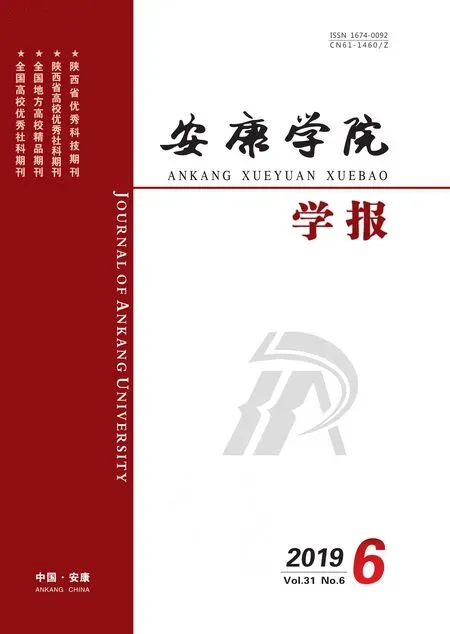《尘埃落定》的儿童叙事研究
白若凡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以往对一段历史的叙述,创作者惯用宏大的全知视角保持对历史理性的延续,而傻子叙事往往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于荒诞的、无规则的、自由的叙事。当叙述者失去了原有的权威,其严肃性便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傻子的语言和情感,这就不得不让人怀疑历史是否真实。如果说,一段历史或故事的叙述者,他的权威性决定了历史或故事的真实性,那么叙述视角的转变无疑对历史或故事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在小说《尘埃落定》里,儿童叙事与傻子叙事的交织与浮现便印证了这样的挑战。
一、被遮蔽的叙事
在《尘埃落定》中,傻子叙事替代了权威的历史叙事,这是文本带给我们最直观的体验,傻子所具有的呆傻特性并没有使文本发生常理上的混乱,他的叙述是非常自然而完整的。同时,“傻子是否傻”这个疑问贯穿了整个文本,并通过小说人物之口做出了反复的解答。从小说一开始,傻子就已经回应了这个问题,“我是个傻子。我的父亲是皇帝册封的辖制数万人众的土司。所以,侍女不来给我穿衣服,我就会大声叫嚷”[1]4。这里对“我是个傻子”的因果做了非常刻意的解释,由土司醉酒所生的儿子,不穿衣服而大声地叫嚷,以至所有人(包括“我”)判定“我是个傻子”。这同时说明,傻子的“傻”是被误解的,这样的“傻”更类似于孩童的嬉闹,只是孩童的特性表现在“我”的身上,这不符合常人的认知,于是“我”便成为众所周知的傻子了。因而在小说里,傻子身体里潜藏着一个儿童,一个被定义为“愚笨”的顽童。在这个层面,叙述者的身份并没有越界,在显性文本中,依然是傻子在叙述一切,但同时存在着一个潜在的叙事结构——儿童叙事,它被“我是傻子”的反复证明遮蔽了。视角的转变并不意味着越界,儿童潜藏在傻子的意识底层,儿童特有的游戏心理使得叙事发生了奇妙的变化,这种变化成了文本内部一条时隐时现的叙事线索,掌控着叙事的节奏与速度。
二、儿童叙事的隐与现
(一)时间开始了
童年对于“我”,是从十三岁开始的,除此之外“我”的年龄增长在文本中皆是模糊的。“我记事是从那个下雪的早晨开始的,是我十三岁那个早晨开始的。”[1]14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叙述。一般来说,十三岁已经越过了童年的时间节点,但生理年龄的限定并不意味着童年的结束,儿童心理的特性从“我”的十三岁开始显现,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童年开始了。值得注意的是,从“我”睁眼看世界到“我”的第一次记事(完成了成人礼),作家以非常快的叙事速度和篇幅完成了这一过程。一个婴儿从脱离母体,啼哭,睁开眼睛,学会走路,度过童年,长大成人,这在生理上是必须经历的阶段,而“我”则是通过害了雪盲—蒙上眼睛—卓玛要走—甩掉蒙蔽眼睛的毛巾—与卓玛完成了成人礼,模仿并加速了这一阶段。到这里,“我”虽完成了身体上的成长,似乎成了一个成人,但这一成长并没有使“我”真正成为成人,“我”仍处于童年,卓玛的到来无疑为仍是儿童的“我”的性意识提供了爆发的契机,这种契机同时是合法的。因为“我”是土司的儿子,并拥有一个十三岁少年的身体,而卓玛是女仆,于是一切便合理地发生了。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从童年跨越到了成年的阶段,“……对男性和女性关系的理解,总是带有某种片面性。这个片面性就是,他们认为一种身体的自觉,就是一个人长成的一种标志”[2]。作为叙述者的“我”,借用傻子的外衣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婴儿由三岁起,即显然无疑地有了性生活”[3]。叙述者潜意识中幼年经验的显现并不是个例,在很多作家如莫言《透明的胡萝卜》中已经存在。总的来说,成人并不意味着儿童记忆和心理的结束,而恰恰代表着顽童隐藏在叙述者背后,开启了小说情节的大门。
卓玛的出嫁剥离了“我”对童年记忆的依恋,而一旦孩童失去了所爱便会哭闹,在“我”的身上便表现为情感的宣泄和转移,塔娜的存在代替了卓玛在“我”心里的角色。相似但不同的是,“我”承认自己“已经长大成一个真正的男人了”,“我听到自己的声音一夜之间就变了:浑厚,有着从胸腔里得到足够的共鸣”[1]103。在这里,叙述者“我”——这个孩童,而不是傻子,用自己装扮的浑厚的成人声音掩盖了孩童式的逆反心理,那是因为卓玛在此之前曾说:“我喜欢他是个大人,喜欢你是个娃娃”[1]64。这样的心理导致了“我”一定要用同样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成长以获得卓玛甚至是官寨里所有人的注意,于是塔娜的出现帮助“我”从心理上转变为成人,但实质上,叙述者只是暂时地装扮为大人,其叙述的语言仍充满了孩童式的稚气和逻辑。在所有人包括读者接受了“我”已经在文本中转变为真正的成人,使这个隐秘而巧妙的谎言暂时实现的时候,儿童叙事的力量衰弱了。之后,作为土司家成年的儿子,“我”被派去巡游麦其家的领地,人们即使对“我是傻子”有所怀疑,但无疑不会将“我”当小孩来看待了。“我”已经成为大人,没有人能怀疑。
(二)浮现与复活
叙述者的谎言并没有持续很久,儿童式的叙事再一次浮现了。当“我”和哥哥送走远道而来的姐姐后,“我”和哥哥之间有一段关于“我不是傻子”的辩论,哥哥坚持“我”不是傻子,而“我”告诉哥哥“我”不可能不是傻子,土司在“我”和哥哥之间做了裁决,结果是“我”确实是个傻子。“父亲伸出手来,抚摸我的脑袋。我心里很深的地方,很厉害地动了一下。”[1]165在这里,土司作为父亲的情感是复杂的,但更多的是将“我”当作一个“傻孩子”来看待,“我”在此刻与父亲的距离是最为亲近的,父亲亲昵的举动唤醒了孩童心里最柔软的最需要父母关爱的那部分,伪装的成人世界被点亮了,可惜的是,这种父子之间的感动只是短暂地存在过,很快就熄灭了,那个属于孩童的心理世界仅仅浮现了一瞬,便又回到了成人的世界。
在这之后,傻子的叙述声音逐渐减弱了,这样的转变发生在“我”去北方边界之后。“我”的所作所为更让众人信服,“我”是大人并且是个聪明人,与曾经那个傻子,那个顽童早已告别。聪明人充当了叙述者,“我”的言语合乎逻辑,“我”的行为符合一个聪明人的标准,“我”知道怎样在拉雪巴土司和茸贡土司之间得到胜利。小说的叙述者似乎开始恢复正常的叙事,傻子消失了,顽童也消失了,“我”具有了聪明人的狡黠,先知般的智慧,而小说的情节却开始走向枯燥,原先那些人物的轻巧和语言的奇妙也似乎失去了活力。这也许是成人世界的黯淡、权力的介入和聪明人自作聪明的愚拙所带来的效果,相反地,它也是儿童视角所能打破的束缚以及所能扩展的叙事边界。直到“我”遇到草原上的卓玛,叙述者背后的儿童才又得以暂时地复活。
厨娘卓玛目睹了草原卓玛与“我”在温泉里的欢爱,小说的叙事空间发生了重叠和扭曲。拥有同一个名字的两个女人,在同一个地点出现,目睹或经历了同一事件的发生,厨娘卓玛因此受惩罚要被挖掉眼睛,但她却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赴死之前卓玛在温泉的情节颇具诗意,厨娘卓玛唱着歌,那个年轻活泼的侍女卓玛又回来了,侍女卓玛的“复活”在同一时间复活了孩童时代的“我”。可是卓玛的复活却是暂时的,“我”意识到自己对卓玛的牵挂就此了断了,此时孩童的视角也得以重启。但卓玛很快恢复到厨娘卓玛的身份中来,“我”却还停留在孩童的记忆里,这一发展激怒了叙述者,其背后的孩童又出现了,“当你的厨娘去吧,做你的银匠老婆去吧”,“再打你一下,我会更高兴”[1]190,这样的气急败坏和无理取闹重新燃起了鲜活的叙事风格。尽管在此后“我”在北方边界直至重回麦其官寨仍然具有傻子和聪明人双重的矛盾特性,但儿童视角一直以若隐若现的方式延续着,直至最后的高潮与终止。
(三)加速的叙事
小说情节发展到“我”从北方边界重回麦其官寨,“我”所带来的奇迹让狂欢的人群更加沸腾了,被人群涌向麦地的“我”完成了被拥立为权威的仪式,这就直接导致了麦其土司将土司的位置让给大儿子旦真贡布的举动,与此同时重新恢复语言能力的翁波意西质疑了麦其土司的决定。翁波意西的话推翻了小儿子是傻子,大儿子是聪明人的判定,但最终权威战胜了历史,翁波意西再次失去了舌头,成了哑巴。土司让位与翁波意西失去舌头,意味着“我是聪明人”“我是成人”“我是麦其土司的合法继承人”全都被否定了,那么“我”反抗的形式便是和翁波意西一样不再说话。不同的是,翁波意西成为哑巴是被动的,他的舌头是被强力剥夺的,而“我”再一次成了顽童,做出孩童逆反父权的举动,“我知道书记官已经再次失去舌头了,这种痛楚是从他那里传来的。于是,我说:‘我也不想说话了’”[1]272。“我”决定和翁波意西一起承受被否定的痛楚,那就是翁波意西建立的真实历史被压抑的痛苦,以及“我”建造的成人世界被毁灭的绝望。叙事在这里并没有停止,“我”成为一个哑巴更像是一个顽童回归了婴儿时期,回到了最初的原始状态,同时叙述者再一次出发,并加速了这一过程。
不被承认的“我”再次回到了边界,那是“我”建造的独立王国。回到边界的“我”,多次感觉到“时间过得越来越快了”[1]313。叙述者在最后仅仅用了几十页的篇幅覆盖了土司最后的聚会、外来汉人的到来和土司制度的崩溃。而“我”并没有将沉默延续太长的时间,回到边界以后“我”和身边的人都迅速长大了,“我不知道他们多少岁了,就像我不知道自己现在多大岁数一样。但我们都长大了”[1]323。当“我”意识到长大,作为叙述者的“我”开始变得焦灼不安,在“我”眼中,土司们最后的聚会像是最后的狂欢,当有颜色的汉人到来,“时间变快了,而且越来越快”[1]353。叙事的节奏越来越紧迫,时间和情节的速度一晃而过,叙述者背后的儿童退到了幕后,那些有关土司和汉人的叙述,便由长大的“我”来代言。此时的“我”既不是傻子,也不是聪明人,没有对爱人的依恋,也没有对父母的依赖,最后的叙述非常平淡,好像叙述者已经成为这段历史的旁观者,冷静而克制。
(四)“自杀”的叙述者
叙述终于要终止了,麦其家族历史的终结也到来了。在终止之前,“我”又回到了童年。“我醒来了,发现自己睡在小时候住的那个房间里,就睡在小时候的那张床上。就是在这里,那个下雪的早晨,我第一次把手伸进了一个叫桑吉卓玛的侍女怀里。”[1]372这意味着童年记忆再一次的浮现,但叙述者在最后并没有完全以孩童的视角去打量周围的事物,面对麦其土司家族最后的灭亡,单一儿童视角的力度是不够的。在叙述者的身体内部有两个声音交织着,属于成年人理性的视角完成了与汉人对话的任务,“他”需要面对真实可感的崩塌,而在儿童视角,“我”需要面对自己的死亡。面对麦其家的仇人,“我”并未反抗,因为“我”需要通过被复仇杀死自己,同时也杀死叙述者。在麦其土司官寨倒塌之后,麦其家的傻瓜儿子也一同与麦其家族消失了,“我”存在的意义没有了依据,因为属于麦其家的时代已经成了历史。于是,麦其家的仇人杀死了“我”,在此时,“我”不是麦其家的傻瓜儿子,也不是一个聪明的商人,“我”的身份最终保持着最原始的状态。对于死亡,“我”没有任何反抗,甚至带着戏谑和游戏的心理,与其说“我”被杀死了,不如说“我”借用仇人的刀杀死了自己。
三、限制与消解
儿童作为叙述视角之一,拥有其他视角所不能触及的叙事范围。在《尘埃落定》里,儿童叙事只是一条时隐时现的线索,而不是唯一的。叙述者内部潜藏的儿童,更像是一个顽童,他被赋予了土司最后一个时代沉重却又轻如尘埃的历史。有趣的是,顽童并不时时背负历史,而是自由地嬉戏,他出现在不经意的文本当中,永远也不忠于严肃古板的历史叙事。
首先,儿童叙事消解了文本中成人世界与权力世界的规则。以儿童视角来看,成人世界的复杂性被简化了,土司之间的冲突和战争,主人与仆人之间的从属关系不再遵从世俗意义上的定义,土司最后一代的历史被置放在个体所能触及的范围内。换句话说,《尘埃落定》里对于个体生命、宗教与权力、制度的建立与崩塌的阐释是远远大于一段历史的重现与记录的,儿童叙事的介入无疑将历史解构了,就像是一个顽童闯入了成人世界,那些有关成人与权力、宗教与制度的表达,由于儿童视角的切入变得单纯而直白,土司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宗教是什么?土司便是土司,历史便是历史,宗教便是宗教,反言之,同样成立。那些力图被证明的无解命题,在《尘埃落定》里,通过一个潜在的视角做出了一种解答,尽管这种解答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正确的,但却是独特的,是值得被思考和阐释的。
其次,儿童叙事也具有不可靠性。儿童叙事所能达到的叙事边界是有限的,它为小说本身带来了一种奇特的诗意,这种诗意异于成人语境里熟透了的“诗意”,它是干净的、单纯的、虎头虎脑的、横冲直撞的,在这个层面上,小说是具有诗性的,但不等同于史诗。《尘埃落定》并不具备史诗的要素,它没有民族的英雄主义色彩,也远远达不到对一代历史的传颂,更没有绝对久远的史诗距离。创作者也证实了这一点,“我知道我将逃脱那时在中国文坛上关于历史题材小说,家族小说,或者说是所谓‘史诗’小说的规范。我将在这僵死的规范之外拓展一片全新的世界,去追寻我自己的叙事”[4]。《尘埃落定》不是一部史诗,但小说存在诗性,作者借助这种诗性呈现了一段“似史诗”的故事。若换一个角度,由一个盲诗人讲述一段久远的土司历史,像《伊利亚特》 《奥德赛》一样,那便是一部史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