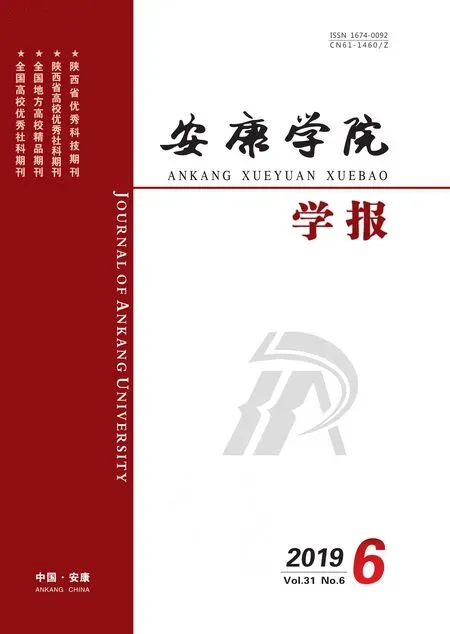对话中的升华
——《〈文心雕龙〉三十说》
吴婉婷
(陕西理工大学 文学院,陕西 汉中 723001)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文论著作,对它各角度的研究从齐梁至今方兴未艾。其中,围绕版本、校勘、注释、音韵等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世纪末,文学繁荣的景象带动中西文学的交融,美学、文学理论等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学者加入文学研究这一行列,并为中国文学文论研究增添新的路径。“国际交流的日益发展,也加强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国际合作,大家称《文心雕龙》的研究为‘龙学’”[1]323。童庆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学者,长期从事美学、中国古代文论、文艺学、文艺心理学、文学文体学等方面的研究,他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打开了“龙学”研究的新局面,最终将研究成果汇集成《〈文心雕龙〉三十说》(以下简称《三十说》)出版发行。
“在古代文论的研究中要采取古今对话的学术策略,这个策略包括以下三点:历史优先原则、对话原则、自洽原则。”[2]在《三十说》开篇的《中国文学之道的美学解说》一文中,童庆炳就说明了其研究《文心雕龙》的旨趣,要在文学理论的范畴,重视古今比较,运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对《文心雕龙》进行研究。这种研究思想突出表现在他对“对话”精神的运用上。“只有通过各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对话,才能促使‘世界文学’时代早日到来。”[3]“传统、西方、当代本土——中国当前的‘三方会谈模式’,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被舍弃,同时也都很难以形成‘独语’的局面。”[4]
一、古今对话
童庆炳长期从事文学基本理论问题的教学与研究,对中国古代文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而开始了对《文心雕龙》的研究与教学。在《三十说》中,童庆炳一直在用自己的文学理论知识研究《文心雕龙》,使《文心雕龙》焕发出新的光彩。
(一)与古代文论的对话
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大成之作,在童庆炳的《三十说》中,他将刘勰提出的观点直接用古代其他文论知识加以说明,形成了与古代文论之间的对话。在《〈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一文中,为理解刘勰的“原道”思想,童庆炳列举了产生于《诗经》的“兴”,并对“兴”进行解释说明,进而得出“异质同构”的概念。同时将“异质同构”与儒家的“君子比德”进行比较,说明人们看重的是物体所象征的精神意识,并用《论语》中的《子罕》篇、《雍也》篇印证。同样在《〈文心雕龙〉“比显兴隐”说》一文中,童庆炳引用钟嵘的《诗品序》说明“兴、因物喻志”的特点,又用《诗经·关雎》中的强调“兴”对于诗文在“气氛、情调、韵味、色泽”上的重要性。在《〈文心雕龙〉“胸中意象”说》一文中,童庆炳指出刘勰的“意象”来源是《庄子·达生》中的寓言,给刘勰理论启发的是《周易》。他指出:“中国古代理论能够说清楚如何将思想感情表现在语言文章上的首推《周易》。”[5]138《南齐书·文学传论》是我国南朝时期一部重要的文论作品,童庆炳在《〈文心雕龙〉“自然成对”说》一文中引用萧子显在《文学传论》中的说法,证明当时文坛出现的“文章殆同书抄”的特点,证实刘勰受当时思想倾向的影响,认为典籍和博见比生活经验要重要,也比生活经验难以练就,这就是刘勰在《丽辞》篇中提出的“征人之学,事对所以为难也”[6]。
(二)与刘勰的对话
文学理论的研究一定要和具体的文学文本分析相结合、与文本产生的时代相联系、与文学发展的历史相观照,来探讨文学理论概括的文学基本原理。因此,童庆炳在《三十说》的研究中,立足文本,还原刘勰时代的社会政治、文学风貌、习俗风尚等特点,并对刘勰的观点态度进行分析和研究。在首篇《中国文学之道的美学解说》一文中,童庆炳就对刘勰其人及《文心雕龙》成书原因进行了探讨,揭示当时活跃的社会氛围、谈玄之风、“文学的自觉”发展等社会大环境。童庆炳将自己置身于刘勰生活的大环境中,来感受刘勰的创作历程。在《〈文心雕龙〉“感物吟志”说》一文中,对于刘勰所说的“物”,一般研究者将它理解为“外物”,是一种绝对的理念,童庆炳则指出刘勰说的“物”是诗人的对象物,他把诗歌看成密切相连的多环节复杂系统。在《〈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一文中,童庆炳既是充满问题意识的质疑者,又是立足《文心雕龙》文本的问题解答人,从而将刘勰的原典放于文中,分析刘勰面对当时文坛的“穷”如何来“变”,又是怎样提出“会通”,阐释“变则其久,通则不乏”的原理。在其篇章中童庆炳都是坚持用刘勰的观点作为基础,来探讨各家学术优缺,与刘勰形成对话互动,从源头上力图将真实的刘勰、真实的《文心雕龙》理论展示出来。徐复观在《答辅仁大学历史学会问治古代思想史方法书》一文中谈道:“先让材料自己讲话,在材料之前,牺牲自己的任何成见”。[7]童庆炳多次表达对徐复观的敬重,在对待古文论材料时,其治学态度亦与徐复观相承贯。
二、名家并参
童庆炳的《文心雕龙》研究并不仅仅局限于对自己的研究方法与研究成果的呈现,而是将自己的心得和“龙学”研究者的菁华放在一起进行整理归纳,形成对于刘勰理论的百家争鸣、和谐共处的局面。针对各家的研究成果,童庆炳始终保持高度的尊重,从前辈的研究结论中得到灵感和创新,正如朱熹所言:“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文心雕龙》能成为中国文论的最高典范,“是与名家的论述形成互文和对话关系,进而把《文心雕龙》推至文章学或文论经典的地位”[5]17。
(一)与不同理论观点的对话
《原道》是《文心雕龙》的首篇,其中对于“道”的解释,历来是讨论的热点。《三十说》中《〈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一文就列出了对刘勰的“道”的四种解释,其中有“儒家之道”“道家之道”“儒道两家之道”“自然之道”。童庆炳比较赞同“自然之道”。他在黄侃和刘永济的观点的基础上又提出自己的见解,既聆听他们的雅教,更揭橥自己独到的理解。童庆炳认为刘勰的思想不是受一家或两家思想的影响,而是在儒、释、道、玄等多种思想的基础上渗透演化出来的,其中包括自然美、人工美,以及艺术美的天、地、人、文并列的整体艺术思想。
通览童庆炳的《三十说》可以看到,他对于黄侃、范文澜的研究成果是比较重视的,但并不是把他们的观点作为评判的标准去衡量,而是让他们平等地参与到对话之中。在《〈文心雕龙〉“体有六义”说》一文中,童庆炳就列举了徐复观的《文心雕龙的文体论》,点明徐复观对黄侃、范文澜关于“道”解释的不满,以及对郭绍虞、刘大杰关于“文体”观点的不满。在《〈文心雕龙〉“‘文体’四层面”说》一文中继续对文体中有无心志因素参与进行探讨,其中重点介绍了徐复观和龚鹏程的观点。徐复观认为,文体出于性情,将文体分为体裁、体要、体貌三个基本要素,而龚鹏程则认为,文体是客观知识,与作者的心志内容无关。童庆炳认为,徐复观不能明确文体四要素及其关系的理解,龚鹏程则混同了文体与文类。他将刘勰的文体观念分为四个层次,即体制、体要、体性和体裁,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更准确地把握了刘勰的文体观。此观点的得出是童庆炳参与到郭绍虞、刘大杰、徐复观、龚鹏程的集体对话中,兼听并照,慧心衡鉴而得出的。
在《〈文心雕龙〉“会通适变”说》一文中,对于刘勰在《通变》篇中所侧重的到底是“通”,还是“变”。童庆炳列举出以纪昀、黄侃为代表的“复古”说,以刘永济为代表的“常变”说,以陆侃如、牟士金为代表的“继承革新”说。在《〈文心雕龙〉“循体成势”说》一文中,对“势”的解说,童庆炳列出以黄侃为标准的“法度、标准”说,以刘永济为代表的“体态”说,以陆侃如、牟世金为代表的“表现形式”说,以詹锳为代表的“风格倾向”说,以王元化为代表的“文体风格”说。在《三十说》的其他篇章中,童庆炳也在论述中陈述了各家的不同观点和思想,对于这些观点童庆炳一直是用平等的态度去看待,让各家的思想都能在他的文章当中参与对话,达到各种学术上的交流,进而深入思考与刘勰观点更加契合的解释。
(二)与同类作品的对话
童庆炳在《三十说》中提到的各种关于《文心雕龙》的研究书目有很多种,从这些经典的研究著作中童庆炳保持着赤子之心,从中汲取着观点和看法,去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加以创新。正如姚爱斌所言:“在这些‘龙学’成果面前,童老师是严谨的,他尽量不埋没任何一项有价值的前人发现;童老师是谦虚的,他总是对前人的‘龙学’成就给予充分肯定;童老师又是勇于精进的,他总是能够在万水千山之外再辟出一片新天地。在阐释《文心雕龙》中的每一个范畴或命题之前,童老师都会细心梳理相关问题的‘龙学’历史,斟酌其得失,又在梳理和斟酌中透出自己的眼光和境界,伏下推陈出新的理念和思路。”[8]
纪昀对《文心雕龙》的评语体现了“辨章源流、考镜学术”的治学宗旨;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一书对《文心雕龙》的文本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剖析,将前人的见解与自身的学术理论进行融汇,开拓了《文心雕龙》研究的角度和风气;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一书取材丰富,注重文字校勘,以注为论;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一书对《文心雕龙》的论文主旨和文论研究精明简要;徐复观的《文心雕龙》研究较早对刘勰的创作思想做出全面深入分析;詹锳的《文心雕龙义证》一书引证广博,按断慎重;等等。这些著作上起清代,下迄当代,地域涵盖海峡两岸,他们在童庆炳《三十说》中反复“登场”诉陈自己的识见,在双向互动之中体现了童庆炳对“龙学”研究史的梳理及其严谨认真的学术态度。“对话就是交流,交流的结果就是对问题的认识和总结,总结《文心雕龙》研究发展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在一些薄弱点上投入大量的研究力量,同时寻找新的研究角度和切入点,这才可能使《文心雕龙》研究跨上一个新的台阶。”[1]596
三、中西文论的晤语
童庆炳说:“我从长期的文学研究、文学教学和文学创作中体会到,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文学作品和文学欣赏总是带有一定的共同规律的。”[5]29这种共同的规律,就会产生出相类似的文学理论。从时代先后来看,中国古代文论虽然不可能受到西方当代文论的影响,但现当代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却不由自主地受到西方的影响[9]。童庆炳在最初的研究中一直致力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建设,对于西方的文学理论有深入的研究,之后发现并开始探究中国古代文论的艺术魅力。在《三十说》中,童庆炳就将西方的文学理论运用到自己的文章当中,在中西对话之间,将自己论述的观点表达得更加准确,让中国古代文论焕发出新的活力。
在《〈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新探》一文中,童庆炳将刘勰的“原道”说与阿恩海姆的“异质同构”说进行比较。面对鲁迅和蒋祖怡对刘勰“原道”思想的质疑,童庆炳用“异质同构”说进行解释。他指出刘勰将天、地、人并举归为一类,是因为三者“都具有文采”,可以“把外在的自然,衍化为内在的人的情感,不同质却可以同构,天文、地文就这样变成了人文”[5]65,这样就清楚回答了鲁迅和蒋怡祖的疑问。
在《〈文心雕龙〉“风清骨峻”说》一文中,对于刘勰“风骨”论中关于内质美的论述,童庆炳将它与黑格尔的“意蕴美”进行比较。黑格尔“意蕴美”理论中的外在媒介,和通过外在媒介指向内在的意蕴,正好对应刘勰所说的骨即文辞、风即文意。童庆炳进一步指出,对于意蕴黑格尔并没有进一步说明它的美学范畴,刘勰则对文意有特殊的美学追求,这就在中西理论的对话中进行优势互补。在《〈文心雕龙〉“杂而不越”说》一文中,童庆炳引用苏珊·朗格的“生命的形式”理论对刘勰的作品生命形式是什么,做了进一步补充说明。
在《〈文心雕龙〉“情经辞纬”说》一文中,对于刘勰的诗情需“蓄愤”“郁陶”的观点,童庆炳认为这和华兹华斯的“沉思”说、托尔斯泰的“再度体验”说、苏珊·朗格的“非征兆性情感”说是一致的,他从对这些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理论的分析中得出刘勰普遍意义的文学艺术规律。
在古今中外不同理论对话的过程中我们还应该看到,“中西文化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而应该是‘对话’问题。这里有两个对话,一个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对话,一个是传统与现代的对话……‘对话’是平等的对话”[10]。中西理论没有绝对的一致,也没有绝对的对错,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见解和主张的出现,也乐于看到百家争鸣的理论碰撞。
在《〈文心雕龙〉论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中,童庆炳指出,对于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在中国是一个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最早在《诗经》中就有了“赋、比、兴”的艺术思维,道家的思想中对于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就更加深刻,并影响了后代的诗歌、音乐、绘画等。西方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是一个缓慢发展的时期,西方重写实,自然只是作为一个背景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他们对自然的看法是征服而非欣赏,直到十九世纪初浪漫派、湖畔派诗歌的出现,才推动里普斯“移情说”的提出。在重写实和重写意的两种文化中,西方的“移情说”和中国的“应物斯感”说,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不同的概念,童庆炳将这两种学说理论放在一起进行对话研究,力图从心理学的角度发现新的价值。
中西之间的对话可以让不同的文化、观点、理论进行交流沟通,找到相同点,解释人类文学文论演化的共通规律,也可以在不同之间找到欠缺、学习的部分。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发展的过程中,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文论发展主要借鉴了西方的文论理念。曹顺庆指出:“中国现当代文论界,对中国古代文论总的来说是比较陌生的,在大量的文学实践和文论实践之中,基本上对中国古代文论不认同。许多人对西方文论、对苏俄文论更熟悉,在心理上甚至感情上更靠近西方文论(包括苏俄文论),而对中国古代文论始终感到格格不入。”[11]在这种环境下,童庆炳提出用“中西互证”的方法发展中国文论,让西方文论参与其中,这不仅能让更多的研究者重视中国古代文论的精华并用它来建设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更能让中国文论成为一股独立的力量参与到世界文学的讨论之中。这便是童庆炳在《三十说》中不惮辞费地昌言:“刘勰的确发现了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艺术规律”[5]237,“刘勰提出要重视文章的整体……含有现代结构主义的基本精神”[5]322-323的深切宗旨。
四、自我革新
在古今、中外的交流对话之中,童庆炳也没忘记与自己的对话,他没有止步于前,在进行《文心雕龙》研究之前他就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并在《三十说》中加以践行。在《三十说》首篇,他讲到自己在开始研究《文心雕龙》时就自觉地运用“文化诗学”的方法,“文化诗学有三个维度:语言之维、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有三种品格:现实品格、跨学科品格和诗意品格;有一种追求:人性的完善与复归”[12]9。面对当时文学脱离现实、脱离实际的问题,童庆炳提出的“文化诗学”对于文艺理论的建设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童庆炳在《三十说》中运用文化诗学的方法,在研究中注重回归南朝时期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立足文本深入分析对刘勰造成影响的各种因素,在宏向的文化语境拓展和微观的语言细读拓展中对《文心雕龙》进行分析。
在《文心雕龙》的研究中,童庆炳回归语言本身,细读语言在特定时代所阐释的意义。他赞同刘勰提出的“声得盐梅”,同时对其在声律上宽松与严谨自相矛盾的一面,童庆炳根据当时文坛特点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分析。在《〈文心雕龙〉“杂而不越”说》一文中对刘勰美学思想内涵的理解上,童庆炳将刘勰的结构谋篇原则分为生命的形式原则、整体优先原则和依源循干原则,最后提出了“和”“协”的审美原则。刘勰“杂而不越”的审美原则,就蕴含在中国古老的“和而不同”的审美中。在《〈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一文中,对刘勰的《文心雕龙·原道》篇提出的文原自然的说法,面对同类研究者的疑问,童庆炳根植于中国文化,列举了《诗经》中的“兴”、《易·系辞下》的“观、取、通、类”、《论语》中的“水”,在中华文化的语境中解决疑问,理解刘勰的“原道”说。凡此种种,都是“文化诗学”在具体研究中的应用。
“文化诗学关怀文学现实的存在状态,具有一种现实性的品格,它紧扣中国的市场化、产业化以及全球化,折射到文学艺术中出现的问题,要加以深刻地揭示。”[12]6童庆炳在进行《文心雕龙》研究时,特别关注“龙学”研究中现实存在的问题,既注重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分析,又注重让自己的研究成果服务于当下的社会研究。他没有局限于中国文学一贯的研究思路,而是运用语言学、文艺学、心理学、文艺心理学、西方文论等学科进行综合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形成了多学科交叉互补的交流模式,使研究过程完善化,在多学科的对话交流中发掘古代文论研究的新思路。
童庆炳在《三十说》的研究中灵活运用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将三个维度、三种品格、一种追求贯穿其研究过程。“文化诗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但可以拓宽文学理论研究的学术空间,更重要的是它以关联性方法的研究,展现文学全部复杂性、丰富性的无穷魅力。”[13]
童庆炳在自我对话中完成自我革新,尽力弥补昨日之“我”的缺憾。在《三十说》中几乎所有的文章都将其发表时间及刊物标注其后,有十余篇还标注了修改的历程。其中《〈文心雕龙〉“‘文体’四层面”说》 《〈文心雕龙〉论人与自然的诗意关系》前后修改的时间间隔都长达八年之久。《〈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1994年完成后2002年再改,十年后随着研究的深入,2012年童庆炳又写出《〈文心雕龙〉“道心神理”说新探》,从西方现代心理学观念入手,补前文之不足。
《三十说》是童庆炳先生后期研究的重点之作,在他看来,“古代文论有着独特的审美意义,对它的理解与坚持不仅有利于个体的人文修养,更有利于整个民族艺术思维的开阔”[14]。全书充盈着一种严谨的对话精神,在理智而又热情的对话中,激活古人,让古人成为一个主体,参与到当代世界文学理论的建设中。如在《〈文心雕龙〉“丽词雅义”说》中童庆炳先生指出:“刘勰在《诠赋》篇所提出的赋的创作原则,同样也适用于一切文学艺术创作。”[5]378通过对话,让传统的、当代的、西方的、群体的、个人的话语形成一种“会谈”格局,在相互交流鉴赏中,完善彼此知识理论,为其研究创作提供新机。童庆炳在对话精神的指引下,贯通古今、融汇中西、自我革新提出文化诗学的研究方法,在《文心雕龙》研究过程中激发了旧材料的新活力,全方位、多层次地把握了刘勰的思想,让《文心雕龙》这部历经千年的文论巨著,在今天依旧其命惟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