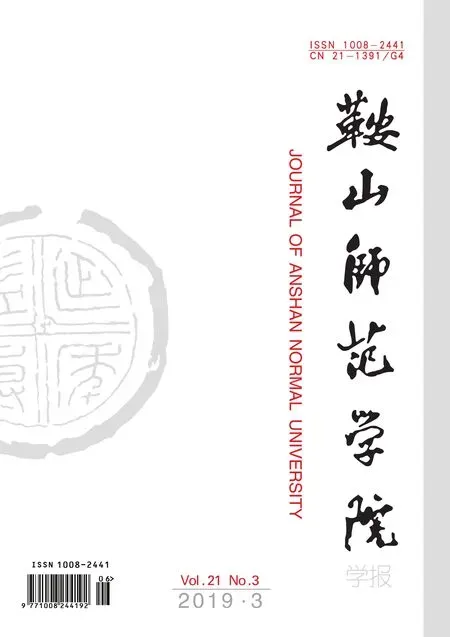孟子修养论视域下的穷达观研究
栾 哲 洪 丽,2
(1.辽宁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辽宁 沈阳 110036;2.鞍山师范学院 外国语学院,辽宁 鞍山 114007)
孟子的修养论体系是一个较为完整的伦理思想体系,穷达观是其修养论的核心命题。从“存心、养心、放心、正心、明心”五个方面,对孟子的穷达思想加以研究,梳理孟子穷达思想的大逻辑,通过“穷于心——达于道”的思想路径,建构孟子修养论视域下的穷达观。
一、存心
(一)存心尽性
孟子的修养论也可称之为修养实践论,心、性、天三者在孟子修养论视域下达成了和谐统一。孟子把存心看作是君子与小人的本质区别。在“存心”方面,孟子主张存有“四端”。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1]。”孟子所论述的四端从根本上体现出人与动物之间的根本区别,人之四端是天赋的,是生而有之的。但是,这四端还受到外在的、客观的、实在的环境的影响,其本身有着固有的局限,故而需要后天的扩充和完善,需要对四端进行发散,不断从外界的社会环境、道德环境、生态环境中获得动心忍性的正能量,获得增益其所不能的内在动力,获得内心中的淡定和从容。这样四端的理念和思想才能像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存“恻隐之心”,以建立关于“仁”的价值与尺度。人皆有不忍,一个年幼无知的孩童不慎掉进井里,我们会想象到,如若我们不施以援手,井水阴寒,井壁光滑,难以支撑,他必将丧生,这是“感同身受”,简言之为同感,抑或通感。以同感为前提,人就会在不考虑种种利害关系的情境下,纯粹出于善的潜意识去加以援救,这种情感叫作同情,这是人的本性、本质和本能。救人这一行为不是出于同感而是同情,危机的瞬间也不由得人加以思考和想象,完全是出于“恻隐”之心。“恻,伤之切也。隐,痛之深也。[2]”这反映出人们的心性与他人的痛楚是存在某种情感性关联的,这种关系之所以可以建立,原因有二:第一,恻隐之心的具体性,这是因为人们产生同情的对象是具体的、有内容的、丰富的实体或者事实;第二,恻隐之心的指向性,恻隐源于通感,也就意味着人们在用自己的心灵之镜反映别人的痛苦和悲哀。故而,恻隐之心永远指向他人、他事、他物。
存“羞恶之心”,以建立关于“义”的本源和基础。“恶”应当与“误”同音,作动词,表“厌恶”之意。“羞”是对自己言行之错误表示惭愧和懊悔,而“恶”是对他人行为之过失表示愤慨和谴责。在哲学伦理学的研究背景下研读《孟子》,其“羞恶之心”应然是人的内心所具有的内在的本能,羞耻感和厌恶感是“义”的缘由,人们根据羞恶的标准来判断好坏对错,来辨别是非曲直。倘若一个人缺少了羞恶之心,那结果便是此人对于外在事物的感知有失偏颇,失去了对与错的分辨力,也就是失去了人所应然具有的批判力和创造力,其审美变得麻木,在行为上的外在表现也必然失去其应有的道德规范。
关于“羞恶之心”是人心固有的还是后天形成的问题中西方仍未达成统一的意见。通常意义上,学界对于恻隐之心和羞恶之心的差异有既定的认知,对孟子心性思想的研究已然非常成熟。恻隐之心是一种实能,而羞恶之心则是一种潜能,人们的同情心源于通感,但羞恶之心却不一样,它和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习惯相关,就如同各种社交礼节、衣着打扮一样,需要后天去学习、去锻炼、去补充。各种观点和视角不一而足,各有其意义,综合比较来看,我们可以尝试着把羞恶之心作为恻隐之心的延伸和展开,一方面表现为关乎自我的自尊和自爱;另一方面表现为关乎他人的批评和指责。“羞,耻己之不善也。恶,憎人之不善也。[3]”前者可以为我们建立“自尊、自爱、自强”的人格提供助力,后者可以引导我们见贤思齐,见不贤而自省。在两种心理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并完善我们的人格,提升我们的精神境界。
存“辞让之心”,以建立关于“礼”的系统和谱系。“辞,解使去己也;让,推以与人也。[2]”辞让心乃是恭敬心,是礼的根源,其最大作用就是教导人们秉持谦逊泰然的意向去对待生活,克己以复礼,肯定自我的超越性,不为外物所累,志于道而据于德,将自我转化成一个纯粹的实体,进而实现超我,不为物役,实现全面的自由个性,达于人性、达于大道、达于逍遥。此外,对于自我之外的他者,肯定其具有的道德品质是纯善的,这种本然的善使得万物皆备于我,万物万法与我同一。
存“是非之心”,以建立关于“智”的求索和判断。“是,知其善而以为是也;非,知其恶而以为非也[2]。”谈及“是与非”,就给我们提出了“做出判断”的要求,要求我们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真假、对错、好坏等。故而,“智”的作用便在于施加某种引导,使人的言行举止倾向“是”并成之为“是”,这不仅是价值的判断,更是道德的判读。
孟子认为,四心乃是人之“常情”,所谓“常”是指主体自身,生而有之。所谓“情”,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而仁、义、礼、智,性也。四者是“性”之所“及”,心统性情者也。而“端”即是“绪”。所谓心统性情,孟子所言及的四心、四端都归摄于“心”,就如同心控制四肢一样,是人自觉的能力,如果有人不具备这种能力,那便是“物欲蔽之”的结果。四心加之整全的“心”的统觉,为孟子构建性善论的完备体系提供了逻辑可能。
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共同构成了孟子先天人性论的基础,四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具有相互联结的内生性逻辑结构和系统性思维模式。恻隐之心是善的根源,是良知的基础,是其他三颗心的始发站;羞恶之心从恻隐之心出发,与身边经历的人或事产生通感,也可以理解为“共情”,然后对万物产生怜悯之心,开始反思自己言行当中的不当之处,时时反省自身,产生愧疚感,产生自爱之情;辞让之心从恻隐之心出发,移情于他者,能够带着欣赏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世界,发现他人、他物的美感和好处,心生敬畏,敬畏自然、敬畏科学;是非之心从恻隐之心出发,移情于物,人以“善”为价值标准明辨是与非、对与错、好与坏,进而能够弃恶从善,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这三颗心最终又能统一于或是复归于恻隐之心,以人的现实的活动为依据,对恻隐之心予以发散和补充,造就一颗更强大的知觉灵明之心。知羞而后存敬,知敬而后扬弃,心存好恶,知耻后勇,志于道而据于德,学会见贤思齐,学会见不贤而自省。明“是”知“非”,知非后知羞,知羞后能自惭,过而后能改,进而能够引人向善;对“是”存恭敬之心,是其所是,能够帮助一个学者树立应然的使命感和价值观;对“非”存有敬畏之感,理性地加以批判,加以修正,在“是是非非”(第一个是应当取判断动词之意,第二个是应当是名词;非,同理可知)的过程中,实现自我人格的陶冶、修养和完善。
孟子的四端学说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相互联结、相互印证、相互作用、相互补充的逻辑基础和思维模式上,得以发挥并且日益完善,进而使学者们能够以此为基础成就自身,使社会中的人们,能够以此为基础惩恶扬善,为善去恶。由于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体现出天的至善至公;由于天人合德,故人能够达于天道、求其公正、求其本善。
(二)居仁行义
“存心”的最主要方法是居仁与行义。“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4]”。“仁学”应然是一门“道德之学”“心性之学”。义由羞恶之心发出,根本在于恻隐之心,在于“仁”且内证于人,所以义是人路,是由仁心所指向的正路,是人能够实现“仁”的有效途径,是找到“仁心”之宅院的羊肠小路,曲径可通幽。
君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5]”。四端生发君子之道德,在这一层面,四心于仁可视为同根、同源、同义,道德由仁爱之心生发,进而在“义”的漫漫长路中上下求索,孔子所说的“艺”即所谓“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便是实现“仁”并且归于道德的必然途径。
穷四端以尽心,尽心立志达“道”,此道应然是天理人伦的高度统一,以此为人性之本,立足于君子仁心,内化爱的动机,外化的表现便是“义”,多样的表现为“孝义”“忠义”“侠义”“道义”“信义”,以至于生发“创义”“法义”“疑义”“释义”等诸多概念和意义。
二、养心
(一)清心寡欲
孟子修养论视域下的穷达观首先是对孔子、子思等儒家思想的直接继承,而且也在百家争鸣的过程中,受到了道墨两家思想的深远影响。老子主张“尚仁”“见素抱朴”“寡欲”,而孟子在与道家的论战和相互批判中,吸收了道家关于 “寡欲”的部分理论,为儒学理论的系统化服务。
孟子修养论视域下的穷达思想的核心就在于“养心”,或者说孟子的整个修养论体系的核心方法是“养心”。“养心莫善于寡欲[6]”,孟子提倡寡欲,人的欲望一旦不加节制地泛滥开来,就会完全将内心修养、道德观念等抛到九霄云外,存在于内心当中的四端不能生发,那么就会“非人也”,也就是说人与动物基本没有任何区别。因此,寡欲的“寡”可以理解为“少”,我们常说心房,如果我们把心比作一个特定大小的空间,那么欲求的增多势必会挤压或者占据内心中“修养与善”的空间,眼耳鼻舌身各有各的喜好和欲求,好声、好色、好味等不但占据了人的心理空间,而且也浪费了人的时间,其对于养心的危害不言而喻,因此,要养心必须要寡欲。
养心之道重在“养”字,而养心最根本的方法在于节制自己的欲求。欲望也可以称之为后工业社会最大的悲哀,所有的一切在发达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之下都显得不那么重要,拥有批判精神的个人在工业流水线的作用和影响下变成单向度的人,于是,物质变得极其丰富,但人性却变得越来越卑微。人也在“历时态”中经过长期的努力,走出了“人的依赖”性的误区,可悲的是,与此同时,人类也在“共时态”领域中坠入了“物的依赖”的深渊。
(二)染丝之变
墨家的“兼爱”思想与孟子或者说整个儒家的“亲亲尊尊”原则是背道而驰的,孟子也曾言辞激烈地批判墨子,“墨氏兼爱,是无父也[7]。”但是,孟子也潜移默化地受到了墨家学派的影响,比如说墨子扩展“兼爱”为“兼相爱,交相利”,而孟子则提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推己及人,行忠恕之道,这与墨家的思想也大有关联。在修养身心方面,孟子与墨家的观点也有一致性,都承认并且看重客观环境对于道德主体自身的人性建构的影响。
养心的途径和方式大体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以心斋、坐忘的方式清心寡欲,其修在内;另一方面,则养于身体之外。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曰:“染於苍则苍,染於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8]。”借用这一典故来说明客观环境对人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正因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故孟母三迁以求芳邻。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养之者。至于身,而不知所以养之者,岂爱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9]。”对于小的树苗而言,它的培育方式是众所周知的,那么对于自身而言,自我对心性的培养、充实和发展却感到混沌和迷惑,实则爱身一如爱树,关键在于是否下功夫,是否用心做,小树苗的培育尚且要客观环境赋予其生长条件,那人心的培养是否更应该如此呢?植物的成长需要良好的温度和湿度条件,人心的培养则更需要一个积极的、健康的氛围,包括家庭环境、校园环境,还有社会的氛围。
三、放心
(一)求放其心
“求放其心”[10]是孟子居仁行义的根本方法。“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放心而已[11]”。人之初,性本善。这个善良的品质是先天固有的,虽然这也没错,但是,这样的说法极其容易混淆我们的认识。善的品质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拥有就不会失去,因此,孟子提出了“求放其心”。也就是说,我们在日常学习和生活的过程中,要不断地进行反思,要不断地放逐消极能量,并始终以积极的态度去坚信善念、坚持善感、发动善心。
对于现实社会生活当中发生的种种被物质污蔽人心的现象,孟子感到非常悲哀,并对此做过一个比喻,人有小鸡小狗丢失,都会焦急地去寻找,而固有的良心不见了,却不知道去寻找,浑然不觉,这是非常悲哀的事。
关于“求放心”的方式方法问题,孟子提出了“思诚”,即时时刻刻都思考“诚”,以“诚”为标准反省和叩问自己的内心,“思诚”也可以直接理解为“求善”。思诚的本质是不断发掘自己的知觉灵明之心,是通过自身不断扩而充之的人生智慧去反省和检讨自身。作为反求诸己的根本方法,思诚即反身而诚,是以反己的方式不断地完善自己,不断地遇见更好的自己的过程。
(二)反求诸己
“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12]。”反者覆也,指引我们要回归自身去寻找原因,以放心为前提,在放逐不善之后,回归于自己的心性,尤其是心性中善的本质的部分。早上起来照镜子,觉得镜子里的人很丑,这绝不是镜子的事,这就是所谓的“认识你自己”。我们要充分地自我反思,使得自己的心性获得稳定的、持续的、健康的正义理念,这便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在这个前进的过程当中,我成了一切的根源,善则构成了这一切的起始点。
“反求诸己”也是“存心”的一个方面,即返回自己的内心,时刻检讨自己,进行自我批评,寻找自身的不足,予以改正,寻找回自己丢失的本心,寻找回善良的本质。这种方法在具体环节方面可分为四个步骤,四者相互联系、相互交织,不可分割。
其一,反身而诚。“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治;礼人不答,反其敬[13]。”你对别人施予爱心,却感到别人不亲近你,得不到别人的认可,那么就要进行自我反思,寻找原因,是不是自己的仁心不能够满足对方呢?你管理别人,他人却不买你的账,是不是自身的管理方式又笨又蠢呢?孟子这种“自问法”是行之有效、用之有益的,这是一种严于律己、及时反思的行为方法。
其二,知耻明理。“无耻之耻,无耻矣[14]。”所谓知耻而后勇,这个“勇”也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做到。人应当有这种勇于认错、勇于改正的大情怀,但是这种耻感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担当起来的。孟子说,“无羞恶之心,非人也[15]”,在孟子看来,这样的人已经不成其为人了,这是关于“美女与野兽”的大问题,是人与兽的道德选择问题,是社会人生观的价值选择问题。
其三,改过自新。知耻只是人心理活动的一个方面,是人内心之中对善本的感念,本质上仍是心理活动过程,而改过则是其在客观物质层面的积极的、乐观的回应。孟子主张及时改过,改过方能自新,这个“新”,是有些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意味的,新之于自身,是干净的、明了的,是弃恶从善的整洁;“新”之于他人,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惊喜,是见贤思齐的清新和喜悦。
其四,从善如流。三人行,必有我师,见贤思齐的思想在此处得到了恰当的发挥和表现,君子与人一道为善,志同道合,真的是其乐无穷。这种善于向他人学习、善于听取他人意见,同时也善于表达的人文环境,正是孟子的大理想。孟子于行文和行为中都表达了这种大丈夫气节,这种思想不仅仅是孟子提倡,这更是孔学之门一以贯之的社会性人格,“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16]。”
四、正心
(一)不动其心
人到无求品自高,正心首先就要不动心。孔子四十而不惑,旨在不为外物所蒙蔽,能够做到“不动心”,反而会大有感通,以一颗清正之心看穿一切事物,透过表象看事实,透过映象看本质,进而明理,“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17]。”不动心得以养“勇”,勇于存心、勇于养心、勇于放心,每一种抉择都需要割舍,每一次自省都是一次自责。勇之于人,是“大我”的成就,是成就的大我。
(二)浩然正气
孟子在关于“气”的概念和思考方面,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气”。第一种是“夜气”,夜里的气经常性地呈现出祥和静谧的色彩,给人的心以安宁、以修养、以平和,帮助人静思和体悟,感受生活的变化,反思和反省自身;第二种则是“浩然正气”。“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8]。”多数人谈及养浩然之气的方法,往往都在关注“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后面的部分,却忽视了孟子所说的“我知言”,养浩然之气贵在知言,重在倾听,学然后知不足,见贤思齐,才能成就浩然。
孟子对“浩然正气”这样解释:“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在孟子及其后来者看来,这种浩然之气在没有被耗损的情况下,始终环抱着我们生活的空间,始终充斥着整个宙宇,但是至大至刚的前提是必须与道义、仁心结合起来。反之,一旦失去了道德品质,它便什么也不是了,会变得极其软弱无力。因此,孟子主张求于内,不间断地反省自身行为,叩问本心,进行浩然之气的修养。
实际上,“浩然正气”是以儒家的道德为精神内核的精神品质,它生生不息。在孟子看来,它就是人之善端,是一种在本能道德之心的驱动下,形成的一种道德责任感和使命感。因此,要多行正义之言,做正义之事,使内心的浩然之气不断充实不至于疲软,使自己的心志坚定不至于受蛊惑。古今之人都对“以心控物”做过论证,不管是内证还是实证,其结果殊途同归。孟子养浩然之气,配义与道,以主观的心性之义控制行为,而不是以客观之义强加于心,制约万物。四端之心、清正之心、寡欲之心赋予了“义”以价值,进而使人能够参天地、赞化育。
五、明心
(一)穷心之本
人生是一个由生至死却又向死而生的圆周,在一定意义上展开,也在一定意义上消亡。人,生而有穷达,穷达知力命,力命分贫富,贫富现荣辱,具体关系如下:
人生而有穷达,穷易认命,达易算命,但穷达的“穷”更意味着困厄的处境,而非单指物质上的匮乏,这也正是“穷”不等同于“贫”的原因。穷并不可怕,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终成大我。这个“大我”便是由穷而明的结果。穷心之本在于明心,所谓明心即心思澄澈、心境澄明,穷到极致故生明,明到穷处自放达。明心以穷心为手段,穷心以明心为终极追求。明心作为一种终极追求,求而不得者众,得者便是大贤,一如颜渊,一如朱熹。明心之“明”主要指明理,意图获得内心深处的澄澈、澄明;明理之“理”主要是“天理”,而不是单纯的经验知识,这个“天理”蕴含着伦理追求。
我们通常说“穷心达道”,所达之道便是天理,知天理便意味着心思澄明。也就是说,明心即达道。“达”有着两方面的含义,一指飞黄腾达,二则是痴狂放达,两者彰显出不同的思维模式,更是两种迥然不同的人生志趣和境界,由此可见,“达”也不等于“富”。穷则更加注重“力”,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达则更注重“命”,多少高官求神拜佛,由此可见一斑;由力命之不同则出现贫富差距,两极分化,贫者更加一贫如洗,而富者愈发富可敌国。况且人道不同于天道,人们往往都是损不足而奉有余,贫富的分异造就了整个社会的不平等。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导致公平与正义逐渐丧失,使得人们以物为荣,以财富的积累量来评定荣辱。
(二)穷达之道
每个人都经历一个时空的圆周,一个循环下来,人的意义也同时被这个圆周碾压得所剩无几。实际上,穷达问题的根本在于“活着”,但是怎样活着,怎样勾勒自己人生的轨迹,在轨迹当中又何以安身立命,对于每个人而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存心、养心、放心、正心、明心,我们在这一过程中释放了自己,也找到了自己,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失去了自己,也成就了自己,种种范式和样法,旨在寻回遗忘的存在,旨在寻回遗失的美好。
若能够寻找到遗失的美好,那便能够达于道。达道是具有现实指向和现实意义的。达道的表现在于成己成人,无论是对个人修养还是对社会进步都能起到促进作用。放眼看现代中国,无论是英雄人物,抑或是大政方针,“达道”的例子不胜枚举。例如,感动中国人物秦玥飞于耶鲁大学毕业后放弃功名利禄,志愿回祖国农村做一名村干部;随后又放弃被提拔的机会,跑去更困难的村落去帮助建设,并取得了傲人的成绩。他放弃殿堂,扎根田垄,为建设祖国乡村不遗余力,同时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达道者,能够在成人中成己,不但能让自己变得更好,更能够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化与发展。
孟子修养论视域下的穷达观是一个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思想体系,以“明心”(明确穷达的本质,求索人生的价值)为最终目的或最终境界。我们首先从“存心”(人之善端、四心)这一环节出发来逐步思考并加以论证,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三心出于一心”的观点,随后做出具体的论证;其次,先天的善并不完备,所谓“端”,仅仅是善的心性和善的概念的一个小小的起点而已,因此,在“存心尽性”的同时要通过“养心”(主体寡欲、控制环境)和“放心”(求放其心、切己有反)的途径和方式对先天之善端加以后天不断地完善和充实;最后,通过“养心、放心”这两种修养方式,使得“善端”得到很好的保养、充实,进而就会使道德主体“正心”(对诱惑的不动心、自身的浩然正气)。孟子认为,对于善端的存养不仅仅需要寡欲,更需要“气”来充实,这种浩然正气是道德主体长期“集义”产生的一种强烈的精神理想,可谓之信仰,助其坚定穷达之心,不会在人生由善端起点到穷达终端的过程中迷失自我,也不会放浪形骸,最终使道德主体回归于穷达的本质,探寻到人生的价值——“穷不失义,达不离道”。
孟子的穷达思想是孟子修养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穷与达的关系贯穿于孟子修养论的始终,也是孟子的伦理谱系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对于穷达问题的理解,对于人生价值的寻求,这不仅仅只是孟子的处世观,更是孟子的伦理人生观的重要观点和态度。就穷达观表层而言,是道德主体对于穷达的态度问题,但究其深层而言,则是道德主体核心价值观取向的问题。孟子穷达思想源远而精深,其人格与价值也远非现代社会所能完全理解并效仿,但是对于我们现实生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