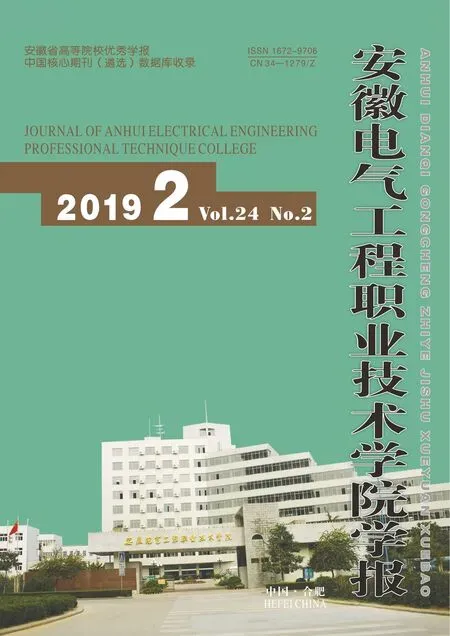早年陈独秀与安徽革命启蒙
王晓冉,程 升,陆发春
(安徽大学,安徽 合肥 230039)
安徽位于中国内陆,属于中部省份,地理上处于华中腹地,也是南北文化的过渡地带。明清以来以安庆和徽州为核心的两大文化中心区,培育了众多的文化名人。安庆府桐城县域为核心区自明末时期开始形成的桐城文派,对中国文学和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徽州,在徽商的强大经济基础支持下,新安理学、皖派朴学、新安画派等在全国享有盛名。近代以来,安徽地区以陈独秀、胡适、陶行知为代表的文化名人,在近代中国文化转型时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出身于安庆文化圈的陈独秀,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上知识份子的领袖人物,他的生平活动与安徽的革命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安徽为陈独秀的成长与社会实践提供土壤,陈独秀在安徽的革命实践推动了安徽的社会思想启蒙与解放。
一、陈独秀早期思想的转变
学界常把陈独秀的思想以政治观念为标准,以“五四”运动作为分界线,笼统地分为前期和后期。这种简化后的模型,容易让人忽视陈独秀早年思想的复杂性及演变过程。因此,对于陈独秀早年思想的研究和探讨仍有必要。
陈独秀出生在有“万里长江此封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称的安庆,桐城派在此地的文化氛围、理学渊源乃至教育方式,给陈独秀留下天然的影响。父亲去世得早,在陈独秀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一个严厉的祖父,一个能干而慈爱的母亲,一个阿弥陀佛的大哥”[1],陈氏家族“习儒业十二世矣”,陈独秀在祖父的教育下读书,严厉的祖父对他期望很高,要求他熟背四书五经,以求中举做官、光耀门楣,因此,陈独秀接受了较为系统的传统教育。这些早年的教育经历,可以说深刻地影响了陈独秀的思想观念的基础,即使是在他历经几次重大思想转变后,仍能有所体现。例如其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与康有为之论战,虽批孔热忱一发不可收拾,但细读其文章我们可以发现,其所批的,并不直接针对孔子本人及儒家思想,而是批判康有为假借孔子和儒家之名的所行之事[2]。1897年,时年十八的陈独秀赴南京参加乡试,因在乡试考场亲眼目睹了科举考试的各种怪状:“由那些怪现状联想到这班动物得了志,国家和人民要如何遭殃;因此又联想到所谓抡才大典,简直是隔几年把这班猴子、狗熊搬出来开一次动物展览会;因此又联想到国家一切制度,恐怕都有如此这般的毛病;因此最后感觉到梁启超那班人们在《时务报》上说的话是有些道理呀!这便是我由选学妖孽变到康、梁派之最大动机。”[1]由此反思,陈独秀完成了其人生重要思想转变中的第一次,即从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转变为维新“改良派”,成为康梁的拥护者。
如前揭所述,新文化运动开始后的陈独秀对康有为及梁启超都曾有过直接或者间接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康梁两人对陈独秀早期思想都有很大的影响。客观而言,甲午战争的失败,不能不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强烈的冲击,陈独秀的精神上亦受到强烈刺激。据陈独秀自己所言,读了康梁文章,“始恍然于域外之政教学术,粲然所观,茅塞独开,觉昨非而今是。[注]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二卷第3号。”康梁想以改变国家制度而救亡图存的尝试,激发了众多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也使得陈独秀产生了民族主义的萌芽。
若论康梁的国家和民族观念,应分为两个方面来看。1898年以前,梁启超追随康有为,他们的民族观念并无很大分歧;1898年以后,由于流亡海外,梁启超渐接受异域学说,与其师开始有了较大差异。梁启超后来介绍到中国的这个不合传统的国家民族观念的主旨有二:一是民族国家的意识,区别于传统的华夷之辨;二是百姓的公民观,区别于封建的家国观。陈独秀的民族主义应是受梁启超此时的影响。1901年至1903年陈独秀曾两度赴日留学,彼时梁启超正在日本主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日留学生几无不受之影响者,他通过这些报刊接受民族主义自然毫不奇怪[3]。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重,清王朝反动性质的日益凸显,陈独秀也开始变得激进起来。在政治观念上,陈独秀不满清朝官僚“保国休谈,惜钱如命”、“干爹奉承,奴才本性”[注]陈独秀:《醉江东,愤时俗也》,《安徽俗话报》1904年3月31日。,但此时陈独秀依然在康梁改良思想的框架之内,仍是强调所谓“守国家秩序”,“顾国体”,戒“诋毁”,主张“徐图建设”[4]等等。
使陈独秀真正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则是清政府对“拒俄义勇队”的镇压。1900年春天,八国联军入侵,沙皇俄国以“护路”为名入侵我国东北地区,所到之处,制造了各种骇人听闻的惨案。陈独秀此时正居住在东三省,有些情景,为其所目睹。“僕游东三省时,曾目睹此情形……前年金州有俄兵贱淫妇女而且杀之,地方老绅率村民二百人向俄官理论,非徒置之不理,且用兵将二百人全行击毙。俄官设验疫所于牛庄,纳多金者则免,否则虽无病者亦置黑狱中,非纳贿不效。其无钱而囚死狱中者,时有所闻”;“中国人坐火车者,虽已买票,常于黑夜风雨中被俄兵乘醉逐下,或打死于车中,华官不敢过问。沿铁道居民时被淫虐者,更言不胜言。”[注]陈由己:《安徽爱国会演说》,《苏报》,1903年5月26日。沙俄的暴行激起了中国民间持续五年的拒俄运动,陈独秀亦是其中的积极分子。
1902年,从日本回国后,陈独秀在安庆与何春台、潘赞化、柏文蔚等进步青年组成了“励志学社”,在藏书楼发表演说,宣扬爱国理论,开始了反封建、反专制的革命道路,他在演讲中,首次提到了要求民主与科学。1903年5月,在全国的拒俄浪潮影响下,陈独秀在安庆藏书楼发表拒俄演说,激励了一大批青年学生,反帝爱国热情十分激烈。同时,为了把拒俄运动开展起来,陈独秀联同一批爱国进步青年,组成了“安徽爱国会”,展开拒俄运动。这一运动遭到了安徽巡抚的镇压,很快平息下去,但是它对于安徽的思想启蒙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此之前,安徽受康梁等人维新思想的影响较大,大多提倡改良主义。运动遭到镇压之后,进步人士逐渐看清了清政府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反动本质,逐渐由改良主义走上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道路。而陈独秀由康党、梁党,转化为比较完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是在这一过程中完成的。
随后,他由皖赴沪,与章士钊、苏曼殊等人一起在上海创办了《国民日日报》,《国民日日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喉舌,陈独秀作为其重要编辑,发表一系列“论说”,体现其作为革命者的坚强反抗。不过,《国民日日报》的革命色彩很快被清廷看出,但由于其在英租界不便直接封禁,只能发布命令禁其传播。但该报最终由于内讧而停刊,陈独秀也于当年年底从上海返回安庆。
在上海创刊的经历给陈独秀积累了经验。陈独秀在停刊返回安徽之后,于1904年3月创办了《安徽俗话报》。《安徽俗话报》从创刊到停刊仅有一年半的时间,然而其影响之大,销路之广,成为当时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白话期刊之一。在此之前,陈独秀已经完成了由“康党”到“乱党”的转变,因而《安徽俗话报》也成为他宣传新思想的一个重要阵地。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顺应了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出现的办俗话报的潮流,各地纷纷出现俗话报的同时,“我就想起我们安徽省,地面着实很大,念书的人也不见多,还是没有这种俗话报”。陈独秀在创刊初表示:“第一是把各处的事体,说给我们安徽人听听”;“第二是把各项浅近的学问,用通行的俗话演出来,好教我们安徽人无钱多读书,看了这俗话报,也可以长点见识”;“门类分得多,各项人也都可以长长见识”[5]。可以看出,在创刊之初,陈独秀希望能够通过俗话报能够让所有的安徽人都能买来看看,对下层民众进行思想启蒙。面对在帝国主义威胁下日益严峻的国内形势,陈独秀在文章中大声疾呼:“要知道国破家亡,四字相连,国若大乱,家何能保呢!”[注]三爱:《亡国篇》,安徽俗话报,1904.08,人民出版社,1983 年影印本。他用通俗简明的语言,旗帜鲜明的反对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而没有像同期俗话报一样,充满过于激进的排满言论。实际上,《安徽俗话报》读者群并没有像预期一样,覆盖到广大下层群众,它的主要购买群体仍然集中在青年学生。但是,报纸所宣扬的进步思想在安徽广大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强烈的反响,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将文化启蒙与革命思想联系在一起,“做的是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工作”[6],使当时许多安徽学生都以陈独秀为革命榜样,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在办报期间,陈独秀还在安徽公学任教,鼓吹革命思想,前往皖中、皖北地区进行宣传,进行革命联系与策动。在这种形势下,1905年,陈独秀与柏文蔚等人在芜湖创办了岳王会,“这个会的取义,是要大家效法岳武穆的精忠报国,实际上是一个专搞军事运动的机关。会员入会,采取江湖上习用的烧香宣誓方式,绝对保守秘密,不作对外宣传。联络对象,主要是安徽武备练军学生、新军中下级军官以及警察学堂学生。岳王会会员为了运动军队,有不少的人投入新军中充当士兵或下级军官。”[7]有学者评价岳王会在辛亥革命中的重要性并“不逊于‘光复会’和‘华兴会’的地方”。重视军队的力量,在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发动新军走上革命道路,是陈独秀早年重要的一次革命实践。1908年11月,安庆爆发新军马炮营起义,不能不说这与岳王会的革命宣传有着密切的关系[注]此方面详情,参看陆发春:《马炮营新军血战安庆城》,《安徽重要历史事件丛书·军事纵横》第201~208页;安徽人民出版社版1999年版。。
二、陈独秀对安徽社会启蒙的探索
在经济上,安徽自然资源丰富,地理位置优越,沿江交通便利,近代资本主义起步时间早,工业起点很高。1861年,曾国藩曾在安庆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这是中国的第一个近代工业企业。芜湖自1887年开埠后,渐成全省最大的工商业经济中心,仰仗其便利的地理位置,成为长江流域重要的通商口岸,也带动了沿江地区商业经济的发展。然而,在腐败的吏治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情况下,安徽的工业发展迟滞,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中国有开矿、设厂的权利,安徽的安庆、贵池等多地铜矿的墈采权被英、日、德等国家攫取,因而,安徽虽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近代工矿业的发展却举步维艰。就总体状况而言,安徽是一个农业大省,自然灾害对其社会经济的影响相当大。辛亥革命前夕,《安徽白话报》中曾专门设立“灾异界”栏目,刊登各地的受灾情况:“宿松灾民闹灾”、“盱眙县灾异又流行”、“(怀宁)灾苦愈绵”等报道层出不绝。加之各种苛捐杂税,地方政府的压榨,民生艰辛,其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与资本主义的起步时间很不相称。但是,这种资本主义起步时间早与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之间的矛盾,体现在民众心理上,反而形成了一种开放性的优势。
晚清时期,内忧外患并举,千古未有之变局的形成促使着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们思想的转变,这其中首推的就是魏源的“通经致用”的思想,清末的维新派更是明确地提出了“采西学”“制洋器”的思想。而受此影响,在清代学术上有着重大影响的桐城派也深受经世风气的影响,而其又反过来在晚清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和西学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回顾陈独秀早期启蒙思想确立的基本路径和其文学理念的深刻革命性,不难发现这都与“谋求匡时济世之道的晚清学术”趋向相映征。而通过陈独秀的个性人格,如在他身上所呈现出来的敢作敢为、勇于担当,积极入世等精神的品质,也与晚清的经世传统存在着明显的联系[8]。
不过这一时期,在安徽生活的陈独秀,还没有在政治场上风生水起的操戈,处在政治文化圈的边缘。1897年,陈独秀从安庆出发,去南京参加江南乡试,这一年,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这一形势激发了许多进步青年的爱国热情,在这一浪潮中,在乡试中认识到科举腐朽与清廷无能的陈独秀,“痛感时事日非,不堪设想”,撰写了《扬子江形势论略》。在这篇文章中,他阐述了自己关于长江防务的见解,讨论从荆襄到淞江口防线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旨在向清政府谏言献策。此时的陈独秀,像当时的大部分知识分子一样,希望清廷能够像日本一样,进行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进而走上自强的道路。而在戊戌变法和庚子事变之后,陈独秀意识到,单靠清政府是不能完成救国任务的,于是在安徽的这一阶段,他专注于社会启蒙,启发民智,发动民众的爱国热情。虽然这一时期,他在安徽地区的活动影响力远没有五四之后深远,但仍然极具研究价值。
戊戌变法之后知识分子纷纷开始了自下而上的民智启蒙,出现了大量以中下层民众为主要读者的“俗话报”、“国民报”。陈独秀在这一时期,展现了出了他非凡的政治才能。1903年5月份,他在安庆发表拒俄演说,指出国难当前,“思之将一大痛哭”,单是陈独秀的演讲,就打动了在场一大批人。而陈独秀所整个发动的安徽拒俄运动,震惊了整个江淮地区。当时就有报纸如此评论,与会人员“旨趣皆相同,而规则整严,精神团结,此吾皖第一次大会,而居然有如许气象,诚为难得。”[注]《安徽爱国会之成就》,《苏报》,1903年5月25日。之后的两年里,陈独秀运用自己的口才和文字进行宣传和演讲,致力于国民启蒙。
陈独秀对安徽的社会启蒙的表现形式首先是兴办了《安徽俗话报》。陈独秀之所以选择报刊成为自己的阵地,与其经历有不可分割的关联。正如他自己所言,他从“选学妖孽”变为“康党”,《实务报》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从“康党”转变成为革命党的过程中,又与其所接触的一些宣扬新思想的报刊不无联系。在开办《安徽俗话报》之后,除了稿件撰写之外,几乎大大小小的办刊事宜都是经他的手亲自完成,“我那时也是二十几岁的少年,为革命感情所驱使,寄居在科学图书社楼上,做《安徽俗话报》,日夜梦想革新大业,何物臭虫,虽布满衣被,亦不自觉。”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革命之投入!
而细读《安徽俗话报》后,不难发现,它所承担的正是启蒙民智的作用。面对当时列强瓜分中国的形势,他大声疾呼:“我们中国人,又要做洋人的百姓了呵!”而大部分的中国百姓,还远没有认识到形势的严峻性,“这不是要活活的急死人吗!”在启发民智方面,他首先指出,“当今瓜分之风甚烈,急需一般忠义人,若不趁早来培植,试问你们等何日”,着重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其次,他还认识到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瓜分的危害性,他在《安徽的矿务》一文中,认为要学习湖南人的做法,提出安徽人要把安徽的矿务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以免像东三省一样把矿务交到俄国人手中,惨遭欺凌。他还在多个栏目中强调“恶俗”的危害,在其中有不少清除旧文化的言论,对于后来在新文化运动中清除封建糟粕的思想,做了提前的预习。从卫生、诗词、行情、婚姻、迷信等多个角度来阐释废除恶俗的必要性,“我们中国人,专喜欢烧香拜菩萨,而菩萨并不保佑,我们中国人,还是人人倒运,国家衰弱,受西洋人种种的凌辱”。除了宣扬革除陋习,陈独秀还致力于传播新思想,例如《说国家》对国家的新内涵的介绍。其中主要包括国家的概念和对亡国的解读,这些理解主要受梁启超的影响:以近代西方政治理论为依据,以欧美列强为蓝图,并立足于清末内忧外患的现实基础。这正符合当时时代之需要,对启发民智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9]。
由于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启蒙对象开始由上层向下层转移,陈独秀在此时办报,放弃当时普遍使用的文言,采用俗话的形式,图画与文章结合,用通俗易懂的形式,试图向安徽人介绍时局形势,撰写安徽农业调查报告,探讨针砭时弊的话题,启蒙思想,进而进行革命启蒙,在安徽近代史上具有重要的作用。而他用俗话的形式,着眼于下层民众,也无意识的显示出了他的思想倾向。
陈独秀早年的反清革命实践,使他成为安徽地区最有代表性的一位革命启蒙者。1906年3月,陈独秀还在芜湖创办“徽州公学”(“徽州初级师范学堂”),该校的教员多数是革命党人,成为陈独秀在安徽宣传革命的重要阵地。到1915年秋,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时,汪孟邹协助其出版事宜,将芜湖科学图书社作为该杂志的“代办处”,为新思想在安徽的传播架起了桥梁。此后,陈独秀离开安徽,结束了其地区性的革命启蒙,走上了更有影响力的人生阶段[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