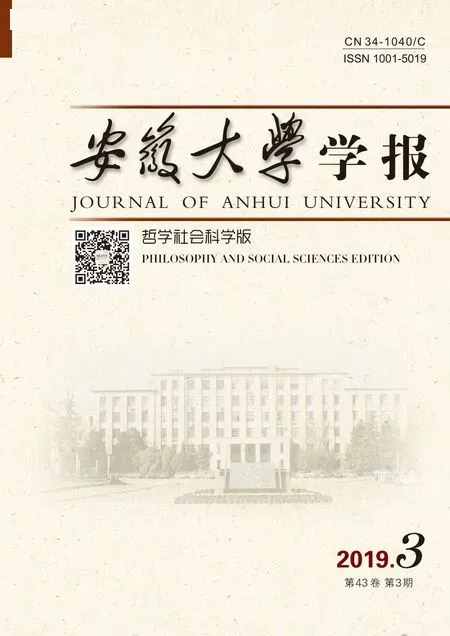“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
——谱系学视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
陈文新,王少芳
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最多产的国家是日本,其中,作为明治期间(1868—1912)井喷而出的文学史著作之先河的,是日本汉学家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这些出于明治日本汉学家之手的“中国文学史”,对于清民之际中国学者的文学史写作影响巨大。比如曾毅在其著作《中国文学史》弁言中即坦承“颇掇拾东邦学者之所记”[注]曾毅:《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图书局,1932年订正版,第1页。,林传甲也在其著作自序中谈到“将仿日本笹川种郎《中国文学史》之意,以成书焉”[注]林传甲:《中国文学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第2页。。
末松谦澄所写的“文学史”,以历史、哲学、法制等内容的叙述为主体,从现代学术标准来看,称之为“文化史”其实更为恰切。本文的宗旨不是对末松谦澄笔下“文学史”与“文化史”的错位现象做出价值评判,而是基于谱系学的立场,探讨其形成缘由、谱系归属,以期更加准确地把握早期中国文学史著作书写的理路,更加明晰地厘清中国学者的文学史书写的历程。
谱系学的概念是从法国哲学家福柯那里移植来的,它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种哲学观点。作为研究方法,它强调对事物“出身”和“发生”的考察;作为哲学观点,他强调对既定知识秩序的质疑。从谱系学角度切入中国文学史著作研究,一方面提出了重写中国文学史的必要性,另一方面也提供了若干新的研究思路。
一、文化史:《中国古文学略史》的书写对象和宗旨
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上及《周官》,下迄《国语》,是一部春秋战国时期的断代文学史。全书共十七节,大致以统一模板对作者的时代、思想、作品真伪等展开论述,其中以思想叙述最为主要,而作品的功用——包括其社会效应以及对历史真相的探究效用,也得到极大关注。以现代学术标准来衡量,更像是一部“文化史”,而不是“文学史”。唯“屈原宋玉”一节,不仅关注作者所抒发的真情,也包含作品所引起的读者的情感反应,与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较为吻合。
《中国古文学略史》(下文简称为《略史》),原本是末松于明治十四年(1881)在英国伦敦对日本学生会的同胞所做的演讲,经过整理后于次年(1882)在日本出版[注]末松谦澄:《中国古文学略史(下)》,1882年,第30页。,分为上下两册,是目前可见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著作。末松选择先秦的原因,一方面是他在《略史》中提到的:“(中国文学中)春秋之末至战国之末乃最为紧要的。盖中国人气最为发达、学术文章技艺最为进步而能如战国者未之有也。春秋则为其先导。”[注]《略史(上)》,第1页。另一方面是在与欧洲文化对比时,中国比对的是希腊罗马时代,因此他更为关注同样具有渊源性质、在时间上也属于同时期的春秋战国。“略史”二字,则表明末松并不想对每部作品条分缕析,而致力于提示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典籍的要领,如河田熙在序言中所说:“(此作)令后生知汉籍之梗概,譬之航海,先辈既按星象、测地维,定其针路,制之图册,后生因得知其远近险易、礁洲津港,则事半而功倍焉。”[注]《略史(上)》,序言,第2页(原文为汉文)。
末松的书写对象,以诸子群经为主。《略史》不分章,无目录,除开篇总论外,仅以所介绍的著作或人物标目,共有17个小节,分别为“周官、管子、老子、孔门诸书、晏子、杨朱墨翟、列子、孟子、商子、公孙龙子、庄子、孙吴兵法、苏秦张仪、屈原宋玉、荀子、申韩、吕氏春秋竹书纪年左传国语”。“孔门诸书”一节介绍的是五经和四书,不过四书中以《孝经》代替了《孟子》,而五经中的《礼》指的是《礼记》,《周礼》则被单列在著作首位。《略史》的论述,大抵以人物派别为组,以时间为序。所以,虽然他认为中国最古的著作是《尚书》,但由于《尚书》是儒学的五经之一,故仍归在孔门一节。至于《吕氏春秋》等四部作品,由于同属历史书籍,故一并放在最后一节。此外,如公孙龙子、杨朱的著作虽已佚失,但经常为其他典籍所涉及,也分别单列一节。
末松的书写宗旨,偏重于揭示诸子群经的文化内涵和文化史意义。从小节题目看,作为明治“中国文学史”发端的《略史》,将其改为“学术史”“文化史”,也不会有多少违和感。末松自己也承认,此书是为了让“后世专攻中国古学者”,“可以明晓东洋文化之本源而举其大纲”[注]《略史(下)》,第30页。。可见,在末松的眼里,“文学史”和“文化史”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两者可以混用。事实也确实如此。首先,《略史》尽管不像儿岛献吉郎的《中国文学史》那样直接分为“群经文学”“诸子文学”“诸史文学”等章节,但末松论述的主体同样是经史诸子,这些经史诸子本身也几乎不被视为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作品”,而是文学、哲学、历史著作的综合体。其次,末松的论述罕见纯文学角度的分析,反而是历史、哲学的说明和相关考证占了更多篇幅。如“孟子”一节,《孟子》的表达方式和文辞之美几乎未得到关注,其理论内涵才是论说的重中之重。孟子在性理学史上的首唱之功,他的性善论和良知良能,以及在政治策略上的不合时宜构成了末松《孟子》论说的主体。所引的原文也是为了论证其理论内涵,彰显其哲学思辨。其他一些叙述,例如总论开头,针对三皇五帝、仓颉造字、伏羲演八卦等沿袭已久的传说,一一从文献学讲求实证的角度表示怀疑;根据《尚书》“稽古”二字及其文体推断尧舜二典、禹皋陶二谟虽不成于尧舜、禹皋陶之世,但断不晚于周代;在论说《老子》时,根据《史记》和他书散见的记载确认老子当在孔子之前;论述《左传》虽仅有数语,却仍关注左氏是否即为孔门弟子左丘明。所有这些都表明一点:末松对作品真伪、作者年代、成书时间等都报以极大热情。这种偏重于哲学思辨、历史考证而忽略文辞的叙述,在《略史》中比比皆是。其三,末松评判作品高下的标准不是作品的表达,而是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在首节“周官”中,尽管末松指出《周官》记事繁杂,读来容易使人厌烦,但由于《周官》有助于了解周世的制度风俗,故仍花费近乎整节的笔墨将六官与今之制度一一加以比照。而论《荀子》时则重视其破除蒙昧的卓见,述《礼记》则强调孔子复仇论对东亚风俗的深远影响。
20世纪50年代中叶,游国恩《关于编写文学史的几点意见》一文曾讨论过先秦文学史应不应该纳入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的问题,其答案是肯定的。理由有二:其一,“一般说来,先秦诸子的著作都是有关哲学、政治的理论文,应该归入哲学范围。但那些理论文特别是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诸家的散文都是各有其特点的。他们的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不是干巴巴的只有概念式的推理或说教的哲学论文和政治论文,而是极为生动、富有形象性的优秀的散文。它们有民主性的进步思想,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方法,同时也有恰当的表现形式:一般都是条理清楚,结构紧严,语言明白流畅,通俗朴素,说服力很强,特别是运用寓言故事和譬喻等表现方法,生动具体,形象鲜明,读者不但不觉得枯燥无味,不但不觉得抽象化、概念化,反而有极大的吸引力,使人感到愉快,感到一种‘怡然理顺,涣然冰释’的愉快。我们不能因为先秦诸子的散文其目的在于说理,就抹杀它们的艺术性,就不承认它们有文学价值。”其二,“在先秦时代这些理论文也和历史散文一样,都是我国散文的源头,如果不讲它们,则后来的所谓‘古文’便没有根,韩、柳以后的古文都不应该讲。如果不讲先秦散文,而讲唐、宋古文,固然说不过去;如果由于不讲先秦散文因而索性连后来一切作家的散文都不讲,那就更说不过去”[注]游国恩:《关于编写文学史的几点意见》,《游国恩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27~528页。。游国恩的答案表明,由于春秋战国时期文史哲浑融未分,即使是写纯文学意义上的文学史,也不能忽略诸子百家和历史著述。但需要指出的是,末松并不是在这个意义上展开叙述的。他关于诸子百家和历史著述的评介,丝毫不在意其“艺术性”,而仅仅关注其历史价值、思想价值和文献价值。如果拿现代意义的文学史著述中的先秦部分与末松的《略史》对照,其文化史品格就更为显著了。
从以上的讨论可以看出,无论是书写对象,还是书写宗旨,末松的《略史》都更近于现代学术视野下的文化史和学术史。如果把《略史》中所有的“文学”都用“文化”替换,几乎不会遇到什么困难。
二、幕末明治时期末松谦澄的汉学观、史学观、文学观
末松何以将“文学史”写成了“文化史”?
本文的答案是:《略史》对“文学”和“文化”不加区分,与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文学”概念依然偏重“知识”的学术背景息息相关。相关的谱系追踪从三个层面展开。
(一)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与末松谦澄的汉学观
末松谦澄对于“文学”与“文化”不加区分,这一学术取向与其学习、人生经历是分不开的。末松自幼入汉学私塾专习汉学,及长又在时代的潮流下学习西学,作为福泽谕吉所谓的“一身两世”人,他在汉学的基础上接受了西方新的知识概念。但是,这种接受并不是简单地全盘西化,他固有的汉学知识结构在吸收西学的过程中仍在微妙地发挥作用。新的知识改变了旧有的观点,旧有的知识又影响着新概念的理解与吸收。两者互相作用的结果是,作为对时代思潮进行回应的《略史》,既有超出原有汉学传统的一面,又有继承原有汉学传统的一面。当西学伴随着帝国主义的殖民扩张大规模进入东亚,在师夷长技不能制夷之后,汉学家的“和魂汉才”之梦也宣告破灭,政府所主导的学制等方面的改革更是明显模拟西方。传统汉学显示出向中国学转向的态势,“按照西方文化的价值体系,对中国文化进行‘对号入座’式的比较、评价”,迅速成为时尚[注]详参李庆《日本汉学史第一部:起源和确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年;王晓平:《日本中国学述闻》,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
日本的传统汉学研究,主要指明治初期前的中国相关研究,其时中国的“他者”形象并不强烈,反而是作为东洋之中国、日本文化源头之中国被认识的。其研究以中国古代为对象,以经史子集的译注、训诂、阐释为主,对中国文化怀有倾慕心理,怀有憧憬的热情。而明治以后形成的中国学研究,则是在教育制度影响下,在学术分科、专门化的视野下进行的,中国被视为世界之一国,不具有特殊地位。受到欧美学术界的影响,研究领域开始涉及中国近代,包含政治、周边关系等。实际上,日本中国研究的转变与欧美从“Sinology”向“Chinese/China studies”的转变大体是一致的。
在汉学向中国学转向的过程中,末松对这一转向多有批判。但其《略史》以西方的体系来对照中国文化,却正是转向时期的普遍现象。他对照西方文化发源地的希腊罗马文化,来研究作为东洋文化之源的中国文化,因而聚焦于中国文化的奠基阶段——先秦,表明他与转向期的汉学其实是同步的。不仅是末松,随后的藤田丰八与儿岛献吉郎起初写的也都是先秦文学史。
末松的人生经历也加强了他的这一学术取向。作为政府官员,末松肩负着向欧洲社会宣扬日本文化的任务,为了使日本与其他欧洲国家站在平等的位置上,他必须说明东西方的同一性。他在《略史》中多次提及“中国之于东洋,正如希腊罗马之于欧洲”,其意义在于确认东方文化并不比西方文化低劣。尽管在西方殖民扩张的背景下,他也许认为希腊罗马文化优于中国上古文化,但出于文化自尊的考虑,确认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等地位是必要的。而作为东方文化源头的中国文化,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代表了它的轴心时代,是公认的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中国文化的诸多元典,都产生于这一时代,也理所当然得到末松的格外重视。在《略史》首节“周官”中,末松不厌其烦地将六官一一与近代官职对应,除了与他历任多种官职有关,也有证明东方文化中有与今之西洋制度类似的职官之意。
(二)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与末松谦澄的史学观
尽管日本的国学和西学并没有像中国目录学那样的学术分类方法,但日本的汉学则通常以中国目录学的方式对学术进行分类。根据高山节也的研究,在佐贺藩的藏书中,尽管存在个别差异,汉籍使用的普遍是四部分类法。而在四部当中,经史子集的比例是高低高低的模式,集部和史部相对来说处于整体偏低的地位[注]高山节也:《江户时代的汉籍目录》,见叶国良、徐兴庆编《江户时代日本汉学研究诸面向:思想文化篇》,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9年,第347~390页。。但在幕末明治时期,随着西学的进入,有别于“经史子集”之“史”的实证主义史学逐步兴起,而这一过程同样离不开汉学家的努力。
明治初期修史局(修史馆)在“国史编纂”上出现的分歧,象征着实证主义史学开始摆脱汉学的制约。作为中心人物之一,擅长古学派考证的重野安绎倾向于西方历史学编纂方式,站在合理性实证主义的立场上反对汉学家川田刚“名教道德”下的传统史学。这场论争以川田的离开告终,标志着日本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过渡。此间,为了学习西方史学,重野申请派遣末松到欧洲学习英法的历史编纂方法。末松于1878年赴英留学,留心英、法历史编纂之法,并从G.泽鲁菲处获得了一部历史编纂参考书[注]详见永原庆二《20世纪日本历史学》,王新生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15页。,为重野的史学革新提供了养料。史学革新的要旨是,摒弃传统的名分道德论而注重真实的史料。
尽管末松在后世汉学与史学的研究中都没有受到过多重视,但他无疑是这个革新过程的重要参与者。他获赠于伊藤博文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本身也十分注重对史料的考察收集。由此可以推测,末松的史学观与重野“注重考证而抹杀一切虚妄的史料记载”[注]刘正:《京都学派汉学史稿》,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年,第21页。是接近的。他在《略史》中强调:孔门论述尧舜之政绩缺乏实证,多有夸大之辞,不能视为信史,甚至认为《春秋》不过是日记体而非史体,从西方史学观来看当不得史书[注]《略史(上)》,第2~3页、20页。。在末松看来,儒家以治乱来论文化的“有道无道”不适用于史学,如果据史学真意来论中国史书,则知中国“无史学也”[注]《略史(下)》,第29页。。末松受邀编纂的《防长回天史》,也折射出他的实证主义史学倾向。这样看来,末松在《略史》中喜好评论典籍的史料价值也是理所当然的。
(三)幕末明治时期日本的“文学”观念与末松对“知识”的重视
传统史学原属于日本汉学的一个部分,随着近代学术的发展,才逐渐从传统汉学中独立出来。并非偶然,日本传统的“文学”概念,原本也笼罩在儒学之下,“‘文学’始终是用来指代以儒学为中心的学问与汉诗文”。即便在江户时期,“文学”也多指经学与诗文之学的混合物,“没有出现像欧洲近代那样将诗歌、戏曲、小说等纳入同一种语言艺术的观念”,并且各种文体的地位均低于汉诗[注]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王成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61页、82~83页。。
这里有几个现象是需要留意的:一,传统汉学家在研读汉籍时也会接触到小说戏曲,但并不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从中日两国的交通史来看,江户时期中国的小说戏曲已大量进入日本,只是,这些书籍或者作为学习唐话的教材[注]廖肇亨:“在唐通事的训练过程中,《今古奇观》《三国志》《水浒传》《西厢记》等明清白话小说戏曲成为当时学习汉语的教材。”(廖肇亨:《领水人的忠诚与反逆:十七世纪日本唐通事知识结构与道德图式探析》,见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三辑,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213页)不仅日本,琉球同样将小说戏曲作为学习汉语的材料。木津祐子曾说:“这些小说是用白话写成的,内容可说是典型的才子佳人和教训谭,而在琉球是被通事作为长篇会话课本来使用的。”见木津祐子《琉球的官话课本、“官话”文体与“教训”语言——〈人中画〉〈官话问答便语〉》,见张伯伟编《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四辑,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23页。,或者作为翻案文学的对象[注]如“牡丹灯记”在日本受到许多作家的喜爱,多次被作为改编、翻案小说的对象。,或者作为闲暇消遣的读物,尽管受到大众的欢迎,甚至许多汉学家也耽于阅读,但并未纳入学术意义上的“文学”范围。二,在日本,“文学”与“literature”对译早已有之,但与近代使用的语意仍有差别[注]铃木贞美指出,“literature”原意有“文献、文章艺术”等,用来指“精通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读写能力,以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古典书籍为中心的高级书籍,博学多识”,与“汉字文化圈内由精通中国古典(一般指经史之学以及老庄和佛典等学问)的观念”基本对应。见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第103页。。幕末明治时期的日本,“文学”仍然倾向于传统的“学问”“文章”,是哲学、历史、文学的混合体。三,作为模仿西式学校建立的东京帝国大学,其学科设置中文学、历史、哲学的最终明确分离要到1904年。近代“文学”概念的确立,也要到20世纪初至1910年间[注]铃木贞美:《文学的概念》,第220页。铃木贞美指出,如果要划线的话,可以选定1906年。。而末松留学英国,正是英国古典学兴盛之时,他对“文学”的理解倾向于古典的“希腊语和拉丁语为中心的高级书籍”的意涵,与幕末明治的学术氛围可说是不谋而合。英国古典学语境中的“高级书籍”,如果要在中国寻找对应,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采用了典雅的文言,通俗小说、戏曲是不能包括在内的;二是产生于特定意义上的“时代”,只有春秋战国的经典才符合要求。末松之所以在书名中醒目地标出“古”字,也许就有与“古典学”之“古”呼应的意味,与通常所说的“古代”之“古”,含义是不一样的。
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文学”概念依然偏重“知识”等等要素,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了末松谦澄。可以说,末松所处的时代,正处于新旧转换的过程之中。他的学术实际上是江户时代汉学向明治中国学过渡的产物。既有对传统汉学的接受、排斥,也有对西学的“误读”、涵濡。基于以上原因,他以“文学”指代“文化”,将“文学史”写成“文化史”,提供了一个颇具个案考察价值的文本。
三、《略史》“诗学观”及“离骚观”的折中性质
在传统汉学和现代中国学的视野下,《诗》和《离骚》具有不同的定位。传统汉学视《诗》为儒家的五经之一,而中国学则视《诗》为纯文学作品;传统汉学把《离骚》放在集部,其地位远在经部的《诗》之下,现代中国学则将《诗》和《离骚》视为地位相当的两部纯文学经典。那么,在末松谦澄的“文学”视野下,他给《诗》《离骚》怎样的定位?又是如何解读的?
《诗》是儒学的经典,故末松仍将其放置于《管子》和《老子》之后的“孔门诸书”一节。末松提出,《诗》与说理的《易》、记事的《书》虽然相异,但三者在功能上是大同的。在否定孔子所说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在当今的意义之后,他指出《诗》是上世的辞藻,从中可窥古人对宇宙自然之怜,见人情穷通之迹。末松对《诗》的“史料”价值的揭示表明,《诗》仍然是作为经学被认识的,尽管他在其中看到了人情。
末松指出,《诗》的秀逸之句是后世陈腐雷同之诗不可同日而语的。他举了《国风》中的五例来加以论述。《唐风·绸缪》“绸缪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见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一章,传统的经学多解释为符合礼节的男婚女嫁,而末松则认为“此乃田舍少年女子的野合之诗。无鄙野之痕也”[注]《略史(上)》,第18页。。《唐风·葛生》之“角枕粲兮,锦衾烂兮。予美亡此,谁与独旦”,毛序、孔疏都认为是刺君之说,末松则只说“寡妇独居之诗。愈读愈见其情思缠绵”[注]《略史(上)》,第18页。。《魏风·陟岵》之“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无已。上慎旃哉,犹来无止”,毛序认为是行役孝子对家人的思念,批判的是国家在征役上的剥削,末松则解读为客留他乡的游子思乡之情。除了上述三处,尚有《王风·黍离》《卫风·竹竿》,末松都是从人情出发,不涉及《诗》的深层含义是否含有讽谏、劝教的道德教化功能。在对《诗》的解释上,他与汉代学者的诠释差异加大,反倒与朱熹《诗集传》在方法和具体解读方面有一致之处[注]朱熹从文本出发,以体悟人情为主的解《诗》方式,尽管最后落脚点仍在“淫诗”也能惩恶劝善,但在具体解读上指向人情,具有解构汉代以降习以为常的政治性解读的功能(参见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在日本,尽管古学派和末松都明确对以朱子为代表的宋学提出批评,但在解《诗》的路径上却是暗合的。。
作为五经之一的《诗》,其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孔子。大体而言,孔子的《诗》论主要着眼于三个层面:一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作用,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注]《论语·子路》,刘宝楠:《论语正义》,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85页。,“郑声淫,佞人殆”[注]《论语·卫灵公》,刘宝楠:《论语正义》,第339页。是也;二是社会交往功用,在各种重要场合,例如外交场合,赋《诗》言志乃是重要人物必须习得的一种表达方式,所谓“不学《诗》,无以言”[注]《论语·季氏》,刘宝楠:《论语正义》,第363页。是也;三是克己复礼、修身求仁的功效,所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注]《论语·为政》,刘宝楠:《论语正义》,第21页。是也。概括地说,就是《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最低限度也能“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注]《论语·阳货》,刘宝楠:《论语正义》,第374页。。其中,孔子论《诗》关乎“诗教”的部分,被后世儒家继承并大力发展,《诗序》所谓“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注]《毛诗序》,郭丹主编《先秦两汉文论全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2年,第429~430页。,很长时间都是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日本《诗》学,尽管在细节上稍有不同,但从经学的角度认识《诗》则是一致的。这种经学视角,直到江户中晚期才受到古学派的大力驳斥,《诗》对人情的表达被视为根本,道德教化作用逐渐淡出阐释视野。这一转向,大概与日本和歌向来重视“情”之阐发有关。而末松谦澄在经学的框架中突出对作者个人感情的解读,表明他已意识到经学视野的局限,并试图有所突破。
末松谦澄对于屈原的解读,与其《诗》的解读,显示出微妙的差异。
本间久雄在《文学概论》中曾说:“‘先有知识(knowledge)的文学,其次有力(power)的文学。前者的职能是教(teach),后者的职能是动(move)。’……他所谓知识的文学,是科学上,哲学上及其他以知识的传达为主的学问,力的文学,便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而文学的动人,不外乎上面所说诉于读者的想象和感情。”[注]本间久雄:《文学概论》,台北:台湾开明书店,1976年,第16页。总体说来,末松的《略史》偏重的是“知识的文学”,偏重的是文化。不过,他对屈原的解读表明,非知识性的作品,在他看来也有其价值,论“离骚”一节即显现出了他对“力的文学”的鉴赏能力。
《略史》此节虽名为“屈原宋玉”,但实际上主要讲的是屈原,宋玉仅一笔带过:
此时代体裁异于前诸书之作、可见中国文学之盛者,乃屈原宋玉诸赋。二人作品可详见于《楚辞》。其文不与寻常作品相同,杂有荆楚方言,故难解之处多。屈原将自身比拟于女子,诉不遇之慨叹,足以动人心。秀逸之句颇多……《诗》之诗体过于简古,楚辞之赋体则多方言,皆不为今日所能模拟。然诗之妙境只有活用古体方能达。盖中国诗体在律绝体行于世后遂失其真调。律绝体始于唐代,而唐之大诗家如李白杜甫者,大异于后世雷同者,尤其李白的诗首以奔放自在称,杜甫虽稍拘泥规矩,但亦不尽力于严对,皆自著新意妙句以感动人心。清初以来却专以纤巧为先而后真情。和歌之沿革亦如是也。《万叶集》时代长歌多,故名歌不少;至《古今集》时代,则以三十一字之纤巧为要,其后遂至千首雷同之弊起。其弊今极,实可叹也。此论与东洋词艺之盛衰颇有关系,故兼述于此。[注]《略史(下)》,第16~19页。
末松曾说,赋异于其他作品,他这一小节的论述也明显异于其他各节,少见地没有对屈原思想侃侃而谈。不只是作者的情感被重视,读者对作品的情感体验也受到重视。如在《涉江篇》引文后说:“读之凄凄恻恻,使人酸鼻。”引文的作用不再是论证作家的思想内涵、历史地位或文献价值,而只在于情感的反馈。而对屈赋“多杂有荆楚语”的阐述,也是他罕见地注意到文字语言对文学作品影响的一例。
在“文学”即“文化”的视野下,末松为何会如此重视对“情”的解读?这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经史子集视野下的屈原解读本有重视其感情抒发的一面。在中国的诗学传统中,《诗》《骚》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范。“温柔、敦厚,《诗》教也。”[注]《礼记·经解》,见孙希旦《礼记集解(下)》,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54页。而屈原的《离骚》却以激越感情的抒发造成了对读者的巨大震撼,以至于汉代班固在《离骚序》中批评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谓之兼《诗》风雅,而与日月争光,过矣”[注]班固:《离骚序》,见郭丹主编《先秦两汉文论全编》,第760页。。晚明袁宏道《叙小修诗》则不避偏激地赞扬说:“大概情至之语,自能感人,是谓真诗,可传也。而或者犹以太露病之,曾不知情随境变,字逐情生,但恐不达,何露之有?且《离骚》一经,忿怼之极,党人偷乐,众女谣诼,不揆中情,信谗赍怒,皆明示唾骂,安在所谓怨而不伤者乎?穷愁之时,痛哭流涕,颠倒反覆,不暇择音,怨矣,宁有不伤者?且燥湿异地,刚柔异性,若夫劲质而多怼,峭急而多露,是之谓楚风,又何疑焉!”[注]赵伯陶编选:《袁宏道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年,第132页。《离骚》的情感抒发之激越,即使是在以经史子集为知识框架的传统中国,也没有被遮蔽。换句话说,日本的汉学视野,也不大可能遮蔽《离骚》的这一特点。
其二,这也与末松谦澄原有的知识储备有关,西学的影响倒在其次。说到末松谦澄的知识储备,不能忽略末松曾在汉学私塾专习汉学,而水哉园的特点之一是注重汉诗的研读。村上佛山一方面通过参加节庆来实践德育,一方面通过汉诗来培育“情”[注]Margaret Mehl:《明治时期汉学私塾之教育功能》,见张宝三、杨儒宾编《日本汉学研究初探》,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95~298页。。末松谦澄也受到其父的影响。他的父亲末松房澄是歌人,而日本和歌以情感的无拘无束的抒发为主,对末松的“以情论诗”当也有所启发。从他对《古今集》之后和歌的批判和对清诗的批判可以看出,他的和歌论与诗论是一致的。在他看来,为文的技巧虽然重要,但较之对格律的极致追求与巧饰,独创性和“情”处于更加核心的位置。后世的诗人、歌人因过于讲求技巧而多雷同,既丧失了真情,又缺乏独创性,乃是东洋词艺渐趋没落的根本缘由。末松的这一论述,不仅打破文学为儒学独占的观念,将和歌也纳入文学,并且与近代文学以感情为第一要素且强调文学的不可复制,无意中达成了一致。
在末松的《略史》中可以看到,他遵循的仍是传统汉学中注重作品功用的原则,但不同于以往的是,以政治解《诗》的汉代诗经学被放弃了,取而代之的是直指文本的解读策略。在论述《楚辞》时,末松重视感情的倾向更为凸显,诗人的个人情感得到更进一步的关注,而基于道德判断的屈原的忠君爱国精神则被忽略。末松罕见地没有赋予作品任何功利性作用,文学作品单纯地以其动人的感情而受到肯定。末松谦澄的这一路径,虽然可以为传统汉学所容纳,却在一定程度上暗合了正在兴起的中国学的品格。《略史》的路径选择具有折中性质。
四、结语:作为“文化史”的“文学史”
末松吸收西学的一大重点是对实证主义史学的构建,即抛弃传统史学的道德紧箍咒,取而代之的是对真实史料的重视。他的《略史》,将大部分著作的历史价值视为重要“文学”作用,而忽视了艺术表达的价值,就是这一观念的体现。另一重点是,他对欧洲古典学的吸收,使得在选择对象时将目光对准先秦,并且对“文学”的概念理解倾向于“古典、高级文献”的原始释义。他的汉学训练,也加强了这一倾向。可以说,末松谦澄以其基于汉学的知识结构,尝试写一部与西方思潮有所关联的中国“古文学”史,尽管偏离了近代意义上的文学意涵,但是从他的学术立场来看却是顺理成章的。
旧的观念和新的知识不是单纯地取代或者相加,而是处于一种浑融的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身处新旧之交、东西碰撞之时,又兼具国学、汉学、西学的素养,末松对新的学术范式的尝试在诸多日本明治学者和清末民初的中国志士中都能见到。末松无意中写出了一个具有转型时期标本风味的文本,其意义在于,它有着丰富多彩的不确定性,并将召唤出一系列的继续展开尝试的文本。对于这些文本,首先需要深入的体察、理解,其次才是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