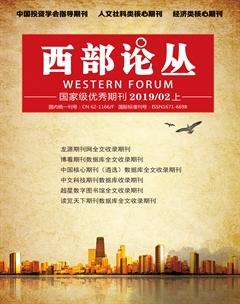“活济公”的内心世界
访谈时间:2016年11月
访谈地点:游本昌先生家中
人物简介:游本昌(1933.9.16— ),祖籍江苏南京,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北京本昌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长。1956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1985年因主演电视剧《济公》享誉海内外,并获得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奖、太平洋杯“青年最喜爱的电视男演员”奖。参加话剧《一仆二主》、《棠棣之花》、《大雷雨》、《黑奴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槐树庄》、《枫树湾》、《枫叶红了的时候》、《大风歌》等。受邀参加中央电视台1984、1987、1988年春节联欢晚会,主演小品《孙二娘开店》、《急诊》,哑剧《淋浴》等。制作并主演电视剧《济公游记》、《哑然一笑》、《了凡》。参与出演电影《剑雨》、《刀见笑》和《画皮2》等。2010年10月,出品话剧《最后之胜利》,饰演弘一法师,获得2011年第二届全国戏剧文化奖。
一、环境浸染造就表演之路
潘晓曦(以下简称潘):1951年,您从南京钟英中学完成高中学业,由南京市文联推荐加入南京文工团。1952年初随团调任上海华东人民艺术剧院演员,是什么原因促使您进入到戏剧表演的领域呢?
游本昌(以下简称游):我从小就喜欢戏剧表演,主要是受我二姐的影响,她是30年代的中学生,40年代的大学生,那个时候很多歌曲都是因为她在家唱我学会的,比如《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夜半歌声》、《义勇军进行曲》等等。在上小学之前,我们县里有广场电影,《渔光曲》、《迷途的羔羊》是那个时期我最喜欢的电影作品。三十年代上小學之后,我二姐经常会带我去看话剧,那是业余剧人时期,她业余的时间会去演话剧,参加上海剧艺社等,实际上那个时期剧团会用中学生跑龙套。后来也开始接触卓别林、秀兰邓波等。我第一次登台是在初中一年级,当时就读的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在平安夜演出《平安之夜》,这个日子我记得很清楚,1945年12月24日。我们是男子部,按照剧情需要饰演一对穷苦人家的姐妹,姐姐的扮演者是高年级的同学,我饰演妹妹,圣诞老人由我们班长饰演。故事的剧情是穷人家的孩子过圣诞节什么都没有,午夜时分圣诞老人降临,带来了很多的礼物。之后登台演出的机会是在高二, 1949年的冬天南京水患,我们做了赈灾的义演,演出的剧目的是陈白尘的话剧《升官图》。当时我们班上有几个也非常热爱表演的同学,大家一起讨论,把原本的五幕戏改编成三幕。不过我们的演出只演了三场就被停演了,主要是因为题材问题。那个时期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的具体要求,我至今记忆犹新:它提出文艺作品有三种形式,一种是牛奶,为人民提供营养;一种是白开水,可以解渴;一种是毒药,绝对不可以做毒药。在当时的环境下,普遍认为陈白尘的这个作品是毒药,所以后来就没有继续演出。这是我印象中最初的有关戏剧教育意义的观点,可以说这个观点我记住了一辈子。
1950年南京开展业余青年文艺指导委员会,由教育局、青年团、文化局、文联几家单位联合成立青年文艺指导委员会,到各学校进行表演艺术辅导,组织业余剧团,排演话剧。当时我即将高三,在南京市戏剧研究会杨颀老师的指导下,排演了独幕剧《胜利之歌》。该剧的创作者为南京大学的教授陈寿竹和沈蔚德夫妇,主要内容讲述在困难时期,一个50多岁的进步老教师,带领着学生和校工,进行生产自救的故事。年仅16岁的我在剧中饰演老教师。这个戏在区里获得一等奖,后来又获得全市的一等奖。1950年8月26号南京的《新华日报》上有相关的记载和评价,认为主角演的好。就是因为这个戏的演出成功,南京文联推荐我加入南京文工团,1952年初随团调任上海华东人民艺术剧院担任演员,并被保送中央戏剧学院华东分院表演系调干学习。
二、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的“佐料演员”
潘: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据说当时原本毕业分配计划是去贵州话剧团,可以介绍下是什么机缘让您在中央实验话剧院成立之初就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呢?
游:我毕业的时候开始是预备分配到贵州的,但是我们毕业大戏的成功演出却让分配方案发生了改变。我们班的毕业大戏是一个苏联喜剧,叫做《一路平安》,或者也可以翻译成《祝你成功》,这是苏联很著名的一部话剧。这个戏主要是讨论青年的道路问题,当时上海市团委和教育部门,让我们毕业班在学校的礼堂演了一个多月,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剧本也在后来被我们班的班主任陈芸,把内容改写成关于中国的“年轻一代”的故事。就在这个时期,欧阳山尊在《戏剧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呼吁成立国家话剧院。正好当时库里涅夫的表演干部训练班,把全国各剧团的骨干都集中起来了。戏剧学院的老院长欧阳予倩当时就想,把这批人留下来,作为国家级话剧院的表演骨干。
潘:1959年起,您先后在《一仆二主》、《英雄列车》、《百丑图》、《棠棣之花》、《大雷雨》、《黑奴恨》、《桃花扇》、《同甘共苦》、《小市民》等话剧中扮演各种角色,尤其在《克里姆林宫的钟声》里成功地扮演了列宁,体现了伟人的外部形象和精神气质,参加了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纪念演出。您在以往采访中提到过,济公是您的第80个角色,可以聊聊济公之前的79个角色吗?
游: 1959年我最开始是饰演剧中仆人这个角色的B角,当时的A角主演是李丁。连苏联专家都说《一仆二主》是放光的,之所以放光,是因为仆人的表演放光,那真是演得好。侯宝林都来观看了三次。有一次,在小院里聊的时候,我说五年以后,我想演这个角色。因为当时来讲,作为演员应该有他的理想角色。而我呢?当时是服务工农兵,我不是一个高大全人物角色的材料啊。所以听着人说小游刚进来,一点都不起眼啊。因为,我那个时候不是个大材料,个也不高,形象也不饱满。
潘:我看过一篇您的采访,您在采访里自谦,说您是一个佐料演员。
游:我说自己是佐料演员,那是实事求是。我看过一本美国翻译过来的著作,其中讲到演员素质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有自知之明。想象力,自识力,模仿力是演员的主要素质。自识力,就是对自己的能力和特色有清晰的了解和认知。
潘:这是您对于大众所谓的“龙套角色”和您心目中的“佐料演员”不同的艺术理解,也是您在舞台上创造出79个生动人物角色的心路历程。这个观点我认为对于我们现在的演员而言,是有非常大指导价值的。能不能请您具体谈一些您的经验体会?
游:我就听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老人家的教导,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没有小角色,只有小演员。要热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自己,这可以说是我毕生的格言。
热爱自己心中的艺术,而不是艺术中的我,艺术中的自己。我热爱艺术,我愿意参加一台都是优秀演员的演出,即使我是个龙套,我还是愿意演这出戏。所以我说我是佐料演员。我可以是一个真正的好佐料,也就是戏曲讲的硬里子。曾经我演配角,就是湖南省话剧团的话剧《枫树湾》,我演老地主,一个恶霸地主,全剧共有八场戏。当时出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演到第五场我演的老地主被枪毙了之后,一闭幕,本来应该是接下一场的,结果观众走了,以为戏演完了。
这就是舞台艺术的好处。它跟电影是不一样的,电影是导演的艺术,而话剧是演员的艺术。因为一台戏在观众眼中,任何一个角色,不论角色大小,只要出现在舞台上,出现在观众视线里,谁有戏观众看谁。而影视作品里是导演选择你,通过镜头的运用,我要突出哪个人,镜头就得对着谁,而不是谁有戏给谁。在排练《最后之胜利》的时候,服装道具什么都没有,就在我们的排练场,有观众来看了,特别的感动。所以一部话剧不止上演的那些场次,每一次排练都是一场演出。这就是戏剧艺术的魅力,就是表演艺术。表演是灵魂,是心灵之间的共鸣。
潘:这就是剧场艺术和电影最大的不同。
游:所以我說戏剧泯灭不了,它是影视不可取代的。
潘:因为它是一个共振的完成,是观众和演员公共来完成的。
游:对,这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艺术,所以戏剧表演艺术,他是此时此刻的开始和终结。这是现场的演员和观众的交流,每一场都会不一样。剧本和故事,演员,创造角色,还有观众,缺一不可。这是戏剧和电影最大的不同。
三、“活济公”的内心世界
潘:1985年您在张戈导演的《济公》一剧中出演济公,然后在杨洁导演的《济公活佛》、您自己导演的《济公游记》等作品中为我们呈现了深入人心的济公形象,这也成为了您到现在为止都被观众深深记住的角色,被大家称之为“活济公”。能谈一谈您是如何塑造这个人物的吗?
游:济公这个角色,可以说是我全部艺术生涯的经验、全部生活的经验、全部一辈子的艺术修养都灌注在这个角色里面。那时候刚好是杭州电视台建台两周年,有个作家建议拍摄《济公》并完成了剧本,找了上影厂的一个喜剧导演执导,并且找了曹禺担任文学顾问。不约而同,我那个时候,1984年我也考虑到了,我跟爱人商量说我可以演济公,后来很快在报纸上看到,严顺开跟电视台说好了,他要拍《济公》,看到这个报道后,我爱人还说,看来你就是不走运。所以一开始上海台导演到北京来找我时,我既不敢相信也没有立马答应,因为我不愿意跟他(严顺开)撞车。
当时单位让我去演,说我应该有一个大部头的角色了,确实我也相信我自己能把他演好,但我也不愿意打包票。当时新闻发布会上我还有点抵触,我就在发布会上说了这样一番话:“作为一个演员,这是个新角色,我不可能打包票,我不知道结果会怎样,但我一定会努力。”当时正好有一个跳高冠军朱建华,创造了一个纪录,后来就再超不过去了,我就说,“就像朱建华一样,横杆立在前头,他在起跳之前不知道能不能跳过去,我跟他一样,但我一定会尽可能用最大努力越过去,我不会从横杆底下钻过去。”
《济公》这部电视剧它不像中央电视台拍摄的《红楼梦》、《水浒》、《西游记》等四大名著作品,这些剧目原本的小说就已经保证了这个剧在文学上是站得住的,《济公》不是四大名著,甚至可以说是杂乱无章的。总体来说,从文学角度上看,它是一个不够成熟的作品。济公的故事有很多是话本故事,依靠说书艺人的口口相传,所以它的文学性不高。《济公》这本小说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不可以出版的,认为它包含封建迷信思想,包括说书人不可以说,粉碎“四人帮”后,小说可以出了,不过还是有一篇很长的序言介绍说这是游民文学,在济公身上有些市侩的东西。所以我在接受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跟导演说,有三条标准,第一条要让佛教界通得过,因为当时正好电影《少林寺》出来,佛教界不是很满意,第二条一定要让政府审查通过,第三条一定要让观众喜欢。毕竟原小说是有很大问题的。
这个角色从表演艺术上怎么站住呢?老院长说过表演艺术有两大支柱一个是台词一个是动作,戏剧动作。所以我们后来在建立济公这个人物的时候,运用了大量的形体动作,尤其是哑剧的表演形式。济公能够长年不衰、百看不厌的原因,是观众对这个人物感兴趣,就是我塑造的这个性格化的人物。在塑造济公这个形象的时候,和其他的电视作品不同,我是不太依赖台词的,并不是说轻视台词,只是台词和形体动作并重,而更重要的是形体动作。因为剧本和原小说文学性上的局限性,很多的台词都是我自己现场根据剧本说出来的,有的时候要思考应该说什么,怎么说,百思不得;有时候一句词拍了八遍,然后突然就找到感觉了。这就是演员和人物的关系,你进入这个规定情境之后人物就对了。剧本里的内容,我认为只是完成了一部作品的25%;而这个剧本字里行间所隐藏的75%的东西是需要导演和演员二度创作共同挖掘出来的。济公的形象是活活生生的人物,他不是一个文学形象的,也不是一个文字形象的,而是一个立体的是视觉加听觉的形象。曲艺中的相声,很大程度上是听觉形象,它的视觉形象可以是次要的,甚至没有都没关系。所以相声我们可以听广播,但我们的表演是有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的,是要观众去观看的。拍摄的时候,导演对我非常宽容,我把卓别林的喜剧方式,包括戏曲传统的东西,还有哑剧的东西大量融合在一起,杂糅进来。甚至有一集戏叫戏弄公差,当时在拍摄的时候,我直接把它变成哑剧。这段故事是抓济公,用铁链子锁着,拉出灵隐寺,到进秦相府之前。这一段路上公差们拉着他,我就跟他们开玩笑,让两个公差都掉到水里去。然后他们是推不动,也拉不动,给他们玩一些这样的神通。最后他们扛着我走,我躺在他们背上把我架着,进的这个秦相府。这不就是戏弄公差吗?不需要台词。
《济公》跟《红楼梦》、《西游记》这些经典改编是有区别的,它不是文学著作保证了它的成功,也不是先入为主。因为我演的是济公活佛,而不是丑角笑星济公。
潘:这是您对于这个角色的理解的出发点?
游:是的。不是我演一个喜剧,而是我在演济公活佛,这是不一样的。
四、“以文艺化导人心”是一生的艺术创作坚持
潘:1998年底至2001年底的三年时间里,您创作并主演了电视哑剧《游先生哑然一笑》,是什么原因让您偏爱哑剧这种艺术形式?哑剧的表演与您其他的表演经历有什么不一样的艺术特色呢?
游:当初在饰演济公之前,导演就是看了我的哑剧表演才选择我扮演济公。当时严顺开已经是全国著名的喜剧演员,又得了卓别林的电影节的奖,应该说“阿q“这个角色跟我是擦肩而过了。所以专业演员就是这样,机会在八三年、八四年没有降临到我的头上,而后来我演济公获得了成功。主要是因为我时刻准备着,东窗不亮西窗亮。
潘:就是说您一直都很喜欢哑剧这种表演形式?
游:我对表演艺术非常喜欢。表演艺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语言的一个是动作的,而我尤其擅长于动作的。其实哑剧本身是一个艺术世界,有动画哑剧、杂技哑剧、魔术哑剧和舞蹈哑剧。我的哑剧是介于话剧和舞蹈之间的艺术,我的风格就是这样的。
潘:我了解到《游先生哑然一笑》这部剧的市场并不理想,应该是让您亏了不少钱,您是如何看待在浮躁的大时代背景下,哑剧这种需要静心欣赏的艺术形式生不逢时的现实呢?
游:反正东西我留下来了呀。屠呦呦是怎么成功的,要有甘心坐冷板凳的精神。不管它最终市场的回报是什么情况,起码我把它拍成了,我也把它留下来了,可以被后人所参考,这就是它的价值。我投入了180万,拍了52集,这一次我回到母校,母校跟我要了,准备放在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图书馆的资料里,我认为这就是它的价值。我并不是想拿这个剧去赚钱,我就是游先生哑然一笑,哑然一笑。
潘:2009年您自导自演电视剧《了凡》,饰演云谷会禅师。我们都知道《了凡四训》是袁了凡先生为教育子孙后代所写的四篇家训,是一部蕴含哲理与智慧的传奇故事,也是一部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教育作品,关于创作这部作品的初衷和创作中的故事您可以介绍一下吗?
游:我拍摄这个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是我们的民族所需要的。我们需要了解因果,不了解因果社会就乱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就是因为不了解因果,所以才会有骨肉相残的这种违背中华传统道德的悲剧。
现在我们遇到的不是简单的艺术上的问题,田本相的文章《中国话剧的衰落与世界戏剧的萎缩》,讲到演员表演不专业的问题,这其实不是一个表演是否专业的问题,这是人的问题,也可以说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感情问题,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的,是习总书记在去年文艺座谈会上讲的:“艺术作品究竟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前几年,很多人宣扬一个理论,认为观众到剧场来不是来上课的,不是来受教育的,而是来找乐子的,所以就在文艺作品中展现了各种坑蒙拐骗、卖假货等等不良的社会现象,并且笑那个买假货的人、上当的人,智商低、活该,这就是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和感情问题。之所以会拍《了凡》,就是因为我始终觉得,这种美德是必须要宣传,必须要一代一代传扬下去的。
潘:那您觉得在这种市场条件下,作为一个演员或者说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应该怎样去坚守精神家园?
游:这就是卓别林和苏菲亚罗兰说的那个问题。当时,苏菲亚罗兰是意大利的演员,出演了《两个小妇人》,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后来又出演了一部《香港女伯爵》,结果遭到了观众的差评,让她十分的懊恼。她把自己的懊恼去和卓别林说,然后卓别林跟她說什么呢?“yes or no?你要学会说no了”。所以我的选择就是有所不为,有所为。
《济公》之后,有段时间我出演的角色并不多。其实机会是很多的,尤其是刚演完《济公》之后的那几年时间。但我拒绝了很多人的邀请,后来人家也就不找我了。我的原则其实并不高。只要是及格之作就可以干啊,只要不挨骂都可以。我就是要有选择,但结果这一闲就是近20年。
因为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你要表达你的世界观、艺术观、文艺观。思无涯,是我创造所有艺术形象的根本。习主席说,“以文化人,以德育人”,就是让我们不在意一时一地的得失,坚持,而且自在的坚持不是痛苦的。干还是不干,有所为有所不为,这很重要。人的选择很重要。你到这个世界上来干嘛来了?要人云亦云那有什么意思?表人所未表,演人所未演,写人所未写。所以我觉得,学佛学有很大的好处,就是让你有远见,要有博大的胸怀,宏大的胸襟,以出世的眼光做入世的事业。
潘:在资料上我们可以查阅到,在您六岁的时候,父母便把您送到上海法藏寺拜兴慈法师为师,然后在零九年的时候您正式剃度出家,这个对您创作《了凡》和后来的弘一法师《最后之胜利》有什么关联吗?
游:09年的时候,我并没有出家,当时是为了拍摄《了凡》专门安排了一段时间体验生活。真正的剃度是决定演弘一大师的时候,我是认真的对待了,非常认真的对待了。咱们话剧的创始人李叔同,他从一个才子到出家,这个过程很多人不理解,很多专家都不理解,讨论这个问题的著作有很多。而我既然要表现那一段历史,塑造这个人物,当然要真实地去体会其中的精神内涵。
潘:自2010年初演以来,《弘一大师——最后之胜利》已在国内外演出108场,由文化部带队赴台湾出席第一届海峡两岸文化遗产节,2011年获得第二届全国戏剧文化奖,请您讲讲这个戏的创作、演出过程。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一部剧?
游:我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做。首先我认为这个戏是有价值的,李叔同是话剧的创始人,是个爱国者,又是文化先锋。最开始的时候,我是希望可以和国家话剧院共同合作一起来完成这个剧的,结果他们认为这个剧不是一个票房戏,合作就没有谈成,然后我就觉得自己来做。
潘:您在很多采访中都提到,您的公司并不是商业性的,我能查到的是您公司除了拍了济公之外,剩下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为了完成您的某种艺术理想,比如说哑剧、比如说了凡,包括现在在运做的弘一大师,那么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一个公司如何完成他的生存呢?
游:完成啦。
潘:您是怎么完成的?
游:你看着好像是赔了是不是,我是靠倒西墙补了东墙。
潘:您是靠出演别的角色,来完成自己的艺术理想吗?
游:对呀,尤其是我演济公。所以是济公支持了我。能不感恩吗?说实在就是这么一个关系,我深信因果,“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是深信不疑,我们全家都深信不疑。当初决定做《最后之胜利》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家开会我问女儿老伴干不干?全家都同意,那就干。
潘:您塑造李叔同,也就是弘一法师这个角色时的出发点是怎么样呢?
游:出发点就一个,就是我墙上的这幅字,“以文艺化导人心”。这是九八年的时候,一位高僧送给我的,你看在这幅字里他称我“本昌济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认可。这个后来就成了我的传家宝,我拿着这个字参加了王刚的《传家宝》那个节目。王刚邀请我的时候,以为我跟他一样是一个收藏家,结果我就带着这个去录的节目,我说这就是我的传家宝。
我们做弘一法师这个戏的时候,资金的来源是出售了公司用于经营地的房子。不过我当时觉得房子也是济公给的呀。从开始演出,我们始终都坚持公益演出,所有的一百多场都是公益演出。七年多时间,我们是不从这个演出费里拿一分钱的。在相关单位邀请的时候,我们也是一个裸成本的演出,就是说只包括演员的劳务费、工作人员的劳务费和吃住行的费用,还有设备的租金,包括灯光、音响等等这些和运费。“以文艺化导人心”,这就是我的座右铭,也是我们全团的任务和艺术使命。
说实话,济公和弘一大师,我们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都是有提到过的。关于济公,他说济公关心人民,为民间的事打抱不平,在民间流传着许多关于济公的美丽传说。对弘一呢,总理曾经给曹禺说过,将来你们要写中国话剧史的话,不能忘了李叔同,也就是后来的弘一法师。
很多人最初听说这个戏的时候,都认为这是一个关于佛教的戏,其实并不是。1957年话剧五十年的时候,欧阳予倩写了《黑奴恨》,把原来的《黑奴吁天录》改编成了《黑奴恨》,孙维世导演。当时纪念话剧诞辰50周年的演出我参加了。2007年,陈欣一导演的《吁天》,在人民大会堂演出,当时是纪念话剧诞辰100周年,这个演出我也有幸参加了。我是唯一一个,50年和100年这两场演出都参加了的演员,而且演的是同样一个的角色。我觉得这是挺幸福的一件事,我对得起我心中的艺术,并不在乎这个荣誉或那个荣誉。
“弘一法师”这个戏,经历过一个非常困难和低谷的时期。第一年我们只演了三场,第二年演七场,第三年演九场,第四年演了21场,第五年演了44场,到现在一共演出108场,而且这个演出的场次还会继续不断的增加。所以一个人心中要有信仰,要有理想。习主席说了要坚持,这是很重要的,要坚持我们的目的就一定能够达到。关键是坚持,看你耐得住耐不住寂寞、冷落,甚至是压制。所以今天你作为一个话剧研究者,能够找到我,我是很感动的。
我现在的信条,还是中央实验话剧院建院时期的老院长欧洋予倩和总导演孙维世的训示,就是:“集合一批有共同理想的人,在艺术上,创作上,有共同语言的人。有共同理想,才会有共同语言。那大家在一起,做一些令人难忘的作品,这就是我们的理想。”对于我,只有拥有共同的理想,才会有共同语言,才会有非常好的合作,才会碰撞出非常好的火花来。
潘:我看到您是“芳草地国际学校”话剧团的艺术总监,您也曾经受聘于中央戏剧学院教授表演课程,在戲剧教育这个领域您有什么可以和我们分享的体会吗?
游:除了刚才我们聊过的,是人生精神的传承这个理由之外,就是我们为人民服务,为观众服务。这是我从事文艺工作,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给我的一个启示,给我的一个教育。我从来不写我是怎样演济公的,这种文章我从来没写过,我认为不是我扮演济公,而是济公教化了我。
潘:所以也就是说您认为,整个您的演艺生涯传递这种文化也好,或者说人生的道义也好,这是您从事这个戏剧工作的使命,所以就始终在坚持?
游:使命感和责任感。我第一次出国是因为济公,八七年四月份去新加坡。因为春节期间新加坡电视台播放《济公》,六集《济公》放了一周,收视率节节攀高,一直到突破百万,所以就邀请我和上海明星团一起去了。而到了那之后,一个司机下楼的时候跟我说,“游先生,我们都非常感谢你。”当时我很奇怪,因为一般演员和观众的关系都是,我们非常喜欢你,我是你的粉丝之类的,怎么要感谢我呢?我做什么了要感谢我?他说:“因为我们的下一代都是英文教育,而看了你的电视剧之后,觉得中国有那么好的济公,讲究孝道了、讲究爱了、讲究道德了。”他说我们真感谢你,我作为一个演员觉得很自豪,我的观众不只是在国内,全世界当时八千万华侨都是我的观众,都是我应该服务的对象,我应该多想着为他们。他们是我的观众,这增加了我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而且在国内参加巡回演出活动的时候,不分民族、不分地区、不分年龄,一概的喜欢济公,所以说这是我的济公缘。
“舍我利他”,这是我的艺术生涯想传达的观念。你看“最后之胜利”说明书里的最后一句话,“为人类提供正确的精神指引,以及强大的精神动力”,这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我坚持艺术道路,坚持艺术教育的任务。
在我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之后,曾经到清华大学学生剧团排的《一路平安》这个戏,而且用我们的方法指导他们排,结果蒋南翔校长看了之后觉得非常好,也让他们演了一个多月。这波人退休之后,又回到清华仍然组织校友艺术团,仍然请我当艺术指导,排演戏剧作品,所以我参加了清华的校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戏剧艺术对人生的影响,那么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把这种戏剧艺术的表演艺术这种方法推广,向全民进行推广。
我是2007年,在北京史家小学最早有了配合他们成立话剧艺术团的想法。其实我这个想法最早是在1962年,在中央电视台,银河之前成立了少年电视演出队,这个队里出了洪剑涛,祝新运等。这种戏剧艺术是完全可以推广的。推广什么呢?人人都应该学会戏剧表演,人人学会了戏剧表演都会有好处,不一定都是要当演员。比如清华大学的那些毕业生,他们都是工程师,但是退休之后,当年的小伙子小姑娘,都已经是白发苍苍,但他们依然很热爱戏剧表演。我对戏剧表演的认识就是人生艺术课,但是表演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的表演方法很多都是演戏,就是“演”。
潘:那您心目中的表演艺术应该是什么样的?
游:是“化”。化作人物,人物和演员合二为一,进入化境。人物就是我,我就是人物,从我出发到达人物,到达角色,从而和角色化为一体,这样的表演。“最后之胜利”这个戏,为什么有人会观看16次,看6、7次,这次11月30日、12月1日,我作为上海戏剧学院毕业60年的一个毕业生,回到母校,在上海戏剧学院71周年校庆的庆典上,在我毕业公演的剧场进行演出。这个剧场当时是戏剧学院实验剧场,后来命名为“端钧”剧场,朱端钧是我的老师。
潘:我觉得这个特别不容易,毕业60年还可以回母校去演出。
游:我们入学是45个人,毕业时是26个同学,其他人都转行了,最后做了演员的只有不到15个人。现在还在舞台上的只有我一个人了。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学校4年的教育。我在学院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学校4年,受用一生”。就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我为什么讲这个,我认为艺术观、生活和人生观是非常一致的。陈老总的诗,“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还有陶铸同志写的松树的风格。我觉得我有点儿像黄山松,黄山的迎客松,他不是挺且直,它从山体缝隙里挤出来的,它不是直的,不是挺拔的,它是从石头缝里长出来的。在它成长的过程中,一直到形成到有伞盖了,才是黄山迎客松。所以我实际上有过好日子,有过艰难的日子,正因为有一开始的好日子,打下我的一个基础,对生活的热爱,对艺术的热爱。然后艰难的日子也一直坚持。
四、访后跋语
那是初冬的一个午后,我在朋友的引荐下如约来到游本昌先生家中。济公的故事,经由清代小说家的整理流传于世,却是因为当年游本昌先生的演绎,使得这位“非俗非僧,非凡非仙”、嬉笑怒骂、狂放不羁的传说人物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传奇。一部戏,一辈子,更伴随一众人的成长,尽管游本昌先生在访谈过程一直在努力卸下“济公”在他身上烙下的喜剧演员的印记,但在实际生活里,老人家却有太多记忆和“济公”缠绕在一起,甚至连个性都如济公一般与人为善,广结欢喜缘。
与先生短暂的相识和谈话,先生多次表达了对于我们这次采访的感谢,但其实先生对于戏剧舞台的热情,对于艺术人生的感悟和坚持也让我深深的被震撼。无论是戏剧舞台,还是电视和电影作品,先生用其精湛的表演塑造了无数鲜活的人物和角色,记录这般“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经典历程,是责任,是怀念,是不想错失,是盼望再有辉煌。84岁的高龄依然站在舞台中央,先生的言传身教会陪伴话剧藝术到达更加光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