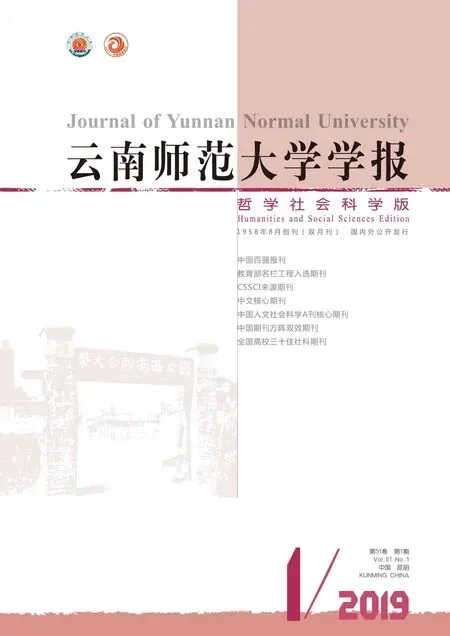汉语的欧化与欧化的汉语
——百年汉语历史回顾之一
刁晏斌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引言
如果从1919年“五四”运动算起,现代汉语从形成至今正好一百年的时间。毫无疑问,历经百年的现代汉语非常值得而且应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角度进行全面的回顾与总结。
在百年汉语的发展历程中,“欧化”的思想与实践伴随始终,并且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前者的基本面貌、精神与走向,因此正是一个对百年汉语进行回顾与总结的重要角度与方面。
把欧化概念用于文学及语言,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最早见于傅斯年,他提出“欧化文学”“欧化国语”以及“欧化的白话文”等概念,主张做白话文时要“取个外国榜样”“总要想方设法,融化西文词调为我所用”。至于“西文词调”的具体所指,“就是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figure of speech)……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J].新潮,1919,(1). 这里的“词枝”后来一般译为“修辞格”。。作为“五四”新文化及新语文运动的重要规划者与参与者,傅氏的这一观点影响巨大,而自此以后,“欧化”一词就频繁出现在“五四”新文化建设者们的口中与笔下,以及后世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中。
如果从傅氏提出“欧化文学”“欧化国语”等算起,时至今日,“欧化”的概念恰好经过了一百年,它与百年现代汉语一起历经风雨曲折,其内涵等也不断地发展变化,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概念史”。[注]语言学界似乎鲜少有人提及概念史。我们认为,某些重要的概念及其内涵、外延等的发展变化,既有个体(概念本身)研究的意义,同时更具整体(概念所属“本体”)研究的价值,而“欧化”无疑正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站在今天的立场及角度,我们对“欧化”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它是一个核心的概念。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欧化的主张与实践,现代汉语绝对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所以,它理应成为我们了解与认识百年汉语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最为重要的“关键词”之一。
第二,它是一个历时的概念。无论就内涵还是外延而言,“欧化”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都有明显的发展,并随时代而变化,由此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内涵丰富的概念史。所以,我们对它的了解与认识不能仅局限于某一点(特别是其“起始点”,即最初提出时),而应当用发展的眼光历史地看待它。
第三,它是一个“跨界”的概念。欧化不仅有强烈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同时也是覆盖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与发展的一个重要概念。所以,不仅语言学领域在研究它,其他一些学科领域如政治、文化、历史、文学等也都在关注和研究它。特别是文学研究领域,由于对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关系探寻热情的长久持续,所以对欧化问题尤其重视,并且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增广或拓宽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语言学界研究的不足。
如果立足于以上3点来看汉语的欧化与欧化的汉语,一个直接的认识就是欧化问题还有很大的讨论空间。着眼于相对宏观的层面,相关的讨论大致可以在共时与历时两个方面进行:共时方面,主要是进一步理清对欧化概念的内涵与实质、对象与范围等的认识;历时方面,主要是梳理汉语欧化的过程与脉络,具体包括起始时间,重要的节点及其与现代汉语的关系等。
本文即在这一思路下,对上述问题择要进行讨论。
一、欧化的内涵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建设者们虽然大力提倡欧化,但对它却没有给出一个完整准确的定义。我们所见,张星烺所作的界说,是学界较早、较为全面完整的表述:
兹不论其高下,与夫结果之善恶,但凡欧洲人所创造,直接或间接传来,使中国人学之,除旧布新,在将来历史上留有纪念痕迹者,皆谓之欧化……或物质文明部,如天文、历法、医药、测绘、机器、轮船、铁路、电报等等是也。无形部或思想文明部,如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文学等等是也。[注]张星烺.欧化东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2015:1~2.
如果把上述定义限定在语言范畴,略加改造,我们大致可以得出一个关于汉语欧化的定义,即“中国人学习直接或间接传来的欧洲语言,在汉语中除旧布新,并留下痕迹”,而由此形成的语言形式(主要是书面语)即为欧化汉语。
今天谈欧化,首先要结合发展变化来明确其内涵,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以下3个问题。
(一)“欧”的所指范围
关于这个问题,应该有两个立足点:“元初”与“后来”,换言之,应该遵循历时的原则。
立足于“元初”的意义,“欧”无疑是指欧洲,而这也是一直到当下,人们最常作的理解与表述,具体到语言,则指欧洲语言或印欧语言(此外还有人称之为“西洋语言”“西方语言”等),而其具体所指,则是英语。王力说得很清楚:“所谓欧化,大致就是英化,因为中国人懂英语的比懂法、德、意、西等语的人多得多。拿英语来比较研究是更有趣的事。”[注]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1985:334.
然而,立足于后来的语言事实,我们看到,除了欧洲/印欧/西洋/西方语言的英语影响外,近代以来汉语还深受日语的影响。杨海明、周静指出:“汉语除了直接受英语的影响外,还受到英语的间接影响。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日语受到英语的影响之后再影响到汉语。”[注]杨海明,周静.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31.此应属于上引张星烺所说的“间接引进”[注]张星烺.欧化东渐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3/2015.。杨、周书中认为,这种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词汇方面。其实,除了词汇,语法等方面近代以来受日语的影响也很明显,而这可能就不一定属于“间接”的范畴了。梁启超在自述其“新文体”的特点时就说“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中华书局,1920/2010:128.,就其实际情况看,这里的“外国语法”显然并不单指英语语法,至少还应包括日语的某些语法形式。鲁迅的情况基本也是如此,冯天瑜指出,“鲁迅后来的小说、杂文和译作,也多用‘日本新名词’和日本句式。”[注]冯天瑜.新语探源[M].北京:中华书局,2004:434.以上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1932年瞿秋白在大众文艺讨论中批评“五四”新白话是“中国方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以及古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注]宋阳(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N].文艺月报,1932-6-10(创刊号).转引自戴昭明.规范语言学探索[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88.也从正面明确了这一点。从事中日语言交流史研究的旅日学者沈国威教授也认为,所谓的“欧化语法现象”中存在着大量的日本因素。[注]沈国威,李真.徜徉在中日语汇的密林里——沈国威教授访谈[J].学术月刊,2011,(4).
为了明确甚至于强调这一点,有人直接仿“欧化”而造“日化”一词,作为与前者并列的概念,比如寒生指出:“现代的白话文,已经欧化、日化、文言化,以至形成一种四不像的新式文言‘中国洋话’去了。”[注]寒生.文艺大众化与大众文艺[J].北斗,1932,(3&4).转引自袁进.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382.
除了英语与日语外,汉语在不同时期还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并且或多或少地留下痕迹。比如俄语,徐来娣比较系统地考察了俄语在词汇、词法、句法、语义等层面对汉语的影响,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相关发展变化。例如,现代汉语中“如果”有时不表假设(常取“如果……那么”的形式,表示前后句之间的对比或对照,如“如果说政论性文章多引用一点还属正常的话,那么我们再看一个文学作品的例子”)[注]徐来娣.汉俄语言接触研究[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7:122.有人从修辞的角度总结为“超假设”辞格,[注]周明强.“超假设”修辞[J].修辞学习,1993,(4).这一用法就来自俄语,[注]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汉语教研组.五四以来汉语书面语言的变迁和发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153~155.是汉语词汇的意义及用法,甚至于修辞受“俄化”影响的一个例证。
另外,如果把眼光放远一些,历史上来自梵文的汉译佛教典籍也对当时及后世的汉语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下一节再讨论。
如果就“外来词”而言(这是欧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见下),那么涉及的来源范围就更广了。高名凯、刘正埮立足于早期及当时的语料,搜集了来自英语、法语、德语、日语、俄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以及我国几种少数民族语言的现代汉语外来词共一千五百余个,来进行研究。[注]高名凯,刘正埮.现代汉语外来词研究[M].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再如,就俄语的影响来说,徐来娣认为,现代汉语中仅俄源词的总数就在1200个以上。[注]徐来娣.汉俄语言接触中俄语在语义层面对汉语的影响[J].汉语学习,2008,(5).
由此可见,早先提出的“欧化”概念已经无法对所有相关的语言事实形成全覆盖了,所以,不少人试图改用它名,从而使名实相当,比如“现代化”“西化”“外化”“洋化”等。
《现代汉语词典》前五版“欧化”的释义均为“指模仿欧洲的风俗习惯、语言文化等”,从第六版起改为“西化”。释义的这一变化无疑也是着眼于实际,缩小了此词的内涵,并由此而扩大了它的所指及涵盖范围(即外延)。
然而,“欧化”在汉语语言学界的使用已有百年历史,早已成为一个基本甚至核心概念,因而难以撼动、取代;而其“顾名思义”所带来的名、实不符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的其他替代名称也都有局限(如“现代化”并不准确,“西化”范围有限,“外化”的原有意义已经“占位”在先)。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认为应该是重新界定,把“欧”的所指范围扩大到上引谢文所说的“外族语言”即外语。这样,欧化的基本所指就是受外族语言的影响,接受其形式以及由此而引起自身的发展变化。
(二)欧化的具体内容
以下将要讨论的是汉语的欧化涉及哪些方面。这里大致包括大小两层意思,大是指哪些语言要素受欧化影响,小是说在某一受影响要素中有哪些具体的表现。
先看大的方面。在这方面,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归纳一下,大致有一元说、二元说与多元说。
持一元说的人把欧化等同于语法研究中经常提及的“欧化语法”。王力指出:“因为欧化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增加,它虽够不上称为中国现代语法,谁也不敢说它不变为中国将来的语法。”[注]王力.中国现代语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4/1985:4.如果说,这段话还不是特别明确的话,那么以下表述则是明确无误的:“所谓汉语欧化是指受西洋语法影响而产生的,在汉语中出现过的,以及存留下来的新语法现象。”[注]朱一凡.现代汉语欧化研究:历史和现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2).
持二元观点的也不乏其人,我们看到的最近表述是:“具体说来,欧化白话有几个层面,首先是词语——西方的地名、人名、器物名以及制度文化层面的系列新词语,‘满口新名词’是人们对早期欧化作品的直观印象;其次是词组、句法、句子结构发生了不少变化,主要是句子变长、句子结构更加严谨、句子结构中三个以上的分句增多,长定语和定语从句大量出现,以及如被字句、双重否定等汉语传统句法中从未有过的语言现象。”[注]张曦.欧化白话与本土白话的融合与发展——沦陷时期上海写作的语言策略[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
所谓多元说,当然是指比二元说涉及更多要素的观点。
前引傅斯年把“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均纳入欧化的范围,这自然是一个涉及最多因素的概括了,几乎包括了语言及其使用的各个方面。如果说,以上表述还只是“设想”或“规划”的话,那么以下则是基于对汉语欧化事实的总结与归纳:
“欧化”可以概括近代以来汉语与欧洲语言接触产生的文字、词汇、语法、语体等方面的变异,汉语欧化现象曾以诸如“拉丁化”“拼音化”“外来词”“欧化语法”等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注]张彤.欧化汉语研究的热点和趋势——聚焦近代以来欧化汉语研究的两次高潮[J].江汉学术,2017,(3).
有人甚至把标点符号、文字横排等也归入欧化的范围。[注]赵晓阳.欧化白话与中国现代民族共同语的开始:以圣经官话译本为中心的思想解读[J].晋阳学刊,2016,(6).
我们认为,就现代汉语而言,它的三大要素(语音、词汇、语法)与五大内容(在三要素的基础上再加上文字和修辞)都有欧化的问题,虽然表现有多有少,但是均未“置身事外”,所以在讨论欧化的时候都应加以考虑。此外,像上文提到的标点符号、文字横排等,自然也是欧化的表现。所以,今天我们看欧化,应该是一个“全方位”“全要素”的概念。
关于小的方面,即在汉语的某一要素或方面欧化形式有哪些具体表现,或者说哪些现象可以而且应该纳入欧化的范围,目前讨论得还不够充分。已有的相关表述主要集中在语法方面,如谢耀基认为,汉语语法的欧化,通过词、语、句的结构变化,主要表现在新形式、新用法的产生,以及旧形式、旧用法在应用范围和使用频率方面的增加;[注]谢耀基.汉语语法欧化综述[J].语文研究,2001,(1).贺阳指出,“(欧化语法现象)这一概念既指汉语中以印欧语言为摹本,通过模仿而产生的新兴语法成分和句法格式,也指汉语中原本处于萌芽或休眠状态的语法形式由于印欧语言影响的推动和刺激而得到迅速发展的现象。”[注]贺阳.从现代汉语介词中的欧化现象看间接语言接触[J].语言文字应用,2004,(4).后来,贺阳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欧化现象与汉语语法资源相关程度的角度把欧化现象的具体表现概括为5个方面。[注]贺阳.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现象研究[J].世界汉语教学,2008,(4).
把以上几个方面的认识结合起来,我们认为,汉语的欧化以及欧化的汉语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一是“纯”外来的形式,包括外来词语和外来句式等;二是由于受外语影响而产生的某些形式或用法;三是汉语中某些固有形式由于受外语影响而发生的变化。以上3个方面的所指不仅是词汇和语法,此外还包括文字、语音,以及属于语言使用范畴的修辞,以至于标点符号等。
(三)欧化的“善”与“恶”
在汉语的发展以及汉语研究中,欧化一直是一个重要的但又饱受争议的概念,总体而言用“爱恨交加”来形容人们对它的感受可能并不为过。对欧化大加提倡、充分肯定的,不消说“五四”时期的文化先行者们是把它当作改造旧汉语、建设新汉语的良方,甚至是不二法门;就是多年以后,很多人也基于自己的立场与角度,对其进行充分的肯定。比如,张明林、尹德翔认为,欧化为现代汉语的发展打通了一条宽广的大路,为它的壮大提供了一个方面军的支持。文中具体列出3点:一是丰富了现代汉语的词汇,二是完善了现代汉语的语法体系,三是丰富了现代汉语的情感色彩。[注]张明林,尹德翔.汉语的欧化历史与现状[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0,(1).刘泉指出,欧化后的白话文,语法结构更加严密,表意更加明确,表现手段更加丰富,真正摆脱了古旧文言的束缚,最终确立了自身的表达规范。[注]刘泉.文学语言论争史论(1915~1949)[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78~79.总体上看,人们对欧化的肯定多是立足于较为宏观的层面。
当然,对欧化完全或一定程度上持否定态度的也大有人在,但多是基于某一政治立场,或着眼于一些微观、具体的语言现象。对“欧化白话文”批评最为尖锐的是瞿秋白,他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没有完成它的任务”“产生了一个非驴非马的新式白话”。这样的白话 “是不人不鬼的言语”。所以他的结论是,应该打倒这种“五四式的半文言”的“杂种话”。[注]转引自王本朝.欧化白话文:在质疑与试验中成长[J].文学评论,2014,(6).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在突出强调语言大众化的现代文学史上,‘欧化’曾经是一个带有贬义的概念,”[注]张卫中.20世纪初汉语的欧化与文学的变革[J].文艺争鸣,2004,(3).甚至连“维基百科”的解释也是如此:“欧化中文,是指语法、文笔、风格或用词受欧洲语文过分影响的中文,一般带贬义。影响中尤以英文所造成的最为深刻。欧化中文除了缺乏传统中文的特色,也可能因为用词繁琐生硬,导致阅读及理解上的障碍。”
这一认识影响之深,从一些作家的态度及写作实践也能反映出来。例如,巴金在自述中曾经写道,在编辑自己的《文集》时,在过去的作品中找到不少欧化的句子,于是都把它们修改或者删去了。[注]巴金.谈我的散文[A].巴金.巴金文集(第十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不过,更客观、更合理的态度是应当“一分为二”地看待汉语欧化以及欧化汉语,而有人确实在这样做,由此就产生了“善性欧化”与“恶性欧化”的概念。[注]余光中.论朱自清的散文[A].余光中.余光中散文选集(第3辑)[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1997.谢耀基对此做过这样的说明:“善性欧化,指借用外语形式、用法,能够取长补短,‘欧而能化’,增强汉语的表达能力和效果。恶性欧化,指仿用外文语法,陷于乱用、滥用,‘欧而不化’,写出不中不西的语句,使汉语不通、不简、不洁。滥用外来词语,语句中西夹杂,最为人诟病。”[注]谢耀基.汉语语法欧化综述[J].语文研究,2001,(1).
有人甚至据此构拟了一条现代汉语的欧化发展线索:“如果说五四至20 世纪40年代是汉语被‘欧化’,那么,20 世纪40年代以后至今,汉语都处在一个‘化欧’的过程中。也许,若干年后,我们会说,现代汉语不是‘欧化’的语言,而是‘化欧’的语言。”[注]朱恒.“现代汉语”辨析[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0,(10).
从单一的价值评判,到“善”“恶”的二元区分,从“欧化”到“化欧”,既反映了人们立场、观点和认识的发展变化,同时也揭示了汉语欧化及欧化汉语的发展历程,而由此也拓宽了这一问题的研究思路与范围,昭示了其可持续性与发展性。
二、欧化的历史
要梳理汉语欧化与欧化汉语的历史进程,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欧化缘何而起?
其实这个问题很多研究者早已给出答案。赵德全、陈琳指出:“五四运动时期的翻译活动开创了汉语欧化进程的先河,自此,汉语欧化就没有停止过,而且翻译活动始终充当了该进程的原动力。”[注]赵德全,陈琳.翻译活动对汉语欧化的推动作用[J].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5).杨海明、周静认为,“对汉语的现代文艺体文本的建设和发展的贡献首先应归功于那些翻译家。”[注]杨海明,周静.汉语语法的动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0.
欧化起于翻译,但是它的进一步推广,却是由此而产生的进一步影响,即在汉语写作中的常态化与普遍化。倪海曙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近三十年来,在祖国语文的表达方式和方法上,起了重大影响的,是翻译作品和翻译文章……这是因为接触翻译文章和翻译作品,在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曾经是和将要是我们生活中的常事。”[注]倪海曙.语文点滴[M].北京:东方书店,1954:2.
我们认为,站在今天的立场,立足于已有的研究,梳理汉语欧化与欧化汉语的历史进程,应当把握两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充分关注中国历史上两次重要的大规模翻译活动及其对汉语的影响。
(一)汉魏以降的佛经翻译活动
把持续时间很长、规模宏大的佛教典籍翻译活动与汉语欧化联系起来,近年才有人明确提出。李春阳指出,“汉语受外来语的影响,并非自近代始。……今天所谓的‘欧化句式’,至少有一部分,能够在魏晋以来佛教的影响中找到根源,此为跨越千年考察汉语句式演变的线索……是汉语有史以来第一次的系统欧化。”[注]李春阳.汉语欧化的百年功过[J].社会科学论坛,2014,(12).
基于上文我们对欧化的“欧”所指范围的澄清与界定,即把它看作“外语”的等义词,我们比较认同李文的观点,以魏晋以降大规模翻译佛经以及由此而造成汉语自身多方面的变化为汉语欧化的起点。[注]汉代通西域虽然引进了一些外来词语,但是其数量与汉译佛典无法相比。另外,汉语词汇以外的方面在汉代是否受到其他民族语言的影响,至今难以确定,所以综合考量不宜把汉代看作欧化的起点。
以上观点看似标新立异,但是其实已经有一些相关的研究可以为之提供事实的支持,而正是由此,使得我们坚信这一观点的合理性。
李春阳引用梁启超对汉译佛经语言的考察,来证明自己的上述观点。梁氏共列出10个与汉语旧有形式不同的表现,并认为“凡此皆文章构造形式上划然辟一新国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十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36.。王力也指出佛教传入中国后,对汉语产生很大的影响,指出其中的重要一点是句法的严密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把要说的话尽可能概括起来,成为一个完整的结构”;另一方面是“化零为整,使许多零星的小句结合成为一个大句,使以前那种藕断丝连的语句变为一个有联系的整体”。[注]王力.汉语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80:477~478.
沈锡伦主要从魏晋以后句式的变化来讨论佛教文化的影响,归纳为4个方面:一是判断句普遍使用系词“是”来连接主宾语,句末不再出现“也”“耳”“焉”等语气词;二是“被”字句结构趋于复杂化;三是“把”字句的出现;四是动态助词的出现。[注]沈锡伦.从魏晋以后汉语句式的变化看佛教文化的影响[J].汉语学习,1989,(3).此外,孙昌武也列出了汉译佛典在句法上与传统语言表现形式的10个不同之处;[注]孙昌武.佛典与中国古典散文[J].文学遗产,1988,(4).而朱庆之则指出汉译佛典具有两个特点,其中第二个就是汉语和外语的混合。[注]朱庆之.佛教混合汉语初论[A].语言学论丛(第24辑)[C].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以上主要是就语法及语篇而言,此外还有佛教词语的借入,堪称汉语欧化表现最为充分的一个方面。据梁晓虹统计,近人丁福保所编《佛学大辞典》收有佛教语词近3万条,佛教词语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具体表现一是扩大了汉语基本词和根词,二是充实了汉语常用词汇,而由此也奠定了其在汉语词汇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注]梁晓虹.论佛教词语对汉语词汇宝库的扩充[J].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4).
汉译佛经对汉语词汇的影响当然不止于引进了大量的外来词语,此外还表现在与汉语固有词语发生交汇与交融,以及对整个词汇系统的影响。比如,佛教外来词的借用方法包括音译、意译和半音半意译,[注]张金星,姚清地.浅谈佛教输入对汉语的影响[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1994,(2).此外还有仿译,[注]朱庆之.佛教翻译中的仿译及其对汉语词汇的影响[A].中古近代汉语研究[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这些无疑巩固或奠定了后世汉语外来词语引进的基本模式。再如梁晓虹对汉语成语与佛教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注]梁晓虹.汉语成语与佛教文化[J].语言文字应用,1993,(1).此外还讨论了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词汇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注]梁晓虹.佛教词语的构成与汉语词汇的发展[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李仕春、艾红娟讨论了中古佛教类语料构词法的发展问题;[注]李仕春,艾红娟.从复音词数据看中古佛教类语料构词法的发展[J].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周文讨论了佛教传入与中古汉语新词新义的关系;[注]周文.论佛教传入与中古汉语新词新义的关系——以《撰集百缘经》为例[J].咸宁学院学报,2012,(7).董志翘论及佛教文化对中土取名命字的影响。[注]董志翘.佛教文化对中土取名命字的影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再如,王庆立足于中古汉语词汇和语法从多个角度对佛经翻译对汉语的影响进行了讨论,[注]王庆.佛经翻译对中古汉语词汇和语法的影响[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8.骆小所讨论了佛教文化对汉语修辞学的影响。[注]骆小所.略论佛教文化对汉语修辞学的影响[J].楚雄师专学报,2001,(2).
虽然汉译佛经对汉语的影响很大,但是在佛教典籍以外的其他文本(包括文言与白话)中却并未得到充分的表现,更未成为普遍的现象,因此虽属汉语欧化,但却并未像“五四”以后在民族共同语的范围内和层次上形成真正的欧化汉语,[注]这只是基于我们目前有限认识而得出的一个初步结论,这方面有巨大的研究空间。朱恒认为,从汉末至宋初的汉译佛经,重点放在了“名物不同”的处理上,少有语法结构的引入,未伤及汉语筋骨,汉语并未被“化”,可作一家之言。具体情况到底如何,有待于进一步对相关事实进行总结与归纳。参见朱恒.“现代汉语”辨析[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0,(10).而这恐怕也是一般的研究者均未把它纳入欧化及其研究范围的一个重要原因。[注]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欧化”是近代针对汉语与印欧语言的接触与交流以及由此而发生变化的一个概念,有确切的所指,这样“天然地”就把年代久远的“梵化”排除在外了。
(二)近代来华传教士的翻译活动
一般传统观念通常认为欧化始于“五四”时期,然而,近些年来,文学界、翻译学界以及史学界的一些学者却明确主张这一时间应提前。陈历明指出:“通过梳理传教士16世纪以来在中国传教时留下的各类历史文本,可以发现欧化白话并非起源于清末民初,而是明末清初,并与传教士的翻译和写作有着极深的渊源。……近代传教士在使用汉语翻译基督教经典时,已经多次尝试运用欧化白话文了,这种不乏欧化色彩的白话语言,并非中西语言之间的生搬硬套,而是经过中国本土传统的创造性吸收与转化,化欧为己。”[注]陈历明.欧化白话与传教士的事功[J].学术月刊,2013,(12).
在此之前,袁进曾经指出:“中国自身的古白话是何时开始转化为欧化的白话?这要归结为近代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是他们创作了最早的欧化白话文。”[注]袁进.重新审视欧化白话文的起源——试论近代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学的影响[J].文学评论,2007,(1).他还认为,从西方传教士到晚清白话文运动,再到五四白话文运动,构成了一条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展线索。[注]袁进.新文学的先驱——欧化白话文在近代的发生、演变和影响[M].上海:复旦大学出社,2014:377.
站在今天的立场上看,汉语的欧化首先是作为一种“实践”,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这才成为那些先行者们的“主张”,进而又形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规模“实践”,最终成为一个与百年汉语相生相伴、对其产生巨大实质性影响的重要因素,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后者的基本面貌与发展走向。
三、欧化文言
以往人们在讨论欧化问题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立足于白话,似乎只有白话才有欧化的问题。其实,欧化不仅限于白话,传统文言同样也有欧化的实践与具体表现,而这也应当作为梳理汉语欧化与欧化汉语历史进程的重要线索。朱恒指出,“清末大规模翻译西方文学、思想、宗教作品,大多以文言为语言底子。”[注]朱恒.“现代汉语”辨析[J].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10,(10).这种“以文言为语言底子”的翻译,既道出了欧化文言所由此产生的原因,同时也揭示了它的文体特点。
至于欧化文言的产生原因,胡适认为,晚清以来“这个危急的过渡时期,种种的需要使语言文字不能不朝着‘应用’的方向变去”,于是出现了以严复和林纾的翻译文章、谭嗣同和梁启超的议论文章、章炳麟的述学文章以及章士钊的政论文章为代表的“古文范围以内的革新运动”。[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A].胡适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23/1998:201.转引自倪伟.章士钊的“逻辑文”与欧化的古文的限度[J].文学评论,2018,(1).
正是基于对以上事实的认识,有人提出了“欧化文言”的概念,例如曹而云指出,“‘新文体’之‘新’只是相对于未改造的文言和传统白话而已,它是介于欧化文言与传统白话之间的混血语言。”[注]曹而云.白话文体与现代性——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为个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114.这里把“欧化文言”与“传统白话”相对使用。在欧化文言之前,早就有“欧化的古文”的同义说法,胡适就把以章士钊作品为代表的逻辑文称为“欧化的古文”。[注]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A].胡适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23/1998:367.
所以,我们在研究汉语欧化及欧化汉语、梳理其历史进程的时候,也应该而且必须把欧化文言纳入视野范围。
与欧化白话一样,欧化文言大致也经过了“翻译→汉语写作”这样两个发展阶段,以下分别举例说明。
(一)翻译中的欧化文言
大体而言,与欧化密切相关的翻译有两类,一类是宗教典籍的汉译,包括汉唐时期的佛教翻译以及早期来华传教士及相关人员的基督教翻译;另一类是中国本土人士或其所参与翻译的文化、科技及文学作品等。二者在时间上有先后之别,朱一凡对此有明确的说明:“(汉语欧化)最早产生于 19 世纪传教士翻译和书写的汉语文本当中,而后又出现在晚清民初浅近文言和白话的翻译作品中。”[注]朱一凡.现代汉语欧化研究:历史和现状[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2).总体而言,前者进行了以传统文言为资源的实践与探索,为后者提供了基本的“模板”与“范文”,而后者则在前者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把欧化文言推广到更大范围的汉语写作中。
以上讨论的汉译佛典,不消说自应归入翻译中的欧化文言一系,再如两部重要的宗教作品《天路历程》和《圣经》,也都是文言译本在前、白话译本在后。《天路历程》的译者宾威廉先于1853年翻译出版了文言译本,然后在1865年又翻译出版了官话译本;[注]焦良欣.《天路历程》与《圣经》平行翻译进程研究[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1,(2).《圣经》的第一部中文全译本于1823年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译成,用的是文言,[注]毛发生.马礼逊与《圣经》汉译[J].中国翻译,2004,(4).此后翻译出版的9部汉译本,也大致经过了一个文理(文言)、浅文理(浅近文言)和官话(白话)的发展过程。[注]任东升.圣经汉译文化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7:127.
赵黎明指出:“近代中国语言的欧化在鸦片战争前后就开始了,不过总体上说,这时语言的欧化还处于不甚自觉的实践层面,而这个实践活动首先是从以古朴、渊雅古文著称的魏源、严复、林纾的译述活动开始的。”[注]赵黎明.欧化·现代化·民族化——略论现代中国语文“欧化”问题的历史轨迹[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2).就近代以来而言,更具代表性以及对后来的现代汉语影响更大的,是本土人士的欧化文言翻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严复与林纾。康有为曾有“译才并世数严林”的诗句,[注]转引自马祖毅.翻译家严复[J].中国翻译,1981,(3).二人都坚持用古文翻译外国作品,并引以为自豪。[注]马祖毅.翻译家严复[J].中国翻译,1981,(3).
严复翻译了《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等大量西方哲学、政治著作,影响巨大,他“以典雅的古文译笔,阐释近代西方玄理,把外国新酿,包装在古色古香的旧酒瓶中”[注]汪荣祖.严复的翻译[J].中国文化,1994,(1).。
那么,是不是用古文翻译,就一定属于欧化文言?答案是肯定的,下边我们以林译小说为例进行说明。
林纾是清末民初著名翻译家及古文家,也是我国以古文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林译全用文言,但相比传统文言已有很大的变化,钱钟书对此做过相当全面的描述,[注]钱钟书.林纾的翻译[A].旧文四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以下再酌引其他人的两段话,以明其欧化文言的性质及特点:
林纾同样是桐城派的追随者,比严复更“古文”的古文家,但是他的古文在原作的冲击下出现了很多新的气象,古文的清规戒律消失了。他可以打磨纤艳的丽句,可以接纳大量的俗语白话,可以借用“东语(日本)新名词”,可以音译外来词。[注]周红民.严复翻译思想中的文章意识——一个被译界忽略的话题[J].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10,(4).
他(按指林纾)用较为自由的古文,采用俗语入文,松弛古文词句规范,这些做法实际上为古文吸收外来语言因素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他的译述小说中居然出现了外来新词、译音以及欧化的句子。[注]赵黎明.欧化·现代化·民族化——略论现代中国语文“欧化”问题的历史轨迹[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2).
我们曾以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翻译出版的《黑奴吁天录》为例,从词法与句法两个方面对林译的欧化特点进行了分析与说明,并进而指出其在语言学上的研究价值。[注]刁晏斌,刘兴忠.论林纾文言翻译文本的语言研究价值[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
除以上两家之外,“以文言为语言底子”的翻译还有很多。比如,王云霞、李寄认为,鲁迅的文言是“欧化”文言的重要一翼。《域外小说集》既是清末民初“文言复兴”运动的实绩,又是鲁迅现代汉语文学语言、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注]王云霞,李寄.《域外小说集》欧化标点符号的文体效果及语言史意义[J].上海翻译,2009,(4).宋声泉在谈到周作人所译《侠女奴》所用的语言形式时定位为“欧化色彩的古文”[注]宋声泉.《侠女奴》与周作人新体白话经验的生成[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5).;季淑凤指出,作家周瘦鹃在翻译域外小说时,最初多采用极“雅”的文言。[注]季淑凤.翻译与借鉴:论周瘦鹃中西合璧的短篇小说[J].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二)汉语写作中的欧化文言
谈到汉语写作中的欧化文言,无疑当首推影响巨大的以梁启超作品为代表的“新文体”,孙德金称之为“新体简易文言”[注]孙德金.现代汉语书面语中文言语法成分的界定问题[A].汉语书面语的历史与现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何九盈认为,新文体承前启后,是中国语文转向成绩最为显著的一种文体。梁氏在文体解放方面的功劳,与历史上唐宋古文运动相比,其功在韩愈欧阳修之上;与“五四”的白话文运动相比,其功可与陈独秀、胡适、鲁迅媲美。[注]何九盈.汉语三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24.新文体的最大特点,就是梁氏自己所说的,在文言的基础上“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具体而言,则是“吸取了生动活泼的民间俗语、谚谣、口语、俚语,并不时杂采新事物,新名词术语及外国语法,把渊雅古奥、晦涩高古的文言文改造得通俗易懂,使文章向言文一致的方向转化。”[注]梁景时.梁启超文章学思想及其“新民体”[J].学术交流,2007,(3).
梁氏之前,有魏源所著、于咸丰二年(1852)刊行于世的《海国图志》。马西尼对其语言特点作过以下简要介绍:“以普遍使用的双音节词为特征,在古式的语言中句末虚词实际已经没有了,在一般性的语言中不用深奥的词语,所以它的语言通俗易懂。这些特征后来成了19世纪末中国政论时文的特点。”[注]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32.
梁氏之后,汉语写作中的欧化典范当属以章士钊作品为代表的“逻辑文”。孟庆澍指出:“在民初散文影响较大的逻辑文中,句法欧化表现得最为明显,逻辑文的代表作家章士钊善用‘欧化的古文’,表达繁复的意思,高深的学理。”[注]孟庆澍.欧化的古文与文言的弹性——论“甲寅文体”兼及与新文学的关系[J].文艺理论研究,2012,(6).具体而言,它“不仅大量采用了新名词、新术语,而且还大胆地将西洋文法移用于古文的写作,从而创造了一些新的表述方式,达到了传统古文未曾企及的复杂而精密的程度”[注]倪伟.章士钊的“逻辑文”与欧化的古文的限度[J].文学评论,2018,(1).。
总之,以上无论是翻译还是汉语写作中的欧化文言,都属汉语欧化的具体尝试,由此而创造出数量巨大的欧化汉语文本,对此我们不仅应该赋予其指称形式,更应该把它放在汉语欧化的背景下以及进程中,来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
(三)欧化文言与欧化白话
关于欧化文言,我们此前作过一定程度的讨论,[注]刁晏斌.“文言史”及其研究刍议[J].民俗典籍文字研究,2010,(总七);刁晏斌.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2);刁晏斌.关于文言史的几个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1).并由此而形成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一般所说的欧化,均指欧化白话,而在此之前,曾经有一个欧化文言的阶段,由时间而言,汉语欧化以及欧化汉语大致经过了“欧化文言→欧化白话”的发展历程;
第二,欧化白话兴起后,欧化文言并未归于沉寂,二者之间还有一个平行甚至于交叉的阶段与过程;
第三,汉语欧化始于以文言为基底的尝试,由此而奠定了欧化的基本方法与模式,所以研究汉语欧化与欧化汉语,应当自此开始。
关于欧化文言与欧化白话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一些研究者已经有所涉及,曹而云指出,梁启超等人将改造过的文言、欧化的文言等各式的新文体运用到报刊文字的写作中,这些为“五四”白话文运动奠定了良好的社会接受基础,同时为白话的欧化及思想的现代化做好了社会的心理准备。[注]曹而云.白话文体与现代性——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为个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86.很显然,这里是把欧化文言作为欧化白话之前的一个阶段。持同样观点的还有王风,其以周氏兄弟为例指出:“在他们手里,对汉语书写语言的改造在文言时期就已经进行,因而进入白话时期,这种改造被照搬过来,或者可以说,改造过了的文言被‘转写’成白话。……周氏兄弟的白话确实已经到了‘最高限度’,这是通过一条特殊路径而达成的。在其书写系统内部,晚清民初的文言实践在文学革命时期被‘直译’为白话,并成为现代汉语书写语言的重要——或者说主要源头。”[注]王风.世运推移与文章兴替——中国近代文学论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67~168.
至于从欧化文言到欧化白话的发展原因,赵黎明在讨论新民体时指出,“在过去旧派人物看来,梁启超的新民体已经在欧化或东洋化路上走得太远了,但在五四人眼里,他的这一点却恰恰是他的不足,旧气未消、八股气太重,欧化还远未彻底,因此五四人必须肩负起这一重担。”[注]赵黎明.欧化·现代化·民族化——略论现代中国语文“欧化”问题的历史轨迹[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7,(2).要消除旧气与八股气,实现彻底的欧化,就要把以文言为基底改为以国语/官话/白话为基底,即建设欧化白话,而这也正是“五四”新文化建设者们的理想与实践。
(四)欧化文言与现代汉语
我们之所以在“回顾”性的文章中拿出很大的篇幅讨论欧化文言,其实正是着眼于其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密切关联。我们有一个基本的认识:作为“异质文言”的最重要种类之一,欧化文言是沟通古今的桥梁,借由这一桥梁,传统文言成功走进并最终融入现代白话,成为其重要来源之一。[注]刁晏斌.关于文言史的几个问题[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7,(1).
文言成分进入现代白话主要的方式有两种,一是间接进入,即经历了一般所说的“古代汉语→近代汉语→现代汉语”过程;二是直接进入,其中有相当部分即是由欧化文言到现代白话(现代汉语书面语)。有学者也直接或间接地指出了欧化文言与现代汉语之间的关系。孟庆澍认为,从康、梁开始,外国语言对汉语各个层面(字、词、句、段) 的渗透已经开始。梁启超的文章与当时占据文苑主流的古文有明显差异,所使用的句式、句法,和今天的现代书面语已经相去不远。到了章士钊,对西文文法的借鉴和使用变得更加自觉。[注]孟庆澍.欧化的古文与文言的弹性——论“甲寅文体”兼及与新文学的关系[J].文艺理论研究,2012,(6).夏晓虹、王风也认为,晚清的白话文不可能直接转变为现代白话文,只有经过“文界革命”和“新文体”大量引进新名词,现代思想才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现代白话文才能够超越自身缓慢的自然进化过程而加速实现。[注]夏晓虹,王风.文学语言与文章体式:从晚清到“五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5.
何九盈从另外的角度讨论了这个问题:“与其说是翻译文本(欧化名词,欧化语法)造成了现代汉语与古代汉语之间的‘断裂’,不如说是翻译文本弥补了这个‘断裂’。翻译文本在汉语的某些局部‘断裂’的环节上,用‘新名词’‘新文法’沟通了古今之间的联系。”[注]何九盈.汉语三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2007:75.这里所说的“翻译文本”自然包括欧化文言形式,而上述的“新名词”与“新文法”有许多就是直接来自欧化文言。就“新名词”而言,至今仍在大量使用的汉译佛教词语自不待言,此外还有大量的日源词,也是首先在新文体等欧化文言中使用的。马西尼就此指出:“由于日语的学习,日语著作的翻译,以及大批留日学生尤其是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的那些人士对1898年前不久在中国流行的日语词语的使用,从而促使汉语吸收了大量新的日语借词。”[注]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社,1997:128.所以,他认为,“19世纪后半叶用文言写的西学著作,20世纪初的短篇小说以及留日学生的许多政论著作,它们对‘新式国语化的白话’的形成都作出了贡献。”[注]马西尼.现代汉语词汇的形成——十九世纪汉语外来词研究[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社,1997:142.
再就“新文法”而言,大致也是如此,尹德翔说:“如果说倒退一百年,中国人做文章,少不了‘之乎者也亦焉哉’的话,现在做文章,则逃不脱‘因为所以但是既然那么然而当’了。受西洋句式影响而产生的表达方式,已经钙化在汉语的骨骼之内,成为一种不可或缺的支撑。正因如此,对今天大多数人来说,我们的语言已经欧化了,我们却没有知觉。”[注]尹德翔.关于汉语欧化与文学困惑的断想[J].文艺评论,1999,(2).这里所说的“因为、所以、但是、既然、那么、然而、当”等,都是首先用于欧化文言中的。[注]参见刁晏斌,刘兴忠.论林纾文言翻译文本的语言研究价值[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李聪.《万国公报》欧化文言研究[D].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关于欧化文言与现代汉语书面语之间的关系,我们只做过一些简单、初步的考察工作,总体而言,这方面的研究基本还属于空白,这是汉语欧化以及欧化汉语研究中极富挑战性的内容。
在我们构建的“新汉语史”中,文言史是一条重要的线索,而欧化文言既是文言发展一个阶段的实时样态,同时又是联结古今的桥梁,正是借由这一桥梁,大量的文言成分进入现代汉语,并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之一。[注]刁晏斌.传统汉语史的反思与新汉语史的建构[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2) .所以,欧化文言在汉语文言史乃至于汉语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与作用,而另一方面,则是在汉语欧化的历史进程中起过重要的作用,因此也应成为相关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
如前所述,汉语欧化已有长达近两千年的历史,而共同语层面的欧化汉语的形成也已历经百年,时至今日,欧化以及“化欧”的过程还在持续,而这也说明,“汉语欧化史”依然还在延伸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