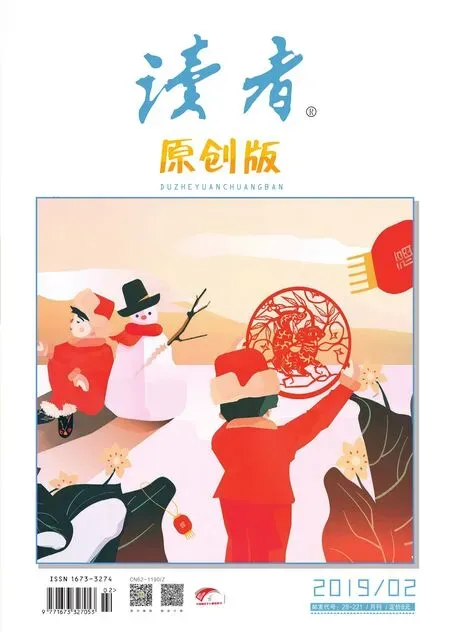向北而行
文|郑晓蔚
2004年,我从南京某大学毕业,入职当地一家都市报社,担任体育新闻版面责任编辑。
一
那时候,中国足球还在蚕食2002年韩日世界杯的剩余红利,“三千足记(足球记者)”是这个行业依然红火的“人证”。以龚晓跃、张晓舟等人为代表的知名球评人尽情玩弄着汉字拆组游戏,编织出闪亮迷人的金球式长句。
龚晓跃优雅地说:“我们传播,我们思索。我们无法忍受失真,我们绝不原谅无耻。仰望无益,俯视无情。所谓俯仰无愧天地的基础,乃是平等地交流、平静地观察、平和地论证。”
张晓舟诗意地说:“假如说马拉多纳是大地与河流的私生子,那么梅西就是一个足球工业的试管婴儿。马拉多纳属于天外边,而梅西则把天空变成他的玻璃房子。”
还有“足记”辛辣地说:“没有血性、没有观点还叫评论吗?从文体而言,那不应该叫‘议论文’,而应该叫‘说明文’。”
我多么想跟他们一样—说出荡气回肠的金句,写出令人拍案叫好的文本。
二
在南京报馆,我每天都妄图抖搂“一身才华”,在那些嗷嗷待哺的体育版面上尽显风流。用一位作家的话说就是,“我只是写”。
当年的报纸行情可不像如今。在智能手机尚未问世的报业暴利期,纸质报刊是公众接触一手信息的重要介质。为了便于市民就着早报吃早点,我们编辑成了夜间工作者。
我们是看不见日出的职业群体。在无数个黑夜,我编发了很多“靠谱”的体育新闻,制作了很多“不靠谱”的体育版面,在纸面上尽情挥洒着我的精与血。
每月发饷,我的银行卡里都会增加6000块。这对一个出身于小镇工薪阶层的孩子而言,宛若巨款。
工作有了,收入稳定,生活品质随之发生了改善,我也矫正了将“班尼路”和“真维斯”当名牌的认识。似乎一切都算是落定了。
父母开始为我张罗买房。我仍记得,同事2005年在南京市区购房的均价是4000块一平方米。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闲钱多的时候,曾借钱给同事买房。
三
我安逸地躺在金陵的温柔乡里。
直到2006年7月,《新京报》体育部主编、我的好友阿丁跟我说:“如果你有更大的野心,你应该来北京,来这里见世面。”
这一下戳中了我的心事。我渴望去北京“实现梦想”,也渴望去新京报社。毕竟,那是一个“一出生便风华正茂”的新闻梦工厂 。那里,还有我所敬重的报人。
我虽有此念,但又有所踟蹰。毕竟对我这个踏入社会仅两年的年轻人而言,由南京至北京是一次勇敢而折腾的迁徙。作为江苏人,南京让我感到踏实,因为跟在老家泰州的父母离得很近。而一旦投奔“皇城根儿”,不仅三个月的试用期意味着前途未卜,未必能够留下,我和父母之间也很难彼此照应。
一半是舒适区的温暾,一半是梦想的沸腾,我一时左右为难。
踌躇了两个多月,直到读到了杰克·凯鲁亚克《在路上》中的金句“我还年轻,我渴望上路”,我便不再犹豫。
那一年,我二十有四,我把自己投进了一节开往北京的夜奔绿皮车厢。
我承认,如果那时候高晓松创作出“生活不只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的歌词,那么我的决定会做得更容易一些。
四
北漂后,阿丁成了我的领导,也成了我的贵人。
他是性情中人,为“诱骗”我来京,经常在电话里向我描绘下夜班后大家消夜拼酒的温馨场景,结果为我接风当天,他就被我“放倒”了。他对部门兄弟们极尽关照,搭伙吃饭总是抢着埋单,单凭一腔子豪情义气,把部门各路人马拢在一块儿。
耳濡目染,我如今也成了一个热衷张罗饭局、偷摸去前台埋单的人。曾有人说,人过了30岁之后,朋友圈就会逐步固化,不再会有扩充。我如今越发品咂出这句话的深味,也就越发珍视纯粹的友情,对纯粹的饭局格外上心。
热爱写小说的阿丁就有一帮固定的饭局搭子—有他的至交、伯乐、前同事、现同事、前领导……而每次组局总会捎上我。
饭局中的诸位都是文化人。一入局中,便似被一个个精神粮仓包围。

这是一群可以催促你上紧发条不断进步的良师益友兼酒肉朋友。阿丁在酒桌上热衷于把话题往文学方向拐带,大家谈论的永远是卡夫卡、博尔赫斯、余华和王小波,这就逼你必须把这些大部头全部看完,才能够在酒桌上夺取话语权。于是,我只得买来《卡夫卡精选集》《博尔赫斯全集》《余华作品集》以及王小波的书,像偷看武功秘籍一般秉烛参详。阿丁和他的朋友们撒欢说一路,我尾随买一路。
当我对外界感知的越多,便自知懂得的太少。
也就是从那时起,我从一个生性自负的人,变成了一个懂得自重的人;从一个“始终保持谦卑”的人,变成了一个以“高调做事,低调做人”为信条的人。
感谢贵人的提携,感谢北京的厚重,感谢饭局的滋养,感谢自己的决定。
阿丁和体育部的兄弟们都“包藏”着出书的野心。他领衔的“横贯线写作四人组”最终都成了事儿,陆续有作品集在书店出售。其他部门同事常戏言,《新京报》最有文化的部门是体育部。
我也通过阿丁结识了一众朋友。但我从未想过,他们会在日后成为我新一轮的命中贵人。
五
落脚“皇城根儿”下三年,历经新闻制作工序的摔打,我的编辑素养和驾驭文字的功力均大为精进。若非阿丁的举荐提携,我的阅世情怀与精神修为恐怕都很难再上一个台阶。
我曾和阿丁发生过一次严重的“业务摩擦”。2007年西甲完结,我考虑用“贝克汉姆作别皇马”收尾,阿丁认为落点走偏,主张专注于“当场最佳球员”。我试着说服领导:“单就本场而言 ,你说得没错;但打量整个赛季,大腕贝克汉姆告别足球主流舞台绝对是最具新闻发酵力的赛末点,这应是共识。”
阿丁一时语塞,转身走了。而我之所以胆敢当面冲撞领导,是因为深知阿丁是一个好人,一个不屑给下属穿小鞋的忠厚兄长。
过了几日,阿丁在饭局上跟我说:“你说得在理。”
受阿丁的熏陶,我不再迷信权威,逐步拥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培育了理性质疑的精神。运用这些工具,我在洞悉真相的过程中获益颇深,而这是过往20年的正统教育所无法给予我的。
而北京的生活,让我变得谦卑、自信,内心强大。
六
当时间这把杀猪刀将我劈成“三张”,当我对这里高企的房价感到彷徨,当急切来京看望我的母亲说“一来北京脚就皲裂”,当我读到王朔《致女儿书》中直达内心的一句话,“既然不能永远在一起,那还不天天在一起吗”,我便决定—卷铺盖回家。
所以说,读书和交友一样,都是令人受益匪浅的事情,都可以为你的生活指引方向。
2009年,也就是北漂的第三年,我买了一张回程车票。
临别前,阿丁张罗了五轮酒局为我饯行,次次含泪称“真不送了”。然后,阿丁会和朋友们交流近期所看书目。
返迁南京时,我支付了不菲的书籍托运费。
七
我回到了此前的报社。
阔别南京千日,房价不复当年—当年我所中意的市区楼盘已被炒高至均价每平方米两万元。有人打趣说我这一趟出去亏了,北京的收入终究没能跑赢南京的房价。
我认真思考过这一问题,并未觉得后悔。是的,在物质层面,我蚀本了;但于精神世界,我赚翻了。我弥合了思考中的逻辑断链,弥补了教育中的历史欠账,让自己变成了一个精神世界更为丰富、强健的人。
而时任领导由于没能出去见过世面,精神世界的构建与格局均受局限,自然不能像前领导阿丁一样,包容异质思维与不同意见。
跟初入社会面对职场不公心生不忿不同,我对眼前所发生的一切有了更为强大的辨析能力,更容易洞悉人心的叵测与人性的幽暗,也更容易做到不以为意与自我消化。
在我看来,报社现实窘境促成了这一切。即便收入锐减,我依然不屑于投机与钻营。我必须像北京老话儿说的那样硬气活着:局气,有理有面儿—否则对不起北京三年豪义饭局的滋养。
八
昔年酒桌谈笑的那帮兄弟之中,有好几个站上红利风口,转行从事了公众号内容生产。
承蒙几个老兄弟看得起,我便有了一些打零工赚稿费的去处。是的,我依然“只是写”,这让我穿上了保有生活尊严的铠甲。
我想,如果不是因为在北漂中结识了这帮古道热肠的兄弟,我可能就会枯坐办公室为稻粱发愁。
北京朋友们的好意还不止于此。其中一位,捧着我的一摞作品进行了前期推荐;而我又捧着我的另一摞作品,顺利通过面试,进入一家薪资颇丰的体育传媒公司。
我发自内心地感恩在北京的那段工作经历,它始终在滋养我。
或许,生活就是一张定期存折:多年前为实现理想所付出的心血、落下的亏空,多年以后都会找补回来,加息奉还。
每当有实习生就是否北漂来征求我的意见,我都会立即为他推开一扇窗,鼓励他向北而行。因为,窗外是你的天空,身后便是你的江湖。
现在不明白不打紧,因为迟早有一天,你会如我一般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