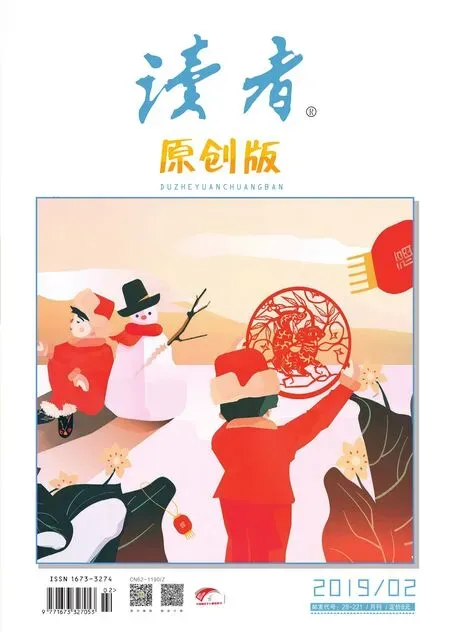陪伴大概如你所说
文|铜豌豆
“爸!”
“干吗?”
“陪我玩!”
“你要玩啥?”
这是近两年,我们之间最多的对话。
一
小区里常能见到一条流浪狗,白色毛皮带着棕色斑块,瘦,跑起来有点瘸。这条来路不明的狗是院子里的另一双眼睛,当我路过它的时候,总觉得它在盯着我,有时在夜里会莫名地想起它,于是有几次,我便把剩饭丢给了它。
我把这条狗说给你听,只不过是打发时间的几句话。然而有一天,我陪你在院子里玩,你突然指着那条狗问:“爸爸,你那天说的是不是这条狗?”“对啊!”
我猛地意识到,你记住了。
我迅速带你去门口的小超市买了几根火腿肠,找到那条正在低着头到处嗅的狗,我把肠衣剥开,一截一截掰开喂它。你起初不敢靠近它,站在旁边学我;后来直接用手拿着肠子喂到它嘴里。直到那条狗吃饱,头也不回地离去。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周五,在我接你放学的路上,你对我说:“爸,我们去找那条流浪狗吧。”
“为啥?”
“上次我喂它的时候,它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
二
两年前,我在双休日带你出去玩时,你常常要求我打车。后来我发现,一些不算长的路,你也要打车。有一次我对你说:“车不能经常打。”

“为什么?”
“因为我们要是经常打车,就不爱坐公交车了,而许多时候,我们还得坐公交车,还得走路。”
这之后,我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常带着你坐公交车。我让你自己看站牌,确定要坐的车次,算好需要坐几站能到达目的地。于是,你有了兴致。
当然,这个过程注定要反复。在车上人多的情况下,你也会说:“兰州要是有地铁就好了。”我知道,你有点不情愿了。我看着挤在车厢人堆里小小的你,说:“我也期待呀。”
2018年5月的一天,我陪你打完篮球,你突然肚子疼:“爸,我想回家大便。”我赶紧站在街边打车。你对我说:“公交车站就在跟前啊,只有一站路,咱们坐公交车吧。”
问题最终解决了。我问你:“刚才肚子疼的时候,为什么要坐公交车呢?”
你说:“我能忍得住。”
三
上学以后,你开始酷爱各种球类运动,篮球、足球、羽毛球、乒乓球,对哪一样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我带着你去体育馆,去大学校园,在小区院子里,一样一样地玩。你问我游戏规则,了解球星的情况,跟我一起看各种比赛。我们在去打球的路上说这些,在打球的时候说这些,在电视机前说这些。后来我发现,你的一些问题,我需要做功课了。
你说:“原来也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啊。”
“肯定啊,许多事情我都不知道,所以我要查资料。”
这次世界杯期间,你问我:“为什么阿根廷队有梅西还会输?”
我说:“足球是11个人的运动,除了球星,还要讲战术。”
“什么是战术?”
“战术就是参与比赛的方法。”
你说:“要是有11个梅西,阿根廷就天下无敌啦!”
“真有11个梅西,那梅西也就不是梅西了。”
“那他不是梅西又是谁?”
对啊,他到底是谁呢?我想了半天也没有结论。“臭宝,这个问题爸爸回答不了。”
你又问:“那谁能回答?”
四
那天我俩走在街上,我从报刊亭里买了一本《读者》(原创版)杂志,那一期用了我的一篇文章。我翻看的时候,你抢了过去。
你说:“爸,你写作文,他们给你钱不?”
“给啊。”
“那你还上班干吗?待在家里写作文就行了。”
“爸爸写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挣钱。”
“那是为了让许多人都认识你吗?”
毫无防备地与这个问题狭路相逢。无疑,作为一个“金线”以下的写作者,出名当然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有名人说过类似“写字给自己看,或者子女们想看也可以,但要是不开心,就一把火烧掉”的话,至少眼下,我还没有这样的境界。我想了想,对你说:“嗯,爸爸也希望让更多人知道我,还希望能从书店买到一本自己写的书。”
“那你就一直写吧。以后别人见到你的时候就会说:‘啊,原来你就是铜豌豆,你好呀,你好呀。’”
我看着你假装和人握手的样子,笑出了声。这是生命中难得的纯粹的笑,我必须以极大的声响来回应。
阳光下,你嘴角上扬,脸颊上淡淡的绒毛泛着光。
五
今年某一个周末的晚上,你递给我一个东西,用纸包着,叠成长方形,封面上还贴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发自内心的话”。
你交给我的时候认真地说:“爸,你拿到单位再看吧。”
到了单位,我揭掉表层的字条,在里面的封套上,你写了一个字“信”。你在“信”里这样写道:“爸,我不像从前那样不喜欢你了,希望你以后能跟我多玩玩,我也希望好多事你能答应我,能力范围外的就不要答应了,里面给你准备了回信纸。来自最爱你的宝。”
我回信时这样写道:“我要感谢你对爸爸的信任,上帝把你托付给我,我觉得肩上的责任沉甸甸的,我要做一个好爸爸,也需要你的帮助,你愿意帮助我吗?”
这“信”让我想起往昔的许多片段。比如,你在家撒欢儿的时候不小心撞到门上,我知道你疼,但并不急着安慰你。我问你:“需要我做点什么吗?”你眼里窝着泪水,一脸委屈地说:“不用。”然后,“哇”的一声哭了出来,我就抱住了你。
比如,你在学校闯了祸,我愤怒地赶往现场,但看到你的时候,我告诉自己还得克制。我把事情处理好,再来面对你的时候,又想,该怎么跟你说呢?我没想好,于是又去问你的老师,跟你妈妈商量,在我确定可以张口的时候,才会跟你说。我就是在这样的反复、这样的谨小慎微中,像没事人一样地面对你,直到几天后坐下来跟你认真地谈。那几天我心里说,你小子是来“练”我的吧,我还得当个好演员。
我承认,你也确实“练”到了我,我首先要像个爸爸那样活着,无论外面发生了什么,面对你的时候,就得像个爸爸。但我有时也不该像爸爸,我要真诚地对你,就必须丢掉“长辈”二字,让你知道高大、完美这些特质原本就与我无关。我有时也的确不那么像爸爸,心烦的时候会独自喝点酒,你问我为什么喝酒,我只好说,爸爸心里不舒服。你就沉默了,远远地跑开,一个人玩。我看着你,又会收起杯子。
文章开头的对话也会发生在电话里。每逢此时,我挂掉电话,常常想起岳飞在抗金前线收到的那十二道金牌;想到孙猴子在天界神游,神仙劝他赶紧回去吧,你师傅受难了;想到这一路最好没有红灯,阳光和煦,天空湛蓝,白云洁净,鸽子蹁跹,路边的杨树叶哗啦啦地响。
我就这样想着,打开家门,又听见你说:“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