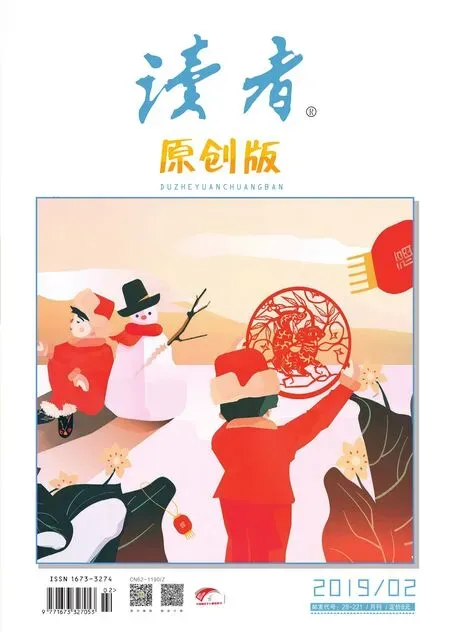菜 园
文|南在南方
程颢有诗:“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心地如常,从来不易。万物若手足,信手写来,多是神往之人、之事。

闲时喜欢看知堂老人的文字,有天晚上卧看他在《瓜豆集》自序里说瓜豆:“我这瓜豆就只是老老实实的瓜豆,如冬瓜、长豇豆之类是也。或者再自大一点称曰‘杜园瓜豆’,即杜园菜。吾乡茹三樵著《越言释》卷上有‘杜园’一条云:‘杜园者兔园也,兔亦作菟,而菟故为徒音,又讹而为杜。今越人一切蔬菜瓜蓏之属,出自园丁,不经市儿之手,则其价较增,谓之杜园菜,以其土膏露气真味尚存也……’”
“土膏露气真味尚存也”,这句平淡的话忽然惹得我不安起来,像是一只猫想要捉住自己的尾巴,分明是自己的,却捉不住—“杜园菜”也有,只是隔得太远。这样想时,不免又叹气,是以前有,现在也没有了,菜园还在,荒在老家。
农家菜园,鲜有常换地方的,比如我家里,那块菜园一直在那儿,离屋不远,能接近肥水,至于鸡,扎下篱笆就好了。
祖父喜欢兴菜园,一年四季都有绿色。就算大雪封山,雪来之前,他用苞谷秆盖在芫荽上,盖在菠菜上,菜依然鲜绿。就算不盖,豌豆苗顶着雪,那一抹娇滴滴的绿,也是惹眼。
菜园里的祖父是个园艺家,篱笆上一半爬豆角秧,一半是黄瓜秧,南瓜一定是种在地头,其余的,无非是茄子一行,辣子一行,给小青菜留地方,给蒜留地方。每一样菜蔬,他让它在哪儿就在哪儿,看上去疏朗清爽。祖父80多岁时还要去菜园,站不了,他坐在小板凳上;从前的锄头也拿不起了,打了一把小号的锄,像个玩具,他坐在菜园里锄草,可爱极了。
祖母在灶前灶后忙,偶尔唤我一声,去菜园摘个黄瓜,去掐点儿葱……像是一眨眼,我就办好回来了。那时祖父总要说一句:“可别摘瓜种啊。”瓜种是他选好的,一般都是藤上的头一个瓜,就像皇上的头一个娃儿,那是要当太子的。
《笑林》里说:“有人常食蔬茹,忽食羊肉,梦五藏神曰:‘羊踏菜园!’”后来人喜欢用“羊踏菜园”形容生活清苦。不过,那时没多少荤腥,有个菜园,有些菜蔬可吃,也是极大安慰。
很多年过去了,祖父祖母不在了。时间于我像拱猪,不知不觉把我拱在高处拱到远处,够不着一棵菜园里的白菜。
偶尔在书里看见菜园,总要失神。
南朝周颙在山里修佛,卫将军王俭问他吃啥,他说:“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文惠太子问他何菜好吃,他说:“春初早韭,秋末晚菘。”
这答的,好听,好看,好吃。早韭、晚菘都在菜园里头。杜甫念念不忘“夜雨剪春韭”,想来这春韭也是种在菜园里的,不然,那么细的叶子,又下雨,去哪儿剪呢?
种菜用不着快刀斩乱麻,缓缓地,甚至笨笨地,都是趣事。子贡南游湖北,准备回山西,经过陕西汉中,看见一个老头抱着瓮,给菜园浇水,一会儿一趟。可是瓮里的水,浇不了多少菜。他好奇啊,问老头为啥不用桔槔汲水浇呢,现成的啊。老头说,我不是不知道,我就是喜欢这样浇园咧。
这个古老的乡党老头是我喜欢的,这样的老头在老家至今还有。
虽然有铁牛犁地,快过耕牛,他不用,因为铁牛犁地不晓得深浅,而耕牛拉着唐时流传至今的曲辕犁,一步一步走过去,翻过的都是熟土;他不肯用除草剂,那些草啊,从古至今都长着,从古至今都是锄头在锄它,可是劈头盖脸给它洒农药,叫它服毒,这是辱没草咧。
每次听闻,都想要铺天盖地地赞美他,似乎也没有特别的意义,就是一份古意在。陶渊明写:“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他回家了,我还在城里挣扎。
布衣暖,菜根香,读书滋味长。
知堂先生说:“咬了菜根是否百事可做,我不能确说,但我觉得这是颇有意义的,第一可以食贫,第二可以习苦,而实在却也有清淡的滋味。”
我在阳台上弄了一个菜园,说是菜园,其实是个直径不到一米的大塑料盆,里头填满了土,放在支架上,工具只有一把孩子玩沙子的铲子。我在里头种过苦菊、小葱、紫苏,有一年栽了四株朝天椒,最后摘了一篮子红辣椒,收获感油然而生。
这不是我想要的菜园,总想着哪一天回老家,如同黄梅戏里唱的“你挑水来我浇园”。菜地在,锄头在,水井在,人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