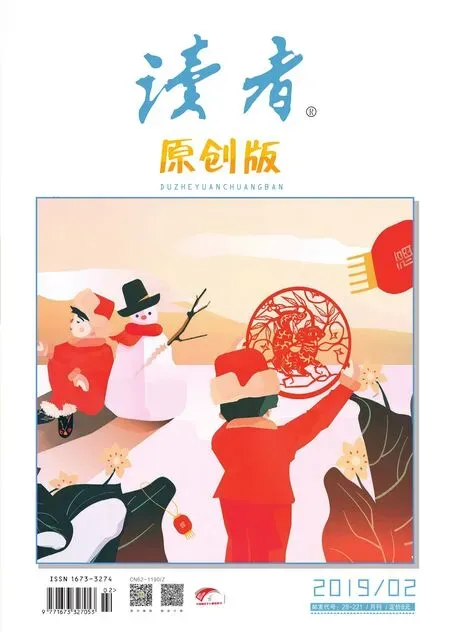恋人的围巾
文|沈书枝

12月初,南方的初雪普遍降临这天,北京也冷到了不可思议的程度,只是太冷、太干,雪依然毫无消息。丈夫罕见地在上班路上发来消息:“比昨天还冷,脸都吹没了!”
他又说:“从地铁到公司那200米冻死了……感觉回去好艰难。”
我说:“这个时候应该系我给你织的那条厚围巾,把脸遮住啊。”
“没找到,就看到挂着的毛茸茸的那条。”
我不说话,给他回了一个“微笑”的表情。
一
在我人生拥有的屈指可数的笨拙手工技能里,编织勉强算是其中一个。这得益于小时候村子里的女孩们对于编织的爱好,因为整体的风气,而使得它蔚然盛行。那是我们甚少有能力购买衣物的年代,冬天唯一的毛衣尚要依靠妈妈一辈的女性用竹针编织,整件细密洁净的元宝针,或是在胸口扭出美丽菱形花纹的麻花针,这样厚厚的一件新毛衣穿到身上的日子,足以使人珍惜整个冬天。出于这种生活的影响,女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织毛线了。(事实上,那时七八岁的小男孩喜欢织毛线的也不少,只不过等他们稍长大一点,大人们便开始认为这样的行为与他们的“男子气”不符,于是一概被制止、呵斥,从而停止了)我们小女孩没有钱买毛线,在妈妈的允许下,把家里旧得挂了大洞的毛衣拆掉,或是用大人织毛衣、毛裤剩下的一小团毛线,拿来练习。
首先的入门产品是一条裤带,因其简单、实用且易完成。然后是一双或一小只半截手套。反复量着手腕起针,其上逐渐加针,在大拇指高度留下分缝,织到手指半截长度时封针,再把拇指补上半截。这手套用以在灶屋里挂的洗脸毛巾冻成一块冰碴的寒天里写字,可以保持手掌的下半截不冷。但手指上半截仍露在空气里受冻,不久还是起了斑斑红点,很快肿起来,连成一片,在夜间被窝里发出奇异的痒与热,最终变成一大块破烂溃痈,疼痛不可触碰。再往后则是一条围巾—不在于其难度,实际上也并不难,而是在于织一条真正的长围巾至少需要两大团毛线,这对那时的我们来说过于奢侈,难以实现。织围巾还要用棒针,需要特地去买,不像织裤带或手套,只需用村道边折下来的短短的苦竹枝,用削铅笔的小刀把两头削尖即可。偶尔我们在家里偷4根竹筷,用小刀慢慢削细、刮圆,就是非常讲究的了。这种竹针假如用来织围巾,就太细,织的针太紧,既费时又费线,谁也没有那么多钱。
编织手艺在乡下最高水平的彰显,当然是穿的毛衣或毛裤,这是为家人操持的劳务,几乎无一例外地属于待婚或已婚女子的任务。一年四季空闲的日子,我们常能看到村子上的年轻女人手上拿着织到一半的毛衣,一边飞快地织着,一边与人聊天。特意从街上买来的洁净的新毛线,绕成整个手掌也难抓下的大毛线球,装在手肘上挎着的塑料袋中,每织几行,就回头扯出一大截。纤细的银色钢针也特地为织毛衣而买,在编织的漫长过程中,因为被反复捏了无数遍,钢针中间微微变形。婚姻给女性生命带来变化的负担,那时的我们也已经隐约窥见,只是那时我们还远不明白。
二
织围巾因此是少女的梦,是念初中的女孩子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类似为房间编织风铃与串珠帘。有一年我们流行用粉红色的毛线织一种带大洞的围巾,具体织法是每打一针,要把线在棒针上缠5圈,再打下一针,下一行再脱下线圈用针头交缠。这围巾据说织成后很是飘逸,但我们未经打磨过的棒针实在太涩,根本没法完成那样高难度的织法,最后无一人成功。
高中忙于功课,无暇他顾,而世界于此时发生了巨大改变:打工浪潮席卷整个乡村,青壮年们纷纷进入城市,不再完全遵循过去生活的轨迹;小商品市场的成衣大批出现在县城,买衣服和鞋变得极其普遍,而不是像从前那样,都由家中女人预备。我们的编织手艺从此停留在织手套的浅显程度,再也没有—也无必要—学会织毛衣、毛裤那样复杂的东西。
我的织围巾梦到大学时才得以实现。那时大学后门外有一条运河,河边靠着宿舍楼的一条街上,开着许多家卖廉价衣服的小店。当时淘宝网尚未兴起,除了偶尔专门去遥远的服装批发市场,女学生们平常多喜欢逛这样的小店,每到周末就结伴去看有没有新进的衣服,多半也只是看看。冬日,小店高处挂起店主自织或请人代织的围巾,兼卖棒针与各色毛线,毛线堆在角落,十分显眼。毛线花色众多,价亦不高,两团不过十几块钱。不知是谁第一个买回,很快在宿舍楼里掀起织围巾的风潮。我们特意去店里寻找喜欢的花色,买了棒针和线,观赏店主挂在高处织好的围巾,遇到好看的,就可以让店主教授织法。店主做成了生意,和颜悦色,一一指点,不惮其烦。我在那里学会了之前没织过的元宝针和一种织出来如同斜斜波浪的花纹。从没有打过毛线的,甚至可以让店主帮忙起针,教好最初几行再拿回去。
一时间,宿舍楼里到处是忙忙碌碌织围巾的身影。所为也无他,只是送男友而已。江南冬日寒冷,躲在宿舍的床上,打着打着忽然发现少针或多针了,只好往回拆几行,重新再打。奋斗了几天,人生第一条松松垮垮的编织品终于大功告成,第二天就围到本校的男朋友脖子上,勒令不许不戴,作为那个冬天彼此爱情甜蜜的见证。此间自有一种亲密,以围巾代替自己,如陶渊明《闲情赋》所写,“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
三
我没有男朋友,只能给自己织,先织一条蓝色的,一个人窝在上铺,除了上课、吃饭和睡一点儿觉,几乎不做别的事,一心一意织围巾,到第二天下午,一条围巾便织完了。心里犹不满足,又织了一条小小的红色的围巾,将毛线剪成段,攒成两个小球,系在围巾两端。这里的棒针比我们从前在乡下用的要光、要滑,也更细一点,打起来很方便,因此很快。也要到这时候,我才意识到从前织不出那种有洞的围巾,未必不是因为我们拥有的唯一一副棒针太大、太粗了。
有一天晚上,忘记是为什么,也许是临近期末吧,宿舍熄灯后,我独自搬了凳子到走廊上复习。出来却看到对面宿舍住的同班的一个女孩子也在走廊上,就着昏暗的灯光正跟一条围巾“斗争”。问她为何不睡觉,答曰,围巾只剩下最后一点,想今晚打完,明天好送给男朋友戴。这个女孩子的男朋友也是我们班的,我便不再多话,各自做自己的事。过了一会儿,她忽然发愁道:“唉,我不会封针,这围巾不知道怎么结束。”我起身去教了她,她还是不会,说:“要不你帮我封针吧?”
我心里一惊,不知她怎么会提出这样的建议。因她的那位男友,和她在一起以前,曾于饮酒后向我告白,在我因为过于羞涩的沉默之后,不久便和她成为情侣。我因之陷入长久的忧愁,而她对于这件事,大约并不是完全的一无所知。我无从拒绝,实际上也不愿拒绝,遂接过围巾帮她织了起来。看看毛线还剩下不少,又多织了几行,而后封针、断线,最后把毛线剪成一段一段,几根并作一绺,均匀间隔着系到两头,再剪成整齐的两排,作为装饰的流苏。一面做着这些,我一面微微心酸地想,他会不会知道这围巾最后的收尾工作乃是出自我手呢?大概不会知道吧。然而实际上,就是知道又如何呢?相比之下,还是不知道少一点尴尬。
四
后来,当我也有了自己的男友之后,冬天到来,我有没有为远方的他织过围巾呢?如今已记不清了。多半是织过的—当围巾越织越长,超过我的身高,甚至连举手也不能将其拉展时,想看看还要不要继续往下织,我便在上铺将围巾从床沿上垂下去,看它已有多长—记忆里依稀有着这样模糊的画面,只是记不真。对方仿佛也很珍视,当时的感动自不必说,临毕业时,也将那条围巾从学校带了回去。
此后我便与织围巾大业告别,再也没有织的兴致。直到七八年后,与丈夫初识不久,相隔两地,我在阴冷多雨的南方的冬日,听他抱怨北方室外寒风割人面颊,于是蠢蠢欲动,去毛线店买了线与棒针,赶出一条深蓝色围巾奉赠。因为太久没有织过,我早已忘记当初喜欢的波浪形花纹是什么织法,开头拆拆打打几次,才终于织出。这条围巾在之后几年里,我从未见他戴过,从我们租的一个房子搬到另一个房子,它始终躺在衣柜某一角落。偶尔问他要不要戴,答地铁太热,不需要这样厚的围巾。这样的话大约也是实情。有时我想,是毛线刺脖子,戴了不舒服吗?我试了一下,柔软得很。直至今年夏天,收拾衣柜时又看见衣架上挂着的那条围巾,因为年深日久,已变得黯淡陈旧。心下愤懑,扯下来丢进一堆要扔的几年没穿的旧衣服里。要扔时,到底没有忍住,向他抱怨几句,于是又被劈手夺下,然后—然后又随手丢在什么地方。几天后,我叹一口气,把它叠起来,深深塞进衣柜里。在这个丈夫又一次抱怨室外寒冷的冬天,我会再把它从某个我也已忘记的角落里找出来吗?我想可能是不会了。多快啊,时间已到寒冷的冬天,“你大概已停止了分赠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