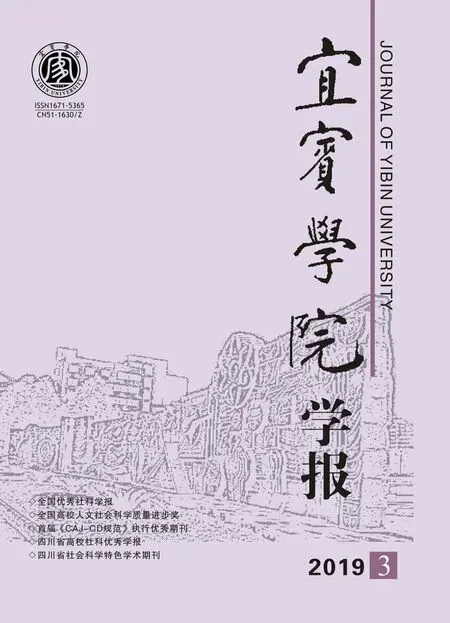论专利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的独立诉权
——基于诉权约定的取得
汤贞友
(西南政法大学 民商法学院, 重庆 401120)
专利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的诉权问题已有不少学者探索,主流意见认为:我国现行法中当然许可被许可人无诉权,但应授予其诉权。但根据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及司法实践,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经专利权人授权可享有诉权,但非独立诉权,故真正应探索的问题为:其是否能享有独立诉权。此外,大多观点只停留在浅层面上,仅从授予当然许可被许可人诉权的现实性和必要性出发,未能从深层次上考虑到授予其诉权可能产生的理论冲突。现实性所催生的需要,必须从实践回归理论的视野,对其进行解释,从而提供正当性的支撑。如果当然许可被许可人享有独立诉权,随之而来的是诉权行使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如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的诉讼地位、诉讼利益的归属等,其独立诉权在专利侵权诉讼中如何与现有诉讼体系相协调必须深入研究。
根据《专利法》第60条,未经专利权人许可,实施其专利,引起纠纷的,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何为“利害关系人”?被许可人是否属于“利害关系人”?最高法院对专利法诉前停止侵犯专利权行为的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利害关系人”只能是独占被许可人和排他被许可人,不包括普通被许可人。同时根据最新的知识产权行为保全的司法解释,被许可人申请诉前责令停止侵害知识产权行为的,普通被许可人经权利人明确授权以自己的名义起诉的,可以单独提出申请。①该司法解释虽只就诉前禁令请求权作了规定,但实质上已明确经专利权人授权普通被许可人可享有起诉权。因为诉前禁令是一种临时措施,为起诉前的行为保全而非终局性裁定,申请人必须在采取行为保全措施后30日内起诉,②如普通被许可人没有随后的起诉权而权利人亦不起诉,那该诉前禁令将毫无意义。而且,司法实践早已普遍承认,专利普通被许可人经授权可取得诉权,该司法解释仅为将实践经验上升为纸面规定而已。③
最高法院此举实质上统一了知识产权普通被许可人的诉权可经授权取得的做法,结束之前仅在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以及植物新品种权的司法解释中规定该做法的局面,④避免了是否能在专利法和著作权法中类推适用所带来的困扰。⑤然而,虽然专利普通被许可人经权利人授权可享有诉权,但其没有独立的诉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简称《送审稿》)第83条规定,当然许可期间,专利权人不得就该专利给予独占或排他许可。故专利当然许可被许可人仅享有普通许可。按照我国目前的法律,专利当然许可一旦建立,在该制度之下,所有被许可人均无独立诉权,如专利权人不授权被许可人起诉,亦不主动提起诉讼制止侵权行为,被许可人将无法救济自己的权利。况且,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侵权现象严重,是否有必要授予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独立的诉权?如其享有独立诉权,应如何与现有的诉讼体系相协调?
一、专利当然许可被许可人享有独立诉权的必要性
专利当然许可被许可人能否享有独立诉权,应从我国实际出发,植根我国社会现实与司法实践的土壤,结合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的特殊性,分析其必要性。我国知识产权侵权现象高发,当然许可之下,被许可人均无独立诉权,为了在专利权人怠于制止侵权行为之时有必要的救济手段,应授予其独立诉权。
(一)知识产权侵权现象高发
2016年,人民法院共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比上一年上升24.82%,新收专利案件同比上升6.46%。[1]2017年,案件数量持续增长,人民法院新收知识产权民事一审案件上升幅度达到47.24%。[2]知识产权案件数量不断增加,这种现象一方面固然体现了知识产权人逐渐增强的维权意识;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识产权严重的侵权现象。正所谓“乱世用重典”,知识产权侵权现象多发,权利人应有更多的手段,以更便捷的方式维权。当然许可被许可人虽不是专利权人,但侵权行为与其利益息息相关,其应有救济手段去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而这种手段就是诉权。如果高发的侵权乱象得不到制止,容易纵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这对当然许可被许可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因为侵权者能以更低的成本与被许可人竞争,被许可人在市场竞争中无疑处于劣势,进而导致专利实施者丧失对取得合法当然许可的热情,影响当然许可制度的有效运作。因此,不授予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独立诉权可能会滋生更多的侵权行为,不利于维护被许可人的利益以及良好的市场竞争秩序。
(二)专利权人不作为的救济
较一般的普通被许可人,当然许可被许可人更为特殊。在专利当然许可中,被许可人均为普通被许可人,除专利权人外,如无专利权人授权,所有被许可人都不能提起诉讼禁止侵权行为。面对第三人的侵权,当专利权人怠于行使诉权亦不授权被许可人起诉之时,当然许可被许可人将无法有效维护自己的利益。虽然在一般的专利许可中,亦存在仅有普通被许可人的情形,但是现实中,因许可使用费更高的原因专利权人更多地给予独占或排他许可,市场上仅仅存在普通被许可人的情况较少。更为重要的是,当然许可之下,专利权人的目的多为获取专利许可费,容易出现怠于行使诉权的行为。因为专利权人申请当然许可后,其专利的垄断性减弱,被许可人数量大幅增加,竞争变得尤为激烈,专利实施的获利减少。故专利权人本身可能并不实施专利,市场上的侵权行为对其利益影响不大。同时考虑到高昂的诉讼成本和专利被无效宣告的诉讼风险,专利权人对制止侵权行为可能并不热衷,容易出现“拿钱不办事”的现象。此外,当然许可作为一个开放许可,可能出现众多被许可人,有时难分真假,如果侵犯当然许可专利权的行为无法得到及时的制止,容易产生更普遍的侵权者非法逐利的现象。在专利权人怠于禁止侵权之时,被许可人的独立诉权无疑可以打破这一困境。
二、授予专利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独立诉权的理论障碍与突破
现有研究多停留于授予当然许可被许可人诉权的现实性需要,或局限于比较法视角,两者固然重要,但仍要从深层次理论寻求“所以然”。因此,必须从理论上寻找授予其诉权的正当性依据。直接利益受损理论认为,直接利益受损者都能享有诉权,普通被许可人在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中利益受损,可享有诉权,但该理论与普通许可实施权所具的受限排他性产生了冲突,无法为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的诉权提供有力的支撑,必须为其寻求新的理论支持,实现理论体系的自洽性和内在和谐。
(一)直接利益受损与普通被许可人有限排他性的理论冲突
首先,从诉权理论分析,对发生的民事纠纷具有利益或者权利保护的必要性,是形成诉权的主体适格条件,诉权的享有者是该案件的利害关系人。[3]258有学者认为,被许可人的利益至少包括取得市场竞争优势和取得经济利益,这种利益在第三人的侵权中必然遭受了损害,直接利益受损者理论上都是直接利害关系人。[4]专利权具有垄断性,被许可人通过取得该专利的合法授权,独占或者分享专利权人专利权的专有性,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取得准入的优势,其他人因无合法许可而不得进入该领域,或擅自实施成为侵权者而被要求停止侵害。因此,被许可人能运用垄断性和先发优势实施专利占领市场,从而获取利润。当普通被许可人的实施范围内发生了侵权行为,普通被许可人的市场份额将受到侵占,可预期的利润随之减少,普通被许可人因侵权行为而利益受损。从这个方面来看,仅享有普通许可的当然许可被许可人也是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是诉权的主体适格当事人。
但是直接利益受损理论忽视了重要的一点,专利普通许可实施权仅具受限的排他性,不能禁止他人实施专利。在普通许可使用的情况下,被许可人仅依合同取得知识产权使用权,其无权禁止权利所有人对该知识产权进行再许可,亦无权禁止他人使用该知识产权。[5]即普通被许可人只有积极的实施权,而不具有消极的禁止权,不具备支配权的属性。在Overman Cushion Tire Co. v.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一案中,法官认为第三人的专利侵权行为并不会给普通被许可人造成法律上的损害,正如侵入他人土地者不会对该土地仅具有非排他性通行权的地役权人造成损害一样,因此,很明显普通被许可人在专利侵权诉讼中既不能独自起诉,也不能与专利权人共同起诉。⑥因为普通被许可人的专利实施权的排他性是有限的,甚至根本无排他性,其具有容忍的义务,侵权实施者与合法许可使用者对其影响并无二致。只要无权通行者不妨碍非排他性地役权人的通行,并不会对该地役权人造成损害。同理,专利侵权者即使在普通被许可人范围内未经授权实施专利,也不会对其造成法律上的损失,只要不妨碍该普通被许可人的积极实施权。从这个角度看,普通被许可人根本就没有直接利益的损失,难称之为利害关系人,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的独立诉权也不能获得正当性的来源。
但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确有制止侵权行为的需要,因侵权者无需代价即可实施专利,实质上利用了不正当的手段获取了竞争优势和利益,使获得合法授权的被许可人反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市场利益受损,属于一种不正当竞争的行为。但是,其并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具体规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恐难为现行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即使由该法规制,也存在如何衡量被许可人实际损失的难题。然而,这种现象对当然许可被许可人明显是不公平的,其在这种情况下有可保护的利益。况且,较之于一般的普通许可人,在当然许可之下,被许可人更容易面临许可人怠于制止侵权者的困境,因而,其应享有独立诉权作为救济手段。为此必须要寻求新的路径,运用新的理论去解释当然许可被许可人诉权的正当性,实现法律体系内在的和谐统一。
(二)诉权约定理论
被许可人的许可实施权为准物权抑或债权,多有争论。被许可人的许可实施权根据许可合同产生,因而多被视为债权。如有观点以许可实施权不符合物权法定、一物一权原则为由,主张其应属于债权[6];亦或认为现行专利法反对专利权期限受限、地域受限的转让,况且许可内容为当事人意定,无法产生对世权效力的独占实施权,因而许可实施权为债权。[7]但债权为相对权,把许可实施权视为债权的做法无法解释独占、排他许可突破债权相对性具有排他性的现象,也无法有效解决普通被许可人的利益保护问题。针对这种不足,有观点主张引入德国的二元知识产权体系,即分为完全知识产权和定限知识产权,许可是定限知识产权,类似于用益物权,因而把许可视为准物权。[8]但是,实际上普通被许可人并无消极禁止权,不能禁止他人实施专利,许可一律属于准物权,反而使得普通许可实施权亦产生了对世效力,明显不符合普通许可实施权的性质。更有学者反对目前授予独占被许可人诉权的做法,认为独占被许可人可通过违约之诉维护自身利益,无需授予诉权[7],但专利权人是否有这种积极作为制止侵权行为的义务存疑,而且恪守传统债法的相对性只能起诉许可合同相对方专利权人的做法,缺乏灵活性,专利权人必然会另诉侵权者,或法院将其追加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将诉讼法律关系复杂化。更为重要的是,违约之诉排除了独占被许可人取得惩罚性赔偿的可能,该方案也无益于解决保护普通被许可人利益的问题。
局限于认定许可实施权的性质可能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因其可能并不属于债权或物权,因为知识产权相对于传统民法自有其独特性。更为合理的做法是跳出界定许可实施权性质的框架,将被许可人的许可实施权视为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对独占垄断权的约定,进而建立诉权约定制度。将专利许可的内容及诉讼权利交由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意思自治决定,因为知识产权许可中许可人和被许可人的利益关系是十分复杂的,合同主体才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9]其次,知识产权的客体为信息,[10]10信息具有共享性,知识产权可为多人共享和行使,这是知识产权区别于其它民事权利,特别是物权的又一重要特征。[11]13与物权人对物的控制通过占有方式不同,专利权人对信息的控制依靠法律授予的独占垄断权,又基于信息所具的共享性与知识产权可为多人行使,专利权人可将专利的独占垄断权授予多人行使,甚至限制自己的使用权能,授权他人独占或排他性地行使,但该专利权的控制权能仍属于专利权人;物权的保护对象亦可与物权人分离,但必须通过直接占有与间接占有的方式实现。专利权的控制权能比传统物权的占有具有更强的支配力、管控力。基于这种特性,专利权人有更多的意志自由与选择自由,即使专利权人将独占垄断权以不同的形式授权多人行使,亦不会引起公众对权利主体的识别困难与经济秩序的混乱。
然而,这种多样性的许可使用方式,也产生了具有不同排他性权利的被许可人,对这些对象的保护存在很大的难度。面对许可所产生的复杂性,在遵守传统民法基本框架的基础上,保护方式有所创新亦属必然之举。不妨将这种复杂性,交还民事主体本身的自由意志去解决,合同当事人不仅可以自主协商许可中的权利义务,亦包括作为实体权利保障的诉权。
但诉权能否约定?诉权为私权抑或私权,多有争议,历来有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又或二元诉权论,此处无意探讨诉权的性质。对于诉权,其与实体权利或实体法上的利益密切相关,任何人均无法否认。诉权本身就包含实体权利的内容,不可能在诉权外再创设实体上的诉权。[3]256诉权不可能脱离实体权利而独立存在,实体权利亦需诉权的庇护。根据意思自治原则,在一般情况下权利人能通过合同约定将自己的实体权利转让给他人,正如法谚所云“无救济则无权利”,权利的救济作为权利本身的“从物”当然也随之一起转让给受让人。[11]13实体权利转移,作为救济手段的诉权自然也应随之转移。诉权转移实不应为忧虑之事,真正应警惕的是诉权的单独转移,诉权基于实体权利而存在,脱离实体法的诉权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单独约定诉权的转让而无实体权利转移的行为才应为禁止之事。在《上海百货》杂志社诉富昱特公司等著作权纠纷一案中,法院认为,普通被许可人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具有实体权利的基础,并不构成纯粹的诉权转让。⑦专利当然许可之下,被许可人虽仅享有普通许可,但仍具实体权利,并不存在实体法与诉权分离的危险。
诉权约定制度,国外早已有之,我国普通许可中亦出现大量诉权约定的司法实践。英国《专利法》规定,除非有事先的“特别协商”,当然许可被许可人可请求专利权人提起诉讼制止专利侵权行为。[12]560再如,《法国知识产权法典》中:独占被许可人在“合同无相反约定”且专利人在催告后未提起诉讼的,可提起诉讼。[13]181我国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司法解释也规定,普通被许可人经专利权人明确授权,可以提起诉讼。⑧普通被许可人诉权经许可合同约定取得早已成为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乃至知识产权法的常态,只要普通被许可人经专利权人明确授权,法院直接认定其为适格的诉讼主体。⑨我国虽未在独占、排他许可中全面建立诉权约定制度,但诉权可经约定取得已不成问题。
(三)怠于起诉视为专利权人默示授予诉权
当然许可被许可人通过专利权人授权固然可以取得诉权,但非独立的诉权,如专利权人不授予其诉权亦不自行起诉,被许可人仍难免陷入困境。必须在诉权约定的基础上,赋予当然许可被许可人催告权以打破困局。英国《专利法》规定,当然许可之下,被许可人可请求专利权人制止侵权行为,经催告后两个月不作为,被许可人能以自己的名义起诉。[12]560根据法国《知识产权法典》,面对专利侵权,专利权人被催告后未提起诉讼的,被许可人可起诉。[13]181英、法两国在授予当然许可被许可人诉权方面规定类似,均在专利权人怠于起诉之时,赋予被许可人催告权。唯一的差别在于,英国设置了两个月的催告期限,而法国没有明确该期限。两国在授予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独立诉权的路径为我们提供了可供本土化的方案,当然许可之下,面对第三人的专利侵权,被许可人有权催告专利权人提起诉讼,在催告后的合理期限,如专利权人不起诉,被许可人可自行起诉。催告后的合理期限,仍有待研究,但我国现阶段知识产权侵权严重,该期限应比英国的2个月更短。这套方案完全可以运用诉权约定理论解释其正当性。
专利权人作为权利所有者,较之当然许可被许可人,其诉权具有优先性。但是,当面对专利侵权行为的持续进行,逐渐挤占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的市场空间,专利权人依然选择不作为的方式,对侵权行为置之不理,被许可人有合理的理由怀疑其怠于行使诉权,甚至放弃诉权以及诉讼利益。基于理性的考虑,为维护自身利益,当然许可被许可人应及时催告督促专利权人制止专利侵权行为,排除专利权人对侵权行为处于不知情的状态。催告后的合理期限,专利权人明确表示拒绝起诉或依然采取沉默不作为的方式放纵侵权行为,这种怠于起诉的行为有充分的理由可被视为专利权人对自身诉权及诉讼利益的放弃。
《民法总则》第135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其他形式。意思表示的外部要素即表示行为,该行为依其表示方式之不同,有明示与默示之别。[14]193书面形式及口头形式是一种明示的意思表示,默示行为可归入其他形式。专利权人被催告后明确拒绝起诉,可认为其以明示的方式作出放弃此次诉权及诉讼利益的意思表示;如在催告后合理的期限内无任何起诉的准备,应视其通过默示行为作出此等意思表示。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的催告实质是一个明示的意思表示,如专利权人不行使诉权,该权利即让渡由当然许可被许可人行使。专利权人如果被催告后明示拒绝起诉或沉默不作为,不仅视为对其此次诉权及诉讼利益的放弃,更以默示方式授权当然许可被许可人提起诉讼,在催告期限结束后,当然许可被许可人即可自行提起诉讼。
三、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独立诉权在专利侵权诉讼中的协调
面对侵权行为,当然许可被许可人履行催告义务后,如专利权人依然怠于行使诉权,亦不授权被许可人起诉,其可自行起诉制止侵权行为。当然许可被许可人取得独立诉权仅为开端,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其独立诉权与现有诉讼体系的协调。在侵权诉讼中,被许可人居于何种诉讼地位?是否应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
(一)专利权人与被许可人的诉讼地位
当然许可之下,对于专利权人提起的诉讼,《法国知识产权法典》规定,所有被许可人可参加专利权人提起的侵权诉讼,以获得应有的损害赔偿。[13]181但是,如果专利权人主动提起诉讼,当然许可被许可人原则上并无诉权,除非经过专利权人明确授权,可以与专利权人共同提起诉讼。实践中,如被许可人与专利权人共同提起诉讼,法院一般视其得到了专利权人的默示授权。⑩此外,当然许可之下,被许可人众多,何者能提起诉讼?应为发出催告的被许可人,因发出催告的被许可人才能得到专利权人的默示授权。在多位当然许可被许可人催告的情况下,所有被许可人应以共同原告起诉。起诉的当然许可被许可人是否有利害关系,应由法院判定。在催告期满前,如当然许可被许可人与专利权人达成了协议,双方约定共同起诉或授权被许可人单独起诉,共同分配损害赔偿的利益,如不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法院也应允许,因其符合合同自由原则。
英国《专利法》规定,当然许可之下,在被许可人提起的诉讼中,可将专利权人列为被告或抗辩人。[12]560被许可人可将专利权人列为被告,可能是基于专利权人不作为的违约责任,但这与我国理论设计不一致。专利权人在催告后不提起诉讼,即意味着其放弃了诉权,根据诉讼法“一事不再理”原则,其不能以相同的事实与理由再次起诉,故专利权人无权参与此次的诉讼,但面对新的侵权行为,专利权人依然有权提起诉讼。
(二)被许可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
当然许可被许可人不是专利权的所有者,在侵权诉讼中,其是否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有观点认为,普通被许可人享有的许可使用权具有受限的排他性,并不能对抗对其造成侵害的第三人,故不享有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诉讼利益归属应与实体权利保持一致,因此损害赔偿请求权应归属作为权利所有人的专利权人。[5]司法实践中,有法院认定获得授权起诉的普通被许可人属任意诉讼担当人,为专利权人的利益而起诉。专利普通被许可人只享有对专利权的积极实施权,不能排除他人使用,无其他财产收益权,故本身并不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但是,在当然许可之下,如专利权人在被催告后的限定期限内不起诉,不仅视为诉权及诉讼利益的放弃,而且其此次诉权及诉讼利益将让渡于被许可人。因此,该被许可人不仅有权起诉,而且亦获得了损害赔偿请求权。
损害赔偿数额应该如何计算?应以专利权人的利益受损作为计算标准,因为一方面在催告后的合理期间结束前,当然许可被许可人作为普通被许可人仅享有积极的实施权,无消极禁止权,无权禁止第三人的侵权行为,此时其在专利法上并无直接的利益损失。其虽可主张因第三人的不正当竞争而利益受损,但该利益难以计算,而此处主张利用专利法进行规制;另一方面,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的诉权是基于专利权人的诉权放弃及默示授权,被许可人的诉讼利益来源于专利权人对其利益的放弃,因而自然应以专利权人的标准计算。同时,法院在判定最终的损害赔偿数额时,宜直接以合理许可费方法计算损害赔偿数额。理由有二:一是专利当然许可声明中包含确定的许可费,且该许可费无差别地适用于所有的被许可人,容易满足合理许可费方法的适用条件;二是专利权人的主要目的多在于获取专利许可费,本身可能并不实施专利,因此专利权人的利益受损也多表现为许可使用费的减少。此外,现实中专利权人可能会与当然许可被许可人之间达成诉讼利益的分配协议,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两者的损害赔偿分配约定应有效。此举有利于鼓励合同主体对诉讼利益及诉讼风险作明确的事先约定,可减少诉讼的纠纷,也为当事人以更为规范的方式订立许可合同提供指导。
结语
探索授予当然许可被许可人独立诉权的意义不仅仅局限在专利当然许可制度之内,更是对全面建立知识产权的诉权约定制度有开拓性的意义,对解决普通被许可人的保护困境亦有助益。信息的共享性以及知识产权的可由多人行使的特点,使得知识产权的许可表现出比传统物权更为复杂的特点,知识产权仍在不断发展变化中,面对这种复杂性与潜在的变化,最好的方法是回归民事主体的自由意志,诉权约定制度基于民事主体的意思自治,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知识产权许可制度中有很强的生命力。
注释:
①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2条。
②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查知识产权纠纷行为保全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6条。
③ 参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2012)石民五初字第00371号民事判决书,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粤民终1093号民事判决书,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1民初156号民事判决书。
④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犯植物新品种权纠纷案件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1条。
⑤ 虽著作权法、专利法的司法解释未规定普通被许可的诉权可经授权取得,但司法实践早已将该做法扩展至两者普通许可中,视作知识产权的统一规定。但又因两者的司法解释对此未作规定,被告往往以其作为抗辩理由,主张诉讼主体不适格,耗费权利人的举证精力和不必要的质证时间,导致法院无法集中审理实质的争议焦点,增加法官的论证说理的难度。如富昱特公司与华中师范出版社等的作品复制权纠纷中,被告即以“当事人不能设立诉讼信托或讨债信托”为由主张原告主体不适格,参见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16)粤73民终373号民事判决书。
⑥ Overman Cushion Tire Co. v. Goodyear Tire & Rubber Co., 59 F.2d 998, 14 USPQ 104 (2d Cir.), cert. denied, 287 U.S. 651, 53 S.Ct. 97, 77 L.Ed. 562 (1932)。
⑦ 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4)沪一中民五(知)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
⑧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不正当竞争民事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5条。
⑨ 参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33号民事判决书, 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4)湘高法民三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书, 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申字第54号民事判决书,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4)高民终字第278号民事判决书,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闽民终322号民事判决书。
⑩ 注册商标武汉地区的普通被许可人,与商标权人同时提起诉讼,可以视为获得了商标权人的授权。参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鄂武汉中知初字第01854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