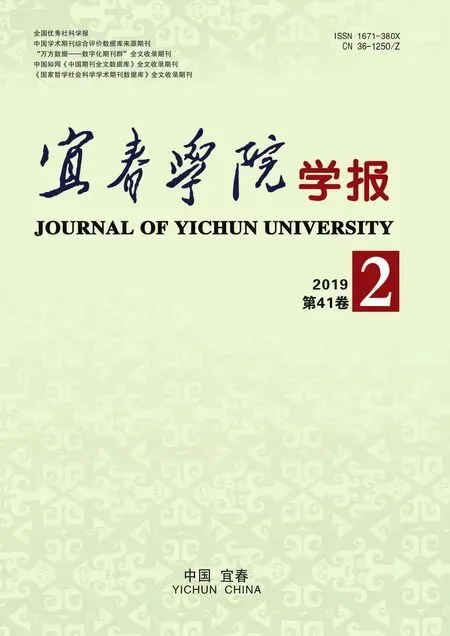吕本中“少时戏作”说探微
王开春
(合肥师范学院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江西诗社宗派图》虽为吕本中所作,但因为吕氏文集散逸,现存有关《宗派图》内容的记载全部来自南宋人的转述。有关《宗派图》的种种议论也发生在南宋。韩驹、徐俯、胡仔、孙觌、曾慥、范季随、曾季狸等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对其发表过意见,十分热闹。不过,吕本中本人却屡次声称此图为“少时戏作”、“少时率意而作”,甚至说“甚悔其作”。对这份受到广泛关注的《江西宗派图》,他似乎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吕氏的这些说法,时人和后来论者都已经注意到。但很多人仅仅从考察《宗派图》作年的角度来认识这些材料。部分学者注意探寻吕氏这些说法背后的原因,并从不同角度做了一些解释。但是笔者感到吕氏这一说法背后尚有待发之覆,故草成此文,力图在说明吕氏本人态度的基础上,对背后的原因做进一步解读。
一、群体意识的消散与吕本中的回避态度
吕本中的说法,见于范季随《陵阳室中语》和曾季狸的《艇斋诗话》:
家父尝具饭,招公(韩驹)与吕十一郎中昆仲。吕郎中先至,过仆书室,取 案间书读,乃《江西宗派图》也。吕云:“安得此书?切勿示人,乃少时戏作耳。”他日公前道此语。公曰:“居仁却如此说!”《宗派图》本作一卷,连书诸人姓字。后丰城邑官开石,遂如禅门宗派,高下分为数等。初不尔也。[1](P704)
东莱作《江西宗派图》,本无诠次,后人妄以为有高下,非也。予尝见东莱自言少时率意而作,不知流传人间,甚悔其作也。然予观其序,论古今诗文,其说至矣尽矣,不可以有加矣。其图则真非有诠次,若有诠次,则不应如此紊乱,兼亦有漏落。如四洪兄弟皆得山谷句法,而龟父不预,何邪?[2](P296)
在这些记载中,他轻描淡写地将其称做“少时戏作”,是“率意”之作。甚至表示“甚悔其作”,要求人们不要传播它(“切勿示人”)。吕氏这个说法,即关系到《宗派图》作年之确定,又和《宗派图》在当时巨大的影响形成反差,值得仔细推敲。
对于这种说法,范季随和曾季狸是接受的。范季随在引用吕氏之言后,又介绍了韩驹的态度:“居仁却如此说”。看来韩驹对此说法颇不以为然。紧接着,范季随写道:“《宗派图》本作一卷,连书诸人姓字。后丰城邑官开石,遂如禅门宗派,高下分为数等。初不尔也。”(见前引)他认为《宗派图》中的诸人名单,本无次序。将其认作有高下之别的,是一种误解。此言紧接韩驹的话后,有替吕氏解释的意味。大概他认为韩驹之不满,在于名单中的次序问题,而他则接受了吕氏“少时戏作”的说法,认为其“连书诸人姓字”,并无区分高下之意。
曾季狸的态度稍显复杂。他在介绍吕氏所说之后,推许《宗派图》的序文为不刊之论,似乎不大理解吕氏“率意”、“甚悔”之说。接着,他说:“其图则真非有诠次,若有诠次,则不应如此紊乱,兼亦有漏落。”(见前引)看来,他认为吕氏所说,主要是针对名单而发的。认为这份“紊乱”而“有漏落”的名单,确实不够严谨,宜乎吕氏有悔其作。
现代学者有的接受吕氏的说法,并对其进行解释。如胡明认为吕本中后悔的是自己在入选名单上的轻率,没有根据“某种统一的标准和明确的条件,经过一番严峻的甄别”[3](P119)。伍晓蔓认为吕氏作《江西宗派图》无疑大有深意,而其“甚悔少作”的说法,除了“著录未必精当”的原因外,还应是针对自己在序言中对黄庭坚和宗派诗人过高的推许而发的[4](P15-16)。
也有人对吕本中的表态表示非议。如周煇说:“是皆党东莱者创此说以盖时论,非本语也。”[5](P354)认为这是别人的捏造。应该说,范、曾两人不约而同的记载,是不能轻易否定的。但是周辉认为这种说法的出现,是为了应对“时论”,即有关宗派图的种种非议,却启人遐想。即,吕氏此说,是出于不得以,不能全盘接受。现代学者黄宝华就认为:“(吕本中的表白)是为了对付舆论,淡化此图有意闪烁其辞。”[6](P68)孙鲲也据范季随所记,推测吕本中“少时戏作”的说法,是一种搪塞之辞。[7](P41)不过,与周煇不同的是,黄、孙之论有一个大前提,即他们认同吴曾《能改斋漫录》之说,认为《宗派图》作于绍兴三年,而非北宋末年。
综上,接受吕氏之说的,大都注意其“戏作”的表述,并解释其原因。否定吕氏之说的,则主要是指出“少时”之说不准确,并推测其原因。可见,要深入阐释“少时之说”,势必涉及《宗派图》的作年问题。
笔者拟从诗人群体的形成与消散这个角度,分析吕氏此说的背景,并对《宗派图》作年的判定,提供一个新角度。
《宗派图》的写就,是吕本中对当时客观存在的一个诗人群体的主观把握。所以,我们既要关注这一群体形成的历史过程,更要关注吕本中本人态度的变化。关于前者,伍晓蔓通过史料耙梳,清晰地勾勒了这一群体在北宋末年形成的过程,认为“在大观末、政和初,形成了一个以江西诗人为主体,却又超越狭隘的地缘概念,诗宗山谷,更以元祐文化承传多元性为特色的全国性诗人群体[4](P162)。在这一群体中,吕本中无疑是核心成员,而据王兆鹏的研究,吕氏也特具一种领袖意识。他不但自觉为群体的一员,更自视为领袖。王先生引用《师友杂记》中的两条材料:
徐俯师川,少豪逸出众,江西诸人皆从服焉。崇宁初,见予所作诗,大相称赏,以为尽出江西诸人右也。其乐善过实如此。
政和初,无逸至京师省试,尝寄予书,极相推重,以为当今之世,主海内文盟者,惟吾弟一人而已。又语外弟赵才仲云:“以居仁诗似老杜、山谷,非也。杜诗自是杜诗,黄诗自是黄诗,居仁诗自是居仁诗也。”
王先生认为吕本中在这些记录中是标榜自己的诗坛盟主地位。[8](P45)其实《紫薇诗话》中还有一条记录,也与此相关:
曾元嗣续政和间尝作十友诗,盖谓颜平仲岐、关止叔沼、饶德操节、高秀实茂华、韩子苍驹及余诸人共十人也。其称余诗云:“吕家三相盛天朝,流泽于今有凤毛。世业中微谁料理?却收才具入风骚。”[9](P365)
从中也不难看出吕本中自鸣得意的态度。而上述材料所提示的时间点,也与伍晓蔓所说的大观末、政和初合拍。可以说,无论从诗人群体内部联系的紧密程度,还是就吕本中个人的群体意识来说,《宗派图》出现的条件都已经成熟。
到了南宋初年,情况却有了新的变化。论者都注意到南宋初年政治文化环境更为宽松,元祐学术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最高统治者也对黄庭坚的艺术表现出喜爱之情,认为这一背景有利于、甚至促成了《宗派图》的出现。不过,如果我们从这个宏观背景移开目光,去关注江西诗人群体的变化,特别是吕本中本人心态的变化,就会发现,在宏观大背景下,江西群体这个小气候的情形,也许并不那么令人激动。
江西诗人群体的形成,是与特定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关的,这已为学者们指出。沈松勤说:“江西诗派首先是政治上的党争分野而成的一个文人群体,其次才是文学意义上的一个诗歌流派。”[10](P187)在元祐学术受到压抑的时刻,诗派中人大都处于“蛰伏”的状态,可是在徽宗统治的末年以及靖康年间,随着政治矛盾的变化,诗派中人在文行出处方面的差异凸显了出来。
首先是吕本中自己的境遇有了变化。论者都注意到《宗派图》出自吕本中之手,是和吕氏特殊的身份地位有关的。简言之,吕氏一门在北宋,无论政事、学术都颇为显赫。吕本中以吕希哲长孙的身份,在当时旧党圈子里,交游很广,颇有人望,自己也很自负。由他出面,写下一份以同情元祐学术为基色的诗人名单,是很正常,也是吕氏足以自信的。
但是南渡以后,情况却有改变。吕本中之父吕好问,在靖康之变中,参与谋划了迎立张邦昌的行动。也许确是事出权变,有不得已之苦衷。但这毕竟是政治上一个阴影。当时舆论对此也颇有非议。庄绰《鸡肋编》卷上有这样一则记载:
“北敌焉知鼎重轻,指踪原是汉公卿。襄阳只有庞居士,受禅碑中无姓名”。人云吕本中居仁诗也。而其父好问,在围城中预请立张邦昌之人,遂为伪楚门下侍郎。有无名子大书此绝于常山县驿,云吕本中骂厥顽之作云。[11](P32)
陈善《扪虱新话》也记载了此事,文字稍有不同。孙觌在给曾慥《与曾端伯书》中,还提到徐俯痛骂吕好问之事:
靖康末,吕舜图(引者按:当作“徒”)作中宪,居仁遇师川于宝梵佛舍,极口诟骂其翁于广坐中,居仁俯首不敢出一语,故于《宗派》贬之于祖可、如璧之下。[12](159册P55)
在公开场合,当着吕本中的面,痛责吕好问,确实有点过火。不过,徐俯当时在围城中,颇以气节自重。据说,在张邦昌被拥立之时,他偏偏将自己的女婢命名为“昌奴”,“遇朝士至,即呼前驱使之”[13](P82)。以此衡之,孙觌所说之事,当非虚构。
这种舆论不可能不给吕本中造成压力。他也不止一次婉转地为自己父亲辩解:
胡康侯与唐恕处厚,皆推明东莱公围城中所立,为可以激劝后世。或以为不然者,二公必与之辨论。处厚笃实自守君子也。崇宁初,与其弟倶为湖南知县,新法行,皆弃官去,终宣和世不出仕宦。东莱公之薨,处厚为挽诗三章云。[14](P21)
政和间,陈莹中自通徙江州,过扬州,见荥阳公及东莱公,甚款。莹中与东莱公从容论天下事,云:如瓘止可为公家欧除尔,若是经纶事业,须是公始得。及后靖康围城之变,苏嘉景谟太博老矣,谓家叔舜察云:「舜徒乃能做许大事业,吾辈做他底不得也。」然是时纷纷之论亦不一,景谟亦不顾也。[14](P27)
这两则材料中,吕本中没有直接出面,而是借胡安国、唐恕、陈瓘、苏谟等人之口,为自己父亲开脱。暗示吕好问不惜名节而行实事,是过人之举。同时,这些材料中也透露出当时“纷纷之论亦不一”的环境。从吕本中这些回护之举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的尴尬和不安。
同时,在北宋末年混乱的政局中,在靖康之变的大动荡中,名列《宗派图》中的一些人,也不免随波逐流,甚至作出有亏节操的事来。
韩驹早年曾从陈瓘、苏辙等人游,在政和年间和吕本中等人有“十友”之称,已见前述。宣和年间,他在仕途上突飞猛进。韦海英引用《三朝北盟会编》中的记载:“蔡攸,字居安,京之长子也,长于柔佞谄谀,自幼出入宫禁,……累加宣和殿学士,深结内侍以固宠,荐引门人刘僴、韩驹、吴敏等数十人,皆以禁从。”认为韩驹仕途上的进步可能得力于蔡攸。[15](P160)
此外,胡寅在为翁彦深所作的《神道碑》中也曾提到:“少监蜀人韩其姓者,方以词采受梁(师成)知,犹难于越公(翁彦国)而进,乃以日食不奏出公,翌日韩即召试知制诰。”[12](190册P222)此条材料提及的“少监蜀人韩其姓者”,当是韩驹。关于翁彦国因日食事而外任一事,《神道碑》有详细记载:“八月朔日食,太史前一夕以奏,且移省知,而执移者误送著作局,及期百官赴明堂待班,朔,车驾不出,始知日食。公坐是降两官,守济南。”[12](190册P221)按《宋史》徽宗本纪,宣和五年八月朔有日食。则上述事件发生在宣和五年,而据韦海英《江西诗派诸家考论》,韩驹宣和五年任秘书少监,次年迁中书舍人[15](P162-163),正与《神道碑》中所谓“韩其姓者”履历相同。可见,在胡寅看来,韩驹的晋升正是走了梁师成的门路。绍兴五年,当韩驹去世之时,朝廷制词也说:“韩驹早以词艺,跻于禁严。附丽非人,饭蔬奚怨。”所谓“附丽非人”,是十分严苛的评语了。据李心传说,韩驹家人所编的韩氏年谱,特别将这一句换掉,可见他们自己也是有愧于心的。[15](P175-176)
和韩驹一样,卷入北宋末年官场政治的还有高荷,据叶梦得说他“晚为童贯客,得兰州通判以死。既不为时论所与,其诗亦不复传云”[16](P419)。洪炎,宣和间曾为秘书少监,据说也和蔡絛有关。[15](P83)而洪刍则在靖康之乱中,未能保持气节,为金人搜刮金银,甚至诱纳宫人,并于建炎元年被流放沙门岛。[15](P78)
在经过历史风雨的洗礼之后,无论是陷入非议的韩驹、洪炎、洪刍,或者背上包袱的吕本中,乃至一贯傲气的徐俯,他们之间,可能都很难再有北宋年间那种同气相应、同声相求的群体感了。再进一步设想,此时的吕本中可能也难以自信地写下、面对这份名单了吧。
综上,笔者以为,立足于诗派中人文行出处变化,关注南宋初年江西诗人群体意识的消散,不仅可以进一步解释吕本中“少时戏作”说背后的原因,还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宗派图》的创作时间,不应在南宋初年。
二、无意于文的提出与吕本中的诗学反思
以上的讨论主要围绕江西诗人群体进行,认为南渡前后部分群体成员文行出处的变化,导致了群体意识的瓦解,也使得吕本中面对这份名单时,不免感到尴尬,因此以“少时戏作”加以回避。
我们知道《宗派图》除了一份名单外,还有一份序言。其文主要见于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和赵彦卫《云麓漫钞》的引述。两者都是概略引用,文字略有不同,但主要内容一致。从序文中可以看到,吕本中梳理了古文和诗歌演变的轨迹。这其实是吕氏从个人视角出发,对文学史的一种构建。其实质,正如朱刚所指出的那样,是以一种“复古”的观念来构画诗歌的发展历史,认为宋诗“成”于黄庭坚,并确立了由黄氏及其后学组成的宗派,作为当代诗坛正宗正派的地位。[17](P403)或者如伍晓蔓所说,是构建了一个“诗统”,定江西宗派为诗歌的正派。[4](P427-429)
有学者说“《宗派图序》推尊黄庭坚到绍续诗统的高度,又给予《宗派图》诗人以‘尽发千古之秘’的过高评价,无乃过激。二十年后作者一度悔其少作”[4](P15),认为南渡后吕本中对少年之论感到不满,才有“甚悔其作”的表态。从吕本中诗学思想的变化入手,解释他“少时戏作”“甚悔其作”的说法,有其合理性。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序文中所表示的意见,是否是思考不成熟的一时戏言?二要明了吕氏南渡后诗学思想的新思考是什么?
首先,吕本中虽然声明《宗派图》是“戏作”、“率意之作”,但是《宗派图序》中表现出的“诗统”观,决非率意之言。因为吕本中在另外一个场合,也说过类似的话。政和三年四月,吕本中和其外弟赵承国在楚州宝应相见。后者向其请教“为学之道”,吕本中便“录予之闻于先生长者本末告之,随其所问,信笔便书,不复铨次。”①这便是记载在《耆旧续闻》中的“与赵承国帖”。其中说到:
自古以来语文章之妙,广备众体,出奇无穷者,唯东坡一人;极风雅之变,尽比兴之体,包括众作,本以新意者,唯豫章一人:此二者,当永以为法。[18](P54)
这段话,分别推举苏轼、黄庭坚为文章和诗歌的极致。特别是有关黄庭坚的一段话,和《江西宗派图序》中的相关论说高度一致:
元和以后至国朝,歌诗之作或传者,多依效旧文,未尽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扬反复,尽兼众体。[19](P327)
其推尊黄氏是非常明显的。当然,吕本中也没有忽视苏轼的诗歌成就,在“与赵承国帖”中,他说:
学诗须熟看老杜、苏、黄,亦先见体式,然后遍考他诗,自然工夫度越过人。[18](P52)
立起杜甫、苏轼、黄庭坚作为标本。不过,在排序上,将黄氏放在最后,颇有一点以黄氏为结穴所在的味道。这不是笔者的猜测,因为紧挨着这段话的,就是这样一段话:
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18](P52)
苏轼一样排在最后。结合上面分别推举苏、黄两人为文章、诗歌代表的那段话,可以看到这两段话中人名的排列,是有其深意的。②
可见,“与赵承国帖”和《江西宗派图·序文》的观点相近,皆以苏黄为诗歌之范式,尤以黄庭坚为宋诗发展之结穴。在不同的场合,反复表述同一观点,应该说,这是吕本中严肃思考的结果,决非率意。
所以,吕本中所谓“少时率意”、“甚悔其作”的表述,如果是针对序文而发的,就只能是其诗学思想有了新的变化。
其次,关于吕氏南渡后的诗学思想,很方便的一个说法是吕氏在南宋初认识到江西诗派的弊端,并以“活法”论,或者引苏济黄,来进行纠偏。不过,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活法”之说,是吕氏由来已久的看法。而苏黄并提,在政和年间的“与赵承国帖”中就已经形成了。所以吕氏南渡后诗学思考的新变,还需梳理。
由于吕本中文集散逸,我们今天据以了解吕氏诗学主张的,主要是《师友杂志》《紫薇诗话》《童蒙诗训》等文献。这些文献,虽然成书于南渡之后③,但其中所记多有北宋时言行。所以在引用其中言论的时候,应该注意结合《夏均父诗集序》《与曾吉甫论诗帖》等作于绍兴初年的文献,做统一的观察。
笔者注意到吕氏《童蒙诗训》中的一则材料:
《吕氏童蒙训》云: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有近质野处,如《封主簿亲事不合诗》之类是也;东坡诗有汗漫处,鲁直诗有太尖新太巧处,皆不可不知。东坡诗如‘成都画手开十眉’,‘楚山固多猿,青者黠而寿’,皆穷极思致,出新意于法度,表前贤所未到;然学者专力于此,则亦失古人作诗之意。[19](P328)
这段材料中值得注意的不是吕本中对苏黄短处的揭示,而是指出“然学者专力于此,则亦失古人作诗之意”。吕氏在苏黄之外,指出另一个参照对象“古人作诗之意”。无独有偶,在《夏均父诗集序》中,吕氏在盛赞黄庭坚诗歌“黄鲁直首变前作之弊,而后学者知所趋向,毕精尽知,左规右矩,庶几至于变化不测,而远与古人比,盖皆由此道(引者按:即活法)入也”之后,接着说:“然予区区浅末之论,皆汉魏以来有意于文者之法,而非无意于文者之法也。”[12](329册P107)可见,他对自己“顷岁”热衷讨论活法的观点,进行了反思。指出学诗者还应重视那些“无意于文者之法”。从吕本中的表述看,苏黄诗歌的成就,是新变出奇,出新意于法度,但总归还是“有意于文”,而此时吕氏更希望学者关注古人作诗之意,即“无意于文之法”。
在同样作于绍兴初年的《与曾吉甫论诗第二帖》中,吕本中说:
欲波澜之阔去,须于规摹令大,涵养吾气而后可。规摹既大,波澜自阔,少加治择,功已倍于古矣。……曹子建《七哀诗》之类,宏大深远,非复作诗者所能及,此盖未始有意于言语之间也。近世江西之学者,虽左规右矩,不遗余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头,不能更进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12](174册P80)
所谓“未始有意于言语之间”正是前文所说的“无意于文者之法”的最好解释。在吕氏看来,曹植《七哀诗》宏大深远,非在言语文辞上的功力。总之,吕氏此前论诗,无论是强调体式,还是主张活法,大都是就“文字”、“法度”来论诗。而这两篇文献中表现出的观点,就颇有点跳出诗外的味道了。
可以说,“无意于文者之法”、“未始有意于言语之间”等说法的提出,正是对“活法”说的超越,把关注的焦点从诗歌文本移开,转向创作主体的修养和诗歌的社会作用。
相对来说,江西后学在学习前人时,往往单纯注目于句法的传习。所以,南渡后,吕氏在推尊黄氏及其后学的同时,自然也不忘提醒后来的学者注意“古人作诗之意”,希望他们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这样,他自然可能对《宗派图序》中过于绝对的论断,感到不满意了。而促使吕本中产生这样新思考的原因,大概是年龄增长,更历时事的人生经历,特别是靖康之变带来的冲击。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因为自身文学思想的变化,加上《宗派图》成员文行出处的差异,使得吕本中对《宗派图》采取了回避态度。但是,《宗派图》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学群体的勾勒是客观的,其构建的“诗统”,也代表了中国诗歌史中最有成绩的那部分。因此,《宗派图》才能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而由其派生出来的“江西诗派”也成为文学史中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概念。
实际上,南渡以后,包括后世关于《宗派图》的各种讨论,大都将其视作一个单纯的文学群体,或者是诗歌流派。而吕本中本人,也不拒绝在这个意义上使用“江西诸派”这个说法:“学退之不至:李翱、皇甫湜,然翱、湜之文足以窥测作文用方处。近世欲学诗,则莫若先考江西诸派。”[20]597这里的“江西诸派”,应当是指《宗派图》中所勾勒出的那个受到黄氏诗风影响的诗人群体。
而这种视野下的《宗派图》,在一定意义上已经脱去了具体的历史场景,变成一个纯粹的文学概念了。这种抽离,对外人来说,是很容易的,甚至是自然而然的。但是对这一历史过程的亲历者——吕本中——而言,这也许并不容易。
注释:
①陈鹄《耆旧续闻》卷二,《全宋笔记》第六编,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五册第54页。参见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第396-397对此帖的考证。
②关于这份书帖的意义,朱刚《唐宋“古文运动”与士大夫文学》有专节论述,本文受其启发良多。不过,朱刚认为吕本中在此帖中将“苏黄”并提,避免了独尊黄氏的不妥当做法。本文观点有所不同。
③《师友杂志》提到绍兴元年吕好问去世之事,自当成于此后。《童蒙诗训》后人是从《吕氏童蒙训》中摘出论诗之语而成的。考《吕氏童蒙训》卷下称徽宗为“上皇”。《紫微诗话》中有“元符末,上皇践阼”之说,亦称徽宗为上皇。则两书当作于靖康之后,最有可能在建炎、绍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