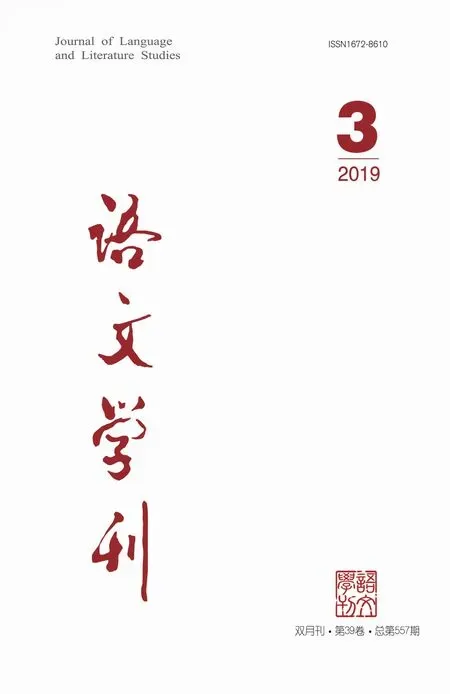危机时刻下的现代性寓言
——以《悬荡》《封锁》《南方高速》为例
○周启星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北京 102488)
小说创作的基本事件是须先创造一个时空,将一个本不存在的时空由小说家的脑海中置入文本,而文本经由阅读,又从一种文字时空转化为读者的心理时空以及社会的舆论时空,一个被虚构的时空就此脱胎而出,成为现实及可以共同谈论的存在场域。而这一虚构的时空并非寻常所为,实乃深有所寓。小说家拈取生活中的片段,进行时空异化处理之后,将这些片段抽象为一则寓言,寄寓一定的哲学思考甚至精神追求。寓言这种文学体裁可追溯于先秦战国时期,《庄子》运用得最为熟稔,如《齐物论》中“庄周梦蝶”,《逍遥游》中的“鲲鹏”等故事都是古代文学中引人深思的寓言。对于寓言的形式功能,成玄英疏中有言:“庄子寓言以畅玄理,故寄景与罔两,明于独化之义。”[1]59征引一个意象或一则故事,来畅叙幽妙玄通之理,言明个体生命之悟,是其旨要。寓言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往往以其奇诡的想象力,丰富的夸张、比兴等修辞手法引人入胜。文中之事迥异于日常现实,情节更为新奇刺激,矛盾冲突更加激烈,使人在凡俗生活之外发出惊叹,以造成可以思考作者所要传达“玄理”的契机。然而,现代小说中的寓言,却往往异于此道。现代小说中的寓言,不同于《庄子》中奇诡怪谲,汪洋恣肆想象力,而是在逼近现实中引人深思,在捕捉庸常时发出喟叹。
短篇小说作为体裁而言,无疑是寓言的上选,寓言的写作目的不在于塑造人物,或铺叙情节,也不在于记录历史,或抒发情感,而在于畅玄理,明大义。短篇小说精细的情节设计,剪影式的人物造影,片段时空的凝眸,正适合用以寄寓一则玄理。本文选取张大春的《悬荡》、张爱玲的《封锁》以及阿根廷作家胡里奥·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这三部短篇小说进行比较考察,其作者及创作时期都相距甚远毫无关联,而情节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相似的情境设置之下所要传达的寄寓却又有着微妙的差别。
一、危机时刻下封闭空间的背景创设
张大春自述,在十八岁时“花了大约半年的时间,琢磨了一部题目曰《悬荡》的小说,此作全仿朱西宁,描写一个大学联考后发榜前出游散心的十八岁青年陷身于缆车事故,与十几个惊慌恐慌的旅客困处于两座峭壁间下临无地的半空之中”[2]4-5。而《封锁》则写于香港陷落,张爱玲逃回上海,又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辍学之后,收录到小说集《传奇》中。这篇小说描写上海因战时短暂的道路封锁,电车上两个本不相识的男女互相倾诉、爱恋,甚至起意婚配,封锁解除之后各自分散,泯然众人。这两篇小说都属于作者的早期创作,艺术手法上显见得未臻成熟,但早期的作品往往是一个作家后期创作变化万端的源头与雏形。
胡里奥·科塔萨尔的短篇小说《南方高速》则创作于他的中年,最早收录于他的小说集《万火归一》。小说叙述法国南部一条高速公路上一次严重的堵车事故,在动弹不得而食物饮水又极度匮乏的状态下,车主们纷纷组成一个个团体互相照顾,集中分配食物。一段阻塞的道路上汇集了人类生老病死的生命之常与无常,数日后交通恢复,人们各自回城,紧密的依恋感令人留恋却自然消逝。胡里奥·科塔萨尔目前在中国大陆文坛尚不出名,但个别了解的学者对他作品的评价却不低,谓之与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各有千秋。格非在推介刚出版的小说集《南方高速》(收录了《秘密武器》《克罗诺皮奥和法玛的故事》《万火归一》三部小说)时说:“我觉得有两种类型的作家,一种类型的作家,比如博尔赫斯、马尔克斯,他们的作品之间有高度的统一性。马尔克斯早期的作品就能看到他非常成熟,只是在写作的过程中打磨得越来越晶莹剔透。还有一类作家,会在各个层面、各个方面展开他的探索,包括幻想性跟现实性之间的关系。”而科塔萨尔就属于后一类作家,“他的变幻不定,特别迷人。他的探索不管是内容、故事形式、社会风貌,包括叙事技巧,都不知疲倦,他永远在探索,这个给我带来的震撼非常巨大”[3]。
这三篇小说的情节中最外化的相似点在于,小说的背景都被设置在一个突发危急时刻下的封闭空间中。“背景可能是一个人的意志的表现。如果是一个自然背景,这背景就可能成为意志的投射。”环境的危机也是人物内心的危机,但封闭的环境却往往使人释放内心的封闭状态。“背景又可以是庞大的决定力量。环境被视为某种物质的或社会的原因,个人对它是很少有控制力量的。”[4]249在特殊的环境之中,人往往失去自主控制而背离平常的意志。在危机之中,人物会表现出脱离日常的行为与心理状态。在这三篇小说之中,这些异常表现为隐伏在日常生活中,平时意识不到的焦虑、压抑情绪的激发;抑或是人在特殊环境中寻求越轨、刺激,日常生活之外的情感释放。而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往往使人对身边的人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投射,即使是对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在危机之中也会产生恍惚的依恋感。
危机时刻在《悬荡》与《南方高速》两部作品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前者的危机感在缆车停电那一刻就已经产生并一直持续着。高悬于山谷之上的缆车内,闷热、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使人的情绪极为烦躁不安。一车人面临着粉身碎骨的险境,苍鹰在外盘旋,暗示着尸体被叼啄撕咬的场面;而后者的危机随着水和食物的耗尽而逐步加深。堵车开始时人们尚能谈笑自如,王妃上的姑娘还能与标识203上的小女孩儿逗笑,但随着开凯路威的男子服毒自尽,双马力上的修女神智失常,ID上的老太太一点一点油尽灯枯,风雨寒夜消磨着人的意志,危机感一步步逼近了这群被困住的人。而这两部作品都反映了人在特殊环境背景下的反常心理状态和行为动向。《悬荡》以联考结束后出游的“我”的视角来展开叙述,令人眩晕的心理描写,烦躁时无数念头胡乱窜杂,也是放大了的每一个人的心理状态。“我”在缆车上恐高的感受,让“我”回想起当年联考落榜,跑到电子大楼去自杀的情境。再由小女孩儿的酸梅汤,“我”怀念起当年“我”妈常做的烹调细致、用料考究的酸梅汤。由牙根上的酸涩味觉,引发心中的“隐痛”,遂想起两年前的落榜。再由小女孩水壶上的卡通袋鼠,联想到电影镜头:沙漠中一堆白骨之上盘旋不去的老鹰。这种联想是无穷无尽的迷思,无止境的心理牵连也正是人心的日常状态,只不过平时安全无虞的生活状态使之隐入众多琐事之中,一到危机时刻,这种心理状态便会加速、强化、凸显,神思疾飞,心乱如麻。《南方高速》一次意外的堵车事故,将一群毫无联系的人群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女人们纷纷承担其照顾别人的角色;而男人负责解决生存配给;有所擅长的人主动而义务地医疗救助;养生葬死其乐融融。陶努斯成了自然而然的“首领”也是大家的依靠;工程师与王妃上的姑娘甚至陷入恋爱。而这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可能永远不会发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联,在这危机时刻,一条被阻塞的道路上,却发生在了数日之间。
《封锁》在情境的设计上与其他两部小说稍有不同。战时道路封锁谈不上危机,但停滞封闭的电车厢使人的距离瞬间拉近,也打开了原本封锁的内心世界,使人想要做出越出日常生活轨道的事件。一对都市男女,被夫人的菠菜包、报纸、发票、章程、名片埋没了的银行会计师宗桢,与在家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是一个好学生的翠远,由于这次意外的邂逅,也因封闭的空间制造了一个绝佳的倾诉环境,两人被凡俗所压抑的情感诉求开始被唤醒。宗桢起初对翠远的亲近其实是为了向他的表侄示威。宗桢提出要娶翠远出自他内心潜藏着的,要摆脱毫无兴趣只为谋生的工作、无法交流的夫妻关系的念头,而翠远则是为了反抗要她找个有钱女婿的家里人,为要气气“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两个心存反叛庸俗日常的人在一个特殊的时刻,短暂地产生了越轨的念头。
然而,无论是异常情绪的激发与释放,还是特殊的情感投射,这一切更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背景的“决定力量”而非人物的自主意志。小说家们着意创设的环境背景,不仅制造了外在封闭环境与内心开放世界的悖反关系的转化,更用这凝滞的时空,驱散了生命中旬意义与无意义的迷雾。
二、“慢”叙事与全知视角下的凝视与再思
缆车、电车、高速公路,这三个短篇所设情境的空间都有着“在路上”的象征意义。在路上的行进状态是人的生命本态,而停电、封锁、堵车使得原本在路上飞驰的生命被按下了暂停键,人被钉在了前后无尽延伸的道路上。而缓慢的叙事形式也与作品的内容互相生发。现代人生活在快节奏的生活状态之下,渐渐无感于生活中的日常事件,但突然之间“封锁了。摇铃了。‘叮铃铃铃铃铃。’每一个‘铃’字是冷冷的一小点,一点一点连成了一条虚线,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小说家刻意放慢的叙事速度,使得原本因飞速奔驰而模糊的日常事件,在寂静之中引起了人们的惊觉,埋藏在心底的细微情绪被感知放大,原本忽略了的生命意义此刻被小说家唤醒,或者赋予。
小说的叙事节奏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小说的内容表达,短篇小说在短小的文本篇幅中叙述极短的故事时间,是为了造成故事时间及阅读时间的停滞,以便捕捉被略过的细节。米兰·昆德拉曾自述他的小说创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音乐的影响,含有一种内在的叙述速度与节奏。在一次访谈中他以音乐节拍来类比他的小说作品,《生活在别处》的七个部分分别对应中速、小快板、快板、极快、中速、柔板、急板。而当被问及三十一页中有十七个章节,原本应属于快板的第六部分为何被归为柔板时,昆德拉解释道:“因为速度还有其他东西来决定:一个部分的长度跟所叙述事件的‘真实’时间之间的关系。……章节那么短小的作用就是让时间过得慢些,将一个伟大的瞬间凝固下来……”[5]111张大春在他的《小说稗类》中提到了这一段,将之用在了他对老舍小说《断魂枪》的分析上,并有所阐发:“速度感还必须渗透到角色内部、渗透到叙述内部、渗透到意义内部。换言之:小说家设计了使用多少个字以描述多少时间里的多少活动,都不该与作品的整体要求无关,都不应该与‘内容’无关。”[6]72显然他对此深有体会。尽管笔者认为他在十八岁创作《悬荡》之时,很可能还未读过昆德拉这段精辟的论述,但从他后来的捉摸不定的创作风格来看,张大春与昆德拉、科塔萨尔,同样对文学形式有着不懈的探索精神。
这三部短篇小说都将倥偬人世寓为一辆疾驰而过,永不停歇的列车。小说中所设的停电、封锁、堵车情境,都意在凝固一些瞬间,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它们无一不是再日常不过的琐事,早已习以为常的社会现象,但由于凝固这一行为本身而有了意义,而引起了人们的重新思考与重视。
在停滞的车厢中、道路上,人物在寂静、凝固的时刻,感知力倍增,日常生活中不曾留意的情绪、生活细节随之放大。《悬荡》中整节车厢里原本面目模糊的脸因悬停而清晰起来。车厢内的炎热、燥郁氛围更为强烈,原本并未注意到的下边谷中瀑布的声音也变得特别,像是耳朵“塞上了两堵棉花”,听不真切,却又很妙。而许多生活中的细节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比如“我”回想起联考落榜后跑到电子大楼自杀,站在楼顶时“风很大,衣领子翻起来打在脸上”这一原本毫无痛感的生活细节被贴上了极强的心理标记,一种恼人的羞耻感。而在日常生活中一件再正常不过的小事,小女孩儿尿急,成了整个小说中矛盾冲突最激烈之处,成了危机之中的危机,映照出人性的多面。
把捉生活细节之于人物的特殊意义,其深层的意图在于对人物生命的普遍探寻。小说家对生命状态的此种凝视与探寻,往往伴随着上帝视角,即使是出自第一人称的叙述(《悬荡》),也泛出了有限的感知,而对所有人的心理幽微都无微不知。由此,小说也就不再停留于正在叙述的故事,而具有了普遍的寓言性。小说的叙事视角也与小说内容寓意不无关联,全知视角使得小说中所叙述的时空处于无限延伸、多重关联的状态之中。
《封锁》除了书写平凡都市男女的情欲冲动之外,更蕴含着张爱玲对人生世态的思考,通过静止的车厢内各个人物传达出来。“可怜啊可怜!一个人啊没钱”!小说中重复了三遍,分别由乞丐与电车司机唱出。一位太太提醒领着熏鱼口袋的丈夫远离他的西裤,“现在干洗是什么价钱,做一条裤子是什么价钱”?物质与金钱施加给人的隐形枷锁被这几句自语轻巧地点出,无论是乞丐、电车司机,还是其他市民,莫不如此。翠远利用停车的时间改卷子,给一个男生抨击都市罪恶的文章打了“A”等,只因“他拿她当一个见多识广的人看待,拿她当作一个男人,一个心腹。他看得起她。”张爱玲在此映射出了陷身于都市的人们,习惯了好言好语与塞责敷衍的庸俗腔调。“世界上的好人比真人多……翠远不快乐”,这“不快乐”不是翠远一个人的不快乐,而是这个时代的消极状态。
这三篇小说都通过镜头式的语言,凝视了现代人的日常。而科塔萨尔的《南方高速》这一则寓言,在开掘人类普遍生存状态的方面,则更为深远、广阔。止庵谈到他的阅读感受:“《南方高速》实际上是堵车的经历,但是对他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史诗性的作品,因为把整个人类的历程都写到里面。”[3]讽刺现代性是这篇小说最直观的阅读体验,双马力、王妃、菲亚特、标识、ID、凯路威等汽车品牌代替了人名,工业时代的金属气息抹平了人的个性,人不再具有个体性而成了一个个符号。小说起笔就进入了停滞的时间之中,事故引起的大堵车将人们抛掷在了道路上。被抛掷的感受也出现在《悬荡》之中。车厢中人用“近乎儿子巴望母亲的神色”,等待站台的解救,却“猛地发觉自己是个弃儿”。对于事故发生的原因,《南方高速》中充满了无数的猜疑,众说纷纭而莫衷一是,真相无从得知。人只是被阻滞于不见眼前无望身后的道路上,这是西方哲学主题的又一演绎,人对生命本源的追问与失语。而救援迟迟未到,等待救援、食物、好天气,挨过时间,甚至在等待中忘记了等待什么。这一情境不难让我们联想到《等待戈多》,生命的虚无状态是现代人的共同感受。在充满细密的铺叙文本中,没有一个人是故事的主角,意外、危机、死亡都不是生命的主题,唯一的文本核心,是全知视角下无尽延伸,并无意图的广大世界。
三、叙述与意义同归消解
这三篇小说有着极为相似的结构:由于事故而引发的交通阻滞,本不相识的人物短暂的情感释放甚至依恋,恢复常态之后的若有所失,惊觉之际自然而然的无可挽留。而在小说的篇末,这三篇小说也表现出叙述与寓意上的同型结构,即在叙述中否定叙述行为,在寄寓中消解所寓之意。
张大春在小说集《四喜忧国》的序言中回忆《悬荡》的创作,起于对朱西宁的一部作品《蛇》的模仿,依张大春的解读,这一组小说写的是“没事”。《蛇》写的是解甲归田的两个战士睡觉时以为有蛇钻入裤脚管,折腾了半夜才发现只是根带子。张大春从这部作品中体会到,原来小说不必写杀人盈城,血流漂杵之事,平凡的琐事同样可以令人低回吟咏[2]4-5。文学创作宏大叙事的价值于此被消解,文本的重大意义滑向庸常的无意义。这一体会被移用到了《悬荡》之中,张大春总结这篇小说的所叙之事:“他们只是共同遭遇、共同度过,而后相忘于江湖。是的,没事。”车厢悬停在山谷之上时,种种念头、危机袭来,而随着危机解除,人物抵达对岸并纷纷下车各自分散,那些曾经惊心动魄的事件便无迹可寻,曾一度被放大、凝视的细节也不再具有意义,已经“没事”了。小说的结尾处,“我”暗自思忖,“刚才悬在那里的时候,许多的感觉,许多的思虑和顾念,一时之间,打心底漫上来,让我觉得自己是神经过敏了一场”,随后又追问了一句“果真是这样吗”?这句追问不可能得到回应,真相是不得而知。
创作《悬荡》时的张大春对人生的解读已然充满了萧条之感。他捕捉到事件对于人生实无确定意义,事件的发生与终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意义也随着事件的结束而流逝。而张爱玲的《封锁》则充满了对人生稳定性与恒常性的怀疑与无奈。正如她自己的喟叹:“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7]13在封锁之时,宗桢与翠远已亲近到谈婚论嫁的地步,宗桢慷慨激昂地说:“我不能让你牺牲了你的前程!”而当封锁解除,车子动起来后,宗桢起身挤进人丛,也没有下车,翠远明白了他的意思:“封锁期间的一切,等于没有发生。”那份慷慨激昂自然也就没有存在过,偶然的邂逅与情欲只不过是在一个城市打盹时做的一个不近情理的梦。城市醒了,梦境随之消失,当然,梦境中的事本就不曾发生过。张爱玲对于世俗情感、人生安稳的虚假性通过这一则寓言被深刻地揭示出来。
科塔萨尔一生辗转流徙,幼年时父亲不告而别,由母亲独自抚养,大学时学习哲学,后因经济压力改学师范,在中学授课同时进行文学创作,后又在门多萨省库约大学教授英法文学,曾经历过房屋被军政府侵占(写成自传作品《被占的宅子》)、被驱逐等政治迫害。他的经历也影响了他对文学创作的态度。小说集《万火归一》的译者,同时也是《百年孤独》的译者范晔认为:“对于建立在十八世纪以降盲目乐观的哲学和科学体系之上的‘虚假的现实主义’(科塔萨尔语),这位阿根廷作家几乎是出于本性地报以不信任的态度。……科塔萨尔的策略与十九世纪‘幻想文学’的前辈们不同,他从未谋求全然跳脱既定的现实情境,而是致力于寻觅或开启日常现实中的罅隙,从中窥见另一种真实,介入另一种时空,邂逅另一个自己。”[8]199-200《南方高速》正是这样一篇从既定的现实情境中窥见另一种真实的创作。创作时作者已过天命之年,自然也对世道真实有了更深层的体悟。小说布满了种种可怕的、温馨的细节,都是由意外事故而引发的日常事件的集中展现:开凯路威的男子突然的自尽,ID上的老太太转危为安之后死亡,出去觅食的几个人神秘失踪,清晨女人们分配给养,男人们例行碰头开会,孩子们玩着小汽车,修女们手捻念珠,王妃上的姑娘与工程师的温存,这一切都随着交通毫无征兆的恢复而把捉不住。工程师上一刻还在幻想着回到巴黎之后能与王妃上的姑娘相亲相爱嬉闹一番,随即便发现王妃已经消失在了急速飞驰的车流中。他仍然沉醉于这意外带来的假象之中,“只有一件事他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匆忙,为什么深更半夜在一群陌生的汽车中,在谁都不了解谁的人群中,在这样一个人人目视前方、也只知道目视前方的世界里,要这样向前飞驰”。科塔萨尔在小说中借工程师之口揭开了现代社会人人目视前方向前飞驰的非理性日常。人只有在意外时刻,生活节奏慢下来,才可能感受到生命的存在意义。而在凝固的时空中被挑起的人的感知力,在被赋予特殊性的瞬间,随着道路的解封时间的继续,又淹没在日常之中,回复了无感知无意义的状态。他在这则寓言之中描述了他所看到的现代社会的虚无状态,也试图以此寓言道出真相:被凝固的瞬间,不过是人类自己赋予的假象,意义缺如才是生命的真实。科塔萨尔这种虚无的世界观,植根于现代社会的日常状态,但也是现代主义的巨大迷障。
《封锁》《悬荡》《南方高速》,分别于20世纪40年代、70年代、60年代出自三位无有交集的作家之手,却以极为相似的情节结构、互有共通的现代性指涉,默契地书写了20世纪的时代寓言。这样的文学现象并非是纯粹的巧合,而是这三位对时代体征极为敏感的作家,共同感受到了隐伏于喧嚣嘈杂之下的现代社会问题。而他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寓言式的短篇小说来承载他们各自对时代的醒世思考与忧虑,也与短篇小说适合言说真理的体裁功能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