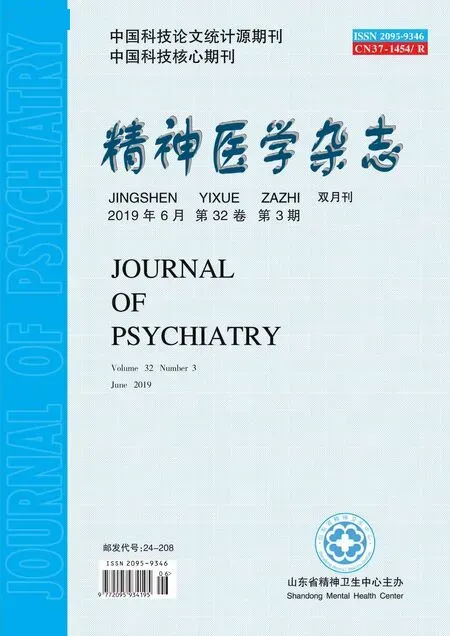不同亚型抑郁障碍自发及诱发脑电研究进展*
抑郁障碍(Major Depressive Disorder,MDD)是高患病、高复发、高致残、高自杀和负担沉重的精神疾病与公共卫生问题,终生患病率为10%~20%,自杀率15%~20%[1,2]。由于其临床表现复杂多样,为了更好地进行个体化治疗,可以分为不同的亚型。根据最新的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5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Fifth Edition,DSM-5),抑郁障碍可根据其临床特征的差异进行不同的标注,其中最常见的包括伴焦虑痛苦、伴忧郁特征、伴非典型特征、伴混合特征、伴精神病性特征等[3]。
1 抑郁障碍亚型
1.1 临床特征分类方法
1.1.1 伴忧郁特征 伴忧郁特征(With melancholic features)的抑郁障碍主要表现为兴趣和乐趣的丧失,对令人愉悦的事物缺乏应有的反应、做事缺乏动力、几乎不参与任何活动。还存在晨重夜轻、睡眠不佳、食欲减退、体质量减轻的问题。相比其他亚型,伴忧郁特征的患者自杀风险更高、复发风险也更高[4]。
1.1.2 伴非典型特征 伴非典型特征(With atypical features)的抑郁障碍主要表现为具有情感反应,或者伴有明显的体质量增加或食欲增加、嗜睡、自觉躯体沉重(主要在手臂或者腿部有铅样沉重感)、长时间社会功能受损[5]。非典型特征的抑郁障碍通常在低年龄段发作,女性患者约为男性的2~3倍。非典型特征的抑郁障碍比典型抑郁有更多的共病,包括:社交恐惧症、双相情感障碍、饮食障碍和物质依赖。非典型抑郁障碍患者会表现出更多的低自尊、社交焦虑以及品行障碍的问题[6]。非典型特征的患者症状复杂,临床鉴别上更加困难。
1.1.4 伴精神病性特征 伴精神病特征(With psychotic features)的抑郁障碍一般占重度抑郁障碍患者的19%~25%,症状比较严重,存在与忧郁状态不一致的幻觉或妄想,患者一般伴有较强的自杀观念,治疗效果不佳,有重性精神病的阳性家族史,且复发率较高[8]。伴精神病性的抑郁障碍是重性抑郁障碍中比较难治的亚型。
1.1.5 伴混合特征 伴混合特征(With mixed features)的抑郁障碍是指在抑郁发作的状态下,患者表现出类似轻躁狂或者躁狂的症状。在临床上一般表现为心境高涨、自我夸大、精力充沛、冲动行为等[9]。伴混合特征抑郁障碍的临床特征与伴非典型特征抑郁障碍相类似,因此鉴别诊断非常重要。
1.2 其他分类方法 Sharpley CF等[10]根据抑郁障碍患者的临床表现和神经通路的不同,将抑郁障碍分为抑郁心境(Depressed Mood)、快感丧失型抑郁(Anhedonia Depression)、认知症状突出型抑郁(Cognitive Depression)、躯体症状突出型抑郁(Somatic Depression)。随着功能磁共振技术(fMRI)和生物标记技术的发展,有研究者通过分析抑郁障碍患者额叶纹状体和边缘系统的关系,将抑郁障碍亚型通过生物学方法分类,分成4个神经生理学亚型,这些亚型是由边缘和额纹状体网络中不同的功能失调连接模式定义的,是对传统分类方法的超越[11]。
2 脑电图
脑电图(Electroencephalogram,EEG)是由脑皮层神经元突触后电位同步总和的表现,在人们无刺激和清醒放松状态下记录的EEG被称为静息态EEG[12]。EEG捕捉自发脑电,反映了大脑皮层神经元细胞群自发性和节律性的电生理活动,包含了大量生理与病理的信息,因此EEG在临床上有着广泛的应用[13]。
依据EEG信号波幅、功率等参数所绘制的脑电图已经在一些精神疾病的诊断中占有重要地位。另外,研究者可以基于EEG的信号来检测大脑的活动状态。Bruder GE等[14]对比了25例焦虑型抑郁障碍患者和26名健康被试的EEG,发现焦虑型抑郁障碍患者的右半球大脑α波活动明显少于左半球。Manna CB等[15]采用言语(词发现)和空间(点定位)的神经认知任务,对比了14例高焦虑抑郁障碍患者、14例低焦虑抑郁障碍患者以及21名健康对照的EEG差异,结果发现:高焦虑组在空间任务中右侧中央区和顶叶区的激活程度比左侧大,相反,低焦虑组在言语任务中左额叶和中枢激活更多。这些研究都证明了,焦虑型抑郁障碍会增加患者不对称的半球活动,且这些节律性活动大多持续出现在右半球。
除了对个体的高级认知功能的检测,EEG也能反映个体对决策的反应和情绪的变化。Stewart AS等[16]记录了34名健康对照、48例非忧郁型抑郁障碍患者以及17例忧郁型抑郁障碍患者的脑电图,结果发现在奖赏处理的最后阶段,忧郁型抑郁障碍患者和非忧郁型抑郁障碍患者的后脑EEG表现出不对称性,且忧郁型患者的右后脑活动相对较低,非忧郁型患者的左后脑活动相对较低。可见非对称性是抑郁障碍患者奖赏加工的异常标志。
3 不同亚型抑郁障碍的脑诱发电位
脑诱发电位是指接收到人为施加特定刺激(一般指声、光、电刺激)产生的脑电信号电位的变化。脑诱发电位在临床的抑郁障碍发病机制的研究、亚型分类研究中都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常用的脑诱发电位包括:视觉诱发电位、听觉诱发电位、躯体感觉诱发电位和事件相关电位[17]。
3.1 视觉诱发电位 视觉诱发电位(Visual Evoked Potentials,VEPs)是从视觉皮层上提取的脑电信号,VEPs功能的实现是基于所有层次的功能完整性,包括眼睛、视网膜、视神经、光辐射和枕皮层[18]。
VEPs属于皮层电位,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患者的精神状态,因此VEPs的指标可以用作抑郁障碍亚型分类的参考标准之一。Fotiou F等[19]对50例抑郁障碍患者进行VEPs的记录,其中14例是伴非典型特征的患者,16例是伴忧郁特征的患者,32例是伴躯体症状的患者,9例是伴混合特征的患者。结果发现:伴非典型特征的患者N80和P100潜伏期明显缩短,而伴忧郁特征的患者N80和P100潜伏期明显延长。可见不同亚型患者的VEPs指标会呈现明显的不同,VEPs对于抑郁障碍的分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国务院相关文件曾对游学活动作过粗略分类,凡在学期内进行的称为研学旅行,学期外进行的叫夏、冬令营。国家对游学产业的支持力度逐年增大。研学旅行试点工作从2013年起先后在上海、安徽、陕西、重庆、新疆等8个省(区、市)启动,有574所学校、60多万名学生参加。有关教育专家认为:研学旅行在推动培养学生集体观念、生活技能、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同时,也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增长。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研学旅行项目存在一定安全风险,一些地方政府有所顾虑,推进速度并不理想。不过,夏冬令营发展势头却比较乐观。
另外,VEPs还可以用来检测患者的情绪识别功能及其他高级认知功能。刘纪猛等[20]选取28例伴忧郁特征抑郁障碍患者和31名健康人,让他们接受面孔情绪识别任务并检测他们在执行任务时的VEPs。结果发现,相较于健康被试组,患者组的头颅局部N170潜伏期差异显著,而N170波幅差异不显著。可见伴忧郁特征的患者在发作期对于不同情绪的面孔认知加工有损害,其高级认知功能受损。
上述研究表明,VEPs在研究中可以用作抑郁障碍亚型的区分技术,同时也可以用作患者认知功能水平的监测。但对于存在视力损伤或者注意不良问题的患者,由于无法对刺激进行良好的反应,VEPs并不是研究的首选。
3.2 听觉诱发电位 响度依赖性听觉诱发电位(Loudness Dependence of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s,LDAEP)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的检查方法,主要利用声音刺激患者做出反应,在临床研究中运用较多,尤其是在血清素活动水平的监测方面非常敏感,高血清素活性表现为低振幅的LDAEP[21]。
由于自杀行为与患者体内血清素水平密切相关,因此LDAEP的水平常作为评估抑郁障碍患者自杀倾向的标志。Lee SH等[22]选取了53例伴非典型特征的抑郁障碍患者和68例伴忧郁特征的抑郁障碍患者,用5种不同的声音强度(55、65、75、85、95dB)对患者进行刺激,记录LDAEP。试验结果表明,伴非典型特征患者的LDAEP值较伴忧郁特征的患者高。由此可以证明,伴非典型特征的患者血清素能活性相对不足,LDAEP反映了情绪表现。情绪脆弱性引起的血清素活性的短暂下降可能导致伴非典型特征患者的自杀倾向。
不同亚型的抑郁障碍患者对于自杀的意念也是不同的,除了临床症状上的不同,患者的生理活动上也会反映出不同。Paul B等[23]选取了14例伴忧郁特征的抑郁障碍患者和13例其他亚型的抑郁障碍患者,用强度依赖性听觉诱发电位(Intensity Dependence of Auditory Evoked Potential,IDAEP)对他们进行测评。结果发现,伴忧郁特征患者的IDAEP坡度小于其他亚型患者的坡度。IDAEP和血清素活动水平有很大的相关性,血清素的活动水平越高,IDAEP的坡度也就越小,与LDAEP大致相似。检测结果可以表明患者自杀风险的高低,医生可以根据检测结果决定患者是否需要尽快接受药物治疗,而这作为客观的指标具有较高的可参考性。
听觉诱发电位中最常见的就是LDAEP,它在血清素的监测方面有着极高的敏感性,对细微的变化也能有效应答。因此医生可以借助LDAEP的水平来判断患者潜在自杀风险的高低,能对药效进行及时的监测分析,从而选择最佳疗法。LDAEP的应用对抑郁障碍的个体化治疗提供了新的思路。
3.3 事件相关电位 事件相关电位(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是一种特殊的脑诱发电位,它是个体接受某项刺激(视觉、听觉或触觉)后产生的诱发电位,反映了患者认知过程中大脑的神经电生理变化。常见的ERP技术包括P300、N400、关联性负变(Contingent Negative Variation,CNV)和失配性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MMN)。此外,还有P50、P200、N100等[24]。
ERP在研究中应用广泛,目前临床上使用最多的是P300,它是ERP的一个内源性成分,对患者认知功能障碍尤其是执行功能损害的严重程度能够有效评价。P300是一种比较稳定的指标,除了能作为认知功能的评价工具,对抑郁障碍的临床治疗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25]。在不同亚型抑郁障碍的分型上,P300可以检测出不同亚型患者之间的电生理差异。Santosh PJ等[26]对20例伴精神病性的抑郁障碍患者和20例其他亚型的抑郁障碍患者进行P300的检查,结果发现伴精神病性的患者P300的波幅偏低。
在临床研究中,ERP与生化指标的结合是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姚丽敏等[27]选取45例伴焦虑特征的抑郁障碍患者和50例其他亚型的患者,检查他们的P300潜伏期和波幅,并测定其血清游离和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T3)、甲状腺素(FT3、T3)以及雌二醇(E2)、睾酮(TESTO)等激素水平。结果发现这些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和甲状腺激素、性激素水平以及焦虑水平相关。
ERP最主要的功能是检测患者的认知功能,ERP的指标与大脑的活动密切相关,可以广泛结合视觉、听觉的刺激进行临床研究。Qiao Z等[28]对24例伴焦虑特征的抑郁障碍患者和24位健康被试进行oddball测试,记录他们的听觉MMN,结果发现患者组大脑前中额区的MMN波幅只在延时的情况下降低,而短时情况下两组的MMN波没有差异,这证明了患者在前意识信息加工上并无缺损。对于接受物理治疗的患者,ERP可以作为疗效检测的方法之一。Choi KM等[29]选取了18例伴忧郁特征的抑郁障碍患者,对他们进行为期3周的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治疗,然后对他们的脑电信号进行采集分析。结果发现,P200的波幅有了明显的提高,这说明rTMS在患者的左前脑回区域有明显的治疗效果。
ERP一般用于患者认知功能的检测,能识别抑郁障碍患者的认知缺损程度,在情绪识别、感知觉测试中的表现尤为突出。ERP也能反映抑郁障碍状的特异程度,这对抑郁障碍的亚型分类很有帮助。另外,ERP对于其他检测方法具有较好的兼容性,可以结合生化等其他方法以达到更全面精确的检查结果。ERP受限于自身的空间分辨率,未来的研究中可以搭配其他影像学检测方法,如CT、fMRI等。
3.4 错误相关负电位 错误相关负电位(Error-related Negativity,ERN)是个体在识别正确刺激任务范式中给出错误应答后50~100 ms之间出现的一个较大的负电位。ERN可以有效反映人脑对自身错误行为的监测,是一种高级的认知功能。由于抑郁障碍患者对环境中负性因素有着更高的敏感性,对信息的加工往往也是负性的,因此ERN在抑郁障碍患者的相关研究中是一种有价值的神经生物学指标[30]。
Weinberg A等[31]选取了处于缓解期的伴忧郁特征抑郁障碍患者29例(rMD组)、其他亚型抑郁障碍患者56例(rNMD组)以及健康对照组被试81名(HC组),检测他们对奖赏的神经反应。实验通过博弈范式记录患者对于收益与损失反应的ERN数据。相对于HC组和rNMD组的患者,rMD组患者的主要特征是对于奖励反应的迟钝。结果可以表明,对奖励的迟钝反应是伴忧郁特征抑郁障碍患者的一个确切特征。
ERN在临床研究中多用于患者的认知测试,尤其在精神运动性迟滞方面,两者相关性非常高。ERN对错误反应后的再次反应时长有一定的预测作用,反映个体对自身错误的监测过程,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4 小结
大量过往研究均证实了EEG在探测抑郁障碍个体脑功能活动的异常中有一定的效果,但并没有临床研究证实EEG能成为抑郁障碍确诊的手段和抑郁障碍亚型的分型手段,其原因就在于很多异于正常人的脑电特征并非抑郁障碍患者特有[32]。今后的临床研究中,可以再对不同患者的EEG进行更加微观的研究,以期找到EEG作为抑郁障碍诊断及分型的证据,为以后的诊断和治疗提供新思路、新方法。
脑诱发电位是临床上应用很广泛的电生理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用途:第一,用作抑郁障碍的鉴别检查手段;第二,区分抑郁障碍的几种亚型;第三,用于抑郁障碍临床药理研究;第四,检测抑郁障碍患者的认知功能水平。脑诱发电位包含的方法很多,但是具体针对抑郁障碍亚型的研究还比较少,部分研究的结果也显示出不一致性,这主要反映出抑郁障碍亚型特异性的变化。之前有研究证明,ERP对于抑郁障碍和焦虑障碍的区分仍存在各种缺陷,因此,ERP对抑郁障碍的诊断价值仍然需要其他临床研究的支持[33]。
ERP在研究的精度上并不如影像学检查,而且大多数情况下需要患者密切的配合才能获得准确的数据。由于EEG和ERP检查的经济性和高效性,在未来临床研究中,这两种方法依旧是电生理检查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