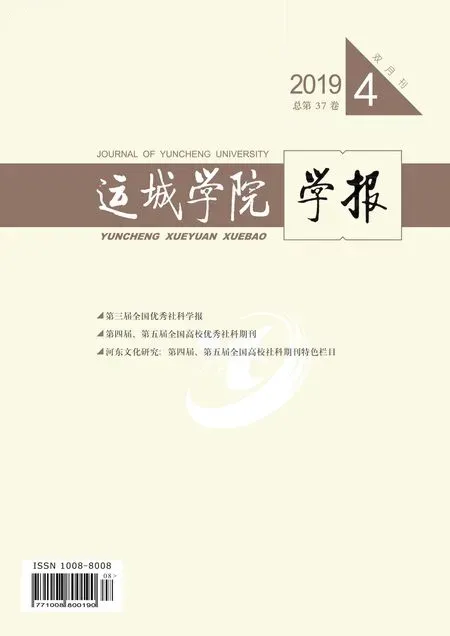礼制与政治的互动:论明嘉靖孔子祀典改革
王红成,张之佐
(1. 河西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甘肃 张掖 734000;2. 西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张璁对孔子祀典的改革,是嘉靖时期礼制变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关于孔子祀典改革相关问题的研究,现今学界多数学者认同黄进兴的观点,主要关注道统与治统的关系,以及孔子祀典的改革是否是尊孔行为,或是否为了提高皇帝地位、树立英主形象等内容。[1]107-137、[2]182-184、[3-5]这些看法均是以儒学史、学术思想史等为视角的研究。张璁是嘉靖时孔子祀典改革的主要实施者,但学界关于二者的关系及孔子祀典改革政治意蕴的研究还不够充分,仍有拓展的余地。所以,本文通过对张璁改革孔子祀典的条件、原因、目的以及过程等的讨论,探究张璁改革孔子祀典的政治意蕴,以及这次改革在帝制的历史长河中呈现出的历史特性与价值。
一、封“王”不是真正的尊孔
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便将儒家思想视为国家正统的意识形态,作为儒学开创者的孔子,其地位自然也不断提升,祭祀孔子成为历代统治者力行不辍的事情,孔子祭祀也由阙里孔氏的私家行为逐渐演变为朝廷祭祀典制的重要内容之一。经由历代的发展和开拓,孔子祭祀逐渐具备了朝廷祀典规模,最终在唐代定型。它的内容有很多,主要由谥号、章服、笾豆、乐舞及配享与从祀体系等几个方面构成。其中谥号为孔子祀典的核心,其他方面都随谥号的尊卑而变。
由于孔子去世时的爵位为士,依礼不当有谥号,唯有鲁哀公诔文中尊称孔子为尼父。但从后世史料来看,孔子后人及其后学没有沿用这个称谓。迟至两汉时期,儒学大发展,从私学转变为官学,孔子地位得到极大提高,但此期间并没有追谥为王、公。只有在王莽擅权时,于汉平帝元始元年追封为褒成宣尼公。不过,王莽此举并非出于尊崇孔子之心,而是想借助孔子之名,达成篡权之实。他的意图昭然若揭,正如明儒丘濬所说:“夫平帝之世,政出王莽,奸伪之徒假崇儒之名,以收誉望,文奸谋。圣人在天之灵,其不之受也必矣。”[6]559王莽篡权仅仅为昙花一现,追谥之称也烟消云散。东汉光武建国,没有沿用王莽追谥的公号,仍以圣师称之。魏、晋承袭汉制,孔子尊称与汉代相同。东晋南渡,以及宋、齐诸代,也未有追谥孔子王、公之事。鲜卑拓跋氏建立北魏,反倒追谥孔子为文圣尼父。这里没有沿用王莽篡汉时追封的公号,而是运用父这一美称,与鲁哀公时的尊称比较接近。北朝战事频繁,此谥号转瞬即逝,没被后世王朝继承。自此至唐初,孔子谥号屡屡变动,或称尼父,或称公,或称宣父,或称太师,不一而足,但汉代时孔子的圣师尊号,却一直沿用未废。
孔子第一个被长期沿用的谥号,是唐玄宗于开元二十七年(739)追封的文宣王。除了孔子本人以外,他的门人颜回、曾子、闵子骞等均追封公、伯、侯爵位,与各自谥号、爵位相匹配的章服、乐舞、礼器等都形成了一定规制。后世对玄宗此举大加褒扬,认为这将孔子地位抬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是儒学极为昌盛的表现。若结合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在追封孔子之前,唐玄宗先是追封道家老子为玄元皇帝,继而又尊崇姜尚为武圣,最后才追封了孔子,“盖有不得而阙然者也”[7]182。至于说他有尊崇孔子与提升孔子地位之心,也是子虚乌有的事。李唐王朝自认为老子的后裔,玄宗更追封老子为皇帝,这种看似个人或李氏家族的行为,实际是整个国家的价值取向。至于追封王号的孔子,地位则明显低于老子,这是毋庸置疑的。既然如此,又如何谈得上孔子地位的上升呢?
宋代统治者仍沿用唐代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增孔子所用冕旒为十二,形成了四配、十哲、七十二贤等附祭系统,较前代典制更加完备。经过宋代的增益与调整,孔子祀典的等级有较大提升,这就暴露了孔子祀典中的内在矛盾。唐、宋两代皇帝只是把孔子追封至王爵,而孔子祀典所用礼秩却与天子同等,这就使封号与相应礼秩之间出现失衡的状况。为此,他们想通过进一步追封孔子为皇帝的办法,协调这种不和谐的礼制。到宋神宗时,常秩、李定、黄履等人便上奏疏,请加孔子帝号,遭到杨绘、李清臣等人反对,认为此举非礼,论争的结果是保持孔子原有谥号。孔子谥号称帝的升格运动没有就此结束,直到明代时仍有周洪谟、郑纪、吴世忠、杨子器、何孟春等人提出这样的主张,也都被一一否决。经过几次建议,他们的目的都没有达成,便将追封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李清臣等人,认为他们“得罪圣门,至今不能无笔诛之忿”[8]34。或许常、周等人追封孔子爵位的目的在于尊崇孔子与提升孔子地位,但这并不代表孔子称帝能达到他们尊崇孔子的预期,尤其忽略了当时皇帝的考虑。北宋祥符元年(1008),宋真宗在拜谒曲阜孔庙之后,对臣下说:“唐明皇褒先圣为王,朕欲追谥为帝,可乎?”于是“令有司检讨故事以闻”,但事与愿违,朝臣并不认同他的想法,而以孔子为“周之陪臣,周止称王,不当加以帝号,(宋真宗)遂止增美名”[9]268-269。可见,宋真宗追封孔子爵号的真正意图,就是要在某些方面表现出对前朝的超越。关于孔子的封号,唐玄宗封为文宣王在先,宋真宗要想证明本朝胜过前朝,最好的途径就是在前朝的基础上对孔子进一步加封,把孔子爵称增为至圣文宣王。换句话说,宋真宗对孔子的追封,根本不是出于对孔子的尊崇之情,更达不到尊崇孔子的效果。相反,孔子称帝或加封不仅不能提升孔子地位,反倒使孔子沦为君权的附庸。[10]182-186
后世之所以铭记孔子,是因为其学说的永恒性,判断他的地位是否得到提升,应该以儒学的昌盛与衰落作为标准。纵观自汉至元的历史,儒学地位最高的时代莫过于两汉。孔子曾言:“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1]3297孔子创建的儒家学说,不止是一种学术思想,终极目的是对现实的关照,也即后世所谓“经世致用”。在此期间,只有汉代儒生能发展自己的学说,可以将之运用于现实之中指导实践,这在后世任何朝代都不曾出现过,更是后世儒生可望而不可即的。正因为儒学在两汉时极为昌盛,才带动了孔子地位的上升,这是毋庸置疑的。进一步讲,汉代儒学的昌盛使孔子地位得到了极大提升,没有为孔子带来帝、王、公等尊号,更没有哪个皇帝、儒生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他们都以圣师称谓孔子,因为他们知道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尊崇孔子。这说明与孔子地位相关的是儒学的兴替,而不是孔子追封爵号与否。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唐、宋二朝中佛教、道教的地位是可以与儒学分庭抗礼的,有时甚至超过了儒学,像唐代七迎佛骨与宋代徽、钦二帝自称道君皇帝等。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而宋孝宗的一句话道出了真意。他说:“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12]116儒学本是内外兼修的学问。在宋代皇帝眼里,儒学只剩下“道问学”,而“尊德性”的部分由佛、道取代。这就再次衬托出,儒学在当时人思想中所占的比重,要比汉代人低得多,那又谈何因封王而致孔子地位的上升?
二、大礼议遗留问题的解决
孔子祀典改革是“大礼议”的延续,是对“大礼议”遗留问题的进一步解决。“大礼议”争论的核心是世宗能否更换父母的问题。想解决这个问题,还要回到当时的历史实际中寻找依据。世宗继承皇位的最主要依据是《武宗遗诏》,但通观《武宗遗诏》所言,与明历朝皇帝的遗诏并无差别,基本属于对武宗执政得失的总结。至于世宗是否需要更换父母,《武宗遗诏》没有明确指出。《武宗遗诏》中与此问题相关的词句,只有援引《祖训》“兄终弟及”条。可这条文的表意很不明晰,这就决定了议礼双方需要对《祖训》做进一步诠释,才能更好地论证自己的观点。
“大礼议”双方依照不同的目的,采取了不同的诠释方式,得出的结论也不同。杨廷和等人出于维护自身的政治利益,认定《祖训》中“兄终弟及”仅是指同父兄弟间的帝位继承关系。为了契合这一概念,强迫作为武宗堂弟的世宗入嗣孝宗,使世宗与武宗成为亲兄弟,并援引与此不相类似的汉、宋故事,论证他们观点的正确性。世宗继承皇位是否需要入考孝宗,只能置于明代政治、社会等历史实际中,断定某一方更合情理。杨廷和等人援引汉哀帝、宋哲宗及魏明帝诏书等历代故事,都是预养于宫中,作为族子继承的皇位,与明代史实有所不同。
张璁等人为了维护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将《祖训》中“兄终弟及”解释为一种递进式的宗法关系,依照宗亲五服关系、由嫡至庶、由长至幼的彝伦顺序,决定皇位继承人。张璁说:“孝宗兄也,兴献王弟也,献王在,则献王天子矣。有献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谓‘伦序当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7]23兴献王是孝宗的亲弟,当武宗无嗣时,皇位自然由兴献王一系继承。由于兴献王去世,世宗是兴献王的长子,本有继承皇位的资格,没必要入嗣孝宗为后。且《武宗遗诏》中明言“迎取(世宗)来京嗣皇帝位”[7]36,也与张璁的阐释相呼应。
张璁通过对《祖训》的解读,维持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并以诏书的方式,确定了这次论争的判定结果。不过,这不意味着赞同杨廷和等人主张的那些人已经认同了张璁等人的观点。相反,不少人仍坚持原来的想法,且他们在社会上仍有一定社会基础,尤其像杨慎这类人,在在野文人心中的地位非常高,言行具有导向作用,被贬谪之后,不仅没有遭到批评,名声反而大震,文章更是随写随刊,影响力决不容小觑。即使到了嘉靖九年,黎贯仍不忘要借改称孔子为先师之机,讽刺“大礼议”中追封未曾实受帝位的兴献王为皇帝。这都说明当时的舆论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杨廷和等人,因此有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大礼议”中世宗保持与兴献王父子关系的合理性的必要,以解决“大礼议”中遗留的舆论缺陷的问题。
张璁推行孔子祀典相关措施中,另建启圣祠供奉叔梁纥、曾皙等诸为父者,与“大礼议”关联最为密切。这项措施的目的是为了纠正孔庙配位次序的颠倒。先前,孔庙中的位次是孔子居中,四配立于孔子左右,十哲等序列于堂。他们的父亲从祀于两庑,处于从属地位。父子乃人伦之大本。孔庙是宣扬教化之处,父子伦序关系若是错乱无序、有违伦常的,对教养百姓起到的必定是负面效应,因此必须予以更正。张璁的措施是在孔庙外另建启圣祠,祭祀供奉于孔庙堂上者之父,叔梁纥居中,以曾皙、颜路等为配。这项措施的直接结果,就是提升了“父”的地位,纠正了错误的伦序关系。此外,张璁还有更深层的意图。“大礼议”期间,在张璁等人的支持下,世宗保持了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拒绝了杨廷和等人的安排,终以诏书的方式,确定了这次论争的判定结果。由于理论论证尚有欠缺,当时“统、嗣合一”的观念在士人心中具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张璁必须要进一步完善论证保持世宗与兴献王父子关系的正确性,来说服这些人,以免使得世宗“陷入道德困境”[13]92。张璁对孔庙配享体系的改革,则凸出了“父”的重要性,强调父子关系在纲常伦序中的核心地位,这就为“大礼议”的判定结果,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过去认为孔子祀典改革与“大礼议”没有直接关系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二者是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前者是后者的延续。
三、孔子祀典改革的历史意义
在明代,祖制具有宪法性质,是明代历朝皇帝必须恪守的家法,不容丝毫违背。在明代的历史进程中,祖制发挥了不少的积极作用。但祖制规定的内容有限,随着国家、社会的发展,常常会出现祖制没有规定的事例,祖制自身也会滋生一些问题。对于这些新问题的解决,祖制起到的往往是阻碍作用。所以,是恪守祖制的规条还是遵循祖制大义,便是摆在张璁面前的问题。从历史进程看,张璁选择了后者。值得一提的是,明人往往将太祖、太宗并尊,均称为创业之主,所谓的祖制,不独指洪武典制,有时涵盖永乐典制在内。[14]20-22张璁所推行的孔子祀典等改革,是以洪武典制且“皇祖初建之制”为依据,这就要求他必须重新解读祖制,使祖制的含义仅指洪武祖制。张璁在与徐阶等人辩论,以及推行孔子祀典改革时,除了把祖制作为孔子祀典改革的理论依据,还把祖制作为改革对象,重新加以诠释。他还运用郊祀、宗庙等祭礼的改革,建立起太祖的独尊地位,进而确立“皇祖初建之制”的权威性,并将之运用于实际改革中。此外,推行政治革新时,张璁等人也将制度上的败坏追溯到永乐时,把太宗所施行的一些措施作为改革对象。[15]152-158这样通过一系列措施,张璁将祖制的含义成功限定为“皇祖初建之制”。
嘉靖以前,熊禾、宋濂等大儒都表达过清除孔子祀典积弊的想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历史契机,所以只能停留在理论层面。可是,这种“潜流”式的存在,一旦与可以借助的“突发事件”相接,会很快与之相交融,瞬间会将理论转化为现实。张璁推行孔子祀典改革,便很好地印证了这一点。所谓的历史契机,除了“大礼议”之外,还有政治革新理论建设的需要,共同促成了这次改革的成功。[16]57-59不过,问题的切入点不会是这些独特的历史契机,而是孔子祀典本身存在的积弊。张璁很清楚这一点,在奏疏中也是遵循这个思路,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有力地回应了朝臣的质疑。
张璁改革孔子祀典,仅就孔庙仪制有所损益,对于孔子之父、后人的爵位,并未有所减损。这也使得一些不明就里的人产生了疑惑,甚至有干进之徒如监生詹启等人提出废止孔子后人衍圣公的爵号,以此博得晋升的机会。不得不说,这些人并没有完全理解张璁为何推行孔子祀典改革。张璁曾说:“臣窃惟皇上正孔子谥号,本所以尊孔子也。若因此革其后代封爵,恐非圣明尊崇先师之本心也。夫公号与王爵不同,孔子父称启圣公,子孙称衍圣公,光前裕后之典,皆尊崇之至也。比之以王爵加孔子,使自受之者不同。”[17]33在这里,张璁重申改革孔子祀典的目的,是为了尊崇孔子;追封孔子的父亲、子孙为王爵,旨在凸显孔子的功德,为“光前裕后之典”,其性质与追封孔子完全不同。这说明张璁改革孔子祀典的目的性十分明确,其所以追封孔子之父、后人,是为了彰显孔子对后世的卓越贡献。若将孔子之父、后人的爵号削去,无疑是对孔子功德的否定,这才是对“道统”的贬抑。补充孔子祀典改革原因的寥寥数语,不仅解了众人之疑,而且较为明确地表达了张璁尊崇孔子的本心,更是对朝中反对者的最好回应。
嘉靖革新是历史变革中的一环,孔子祀典改革是嘉靖革新的重要内容。张璁通过对孔子祀典的改革,将“皇祖初建之制”提到独尊的地位,这既是政治革新的一部分,又为政治革新提供理论依据。世宗也明确提出,孔子祀典改革的依据无他,“且以我皇祖之命直断之”[17]304。在“大礼议”中,张璁以《祖训》为据,指出只有太祖才具有皇位授予权,世宗即皇帝位的理论依据是天下乃是“祖宗之天下,天下之天下”[7]19,而不是孝宗个人的私有物品。从“大礼议”发生到孔子祀典改革,可以看出明代由“二祖之制”到独尊“皇祖之制”,[18]107再由独尊“皇祖之制”到能否更改“皇祖之制”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正德到嘉靖时期的政治走向,即从因循旧制向政治革新的转化。只有承认这个前提,才能对世宗更正孔子祀典有最客观的认知。
需要指出的是,在清代考据礼学和现代学术研究观点的影响下,有的学者提出张璁对孔子祀典的改革,是与古礼不相符合的,对此提出一些批评。不得不说,这种观点是经不起推敲的。礼学是一种极重躬身践履的学问,礼制是礼学在现实政治中的外化体现。《礼记·礼运》记载,“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19]618这里的“义”,是便宜、适宜的意思。这句话是说,每个时代都有符合自身特点的礼,在世变时移之后,礼也要随之而变,不能拘泥于古礼仪节。朱熹曾言:“有圣人者作,必将因今之礼而裁酌其中,取其简易易晓而可行,必不至复取古人繁缛之礼而施之于今也。古礼如此零碎繁冗,今岂可行,亦且得随时裁损尔。”[20]2877-2878礼制的制定或改革,必须把握问题的根本,不能拘泥于细枝末节的争论,要以极为务实的态度,制定出“恰到好处”的措施。面对改革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突发状况,改革者要迅速、有效地做出回应,以确保改革顺利进行。在裁断孔子祀典改革是否当行的问题上,关键不是在于恪守古礼条文或“纷更”礼制与否,而在于某礼制是否真正应当变革,改革是否对朝廷社稷确实有益处。张璁通过对祖制的解读,成功将祖制与传统礼义相结合,使祖制成为孔子祀典改革和政治革新的理论依据。关于孔子祀典的改革,是有益于朝廷社稷的改革,是符合“随时裁损”原则的最好案例。
——兼论 “训民正音”创制者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