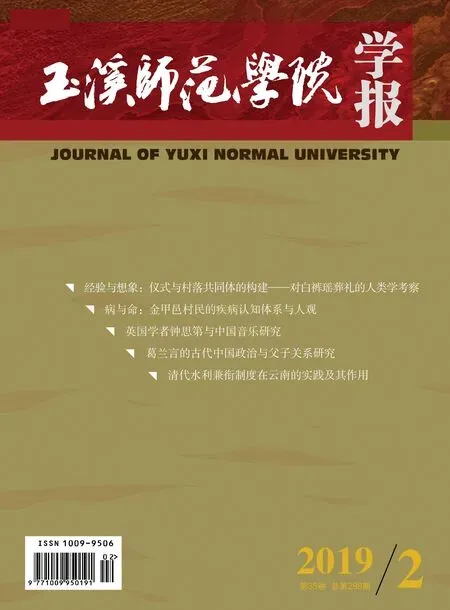档案所见乾隆年间的“丢包诈骗”及处罪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吉林 四平 136000)
丢包诈骗是一种较古老的骗术,犯罪嫌疑人往往利用人们贪便宜的心理实施诈骗。作案者大多为两人以上,行骗时,一个骗子先在受害者面前丢下“钱包”等物,其他同伙随即装成“过路人”将包捡起,当着受害者的面展示里面的钱物,并主动提出与受害人共分钱物。随后,先前丢包的骗子会折身返回,要求对受害者和“过路人”进行搜身,继而采取掉包等手法实施盗窃。笔者在翻检清代档案时,无意间找到乾隆年间与丢包诈骗有关的三件奏折档案,其中朱批奏折两件、录副奏折一件,所描述的丢包诈骗手段与现在如出一辙,地方大吏不断要求加重对丢包诈骗的处罪。
一、云南巡抚张允随奏请对“丢包诈骗”加重处罪
乾隆五年(1740)三月二十五日,云南巡抚张允随奏报云南元江等府、县拿获丢包贼犯三起。张允随在奏折中描述了丢包诈骗的手段:“或二三人为一起,或四五人为一起,分布道路,窥伺孤单行客,即将石块裹作包裹,佯为坠失,以诱行人拾起。如堕其陷阱,即肆行搜攫,或行人不顾,其伙贼即假作行客,将包捡拾,故绐见者商同剖分,因而丢包之贼即赶上搜查。伙贼先将自己行李任其检视,后将行客囊槖帮同验看,见有银两,仍佯言并非所失之物,即代为捆束而去,不知所有银物已于搜查代捆时窃去矣。又或行客并未拾取,而数贼伙同拦截,指为拾包之人,硬将行李检搜,抢夺财物。”据张允随所称,丢包行骗之人并不是云南本地人,而是来滇谋生的内地汉民,“滇省地处边末,民情淳朴。近年以来,各省走厂之民络绎来滇,因而奸良混杂。有不法之徒勾结伙党,或用药迷人,或丢包攫财”。针对当时清廷还未有针对丢包行骗处罪的专门律例,“俱依掏摸律,照窃盗计脏科断。脏至十两以上,止于一杖;数至九十两,不过杖徒”。张允随认为,丢包行骗,“其立心之狡诈,设计之险毒”,其作案手段和所造成的危害比白昼抢夺尤为奸恶。因为“抢夺系明见其物,从而攫取,失主犹可喊救追捕。今丢包之贼,逞鬼蜮伎俩,将人密藏银物公然搜攫,且易于兔脱,不便立时就擒,又踪迹诡秘,朋类虽繁而无勾结之迹,流毒行旅,情罪可恶!”如“仅照窃盗科断”,处罚太轻,“实不足以蔽厥辜”,题请“照抢夺律,不计脏杖徒,重者加窃盗罪二等,刺面;三犯满贯,亦照例拟绞;杀伤人者拟斩,均分别立决、监候。店家知情容留者,照为从减等治罪”(1)云南巡抚张允随.奏为请严定丢包攫财恶贼治罪之例事:乾隆五年三月二十五日[A].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4-01-01-0058-036.。
“窃盗”与“抢夺”是不同的两种罪行,处罪不同。所谓“窃”,即“乘人所不知而暗取之,曰窃”。清律:“凡窃盗已行而得财,以一主为重,并脏论罪。为从者各减一等。初犯并于右臂膊上刺‘窃盗’二字,再犯刺在左小臂膊,三犯者,绞监候。掏摸者,罪同。”“窃盗”因“其所谋所行,皆系为窃,未有拒捕杀伤人之意”,科罪较轻。“盗窃之罪,轻于抢夺,以其心犹畏人也”(2)(清)沈之奇.大清律集解附则:卷之十八:刑律:贼盗:窃盗[G]//大清律辑注:下.怀效峰,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而所谓“抢夺”,释义为“出入不意而攫之曰抢,用力互争而得之曰夺”,对其科罪重于“窃盗”,“抢夺之罪,介于强、窃之间”(3)(清)沈之奇.大清律集解附则:卷之十八:刑律:贼盗:白昼抢夺[G]//大清律辑注:下.怀效峰,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而所谓“强”,即“强劫”,其与“抢夺”的区别为:“人少而无凶器,抢夺也;人多而有凶器,强劫也。”“强劫”及“强盗”,清代法律对“强盗”罪处罪最重。因强盗通常是“持械攻劫”,因此“论盗莫重于强”,对其处罪,“凡强盗已行,而不得财者,皆杖一百,流三千里。但得财者,不论首、从,皆斩”(4)(清)沈之奇.大清律集解附则:卷之十八:刑律:贼盗:强盗[G]//大清律辑注:下.怀效峰,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清律对“抢夺”的定性和科罪为:“公行白昼,不畏人知,有类于强;人既不多,又无凶器,尚近乎窃。故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不计脏数,即杖一百,徒三年,轻于强而重于窃。”(5)(清)沈之奇.大清律集解附则:卷之十八:刑律:贼盗:白昼抢夺[G]//大清律辑注:下.怀效峰,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张允随奏请对“丢包诈骗”的处罪由“窃盗”改为“抢夺”,并强调“照抢夺律,不计脏杖徒,重者加窃盗罪二等,刺面”,是因为“窃盗脏九十两,亦是杖一百、徒三年,倘抢夺脏多,反轻于窃矣,故计脏重者,加窃盗二等科之,以一主为重,并脏论罪,如脏八十,窃盗是杖九十、徒二年半,抢夺加二等,是杖一百、流二千里,谓之加二等计脏重于抢夺本律”,意在加重对“丢包诈骗”处罪(6)(清)沈之奇.大清律集解附则:卷之十八:刑律:贼盗:盗窃[G]//大清律辑注:下.怀效峰,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二、江苏按察使崔应阶奏请加重对“丢包诈骗”的处罪
对张允随的奏请,乾隆帝朱批“该部议奏”。惜未能查检到刑部议奏的相关档案,但从另外一件档案,即近二十年后的乾隆二十三年(1758)十一月二十二日,江苏按察使崔应阶奏请“严丢包贼匪之例,以靖地方而安行旅”的奏折中可看出,对张允随所题请,清廷并未采纳。
与张允随将丢包诈骗之犯指为“窃盗”不同,江苏按察使崔应阶则将其定为“贼匪”。“贼”与“盗”有着本质的不同,处罪也不一样,“杀人曰贼,窃物曰盗。贼者害也,害及百姓,故曰贼;盗则止于一身一家、一处一事而已。事分大小,故罪有轻重”(7)(清)沈之奇.大清律集解附则:卷之十八:刑律:贼盗:强盗[G]//大清律辑注:下.怀效峰,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显然,与张允随所请相较,崔应阶所题请对“丢包贼匪”的处罪要更重。他认为:“此等贼匪情状险狡,谋骗不遂,即加强夺,且习久手辣,则流为老爪贼类,最为行旅之害。而向来办理成案,仅照诓骗财物计脏,准窃盗论,免刺。”(8)江苏按察使崔应阶.奏为定丢包藉词调取赀财匪贼请严律例事: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A].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4-01-01-0226-015.由此可以看出,乾隆五年(1740)云贵总督张允随奏请对丢包诈骗案犯“照抢夺律,不计脏仗徒,重者加窃盗罪二等,刺面;三犯满贯,亦照例拟绞;杀伤人者拟斩,均分别立决、监候”的意见,清廷并未采纳。
对“丢包诈骗”的手段,崔应阶描述为:“纠约伙党,矙知孤单行客带有赀财,先令甲贼与客结伴偕行,乙贼预取碎石、土块等项,假作银包弃置路旁,迨甲贼与客同至瞥见,以路遗银两诱同行客拾取,乙贼旋向寻问,甲贼谬称未拾,暗将假包调换真银,付还行客后先行,及至查出假包,而各贼已先后遁逸。”他认为“贼匪”实施丢包诈骗,“虽由行客贪拾遗物,堕其术中,但藉词搜查,公然调取,按其情形,实与抢夺无异”。而在判决时,并为照“抢夺”科罪,而“仅准窃盗脏治罪,殊觉情重法轻。且得免刺,再犯累犯,无所稽考,尤不足以示惩创而杜爪贼之源”。鉴于此,崔应阶奏请“嗣后拿获丢包贼犯,审实,均照白昼抢夺人财物例分别治罪、刺字。行令地方文武员弁,选差兵役,留心稽查,遇有丢包贼匪,即行拿解究治。事主具报到官者,先行通详勒缉,不得隐讳。倘有贼至满贯,及拒捕杀伤人者,亦照抢窃等案扣限查参。庶办理严密,匪徒知所儆惕,亦安缉行旅之一策也”(9)江苏按察使崔应阶.奏为定丢包藉词调取赀财匪贼请严律例事: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A].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4-01-01-0226-015.。
清律对白昼抢夺的处罪有一个不断加重的发展变化,在顺、康年间,为“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者,不计脏杖一百,徒三年。计脏并脏论重者,加窃盗罪二等。罪止杖一百、流三千里。伤人者,首斩;监候。为从,各减为首一等,並于右小臂膊上刺‘抢夺’二字”。后将律条改为“凡白昼抢夺三犯者,拟绞立决。如抢夺、窃盗各不及三次者,免其併拟,各照所犯之罪发落”。雍正十二年,再次对律条作出修改,改为“凡白昼抢夺人财物至一百二十两以上者,照窃盗满贯律,拟绞监候”(10)郭成伟.大清律例根原:卷61:刑律:贼盗:中[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与对张允随的题请相似,乾隆帝同样于崔应阶的奏折上朱批“该部议奏”,仍未能查检到刑部议奏结果的相关档案。
三、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报拿获“丢包诈骗”之犯及处罪意见
张允随、崔应阶的奏折,均是提请加重对丢包诈骗的处罪,并不是对具体案件的审拟。乾隆三十三年(1768)七月四日,直隶总督方观承所奏报“拿获丢包积匪李斌等审拟事”折,则包含有对“丢包诈骗”团伙作案情形的描述以及对人犯的定罪、处罪,且从审拟情形看,似乎崔应阶的奏请得到了清廷的批准。
该“丢包诈骗”作案的手段,与张允随、崔应阶所描述的基本相同。据方观承奏称:“直隶保定迤南大路,每有一种丢包贼匪,矙知旅客带有赀财,以一贼先作客商,与之结伴同行、同住,另有一伙贼数人阴随其后,乘晓行人稀之时,伙贼预以他物作为银包,装入被套,携弃前途。其与客同行之贼经过,瞥见拾获,声言被套内得有银两一包,许与分用。于时,贼伙数人逸自前途返回寻觅,口称遗失行李,有人见其藏匿银包,欲行搜查。同行之贼伪为主持,将自携行装先给搜查,次及客商。有数贼从旁扰涃间,便已暗将他物顶换,银两入手,于是诡称搜寻无获,各皆托词逸去。待客商检视,知竟而贼已远飚矣。”(11)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报拿获丢包积匪李斌等审拟事: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四日[A].录副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3-1255-034.
“丢包诈骗”团伙及作案的基本情况。方观承奏称:“据邢台、唐山二县及顺德营千总、兵役在邢台康庄铺地方缉获贼匪张栾、赵大、孙演、李二,经邢、唐二县审明,该犯均系徐州府铜山县人,辗转究出李斌、刘玉公等十八名,住居江南砀山、丰县等县并山东淮州。随差役前往缉拿,除刘玉公一犯,经原籍丰县等县拿获,解至肥乡县脱逃,潜回原籍自缢身死,业经丰县验明详报外,计先后获到李斌、赵二、吕三、宋海四、彭实、邹之、岳西等七犯,尚有程文钺、姜三、王义、乔玉、姜二、郭四、黄芮、高贵、王二、张栾等十人未获,将现犯审拟,由府、司勘验前来”。方观承提犯亲审,究出这22人的丢包诈骗团伙,自乾隆二十七年(1762)至乾隆三十二(1767)间,五年时间内作案多起:(1)乾隆二十七年四月初二日,李斌、赵大伙同姜三、姜二、王义五人,“在赵州地方顶窃事主张继宗、陈正道一案,计脏二百六十两”;(2)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十八日,李斌、赵大伙同吕三、程文钺、姜玉、王二、乔玉、姜二,跟随刘玉公,同伙九人,“在唐山县地方顶窃事主王永勋一案,计脏二百五十五两”;(3)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由张栾起意,伙同赵二、郭四,同伙三人,“在内邱县地方顶窃事主王来福一案,计脏一百二十五两”;(4)乾隆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李斌同邹三、宋海四、彭实,听从程文钺并王义、黄芮,同伙七人,“在赵州地方顶窃事主陈自能、刘载周一案,计脏四百九十两,并玉石等物”;(5)乾隆三十一年五月十四日,赵大跟从刘玉公及高贵,同伙三人,“在唐山县地方顶窃事主宋贵一案,计脏四十八两七钱”;(6)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卅日,由李斌起意,伙同邹三、赵二、王二,同伙四人,“在望都县地方顶窃苏二魁一案,计脏三百两”;(7)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初七日,宋海四同程文钺、吕三,听从刘玉公,同伙四人,“在定州地方顶窃事主贾作敬一案,计脏一百四十八两”;(8)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由孙演起意,伙同张栾、赵大、李二,同伙四人,“在唐山先地方顶窃事主张可一案,计脏四十二两二钱”(12)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报拿获丢包积匪李斌等审拟事: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四日[A].录副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3-1255-034.。
该“丢包诈骗”团伙有以下特点:第一,团伙的规模较大,达到22人。第二,异地作案。诈骗团伙成员主要来自江南和山东二省,作案地点则在直隶境内,他们假扮行客,具有欺骗性。第三,这是一个组织松散的诈骗团伙,团伙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领头人,每次作案由一二人起意,成员构成最少3人,最多达9人。第四,频繁作案。五年间,审实的案件就达8起,仅乾隆三十一年,一年内作案达3起。第五,诈骗所得数额巨大,通常每次能达到一二百两,最高一次达四百九十两,最少的一次也有四十二两二钱。第六,“其丢包顶包等诡计,大概均属相同”。另外,张栾曾于乾隆二十七年,在山东茌平县丢包事犯,后又间从赵二,于乾隆二十八年,在江南宿州丢包事犯,被官府拿获,乾隆三十年,逢恩大赦,释放回籍。
方观承审理此案后,将该案定为“劫掠”,称“其顶包行径略同窃贼,而结伙多人,欺行客于旷野,攫取财物,实与劫掠无异。”因此,对拿获的11名丢包诈骗案犯,分别首犯、从犯,分为四个等次,以四种不同律例处罪:
第一,李斌、张栾二犯,“照白昼抢夺人财物,脏至一百二十两以上拟绞例”,分别处以“请旨正法”和“绞监候”。其中张栾一犯,于犯事释放后牵涉2案,其中乾隆三十年十一月三十日顶窃事主王来福一案,由其起意,获脏银一百二十五两,系为首满贯,又参与乾隆三十二年九月十二日顶窃事主张可一案,“应照奸匪伙众丢包诓取财物,照白昼抢夺人财物,脏至一百二十两以上拟绞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而李斌一犯,在上述8起诈骗案中牵涉4案,其中乾隆三十一年八月卅日顶窃事主苏二魁一案,由其起意,诓银三百两,为首满贯,另外参与顶窃张继宗、王永勋、陈自能3案,计脏达一千三百余两,“合照奸匪伙众丢包诓取财物,照白昼抢夺人财物,脏至一百二十两以上拟绞例拟绞。但该犯邀结伙党,诓取财物多案,脏至一千二百余两,实为奸匪之尤,未便仍稽显戮,相应请旨,即行正法,并出示犯事地方,遍行晓谕,以昭炯诫”。
第二,赵大一犯,“比照甘省马得鳌案内满贯、为从数次拟绞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赵大涉案4起,虽然不是首犯,均系为从,但其诓取财物多案,其中参与顶窃张继宗、王永勋二案,脏俱满贯。马得鳌一案,是乾隆三十二年正月间,清廷拿获以甘肃平凉府盐茶厅回民马得鳌为首的百余人盗窃团伙,经审理,查明马得鳌为盐茶厅徐帽儿庄强人,组织起一个百余人的盗窃团伙,让其团伙成员至江南等省盗窃,自己则通过控制团伙成员的家人,坐地分赃。该团伙行窃十余年,作案无数,脏私累累。陕甘总督吴达善拟定,马得鳌“照强盗窝主,身虽不行,但分赃者斩律拟斩立决”,对外出行窃首犯“依窃盗脏至一百二十两以上律拟绞”,对其余行窃从犯“照回人结伙三人以上例,发往伊犁给与种地人为奴,照例刺字”(13)陕甘总督吴达善.奏为遵旨审明巨匪马得鳌等盗窃各案按律定拟事:乾隆三十二年三月初六日[A].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4-01-01-0271-029.。三法司核议后,认为行窃从犯“脏皆逾贯,非寻常窃案可比,若仅律以为从,不足蔽辜”,提出“应照行窃满贯、分赃在一百二十两以上者,亦应照为首例拟绞监候”,获乾隆帝批准(14)陕甘总督吴达善.奏为审明马得鳌案内伙犯木矬子等行窃案按律定拟事:乾隆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A].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4-01-01-0272-008.。直隶总督方观承拟定对赵大“比照甘省马得鳌案内满贯、为从数次拟绞例拟绞监候,秋后处决”,无疑是加重量刑。
第三,赵二、吕三、宋海四、邹三、彭实、孙演、李二等七犯,“均为从一二次不等,均属积匪,危害地方,应俱发往黑龙江,给予披甲人为奴,先行刺字”。《大清律例·刑律·杂犯》内开:“积匪、猾贼危害地方,审实,不论曾否刺字,照发遣之例发边卫充军”(15)(清)沈之奇.大清律集解附则:卷之十八:刑律:贼盗:杂犯[G]//大清律辑注:下.怀效峰,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处罪远重于一般窃盗。
第四,岳西一犯,“应照不应重律,仗八十,递会原籍,严加管束”。其虽曾入伙随行,旋即先自退出回家,并未随同伙窃,应此照“不应重律”科罪。《大清律例·刑律·杂犯》规定:“凡不应得为而为之者,苔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16)(清)沈之奇.大清律集解附则:卷之十八:刑律:贼盗:杂犯[G]//大清律辑注:下.怀效峰,李俊,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这是对一些轻微犯罪,找不到相应的处罚依据,不处罚又不合情理,而立此一律。
上述各犯名下“俵分花费之脏,行令原籍查明家产变解”。其余未获之犯,“查明年貌,知会江南、山东及邻近各省督抚,饬令地方官并各原籍,一体缉拿务获。畏罪自缢之刘公玉,应毋庸议”。(17)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报拿获丢包积匪李斌等审拟事:乾隆三十三年七月初四日[A].录副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3-1255-034.
仍未能查检到乾隆帝和三法司是否批准方观承拟定的处罪意见的相关材料。
四、结 语
上述三件档案所呈现的乾隆年间“丢包诈骗”,其诈骗方式均大同小异:由数人组成团伙,以“丢包”为手段,设下陷阱,引诱行客,达到诓取行人银物的目的。这一诈骗方式,在乾隆年间已从内地蔓延到边疆,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甚至形成了二十余人的团伙,在直隶各地作案数其,所获脏银数量巨大,受害者众,社会危害很大。地方大吏不断题请加重对“丢包诈骗”的处罪。乾隆五年(1740)云南巡抚张允随奏请对“丢包诈骗”处罪原“依掏摸律,照窃盗计脏科断”,改为“照抢夺律,不计脏杖徒,重者加窃盗罪二等,刺面;三犯满贯,亦照例拟绞;杀伤人者拟斩,均分别立决、监候。店家知情容留者,照为从减等治罪”,(18)云南巡抚张允随.奏为请严定丢包攫财恶贼治罪之例事:乾隆五年三月二十五日[A].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4-01-01-0058-036.似乎未得到清廷的批准。乾隆二十三年,江苏按察使崔应阶奏请“照白昼抢夺人财物例分别治罪,刺字”(19)江苏按察使崔应阶.奏为定丢包藉词调取赀财匪贼请严律例事: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A].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号:04-01-01-0226-015.。至乾隆三十三年,直隶总督方观承在审拟李斌等“丢包诈骗”案时,对诈骗团伙的主要成员即“照白昼抢夺人财物例”拟罪。三件奏折档案揭示了这一时期清廷不断加重对“丢包诈骗”处罪的发展变化。不知是不是因处罪较重,起到了震慑作用,“丢包诈骗”得以大幅减少,乾隆三十三年之后与丢包诈骗相关的档案史料,仅查到一件,即光绪二十三年七月保宁府南部县衙“为尽法惩治拦路丢包诓骗财物悟惑愚民事”档案(20)南部县衙档案[A].朱批奏折.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无档案号,缩微号:011300671073.。
现代法治社会下,对包括“丢包诈骗”在内的诈骗的处罪更趋法治化,但这一古老又简单的诈骗手段历经数百年,仍不断发生,危害社会,其花样虽有翻新,但基本的手段并无太多改变。认识到这一点,有助于现今人们更好地对其加以防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