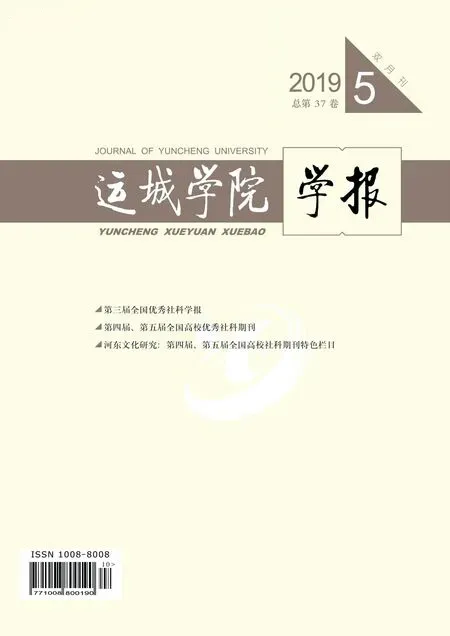记忆与历史困局中的西西弗斯式救赎
——朱利安·巴恩斯的《终结的感觉》
王 乐
(山西大学商务学院 外国语学院,太原 030031)
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s,1946-)是当今英国文坛“三巨头”之一。其作品多采用打破传统模式的实验手法,风格多变,有文坛“变色龙”之称。其作品产量颇丰,三获布克奖提名。《终结的感觉》是他2011年荣膺该奖的力作。小说共两章,叙述者托尼·韦伯斯特,一个平凡无奇的小人物,分别站在两个不同的人生节点回忆过去、叙述过往,结果却把读者也把自己带入了记忆及其个人史的迷局,在那里所有探求真相与真我、弥补与救赎的努力都举步维艰。
该小说延续了作者一以贯之地对记忆与历史真实性的怀疑态度,以及对叙事在自我认知与自我身份建构过程中的中介作用之关注。显然,作为一位活跃于后现代语境下的优秀作家,巴恩斯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同时,在探讨记忆、历史与自我认同、道德责任之间的正负关系时,流露出现代作家典型的人文关怀,表达了对生活在“流动时代”(1)此处借用了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的“流动”的概念。他认为流动性是现代性生活的重要特征,流动的生活是一种生活在不确定环境下的缺乏稳定性的生活。有形或无形的事物普遍处于流体状态,不断终结又不断开始,一遇外力作用便会改变外在形态。的人们,特别是老年人生存困局的关切。在后现代语境下,真实、永恒和确定性已成虚妄,人凭借记忆确认自我的存在、完成自我认同,依靠历史来解读他人与世界,但最终却发现记忆和历史不过是自己制造的幻象。在修筑与破拆、建构与解构、逃避与担当、探求真相真我与难得糊涂之间陷入永恒的困局。托尼这个深陷人生困局的小人物,在经历了追忆、探寻、审视、痛苦和反思之后,似乎终于有了一丝清醒和担当,有了正视伤害和赎罪的勇气,这也使他平庸懦弱的一生依稀有了一抹西西弗斯的色彩。巴恩斯一边质疑和消解真实、永恒与确定性,一边提醒读者人生中尚存“一段漫长的暂停时间”,足以用来思考自己的过去与人生[1]63,由此,在永无终结的记忆与历史困局中,在“你永远不会明白”[1]157的绝望中,作者小心翼翼地留下一点希望,使生活在“浩大的动荡不安”[1]163中的人们获得一丝向死而生、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
一、记忆困局——无法确认的自我与道德责任链
自古希腊圣哲苏格拉底振聋发聩的一问,“我是谁”便成为两千多年来人类苦苦追索的三大哲学问题之一。自我认知是人类永恒的需求。在人类认识自身、反思自身并最终完成自我认同的过程中,“记忆是最深刻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参照”[2]1。“没有记忆,人就无从知晓我之为我的缘由和过程,更无法探究我之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2]1。可以说,记忆是个体了解自己人生轨迹的途径,也是形成自我认同的基石。回忆对老年人来说尤为重要,他们开始清算自己的一生,完成最终的自我道德评判。虽然记忆在自我认知、身份认同以及自我道德评价过程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在巴恩斯看来,随着时间的流逝,人生中的人证、物证越来越少,虚假记忆不断增加,自我的真面目也在扑朔迷离的记忆中陷入一种求而不得的永恒困境。
小说处处透露对记忆准确性的质疑。小说开篇便是叙述者托尼记忆中看似毫无联系且“次序不定”的六个片段,其中甚至包括隐喻性极强的“宽广黝黑的河流”[1]3以及完全臆想出的艾德里安自杀的画面。连他自己也毫不隐晦地承认“你最后记得的并不总是你看到的”[1]3。这些记忆碎片几经扩展、拼贴,最终成为一件完整的“百衲衣”[1]114。托尼的记忆里不仅有碎片化的、臆想的画面,更多的是他在当前情感、动机和目的的驱策下主动遗忘、歪曲的内容和不断强化的不愉快经历。当内心充满屈辱、愤怒与恨意时,托尼或把维罗妮卡“抛在脑后”[1]70、赶出记忆,或将其丑化。在早期的回忆中,他对维罗妮卡性爱多于情爱,后者则处处挑剔,分手前故作矜持,分手后投怀送抱,事后却将床事斥为“强奸”[1]40。与她的相处“不过是一长串的尴尬和难关”[1]83。至于在维罗妮卡家的那个周末则简直不堪回首,女友父兄不得体的玩笑和倨傲的态度令其自尊心大受伤害。这些记忆在托尼后来的生活中反重复出现、不断强化,最终让自己深信不疑。在与昔日恋人分手,特别是恋人迅速移情别恋自己好友之后的很长时间里,托尼需要用遗忘和丑化来宽慰自己、疗治创伤,让自己相信与一个性格强势、心机深沉,甚至酒后乱性的女性分开并不值得痛苦。与此同时,在一次次鲜有变化的回忆中,托尼为自己构建了一个温和、保守、木讷的受害者形象,甚至善良到寄明信片给艾德里安表示衷心祝贺,并在一封“得体的回信”[1]46中祝他好运。作为受害者,“我”自然而然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是好的、无辜的、善良的、值得同情的,而加害者必然是坏的、该遭到道德拷问的。“我”不可能是造成他人不幸的责任链条上的一环,因而不必为恋情的告吹、维罗妮卡日后的艰辛、艾德里安之死以及他智障的孩子负责。
多年后,风烛残年的托尼因福特夫人的遗嘱纠纷与维罗妮卡再次产生交集。几轮博弈之后,他得到了当年给艾德里安的回信复印件。在信中,年轻的托尼极尽挖苦讽刺之能事,谩骂中伤维罗妮卡和艾德里安,甚至诅咒他们的后代。这个确凿的证据迫使托尼重新面对过去那个心胸狭隘、恶毒、刻薄的自己,而在大半生的时间里这封信是他记忆的禁区,从未被触及。在新的证据下,那段为了自我保护,为了不必直面丑陋的自我,不必遭受道德谴责而屏蔽掉的记忆复活了,多年来用以自欺欺人的记忆之城和善良无辜的自我也随之坍塌。不可思议的是,在数度交往过后,在愧悔与同情的复杂情绪中,托尼竟对维罗妮卡情愫暗生,并且这种“新的情感状态重新打通了堵塞的神经通路”[1]131,他开始忆起早已遗忘的与维罗妮卡有关的美好细节,这些细节情爱多于性爱:她秀发低垂,翩翩起舞;那个“难堪”的周末,她送他回房时曾对他低声耳语。再次忆起塞文河观潮,被记忆抹去的维罗妮卡也出现了。那晚,月色溶溶,两人十指相扣,谈论着世事的不可思议。此时,托尼自己也意识到过去头脑中不堪的回忆以及“我”与维罗妮卡的关系,这多年以来“我”一以贯之的印象,即是自己当时所需。“那颗年轻的心遭到背叛,那副年轻的身体被肆意玩弄,那个初出茅庐的青年被屈尊对待”[1]13,因而“可能带有私心”[1]30。
“回忆总是处在当下的命令之下。当前的强烈情感、动机、目的是回忆和遗忘的守护者。它们来决定哪些回忆对个人在当下的时间点上是可通达的,哪些不能被支配。它们还给回忆涂上不同的价值色彩,有时是道德上的厌恶,有时是怀旧的美好。”[3]64在托尼的记忆中,不是情随事迁,而是事随情变。托尼对过往的记忆随着心境与情感的改变,道德判断的变化而发生巨变。曾经的记忆里,只有维罗妮卡的挑剔、冷淡、拒绝和伤害,这似乎也是二人分手的主要原因。而今“爱抚、温存、坦诚、信赖”,这些从未被忆起的美好悉数登场。原来,一直以来在感情里逃避抗拒的是托尼,他害怕,“害怕怀孕,害怕说错话做错事,害怕自己应付不了极度的亲密”[1]128。此刻的迷恋、愧悔与想要弥补的愿望唤醒了曾经被屏蔽的对爱的回忆,也让年老的托尼终于可以直面自己的“恶”和维罗妮卡的“善”。而直面也意味着对过往责任的认定与承担。是自己的胆怯、懦弱与平庸导致了分手;自己的刻薄与诅咒深深伤害了艾德里安和维罗妮卡,甚至于后者的孩子。
托尼说当遗忘发生的时候人的反应各有不同,假装无知、听之任之或积极地搜集资料以为佐证,而所谓的资料也只是人类记忆的书写,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了遗忘、扭曲与篡改。然而“我们的大脑不喜欢被模式化”,在无法入眠的漫漫长夜,那些错置的事实会倏忽而至,让“舒舒服服地走向衰亡的企图彻底落空”[1]122。由此,在记忆中人似乎堕入了一种永恒的困局:积极进取却劳而无功,想得过且过却无法自欺欺人地了此一生。托尼一生平庸软弱、自我麻痹,但年老的他终于在人生最后阶段拥有了探求真相的执着和承担责任的勇气。“那一瞬间,我明白了我如此执着于要回日记的另一个原因。那日记就是证据;它是——它可能是——确凿证据啊。它可能打破记忆单调的重复。它可能会开启一些新的东西”[1]84-85。而新记忆的开启也是自我救赎的开始。托尼通过回忆与再回忆、审查与修正,颠覆了长久以来记忆里那个温良无害的自己,遇见了那个自卑、善妒、狭隘、冷漠、胆怯、平庸的青年、遇见了善于遗忘、自我麻痹、得过且过的自己,最终将过去与现在的自己合而为一,现在的“我”依然要为曾经的“我”造成的伤害负责。这样的认识固然会带来痛苦,但在人生即将终了之时能够更清醒地认识自己,勇敢地面对过去,并为曾经的过错努力弥补,这对于自身来说也不失为最后的安慰和救赎。
二、历史困局——文本化的历史与无可抵达的真实
在现代英语中,“历史”是一个含义暧昧的词,它同时具备彼此相关却有本质区别的两层含义。一方面,它可以指称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和人类的全部经历,即“过去”或“历史事件”。另一方面,它又可以指人对“过去”的记忆、解读、记录、呈现与讲述,或曰“历史编纂”[4]1,也即历史文本(2)后文中的“历史”均指历史文本。。“过去”是我们无法直接触摸的存在,“我们只能通过各种文本来了解过去”[5]16。不通过语言,过去就无法被知晓、记忆、理解和讲述。在后现代语境下,语言与外部世界的脐带被无情切断。语言存在于一个自成一体的封闭空间,与外部世界全无干系。没有任何文本可以指涉过去或客观世界。以语言和言语为载体的历史也只是与文学作品没有本质区别的文本。没有所谓的客观历史,只存在人的主观建构。历史已无法引领人们对过去一窥究竟。深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的巴恩斯在小说中借托尼和艾德里安之口表达了自己对历史的态度:“不可靠的记忆与不充分的材料相遇所产生的确定性就是历史”,它既是“胜利者的谎言”,也是“失败者的自欺欺人”[1]18,更是寻常人讲述的故事。《终结的感觉》主要是托尼自述的个人史,其间还夹杂着诸多对他人历史的评说和他人自述的个人史。而在反复叙述中,很多人与事均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目。
托尼与前妻玛格丽特初遇时,托尼为自己编纂了没有维罗妮卡的历史,他把后者“彻底从人生记录中抹去”,假装安妮才是他的第一任女友,“向别人这样讲述我的过去似乎更容易些”[1]76。托尼脆弱的自尊和耻辱感让他对维罗妮卡和那段旧情缄口不言。直到婚后,他自我感觉渐好,对夫妻关系充满信心,才将真相告知妻子,并且故意“言过其实”,“使自己听上去更像个被愚弄的人”[1]81。旧日恋情留给托尼的是屈辱和痛苦,而“我们的恐慌和痛苦只有靠安慰性地编造功夫缓解;我们称之为‘历史’”[6]258。托尼为自己编纂历史,在这段历史中“软弱改称为美德……无法报复的无能变成善良;懦弱变成谦卑”[7]180。这样的历史美化了自己,丑化了他人。
艾德里安在遗书中也记录了其个人史,而那段文字也成为他人了解其自杀缘由的直接证据。他在遗书中将自杀说成是放弃一份“无人索求的礼物”,“是合乎道德与人性职责的”[1]52。这样的解释严肃、理性、充满哲思,符合艾德里安的一贯风格,也让他的死有别于罗布森“肮脏流俗”的自杀[1]52,是“一流的自杀”[1]53。这样的文字让自杀成为一种哲学思考和行动,成为主动介入人生的勇敢行为,让托尼和其他同伴时过境迁依然对艾德里安充满敬意。而《剑桥晚报》刊登的消息则把他的自杀定性为“青年才俊”在“思维紊乱”[1]53中的疯狂行为。托尼显然对这种论调不屑一顾。他认为这不过是国家的权力话语,是当权者维护自己价值观的说辞,他们害怕艾德里安对自杀的理性解释会破坏他们所规定的生命的本质与价值[1]53。在托尼的评说中,既看到福柯的“话语”、葛兰西的“霸权”,也有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在官方的报道中,以语言和言语为依托的历史俨然成为权力运作的场域。而随着托尼掌握的线索越来越多,他终于发现艾德里安的自杀既不像他自己所解释的是“庄重地拒绝一件既有的礼物”,也不是验尸官所谓的精神失常,他只是“害怕过道里的婴儿车”[1]155。假如事实如此,那么艾德里安的遗书无疑是对自身懦弱的掩饰、对责任的推卸。
与艾德里安逻辑缜密的遗书不同,罗布森留给妈妈的遗书中只有“妈妈,对不起”,而对于自杀的原因这一重要信息则隐去不提。对于六十年代的高中生来说,让女友怀孕将令整个家庭蒙羞。年轻的罗伯森无法承担这样的后果而选择轻生,至死也没有勇气说出实情。这一方面是出于怯懦,另一方面也可能是为了保护家族荣誉和女友颜面。而在“我”讲述的罗布森的个人史和听来的小道消息中,他的死只是一个无名小卒搞大了女友的肚子,然后上吊自杀了。其间,既有“我”对罗伯森的评价,亦有“我们”最关心的细节。这样的历史叙述符合“我”的身份以及性格特征。当时的托尼年轻善妒,缺乏对死亡及生命的反省与尊重,热衷于谈论性爱。当听说平凡无奇的同龄人罗伯森不仅有女朋友,还把她肚子搞大时,居然感到愤愤不平,甚至是嫉妒。而作为官方代表,校长在晨会宣布罗布森的死讯时则将其去世喻为“青春的花朵溘然凋零”,说“他的离开是我们整个学校的损失”[1]14,对于学生们最好奇的罗伯森的死因却只字未提。每个人的历史叙述受到自身立场态度等的影响。作为一校之长,在学校晨会这个正式场合宣布某位学生的死亡,他必须使用严肃庄重的措辞,而对于罗布森“把女友肚子搞大,在阁楼上吊自杀”的个人史则有意省略了,而比喻的使用令这段挽词竟然有了些许悼亡诗的凄美。至此,罗布森的死有了正剧、悲剧和讽刺剧多个版本。正如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海登·怀特认为的那样,历史即想象,历史作品就是“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为表现形式的话语结构”[8]2,它可以用各种方式进行书写。多年以后,年老的托尼对生死有了更深的感悟,对罗布森女友的命运亦抱有更深的同情。此时的他若再次讲述往事,定然又是另外的版本。
生活在后现代语境下的人们其实也像托尼一样,一边借助历史书写记录和理解过去与世界,一边却在自己建造的文本世界中迷失,建构的同时又不断解构,无可救药地陷入永不止歇的困境与轮回。同个体记忆一样,对个人历史的叙述并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不可避免地会与他者和社会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对伤害行为避重就轻的叙述、缄默和美化都是对被害者的二度伤害,因而具备了道德的向度。在巴恩斯笔下,不同的历史版本在道德层面的价值并不相同,这有别于怀特的以各种方式书写的历史在价值上是完全等同的观点。托尼不断修正自己讲述的历史,不断审视自己及他人讲述历史的方式,这一过程本身就具有了道德层面的意义。在永无终结的困境与轮回中,年老的托尼最终选择拒绝只“追求混沌的享乐,而拒绝考虑其他选择”[1]10的犬儒主义生活方式,不再像过去那样在自己制造的幻想里自欺欺人。托尼对历史的重新理解、审视和不断修正不仅是对自我的救赎,同时也是对他人的弥补。尽管探求真相的努力一再失败,但在一次次修正历史讲述的过程中,托尼不断明确自己在历史长河中的定位以及在责任链条中的地位,重建了道德责任感,避免在“平庸之恶”(3)参见汉娜·阿伦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中了此残生。
三、结语
《终结的感觉》是在回忆中写就的一部个人史。巴恩斯在小说中探讨了记忆、历史与自我认同和道德责任之间关系,在质疑记忆、历史真实性的同时对后代语境下平庸迷茫的小人物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记忆与历史两大问题上,巴恩斯虽深受后现代思潮影响,但并不是极端的虚无主义者,他“徘徊于十字路口”[9]386,一方面不再笃信历史的权威和真实,另一方面却依然寄期望于历史,努力寻找逼近真相的途径,肯定了回忆、再回忆与历史叙述的价值。他相信就像托尼一样,也许“从来不明白”,甚至“永远不明白”[1]157,但人总有办法在岁月的迷宫中一步步逼近真相,在对记忆和历史的审视与修正中认识自我、承担责任,完成自我救赎。巴恩斯眼里的记忆和历史虽然令人失望,但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人必须相信客观真实可以抵达,如果不这么做“我们就完了,我们就陷入模棱两可,我们就对不同版本的谎言不加分辨同样看待,我们就在所有这些困惑面前举手投降”[7]262。记忆和历史不是绝对真实,但唯有相信真相的可知性才能获得存在的场域和意义,才能拥有西西弗斯式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