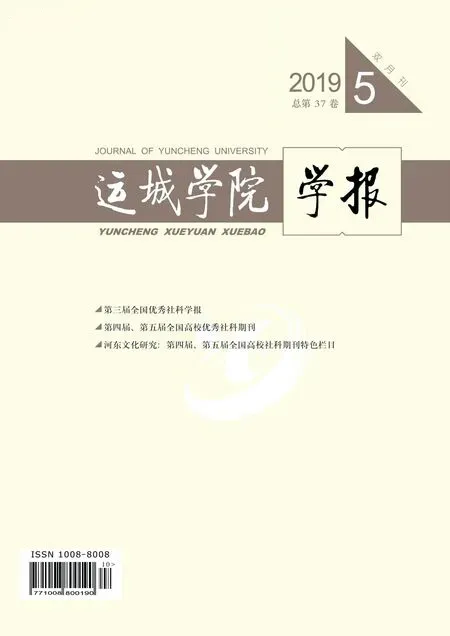论明代山西作家的三晋文化品格
郗 韬
(晋中学院 文学院,山西 晋中 030619)
明代山西,虽无执全国文坛牛耳者,但还是出现了一些具有较高创作成就和一定影响的作家。《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收录其作品或作品存目的常伦、薛瑄、任环、何东序、曹于汴等人,即可称为晋地作家中的翘楚。作家的创作,除了与时代风气、人生经历等因素有关外,也无疑与其生活的地域以及此地域独特的文化传统有较为密切的关系。黑格尔曾经谈论过民族精神和空间条件的关系:“‘助成民族精神的产生的那种自然的联系,就是地理的基础’,由地理要素构成的‘自然的联系’,也即文化生成的空间条件,是民族精神‘表演的场地’和‘必要的基础’”[1]192。自古以来,山西大地无疑是三晋文化产生的必要基础和重要的“表演”“场地”,而明代山西作家的作品,也自然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三晋文化任侠尚武、质朴务实、推崇隐逸等因素的影响。
一、明代山西作家创作概论
在众多的明代山西作家中,常伦、薛瑄、何东序、寇天叙、任环等人取得了一定成就。常伦,字明卿,号楼居子,山西沁水人,传世之作有诗文集《常评事集》和散曲集《写情集》。《常评事集》有赋五首、乐府二十一首、各体诗百余首、传赞等杂著数篇。常伦创作小令100余首,套数9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常伦诗歌既有“沙苑儿驹,骄嘶自赏,未谐步骤”[2]2423之弊,也有“气骨高朗,颇能自运”[2]2423之长。王士祯在《分甘余话》中对常伦的早逝深表惋惜,认为常伦“汗血方新而筋骨未就,秀而不实,殊可惜也”[3]228。常伦散曲质朴豪迈,部分散曲为“酒间度新声”之作,“悲壮艳丽”。王骥德《曲律》指出常伦散曲“多侠而寡驯”。明末名臣张铨全面评价了常伦的文学创作:“文学司马子长;诗宗李杜,上窥魏晋,多自得语;……尤工乐府小词,盛传泽沁间,伎儿优童咸弹弦出口歌之,至今不废,曰:常评事词也。”[4]83
薛瑄(1389-1464)是明代第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永乐进士,宣德中授御史。曾因触怒宦官王振被下狱,几至被杀。英宗复辟后拜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学士,致仕卒。谥文清。薛瑄在文学创作领域笔耕不辍,著述颇丰,诗文平正自然。《薛文清公文集》二十四卷,收录其诗文总计一千七百余篇。四库馆臣评价薛瑄道:“明代醇儒,瑄为第一。而其文章雅正,具有典型,绝不以俚词破格,其诗如《玩一斋》之类,亦间涉理路,而大致冲澹高秀,吐言天拔,往往有陶、韦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2]2293
猗氏(今运城临猗县)人何东序,字崇教,号肖山。喜作乐府古题诗,于明人中别具一格。历官徽州府知府,后巡抚榆林,官至都御史。何东序诗歌艺术价值较高,人称其“诗则开元、天宝,或间出晋魏杂体,故一时识者咸推毂,争上之”[5]586。任环,字应乾,号复庵,长治人。作品多有散佚,“其子孙搜求辑录,所得不及十之一”,即《山海漫谈》。“然就其存者论之,古文皆崭崭有笔力,且高简有法度”[6]5636。其中如《送萧西泉》、《朱蒲西》二序,《德风亭》、《滑县行馆》二记,《与王南崖》、《答王东台》二书,“皆绝非明人文集以时文为古文者,虽置之作者间可也”[6]5636-5637。诗作虽因“后人编次,失于删汰之过”,“而冗俗者多”,但也有如“槎泛星河秋作客,剑横沧海夜谈兵”[6]5636之类可观者。山西榆次人寇天叙,字子惇,号涂水。正德三年进士,授南京大理评事,迁宁波知府,擢应天府丞。武宗南巡,江彬等恃宠为虐,天叙力与之抗,民得不困。后以御寇功,擢刑部右侍郎。有《涂水文集》行世。明代后期解州安邑人曹于汴,平生“笃志正学,操履粹白。立朝,正色不阿,崇奖名教,有古大臣风”。其著作《仰节堂集》、《共发编》均为《四库全书总目》收录。高攀龙认为曹于汴“文足以定群嚣,明学术;诗足以畅天机,流性蕴”[6]5659,冯从吾指出曹“非沾沾以文章名家,而操觚自豪之士,无不退避三舍”。“于汴之诗文,亦在理学、举业之间,或似语录,或似八比。”[6]5659孙传庭(1593-1643),字伯雅,又字白谷,振武卫(今山西代县)人,著有诗文别集《孙白谷集》六卷,卷一至卷三为奏疏,卷四为杂著,卷五为诗,卷六为内、外传和奏疏。传世作品不多。有《四库全书》本《白谷集》存世。
二、三晋文化及其对明代山西作家的影响
三晋最初是指战国时的韩、赵、魏三国,此三国由春秋时之晋国分出,故被称为三晋。虽然当时的晋或三晋疆域都超出了现在的山西范围,但山西始终都是晋和三晋的主体部分,因此后世常用晋或三晋专指山西省。关于三晋文化、晋文化的含意,学者们看法不一。有学者指出:三晋文化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的三晋文化,从地域说,指三晋(韩、赵、魏)控制的范围:今天的山西省全部,河北省中部、南部,河南省北部,内蒙古中部,陕西东部。从空间说,从三家分晋到三晋的灭亡。广义的三晋文化,实际上是山西地方文化,从地域说,限于山西,从空间说,自古至今”。[7]38学者李元庆则指出:晋文化有广、狭两义的区分:“‘广义’的晋文化可以看作是对山西古代文化的概称或泛称”;“狭义”的晋文化是“关于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山西文化的一种指称,也就是关于晋国文化与魏、韩、赵三晋国家文化的统称或合称”[8]39。综合学者们的观点,笔者在此文中所讨论的三晋文化,以山西地域内自古至今的地方文化为主,同时涵盖了西周至春秋战国时代属于三晋文化范围内但在地域方面超出了当今山西地域的文化。之所以做此取舍,主要是考虑到此部分文化自形成以来也一直深刻影响着山西大地。总之,因地理位置和环境形成的尚武精神、发源于三晋大地的法家思想、质朴尚实的风气等文化特质,对山西作家的思想和创作有较大影响。
任侠、尚武精神一直是三晋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拼死救护赵氏孤儿的晋人公孙杵臼、程婴,无不具有侠的品质,为报智伯瑶知遇之恩多次刺杀赵襄子的豫让也有一定豪侠风范。这些历史人物无疑在晋文化史上占有相当分量,何东序在《乡贤十咏》中对他们都进行了热情讴歌。三晋地处华北,在历史上时常与北方强大少数民族政权为邻,因此往往成了一个融合汉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大熔炉。汉民族遭受的无休止侵略和战争,以及长期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熏陶,都极大地促进了三晋大地豪侠和尚武精神的盛行。卫青、霍去病、关羽、张辽、尉迟敬德、薛仁贵等名将皆出身于三晋大地。后周太祖郭威曾云:“河东山川险固,风俗尚武,土多战马,静则勤稼稿,动则习军旅。”曹植《白马篇》用生动笔墨描绘了武艺高强又富有爱国精神的少年英雄,其中诗句“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反映了幽并之地民风剽悍、尚气任侠者众多的状况。隋河东汾阴著名诗人薛道衡创作的一些边塞诗,也突出体现了晋人粗犷壮大的尚武精神,其《出塞二首》其二写道:“边庭烽火惊,插羽夜征兵。少昊腾金气,文昌动将星。长驱鞮汗北,直指夫人城。绝漠三秋暮,穷阴万里生。寒夜哀笳曲,霜天断雁声。连旗下鹿塞,叠鼓向龙庭。妖云坠虏阵,晕月绕胡营。左贤皆顿颡,单于已系缨。绁马登玄阙,钩鲲临北溟。当知霍骠骑,高第起西京。”此诗刚健清新、慷慨雄壮。并州晋阳人王翰,其诗句“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既悲凉伤感,又体现了晋人的豪侠不羁。
受任侠文化影响,明人常伦好谈兵论剑,使气任侠,行事很少顾及世俗目光。常伦曾纵情声伎,诗酒风流,后因庭詈御史,弃官归田。常伦“性本落拓豪放,耻为拘检,又负才凌驾侪辈。一日燕集于所亲,酒酣议论风起,屈其座人,忌者假封事中之,遂用考功例谪外补寿州判官。”[4]82常伦任侠性格在其为寿州判期间也有所体现:“山东盗起,流劫江淮”之际,常伦“募死士,设方略御之,寇不敢犯”[4]83。其《吊淮阴侯》诗在当时豪侠中广为流传。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时期,任侠精神更多地和爱国情怀相结合,成为一种慷慨负国难的尚武精神。此种精神,在常伦散曲《尧民歌》中有明确体现:“摆列着营前铁鼓,摩擦了鞘里昆吾。他便是赤眉铜马待何如?江山社稷要人扶。英雄英雄下狠毒,杀他个片甲无归路。”[9]90此种尚武精神,对晋人何东序、任环、寇天叙、孙传庭等人也都有较大影响。何东序任榆林巡抚期间,率兵出红山寨御敌,大获全胜。巡抚榆林时,有感于北部边患,立志整饬边政。致仕后积三十年之心血,撰成了军事类书《删定武库益智录》二十卷。“该书为培养将帅增智运谋的能力而编,辑录了历代兵家和帝王将相的言论,并以战例作为证明”[10]195,该书收录了大量古代战略家、军事家的论兵之言,分类编辑,条理分明,为丰富中华军事文化做出了一定贡献。长治人任环也继承了三晋文化中的尚武精神。任环视死如归,善于用兵,“御倭颇著奇绩”。曾经“亲介胄临阵,士以公激之,无敢不从”[11]242,连战连捷。甲寅(1554),倭寇侵犯苏州时,任环“以计败之葑门。乙卯,贼复至,复大败之”[11]241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赞扬任环:“倭人入犯,任公大小数十战,功最多。”[11]241山西榆次人寇天叙,也有一定军事才能。巡抚甘肃期间,“回贼犯山丹,督将士擒其长脱脱木儿”[12]3568;巡抚陕西,击退了贼寇对固原的侵犯,“斩首百余。又讨平大盗王居等,累赐银币”[12]3569。相较而言,明末代州人孙传庭在军事领域的影响无疑更为巨大。孙传庭“仪表颀硕,沈毅多筹略”[13]3829。崇祯十五年(1642年)任兵部侍郎,总督陕西。次年升为兵部尚书。陕西巡抚甘学阔不能讨平农民起义军,秦之士大夫哗于朝,共推孙传庭平叛。孙传庭多次带兵击败高迎祥、马进忠、刘国能等起义军。后来镇压李自成、张献忠所部时,由于时疫流行,粮草、弹药缺少,朝廷催战,孙传庭“虽固知往而不返也”[13]3832,但还是被迫仓促出战,兵败战死,马革裹尸。《明史》称“传庭死,关以内无坚城矣”[13]3833、“传庭死而明亡矣”[13]3834。虽然由于种种原因,孙传庭在戎马生涯中也有过数次惨败,但在明末,孙传庭无疑是一位军事素养较高的历史人物。清初吴伟业在《雁门尚书行》中对孙传庭的英勇善战做了生动刻画:“雁门尚书受专征,登坛顾盼三军惊。身长八尺左右射,坐上咄咤风云生。家居绝塞爱死士,一日费尽千黄金”、“长安城头挥羽扇,卧甲韬弓不忘战”。孙传庭出生、成长的代州,一直是古代北方的边塞重地和军事重镇,其剽悍的民风、尚武的传统必然会对孙传庭产生较大影响。
三晋文化中,法家思想源远流长,影响较大。春秋时晋国人子夏,回到魏国后在西河设教,“本来就有法家思想倾向的他,在这个特殊的社会氛围中,学以致用、儒法兼容,培养出了一批著名的法家人物”[14]104,魏文侯、李悝、吴起等人就是其中代表。当代学者冯天瑜也指出:“从学术思想上看,三晋地区是法家的主要发源地,法家思想构成三晋文化的主体。中国最早的成文法产生于春秋末期的郑、晋两国,又以晋成文法的影响最大”[15]336。重法思想,在何东序、寇天叙、薛瑄等人的行事中得到突出体现。何东序廉洁、守法,初授户曹,为临清关税务总监,即以廉洁著称。后任职刑曹时,清正如初。当然,毋庸讳言,何东序也如同商鞅、李斯等法家代表人物一样,因执法严苛忽视人情而为人诟病,《明世宗实录》卷五百六十二就曾记载:徽州府知府何东序与归安县知县李松并著酷声,二人为刑科都给事中赵格所劾,部覆认为“东序廉吏,特用法太严”,因此对何东序未进行惩处,只做改调处理。与何东序相类,山西榆次人寇天叙执法亦严。任浙江宁波知府时,对横行乡里号称“二虎”的冯氏兄弟依法给予了严惩。任应天府丞时,寇天叙敢于坚持原则,以“南京百姓穷,仓库竭,钱粮无可措办”为由拒绝权臣江彬的勒索,使其“无可奈何而止”。对江彬手下那些横行于市、强买货物的边军,寇天叙亦选矬矮精悍之人制约这些不法之徒,使其大受挫折,后遂敛迹。明初的薛瑄也执法严格。任监察御史巡按湖广时,薛瑄经常微服私访,体察民情,平反冤狱,革除弊政,严惩贪官污吏,百姓无不称快。正统初年,太监王振把持朝政,专横拔扈,妄图篡权,拉拢薛瑄,被薛拒绝。薛瑄任大理寺少卿期间,曾一连平反了乱臣制造的十几起大冤案。在秉公处理王振之侄王山之案时,被王振党羽御史王文诬告,几乎丧命。任大理寺卿期间,苏州发生罕见灾荒,二百多名灾民在无法生存、走投无路之际,打开豪绅粮仓,并放火焚烧了豪绅房院,被巡视此地的朝臣王文以反叛罪下狱,判处死刑。薛瑄竭力为百姓争辩申冤,被捕灾民终因薛瑄尽力抗争而活命。薛瑄生平不畏强权,坚持维护法令权威的做法与三晋文化中法家思想的影响密切相关。
“贵在真淳轻华丽,崇尚务实不虚玄,是三晋文化的又一特色。三晋大地,土瘠民穷,其俗朴质、敦厚”[16]67,与此相对应的文化,也就绝少艳丽、纤巧、矫柔之习。三晋文化中俭朴务实、摈弃奢华的特质,在舜禹时期即已初步显现:郑玄《诗谱·魏谱》写道:“昔舜耕于历山,陶于河滨。禹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此一帝一王,俭约之化,于时犹存。”[17]159受此文化影响,晋人为人质朴,行事注重实用性。薛瑄十七岁,就厌恶“科举之学,慨然以求道为志。精思力践,一言一动,必质诸书。微有不合,竟夜反侧不成寐”[18]49。薛瑄厌恶科举之学的原因,当与其重视实践而反对形式、反对空谈有很大关系。薛瑄重实践,明人霍韬在《薛瑄从祀议疏》中高度评价了薛瑄学行皆重实践躬行的突出特点:“薛瑄造诣不及董仲舒,而笃实似之。颖悟弗及韩愈欧阳修,而笃行过之。粹精渊微弗及程颢,而浑厚似之。出处不改其操,祸患不易其节,贫贱不移其介。身为世师,言为世训,动为世式,晦而弥彰,抑而弥光。非真诚积累之素不能也。”[19]3632薛瑄重视道统,也与儒家思想在三晋大地持续不断地薪火相传有关。子夏、荀子皆为先秦三晋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孔门十哲之一的子夏开创了西河学派,在儒家思想的发展创新方面取得巨大成就。荀子进一步发展了儒学,开创了法家学派,对后世影响更大。隋代知名儒学家王通,设教河汾之间,受业者千余人,有“河汾道统”之誉。王通学说承接孔、孟,对唐代的韩、柳,以及后来的宋明理学都有很大影响。北宋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经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释,与周敦颐、邵雍、二程、张载合称为北宋“道学六先生”。薛瑄在前贤基础上开创河东学派,成为明代第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受薛瑄思想影响,寇天叙所为诗文也以实用为主,陈元珂在《涂水先生文集叙》中称:“先生(寇天叙)之志不欲以空言自见,先生之文不假于辞章以传”。明末的曹于汴,也是一位重要儒家学者。曹于汴一生研修儒学,曾跟从高攀龙、冯从吾二人讲学。曹于汴讲求兵农钱赋、边防水利之要,其学术中重视社会需求的实用思想与三晋文化务实传统一脉相承。
除以上几方面以外,隐逸文化也是三晋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隐逸文化“是指一种在历史上处于边缘地位的非主流文化,其哲学根基是以老、庄为核心的道家思想,但又渗透了儒家、禅宗文化的影响”[20]212。隐逸思想源头甚长,老庄即有功成、名遂、身退、无功、无名的隐逸思想,孔子也有“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隐居以求其志”的观点。注重儒教、释道氛围浓厚的晋地有较多隐士。春秋时期晋人介之推,助重耳获得君位后,隐居绵山。隋唐之际绛州龙门人王绩,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隐居,被明人何良俊称为“唐时隐逸诗人第一”。王绩大力推崇、仿效陶渊明,尝作《五斗先生传》。其名作《野望》于萧瑟宁静的景物描写中抒发了惆怅、抑郁、孤寂的情怀。盛唐河东蒲州人王维,创作了大量含蓄、清新、明快,极富音乐之美和绘画之美的山水田园诗。王维归隐终南的生活方式、闲逸萧散的生活情趣,无疑会对后世晋地文人产生深远影响。晚唐河中虞乡(今山西运城)人司空图也曾长期隐居永济王官谷,其《二十四诗品》主要是陶渊明、王维一派山水田园诗的创作经验做了总结。
隐逸文化在三晋大地一直被士人重视,明代山西作家因朝政腐败等因素影响,普遍具有归隐经历。明前期河津人薛瑄,晚年被任命为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大学士后,屡次坦诚直言,献计献策,但后来发现英宗屈杀忠臣,平庸无能,自己难以有所作为,即以老病为由辞官还乡。薛瑄推崇陶渊明淡泊名利的思想,曾在《读陶诗》中写道:“靖节一何高,理凿时运表。返耕甘苦饥,弃世乐枯槁。所以见诸诗,淡泊出天造。掩卷思其人,清风起林杪。”[21]52常伦也曾因庭詈御史,弃官归田。何东序中年因与权臣高拱不睦,于万历初返里丁忧,从此再未出仕,家居近四十年。何东序曾作《乡贤十咏》,对夷齐、介之推、王绩、司空图等人都用专篇进行了吟咏,可知何东序对三晋隐逸之士颇为推重。曹于汴仰慕晋人陶渊明(谥靖节)与宋人邵雍(谥康节),故其诗文别集名为《仰节堂集》。为左都御使时,曹于汴助朝廷除掉了以魏忠贤为首的宦官阉党,却又对诤臣受压的朝廷大环境无可奈何,只好告老归隐。这些隐逸之士,基本上都有过立志报国的思想,也曾为之尽力,但终因政治的黑暗腐败而选择归隐,转而追求人格的独立和道德的完善。
三、诗文创作——三晋文化影响下的多元风格
三晋文化中务实、质朴、重法、任侠等因素,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三晋作家的文学创作。受此影响,三晋作家的创作更多表现为反对绮靡纤巧,注重明道实用,较少注重作品语言和形式的华美。战国末期赵人荀子,对“三晋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其文风较为质朴,逻辑严密,说理透辟。中唐河东文学家柳宗元大力反对华而不实的骈丽文风,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指出:“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釆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被誉为“一代文宗”的山西作家元好问,推崇具有雄浑刚健风骨之美的诗歌,欣赏陶渊明“一语天然万古新,豪华落尽见真淳”的不假雕饰之作,反对“斗靡夸多费览观”的陆、潘之作。元好问的“纪乱诗”悲壮慷慨,继承了杜甫现实主义诗风,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柳宗元、元好问同为山西文坛巨擘,其推崇朴质文风的思想无疑会影响到后来的三晋作家。柳宗元在永州曾作《八愚诗》及《愚溪诗序》,并在诗序里道出自己将溪以及溪边的丘、泉、沟等命名为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的原因,并言己为“真愚”,隐然有和“八愚”并为“九愚”之意,既自嘲,又含蓄抒发了愤懑不平之气。明人何东序与柳氏同为山西河东人,也因正直守法而仕途坎坷。何东序将诗文集命名为《九愚山房诗集》、《九愚山房稿》,无疑是在以柳氏为效法对象。
明初薛瑄的诗歌创作,重视情感的真实表达,反对纤巧文风。薛瑄认为“凡诗文出于真情则工”,指出《诗经》、《出师表》、《泷冈阡表》等诗文“皆所谓出于肺腑者也,故皆不求工而自工。故凡作诗文皆以真情为主”[22]174。薛瑄反对过分注重形式的文风,他批评“铅华”、“雕虫”之弊:“铅华灭素质,雕虫失本根。”薛瑄诗集中,部分诗歌“可以一言契道,而不坠理窟,不落理障,同时也不致破诗人之格”[22]174其五言诗淳雅,“绰有陶、孟、韦、柳之风。论者谓‘宋之晦菴,明之敬轩,皆不堕古人理趣’。”[23]641(薛瑄号敬轩)薛瑄受隐逸文化影响,推崇淡泊自然的诗风,他曾在《读陶诗》中赞同陶渊明“返耕甘苦饥,弃世乐枯槁”[21]52的生活态度及其“淡泊出天造”的创作方式。四库馆臣论薛瑄诗歌道:“间涉理路,而大致冲澹高秀,吐言天拔,往往有陶、韦之风。盖有德有言,瑄足当之。”[2]2293作为著名理学家,薛瑄部分诗歌善在写景中融入理趣,其《桐井甘泉》写道:“树环嘉木桐阴合,井冽寒泉地脉通。彩凤九霄应有待,道源千古自无穷。”[21]103又如《锦城寓馆》其一,先描绘了初日下的花林、带露的庭竹、宛转鸣叫的野禽,再自然言理:“心无一念杂,窗绝半尘侵。道理无边在,悠然思转深”。这些诗既有陶、孟等人诗歌的自然、质朴,又多了一份理趣。因对故乡秀美山水的热爱,薛瑄名其诗集为《河汾诗集》,集中有较多歌咏晋地风光的诗,如卷七的《禹门十二咏》、《登平陆城门楼》,卷八的《汾上春日二首》《汾上春行》等。
以散曲创作而为世人所重的常伦,其散曲中有晋人诗文中惯有的质朴、雄健豪放:“扶摇万里上云霄,重仰中天日月遥。雕鞍骏马长安道。候朝鸡,还报晓,打叠起山野风骚。报不尽皇王圣,报不尽慈母劳,尽忠孝正当吾曹”[9]64(《水仙子》其一)。常伦恃才傲物,且具有较为浓厚的幽并之地常有的任侠思想,因此仕途颇不得意,使得他一些词作或抒发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慨,或表达归隐以全身避害的无奈,:“心慵意懒,叹云霄回首,梦破邯郸。功成名遂,更迟留,谁免忧患?青山挥洒孤臣血,宝剑催残壮士颜。封侯印,拜将坛,虚名妄与后人看。长安道,行路难。不如归去旧青山”[9]89、“洒泪江州,行吟泽畔,笑黄犬东门叹。总不如挂冠住山,倒大来无灾患”[9]72。豪放恣肆的情感,出之以平易通俗、本色流畅的语言,是常伦散曲的一个显著特点,如其《山坡羊》曲中之句:“闷葫芦一摔一个粉碎,臭皮囊一挫一个蝉蜕,鸦儿守定兔巢中睡”、“来来往往,无酒也三分醉”“恢恢,试问青天我是谁;飞飞,上的青云咱让谁。”[9]69这些句子酣畅淋漓地表达了常伦无所顾忌、雄视一世的气概。任中敏认为此等曲句“亦愤慨,亦解脱,若癫若狂”[24]427-428。任侠精神则在常伦乐府诗《结客少年场》中得到了集中体现,其诗写道:“结客多少年,鞍马何翩翩!驰过邯郸娼,夹坐唱鸣弦。沾醉一然喏,剑挺起当筵。壮士行何避,轻斋入幽蓟。断彼仇者头,漆之为饮器。生当持报君,死当为鬼厉。”[9]13常伦作品平易、情感酣畅淋漓、才气纵横。
与常伦的恣肆、任侠不同,任环为人无愧忠孝,其“古文皆崭崭有笔力,且高简有法度”。任环善用平易通俗的语言表达出忠君爱民之思及慷慨赴国之情。任环古文关注现实,注重教化,有为而作,有感而发,较好反映了他胸怀大局的气概。在《军中寄子书》中,任环将生死置之度外,决心“臣死忠,妻死节,子死孝,咬定牙关,大家成就一个是而已”[25]卷一,批评儿子在“倭贼流毒,多少百姓不得安宁”之际“风云气少,儿女情多”[25]卷一。任环古文语言平易、质朴,极少芜词累句,但气势充足,和当时专讲形式、空洞迂腐的时文大相径庭。这主要是由于任环为文既“高简”又“有法度”,善于蓄势、善用排比句、善用长短句交错运用的方法强化其笔力,如其《重修徳风亭记》、《止碑书与沙博王南崖》等文。任环诗歌质朴之中不乏壮志豪情:“昔年走马燕山道,今日驱兵沧海涯。三尺龙泉书万卷,丈夫何处不为家”、“放船中道转狂风,雪浪排山一点蓬。燕寝先生明旦死,惊危不在海涛中”[25]卷三(《示尔孝等二首》)。这种豪放慷慨也可以看作是三晋尚武精神的体现。
何东序的一些乐府诗,也具有平易质朴的特点,如其乐府诗《猛虎行》、《养蚕词》等,抨击了明代中后期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不合理现象,体现了乐府诗常有的现实主义特点。《猛虎行》以七言为主,间有杂句,语言上保持了古乐府质朴真挚的一面,抨击了收税者及其帮凶的冷酷。《养蚕词》中“人言遭虎多辟易,何如头上逢酷吏”、“衙吏追呼夜未央”、“一条鞭打骨流髓”等诗句质朴、形象。何东序这些乐府诗,骈句络绎,句式错落,语言朴素,以叙事为主。其另外一些乐府诗则辞藻缤纷,多用典故,以抒情为主,与汉乐府民歌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格,如《行路难》等诗。“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连用韩信、贾谊之事,“豺虎饿耽偃月堂”[5]601既用比喻,也兼用典。《行路难》其三中“兰荪纫奇服,松柏拟贞坚”等诗句,则继承了《离骚》中“香草美人”的象征手法。乐府诗之外,何东序有一组诗很好体现了其重法思想,表达了诗人对遭受政治迫害的正直士人的深切同情、对严嵩之流的痛恨。组诗记载了23位官员的事迹,包括海瑞、沈炼、杨选等不畏强权的守法名臣。因有边塞征战经历,何东序写了较多和战争有关的诗篇,如《师还紫荆道中述怀用张使君韵》、《白石口》等。
作为明后期知名的理学家,曹于汴部分诗文有偏重说理而轻视形式的特点,四库馆臣论其诗文:“亦在理学、举业之间,或似语录,或似八比,盖平生制行高洁,立朝风节,凛然震耀一世,远者大者志固有在,原不以笔札见长”[2]2333。曹于汴一些较成功的诗,语言平易,说理自然巧妙,如其《省躬诗》一首写道:“风从水上过,文成风不知。水亦不自文,观者乃文之。”[26]卷十四又如其《题北园》组诗其六写道:“梦里分明玉帝旁,骑龙驾虎任翱翔。回头世界些儿大,不是争蜗是怒螳。”[26]卷十四高攀龙曾称赞曹于汴诗歌“见于咏歌者足以畅天机、流性蕴”,这些诗大抵如此。
明末军事家孙传庭,戎马一生,有较多诗歌反映了乱世的动荡和人民的不幸,语言质朴,风格雄浑悲凉。三晋文化中质朴、务实、尚武的特点,在其诗作中有所体现:“频年戎马任纵横,此日长驱气转盈。两镇元戎争料敌,一时健旅尽婴城。楼烦碛外朝鸣角,石岭峰头夜合营。燕壁晋藩俱咫尺,令人击目泪如倾”、“纵横道路满豺狼,浩淼况隔大江水”、“九边此日仍多垒,四海何时可息肩。为语登闳新谏议,苍生满眼尽堪怜”、“去岁游兵猎雁门,雄关虎豹自云屯。请缨漫切书生志,闻鼓偏销战士魂。草垛阴风吹白昼,桑乾磷火照黄昏。只今痛定方思痛,又见烟尘满冀原。”[27]卷五(乙亥警其一)对民众不幸的悲悯、对国事的忧虑,都化为平易、苍劲的诗句。明代山西作家多重气节,为宦时能严守法令,作品大多具有刚健、质朴的共同特点。因政局动荡和三晋文化中尚武、隐逸文化等因素影响,作家们创作了较多与战争有关的诗文,以及较多描绘三晋山水田园风光、抒发隐逸思想的诗歌。作家对现实的普遍关注,也体现了三晋文化中务实精神对作家创作的影响。当然,在具有一些普遍共性的同时,作家们的创作也各有特色,如常伦的豪放恣肆、薛瑄的融理入景、任环的高简有法、曹于汴的说理自然、孙传庭的雄浑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