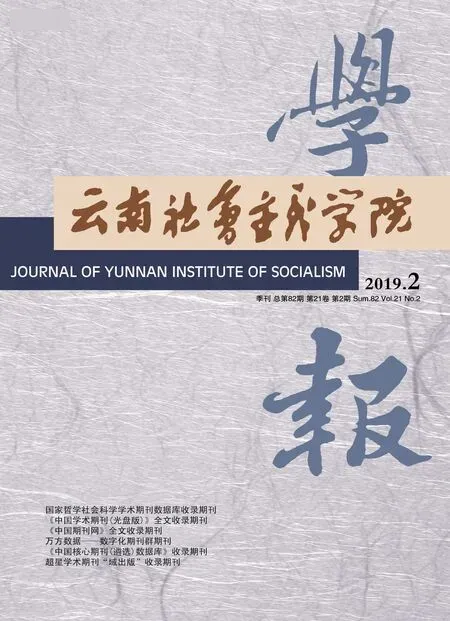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国民外交
孙 敏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 党史党建教研室,广西 桂林 541002)
国民外交是指国民对国家外交行为的参与,是国民以一定的组织形式通过舆论、运动等压力手段来表达自己的意志与实力,从而影响政府的外交决策,左右政府对外关系的趋向[注]王立成:《中国近代外交制度史》,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19年,第162页。。它又被称为人民外交、民间外交、民众外交等。 国民外交充当了政府外交的后援,其主要目的是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维护国家主权完整,其实质是一种群众运动,它是民族民主运动的产物,包含着国民特别是各种团体对外交的直接参与和间接参与。本文主要梳理国民外交兴起的背景,分析国民外交运动在五四运动时期展现出来的新特点,探讨其历史意义。
一、五四运动爆发的时代背景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国民外交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初清末抵制美货运动,到拒俄运动、抵制日货运动、收回利权运动及抵制二十一条运动等,这些运动大多是分散的,缺乏有效的方法与手段,因而效果也是有限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落幕之即,美国总统威尔逊于1918年1月发表了“十四条宣言”,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战后国际关系原则,如:无论国家大小“一律享同等之权利”、在对待国际事务中要以“绝对的公道为判断”。关于战后议和问题,他提出五条大纲,其中“各国人民权力平等,待遇毫无轩轾”[注]天津市历史博物馆:《近代史资料专刊·秘笈录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30页。排在首位。威尔逊的这番言语极具迷惑性,为追求私利最大化的美国外交披上了一层道德外衣。对于近代以来一直处于受压迫、受剥削地位的中国民众来说,无异于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正如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所说,这一消息“已经传到中国最边远的地区”,“世界上或许没有一个地方像中国那样对美国在巴黎的领导寄予那么大的希望”[注][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李抱宏、盛震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76页。。
当时的中国虽然仍处于南北分裂状态,但在遇到重大国际问题时,受传统观念影响的中国人会停止内乱、一致对外。因此,举国上下,无论南北政府还是商工学报各界人士,都期望能够通过巴黎和会夺回主权,实现民族独立。并且大家对当前形势的估计十分乐观,认为作为战胜的协约国,中国一定能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势力范围问题、领事裁判权等问题也将迎刃而解。蔡元培表示“深信民国八年,实为新时代之新纪元”[注]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550页。,李大钊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1919年是“人类生活中的新纪元”,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和平宣言“是这新纪元的曙光”[注]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606-608页。。
因为有过因政府软弱而导致外交失败的前车之鉴,国内有识之士提出,要广泛发动国民外交的力量,杜绝秘密外交的危害。在这种呼声下,协约国国民协会、国际联盟同志会等外交团体纷纷成立,其中最具影响力的要数以张謇、熊希龄等人为理事的国民外交协会。该协会旨在传达公众民意、充当政府后援,其成员包括了大学生、文人学者、国民党员、各地爱国人士等,是国内第一个全国性的、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民外交组织。
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后,广泛征集各省议会、商工学报各界团体的意见,汇总整理成七条外交主张,送抵巴黎和会委员手中。其中包括公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种全面废约的主张可以说是相当大胆的,在以前的国民外交运动中很难见到。国民外交协会还致电此时正在巴黎开展国民外交活动的梁启超,附上中、英文请愿书各一份,希望他能代为传达国内民意。梁启超表示“不敢辞匹夫之责”,之后在各种场合宣传国内民众的外交主张,并随时将巴黎和会的进展情况告知国内,起到了中国代表不能起的作用。
然而,巴黎和会最终因中国政府的退让而以失败告终,无疑给满怀希望的国人泼了一桶凉水,中国人民被彻底激怒了。这个消息最早是通过国民外交途径传到国内的,可以说是国民外交直接点燃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
二、五四运动时期国民外交展现的新特点
在特殊的国际国内环境下,五四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具有了崭新的特点。
(一)具有反帝反封建双重性质
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国民外交斗争由过去单纯的对外性质变为对内对外的双重性质,反帝反封建的性质更加明晰。以前的民众运动,都只着力于对抗其中一个方面,而五四运动具有了双重性质,矛头直指政府。巴黎外交的失败使民众认识到“青岛交涉,在和会之完全失败,虽曰日人手腕之灵巧,实为我卖国党人局中牵制,甘心葬送,以媚日期人所致”[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154页。。他们意识到内政与外交是互相连动的,内政不清则外交不济。因此,五四运动锋芒直指亲日派卖国政府,而不是个别的卖国贼,使得这次爱国外交运动具有了强烈的对内意味。
正如梁启超所说的:“五四运动与其说是纯外交的,毋宁说是半内政的,因为他行进路向含督责政府的意味很多。”[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七,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第52页。毛泽东也指出:“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注]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19年,第561页。。5月5日,北京联合会通过的决议更体现了这一特点,“对外:力争山东问题,以护国权,务达最后之目的而后已。……对内:诛卖国贼,北京方面已于昨日由全京各校学生一致签名,提起公诉。打消军阀势力……”[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上册),第177页。7月1日召开的上海国民大会,工界代表申岳君云:“救国必须从根本解决,就是要推翻卖国政府,因卖国政府一天存在,他可能在外交上,内政上活动订约借款,压迫国民,为所欲为。”[注]彭明:《中国现代史资料选辑》(第一册),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71页。因此,五四运动时期的国民外交具有对内对外的双重性质。
(二)采用了内外联系的新形式
五四运动扩大了国民外交的方式与途径,由过去的国内运动发展为内外联合,国民外交斗争方式变得灵活多样。
五四运动时期,社会各团体、各阶层继续举行各种传统意义上的国民外交活动,广大民众以游行示威、请愿、追悼烈士、罢工罢课、演讲活动、抵制外货等方式,继续关注外交形势发展并施以舆论压力,这仍是主流形式。与此同时,国民外交的形式变得多样化,这主要体现在联合方面。这种联合是双轨并行的,首先是影响高层领导人,其次是民间交流。五四运动中,国内各民众团体对内对外宣传的力度都明显加大。
一方面,国内各民众团体直接向国家领导人及与会代表发出通电,如北京学生联合会致电巴黎各专使,“失败外交,举国痛愤,公等受国重托,务望始终坚持,勿稍退让,倘和会不容我合理之主张,即请撤旗回国,勿予签字。”“尺土寸地,一草一木,不可轻弃;宁愿暴力夺占,不可拱手让人,或至万不得已,而忍辱签字,亦当加以但书,关于山东权利,由德国直接让与日本,中国断不承认,否则仍勿签字,以保主权,而维国家之体面。倘一屈百屈,负国辱命公等固不能失其咎也。”[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上册),第355页。关于巴黎和会请愿大纲,国民外交协会等团体致电驻法公使,要求撤销势力范围。关于扶助中国外交,国民外交协会还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国际联盟组织的成立能够为世界造福,中国人民表示赞同,并希望“中国各种外交问题,敬请大力扶助解决”[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486页。。可见,国民已经以独立的外交主体身份参与国际事务,成为国际力量不可忽视的民意表达。这样,民众的呼声不得不成为国家决策者需要考虑的因素。
另一方面,积极进行民间思想文化交流,向世界民众宣传中国人民的主张。1920年5月,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在李大钊的支持下访问日本,并积极与日本黎明会展开交流。所以有一大批日本进步人士支持和同情五四运动,黎明会的主要成员吉野造作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李大钊在1919年6月5日写给吉野的信中,向他解释了中国的五四运动:“此次敝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的公正的公民无丝毫的恶意。惟不幸而两国纷争问题表现之,诚为遗憾万千。”[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00页。正因为这样,才得到了吉野的正面回应,吉野在黎明会的刊物《解放》上发表文章,指出应该对五四运动有恰当的认识,“他们反对的是帝国主义的日本,如果知道还有和平主义的日本,必定愿意与后者提携”[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第301页。。这对于日本人民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的合理诉求具有重要意义。
一个国家外交的胜利仅有本国人民的支持是不够的,还必须取得世界舆论的支持。这种内外联合的国民外交对于国内外互通声气,让世界了解中国起了很好的作用。
(三)斗争方式更加理性
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国民外交较为理性,理智地用文明斗争方式区别对待军阀主义与和平主义。
这一时期的外交斗争体现了文明斗争的思想,少了几许暴力成分,上海商学工学报界的对内对外宣言就体现了这一思想,其对内宣言中表明这“纯粹为对内的行为,对外概守相当的敬礼与友谊” ,会“尊重市场秩序,拥护法律之自由”。对外宣言“深望各友邦国民,对于吾人困苦之境遇,及不得已之苦衷,加以鉴谅。尤冀为扶持正义,与吾人以精神的援助”[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上册),第355页。。可见,斗争不再是一味的武力抵抗、暴力破坏,而是概守礼谊,诚恳地道述本国之困境,即所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以取得国际友人的同情与支持,这样更容易为国际舆论所接受,更符合国民外交斗争的目的。
这一时期的国民外交斗争并未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理智地区分了国际和平主义与军阀主义。这一态度在1919年商教联席会议关于华盛顿会议的对外宣言中就有集中体现。宣言除了声明否认列强未经中国同意强加给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反对列强非法侵占中国的任何权利之外,又表示“我国民为谋国际间之福利,主张开放门户,予各国以机会均等,其开放程序,应按内政之进步,督促当局推行,并希望各友邦修改条约以辅助之”[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第486页。。他们既反对军阀主义的产物即不平等条约,又主张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实行门户开放,这是一种理性的态度。因此吉野指出,“邻邦青年运动的潜在精神之内,存在着真正产生中日亲善的种子”[注]王晓秋:《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第302页。。美籍学者周策纵也认为,当时“中国人的愤慨主要是针对国际强权政治而非一般外国人的,……从根本上说,排外主义与五四运动的立场是相对的”[注][美]周策纵:《五四运动史》,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292页。。毋容置疑,这种理性对外的态度是国民外交的一大逬步。
(四)注重法律手段的运用
此时的国民外交更注重法律手段的运用,运用国际外交原则和中国的立约制度,指出和约缔结的不合理性,为我国拒签和约提供法律依据。
五四运动之前,中国人民在外交干涉中法律意识并不强。以五四运动为起点,国民外交运动重视运用法律维护合法权益,国民外交协会在1919年5月就指出:“此等行为依国内法应置诸重点,不认其契约为有效,既无效力可言,我国民当然无服从之义务。废约重公法,诸友邦决不承认之。”“不知此等换文,乃当局者暂时之约朿,尚非正式之合同,必各依国法规定之手续,其条约始能生效。我国现行国法缔结条约须经国会通过。当时此种秘密换文,国会从未与闻,遑论通过。”[注]《国民外交协会成立宣言》,《民国日报》1919年5月6日。
不仅仅是外交协会,学生和各业界也在指责不平等条约的非法性,北京学生在上书徐世昌总统的文章中指出:“故德国因武力失败,当然应将青岛交还中国。按国际之公法断无日本继承权利之理。若谓日本继承德国权利,根据四年五月七日之中日协约,则此次协约在国会解散,袁氏帝制胎生时代。未经国会,按之约法二十五条之规定,断不能发生效力。”上海商工学报各界也发表对外宣言说:“查我国约法,媾和缔约,须经国会同意,凡属二二人私订者无效。”[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五四爱国运动》(上册),第390页。这些都反映国民的外交斗争已开始依据法律知识。
努力寻求法律依据是国民外交在策略上的进步,对后来的国民外交也产生了影响。商教联席会议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关于废除二十一条的议案,就指出二十一条不符合国际公法。
(五)境界更高
这个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立足于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主张推翻世界军阀主义与侵略主义,将国民外交提升到一个更高的境界。
陈独秀指出:“我看两个分赃会议,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隔得不止十万八千里,非全世界人民都站起来直接解决不可。”[注]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1919年5月4日。作为这次运动的领袖人物,他从“世界永久和平,人类真正幸福”的立场出发,号召人民团结起来,成为这次运动的最高宗旨。在实践活动中,人民的斗争也体现了这一愿望。1919年6月22日,上海商工学报各界在对外宣言中指出:“我友邦人土,素爱和平,深爱正义,必能锄强去恶,而不使德意志之武力万能主义,再见于东方,亚欧大陆化为巴尔干第二也。”[注]陈独秀:《两个和会都无用》,《每周评论》1919年5月4日。他们号召外国同胞铲除“武力万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在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的信件中,痛陈军阀主义是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的障碍,“苟一日不解此万恶之军阀,则两国人民,永无亲善之望。各欲解脱其军阀政府,则非互助不可。…诸君须知中日两国人民,同蛰于军阀恶魔之下,正宜同病相怜,患难兄弟之间”[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41页。。他们替日本同胞分析了日本的发展前景与日本人民的切身利益,不仅反对日本对我国的侵略,还把斗争升华到反对世界的“武断主义”。这一观点得到了吉野的认同,他认为在反对军阀主义的斗争上,中国与日本有着共同的精神与任务。又如上海工商界函请全国商会联合会,转致各省商会,呼吁世界和平:“本会鉴于世界大势及将来万国平等方针,……公同组织中华工商保守国际和平研究会,冀以促成永久和平,尽世界一分子之天职。”[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41页。可见国民外交已经具备了更高的境界,在维护本民族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也将维护世界和平与人类幸福作为奋斗目标。
三、五四运动时期中国国民外交的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时期,由于国民参与,中国的外交有了坚强的后盾。国民外交在发动民众、反映民意、监督政府的外交斗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扮演了民间先行的角色,具有多方面的历史意义。
(一)对中国政府出台对外政策和列强对华政策产生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的国民外交活动,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巴黎和会代表团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据顾维钧回忆,当时在巴黎的政治领袖、中国学生、华侨代表等,每天都会跑到中国代表团总部,不断要求代表团明确保证不在和约上签字。他们还威胁代表团,如果签字将“不择手段,加以制止。”[注]天津编译中心:《顾维钧回忆录缩编》,上海:中华书局,1997年,第64页。可见,在当时的条件下,人民对代表团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从而影响到政府的对外决策倾向,这在中国外交史上,“实可谓第一次差强人意者也”[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352页。。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政府更加明确地宣布废除旧约,1919年4月28日,徐世昌大总统宣布,以后所有无约各国愿与中国订约者,均以平等为原则。5月,中国政府宣布无约国在华商人应守中国之税率法律。同年,捷克、波兰、希腊、立陶宛等国政府均要求与中国订立商约,希望获得领事裁判权,中国均予拒绝。中国外交出现了局部改观,除了与小国发展平等关系外,还同战败的德国、革命的俄国签订了平等条约。德国与中国的关系调整后,德国归还了八国联军侵华时抢走的天文仪器,还支付了四百万元清理德的在华产业。可见,中国政府调整外交政策,在国际事务中争取平等地位,这种积极的姿态转变与五四运动时期国民外交运动有着密切关系。
经过这次斗争,列强对中国的认识也有所改观。王正廷把这次外交斗争称为中国外交的进步,认为它使世界认识到中国主权在于国民全体,而不是政府中少数人所能愚弄。各国见到中华民族捍卫主权的决心,不敢再随意轻侮;各国知道中国人民已懂得一定的外交手段,不敢再简单地武力胁迫;各国了解到不平等条约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于是想办法化解民愤……“故各国对于中国,一变其强权压迫的态度,而为亲善之态度。实可谓外交上之一大转机”[注]王正廷:《近二十五年来中国之外交》,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3年,第145页。。可见,作为中国代表团中力主拒约的中坚代表人物之一,王正廷极力肯定五四运动中表现出来的积极的外交姿态所带来的有益影响。
(二)对中国的外交运行机制产生了一定影响
五四运动时期的国民外交冲击了旧的官僚外交运行机制,展示了强大的舆论力量。一直以来,外交是个敏感而又高度集权的领域,为政府所专有,有时实际被少数官僚所垄断,民众与在野士绅不得与闻。这种垄断了民意表达的纯粹的官僚外交,使本已处于弱国地位的中国之外交,由于缺乏民意支持而显得更加虚弱,而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国民外交改变了这种状况。五四期间,各业界召开国民大会讨论外交问题。1919年7月1日,上海国民大会开会,各界参与讨论拒约救亡办法,声势浩大。翻阅史料不难发现,诸如此类的运动举不胜举。这表示,以往官僚外交的旧局面开始改变,国民外交逐渐发挥其作用,开了民众成功干预外交的先河。
人民要求公开外交,反对秘密外交,发出呼声:“中日两国人民,应该要求政府立时将从前所立的密约在平和会议上废止。不可听任两国军阀在那里秘密作鬼。”[注]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册),第176页。“秘密外交这一类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注]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册),第221页。国民外交的崛起,成为民意表达的声音,有效地监督了政府的外交行为,否定了秘密外交的暗箱交易,促进了公开外交的发展,对我国外交机制的健康运行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促进了中国人民国民意识的觉醒
我国国民誓死卫国的决心,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方刚气魄,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国际地位。
五四运动中,中国各业界、各阶层密切关注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对于我国局势发展的影响,对外力争国权,对内严惩国贼,维护国家领土与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设国耻纪念日、建爱心社团,国民意识悄然觉醒,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向心力。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从巴黎和会决议的祸害中,产生了令人鼓舞的中国人民的觉醒,使他们为了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注][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285页。在这种“共同的思想”和“共同的行动”下,中国人民增强了民众的国家主人翁意识,形成了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在国民的外交斗争中,中华民族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团结。在外交斗争中,国人奔走呼号、殚精竭力,运动所表现出来的爱国拳拳之心,众志成城御外敌的力量为世界人民所敬畏。
四、结语
美国驻华外交官芮恩施评价五四运动说:“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奋起,并且使他的政府屈服。这个教训非常深刻。运动的领导人认识到,这一行动只是一个很小的开端,但重要的是,这个行动已构成了一个开端。”[注][美]保罗.S.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1913-1919年美国驻华公使回忆录》,第285页。
五四运动中的国民外交虽然不免带有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如民众舆论追求立竿见影的效果缺乏长远规划,执着于既定目标技巧不够灵活等等,但它不仅开启了中国外交史上一个跨时代的篇章,而且使国内政治民主生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是外交史发展中伟大的成就,其历史意义相当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