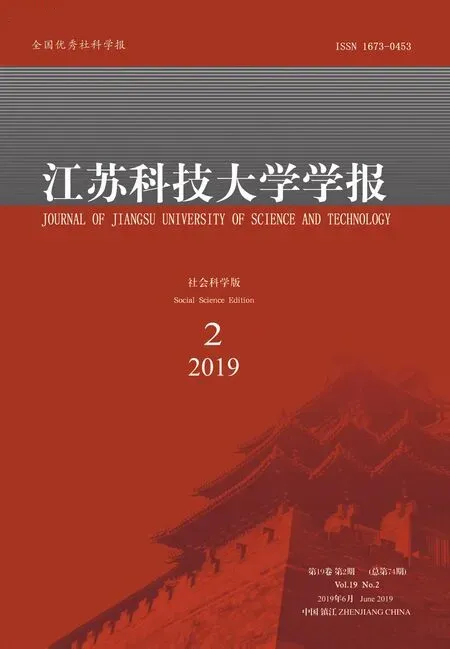论金圣叹诗歌中的陶渊明
卢 洁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金圣叹(1608—1661),处明清鼎革之际,以“衡文评书”[1]300而“才名千古”[2]。陶渊明(365—427),丁晋宋易代之间,以“古今隐逸诗人之宗”[3]28为后世师范。金圣叹和陶渊明所处年代甚遥,实是两心相契于千载之后的隔代知音。目前学界对金、陶二人的研究寥寥,陈洪先生始开其端,他在《金圣叹传论》中提及金圣叹和陶渊明的相似处,主要用陶渊明来印证金圣叹对清朝新政权的态度[4],但余言未尽。稍后如陆林先生,他仅以只言片语道出金圣叹对陶渊明的仰慕[5],并未深论。再如吴子林先生,在《金圣叹与“魏晋风流”》一文中着重以陶渊明为例证对象,探讨金圣叹的人生哲学与“魏晋风流”之关系,多涉论陶渊明的人生哲学和人生态度[6],而未言其他。其后,陈飞先生在探测金圣叹的家世背景时,指出金圣叹的父亲是陶潜式的人物[7],又在《千秋一叹:金圣叹传》一书中深刻揭示了金圣叹与陶渊明的关系[8],所论逸出皮相,拨开了一些疑云。
上述前贤时彦的著述,多从金圣叹的评点文字和陶诗的视角讨论,鲜有立足金圣叹诗歌探讨二者关系的研究。笔者拟以金圣叹诗歌(《沉吟楼诗选》)为对象,论述金圣叹对陶渊明人格形象的推重、刻画与借用,以及对“陶渊明意象”的援引与化用的情况,以窥金圣叹对陶渊明的受容和认同,兼论产生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从侧面揭橥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深远影响。
一、金圣叹诗歌对“陶渊明形象”的推重与借用
据古贤书传,陶渊明自晋已有声名。南朝钟嵘品陶曰“古今隐逸诗人之宗”[3]28,唐杜甫诗云“陶潜避俗翁”[9],宋徐铉谓“陶彭泽古之逸民也”[10],明李梦阳曰“高才豪逸人也”[11],清乔亿云“后世名在隐见间”[12],潘德舆言“(陶)诗乃千古之冠”[13]云云,皆以“隐士”“千古诗宗”等标榜渊明。陶渊明是以“隐士”和“诗人”的主体形象和典型符号呈现于文学史上,而在“灵鬼转世”[14]的“评点家”金圣叹的诗歌中,陶渊明是一个集“隐士” “遗民” “酒士” “贫士”“诗翁”和“高僧”于一体的多重形象。金圣叹对陶渊明的人格形象不仅甚为推重,并频频借用以立言抒情。
首先,金圣叹对陶渊明不为二臣的“遗民”形象和不与世接的“隐士”形象深为服膺,借陶以言志。据《宋书》载:“(陶)潜弱年薄官不洁去就之迹,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15]2288义熙元年(405)后,陶渊明走上了归隐之路。金圣叹对陶渊明“不事二主”的高风峻节和旷世独立之致尤为景慕与向往。他有两首题“渊明抚孤松图”的诗,其一为《题文彦可画陶渊明抚孤松图》,诗云:“先生已去莲花国,遗墨今留大德房。高节清风如在眼,何须虎贲似中郎。”[16]80由诗题可知,“渊明抚孤松图”是文彦可所作,画面取自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抚孤松而盘桓”句。其二为《题渊明抚孤松图》诗:“后土栽培存此树,上天谪堕有斯人。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遗民。三径岁寒唯有雪,六年眼泪未逢春。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16]102金圣叹不吝笔墨再次选取“孤松”意象题诗,旨在表现陶渊明孤迈独立、坚韧不屈的气节。清人方东树云:“古人处变革之际,其立言皆可观其志性。”[17]金圣叹赞渊明“不曾误受秦封号,且喜终为晋遗民”,实可视为自己在易代之际处世的一个注脚;诗尾又曰:“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16]102,亦是深寓己志。在明祚覆亡后,他以渊明为师为友,意欲做一个“不事二主”的“遗民”和“隐者”。其诗《有感呈诸同学》已微露隐逸之心迹:“世事已如此,吾侪不隐居。干戈随地有,礼乐与时疏。学士宜飞锡,深山可结庐。还同林下宿,晨夕论金书。”[16]39他清醒而深刻地认识到,世道险阻,应如渊明澹泊绝俗,结庐山中。可以说,在明清鼎革之际,陶渊明的“遗民”和“隐士”形象已深入圣叹的精神和灵魂深处。
其次,金圣叹对陶渊明以酒为乐的“酒士”形象和知人间冷暖的“贫士”形象着墨颇多,借陶喻人喻己。金圣叹颇为赞赏陶渊明醉饮孤松五柳间的豪迈、洒脱的胸次和风范,故而常用陶令耽酒的形象设喻。如“陶令门前白酒瓢,亚夫营里血腥刀”[16]69,暗喻不屈的民族气节;“曾点行春春服好,陶潜饮酒酒人亲。沉冥便是桃源里,何用狺狺更问津”[16]105-106,引喻友人王子文孤隐之风流;“孤松底下青篱竹,五柳门前白板门。一个先生方卧醉,四围黄菊并无言”[16]80,欣然将友人王斫山比作陶渊明,其志行可见一斑。实际上,陶渊明在金圣叹心中不仅是一个自在洒脱的善酒之士,更是一个生活困窘的寒素之士。陶渊明自叙:“吾年过五十,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18]187“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18]159渊明常以“贫士”自居,有《咏贫士》诗,当为自咏,他甚至还向亲友乞讨,作有《乞食》诗。金诗中屡以陶渊明“贫士”形象自喻:“子美篇篇老,陶潜顿顿饥。迟生又千载,惆怅与谁归。”[16]28“彭泽妻孥相对饿,鹫山主伴自相称。”[16]127金圣叹成家后生活陷入困顿,落到依靠友人接济的地步,遂有三首诗以陶渊明“冥报”自比。“冥报”的典故出自陶渊明《乞食》诗:“衔戢知何谢,冥报以相贻。”[18]48今生无法相报,只能等到来世。金圣叹曰:“悠悠罢弹铗,顿顿食无鱼。卧病烦同学,提携过草庐。加餐倍珍重,醉后默踌躇。冥报成何语,相敦自有初。”[16]20“范叔一寒方至此,陶公冥报正茫然。抱琴明月君来否,烂醉如今我欲眠。”[16]113“饥驱陶令叩山门,慧远慈悲出酒樽。佛说花开非有相,青天鹤过更无痕。说经夜夜鸡三唱,圆梦朝朝水一盆。笑杀昔人图冥报,枉将丝线绣平原。”[16]139金圣叹的“冥报”之言深寓对亲友救济之恩的无以为报和愧疚。此外,他亦师渊明以“贫士”自居,作《贫士吟》自写胸臆。由前述可知,金圣叹借渊明立言,文辞之间流露出对陶渊明耽酒为乐的洒脱性情的歆羡,亦表达了对其贫寒生活的同情。
最后,金圣叹对陶渊明佛境通达的“高僧”形象和才学高妙的“诗翁”形象推誉至高,借陶褒扬他者。陶渊明以“千古诗宗”之誉在后世独步千古,金圣叹在诗歌中表达了对陶渊明的诗文才学的推崇,《读休老近稿赋赠》云:“子美篇篇岂易解,渊明妙思最难知。不图尚有高山调,互赏清风明月时。”[16]133-134诗以杜甫和陶渊明的诗篇来比喻“休老近稿”,用陶渊明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妙思”来表达“近稿”虚涵难解的意蕴,此言可见金圣叹对陶渊明文学才能的仰慕,对休老的赞赏亦是溢于言表。与此同时,陶渊明“高僧”之境界尤不可及。金圣叹诗曰:“《庄》载汉阴辞自贡,佛言谢客让陶潜”[16]134,此诗意云陶渊明的佛学境界更胜谢灵运一筹,这里把祝寿对象比作陶渊明,其佛学境界自不待言;“先生已去莲花国,遗墨今留大德房”[16]80,亦谓陶渊明的佛学智慧对修行之人沾溉深远;“自嫌婚嫁真无暇,不觉冬春鬓尽斑。他日渊明悉心后,远公可肯宁开关?”[16]110此处将陶渊明与高僧慧远相提并论,足可窥见陶渊明佛学境界之高深。
由上述可知,“隐士”“诗人”“酒士”形象是陶渊明特有的符号和标签,是历代文学史所塑造的鲜明而传统的主体特征,不能完全窥见陶渊明的真实面目。在金圣叹的笔下,陶渊明藏去的几分面目逐渐凸显,其“遗民”“贫士”“高僧”形象显现无遗,较其传统形象而言,更为丰富和立体化,更接近于陶渊明的真实人格。金圣叹对陶渊明人格形象的频繁“借用”,旨在代己立言抒情,可视为金圣叹精神情怀的另类书写。
二、金圣叹诗歌对“陶渊明意象”的援引与化用
“陶渊明意象”在中国文学史上已经形成一种固定模式的“意象群”,亦固化为一种典型的文学符号,其背后蕴含了丰富、深厚的意涵,即“陶渊明精神”,这种精神春风化雨般地浸润着古今文人的生命。白居易曰:“不慕樽有酒,不慕琴无弦,慕君遗容利,老死此丘园。”[19]清代诗话云:“后人慕之,往往有心欲求自然,欲矜神妙。”[20]陶渊明历千载而不朽,让众贤形诸歌咏,金圣叹对陶渊明亦有着浓郁的情愫。他不仅诵其诗文、慕其人格,还在诗中援引和化用大量的“陶渊明意象”(包括典故)。金诗中的“陶渊明意象”大致可以推衍为三类:“陶渊明其人”类意象、“陶渊明诗文”类意象和“陶渊明其事”类意象。这些意象的使用,是金圣叹对“陶渊明精神”认同与契合的重要表现方式。
“陶渊明其人”类意象,是指以陶渊明的姓名、尊称、别称、官职等为主及其衍生出来的意象,如陶令、陶公、陶潜、渊明、陶家、彭泽等,以此类意象入诗者,数量不乏。前文所引诗歌皆有论及,此处略举一二:“陶令门前新柳树,林逋屋后旧梅花。社中许我私开酒,洛下邀人门吃茶。”[16]108“人在山中无历日,客从海上得筹星。未须灵寿承荣赐,正学参差引上真。曾点行春春日好,陶潜饮酒酒人亲。”[16]105-106“万古陶边家士家,门庭耿介绝喧哗。”[16]101这类意象多出现在咏怀、寄赠与唱和诗中,咏怀诗以自咏为调,抒发对陶渊明高洁人格和气节的倾心向往;酬唱诗主要寄咏他人,用陶渊明比拟所赠对象的人格形象、内在气质和文学才能等。
“陶渊明诗文”类意象,是指陶渊明诗文中出现的具有特殊意涵和典范意义的意象,如三径、松菊、黄菊、五柳、武陵、桃源、结庐、南山、斜川、秦汉事、柴桑等。这类意象具有自然、恬静、冲淡、闲雅之情韵,意在营造“隐逸之境”和“桃源胜景”。兹举数例,如:“三径岁寒唯有雪,六年眼泪未逢春。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16]102“孤松底下青篱竹,五柳门前白板门。一个先生方卧醉,四围黄菊并无言。木落霜天天地哀,陶家偏报有花开。老僧结习从来尽,便约维摩去看来。”[16]80“老去看看非越石,穷来渐渐逼柴桑。意忘连夜多风雨,只是深秋足稻米。”[16]86“桃花如锦水如蓝,行尽桃花到水南。洞里仙人问秦汉,忽然记得罩鱼篮。”[16]64以上诗作以咏物为主,通过对自然之物的歌咏和具有“隐逸”色彩意象的运用,建构陶渊明式令人向往的“桃源”,表达对放逸冲淡、澹泊独立、真率自然隐逸生活的向往。值得注意的是,金圣叹在寄赠诗中屡用“桃源”意象,如“曾点行春春服好,陶潜饮酒酒人亲。沉冥便是桃源里,何用狺狺更问津。”[16]105-106诗歌重在表达对寄赠者王子文的澹泊沉冥的“隐者”风范的推崇。“莲花滴漏声声切,木槵为珠粒粒流。便有桃源最深处,那知秦汉事何如。”[16]130此诗意在向酬赠者传达自己归隐的心向。
“陶渊明其事”类意象,是指与史载的陶渊明事迹相关的意象。昭明太子萧统在《陶渊明传》中曰:“(陶)潜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与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将常候之,值其酿熟,取头上葛巾漉酒,还复着之。”[21]这段话记载了陶渊明抚无弦琴和取葛巾漉酒之故事。陶渊明自言:“乐琴书以消忧”[18]161,“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18]86。“陶渊明其事”类意象则有无弦琴(素琴)、饮酒、读书、闲居等,在金诗中频繁出现,且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引“琴酒”以自遣,如《住天池别业》曰:“金银今世界,冰雪道人心。野鹤何天去,孤云随处深。临风时拾橡,候月对弹琴。徒有高山在,谁闻流水音!”[16]27诗中慨叹知音难求,表达内心的彷徨无依。《弹琴》曰:“一阳淡荡雁初归,万木澄阴手欲挥。人在高山招未下,坐临流水事多违。心知别鹤飞辽海,不见游鱼仰钓矶。弹罢泪珠流不住,至今滴作十三徽。”[16]113诗中直接流露出金圣叹壮志不遂的无奈和知音难求的愁苦。二是以“读”为生活中的重要活动,以“闲”“独”为生活的主要基调。金圣叹诗歌中和“读书”相关的意象不胜枚举,如“金书”“读杜”“读书”“作诗”“作书”“开卷”等;以“闲”“独”为调的意象亦俯拾皆是,如“闲坐”“闲身”“独居”“独坐”“山居”等。由此可知,金圣叹的“读”与“闲”与陶渊明的“读书”“闲居”是同一境况。
除以上三类直接援引较为典型和熟知的“陶渊明意象”外,金圣叹亦化用陶渊明其他诗文,这种现象比较少见。兹举一例,如《独坐咏怀》云:“空斋谁与语,开卷寻古人。謦欬竟如故,典型诚可亲。庭花争弄色,林鸟静鸣春。安得素心士,相携数夕晨。”[16]27尾句“安得素心士,相携数夕晨”则是化用陶渊明《移居》诗“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可见二人都渴求在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中寻得“素心”之人,但现世中知音无处觅,只能“开卷寻古人”,从古代圣贤那里寻求精神的支撑和慰藉。
综上,金诗中的“陶渊明意象”甚多,其背后蕴含了丰富的“陶渊明精神”和意涵,可见“陶渊明意象”是“陶渊明精神”的重要表象和承载媒介。金圣叹援引和化用大量的“陶渊明意象”,旨在表现个人心理取向和精神指向。我们亦可通过这些“陶渊明意象”的“指代词”,在一定程度上见出金圣叹与“陶渊明精神”的契合度。
三、金圣叹接受陶渊明的主要原因
综观前文,金诗中表现出了极大的尊陶、爱陶、宗陶和用陶的倾向。金圣叹自云:“爱君我欲同君住,一样疏狂两个身。”[16]102陶渊明是金圣叹在精神和灵魂上的栖所和指归。实际上,金圣叹接受陶渊明并非偶然,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端。
首先,金、陶家世与出身相似,是金圣叹产生陶渊明情结的深层背景。其一,金、陶二人家世皆是远世显赫,当代没落,并成遗孤。陶渊明的家族是魏晋时期的世家大族,《晋书·隐逸传》载:“(渊明)大司马侃之曾孙也。祖茂,武昌太守。”[22]2460其祖上是以官显,到父辈概已隐居:“寄迹风云,冥兹愠喜。”[18]28到渊明代,真正走向没落:“慈妣早世”[18]191,“我年二六”[18]191,十二岁丧母,丧父可能更早,自幼便成遗孤。关于金圣叹的家世,其诗透露一二,《念舍弟》云:“记得同君八岁时,一双童子好威仪。拈书弄笔三时懒,扑蝶寻虫百事宜。”[16]104圣叹八岁就已“拈书弄笔”,可见童年时的家境比较优裕。后来经历了一些变故(可能是家难),“一自耶娘为异物,至今兄弟并差池”[16]104,导致“眷属凋丧”,其年圣叹约八岁[23],与陶渊明一样很小便成孤儿,金圣叹有《孤儿吟》代己立言。其二,金、陶二人都是“多病身”。《宋书·隐逸传》载渊明“躬耕自资,遂抱羸疾”[15]2287。陶渊明也在《答庞参军并序》中自言“吾抱疾多年,不复为文。本既不丰,复老病继之”[18]51,说自己的疾病早已有之,年青时身体就不好,年老了疾病越来越厉害了,“日月遂往,机巧好疏。缅求在昔,眇然如何。疾患以来,渐就衰损。亲旧不遗,每以药石见救,自恐大分将有限也”[18]188。多年的沉痼使他的身体日渐衰弱。金圣叹一生也是疾病缠身,其诗曰“不弃群贤德,难支老病身”[16]30,“晚晴江岸湿,老病杖藜难”[16]33,“西风不肯饶寒屋,旧病公然疟贱躯”[16]97。他可能患的还不止一种病,“謦欬竟如故,典型诚可亲”[16]27,“消渴春尤甚,兵戈道正长”[16]29。二公同病相怜,也真是“苦命人”。由上可知,金、陶二人的先辈并非寻常之人,或有官品,或有身份,或有地位,或有家业,家境十分殷实;到他们这一辈没落为一领青衿,生活穷苦不堪,又多病在身。如此相似的家世和生活环境,可以说是金圣叹产生陶渊明情结的重要因素。
其次,金、陶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出处矛盾逼似,是金圣叹接受陶渊明的现实基础。陶渊明出生于东晋时期,晚年遭遇晋宋易代,心灵遭受了巨大的冲击。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24]金圣叹之在明末,和陶渊明之于晋末略同,都是将近易代之际。他生于万历后期,彼时“经济、财政面临全面崩溃,政治则矛盾纠结、危机四伏,而外敌迅速崛起,败亡之局已经注定”[25]。史家言“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26],当时的社会异常荒唐与腐败。在改朝换代面前,金、陶二人都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想斗争”。依《宋书》载,陶渊明做过三次官,做官期间,渊明两次解官归田,两辞州府辟命,可见他在仕途中是有归隐之想的,后历经一番思想斗争终归田园。金圣叹在明清易代之际,心灵和精神也受到了极大的冲撞。明祚覆亡后,他经历了生离死别,生活日见困窘,“绝意仕进”,“除朋从谈笑外,惟兀坐贯华堂中,读书著述为务”[1]301。《上元词》诗后自注云:“此非道人语。既满目如此,生理逼侧,略开绮语,以乐情抱。昔陶潜自言:时制文章自娱,颇示其志。身此词,岂非先神庙末年耶?处士不幸,丁晋宋之间;身亦适遭变革,欲哭不敢,诗即何罪?不能寄他人,将独与同志者一见也。”[16]63金圣叹以陶渊明为“同志”,面对“生理逼侧”的社会现实“欲哭不敢”,只能像陶渊明一样以“文章自娱,颇示其志”,诗成也只能寄与像陶渊明这样的“同志”阅看。金、陶二人身居异代却恍如一世,这是金圣叹大幅度接受陶渊明的现实基础。
再者,金、陶二人怀骋高志和理想却皆失臂于江山,是金圣叹对陶渊明产生隔代契合的心理根源。金、陶都怀有远大的功业理想,但从他们的经历来看,二人的才华不在政治而在文学。陶渊明少壮之“猛志”异常强烈:“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回海,骞翮思远翥。”[18]117青年时期,曾缅想先世之功业:“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为虞宾,历世重光。御龙勤夏,豕韦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18]27中年时期曰:“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18]16晚年时期感慨壮志难酬:“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嗟乎二贤,逢世多疑。候瞻写志,感鵩献辞。”[18]183其追求功业的理想一生不息。金圣叹同陶渊明一样,有超脱利禄的一面,更有热烈奋厉的一面。他儿时便自负高眄:“为儿时,自负大才,不胜侘傺,恰似自古及今,止我一人是大才,止我一人无沉屈者。”[27]追求功名是他人生的主要情调。金、陶二人虽欲指点江山,却壮“志”难酬,在政治上难有建树,缘于他们的才华不在政治而在文学。陶渊明“少怀高尚,博学善属文,颖脱不羁,任真自得,为乡邻所贵”[22]2460。金圣叹很早就因为文章和个性为乡人所知:“圣叹异人也,学最博,识最超,才最大,笔最快,凡书一经其眼,如明镜出匣,隐微必照;经其手,如庖丁解牛,腠理砉然;经其口,又如悬河翻澜,人人快意,不啻冬日之向火,通身暖热,夏日之饮水,肺腑清凉也。”[28]金圣叹被视为“异人”,可见他的学、识、才、笔,非常人可比。但二人此生精力皆尽于文学而非政治,致使宏愿落空,壮志未酬,这是二人隔代契合的重要心理因素。
最后,金、陶二人对“诗贵真”诗学精神的共同追求,是金圣叹推崇陶渊明诗歌的根本所在。宋苏东坡曰:“古今贤之,贵其(渊明)真也。”[29]清施补华曰:“陶公诗一往真气,自胸中流出。”[30]古今文人、处士尊陶爱陶,皆贵其“真”。陶渊明以“真”为宗的诗学精神和审美要求对金圣叹产生了至为重要的影响。金圣叹的诗歌理论之一即是求“真”,其曰:“诗非异物,只是一句真话。”[31]39“诗非异物,只是人人心头舌尖所万不获已必欲说出之一句说话耳。”[31]49“作诗最要真心实意,若果真心实意,便使他人读之,油然无不感叹。不然,即更无一人能读也。”[31]32他在诗歌创作中亦遵循“情真”的诗歌理论,《春感八首》是其“情真”的典范之作。可以说,金圣叹的诗歌理论和诗歌创作深受陶渊明诗学精神的霑濡,二人都追求“诗贵真”的精神品格,这正是金圣叹推崇和赞赏陶渊明诗歌的关键因素。
概言之,金、陶二人是“千古同情”。客观上说,是时代为之,易代之际的乱世给他们心灵带来极大的撞击。主观上,他们有着共同的理想、志向和追求,但生活寒素,宏愿难遂,增添了他们的寂寞与孤独。金圣叹对陶渊明产生高度的共鸣,不是某一因素的导引,而是以上多种因素合力共振的结果。
“崇陶”自南朝已然,经宋代苏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32]的“追和”后,声名至高[33],钱锺书曰“渊明文名,至宋而极”[34]。至明清两代,“学陶”“爱陶”“和陶”者实亦不少。身处明清之际的金圣叹虽以“评点家”著称,但“平生吟咏极多”[16]2,深受陶渊明之沾溉。他诵其诗文,慕其人格,贵其真淳,用其入诗。在金圣叹的笔下,陶渊明的人格形象和意象得以丰富和发展,陶渊明的精神和意涵得以继承和发扬。更为重要的是,金圣叹不仅为自身寻找到了精神寄托,完成了“以生命印证生命”的验证活动,亦成为陶渊明经典化传承中的重要接力;同时从某种程度上可管窥陶渊明及其诗歌作为一种艺术审美符号和理想精神标志在后世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影响之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