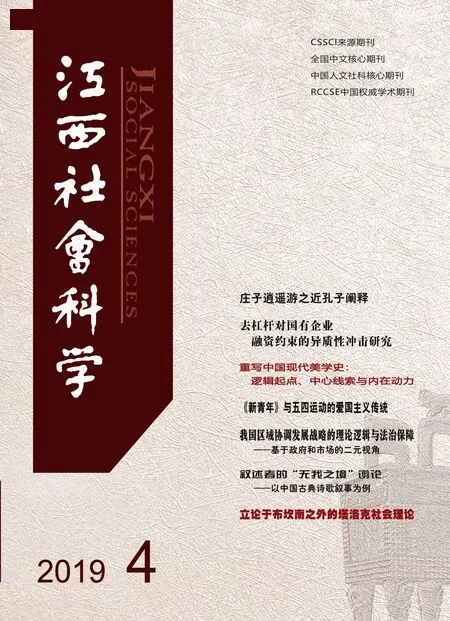《新青年》与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传统
“解放”是《新青年》的关键词,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核心,引导青年从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民族强盛、国家富强而奋斗。晚清以降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思想文化的变迁演进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期名之曰船坚炮利时代。第二期名之曰变法维新时代。第三期名之曰立宪革命时代。第四期名之曰‘个人'‘社会'时代。”[1]《新青年》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为代表,积极倡导人的解放,选取科学与民主作为思想武器,把个人潜意识中的生命冲动和强力引上个性解放的道路,反抗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改造和冲击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模式,批判封建纲常礼教,抨击封建伦理道德,推倒千古偶像,把人从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用自我存在的“醒过来的人”的理念,置换“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封建专制思想文化观念,革除自身封建专制思想文化因素,奋发图强,形成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所以,新文化“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见。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2](P205)。这种“发见”奠定“新青年”的“人的解放”的历史地位。
新青年社团透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等媒介与文学作品,通过传播新思潮,唤醒年轻一辈的爱国心;还借助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重大事件影响力,宣传劳工团结的力量战无不胜,高度关注劳工的群体解放,输入社会主义思潮,并发掘学生这股崛起的新生力量,从鼓吹人的个体解放转变为呼吁民族的解放,把人的解放与社会变革相结合,强调个人的解放服从民族的解放,激发学生的爱国激情,推动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并成为一座鲜明的思想里程碑。在此之前,《新青年》致力文学革命,输入新思潮,反抗封建专制思想文化,进行思想革命,再造新文明,并在五四运动时达到高峰;五四运动后,各种西方新思潮逐渐退潮,社会主义思潮成为推崇对象,并对中国社会产生实际影响,人的解放服从民族的解放运动,为民族强盛、国家富强牺牲个人,奠定五四运动的爱国主义传统,《新青年》与五四运动因此成为文化/政治符号,成为一种精神的载体。
一
《新青年》输入西方新思潮,进行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反抗封建专制思想文化,解放人的个性,影响了中国现代史发展的进程,成为“创造了”一个时代的重要媒体。胡适就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并特别突出强调:“《新青年》的使命在于文学革命与思想革命”[3](P217),破除僵死的封建专制思想文化,造成人的解放高潮,凸显传播新思潮对新青年产生较大影响,推动中国从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融入世界的历史发展进程,由此认定《新青年》的主题是人的解放,副题才是科学与民主。
史家认定科学与民主是《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主题和旗帜,主要依据陈独秀《本志罪案答辩书》这一段话:“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4]陈独秀的这段“答辩”被史家反复征引,证实《新青年》的两大主题是科学与民主。陈独秀咬定,封建专制思想文化与科学、民主格格不入,追求科学与民主就必定要反抗封建专制思想文化。《新青年》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必定无情揭露批判封建专制思想文化,反抗封建伦理道德传统,因此受到维护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旧势力的攻击;反对《新青年》、攻击《新青年》实质就是反对科学与民主,背离历史发展潮流,维护封建专制思想文化。
晚清以降,追求科学与民主价值观成为主流话语,确立了威权地位,无人敢公开挑战。1923年,胡适曾总结道:“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5](P196)民主在各界人士心中的地位比科学更重更高。1922年10月,《东方杂志》就强调:“我们所占着的时间,既然是被科学精神和民治主义两大潮流所支配的二十世纪,则我们估定一切言论和智识的价值,当然以对于这两大潮流的面背为标准;断没有依违两可,在时间轨道上打旋的。”[6]并明确宣布:《东方杂志》衡量一切言论和智识的价值标准是科学与民主。1934年6月,蔡元培总结中国的文化运动演变时,同样以科学与民主为“标准”进行评价,认为:“直至辛亥革命,思想开放,政治上虽不能实行同盟会的主张,而孙中山重科学、扩民权的大义,已渐布潜势力于文化上。至《新青年》盛行,五四运动勃发,而轩然起一大波,其波动至今未已。那时候以文学革命为出发点,而以科学及民治为归宿点(《新青年》中称为赛先生与德先生,就是英文中Science与Democracy两字,简译)……我们用这两种标准,来检点十余年来的文化运动,明明合于标准的,知道没有错误。我们以后还是照这方向努力运动,也一定不是错误。我们可以自信的了。”[7](P422-423)可见,陈独秀选择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公开叫板“非难”《新青年》的人,等于宣称:非难“本志”便是反对科学与民主。陈独秀高举科学与民主大旗,为新文化运动画龙点睛,“德、赛两先生”不仅成为当时的口头禅,而且成为社会团体、政治势力标榜文明进步的共同的合法的思想依据及行为指南。
胡适并不认同陈独秀的《新青年》“两大‘罪案'”说。胡适回忆说:“陈独秀先生为《新青年》所写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那篇文章的时候,他说《新青年》犯了两大‘罪案'。第一是拥护‘赛先生'(science科学),第二是拥护‘德先生'(democracy民主)。可是那时的陈独秀对‘科学'和‘民主'的定义却不甚了了。所以一般人对这两个名词便也很容易加以曲解。……但是在我看来,‘民主'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习惯性的行为;‘科学'则是一种思想和知识的法则。科学和民主两者都牵涉到一种心理状态和一种行为的习惯,一种生活方式。”[8](P355-356)由此可见,陈独秀与胡适这两位新文化运动的主帅对科学与民主并没有达成共识。《新青年》打出科学与民主旗号,只为批孔非儒,反抗封建专制思想文化,为解放人的个性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金冲及就认为:“《新青年》喊出的最响亮的口号是‘民主'和‘科学',那时又叫作‘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和‘科学'的提出不是偶然的。民主的对立物是专制,科学的对立物是愚昧和迷信,这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恶果。”[9](P148)
当代学者解读“《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也认为除科学与民主大旗外,“《新青年》同人再也找不到‘共同的旗帜'。《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涉及众多的思想流派与社会问题,根本无法一概而论。以《新青年》的‘专号'而言,‘易卜生'、‘人口问题'与‘马克思主义研究',除了同是新思潮,很难找到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思想文化杂志,《新青年》视野开阔,兴趣极为广泛,讨论的课题涉及孔子评议、欧战风云、女子贞操、罗素哲学、国语进化、科学方法、偶像破坏,以及新诗技巧等。可以说,举凡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新青年》同人都试图给予解答。因此,只有这表明政治态度而非具体学术主张的‘民主'与‘科学',能够集合起众多壮怀激烈的新文化人”[10]。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是“以编辑为生”,最“直接的原因是缘于生活的无奈选择。将杂志命名为《青年杂志》,其良苦用心是确定青年是杂志面对社会寻求对话交流的主要对象,因为民初的上海不但是中国最繁荣的商埠,也是中国最具革命意识的城市。‘近代上海,如果不算租界内西方的政治模式所建立的一套管理制度,只就华人而言,通过地方自治,新闻舆论自由等,上海人享受到近代民主权利无疑比中国其它地方相对地要多一些'。最向往民主、科学的又是青年,所以,《青年杂志》确定青年为对话对象,把青年学生作为杂志生存与发展的根基”[11]。陈独秀完全预想不到《新青年》会发起一场“新文化运动”,创造一个新时代,自然也就更不可能设计一批议题。站在历史的语境解构《新青年》,可以发现影响新文化运动的议题,几乎都是在办刊过程中逐渐“寻觅”、“发掘”和“策划”出来的。有些话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有些话题没有得到反应。
当代主流史学更是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口号是所谓‘德先生'(Democracy)和‘赛先生'(Science),也就是民主和科学。当封建主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专制,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盲从,有着历史的进步意义。但是,据这个口号的倡导者陈独秀的解释,民主,是指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科学,‘狭义的是指自然科学而言,广义是指社会科学而言'。他强调要用自然科学一样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来研究社会,可是詹姆士的实用主义、柏格森的创造进化论和罗素的新唯实主义这类用某些自然科学成果装饰起来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当时在他心目中也被认为是科学。他提倡民主和科学,是为了‘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即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发展资本主义,‘以求适今世之生存'。这表明,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实质上仍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反对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12](P7-8)。
但是,立足《新青年》的文本,还原《新青年》的历史语境,确定科学与民主为《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的两大主题,肯定不能准确还原《新青年》的“新青年”叙事,更不切合《新青年》的历史语境。筛选、评估确定《新青年》主题,必须立足《新青年》文本及历史语境,从解构《新青年》文本入手。
《新青年》包括“通信”、“随感录”、编辑部通告等各类文字,总计发表各类文章1529篇。其中专门讨论“民主”(包括“德谟克拉西”、“德先生”、民本、民治、民权、人权、平民主义等)的文章,只有陈独秀的《实行民治的基础》、屈维它(瞿秋白)的《自民主主义至社会主义》和罗素的《民主与革命》(张崧年译)等3篇。涉论“科学”的文章也不过五六篇(主要讨论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以及科学与宗教、人生观等)。运用大数据技术计量分析《新青年》词的出现频度,统计结果①显示:
出现频度最高的词是“个人”,出现在536篇文章中,涉及1690段,总共出现2590次;“个人主义”出现在49篇文章中,涉及96段,总共出现138次;“个性”出现在51篇文章中,涉及80段,总共出现117次;“个人”、“个人主义”、“个性”三个关键词合起来统计,总共出现在636篇文章中,涉及1866段,总共出现2845次。
第二名是“自由”,出现在359篇文章中,涉及1146段,总共出现1923次;“自主”出现在53篇文章中,涉及66段,总共出现74次;“自由”、“自主”二个关键词合起来统计,总共出现在412篇文章中,涉及1212段,总共出现1997次。
第三名是“科学”,出现在384篇文章中,涉及991段,总共出现1907次;“赛先生”出现在3篇文章中,涉及4段,总共出现6次;“赛因斯”出现在2篇文章中,涉及2段,总共出现2次;“科学”、“赛先生”、“赛因斯”三个关键词合起来统计,总共出现在389篇文章中,涉及997段,总共出现1915次。
第四名是“解放”,出现在162篇文章中,涉及413段,总共出现629次。
第五名是“民主”,出现在65篇文章中,涉及180段,总共出现260次;“德谟克拉西”出现在46篇文章中,涉及121段,总共出现193次;“德莫克拉西”出现在4篇文章中,涉及4段,总共出现4次;“德先生”出现在4篇文章中,涉及6段,总共出现8次;“民主”、“德谟克拉西”、“德莫克拉西”、“德先生”四个词合起来统计,总共出现在119篇文章中,涉及311段,总共出现465次。可见,在总字数超过541万字的《新青年》杂志中,“民主”关键词的出现频度并不高。
出现频度是确定关键词的主要证据,但结合文本内容也非常重要。《新青年》中虽“个人”、“个人主义”、“个性”三个词合起来统计出现频度最高,却不能确定为关键词,理由是《新青年》使用这三个词,指向都是强调“个人”或人的“个性”获得解放;“个人主义”则突出强调个人须冲破束缚,解放自己,自由自主地发展,核心也是个人获得解放;因此,我们确定“解放”是《新青年》关键词,“个人”“解放”是《新青年》的主题。
确定“解放”是《新青年》关键词,不仅考虑了其在《新青年》中的出现频率,最重要的是《新青年》的“解放”目标指向非常明确——“解放”“个人”。“个人”是“解放”的内核,“解放”是“个人”的形态,所以,“解放”与“个人”紧密相连,密不可分,因此推定“解放”“个人”是《新青年》与新文化运动的主题。殷海光就说:“中国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多数只能算是‘解放者',自己经历的是解放,向人传播的也是解放。”[13](P257)
二
“解放”是《新青年》的关键词,以个人主义(个性主义)为思想武器推动人的觉醒、个人的解放。因此,所谓“新青年”就是从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专制思想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个人。
汉语的“解放”一词最早出自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十月中,以蒲蹧裹而缠之;二月初乃解放。”指对受束缚的物质的解开、放松。《新青年》的“解放”指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反义词是束缚、奴役、约束。“个人”的“解放”特指摆脱精神的桎梏,如政治、宗教、文化、伦理等给人的枷锁,成为思想解放、个性自由自主发展的独立个体。
《青年杂志》创刊号的正文第2页就频繁出现“解放”一词。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是纲领性的文章,主旨就是鼓励青年追求个人的解放。陈独秀指出:“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女〕权之解放也。”开宗明义,把欧洲历史概括为“解放”的历史,并把“解放”置放于文明进步的最高位置,然后才进一步具体阐述“解放”。陈独秀说:“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4]陈独秀突出强调“解放”就是解除约束,得到充分的自由,独立自主地发展。这种阐释大大超过中国此前所有的思想家,奠定中国现代思想家理解“解放”的范式。《新青年》这样“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个人'为价值之源,公开宣扬个人本位,由此揭开了‘个人'和‘个人观念'以现代性的姿态在现代中国出场的大幕。五四前后的个人观念,既是对晚清以来思想变动的承接,又是对民国初期中西两大思想资源的生发、重构和转换。这一阶段,‘个人'无论作为术语还是概念,其自身现代意义上的外延、内涵和概念要素已齐备;而‘个人观念'无论作为思想陈述还是价值评判,其现代性、多元化的观念形态得以真正形成”[15]。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个人观念的变革由于知识精英的进一步推动,不仅逐步扩大了社会影响,而且其形态和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化。具体表现为:一方面,个性解放思潮渐涨渐高,个性、自我等在五四前后一度成为时代的流行词汇;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了个人本位,个人主义在五四前后一度成为主流的思想倾向。简单地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作用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告诉人们:个人是独立的存在,独立的自我最有力量”[15]。
陈独秀选择以个人的解放为突破口阐释“新青年”思想,不仅具有强烈的战斗精神,而且一矢中的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核心。中国封建专制思想文化以培养奴隶人格为价值标准,不关注和重视个人,认为只有融入社会共同行为的人才具有较高的人格价值,才能受到社会的肯定和尊重,从而奉行宗法专制、等级特权。统治者既掌政权,又掌教化,左手刑刀,右手教鞭,皇权主义深入人心,造成一元化的思维,沉淀成一元化的封建专制思想文化、封建伦理道德,美化、神化皇权,以“三纲五常”扼杀人性,禁止独立思考,由服从而迷信,由迷信而丧失自我,由自我的丧失导致浓厚的奴隶意识。陈独秀认为:“吾国自古相传之道德政治,胥反乎是。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16]陈独秀指出,“奴隶的道德”造成“奴隶人格”,极大地满足统治者“牧民”、治民的心理需求。陈独秀因此严厉批判“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Nietzsche)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Morality of Noble),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Morality of Slave)。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首当辨此”[14]。陈独秀以尼采哲学为准绳,有力地揭露批判封建专制思想文化的核心就是“奴隶之道德”,受这种“忠孝节义”的“奴隶道德”思想文化熏陶的中国人,没有“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奴隶当得心满意足。一部中国历史,看不到有“独立平等之人格”的个人,只充斥着“奴隶之幸福”、“奴隶之文章”、“奴隶之光荣”、“奴隶之纪念物”。
个人的“解放”也是李大钊的重要价值理念。李大钊认为,“解放”就是使人脱离少数人的专制奴役,伸张人的个性,反抗压迫,实现个性自由,社会对个人的“压制之程度愈进,解放之运动愈强”,追求“个人”的“解放”,保证人人获得自由。李大钊说:“近世之文明,解放之文明也。近世国民之运动,解放之运动也。解放者何?即将多数各个之权利由来为少数专制之向心力所吸收、侵蚀、陵压、束缚者,依离心力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之谓也。于是对于专制主义而有民主主义,对于资本主义而有社会主义,是皆离心力与向心力相搏战而生之结果也。”[17]追求个人的解放、个性的自由自主独立发展,不仅成为李大钊最高的人生价值理想,并且与其生命本质紧密结合,构成其思想深处最为深厚的人生理性。李大钊还说:“西谚有云:‘不自由毋宁死'。夫人莫不恶死而贪生,今为自由故,不惜牺牲其生命以为代价而购求之,是必自由之价值与生命有同一之贵重,甚或远在生命以上。人之于世,不自由而生存可也,生存而不自由不能忍也。试观人类生活史上之一切努力,罔不为求得自由而始然者。他且莫论,即以吾国历次革命而言,先民之努力乃至断头流血而亦有所不辞者,亦曰为求自由而已矣。……盖自由为人类生存必需之要求,无自由则无生存之价值。”[18]按照李大钊的观点,争取解放就是追求自由,是人类社会的价值目标。一部人类的文明发展史,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争取解放、获得自由而进行斗争。
陈独秀与李大钊的“解放”思想相通,突出个人的“解放”,重视个人的解放、独立、个性自由,“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14],吹响人的觉醒和人的解放的革命号角,强调青年必须追求个人的解放,“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勿为他人之附属品。以一物附属一物,或以一物附属一人而为其所有,其物为无意识者也。若有意识之人间,各有其意识,斯各有其独立自主之权。若以一人而附属一人,即丧其自由自尊之人格,立沦于被征服之女子奴隶捕虏家畜之地位”。所以,“新青年”必须培养个人的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坚持“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16],追求个人的解放,反抗封建道德文化,认清“旧社会之道德不适今世者,莫如尊上抑下,尊长抑幼,尊男抑女。旧社会之所谓不道德者,乃不尊其所尊,抑其所抑者耳,未必有何罪恶可言(如妇人再醮之类)。吾人今日所应尊行之真理,即在废弃此不平等不道德之尊抑,而以个人人格之自觉及人之群利害互助之自觉为新道德,为真道德”[19]。
胡适评价新文化运动,也突出“解放”的主题,强调新文化运动追求“这个那个人的解放”。胡适提出:文化运动的唯一目的就是“再造文明”,保证解放风俗制度,解放思想文化,解放个人:
文明不是拢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晚上拢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现今的人爱谈“解放与改造”,须知解放不是拢统解放,改造也不是拢统改造。解放是这个那个制度的解放,这种那种思想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改造是这个那个制度的改造,这种那种思想的改造,这个那个人的改造,是一点一滴的改造。[20]
胡适不相信能根本改造社会,更不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建起人间天堂,所以高度警惕各类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一生反对寻求一揽子解决的主义,而只相信“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是一点一滴的解放”的渐进之路。
因此肯定,“解放”个人不仅是《新青年》主题,也是《新青年》团体的共识,只有个人获得“解放”,铸造独立自主的人格,对社会有个人独立、有“良知”或“理性”的判断,国家才能得救,所以寻找近代中国前途的关键是个人的“解放”,“这个那个人的解放”,所以,《新青年》高举“解放”的大旗,目的就是把个人从封建思想政治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求解脱而伸其个性复其自由”,“解放”的立足点和出发点是个人和个人主义。胡适认为中国现代思想的发展演变就以1923年为界:“(一)维多利亚思想时代,从梁任公到《新青年》,多是侧重个人的解放。(二)集团主义(Collectivism)时代,一九二三年以后,无论为民族主义运动,或共产革命运动,皆属于这个反个人主义的倾向。”[21](P257)
陈独秀还指出,人的“解放”不要“多在名词上说空话”,而要投入实际的行动,就是“道理真实的名词”,如果“离开实际运动”,也就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个人不要只高喊“解放”的口号,完全没有“解放”个人的实际行动,因为个人的“解放重在自动”:“解放就是压制底反面,也就是自由底别名。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的历史,人民对于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子,劳动者对于资本家,女子对于男子,新思想对于旧思想,新宗教对于旧宗教……况且解放重在自动,不只是被动的意思,个人主观上有了觉悟,自己从种种束缚的不正当的思想、习惯、迷信中解放出来,不受束缚,不甘压制,要求客观上的解放,才能收解放底圆满效果。自动的解放,正是解放底第一义。”[22]
“个人”的“解放”不仅是《新青年》的主题,而且是新文化运动目标,这正如胡适所说:“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23](P511-512)胡适极为精辟地揭示个人解放与国家强盛的密切关系。只有每一个人都获得了“解放”,个性自由发展了,争取到了“个人的自由”,获得充分的思想自由,才能“为国家争取自由”;每一个人都具有独立的自由个性,争得了“自己的人格”,才能“为国家争人格”,因为“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
《新青年》推动“解放”“个人”的思想启蒙,不仅造成一个思想解放的《新青年》时代,成为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而且培养了具有独立的自主个性、独立的思想的“新青年”,为五四运动储备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强大队伍。
三
《新青年》北迁北大编辑后,改变为新青年社团[24]“公同”刊物[25],输入新思潮、再造新文明成为其办刊宗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给中国社会送来了两股新思潮:一是“民族独立和自治”;二是社会主义。受这两股新思潮的冲击,新青年社团的思想也发生变化,追求民族独立和自治,大力宣传劳工的群体解放,输入社会主义思潮,辅导新青年理解“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26],把追求个人的解放融入民族的独立和自治的解放运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 “使得革命思想遍及殖民地”,“唤起了帝国主义国家统治之下的民族的希望,推动了民族觉醒。和平缔造者反复提到民族自决概念,威尔逊公开提出在处理殖民地问题时,‘考虑欧洲政府意愿的同时,也同样应该考虑当地人的利益'。看起来威尔逊倡导的正是民族独立和自治。民族主义者在组织反帝组织的斗争中,也从苏联那里寻求鼓舞,苏联领导者谴责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宣称支持独立运动。总的来说,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27](P1028-1029)这些思潮影响并激发北京大学的学生“反对帝国主义的控制”、争取“民族独立和自治”的斗志,向往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希望“从苏联那里寻求鼓舞”,实行“俄国式的革命”,彻底改变当时中国形态,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族富强。
1918年11月15日,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的消息传到中国,各界一片欢腾。政府放假3天,北京万人上街庆贺,举行一系列庆祝胜利的大会,“学界举行提灯。政界举行祝典”[28]。北京大学的师生更是欢欣鼓舞。“11月14、15、16日,北大放假三天,为庆祝协约国胜利,在天安门外举行讲演大会”,倾全校之力宣传。“十天以后,又在中央公园(即现在的中山公园)举行了连续三天(28、29、30日)的讲演大会。参加讲演的有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陶孟和、陈惺农、胡适以及学生代表江绍原等。讲演者大都按照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调调,宣传协约国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是‘正义'、‘平等'、‘互助'的胜利。……惟有李大钊不同凡响,他发表了题为《庶民的胜利》的著名讲演……不是着眼于协约国的胜利,而是着眼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把十月革命看作是第一次大战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这就明显地反映了他的无产阶级倾向和对历史发展的深刻洞察力。”[29](P82-83)
北京大学组织的三天讲演大会,虽先后有七人登台演讲,但《新青年》只选刊了蔡元培、陶孟和、李大钊三人的演讲稿,并冠题为“关于欧战的演说三篇”。蔡元培的演讲题目为《劳工神圣》,突出“劳工神圣”,强调“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30]陶孟和的《欧洲以后的政治》提出:“欧战”胜利警示中国政治须打破四种观念:一是秘密的外交、二是背弃法律、三是军人干政、四是独裁政治。这四种东西“在国内要扰乱国内的治安,在国外要酿起世界的纷争”。[31]陶孟和虽是针对当时中国政治现实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论点有一定现实意义,但终究没有独特的新见解。
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强调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是协约国的胜利,不是武力的胜利,也不是一般所谓“公理、正义”的胜利,而是一种新的理想、新的主义、新的制度的胜利,是劳工的胜利。李大钊说:“这回战胜的,不是联合国的武力,是世界人类的新精神。不是哪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庆祝,不是为那一国或那一国的一部分人庆祝,是为全世界的庶民庆祝。不是为打败德国人庆祝,是为打败世界的军国主义庆祝。”李大钊演讲的最大亮点是揭示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指出:“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李大钊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阐释战争爆发“真因”,并指出战争的结束全赖劳工的觉悟,协约国的胜利完全是庶民的胜利。李大钊没有追逐主流舆论话语,赞颂协约国的胜利,也不就“战争”论“战争”,而是将第一次世界大战放在革命的延长线上,赞颂“庶民的胜利”,并热烈欢呼这种“庶民的胜利”,向往“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社会“变成劳工的世界”,人人都有“变成工人的机会”,消灭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并强调这种“革命”构成一种潮流,“这种潮流,是只能迎,不可拒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准备怎么能适应这个潮流,不可抵抗这个潮流。人类的历史,是共同心理表现的记录。一个人心的变动,是全世界人心变动的征幾。一个事件的发生,是世界风云发生的先兆。一七八九年的法国革命,是十九世纪中各国革命的先声。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32]李大钊突出强调,社会主义思潮将“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对社会主义充满必胜的信心。
《庶民的胜利》限于篇幅及演讲题旨,没有展开谈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又写《Bolshevism的胜利》详细论述十月革命,明确提出世界大战的结局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Hohenzollern 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廿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我们对于这桩世界大变局的庆祝,不该为那一国那些国里一部分人庆祝,应该为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庆祝;不该为那一边的武力把那一边的武力打倒而庆祝,应该为民主主义把帝制打倒,社会主义把军国主义打倒而庆祝”,最后,热烈欢呼“赤色旗到处翻飞,劳工会纷纷成立”,高度赞扬“俄罗斯式的革命”就“像这般滔滔滚滚的潮流”,“挟雷霆万钧的力量摧拉”障阻的力量,扫荡“历史上残余的东西,——什么皇帝咧,贵族咧,军阀咧,官僚咧,军国主义咧,资本主义”,彻底改变世界,“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Bolshevism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Bolshevism的凯歌的声”。[28]李大钊激情澎湃,笔力千钧,充满坚信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念。
李大钊挖掘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社会主义胜利的进步意义,深刻改写了中国人对“十九世纪文明”和“二十世纪文明”的感觉与把握,把“个人”“解放”的思想启蒙运动推动成为民族解放的运动,造成一个民族、社会“解放的时代,现代的文明是解放的文明。人民对于国家要求解放,地方对于中央要求解放,殖民地对于本国要求解放,弱小民族对于强大民族要求解放,农夫对于地主要求解放,工人对于资本家要求解放,女子对于男子要求解放,子弟对于亲长要求解放。现代政治或社会里边所起的运动,都是解放的运动”。李大钊热烈欢迎“解放的时代”的来临,倡导个人解放紧密相连“大同团结”。李大钊说:
解放的精神,断断不是单为求一个分裂就算了事,乃是为完成一切个性脱离了旧绊锁,重新改造一个普通广大的新组织。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这个性解放的运动,同时伴着一个大同团结的运动。这两种运动似乎是相反,实在是相成。[33]
李大钊强调,个人的解放并不意味个人欲望的放荡不羁,也不意味个人可以随心所欲。个人的解放具有一种内在的方向性规定,衡量标准即是否有利“大同团结”,是否有利于社会整合。只有与“大同团结”的方向相一致的个人解放,才是真正的个人的解放。个人的解放与“大同团结”的内在价值判断,“是以适应他们生活的必要为标准”。因为只强调个性的解放,必将削弱群体的凝聚力,甚至导致群体的涣散;一味强调“大同团结”,势必压抑束缚个人的个性独立自主的发展,甚至导致以群体性替代个性,破坏人的解放的价值观,因此,必须在个人解放与“大同团结”间寻找一个合理的契合点。这个理想状态“就是一个新联合”。
李大钊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北京大学的学生,不仅成为五四运动的思想资源,而且为五四运动储备了人才资源。因为他热心致力校内校外的社团工作,热心扶助学生的社团活动,通过学生社团与学生亲密接触,在学生中有相当大的影响力。1918年秋,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学生发起成立新潮社,编辑为傅斯年、罗家伦,李大钊担任顾问。②《新潮》创刊号刊发《今日之世界新潮》称颂十月革命:“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26]这种论点与李大钊《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观点、用词极为相近,受李大钊思想的影响非常明显。李大钊努力引导《新潮》成员关注民族解放和独立运动的大趋势,传播社会主义新思潮。顾颉刚回忆说:“李大钊同志曾给过《新潮》很多的帮助和指导。他虽不公开出面,但经常和社员们联系,并为《新潮》写稿。”[34](P125)
李大钊与《国民》杂志社的关系最密切。《国民》编辑为许德珩、陈剑修等,在李大钊指导下,发表了很多反帝反封建的文章,突出强调反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李大钊也常在《国民》发表文章,尖锐揭露日本侵略中国阴谋。第五期还发表了《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前一部分,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译本。许德珩回忆说:“李大钊是《国民》杂志社的总顾问,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35](P224)国民杂志社有成员189名[34](P9-14),培养了一批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骨干力量,如北京大学的学生邓中夏、许德珩、高君宇、黄日葵等,都得到李大钊的直接教育和精心培养,成为进步力量的代表,“在‘五四'运动中曾起过中坚的作用。该社的负责人周长宪、吴迪恭等,均是北大法律系学生。周还是《国民》杂志的主编之一。国民杂志社的成员遍及北京国立八校,在北大的会员尤为众多”。他们团结在李大钊周围,成为“一批追求进步、立志社会改革或思想激进的青年”[36](P279),对北京的学生有很大的影响,大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积极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因为李大钊的影响,五四运动前夕,“《新青年》、《新潮》、《国民杂志》就开始合流,而在文化运动和救国运动之间做媒介的,是李大钊先生”[36](P285)。
1919年5月3日凌晨,蔡元培从汪大燮处获知,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受挫,德国是战败国,但它在山东的租界的权益没有归还中国,而是被划给日本,中国外交代表团将被迫签约。蔡元培把消息分别告知傅斯年、许德珩等人,北京大学的学生群情激愤。北京大学曾“以欧洲和美国为楷模、怀有改革中国理想的年青人和知识分子殷切地盼望着1919年巴黎和会会取得好的结果。他们希望美国政府支持取消这些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的完全主权。然而,当这些和平的缔造者同意日本继续干涉中国的时候,这些希望破灭了,这一决定导致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充当先锋的是中国城市的学生和知识分子”[27](P1065)。这些“充当先锋”的学生就是《新潮》社和《国民》社的学生。3日下午1时,北京大学“贴出通告,召集本校学生,于晚间七时,在法科大礼堂开会。是晚参加的北大学生,有一千多人”。“这个转变了中国命运的五三晚间大会,是在感情激昂的气氛中进行的。大会主席易克嶷,湖南长沙人,为当时《国民杂志》主干,为理本科化学门一年级生。他主持会议时,态度沉着,口齿清楚。”学生们群情激愤,“最后大会决议,通告各校学生,于明日(即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大会,会后游行”[37]。傅斯年是五四游行总指挥,许德珩用文言文起草《北京学生界宣言》;罗家伦临时受命,用白话文撰写《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喊出振聋发聩的“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口号,敲响全民警世钟:“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这份宣言精悍有力,更具煽动性,气势如虹,振奋人心,传诵至今,“反映了文学革命的效果,一般人都认为它是青年知识分子的精神最好的表示”[38](P151-152)。《新潮》《国民》的“主干”发起和领导五四运动,《新青年》的影响功不可没。
由此可知,五四运动是青年学生基于爱国心理,要求外争领土主权、内除国贼而发起的,是一场纯洁的爱国运动。这场“运动唤醒了这个国家,唤起这个国家的各个阶层反抗外国尤其是日本的干涉。运动的领导者在演讲、报纸和小说中发出誓言,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重建国家的统一”[27](P1065),奠定了五四运动“是我们的爱国运动”[39]的思想资源及优良传统。
四
新青年社团通过《新青年》《每周评论》影响、联系和团结了进步知识青年读者,紧密联系学生,引导学生,发展革命力量,推动了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李大钊亲自组织、指挥学生运动,胡适、钱玄同参与学生的游行活动,胡适还与刘半农及傅斯年、罗家伦多次亲赴警厅保释被拘学生,保护学生,支持学生。陈独秀以《每周评论》为舆论平台,不仅影响并推动学生参与运动,而且大造舆论声援五四运动,还亲自参加街头游行抗议活动,引导运动的深入发展,推动“民族主义情绪在中国蔓延”[27](P1065),奠定五四运动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自主的爱国主义传统。
新青年社团是五四运动的重要推动力量,影响着五四运动的发生、发展进程。“五四不是一件孤立的事,五四之前,有蔡元培校长领导之下的北京大学教授与学生出版的《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所提倡的文学革命,思想自由,政治民主运动。五四之后,有全国知识青年热烈参预的新文艺运动、新思潮运动,和各种新的政治运动。”[40]这场运动因而烙有鲜明的新青年社团印记。此外,五四运动领袖傅斯年、罗家伦都是新青年社团重要成员。他俩致胡适的信就说:“在外人看起来,《新青年》的分子是一体,几个人的行动,还是大家共负责任。”[41](P4)
钱玄同亲临五四运动游行现场,并始终陪伴学生参加游行,是北京大学为数极少的几个参加五四游行、保护学生的教授。5月4日下午,游行学生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抗议受阻,愤而转向曹汝霖宅,一路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并发生“痛殴章宗祥,火烧赵家楼”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高潮。这一天的学生大游行,北京大学的教师“没有参加游行,但表示同情,始终陪着学生走的也有,如钱玄同先生,即其中之一”[42]。钱玄同“始终陪着学生”,支持学生,保护学生,不仅代表新青年社团从只重思想革命走上干涉政治的社会革命的转变,而且表明“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43]。
北京大学学生大游行,蔡元培是重要的推动者。游行学生被捕后,蔡元培积极组织营救,保护学生。“为了援救被捕学生,五月五日上午,北大召开了学生大会,蔡元培校长也出席了。会上,决定成立统一的北大学生干事会,决心把斗争坚持下去,进一步争取全市学生的联合行动。”随着运动的深入持续发展,学生们的行动更加过激,“反动政府也着了慌。五月七日,被捕的同学全部获释,但是军阀政府又提出‘追查肇事学生、依法惩办'和‘严禁学生扰乱社会秩序'等,进一步迫害爱国学生,而对卖国贼却不予惩办。学生们继续坚持斗争,外出讲演,罢课抗议”[36](P281-282)。
李大钊是五四运动直接指挥者。5月1日,李大钊发表《五一节May Day杂感》,第一次公开提出采取“直接行动”[44]进行斗争,推动群众的革命行动。五四运动发生时,虽没有亲临五四游行现场,但北大图书馆主任室是五四运动的指挥中心,学生代表穿梭往来交流信息,讨论每一个行动方案。为扩大五四运动的影响,李大钊建议北大学生干事会派黄日葵、许德珩到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地联合学生运动;派邓中夏先到长沙,再到上海;同时发动北京的学生坚持罢课请愿,并“组织了很多露天讲演队,劝国人买国货,宣传对日的经济抵制。全国各地的学生也纷纷响应”[40],不仅罢课声援北京学生,还发动工商界罢工罢市,支持五四运动。
5月4日,胡适不在北京,而在上海迎接杜威访华,没有亲历五四运动。5月7日,陈独秀致信胡适,通报4号当天的情况,不仅希望胡适利用其影响力支持五四运动,而且建议胡适为新青年社团的“自卫记”,必须尽快“想出一个相当的办法”。[3](P42)陈独秀还运用《每周评论》的舆论影响推导运动的方向。5月4日,学生游行时悲愤激昂的情绪,《每周评论》做了详细报道,并全文刊登《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胡适虽在沪陪杜威访华,但高度关注学生运动,积极寻机参加学生的游行活动,用实际行动支持学生,影响运动的深入发展。5月7日,上海在公共体育场召开国民大会,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胡适也挤在与会人群中,参加学生游行大会。他说:“我要听听上海一班演说家,故挤到台前,身上已是汗流遍体。我脱下马褂,听完演说,跟着大队去游街,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我一身衣服从里衣湿透到夹袍子。”[45]
胡适陪同杜威回到北京后,听到数百学生被捕的消息,极为震惊,马上与学生代表联系,全心投入营救被捕学生,保护学生,决心与游行学生共命运。5月12日下午,傅斯年“先到文科会同胡适之、陈百年、沈士远、刘半农四先生同赴警厅,交涉‘五七'被捕同学事”[46]。
6月9日,胡适又与刘半农、陈大齐、罗家伦等一起到警厅保释被捕学生。胡适去探望学生的路上,看到“北河沿一带,有陆军第九师步兵一营和第十五团驻扎围守。从东华门直到北大第三院,全是兵士帐棚”[40]。胡适还对舆论界表示,被拘禁学生的待遇十分悲惨,缺少被褥和食物,受伤和生病都得不到医疗。胡适夸大部分事实,故意激发社会情绪,激起社会舆论关注学生,支持五四运动。
陈独秀更是大力支持学生运动,并在《每周评论》大造舆论,支持、宣传五四运动,激发北大学生的斗志。《每周评论》连续出版了第21号(5月11日)、22号(18日)、23号(26日)三期“山东问题”特号,激情高涨地谈政治,组织舆论声援五四运动,推动运动更加激烈地发展。陈独秀还刊发评论,公开赞颂学生的行为是爱国行动。陈独秀说:
国民发挥爱国心做政府的后援,这是国家的最大幸事。我们中国现在有什么力量抵抗外人?全靠国民团结一致的爱国心,或者可以唤起列国的同情帮我们说点公道话。人心已死的中国,国民向来没有团结一致的爱国心,这是外国人顶看不起中国人的地方,这是中国顶可伤心的现象。现在可怜只有一部分的学生团体,稍微发出一点人心还未死尽的一线生机。仅此一线生机,政府还要将他斩尽杀绝,说他们不应该干涉政治,把他们送交法庭讯办。像这样办法,是要中国人心死尽,是要国民没丝毫爱国心,是要无论外国怎样欺压中国,政府外交无论怎样失败,国民都应当哑口无言。[47]
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支持学生运动,认为中国要“抵抗外人”,必须“全靠”学生“团结一致的爱国心”,爱国力量就隐藏在学生中,而五四运动就是学生“做政府的后援,这是国家的最大幸事”。
5月18日,李大钊公开著文指责北洋政府卖国,号召推翻军阀统治:“全因为现在的世界,还是强盗世界。那么不止夺取山东的是我们的仇敌,这强盗世界中的一切强盗团体、秘密外交这一类的一切强盗行为,都是我们的仇敌啊!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决、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48]
5月1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总罢课,参加学生达2.5万余名,提出“和会不得签字”,日本归还山东权益,“惩办国贼”。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响应,造成全国学校罢课。北大学生还组织讲演团,走出学校,到“街上演讲宣传,成心让警察抓去,然后再派更多的学生出来,使其抓不胜抓,最后好迫使政府无法善后,而让步妥协”[36](P267),造成一场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6月3日,北洋政府开始镇压学生运动,抓捕的达900人之多。陈独秀描述这天如此的阴惨黑暗:“民国八年六月三日,就是端午节的后一天,离学生的‘五四'运动刚满一个月,政府里因为学生团又上街演说,下令派军警严拿多人。这时候陡打大雷飐大风,黑云遮天,灰尘满目,对面不见人,是何等阴惨暗淡!”[49]陈独秀之所以强调6月3日“陡打大雷飐大风,黑云遮天”,全因为这天逮捕的学生是以街头演说、抗议示威、罢课等罪名,也就是言论罪、思想罪、表达罪、行使宪法权利罪等罪名抓捕学生,造成中华民国有史以来最黑暗最恐怖的一天。
6月3-4日两天,北京逾千名学生被捕,引起陈独秀的高度关切。6月8日,陈独秀发表《研究室与监狱》,鼓励学生。陈独秀说:“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了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50]字里行间洋溢着战斗的激情和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对学生是极大的赞扬和支持。
陈独秀不仅以《每周评论》为舆论阵地,推动五四运动发展,运动高昂的政治激情也促使他更加激进,在社会革命的路上奋勇前进。陈独秀“的性情一贯地急躁,反对北洋军阀尤其激烈。有一天,他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③,大约有十几条。交由胡适,把它译成英文”[51](P61)。6月11日,他亲自去散发《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12日,陈独秀[终因政治活动]被捕入狱。陈氏是在发散他那自撰并出资自印的反政府传单之时被捕的。”[8](P353)陈独秀是看到五四运动进入胶着状态,需要有人牺牲才能推动运动进一步深入发展时,他决心牺牲自己,达到唤醒民众的目的。陈独秀认为:“五四运动的结果,还不甚好。为什么呢?因为牺牲小而结果大,不是一种好现象。”[52]
13日,北京《晨报》首先披露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全国各地报纸都相继报道,舆论界震惊,各省各界纷纷为陈独秀辩白,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关注,吁请政府当局立予开释。北京大学守旧派教授也奔走营救陈独秀。“刘师培联合北京大学、民国大学、中国大学马裕藻、马叙伦、程演生、王星拱、马寅初等数十位教授,领衔致函京师警察厅,要求保释陈独秀。”[53](P274-275)陈独秀在《北京市民宣言》中提出的政治目标,受到广泛支持。
五四运动因有陈独秀和逾千名学生被捕,激发全国各界的强烈抗议,支持五四运动,反抗政府压迫,政府面临巨大的政治压力,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6月28日,北洋政府拒签《巴黎和约》,并在此前罢免了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的官职。五四运动取得胜利,陈独秀的政治声誉也空前高涨。
总之,五四运动深受新青年社团的影响,反过来又推动《新青年》“干涉政治”,造成《新青年》色彩逐渐变红、变得更加激进,终于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党刊。历时近两个月的五四运动“轰动了全国的青年,解放了全国青年的思想,把白话文变成了全国青年达意的新工具,使多数青年感觉用文字来自由发表思想感情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不是极少数古文家专利的事,经过了这次轰动了全国青年的大解放”[40],不仅为新文化运动做了总结,也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思想资源及人才队伍,成为20世纪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遗产,拉开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社会革命运动。《新青年》与五四运动因此成为一种文化/政治符号,成为中国各阶级都可以接受的一种精神载体,奠定其爱国主义传统。
注释:
①此数据根据北京大学未名科技文化发展公司、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新青年》光盘检索统计。
②《新潮》创刊号刊发《启事》:“本部敬请图书馆主任、庶务处主任为顾问,所有本志印刷、登广告、发行及其他银钱出入事项,即由两主任分派出版部杂务课、会计课事务员执行之。”(《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3日。)《启事》所说的“图书馆主任”就是李大钊。
③《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9日)印刷成一张A4纸的篇幅,上半为汉文,下半为英文,全文如下:“中华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下:(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各处接到此宣言,希即复印传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