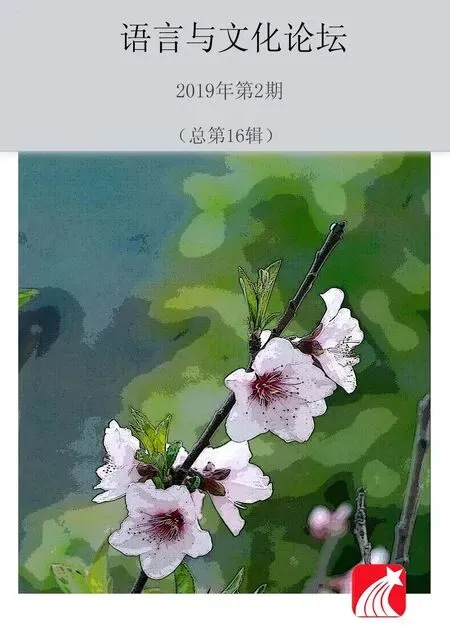到世界去:从《平凡的世界》到《耶路撒冷》
◎ 卢 铭 陈蘅瑾
“到世界去”,是我们常提的议题,无论是现流行的“诗和远方”还是鲁迅青年时的“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①其本质还是到世界去。梁永安曾在《人生没有真正的毕业》中讲到过,文学“是彷徨、是寻找”,他认为信仰是寻找的“终极”。②罗兰·巴特亦于《写作的零度》中提及,小说是“死亡”,它将生命与记忆变成“命运”与“有用的行为”,将延续变成“有意义”和“有方向”的“时间”。③然而,“到世界去”,如何去,怎么去,对我们来说还是个难题,相信路遥和徐则臣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平凡的世界》和《耶路撒冷》是这两位作家的代表作,通过对两位作家作品的分析,或许幸得寻找到一条属于我们“到世界去”的路。
一、“群体无意识”烛照下的“出走”问题
两部作品关于地域的转换都是在离去归来再离去的模式下进行的。这结构与鲁迅小说中的“归乡模式”很相似,都暴露出自觉青年的“出走”问题。两部小说的地域转换由小到大,从一个群体意识到另一个群体意识,最后走向世界。他们似乎都有意无意地抗拒着“群体无意识”的同化,而维系着到世界去的媒介意象“形异而意同”,这些共性显然显现了“出走”这个问题,是城市边缘自觉青年的宿命。
关于归乡模式,钱理群曾于《现代文学三十年》中解释道,叙事者在亲历自己的故事同时,还在讲述着他人的故事,两者相互交汇,形成一个“复调”。④《耶路撒冷》毫无疑问是一部典型的归乡模式小说,而《平凡的世界》中,我们假如仅从少平的视角上看,这也当然是属于归乡模式小说。但不同的是,前者更强调离去途中的精神挣扎,后者更侧重离去途中不断丰富的精神世界。
而在他们的离去与回归之途,从乡土到城市,城市到乡土又到世界。从单一到繁多,繁多回归单一,最终又到无限,是两部作品所转换的地域意象的共性所在,而在两部作品的地域转换中,双水村—原西县—黄原市—铜城矿场—双水村—世界、花街—淮安—北京—花街—耶路撒冷,在这两个地域转移的路径上,我们可以分为三个过程:“在”而“不属于”的乡土、迷人而又困苦的城市、永远都在前方的乌托邦世界。
乡土、城市与乌托邦,可以说是每个时代自觉青年的永恒意象,正如荣格所说的“原始意象”,人类的精神和命运都蕴含在这每一个“原始意象”当中,“每一块原始意象”都有着我们祖先在历史长河上循环往复的“欢乐和悲哀的残余”。⑤他们都是前仆后继地从乡土逃到城市,又从城市逃到世界,他们不断地从一个群体意识,逃向另一个群体意识。李丹指出,徐则臣的北京不仅仅是一座“充满希望的逃城”,更是一座“充满迷魅的罪恶之城”,⑥城市边缘的人,弃乡而来,终又逃城离去。其实《平凡的世界》亦然,无论是黄原还是铜城,只是少平人生的一站,他不会停,他会一直往前。
在离去之中,无论是《平凡的世界》还是《耶路撒冷》,他们都是处在一种挣扎的、矛盾的生存困境中,即钱理群所说的“在”和“不属于”的关系,这是远大理想与平凡生活之间选择的困惑,是奋斗与回归、不甘与落寞、剧变与安定、开创与陈旧等等“两极间摇摆的生存困境”。
当然,这里所说的“不属于”是指精神上的,如《平凡的世界》中的少平,他已经通过书本见识过了真的世界,他不甘平凡的心,怎么会是双水村这个“小天地”⑦所能容下的呢;《耶路撒冷》中,平阳觉得他27年的生活从未如当辅导员时那样漫长,“漫长地令人厌烦”。⑧《平凡的世界》中高中结束,少平不得不返乡务农,但见识了书中的世界之后,少平并不甘愿面朝黄土背朝天地挥一辈子锄头,他觉得他的价值不应该在农田上,而是在世界上;《耶路撒冷》中当烦琐的辅导员生活与自己的学术野望完全不符时,平阳毅然地选择离开。他们从“个体”进入“群体”,“有意识人格的消失,无意识人格的凸显”,⑨他们与群体的意志交互融合,最终变为群体的一分子。他们发觉,他们陷入一种“个人”与“群体”的困境之中,所以他们如果不愿“群体化”“平凡化”,就得选择出走。
而两部作品承载出走的媒介,形异而意同,正如荣格不断强调,意象并不是对于外界的“反映”,而是实践中“内心体验”因而诞生的“幻想”。⑩
小说在实现地域转换时,《平凡的世界》靠的是汽车,《耶路撒冷》靠的是火车,其实所有的小说也大都有此类意象,但是这两部小说不同的是,它们自始至终串联了整部作品,它们是连接乡土与城市的纽带,也是外面世界的信使,是脱离“群体无意识”的媒介,是自由和恐慌的象征,是孙少平和初平阳出走的实际精神的载体。
《平凡的世界》中双水村的汽车意象其实全部体现在金波父亲金俊海的职业上,对于“只走过石圪节的农民来说”[11]金俊海是脱离双水村这“群体”的“个体”,这也是孙少平最初关于世界的印象。在那个时代,双水村确实近乎与世隔绝,而自觉青年想出走的愿望更是强烈的,在双水村,孙少平找不到可以对话的人,这是孤独的、痛苦的。而金俊海的汽车无疑是少平小小世界的明灯,汽车承载了他出走的精神,他借着汽车从双水到了原西,从原西到了黄原,又从黄原到了铜城。毫无疑问,汽车是少平那一代人到世界去的媒介,亦是改革开放初期“个体”脱离“群体”的主要承载意象。
而在《耶路撒冷》中,火车是连接北京与花街的媒介。在开篇之初,平阳就是坐着火车归来,而铜钱想用石头拦火车,通过火车到世界去,火车意象在这里是明显的,小地方的人,通过火车这个载体,到达城市,实现到世界去的理想。《耶路撒冷》的《到世界去》那一章的结尾写道:“火车确实停下来了,那个年轻人死了。围观的人一部分哭着回家了,一部分哭着继续站在那里,在想一个到世界去的大问题。”[12]这个问题其实就是一个“个体”与“群体”、世界与野心、火车以及现代物质文明的吸引力和压迫感的问题。
出走意象,体现在转换媒介汽车与火车这两个载体上,而这两个载体,承载了少平与平阳到世界去的最终追求,是“个体”脱离“群体”独立化的象征。在载体的这个问题上,又无不再次印证乡土与城市二元化的情况和城市边缘青年对于世界的渴求。
杨希帅曾评《耶路撒冷》,这样平阳的出路只有不断地出走,平阳出走的意义不在于寻找的终点,而是他出走本身所具有的一种不断行走的精神意象。这种意象象征着独立个体的人对“庸常生活的反抗姿态”,更体现了自觉青年对于自由的渴求。只有不断出走,才能使生活变得有意义,不再像做辅导员时感觉生命是那么漫长。出走这一精神意象其实就是“生活的自由流动与精神的自由飞翔”。[13]
他们的出走正是要脱离群体泯灭个体的状态,即勒庞于《乌合之众》中所说,人无法在群体之中保持自我,从而由个体变成了“由意志支配的玩偶”。[14]自觉的青年惧怕同化,所以他们需要不断地出走,以此来对抗同化的状态。
而在归来方面,《耶路撒冷》的回归与《平凡的世界》恰恰相反,平阳回归是为了卖大和堂筹钱去耶路撒冷,少平回归是为自己、为父亲,建一孔窑洞。这里体现不同时代自觉青年的不同状态,包含了父母与孩子、人与家庭等关系的转变。一个是卖家离国,一个是建房立尊,安土重迁的观念在时代飞速发展下,逐渐淡去。他们不断靠近乡土,但记忆又不断远离,乡土成了记忆中的故土,正如不断变化的双水村与即将改建的花街,其实他们与故乡越来越远。他们的回归,无论是卖房还是建房,都成了“到世界去”前,“个体”脱离“群体”的一种意象符号。而在再次离去中,无论是《平凡的世界》中励志成为保尔·柯察金的少平,还是《耶路撒冷》中去往心中圣城的平阳,他们都无法回避,人在去向世界,“个体”与“群体”、高空与落脚于大地之间,这个自觉青年的出走问题。
二、“到世界去”背景下他们各自的“存在主义”
萨特在他的《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中说过,因为人的生活,人生才被“赋予意义”,人生的价值在于我们可以“选择意义”,人类所需要的是,理解什么是自己“无法挣脱”的,并找到自己。[15]《平凡的世界》《耶路撒冷》这两部作品的中,无论是长子、幼子、反叛者还是沉默者,他们都在寻找中发现自己的“存在”,在寻找中发现自己“无法挣脱”的,又在寻找中选择他们的意义,然后“到世界去”。
纵观现当代文学史上的作品,幼子形象大多是反抗和斗争的代表。无论是《雷雨》中的周冲、《家》中的觉慧,又或者《平凡的世界》的少平,还是《耶路撒冷》中的平阳,他们的出走其实是寻找一种他们“存在”的凭证,他们在家庭、故土之中自我的凭证被群体化、渺小化,因而他们想要证明自我的“存在”,只能选择反抗来体现“存在”。所以他们反抗,他们出走,回归然后“到世界去”。
关于长子,老舍曾这样说过,他们是“旧时代的弃儿,新时代的伴郎”。[16]他们承担着一切的“存在”,但这一切的“存在”却都不管他们,长子是新与旧的交界,是新与旧的缓冲,他们的“存在”是家族的延续。但是幼子则是全新的,他们完全别于旧的,因而幼子的“存在”意义更多的是自我价值的实现,所以少平渴望出走,反抗蒙昧的生活状态;所以平阳也渴望出走,反抗无意义的生活状态。其实出走亦是新与旧的一种“存在”方式的对立。
幼子的身份似乎成了他们反抗与出走的基础,不同于长子的宿命“在出生伊始已经敲定了一大半”,[17]幼子无须承当家族的重任,无论是延续还是复兴,这一切统统与幼子无关。幼子与生俱来有一种到世界去的物质优势与在家庭中体现自我“存在”的先天弱势,所以他们不需要太过顾忌家庭环境的因素与眷恋家庭中的细微“存在”,《平凡的世界》中少安是孙家“到世界去”的牺牲者与“存在”的承担者,他放弃了学业回家务农,放弃了“到世界去”的选择,选择了在家庭中自我“存在”。而有了少安在前的牺牲与“存在”的接替,少平才有基础与必要“到世界去”。《耶路撒冷》亦然,平阳之前有个姐姐平秋,父母有平秋照顾,祖传的大和堂的“存在”有平秋继承,平阳才义无反顾地“到世界去”。
在地域转换下看,随着人物在地域上的转移,其身上所赋予的意义,亦随之迁移。所以当家庭中的幼子走向世界,幼子身份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专栏作家初平阳、学者初平阳、煤矿工人孙少平。
关于身份的改变,其实是一种对于生活的介入。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过,“生存即介入”。[18]其实,到世界去就是一种对于常态的反叛、一种对于生活的介入。少平是,平阳也是,但是他们的反叛并不彻底,还是掺杂着常态的痕迹,而两部作品中最为典型的反叛者是金波与易长安。萨特又说,人除去自己所理解的以外,其实什么都不是。作者关于金波与易长安的设定也极为相似,他们的反叛既是作者想表达的另一种到世界去的“存在”,亦是对于平阳与少平到世界去的比对。
《平凡的世界》中,金波与少平年龄相同,金波长得白净与安稳,但是他的心却是生硬,他做事也手脚麻利,在班长顾养民、孙少平与郝红梅三人青春期懵懂的关系上,金波毫不犹豫地打了顾养民一顿。而又在关于藏族女子的爱情上,金波甘愿放弃一切而去追逐爱情。这是纯粹的生活的反叛者,他对于生活的“介入”便是为了自由抛弃一切。
但说到抛开一切的,易长安更为彻底。易长安为了反叛父亲的意志,自己把父亲取的名字从震生改为长安,父亲叫他学理,他学文;父亲叫他去城里教书,他去乡下教书。“他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父权高压下的另类代表。”[19]在生活前期,父亲是世界,所以他反叛父亲,之后社会是世界,他又反叛社会。他本可以在乡下安心教书,但是他偏要反抗那不合理的情形,所以他来到北京。而在北京他也是可以干正当职业的,但是他偏要做假证。这是易长安的反叛之处,处处体现着反叛的荒唐,这亦是他对于生活的一种“介入”,是新时代反叛者自我“存在”纯粹的一种体现。
关于他们的“到世界去”,金波最后去青海寻找他的藏族姑娘去了,易长安为了回来签署建立斜教堂修缮会的文书而被抓进监狱,他们“从无到有,从不存在到存在”。[20]他们二者最终皆是困于情,金波困于藏族姑娘,易长安困于景天赐,但前者是爱情,后者是救赎。这是他们的到世界去,他们为了心中所想不顾一切,从这一点上来说,他们的程度强于少平、平阳,但到世界去的本质又是一致的,都是实现自我的梦想和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
少平、平阳、金波、长安他们四者都为了自我强烈的“存在”出走,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顺从者润生与吕冬,卑微且懦弱地“存在”。
润生从小在“强人”田福堂的影子下长大,在家他没有话语权,在外也是少有存在感,他看似没有什么追求,走一步算一步,但是在遇到寡妇郝红梅之后,他的存在感突出了,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男人,在父母强烈的反对下,他不再懦弱,选择了爆发,他反抗父亲的意志,甚至与之断绝关系。这其实亦是一种“存在主义”的体现,面对强权,润生自然地低下了头,但是在“更弱者”郝红梅面前,他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男人”,润生需要一种“存在”的凭证,而郝红梅显示了润生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一种“存在”,润生的世界出现了,所以他会为了世界而爆发,从而到他的世界去。《耶路撒冷》中的吕冬亦然。
吕冬也是生活在强势的母亲的影子之下,面对母亲的强势,吕冬沉默,在母亲的安排之下,按部就班地生活,甚至于妻子也是母亲挑选的,而妻子也是个极为强势之人,在这两个女人强势的重压下,吕冬疯了,或者说“被疯了”。面对强权的“弱化”,精神病院反而是一种“存在”的诞生。在精神病院中,吕冬是前所未有的轻松,甚至翻墙与牧羊人谈天说地。吕冬这是一种躲避,亦是一种爆发,这一种爆发没有直面强权,而是迂回消解。但这种爆发远没有润生的纯粹。
这种纯粹是一种无所顾虑,而这种顾虑随着年龄和时代不断增加,20刚出头的润生与30多岁的吕冬是有的区别的;80年代与21世纪也是有区别的。当简单的80年代生活到了繁杂的21世纪,一切都变得难以决断、难以抗争。正如21世纪评论家们提出的“重返80年代”一样,21世纪缺少了80年代那样的“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而新时代是个“无根”而“无序”的时代。[21]在无序、无根的时代要么是像平阳、长安一样当一个纯粹的反叛者,要么就只能是一个懦弱的逃避者。而吕冬属于后者,所以他面对权威选择逃避,这种情感延续到今,便如现在盛行的“鲁蛇主义”或“丧文化”等以失败、挫折、自嘲为主题的青年次文化,他们对于“存在”与“意义”不以为意,反而认为无意义是最大的意义。这个是我们不得不警惕的文化现象,亦是我们到世界去的一大阻力。
三、“到世界去”的精神内核
《平凡的世界》从文本分析上来看,是一部“成长小说”,“它向每一位底层青年许诺,只要勤奋上进,就能在现实社会中以合法的方式取得成功”。[22]《耶路撒冷》亦然,他讲述了花街那一群少年的成长奋斗史。他们在描写“到世界去”的过程中,都将苦难化为前进的精神动力,小说都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的普世价值观:有付出就可能会有收获,但不付出就绝不会成功。
但《耶路撒冷》本质是通过更深一层次的忏悔和救赎的寻找自我。平阳他们的出走与回归,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景天赐自杀事件,这件事在他们心底埋下出走和救赎的根源。天赐的死亡,像命运的一根线,将花街的那一群人都联系在一起。天赐发疯是因为在雷雨天与长安比赛游泳,被雷劈而发疯;杨杰为了炫耀,给了天赐割腕的手术刀;福小因一时的挣扎,错过天赐的抢救时间;平阳因害怕或是因福小阻止(作者此时在描述天赐自杀这件事是模糊的,当时平阳具体干了什么,小说没有明确交代,其实这里体现了平阳的忏悔与难以面对)而迟疑,也错失了天赐最佳抢救时间。
平阳到耶路撒冷,是一种自我救赎,他不断地“出走”,不断地寻求人生的真理,其实是一场自我救赎之路。花街的那一群人也渴望得到救赎,所以当听到要建立斜教堂修缮基金会时,他们都纷纷回归,他们想要忏悔,得到救赎。而这一场救赎之路,其实是一场寻找自我之路。徐则臣通过《耶路撒冷》,讲述几代人对于天赐自杀的追悔与救赎的同时,暗含着一个更为深远的永恒的人生命题,那就是在这样一个断裂与碎片的世界之中,“人们需要寻找自我的根本与内心解放,本质意义是重新确立与自我出发走向世界的精神自由”。[23]
少平的“到世界去”亦是一场寻找自我之路,在思想被启蒙,离开农村之后,他的精神极渴望远行,但是他不知道世界的终点是何方,他只能不断往前,所以他来到了黄原揽工,之后又到了铜城挖煤。这是少平的一种自我选择,但又是现实给予少平的定向选择,是或者否。而想要“到世界去”的少平其实毫无选择。少平只有一直往前,而往前便是“到世界去”,这与平阳的多元化选择是不同的。在逐渐多元化的今天,选择越来越多。这种转变,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必然的结果。
其实,路遥与徐则臣对于现代化,都体现出一种焦虑,路遥的是若隐若现,“气势磅礴的火车头喷出一团白雾淹没了他”;[24]徐则臣的焦虑是明朗清晰的,“你们这辈人,不会再用火煮饭烧汤了”,[25]到了现在,现代化则是我们需要直面的最大的诱惑和焦虑。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导言中所说,《一九四二》显示了痛苦对于人的限制,而《美丽新世界》却因过度的娱乐而丢失自由。简单来说,奥威尔的不安是“我们憎恨的东西”将会毁灭我们,而赫胥黎的不安是,“我们热爱的东西”将会毁灭我们。[26]现代化,便是我们现在又爱又恨的东西,稍有不慎,它将会毁了我们。
而为了抵抗这种焦虑,他们都选择让笔下的人物出走,以出走来抵消现代化的焦虑,以出走来寻求现代化中最为平衡的点。在一个群体意识到另一个群体意识的转移之中,去寻找属于自己“到世界去”的路。少平的路是煤矿,他寻求参与现代化进程中来,以此来建设自己理想中的世界。平阳的路是耶路撒冷,他发觉现代化进程无法改变,也不能成为自己满意的样子,所以他选择离开,从耶路撒冷这座圣城中寻求自我的精神世界。这便是他们异而相同的“到世界去”的精神内核。
徐则臣曾在他的散文集《到世界去》中说道:“所谓到世界去,指的正是眼睛盯着故乡,人却越走越远。”其实在不断出走的焦虑之中,人已经开始到世界去,“站在故乡的高台上远望火车,在路上,停下来整顿和思量:此三者皆在‘世界’上”。[27]在如今,其实在我们无所知觉之时,我们便已经开始踏上“到世界去”的路。如今的路,较之徐则臣与路遥更多,我们拥有更多的选择,而我们也需要面对更加强烈的现代化与焦虑感,所以我们也拥有更大的迷茫。正如狄更斯在《双城记》中所说:“那是好得不能再好的时代,那是坏得不能再坏的时代。”[28]
其实,归根结底,两部作品并没有跟我们说明如何到世界去,但它们都共同地叙述了如何是无法到达世界的,如少平离开双水、少平帮助被包工头欺负小女孩;又如平阳离开大学岗位、平阳不将房子高价卖给商人;等等。正如猫腻在《间客》的后记曾说过,“最爱《平凡的世界》”,他亦于其中说到,他不知道什么事是正确的,但是他知道什么是错误的,因为那些错误是那么显而易见,并不需要有多深刻的“理论知识”,而“只需要看两眼”。[29]
注释:
①鲁迅:《呐喊》,春风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自序第1页。
②梁永安:《人生没有真正的毕业》,《无锡日报》2015年7月24日,第1版。
③[法]罗兰·巴尔特:《符号学原理》,李幼蒸译,三联书店出版社1988年版,第84页。
④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8-39页。
⑤⑩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等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5页。
⑥李丹:《弃乡与逃城——徐则臣“京漂”小说的基本母题》,《文艺争鸣》,2011年第11期。
⑦[11][24]路遥:《平凡的世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9-503页。
⑧[12][25]徐则臣:《耶路撒冷》,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第33-153页。
⑨[14][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语娴译,远方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13]杨希帅:《读徐则臣〈耶路撒冷〉》,《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15][20][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6页。
[16]老舍:《老舍青岛文集 第1卷》,文物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
[17]周荣:《长子形象的文化隐喻和家国寓言兼论蒋蔚祖》,《文艺争鸣》2017年第4期。
[18][法]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等译,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726-744页。
[19]刘琼:《关于徐则臣长篇小说〈耶路撒冷〉的叙事策略》,《东吴学术》2015年第6期。
[21]张福贵:《新世纪文学的哀叹:回不去的“八十年代”》,《当代作家评论》2013年第1期。
[22]邵燕君:《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小说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0页。
[23]刘迎新:《70年代的成长心灵史——评徐则臣的〈耶路撒冷〉》,《文艺争鸣》2016年第9期。
[26][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前言第2页。
[27]徐则臣:《到世界去》,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第1页。
[28][英]狄更斯:《双城记》,马小弥译,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3页。
[29]猫腻:《〈间客〉后记——有时候》【将夜吧】,https://tieba.baidu.com/p/1182909575?red_tag=2973522990.2019年2月3日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