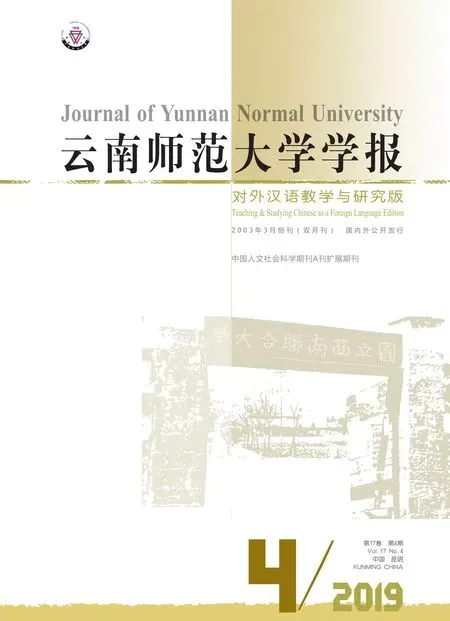语言与场合*
——从汉语与拼音文字的差异谈起
尚 杰
(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732)
一、汉字与拼音文字的根本差异
每个字、词语、句子,都有含义,如果是名词,它代表一样东西,例如面包。当然还有更复杂的词,例如动词、副词、形容词、连接词。说它们复杂,是因为它们不再仅仅像名词那样,安静地指向一个具体的面包,而是动态描述中的语言结构,从而与索绪尔不同。语言是这样一幅动态的图画或活动起来的“电影镜头”之连接:语音带着腔调语气,还附带上身体某些部位的动作、脸上的表情和眼神,词语是和这些因素连带一起的。这就是具体的场合,某个词语不能从这些场合中孤立出来,否则词语的含义既空洞又乏味。
场合或空间的具体化在于,它就是某瞬间发生的事情。“瞬间”与“场合”互为内容、互为真相,两者相互之间的关系乃“换一种说法”。描述瞬间暗含描述某种具体的场合,描述某具体的场合不过是描述某瞬间发生的事情。瞬间的内容就是具体的事情。这有一个从开始到结束的界限,超出这个界限还使用同一个词语,虽然词语没有变,但是词语的含义已悄然改变。这说明词语总是处于某种活动或环境之中。
不必说“使用词语”,词语自身就意味着它处于使用之中,否则词语就不能活。比如你写个“gōng”字我看看?你肯定写不出来。你一定会问我(这问话已经意味着“使用语言”),你是让我写“工人”的“工”?“供电”的“供”?“宫廷”的“宫”?“老公”的“公”?“功劳”的“功”?“弓箭”的“弓”?“进攻”的“攻”?听写汉字非常麻烦。由于传统汉字往往一个单字就是一个意思,同音异义字特别多,单听某个汉字的发音,无法准确写出这个汉字。如果使用标准的汉语普通话,那么某汉字的发音是确定的,但与这个确定发音相应的,有很多汉字单字。如果说的是汉语方言,那就更麻烦了:方言的发音不确定、五花八门,但从原则上说,替换各种方言的汉字是统一的。如果一个闽南人和一个说粤语的广东人用各自的方言交谈,互相听不懂,但两人可以用汉字交谈,两人使用的文字是一样的。总之,汉语的听与写之间是分裂的,使用汉语的人天生具有从“看”(象征)中思考习惯,倾向于意象思维和隐喻性、类比性思维。
但奇妙的是,汉语的音与字在诗词中可以实现完美地融合而不是分裂。古典诗词所使用的汉字之间的连接,要讲究平仄音韵,听上去就像音乐那样有节奏、旋律。这节奏与旋律自身就能使吟诗的人沉醉。与此同时,组成诗词的汉字之间不仅在发音的连接方面阴阳顿挫具有听觉上的美感,而且汉字本身的连接又能唤起叠起的意象,犹如一幅奇妙的画卷。
因此,汉语的听说与书写之间,呈现出既分裂又融合的复杂情形,相比之下,拼音文字更单纯,它的发音与文字书写几乎同一。拼音文字的诗歌即使在抒情,也总像是在叙事,而汉语诗词即使在叙事,也总是离不开婉转迂回的比喻,像是在抒情。汉语精神拥有含蓄中的高雅。汉语诗词的精髓,在于特别善于用各种“喻”(明喻、隐喻、换喻、叠喻等等)捕捉瞬间的感受,唤醒相似的意象,制造美的气氛。诗经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桃花盛开了,青年男女要谈婚论嫁了。这种“兴句”或隐喻的传统直到19世纪中叶才在法国象征派领袖马拉美的诗句中全面体现出来。“象征”之所以能在欧洲成为具有创造性的时尚诗歌流派,恰好说明在传统上西方诗歌不太讲究幽晦微妙的意象唤起关系。进一步说,象征手法描写同时的多意象,有意使用一词多义。这里的“多”是隐藏着的,可以随时不由自主地被心灵所唤醒。普鲁斯特的小说明显借用了马拉美的诗歌写作方法,而柏格森的绵延概念,也与这种方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可知,从汉语结构的天性而论,与其说汉字的意思是听出来的,不如说是看出来的。拼音文字可以听写,汉字则适于识读,即看图识字;拼音文字的听和想之间有直接联系(德里达称之为“语音中心论”),既可以从单词听出一个观念,也可以从单词听出一个图像。但无论是观念还是图像,对于拼音文字来说,都是听出来的,因为拼音文字的字形与图像几乎没有关系,它不像汉字那样是建立在象形文字基础上的。
英语任意一个单词的发音都对应着某个或几个英语字母,这是一种固定的对应关系、固定的环境,但是这只是语言最简单的环境,就像下象棋的人刚刚懂得下棋的规则一样。真正复杂的语言环境或语言用法,在于巧妙地把不同的单词连接起来的技巧,相当于知道棋子如何“走”才能取胜对手。
学习语言不是学习说话,而是学会写作。幼童只要与人接触,哪怕与文盲接触,自然而然地能学会说话,但是要懂文字,则要向识字的教师学习。这意味着阅读与写作比说话更困难更复杂。
学说话是相对简单的,只需要学会一个出声的单词或者句子指代现实世界中的某样东西或者事情,就可以了。相比之下,学习文字、学会阅读与写作,要困难得多。这是因为,说话所使用的词语比写作简单得多。为什么呢?因为在书面语中,很多文字及其连接起来的句子是抽象的,在现实世界中没有对应物。当然这种情形在说话中也是存在的,但其存在相对单纯简单,是简单的意象。文字的字句唤起的意象更复杂更抽象,一个善于阅读和善于写作的人,是一个善于想象或联想的人。识字的人比文盲的思想视野更开阔,因为识字者使用抽象复杂的意象思维,能赋予简单的事物以多层次复杂而细腻的感受,而不识字的人由于不是用“书面语”思维,受口语的局限,想事物时,想得既不深入也不透彻。
在识字者之间又有区别,文字是符号,符号自身又有简单与复杂之别。哲学、文学艺术、科学,需要使用复杂符号。
但是,现在有一个革新的观点,就是认为无论是说话还是文字符号,所唤起的都是某种或简单或复杂的图像:一个苹果是一个具体图像,2+2=4是一幅抽象的图像,X+Y=Z是更抽象的图像。图像的含义就是显示自身,我们直接沉浸在图像之中,图像不能针对自身说话。
以上情形,很像象形文字的书写过程,一笔一划都像是在画画,即使是一幅抽象的画。字是有含义的,但字的含义就是画的含义,但是画同时显示出很多景象或意味,看画或阅读的人不能立刻用简单的语言归纳出所看到的全部感受。也就是说,文字画既把自身显示出来又把自身隐藏起来。
二、语言的场合就是用语言做事情
维特根斯坦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一般地询问一个字、一个句子是什么意思,对这样的问题无论怎样回答,都相当于什么都没有说。我们要问一个字或者一个句子是怎么具体做事情的,它们如何区别于别的做事方式。词语如何做事情?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词语做事情,就是一个词语或者一个句子与另一个词语或句子连接起来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创造了新的意思。我们不是在静止状态下手指一个苹果说“这是一个苹果”,我们早就超越了这种最简单的给事物“命名”的方式。我们在词语或句子之间建立起新的连接方式,这种连接的过程,才是所谓“命名”的过程。显然,这个名字的含义是流动的、不确定的。语言思维和写作的深刻性与趣味性就在这里,它可以让我们在不经意间坐在书房里就能享有不同的世界、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依靠语言所唤起的意象之连接方式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来自我们意志的自由创造。维特根斯坦认为,“想象一种语言就是想象一种生活形式。”[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15.“是”(being)这个哲学本体论的基石,在维特根斯坦这里演变成古代汉语用法,他相当于把“是”理解为“为”、“作为”、“变成”。[注]关于古代汉语中“是”的这种用法的考据,参见我发表的《中西:语言与思想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265~266页.这里不仅暗含着思想镜头的意思,还包括了思想镜头的转换即时间——对此,他只是淡淡地说,词语的意义在于其使用方法。他的意思就是说,词语的意义在于你把它看成什么、作为什么,它就是什么。这里只有差异性,没有一般性或普遍性。因此,在与人交流过程中,最要紧的不是你自己心里想好了要说什么话,而是这句话在倾听者和阅读者那里获得的心理反应,后者与你的意向往往并不一致。别人是根据其自身的心理和文化性格秉性对你说的话作出反应,两个不会产生心理共鸣的人之间说话,属于“对牛弹琴”,听话人理解不了你的好。
从“是”到“为”、到“作为”、到“变成”,心思的方向变化多端,事先根本无从掌握。也就是说,不仅与他人共鸣是奢想,与自己刚才的想法共鸣,也是奢想,否则,人就不会对自己不满了,也不会去修改自己写过的文字。要断绝或者质疑别人和你说的话的真实性(因为这些话只对和你说话的人来说是真实的,对你未必真实),要自己和自己的心里话“聊天”。别人并不关心也猜不到你的心里话,但这些心里话,几乎就是一个人的全部人生。由此可见,人与人之间隔绝的距离多么遥远。
在拼音文字需要使用“是”的句子中,汉语经常把“是”省略,我们不说“花是红的”,而只说“花红”,“是”生成或融化在“花红”之中了。“生成”已经处于时间之中了,而由“是”组成的判断句往往给人一种处于时间之外的感觉,仿佛其判断经得住时间考验。
“视为”或“作为”与“根据”“原因”“为了”——是同时发生的,这就改变了我们关于“根据”“原因”“为了”的习惯心理,因为按照习惯心理,根据或者动机目标之类,发生在行为之前(或者“之外”)。现在,我们把某某看成一个新因素,我们同时创造了一个不需要提供证明的根据,它为了自身而自身,它自身就是自身形成的根据。
哲学判断句的标准形式结构,以“是”或“不是”作为建构骨架,判断句的含义已经在句子前提之中了,连接在系词后面的“什么”的含义,已经被我们事先知道了,因此哲学推论貌似严谨,但多数句子属于同义反复,加上句子冗长,令人昏昏欲睡。文学作品中的句子不是判断式的,即使表面看像判断,其实是描述。描述与判断的区别在于,描述总是在补充或创新刚才说过的意思,下一个句子的意思不可能从前面一个句子的意思中推论出来,它们之间也许有某些相似,但这种相似的景象完全可以是别的样子,并非一定如此。文学类的写作,是边写边明白的。哲学写作中只有出发点是“时间”,而后这个作为出发点的“瞬间念头”就被永恒化了,因为从理论上说,后面的句子都是从“第一个判断”中推论出来的,而文学类的写作却充满瞬间的灵机一动,其描述的方向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全看心思的变化和情绪的节奏,从而情趣盎然。描述中绝非不使用“是”和“不是”,而是把它们当成“作为”“好像”来使用。
也就是说,一个句子里包含着我们看不出来的别的意思,真正有思想的人能把这些别的意思挖掘出来。它明明是这个,但你可以任性地把它看成那个。我们不想知道句子里告诉我们的东西,因为那东西我们早就知道了,关键在于从旧东西唤醒新东西的能力,即告诉人家新东西的能力。这种灵动性在古汉语词性中就体现出来了,例如名词可以当动词用,一句话可以同时理解为断言、描述、甚至疑问:“‘语言游戏’一词是为了强调一个事实,即讲语言是一种活动的组成部分,或者一种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19.语言活动就是生活方式,这里不讲区分真话假话的问题,说假话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我们的说话方式同时就是以这种方式做事情。比如开形式主义(所谓“走形式”)的会议,大家都心知肚明地发言,说着刻板的套话和假话,但作为生活方式它是真实的。哲学家并不关心这里的假话问题,不会因此就义愤填膺,哲学家只考虑思想本身的问题。为了在思想上有所成就,就得不顾常识,在精神上破例走极端,从一般性中发现和发明意外或特例,变不可能为可能。
维特根斯坦所谓“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其实就是瞬间朝向多方向想问题的可能性,任何恶势力也管不住你的心思朝哪个方向想问题。“语言游戏的多样性”还暗含这样的意思,就是瞬间误解的可能性,因为既然不存在私人语言,语言总处于交流之中,但是一句话只要一说出来,意思就暗含很多方向。即使退一步说,两个人都想到一个方向,仍旧存在着微妙的差别。也就是说,交流是必须的,误解却是必然的,但并不可就此而得出结论说,没有必要说话,因为误解并不仅仅产生不快,误解会滋生创造性思维,从而诞生新的生活方式,丰富生活的趣味。
从西方传统哲学著作的角度看,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根本就不算是一部哲学著作,更像是语句例子大全。他绞尽心思挖掘一个句子能被划分为各种各样的种类。他用例子做意象,因此此书也是不同意象转换的画册。甚至可以把他想象为一个以词语做人物角色的“小说家”,他总是在书里设想各种各样的词语用法之情景,这也是现代西方哲学家不同于传统之处。在胡塞尔现象学那里,“好像”的地位非常高,所谓“好像”,也就是在做假设。所谓“现象学还原”就是胡塞尔最重要的哲学假设。
“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在某个关键念头上与海德格尔暂时一致,那就是讨厌问“这是什么”,因为对这种提问方式的回答不会说出点新东西;“语言游戏的多样性”还在某个关键念头上与索绪尔暂时一致,这就是能指的纯粹任意性,例如“海南岛”不仅指中国的一个省份,还可以指一个小孩的名字、一个宠物的名字,可以代表任意东西——总之,一切取决于我们最初的念头。如果两个人在谈论“海南岛”时,对这个名称究竟指代什么没有达成一致,他们之间的交流就无法进行,不是由于不同意对方的意见,而是由于根本误解了对方的意思。因此,语言只能是公共的、社会的,在语言规则和词语的含义上都要事先约定好,以便能重复使用。没有可重复性,语言不可能存在。但如果关于语言的哲学只分析到此,只能算说到一半,更重要的一半还没有说。也就是说,约定只是相对的,语言要丰富自己的表达能力,必须得出现一词多义现象,即同一词语指称的不确定性、增补性,好像词语太少而要想表达的意思太多似的。
三、用语言做事情的具体情形
内心感受永远比语言丰富——指出这个事实,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尼采、弗洛伊德的功劳,他们发现了潜意识流动的重要性。至于“无意识”这个词,完全是针对语言的,因为在传统上,意识(或者思想)与语言是等同的。发现潜意识和无意识,极大地丰富了人对自身精神世界的探索,也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也就是悖谬性,“‘清晰地阐述’根本就不可能被清晰准确表达出来的思想”引号里的这句话是悖谬的,但它描述的是事实,事实比“正确”更重要。维特根斯坦以他的说法说出了类似的意思:“因为只有在语言放假的时候,哲学问题才会产生。”[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29.要像索绪尔那样,约定词语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相当于识字。但识字不等于会写作,识汉字的人未必会作诗,作诗属于使用汉字的能力。这表明联想能力高于辨识能力,联想属于创造新意思,辨识属于重复与模仿。
会想比会说更重要,会想的人有时不能清楚地把想法准确表达出来,但心里是明白的,而无论一个人怎么会说,话一出口就得照顾别人能听懂。也就是说,口语的特征是“一般性”,牺牲了精神的微妙性。鉴赏力只流淌在人的潜意识之中,以感受的形式存活于心,即使没有用语言吐露出来,我们已经沉醉其中,这也是人的真正幸福之所在。
即使一个最简单的行为或者某个符号,其意味也是丰富的、诡异难测,取决于思考与想象能力。受到这种现象启发,人类发明了暗号和密码。语言的第一步是指称事物,第二步是知道词语如何代替事物,第三步是创造性地用旧词语指称一个新事物。写作过程,就是错综复杂地交错使用这三个步骤。重要的是享受词语和句子叠加有异的含义,至于外部世界是否真有某个物理对象与这个含义相符,对享受思想本身来说,并不重要。
在汉语中,有意义和有意思之间,有微妙差别。我把两者混淆起来使用,这种做法本身,也许有意义或有意思。“有意思”这个说法,涵盖了“有意义”,含混不清本身,就是一种哲学观。怎么弄成有意思的效果?前提是得让人家懂,但这种懂的方式,是人家从前没经历、没想过的,因此会有既深刻又幽默的效果。维特根斯坦的书不幽默,就像他的传记作者说的,你和他讲话,你会觉得很累,但是他深刻。
所谓写作,就是写出不同的“语言用法”。即使在一首诗词之中,句子的用法也不相同,一首诗整体上的平仄分配相当于维特根斯坦说的“命名”,维特根斯坦举的例子是,命名就相当于象棋中的棋子已经摆好位置、各就各位,但他说这并不等于已经走了一步棋。走棋,这相当于语言用法,也就像在写作了。识字并不意味着自然会写作,这就像懂象棋规则很容易,但距离一个象棋高手,还差得远。关键看如何走棋,即如何使用词语。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变化多端,不止一种用法、看法、思路。
命名是死板的,只有词语之间流动或联系起来,才形成思想与情趣。下棋的趣味绝不在于把棋子在棋盘上摆好位置,而在于走棋过程中的运筹帷幄——如果把这里的“棋子”换成“词语”,就相当于语言的用法,或者用语言做事情。还没有做事情的词语,就像还没有走一步的棋子,是没有用处的。
创造性思维的方法,往往是把一个已经确定的说法或命题,当成一个不确定的X,经历了这样的转换,不再理睬原来的判断,胡塞尔就是这样的,维特根斯坦也是这样,例如他说,命题相当于事实的图像,还有很多类似说法,这是他的思考方式,这是比喻、好像、“兴”起来的象征,是隐藏起来的词语之诗歌用法。你说它像什么,完全是你随感想出来的,而这样的相像或所谓“家族相似”多的是。
以上,也相当于把时间因素引入判断。就是说,只是摆好棋子在棋盘上的位置根本就不叫下棋,下棋必须“走棋”,而走棋要经历时间。语言也是这样,你不能使思想停滞,满足于思考事物名称的意义,不能只是傻傻的问“这叫什么”或“这是什么”,因为要真正明白它是什么,这个“名词”得“走棋”,也就是连接别的词,使自身变成别的词,词语处于绵延之中,这本身就是在经历时间。
一旦在思想之中真正引入了时间,精神的景象立刻大变,就像坐着高速列车看窗外呼啸而过的道道风景,它们瞬间就转换为别的,乃至“别的”的“别的”。在这个过程中,留恋是弱者的思维方式,渴望前面的风景才是乐观的强者。但“留恋”和“渴望”状态,这是事后总结,我们沉醉于窗外的美丽风景时,根本不会考虑这种停下来才会有的事后思维。一个乘客在座位上看列车窗外的风景,他似乎一动没动,但已经并正在经历着很多很多——这也就是康德所谓“哥白尼式的哲学革命”。此刻的“我”成了太阳,万事万物围绕着我转,我把它们看成什么,它们就是什么,人类成为自然界的立法者。
“我无意找出所有我们称为语言的某种共同点,我要说的是:这些现象没有一个共同点能使我们用一个同样的词来概括一切的——不过它们以许多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着。正因为这种联系,或这些联系,我们才能把它们都成为‘语言’。”[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45.不寻找语言的共同结构,不从总体上判断语言是什么,这与索绪尔不同。维特根斯坦认为所谓语言现象,就是以不同方式(不同用法)在词语之间建立联系,索绪尔曾经以不同的表述说过类似的话,即词语的意义在于词语之间的差异,建立差异就等于创造出语言的意义了。
所谓建立联系,不是胡乱联系,从A联想到B,总是由于某种隐藏或深或浅的幽暗中的相似性,这些相似性引起我们认同、产生共鸣,不要受到维特根斯坦说法的束缚。就是说,不把它们说成“家族相似”也是可以的,不必给它们定性是什么样的相似,它们只是相似,就够了。“相似”只是意境转换或者创造出新思想的一个借口,“相似”具有说不清道不明的随意性,它与人的自由意志有关,但通常都需要先有某个自己比较熟悉的东西刺激自己,使自己联想起从表面上看与这个刺激物并不相似的意象或景象。维特根斯坦所谓“语言游戏的转变”,用人们能听得懂的话说,就是一个名词不再像人们习惯的那样指称A而是指向了B。用于游戏或消遣的语言,不必是真理的语言,但得是有趣有用的语言,显露美感的语言。这相应于弗雷格和胡塞尔都承认的区分词语的意义与指称。语言流露和描述的是意义,至于是否真的存在意义所指称的物理现象,则无关紧要,意义来自创造性的联想与想象。
四、进入不可说的场合才算进入了形而上学
在《哲学研究》中,维特根斯坦似乎始终都在讲语言游戏的规则或使用方法。他早期认为,对不能说的东西要保持沉默,逻辑实证主义者以为这句话是反形而上学的,其实这句话恰恰是在划定逻辑与哲学界限的同时,为形而上学辩护,主张那些不能说的东西才更为重要。回到《哲学研究》,与其说他重视的是按照规则使用一个词语,不如说他更重视当没有按照规则使用某个词语时,会出现怎样的情况,这情况对语言的意义在哪里。他对规则中的例外更感兴趣、对差异更感兴趣、对其他可能性更感兴趣。在书中,他不断地设想各种各样的问题,也就是在寻找例外与差异。
怀疑无禁区。怀疑,就是猜想事情还有其他可能性。这些猜想往往符合事物的本性,因为事物确实是不可定义的(也就是说,事物除了是A,还是B、C等等),因此,怀疑与猜想是创造性思维的“序曲”。就像下面一段话继承了笛卡尔式的怀疑精神:“一条规则立在那里就像一个路标。难道路标就能使我毫不怀疑该有的方向吗?我已经走过路标时它是否表示我该走的方向;是沿着大路还是小径,或是越野而行?”[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55~56.条条大路通罗马,但途径不同,看到的景色就不同。虽然最终都到达了罗马,但是经历了不同的意义。
维氏的《哲学研究》确实是哲学研究,他设想那些“没用的事情”,打破了在《逻辑哲学论》中曾经试图保持的沉默,试图揭示那些“不可说的东西”。他想说在使用语言时,人们经常用错了词语,也就是词不达意,因此也可以把他的《哲学研究》当成一个语文老师在批改学生作业时纠正学生造句中出现的语病,但其深意是哲学的。他想说明哲学的困境,在于我们误用了语言。这就像弗洛伊德认为治疗心理障碍的方法是和病人谈话,告诉病人的心结的真实意思并非病人所想的那样,而是别的意思,一旦解决了别的意思,病人的心病就迎刃而解了。
“词语的意义在于其用法”——等值于把词语看作什么,也就是精神视角或镜头,这还等值于消解了词语的雅与俗之间的界限。就是说,当词语安静地躺在词典里的时候,我们还无法断定其雅与俗。词语雅与俗的区分标准,要从如何使用它们来判断,[注]不能说生僻字或文言、书面语等等先天地就优越于口语,在这方面学界一直有误解,关于20世纪初的白话文运动,有历史的必然性。但是,反过来说,也不能说文言就是死文字。例如“无能为力”与“干不了”各有千秋,关键不在于使用的是文言还是白话,而在于它们要适用当时的场合以及是否能在我们的内心产生美感。在这里我赞成美感,而不挑选“实用”或“通俗易懂”这样的字眼,应该回避没有艺术美感的赤裸裸的通俗易懂。例如李白那首“床前明月光”,用的是极普通的汉字,但经过他的妙笔组织排列起来,品位高雅而不俗气。精神之高贵,不在于辨识更多生僻的汉字,而在于使用普通汉字的造句能力,一种联想的能力。在这方面,维特根斯坦说了,“我们处在幻觉之中,以为我们的探讨中特殊的、深奥的、实质性的东西在于它企图抓住语言无以伦比的实质,即存在于命题慨念、字词、证明、真理、经验等等之间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一种超秩序,可以说存在于超概念之间。可是当然,如果‘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用处,它们一定像‘桌子’、‘灯’、‘门’这些词一样卑微。”[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62.其实,这里既可以说“卑微”也可以说“伟大”,究竟是卑微还是伟大,要看造句的效果,也就是运笔的能力,就像书法艺术一样。其实,我们也不要过分引用他的所谓“不要想,要去看! ” 更全面的说法应当是,要变换花样地去想、去看、去写。在这里所谓的“花样”,就是从哪个方向接触同一个景象或事情等等。景象或事情本身并不说话,怎么想、怎么看、怎么说话的是我们,是人。
换句话说,没有哪一个词语天生就是高贵的,就像人一样,生而平等。词语或人的高贵,要看其思考行为、说话行为、做事行为,是否具有创造性和制造美感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制造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就等同于在制造原创性的思想和原创性的美感。“无秩序也是一种美妙的秩序”,例如战争与革命,似乎现在人们都不喜欢,但没有它们,就没有人的历史,因此它们是藏匿于我们内心深处的本性之一部分,就像“即使在含混的句子中,也必定有完美的秩序。”[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62.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看似没有讨论时间,但他所关心的问题,与柏格森、德勒兹、德里达等法国哲学家的主要论题相似。如果他们从不同途径接近同一个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时代的哲学问题:“一个句子的意思——有人会说——当然可以有这种或那种可能性,但这个句子却必须有一个确定的意思。一个不确定的意思——实际上根本没有意思——这就好像:一条不确定的界限其实根本不是界限。”[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62~63.不是界限,界限消解了,句子原来的结构被拆散了。于是,唯一的确定性在于一切都不确定,因为这里引入了时间,这等于说“是”等值于在生成别的东西的路途之中。
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的陈述句式,经常以“如果”或““假定”开头,就像胡塞尔在书中经常说“好像”,这不仅是词语用法方面的巧合,而是说“特殊的思想场景”(这是某视角下的意向性)成为20世纪第一流的哲学家共同关注的问题。但为什么“假设”或“好像”这个而不是那个?这并没有可参照的客观标准,哲学家只是临时想到了这个或那个。所以,作为读者,我们大可不必细究这个或那个本身,关键在于我们可以想出符合自身之所是的这个或那个。
哲学并没有改变原来的根本形态,哲学能力仍旧在于哲学家辨析词语的能力,但哲学不再承认有唯一正确的真理性质的语言。理想或者理念获得了重新理解,从此没有任何东西是纯粹的,纯粹成为单纯的同义词。从此,理想不再是像一个等待我们到达的目的地,因为当我们经过努力奋斗果真到达那里时,肯定会感到失望。只有走在不确定的路途之中,我们才感到幸福,因为当下的选择十分丰富,我们处于冲动之中,随手捡起最方便的最使我们兴奋激动的东西。当然也可以随时扔掉,假如我们看见更能使我们冲动的场景,这就是21世纪的人类生活方式。在纯粹状态下是无法行走的,就像在真空中无法呼吸一样。“我们想走:所以我们需要摩擦。回到粗糙的地面去吧!”[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65.没有冲突与困难就构不成生活,因此我们需要摩擦,需要粗糙。
一个不确定的意思,有没有意思的意思,似乎禅宗就有这样的主张。禅宗经常讲一些南辕北辙的句子,以显示语言之无用。一条不确定的界限也是“界限”,就像瞬间与瞬间的关系也是“关系”——只要我们不认为界限与关系是确定的,只要我们领悟到界限与关系总处于新的生成过程之中。那些一味喜欢“平平淡淡才是真”的人、那些不相信突发奇想的人、那些不愿冒险去体验“战争硝烟”的人、那些不愿见陌生人的人、那些不愿意从事极限运动的人,还没有真正品味到生活的奥秘与真谛。
要善于理解维特根斯坦,例如他说“我们所做的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67.——这不过是说,思想和写作的才华,在于用极其简单朴素的句子道出深刻而具体的思想,而不能反过来,句子表面上用词怪异生硬,其内容却空空如也。从此,我们尽量少使用“存在”“真理”“命题”这些深奥的字眼,我们用粗糙的日常语言替换它们,因为我们的脚总踏在凹凸不平的地上,我们用意象代替假想的直线与平面。
一切日常语言都含有哲学的意思,而一切哲学的意思都可以用日常语言表达,这两种情形,也叫细节。这些细节已经含有解除界限的意思了。哲学思考与诗人作诗有一点是相似的,那就是从看似没有关系的抽象概念或自然景象之中,看出联系。“解构”或消解原来的结构不是刻意的,而是自然而然的。在这个过程中,思想并没有做作,没有刻意发力。
没有什么“语言哲学”问题,所谓“语言哲学”问题,其实就是语言问题。对语言的思考不一定非得是哲学性质的。使语言的哲学用法回归到语言的日常用法是否会导致取消哲学本身呢?不会,因为语言的日常用法中含有神秘性。如果这些神秘性能够得到澄清或者发现了一个标准答案,那么就确实可以取消哲学了,但问题在于这是不可能的——这就像翻译是不可能的。真实的情况总是这样:我怀着某种意图写出一句话,但这句话在读者内心形成的意思,与我的意图永远是不一致的,读者永远猜不透我的意图。
“哲学只是将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演绎任何东西——由于一切呈现在眼前,没有什么要解释。”[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70.把这句话与马克思的名言对照一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有相似之处吗?要注意相似中的差异,马克思强调的是“武器的评判”或者社会革命,他注意的是宏观世界,而维特根斯坦注意的是语言的细节或语言的微观世界,其意思是说,改变语言的用处就已经等同于革命了。毕竟人类是通过语言思考的,而人怎样思考就会怎样做事情。怎么去改变语言的用处呢?例如不去解释和推论,而是饱含诗意地去描述、显示意思。解释和演绎的东西,并没有给我们新的意思,而在描述过程中,我们正在灵动地联想,充满各种诱惑我们的可能性,时间裹挟着思想走在创造的路途上。
简单的东西是神秘的,形而上的东西就生成于形而下的东西之中:“事物中于我们最重要的方面都由于它们的简单和熟悉而隐蔽不见。人们无法注意某些东西——因为它们始终都在我们面前。”[注]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M].汤潮,范光棣译.北京:三联书店,1992:70.把东西藏在最显眼的地方,因为那地方太平凡了,谁都不注意。
只要有了先入之见,就等于忽略了时间,忽略了场合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动,就是时间。不空洞的写作与生活一样,得有很多具体活生生的临时想法,不惜与刚才写出来的想法不一致。如果全部一致,千百句话只等于一句话,那就成了文章的“雕塑”,如同将很多活生生的瞬间不一样的或粗糙或精致的想法生硬地抹平而冻结为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