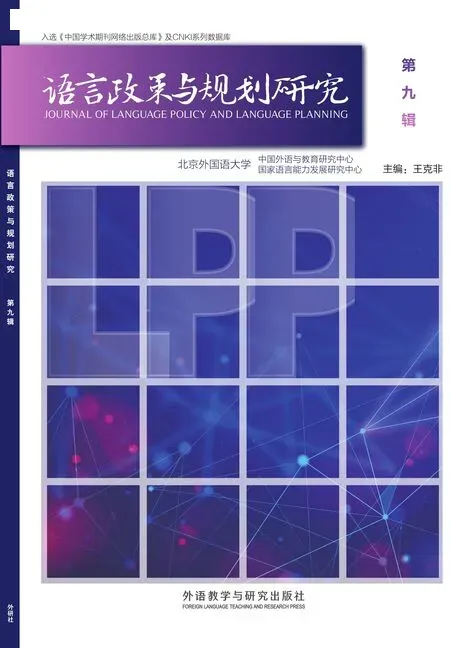原南斯拉夫地区的语言身份和语言政策*
卢布尔雅那大学 哲学院 维斯纳·博日盖伊·哈吉(Vesna Požgaj Hadži)
卢布尔雅那大学 哲学院 塔蒂安娜·巴拉日奇·布尔茨(Tatjana Balažic Bulc)
北京外国语大学 欧洲语言文化学院 彭裕超 (译)
提 要:尽管有诸多标准可以遵循,语言身份的确定仍是一个极具争议的问题。除语言学因素外,非语言学因素同样起着重要的作用。20世纪90年代,南斯拉夫解体,原来的成员国陆续独立成为新的国家,随之而来的语言身份认定具有典型性。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身份问题从19世纪中期开始就饱受争议。这个名称反映出双重性身份: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外部辨识度较强,足以让其与邻国的语言自然区分。但它的内部辨识度较弱,具有“埃”(e)化方言和“伊耶”(ije)化方言两种分化形式,并有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两种分化书写形式。随着南斯拉夫的解体,在新成立的国家,主体民族使用的语言取代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成为标准语:波黑语、黑山语、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相继确立。对这些国家而言,语言是国家身份和民族文化身份的重要象征,因此他们不懈地追求语言身份。
1.引言
在过去几十年里,语言名称身份(language name identity)承载着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从话语到政治层面有着各种运用形式。因此,语言名称身份的确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其本质取决于与他者的相似性(Edwards 2009)和区分性(Skoko 2009)。正如尤日尼奇(Južnič 1993:13)所言:“身份认同是人类存在和归属的感觉。”同时,身份认同是(个体或集体)对自身的理解,这种理解是自然形成的,一般情况下我们很少主动思考这个问题,只有在个体身份或集体身份受到威胁损害时,我们才会去阐释身份认同(Benoist 2014)。胡灵顿(Huntington 2007:32)说过:“个体或集体的自我感觉,是自我意识的产物,这种特质使‘我’成为区别于‘你’的本体,也使‘我们’成为区别于‘你们’的本体。”
一般来说,身份认同的组成要素有民族身份、语言身份、文化身份、宗教信仰身份、社会身份、地域身份、政治身份、历史身份、职业身份和全球身份等。它们与个体、集体、民族有关——当这三者同时发挥作用时,身份认同会显得格外重要。这种复杂现象既包含遗传作用(性别、种族、民族归属等),也包含一些人们自主选择的作用。因此,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人们会不断确定哪些身份要素更加重要、哪些比较重要。除了遗传的身份要素以外,仪式、神话、音乐、符号、语言等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价值,同样能营造人们的共同意识(Barić 2011:2)。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但能让“我们”发生变化的时候,依然保持着“我们”这种共同状态(Benoist 2014)。身份认同会在与他者发生联系的过程中不断建构,并且构成相关的话语。语言是最普遍的交流工具,因此语言在个体身份的构建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本文的研究对象——语言身份,对于自身和他者都具有相当的重要性(Pranjković 2007)。
某种语言的身份,往往在与其他不同身份因素发生作用过程中得以确立和巩固。卡迪契奇(Katičić 1992:47)认为:“一种语言的身份,至少是以下三种不同身份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类型身份要素、遗传身份要素和价值身份要素。”1布加尔斯基(Bugarski 2010,2016)把卡迪契奇所说的第三类身份称为“功能或社会语言学身份”,而不是“价值或社会语言学身份”。
(1)类型身份要素研究如何对一种语言进行描述。语言是符号系统,类型学的作用正是依据语言要素和结构,把这个特定的系统确认下来,与别的语言区分开;
(2)遗传身份要素研究语言是如何形成的。研究清楚语言的起源,便可在语言谱系当中找出它所处的位置;
(3)价值身份要素即社会语言学身份要素,它研究语言的社会角色及其体现的价值。这一层身份取决于语言使用者对于自身语言的态度:使用者如何从社会角度和文化角度,乃至民族象征、政治象征、文化传统象征等角度看待语言问题。
前两种身份要素(类型身份要素和遗传身份要素)是从狭义的语言学角度对语言进行考察,不过这两个指标并不足以对某一语言的身份进行确定。这时,价值身份要素就显得格外必要,因为它考察语言的社会性质,考察语言及其要素在不同价值判断下的反映。这个问题既美好又丑陋,既简单又复杂,既愚蠢又巧妙。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不是人所完全掌握的“工具”或“武器”,而是确认人在世上“得以存在”手段(转引自Periša 2016:8)。
如果某一种语言的类型、遗传和价值这三种身份要素都具备唯一性,那么就可以认为这门语言属于“唯一语言身份类型”,如法语、俄语、蒙古语、阿尔巴尼亚语和日语等。然而,某些语言的三种身份要素并不具备唯一性,我们则认为这些语言属于“复合语言身份类型”,如荷兰语、德语、印地语、葡萄牙语和加利西亚语等。对于后者而言,语言身份的三种内部因素互相抵触、无法调和(Mićanović 2004)。不过,“某些语言学要素相去甚远的语言变体,可以成为一种语言;而语言学要素极其接近的语言变体,也可以因不同的组合而成为不同的语言”(Bugarski 1997:10-11)。卡迪契奇理论下的复合语言身份类型的“三种身份要素截然不同。而且只要其中一种身份要素不能确定,另外两种身份要素也将无法确定”(Mićanović 2004:97)。
史基里安(Škiljan 2000)认为,语言身份问题存在两种基本解决方案:第一种是根据唯物主义理论,通过统一语言名称来确立语言身份(这一解决方案受到现代语言学家的严重质疑);第二种根据实质性理论,为语言身份的构建制定客观的语言学标准。对此,至少存在三种标准:遗传标准、结构标准和务实标准。还有学者提出应增加新的标准,例如马塔索维奇(Matasović 2001)在遗传标准和结构标准外增加了相互理解标准(语言交际功能)、语言使用者身份标准(语言价值功能)以及标准化标准。
相互理解标准(互懂度)看似很容易理解,但它不够完整和明确。两种语言即使存在着复杂的结构性差异,也未必不可交流理解(Kapović 2010:136)。有时说话者使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互懂度虽低,但文字体系又是一样的,文字书写系统也是一样的(如汉语普通话和粤方言);有时说话者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反而可以进行交流(如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因此,说话者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两种方言来对话却不能互相听懂,不代表他们说的是不同语言;反之,说话者使用两种语言进行交流,却可互相听懂,不代表他们用的是同一种语言或者同一种语言下的两种方言(Mićanović 2006:57)。尽管相互理解标准被广泛运用12007年有学者对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中学生进行调研,考察他们是否能理解对方的语言(Barić 2011)。2015年有学者调研过西部斯拉夫语和南部斯拉夫语之间的相互理解性(Golubović & Gooskens 2015)。,它同样面临诸多困难2这是原南斯拉夫地区内外众多学者的共同观点(Mićanović 2004)。。钱伯斯和特鲁吉尔(Chambers & Trudgill 2004:4-5)在评价斯堪的纳维亚语和德语时指出:“‘语言’并不是一个明确的语言学概念。挪威语、瑞典语、丹麦语和德语之所以被认为是不同的语言,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语言学特征存在巨大差异,更多是出于政治、地理、历史、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原因。当然,三种斯堪的纳维亚语言之间的确存在差异,各自都有标准化格式、正字法、语言和文学特征;但更重要的是,它们是三个独立的国家,语言使用者因此认为他们使用的是不同的语言。”
语言使用者对自己语言的理解是确定语言身份的又一重要标准3多项研究显示,语言使用者总是认为自己的母语显著区别于其他语言(Požgaj Hadži & Balažic Bulc 2011)或者邻国语言(Golubović & Sokolić 2013)。。它是语言使用者的主观想法,因此很难采用科学的方法来测量这一标准。此外,标准化标准也不是语言因素的产物。一些语言之所以能成为单独的语言,完全是因为它的使用者有自己独立的国家。这些问题都不是来源于语言科学本身,从上面提到的斯堪的纳维亚语和德语的例子可以看到,国家、民族、社会、政治及其他非语言学因素对语言的标准化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详见Kapović 2010;Mićanović 2006)。
语言身份的确定问题,经常会引起长时间的争论(如马其顿语、乌克兰语、加泰罗尼亚语,以及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下文简称塞-克语))。引发这些争论的往往不是语言论证的缺失,而是当事者缺乏良好的意愿去接受和尊重语言论证的结果,去克服争论中的政治利益(Glušica 2009)。在这种情况下,社会标准变得极为重要,因为“对于语言身份尚未确定的语言使用者来说,语言就等同于民族(这种情况在现代社会中很常见),他们希望语言标准得以确立,并且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在政治和学术层面都取得合法地位”(Barić 2011:3)。本文旨在借助塞-克语的例子,揭示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环境下,非语言因素如何对语言身份的确定造成影响。
2.塞-克语的身份认同
塞-克语曾经存在过150年,关于其语言身份的争议始终存在。1850年,当时的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签订了一份《维也纳文学协议》(Bečki književni dogovor),就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为同一种文学语言达成共识。这一协议对语言名称没有做出规定,导致该问题直到1991年南斯拉夫解体时都没有解决。1954年,另一项重要的语言协议——《诺维萨德协议》(Novosadski dogovor)得以签署。该协议笼统地规定了语言名称的二元性(塞-克语或者克-塞语)、两种次方言(“埃”化方言和“伊耶”化方言)1在南斯拉夫语言当中,古斯拉夫语的二合元音“jat(ě)”分化成三种发音变体,分别是:通用于以贝尔格莱德为中心的塞尔维亚地区的“埃”(e)化方言;通用于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以及黑山地区的“伊耶”(ije)化方言;通用于原南斯拉夫西北地区的“伊”(i)化方言。其中“埃”化方言和“伊耶”化方言平等使用,成为现代塞-克语的基础;而“伊”化方言只被作为地区方言得到承认。和两种文字(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的平等地位2这种情况仅见于波黑,当地的杂志《解放报》(Oslobođenje)同时使用两种文字。除此之外,在克罗地亚主要使用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只用在文学读本中),而在塞尔维亚主要使用西里尔字母。,以及语言规范手册(正字法和词典)的制定(详见Požgaj Hadži 2014)。为了更好地说明塞-克语的身份问题,有必要对南斯拉夫的语言政策加以回顾。
2.1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下文简称南联邦)的语言政策强调三种民族语言的平等地位:塞-克语使用于克罗地亚、波黑、塞尔维亚和黑山,斯洛文尼亚语使用于斯洛文尼亚,马其顿语使用于马其顿3此处所指的马其顿即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而不是古代希腊的马其顿。该国于2018年7月5日正式改名为“北马其顿共和国”。。在教育、媒体、司法等各领域和南斯拉夫人民军队中,这种“多中心的语言统一模式”都得到了法律承认。此外,公民个人自主选用任何一种语言和文字的自由也得到法律保障。然而实际情况却远没有这么简单:塞-克语是联邦政府部门、外交、军队、联邦议会、主要媒体的工作语言,在语言生活中享有特权,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处于次要地位(Gorjanc 2013)。20世纪60年代,人们开始对《诺维萨德协议》中对语言名称的规定展开讨论。当时,塞-克语的名称(海外几乎只用这个名称)比克-塞语(主要在克罗地亚境内使用)更为常用。事实上,两者是同义词,它们的所指是一样的,意味着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是同一种语言(Brozové 1988:3)。
作为统一语言的塞-克语主要以黑塞哥维那式的“什托(što)”方言为基础,这种“变体”1“变体”下的子项还有“表达方式(izraz)”和“用语(idiom)”。在当时的国家版图内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不具备唯一性,包括西部的克罗地亚语和东部的塞尔维亚语两种主要变体,以及两种“标准的语言表达方式”(standard nojezična izraza):波黑语和黑山语(黑山语曾经被认为是塞尔维亚文学语言的次级变形)。塞-克语的西部和东部变体呈两极化趋势:西部以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为中心,东部以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为中心,这种现象影响着语言政策的制定(随着时间的推移,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和黑山首都铁托格勒2这里提到的“首都”均为南联邦的各成员国的首都,联邦的首都是贝尔格莱德。,即今天的波德戈里察,也逐渐成为语言变体的中心)。20世纪70年代,“波黑语标准语言表达形式”也被提倡,它首先是波黑国家的独特语言,同时也是塞-克语两极化的中和物,这一点可以在克罗地亚语变体和塞尔维亚语变体的语料库中找到佐证。黑山共和国1963年和1974年颁布的两部宪法都规定国家的官方语言是塞-克语,直到1992年,宪法中才将官方语言改称为“塞尔维亚语‘伊耶’化方言”(Lakić 2013)。
上述几种变体的差别并不大,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作为“民族独特性见证”的象征意味越来越浓。东部变体(塞尔维亚语)和西部变体(克罗地亚语)的发展在不同的社会和宗教环境中受到了不同影响。比如,西部变体较多受到拉丁语、意大利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的影响,而东部变体较多受到教会斯拉夫语、俄罗斯斯拉夫语、现代希腊语、土耳其语、俄语和法语的影响。除此以外,东部变体在发展过程与“什托”方言基准不断趋近,而西部变体则不断疏离。这些原因导致两种变体逐渐在所有的语言层面都出现了差异:首先是二合元音“jat”的反射差异(即“埃”化方言和“伊耶”化方言)。其次是形态化差异,如“告知”:informirati(克)-informisati(塞),“外交”:diplomacija(克)-diplomatija(塞)。再次是词汇的差异,比如“火车”一词在克语中是vlak,在塞语中是voz。此处还可以举个黑山语表达方式的例子:“明天”sjutra(即sutra)和“我不是”nijesam(即nisam)。在波黑语中辅音k和h有时也会换用,如塞-克语中的“如何”kakva在波黑语中存在kahva的形式。应该说,塞-克语东西两种变体在词汇层面的差异是最显著的,这主要因为它们所受的外部影响,集中体现为20世纪90年代克罗地亚语中新词的“创现”。词汇差异主要是在与其他语言接触过程中出现的,如opći(意为“总体”)和svećenik(意为“修士”)这两个词,是西部变体在与拉丁语的接触中形成的形式。同样的词语在东部变体中与教会斯拉夫语和俄语接触,变成了opšti和sveštenik的形式。另外,不同的历史、文学、文化和宗教(西部为天主教,东部为东正教)因素也给词汇带来了一定影响,如“主教”和“修道院”两词分别为:biskup(克)-episkop(塞)、samostan(克)-manastir(塞)。最后,两种变体在处理外来词时的取向也不太一致:克罗地亚语主张纯粹主义,坚持使用母语中原有的词汇,而塞尔维亚语比较开放包容。如“骆驼”和“药房”两词的形式分别为:deva(克)-kamila(塞)、ljekarna(克)-apoteka(塞)。1关于塞-克语的两种变体的差异的研究,详见Požgaj Hadži和Balažic Bulc(2004)以及Pranjković(2001)。
2.2 塞-克语的双重身份
尽管法律规定南联邦各民族的语言地位平等,但塞-克语无疑更为权威,它不仅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和黑山这四个成员国中是官方语言,而且在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也由于使用人数众多2南联邦1981年进行的最后一次人口普查显示,22,424,885人口当中,16,342,711人讲塞-克语,接近总人口的73%。见 https://sh.wikipedia.org/wiki/Popis_stanovni%C5%A1tva_1981._u_SFRJ (2018年3月30日读取)。而逐渐成为人际交流的“通用语”。国家的语言政策使塞-克语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南联邦护照、货币等。
“塞-克语”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名称为何会带来问题呢?首先,这个名称是人为制造的,它首次出现在德国印欧语言学家格里姆(Jakob Grimm)的研究中(Kapović 2010)。随着这个名称而出现的是一种“超国家理念”,它代表的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语言(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族作为民族并不存在,然而在中南部斯拉夫地区,语言身份往往与民族身份紧密关联)。塞-克语这一案例涉及四个民族(塞族、克族、波什尼亚克族和黑山族),他们有各自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所有这一切都影响着塞-克语的身份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诺维萨德协议》签订以来,塞克双方围绕语言名称问题争论不休,这一争论贯穿整个南联邦时期。20世纪90年代南联邦解体后,这一名称被贴上了“反面标签”(详见Požgaj Hadži 2013)。该问题在本质上具有历史性、政治性和身份性(Kapović 2010)。
“塞-克语”的名字已然反映了其双重性身份,布加尔斯基(Bugarski 2016)认为它的两个次级身份为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标准的塞-克语的身份具有矛盾性:一方面,外在身份强大,使其始终与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自然区分;另一方面,内在身份脆弱,表现为两种方言(“埃”化和“伊耶”化)和两种文字(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的分化形式。进一步说,强大的外在身份让联邦国家层面的语言政策趋同,而脆弱的内在身份使联邦内部成员国之间的语言政策发生异化。
2.2.1 塞-克语语言身份的强大性
尽管南联邦宪法没有规定塞-克语为联邦国家的语言,但它在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有着权威地位。在斯洛文尼亚,塞-克语不仅是大多数人使用的语言,还是政界和军队的工作语言(Gorjanc 2013)。斯洛文尼亚语涉及的不仅有民族问题,还有政治问题(Pogorelec 1983)。由于对斯洛文尼亚语在本国的地位感到不满,斯洛文尼亚语言学家在1975年发起了一场运动,希望规范斯洛文尼亚语的语言使用。1979年召开的“公众的斯洛文尼亚语”会议,标志着该运动达到高潮。该运动是在斯洛文尼亚斯拉夫学会和社会主义工人联盟共同指导和支持下开展的,从学术和政治角度都具有积极意义。由于这些活动,斯洛文尼亚语的功能在语言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发展(详见Gorjanc 2013)。
塞-克语在斯洛文尼亚还具有“预备语言”(rezervni kod)的身份,因为大部分斯洛文尼亚人都是双语使用者,他们主动向塞-克语的使用者趋近。此外,塞-克语的权威身份还因教育语言政策的实施得到加强。在斯洛文尼亚的小学里,塞-克语被作为必修课程教授1在当时的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塞-克语是学校的必修课,而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在其他成员国并没有被教授,由此可以看出三种语言的不平等地位。。媒体、科普读物和专业学术文献所使用的也是塞-克语,使其地位不断上升(详见Požgaj Hadži 2007)。南联邦语言政策的特定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语言教育政策来实现的。1981年,有人提出打造统一课程(即核心课程)的建议,其目的在于缩小南联邦各成员国之间的教育差异,同时在课程中减少母语课程、淡化文学文化差异。斯洛文尼亚公众坚决反对,联邦内部的摩擦也不断升级,该项建议最终未获通过(详见Požgaj Hadži 2013)。
南联邦语言政策在解决语料库建设2本体规划可以被认为是语言标准化的一种途径,公共交际中的用语由此而被确定下来。问题时所起的作用并不理想,矛盾贯穿着语言学术立场和政治立场。主要争议在于:究竟是从联邦国家层面进行整体的本体规划,还是从单独成员国层面,由各成员国自主规划本体?这个例子体现了南联邦语言政策的矛盾性,而非统一性。统一派希望通过建立唯一的标准变体来消除语言变体,分裂派则希望强调语言变体的个体性,把它们包装成标准的语言——这在20世纪90年代陆续成为事实。
需要注意的是,语言政策的“统一性”是以塞-克语正字法为基础的。制定正字法是1954年签订《诺维萨德协议》后的必然举措,当时克罗地亚文化协会和塞尔维亚文化协会对此达成了共识。1960年,一部塞-克语正字法以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两种文字出版发行1《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文学语言正字法及词典》,克罗地亚文化协会和塞尔维亚文化协会联合编著,萨格勒布、诺维萨德1960年出版。(Pravopis hrvatskosrpskoga književnog jezika s pravopisnim rječnikom, Matica hrvatska - Matica srpska, Zagreb - Novi Sad, 1960.)《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学语言正字法及词典》,塞尔维亚文化协会和克罗地亚文化协会联合编著,诺维萨德、萨格勒布1960年出版。(Pravopis srpskohrvatskoga književnog jezika sa pravopisnim rečnikom, Matica srpska - Matica hrvatska, Novi Sad-Zagreb, 1960.)。虽说克罗地亚方面对这部正字法持保留态度,但他们一直使用该正字法,直到1986年克罗地亚语言学家安尼奇(Anić)出版了新的正字法2《克罗地亚语或塞尔维亚语正字法手册》,安尼奇和西里奇编著,萨格勒布Školska knjiga 出版社1986年出版。Vladimir Anić i Josip Silić: Pravopisni priručnik hrvatskoga ili srpskoga jezika, Sveučilišna naklada Liber -Školska knjiga, Zagreb, 1986.。
词典的出版情形则完全不一样。1967年,第一部塞-克语词典出版,采用了双册的形式,一册为拉丁字母,另一册为西里尔字母3《克罗地亚-塞尔维亚语文学语言词典》,克罗地亚文化协会和塞尔维亚文化协会联合编著,萨格勒布、诺维萨德1967年出版。Rječnik hrvatskosrpskoga književnog jezika, I-II, A-K, Matica hrvatska - Matica srpska,Zagreb - Novi Sad, 1967.《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文学语言词典》,塞尔维亚文化协会和克罗地亚文化协会联合编著,诺维萨德、萨格勒布1967年出版。Rečnik srpskohrvatskoga književnog jezika, knjige 1-6,Matica srpska - Matica hrvatska, Zagreb - Novi Sad: 1967-1976.。塞尔维亚文化协会不断对该词典进行修订,1976年完成了第六次修订,而克罗地亚方面对此非常不满,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克罗地亚人认为,该词典不尊重克罗地亚语变体的特性,在术语使用方面不尊重克罗地亚的文学传统。
2.2.2 塞-克语语言身份的脆弱性
如果对南联邦各成员国语言政策的实施情况进行考察的话,不难发现塞-克语自身的脆弱性。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双方对于共同语言的正字法和词典的看法是存在分歧的。1967年,克罗地亚发布了《关于克罗地亚文学语言名称和地位问题的宣言》(Deklaracija o položaju i nazivu hrvatskoga književnog jezika)4关于《宣言》详见:http://krlezijana.lzmk.hr/clanak.aspx?id=274(2018年3月29日读取)。(下文简称《宣言》),此举使双方分歧进一步加深。该宣言旨在促使南联邦宪法对1945年制定的关于使用斯洛文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和马其顿语四种语言的规定加以澄清51945年2月14日发布的政府公报中之指出:“在南斯拉夫境内,官方文件可用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斯洛文尼亚语和马其顿语四种语言书写。”(Pranjković 2006)。《宣言》的目标未能实现,反而受到了政治谴责。作为回应,克罗地亚文化协会(单方面)废除了塞-克语共同的正字法,并且自行组织编写正字法。1971年,克罗地亚为了在联邦中寻求更大的民族和语言权利,掀起了一场名为“克罗地亚之春”的文化政治运动,《克罗地亚语正字法》6Stjepan Babić, Božidar Finka i Milan Moguš: Hrvatski pravopis, Školska knjiga, Zagreb, 1971.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版了。该正字法与这场运动一起被镇压了。
到20世纪80年代,克罗地亚国内关于民族、语言和政治的争论愈演愈烈,并且开始蔓延到南联邦的其他成员国。比如,在波黑的萨拉热窝出现了关于语言身份的争论(Vajzović 2001),在塞尔维亚的诺维萨德出现了关于南联邦语言政策与规划的争论(Vasić 1990)。这些讨论主要在成员国之间展开,联邦解体后,新的民族国家建立,关于语言的讨论转为在民族国家内部进行。
3.新的国家——新旧身份认同
20世纪90年代,在经历了一系列社会政治变革和战争之后,南联邦解体了。1991年,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分别宣布独立。1992年,波黑独立。在南联邦解体之后,塞尔维亚与黑山联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2003年2月4日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年塞尔维亚和黑山各自独立。2008年,科索沃单方面宣布独立。在新的背景下,关于南联邦时期的三种官方语言(塞-克语、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的争论重新展开。正如前文所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分离主义和对语言权利的过度追求已成为了语言问题的最显著标签。1991年联邦国家解体导致塞-克语失去了法律和行政身份,在新成立的国家,主体民族使用的语言取代其成为标准语,即: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黑语和黑山语。语言身份的确立象征着民族地位得到了肯定,但同时语言的标准化进程却不可避免地迎来了新的挑战。语言不仅是实现政治目标的象征1关于语言象征功能的研究,详见:Mønnesland 2013。,还是民族和领土同质化的途径(Baotić 2001)。20世纪90年代起,为了区别“他者”、标榜“自我”,各种语言在词汇规划、正字法规划、语法结构调整、语言地位规划等方面投入了巨大努力。
20世纪90年代,关于塞-克语及其“继承者”的一系列事件引起了国内外语言学家,尤其是社会语言学家的关注,他们积极地为以下的问题寻找答案:塞-克语之下究竟隐藏着多少种语言?一种,两种,三种,还是四种?2很多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如Jedan ili tri jezika?(Kovačević 2001:33),S jednog jezika na tri: premoć politike nad lingvistikom(Remetić 2001:45),One, two, three, four: It's Serbo-Croatian that counts(Bugarski 2005:310),Od jedan do četiri(Škiljan 2002:261),Malo internetske lingvistike: jedan, dva ili bezbroj jezika(Žanić 2007:10)。应该定义塞-克语当中的“多元标准”,还是对“统一的标准”进行分离分裂?回答此类问题也许有很多答案,因为“语言”的定义就有很多种(Mønnesland 2013),对于不同层面的语言问题也存在不同的理解。如果用类型学标准来考察,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之间根本不存在足以让两者相互独立的差别。用遗传学标准来衡量的话,问题同样很复杂,因为它们作为方言的根源难以考察(Kapović 2010)。如果要用语言政策来把一种语言一分为二的话,价值标准(即社会语言学标准)也许是最合适的依据——从这些新成立的国家的语言政策就可以看出,它们极力想把新的语言与它曾经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历史状态分离(Škiljan 1995)。语言是民族身份的重要部分,现在,克罗地亚人说的是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人说的是塞尔维亚语,波什尼亚克人说的是波黑语,黑山人说的是黑山语。
我们都知道,从抽象集体层面(比如民族)上说,语言身份是具有意识形态条件的(Škiljan 2000:219)。南联邦解体之后,语言的这些身份特征就浮现了出来。南联邦的语言政策强调的是“超国家性”,而新成立的民族国家的语言政策坚决强调“民族性”,并希望通过语言来传递民族信念和意识形态。在民族性方面,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波黑和黑山四个国家相互排斥。从前的南联邦成员国之间存在分歧,当今在新成立的国家内部同样存在分歧,这种分歧一般出现在激进派和温和派之间(Mønnesland 2001)。
在语言分裂的过程中,语言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形式,直接显示着意识形态立场(Badurina 1998)。语言是维持和加强民族身份和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因此语言问题时常伴随着一系列激烈的事件12015年8月26至29日在尼克什奇(Nikšić)和黑塞格诺维(Herceg Novi)举行的“涅戈什的日子”(Njegoševi dani 6)活动上,还举行了一场题为“语言的国家化”的研讨会。。标准语言的重新标准化必然会“经历内部标准性重新确立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受政治等社会背景因素所制约,这时候语言的‘声望’显得尤其重要”(Peti-Stantić & Langston 2013:94;Požgaj Hadži &Balažic Bulc 2015;Badurina 2015)。引起语言变化的原因还有:社会政治的变化、语言关系间的变化、人们对语言问题关注程度的变化、语言问题的政治化和激进化、语言政策的集约化等(Pranjković 2008)。
20世纪90年代克罗地亚独立以后,其语言身份出现了以下主要特征:1)纯粹主义——这是克罗地亚语凸显民族性和语言身份的重要方法;2)重新调整与外语的语言关系——历史上,克罗地亚语在德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和塞尔维亚语的阴影下产生了负面的身份效应;3)语言问题的政治化和“神话化”(Pranjković 2007)——“克罗地亚主义”和“新词主义”是加强克罗地亚语言身份的重要理念,在这些理念的影响下,克罗地亚语中出现了一系列具有深刻的民族象征意味的词汇。另一方面,克罗地亚语大力排除语言中的外来词,特别是那些反映塞尔维亚文化的词汇,各种版本的“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差别词典”相继出现(详见Požgaj Hadži & Balažic Bulc 2015;Badurina 2015)。这一时期,语言标准成为了“克罗地亚性”的觉悟标准。是否遵循这些新的语言标准,语言使用上能否做到“民族正确”,将人们分成了“纯正爱国的克罗地亚人”和“南斯拉夫怀旧主义者”(Opačić 2014)。除了词汇的变化,语言政策制定者还有意地制造争议,动摇原本较为稳定的正字法规则,以凸显克罗地亚语语言身份。他们甚至采取如“空格符”这样的标志对语言进行改造,比如把“我不要”这一词由原本neću的形式改写为ne ću,以显示克罗地亚语的独特性(详见Požgaj Hadži &Balažic Bulc 2017)。
与克罗地亚语不同,塞尔维亚语本身具有丰富而稳定的词汇,语言要素比较完备,没有必要通过改变词汇或语言结构去主动排斥克罗地亚语,因此本体上没有发生太大变化。不过,在文字的选择上,塞尔维亚加强了对西里尔字母的坚持。自2006年起,西里尔字母已经是塞尔维亚宪法规定的唯一文字1详见V.10.član Ustava Republike Srbije: http://www.ustavni.sud.rs/page/view/sr-Latn-CS/70-100028/ustavrepublike-srbije(2018年3月26日读取)。。西里尔字母被认为是“塞尔维亚民族文化中不可玷污的尊严。如果西里尔字母的传统不被尊重,就意味着塞尔维亚语不复存在”(Bugarski 2013:102)。《塞尔维亚语宣言》(Slovo o srpskom jeziku)被认为是大塞尔维亚主义的象征,因为它宣称其他的语言都是塞尔维亚语的变体。20世纪90年代,语言民族主义在塞尔维亚的公共话语中留下了痕迹,尤其是一些关于战争和仇恨的话语(Silaški N.idr 2009)。在波黑的塞族共和国2根据《代顿协议》,波黑由穆克联邦和塞族共和国两个政治实体构成,它们各自拥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和警察部队。其中塞族共和国占波黑领土的49%,主要人口为塞族居民。,此类现象更加显著。当前,塞尔维亚语的语言身份在外部面临着来自克罗地亚语、黑山语和波黑语的挑战,在内部面临着两种方言(“埃”化和“伊耶”化)和两种文字(拉丁字母和西里尔字母)的分化挑战(Bugarski 2016)。
自1992年起,波黑的官方语言有三种,分别是波黑语、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这种情况揭示出当地的社会政治现实。大部分波黑语言学家认为,波黑语有三种语言标准和三种语言身份,是既复合又统一的语言。由于语言的名称往往是民族名称的同义词(Granić 2010),关于波黑语,最主要的争论正是围绕其名称展开的:应该是“波黑语”还是“波什尼亚克语”?塞尔维亚语言学家不承认“波黑语”这一语言名称的存在,他们认为“波黑语”给人一种囊括了三种语言的错误印象,而“波什尼亚克语”指的是波什尼亚克族所说的语言,可以成立(Katnić-Bakaršić 2013)。这些问题对人们的沟通交流不构成丝毫影响,但却在“民族和语言权利是否得到尊重”这一层面引起了很多思考(Palić 2009)。如何对三种语言进行规范,三个主体民族无法达成共识(详见Požgaj Hadži & Balažic Bulc 2015)。除此以外,三种语言标准的同时存在,给媒体、司法、教育等领域的工作造成了极大的障碍。民族语言教育政策在课程和教科书里都得到了体现(Veličković 2015),但实际上,三个主体民族的历史文化独特性根本无法表现。可以用“同一房檐下的两所学校”来形容波黑教育的特点——学生们在一所学校里,被按照不同的民族分成了不同的班,不相往来(Trkulja 2017)。
2007年黑山宣布独立,黑山语成为国家的官方语言。自此,政治家从语言问题中发现了政治利益,便把语言问题逐渐升级为政治问题。跟几个邻国的情况不同,关于如何规范黑山语,黑山存在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方主张“拟古主义”,想把黑山语恢复成一百多年前的样子;另一方倾向以塞-克语作为标准黑山语的基础(Lakić 2013;Glušica 2011)。目前,黑山的语言政策主要倾向以新“什托”方言来规范黑山语。因此,黑山语的民族化,还需要经历语法结构的改变。在音素方面,语言学家为黑山语新创了两个音素和字母,即ś和ź,以代替早已存在的sj和zj。这两个新字母的出现,不但给人们的沟通交流造成了障碍,还在社会中造成了巨大的“文化冲击”。有人不支持这样的改变,有人“则一夜之间改变了自己的说话方式,急于表现出政治和民族认同”(Glušica 2010:36)。黑山语的标准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话语体系目前尚还处于“民族浪漫主义”时代(Mønnesland 2009:135),人们对于如何规范这一门新的语言尚未达成共识,遑论在世界范围内推介“黑山语言文化”了。
4.总结
总的来说,我们可以认为语言身份是一种动态现象,它代表了我们对文化的忠诚度,它容许我们做出改变,却保持着始终如一的主体性。尽管已经有很多可以参照的标准和模型,但语言身份的确定往往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会引发持久的争论。人们对语言问题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学问题,它涉及政治、历史、地理、社会、文化等众多非语言学因素。纵观历史,我们发现中南部斯拉夫地区的“语言”可以说是“民族”的代名词,因此语言问题的重要性超乎我们想象。
塞-克语的身份问题一直存在争议,这一名称反映了它的双重身份: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虽然南联邦的语言政策坚持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和塞-克语的平等地位,但实际上塞-克语因为有着最多的使用者,受到了国家语言政策的优待,因而具有更大的权威,处于统治地位。其外在身份的强大性,使其与斯洛文尼亚语、马其顿语区别开来。然而,其内在身份的脆弱性,使语言政策在联邦成员国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的离心现象。
随着南联盟的解体,塞-克语失去了法律和行政地位,被新成立国家的主体民族语言所取代。这些民族语言在新成立的国家里既是民族身份的象征,又是实现民族同质化和领土同质化的途径。语言的“民族性”取代了“超国家性”,它反映出的意识形态属性比以往任何一个历史阶段都要强。每一个国家都推行自己的语言政策:克罗地亚追求语言的纯粹性,主张新词主义,极力清除塞尔维亚文化成分;塞尔维亚将西里尔字母看作语言身份的重要标志加以坚持;波黑着力加强话语中的本土元素和东方文化传统;黑山则通过拟古主义和创造新音素的方式来体现民族和政治认同。每一个国家看待语言都有自己的态度。我们的研究认为,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政治干预后,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黑语和黑山语这四种中南部斯拉夫语言,终于走上了独立而正常的发展道路。它们之间的差别只会逐渐加深,不会再出现融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