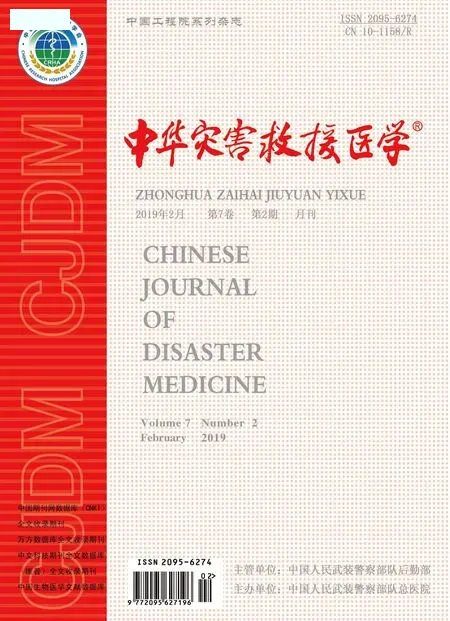急危重患者院际转运的安全性研究进展
谢建雷,杨晓玲,冷志兵,张晓娇,田维艳,苏家琼,蒲亨萍
重症患者转运通常包括院前转运、院内转运和院际转运。院前转运是指危重患者从创伤或疾病现场送到医院的转运,院内转运是指在同一医疗单位不同医疗区域之间的转运,院际转运是指在不同医疗单位之间的转运[1]。研究表明院际转运过程中,急救设备和药品有限、急救人员数量有限、路途颠簸车(机)载时间久、气压、温湿度变化等,使院际转运产生较高风险,转运途中患者发生并发症的风险极大增加,甚至出现死亡[2,3]。因此加快危重患者的院际安全转运研究极为迫切和重要。早在1993年,美国重症护理协会就制定了首份危重患者转移指南[4]。2004年,美国学者Warren等[5]达成了院际转运安全方面的共识。通过5个方面(运输前的协调和沟通、运输人员、运输设备、运输过程中的监测、标准文件)强调如何降低转运风险。随后,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各国也加紧了此方面的研究并制定了符合本国情况的相关共识及意见。我国的院际安全转运标准研究正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对国内外危重患者的院际安全转运研究进行综述,以期为提高国内医疗单位院际转运能力,加速我国院际转运相关标准完善化进程,降低危重患者院际转运风险提供参考和借鉴。
1 转运决策和知情同意
急救中心或急诊科一旦接到患者的转院要求,应立刻对患者病情进行评估。Pakula等[6]主张由专科医师、重症护士、运输团队等共同组成多学科团队进行讨论来权衡风险和收益情况。英国重症医学会(Intensive Care Society)[7]提出当前生理状态可用改良早期预警评分(modified earl warningscore,MEWS)来进行一系列评估(表1)。评分时以患者资料对照参数,分别获取单项参数的分值,各项参数所得分值之和为总分。联合氧饱和度、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及碱缺失等指标评分后将患者按照病情的危重程度分为低、中、高3个转运风险等级(表 2)[8]。
林晓燕等[9]目前已经使用符合本院实际情况的《急诊危重患者安全转运评分表》对患者的生命体征、意识等情况进行综合评分,并得出如评分过低,则应慎重考虑转运的必要性。中国医学会重症分会指出,在现有条件下积极处理后血流动力学仍不稳定、不能维持有效气道开放、通气及氧合的患者不宜转运[10]。但需立即外科手术干预的急症(胸、腹主动脉瘤破裂等)患者,应视病情和条件进行转运。已发生脑疝或血气胸尚未进行胸腔减压排气患者,为空中转运禁忌患者,应待患者病情平稳或进行进一步处理后方可空中转运[11]。
评估后如符合转诊条件,胡翼南等[12]主张立即和家属沟通,告知内容主要包括:患者目前的病情、转诊的目的、转运的目标医院、出发时间、大致的抵达时间、途中有可能发生的风险等,帮助其分析利弊,患者及其家属同意转运后应在转运协议书签字确认。患者的医保卡、门诊病历、各项化验单、影像学检查报告、心电图、出院小结等资料应一起带走。空中转运前还需认真向患者及其家属告知飞行需知,并认真检查患者随身携带的物品,如属机场管制物品,在不影响其病情的情况下均不能携带[11]。

表1 改良早期预警评分

表2 转运风险等级评估表
2 转运方式的选择
转运方式通常包括陆路转运和空中转运。应综合考虑患者的疾病情况、转运距离、携带设备、准备时间、急救人员数量、路况、天气、转运环境、患者的经济能力等来选择合适的转运方式。陆路转运不易受不良天气状况的影响、启动迅速、转运途中易于监测、花费少、途中发生并发症的可能性更低、急救人员更熟悉转运环境[10]。陆路转运通常选择救护车来完成,特定条件下,大规模灾难造成的批量重症伤员转运也可考虑铁路转运。空中转运是指利用飞机(主要是直升机)为急、危、重伤病员提供特殊医疗转运服务,包括患者确认转运需要、现场转运、途中监护和运输等环节[13]。直升机转运具有速度快、机动性强、飞行高度较低的优点,随着经济科技的发展,空中急救转运的优越性愈发明显[14,15]。目前北京、广州和武汉等发达城市已经开展空中急救转运医疗服务[16]。
3 转运前准备
在出发之前,参加转运的医护人员应当对患者的病史及已经进行的治疗和检查进行了解,进行包括体格检查在内的全面临床评估[7]。
3.1 呼吸系统 应充分重视患者的气道安全性,如风险较高,那么人工气道应提前建立。对于已插管患者,为防止车辆颠簸对气管插管深度的影响,应提前标识插管深度,并保证气管插管固定。对于躁动插管患者,应适当给予镇静。同时,应提前测试患者对车载便携呼吸机的适应性。尽量确保模式和参数一致性,出发前至少行一次动脉血气分析[7],并通过动脉血氧分压(PaO2>60 mmHg,1 mmHg=0.133 kPa),血氧饱和度(SaO2>0.90)等来判断患者对便携呼吸机耐受性及氧合情况[10]。
3.2 循环系统 安全的静脉通路是必不可少的,在转运过程中至少需要两条静脉通路(中央静脉或外周静脉)[17]。低血容量的患者转运过程中风险极高,所以转运前患者的活动性出血等导致血容量过低的原因应当被提前控制,并且应当通过补液来恢复血容量。若有需要血管活性药物也可适当使用,确保患者循环功能稳定。条件允许情况下应当进行动脉穿刺置管进行有创血压监测[18]。血流动力学稳定(收缩压≥90 mmHg,平均动脉压≥65 mmHg)[10]的患者才可进行转院。
3.3 特殊处理 对于不同原发病需要不同的处理措施:如出现气胸或可能出现气胸,那么转运前应进行胸腔闭式引流,引流瓶直立并且低于患者身体平面下方;脊柱损伤患者使用颈托和束腹带等进行有效固定;四肢骨折用夹板等护具固定;癫痫、高热惊厥患者适当给予控制防止复发;颅内高压应当使颅内压降至正常水平;对于肠梗阻和机械通气等患者,提前上鼻胃管;有尿管等其他管道的患者,应当将尿袋或其他引流袋内的液体排空,以防搬运时液体反流。对于空中转运患者,由于高空气体膨胀,易使玻璃瓶内的液体回流到通气管。因塑料瓶装液体有一定的可塑性、受气压变化影响小、不易破碎[14],因此空中静脉输液应使用塑料瓶装液体。
3.4 其他 出发前,应与接收单位进行及时沟通,向其说明患者病情,核实床位准备情况,将出发时间和预计抵达时间告知对方,以保证接收医院提前准备医疗设备、人力资源等,确保患者到达后能进行无缝衔接的检查、治疗和监护。空中转运应提前报有关部门审批通过[19]。
4 转运护送人员
高素质专业化转运团队,是安全转运的基础保障。胡冀南等[12]研究发现由专业人员进行转运,严重不良事件的发生率相对较低。《中国重症患者转运指南(2010)》 (草案)[10]指出,转运人员中应至少有1名具备重症护理资格的护士,并可根据具体情况配备医师或者其他专业人员(如呼吸治疗师、普通护士等)来完成。国内尚无统一的急救人员岗前培训专业教材和培训师资格标准,且急救转运队伍不稳定,急救人员缺失现象较严重[18]。急救人员培训和管理标准化、急救医师专科化、急诊专科护士资质和急救员资质的普及是我国急救转运人员的发展趋势。Kupas等[20]还专门分析和强调了专业急救护士在院际转运中的重要性。多数专家学者认为危重患者院际转运应由经过专门训练的医师和护士至少各1名来共同完成[20,21]。医护人员应该掌握心肺复苏术、电除颤技术、止血包扎技术、环甲膜穿刺技术、气管插管术、科学固定与搬运术等;熟悉使用各种车载医疗设备,如心电监护仪、便携呼吸机、除颤仪、供氧设备、吸痰器等;了解患者的基本病情、治疗方案和潜在并发症(如脑疝、大出血、窒息、休克等),并且有能力应对和处理这些病情变化。医疗机构应该对转运医护人员定期培训和考核,运用模拟人定期场景模拟演练[22]。美国要求承担空中转运的医护人员应进行为期12 d的初级培训,执行任务前120 d内参加为期12 d的高级课程[23,24]。德国要求飞行员具有2 000 h以上的安全飞行纪录;医师参加1.5~2.0年研究生课程培训,80学时急救培训课程,20车次救护车工作经验;医护助理参加3年以上的地面急救实践,520 h空中急救培训实践,具有2 750 h的院外急救工作经验[25]。而我国无统一培训标准,多数要求有急诊或重症监护病房工作经验且经过直升机救护专业培训[19]。
5 转运设备
5.1 救护车和直升机 我国卫生部在2007年颁布了《救护车》标准并于2008年开始实施,国内专家吕传柱等[26]通过几年的实践对我国救护车标准进行了详细的总结和剖析。院际转运重症患者应使用标准中所要求的抢救监护型救护车标准,并且至少达到此标准。其对救护车的车辆性能、电气指标、车厢、医疗舱的空间大小指标及设计规范、车辆标识等均作了明确规定。英国和欧洲救护车标准文件无一例外指出人员和装备均应有固定装置,尽量减少行进过程中安全隐患[7]。随着我国科技的进步,医疗设备的发展,我国救护车也在不断向智能化、信息化、专业化发展[27]。目前国内已经有部分地区的救护车达到了现代化一体化水平,车上配备了GPS实时定位系统,音频视频监控系统,诊疗数据实时传输系统等[28],极大提高了患者转运的效率和安全性。目前我国医疗系统使用的有EC120、EC130、EC135、AS350、贝尔407型等,空中转运飞机标准尚缺乏研究,我国尚未见相关政策标准[29]。
5.2 医疗装备 Venkategowda等[30]研究指出各种设备机械故障导致的不良事件占总数的64%。刘佳等[31]对国内转运不良事件的统计分析指出仪器设备发生故障占总不良事件比例的7.9%。朱青龙[32]提出转院前一定要确保常用物资、器材完好处于备用状态,包括气道管理设备、循环管理设备和各种监测设备等。本文笔者主张使用中华医学会重症医学分会[10]提供转运推荐设备(表3)。此表提供的是推荐装备,具体情况应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医疗技术发展状况而定,如部分地区急救车已经配备便携即时检测仪[33],随时可以进行心肌肌钙蛋白等各种指标测定。朱文亮等[34]把体外膜肺氧合技术应用于院际转运中。空中转运时,为避免高空低气压对水银体温计的影响,宜用电子体温计[11]。
5.3 急救药品 澳大利亚[1]、英国[7]、中国香港[35]的安全转运指南中强调了通用备药原则,如应准备能应对危及患者病情发生突变时的抢救用药、针对患者病情的特殊用药和缓解某些临床症状常规用药。中国[10]、印度[36]则提供了详细的最低配备药物清单,这些药物均为保证患者生命安全的基本抢救用药,如肾上腺素、西地兰、阿托品、多巴胺等。《中国重症患者转运指南(2010)》 (草案)还指出,对于病情特殊的患者,还应携带针对性药物。有晕车、晕机既往史者应携带抗晕机药物[11]。国内在院前急救药物品的管理上欠缺统一规定,容易出现救护车内药物品放置不合理、使用后补充不及时、无菌物品过期等现象[38]。
6 转运中监护
有调查显示绝大多数转运不良事件发生在转运过程中[37-39]。《中国重症患者转运指南(2010)》 (草案)[10]指出,患者原有的监测和治疗措施在转运过程中不应被随意改变,并降低转运本身对患者原有监测和治疗不利影响,护理人员应按时(建议1次/15 min)[40]记录途中患者的生命体征、一般情况、各项监测指标、救护车上接受的治疗、有无突发事件及该事件的处理措施等。各国指南及专家都强调途中监护的重要性,鉴于各国所述监测项目各有所长,项目繁多,现从以下几方面概括列出。

表3 《中国重症患者转运指南(2010)》(草案)危重患者(成人)转运推荐设备
6.1 循环系统 监测体温、脉搏、无创血压、心电图、血氧饱和度、末梢循环情况等。间歇性无创血压测量对运动影响很敏感,在移动车辆中不太可靠,而且无创血压会对监护仪电池电量消耗比较大,建议进行持续的有创动脉血压监测。中心静脉置管不是必须的,如果要补充血容量,应尽量在转运前进行相应的补液和治疗。
6.2 呼吸系统 监测呼吸频率、节律、呼吸音、氧气供应情况,机械通气患者还应该对患者的吸呼比、潮气量、气道压力等进行监测和记录。若条件允许,也可监测呼气末二氧化碳分压[17]。对于频繁躁动的患者可以考虑适当使用镇痛、镇静药,但不能抑制其自主呼吸。
6.3 意识方面 澳大利亚[1]和中国香港[35]指南还特别强调通过格拉斯哥昏迷量表和瞳孔反应来评估患者意识,还应定时进行疼痛评分,部分患者还需监测颅内压。
6.4 管道的监测 对于各种管道如气管插管、胸腔腹腔引流管、中心静脉导管、胃管、导尿管等,应注意固定妥善,防止管道的移位、脱落、打折,保证管道通畅。观察患者输液情况:液体量、输液速度、穿刺部位皮肤情况等,保证输液管通畅,维持有效循环。
6.5 其他 对于不同原发病的患者,如颅脑外伤、腹腔大出血、血气胸等因为搬运或转运时体位的变化易引起病情突变,所以应随时注意转运途中各种原因诱发的并发症,随时做好抢救准备。还应对担架或担架车做妥善固定,并且应固定好车上的各种仪器设备,随时监测各种设备的仪器屏幕和报警声音,提高警惕,严防不良事件的发生。对于空中转运患者,起飞降落时加速度、高空气压、气温降低、高空氧浓度降低、飞机震动、噪声等因素都会加大患者病情恶化的可能性,严重威胁患者安全,因此应严密监护患者病情变化,随时做抢救准备[11]。
7 转运交接
抵达接收医院后,转运人员应与负责接收的医务人员进行正式交接来落实治疗连续性。Robertson等[41]调查发现交接时发生的信息错误率达13%,世界范围内,大多转运不良事件归因于转运人员交接时不到位,如移交错误的检查结果、治疗方式、用药信息、手术部位等,遗漏关键的信息,如过敏性体质、传染病史等。Klim等[42]制定了标准且系统的交接框架,有效降低了交接不良事件,提高了交接的准确性和效率。在国内,提出了无缝衔接,此项研究亦可有效提高患者转运时效性和成功率[34]。关键的交接内容包括患者病史、实验室检查、重要体征、治疗经过,以及转运的原因、途中患者各项监测数据、特殊的临床事件和治疗等,交接后应书面签字确认。目前国内尚无统一的危重患者交接单和标准化流程,多为各医院和急救中心自制的危重患者转运交接单。
随着人民群众对高水平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增加,双向转诊等医疗保障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我国科技和航空事业的发展,院际转运患者数量与日俱增。院际安全转运规范和完善符合新时代医疗事业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院际转运过程中各种医疗资源有限,途中不确定因素较多,期间患者的安全问题已受到严重威胁[41]。而国内在转运人员资质与培训、急救药物品管理、转运交接流程标准化等方面均无统一标准。目前尚未见有权威部门发布院际安全转运指南类的文件,多为各急救中心和医院自行制定安全转运规范。本文结合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分别从医疗设备、医护人员、途中的监护、沟通交接等重要环节对院际转运的安全问题进行了综述,以期为国内院际转运标准化流程、建立安全转运临床路径、安全转运质量管理、空中转运规范化流程等提供参考借鉴。通过对比发现,单独将某一国家的危重转运指南汉化并应用于我国院际转运工作中并非智举。应有效整合国外各指南并因地制宜地制订符合我国国情的院际转运规范和标准,从而提高院际转运危重患者的安全[42]。同时,国内空中医疗救援转运体系的构建,空中医疗救援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规范的构建,空中医疗医护人员培训标准的制订等将是下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