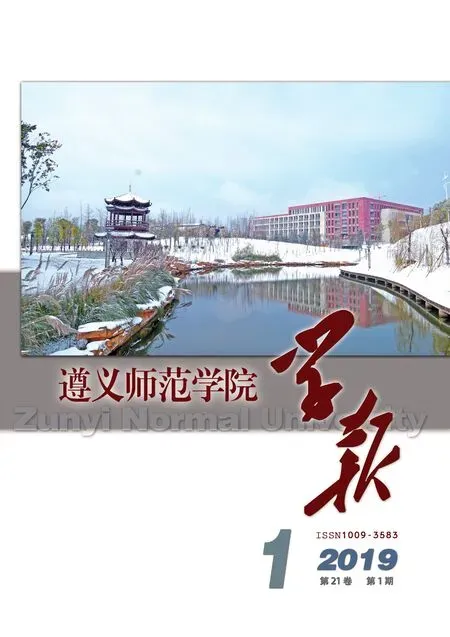“鬼方”新考
杨承友,陈晓芳
(遵义师范学院体育学院,贵州遵义563006)
关于“鬼方”一词在甲骨文、钟鼎文、《易经》《诗经》《竹书纪年》中都有记载,后人觉得古人对“鬼方”的描述不够清楚,产生了“鬼方北方说”和“鬼方南方说”。汉唐时期的学者大都认为“鬼方”为远方、北方国。有学者认为“鬼方”为“方国”,是基于商朝有许多小国都称“方”而考量的,例如土方、吕方、苦方、龙方、马方、蜀方、盂方、羌方、周方等。或者直接就说是西羌的,认为其活动范围大约在我国的西北地区。“鬼方北方说”的典型代表为扬雄、班固等。①鬼方[EB/OL].[2018-09-10].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C%BC%E6%96%B9/803985?F.宋元以降有朱熹等人根据《竹书纪年》记载“武丁三十二祀伐鬼方,次于荆。三十四祀王师克鬼方,氐羌来宾”而另立新说,即“鬼方南方说”,将“鬼方”推定为荆楚西南一带,有人结合殷周地形图揣度其范围大约包括今湖南西北小部分、重庆东南部分、贵州大部和广西北部、云南东部部分地区。[1]P26但是,“鬼方北方说”则认为“荆”指今陕西境内的荆山。
后世考据学的兴起,学者们对“鬼方”研究的兴趣空前高涨。“鬼方南方说”找到了更多支持其观点的证据。《诗经·商颂》称赞殷高宗武丁时大书特书其功绩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而《易经》、《竹书纪年》、《史记》只记载了武丁讨伐“鬼方”且并无讨伐荆楚的记载。学者们据此认为史书记载的都应该是武丁开疆辟土中厥功至伟的大事,所以它们记载的都是同一件事,即《诗经》所载武丁讨伐“荆楚”之事就是《易经·既济》所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之事。思想家王夫之在其著作《周易内传》中也说:“楚人尚鬼,故曰鬼方。”并把屈原的《离骚·山鬼》,宋玉的《高唐赋》和《神女赋》中的巫山云雨这些宗教祭祀作为楚人好鬼的佐证。
也有“鬼方南方说”的学者谈出另外的理由。《史记·楚世家》说陆终有六个儿子,第六个儿子叫季连,“芈姓,楚其后也”。季连被楚国王族尊为始祖。《大戴记·帝纪》称:“陆终氏娶于鬼方氏。”远古时代,山川阻隔,交通闭塞,不似后世交通渐趋发达,所以荆楚距“鬼方”不会太远。故“鬼方”在遥远的北方不大可能,在荆楚的西南面倒是可能。虽然这里面有神话传说,但是谁也不敢说中国古代的神话完全是神话。
当然,“鬼方南方说”所提供的理由,“鬼方北方说”大都持有反驳的意见。
国学大师王国维的《鬼方昆夷玁狁考》基本上肯定了“鬼方”在北方这一位置的观点,并且结合音韵学给以论证,证明“鬼方”、昆夷、玁狁就是后世所说的匈奴,是同一民族的音近异译,并通过对古文字的研究,认为“鬼方”是“畏方”。王国维的权威地位让“鬼方北方说”在学术界几成定论,以后再无撼动者。
笔者经过考证,就“鬼方北方说”存在的一些疑点谈一些看法。
一、王国维关于“鬼方就是畏方”的理论不正确
关于“鬼”字,“鬼”的甲骨文都成身形,大约有三种形状,都是一个大脑袋,下面的身子或者正着,或者侧着,或者侧面跪着。徐中舒《甲骨文字典》根据甲骨文字形的分析解字是“象人身而巨首之异物,以表示与生人有异之鬼。”[2]P1021《说文解字》言:“人所归为鬼。”其所本篆字为侧身之鬼,所从“厶”,乃后世之增繁。《礼记·祭义》云:“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谓鬼。”王国维认为“鬼方”就是“畏方”,是研究了小盂鼎、梁伯戈(又称鬼方戈)二件青铜器上的“鬼方”铭文,并结合大盂鼎、毛公鼎、者尚盘等青铜器物上的金文中的“畏”字铭文作为旁证而得出的结论。王国维认为,《小盂鼎》的“鬼方”之“鬼”字“从鬼从戈”,《梁伯戈》的“鬼方蛮”之“鬼”字是“从鬼从攴”,“二字不同皆为古文畏字”。并说,《大盂鼎》的“畏天畏”二字上一“畏”字是“从鬼从卜”,下一“畏”字是“从鬼从攴”;《毛公鼎》“敃天疾畏”“敬念王畏”都是“从鬼从
卜”;《者尚盘》之“畏”字“从甶(鬼头)从攴”。“畏”字“从鬼从卜”,“卜与攴同音,又攴字之所从,当为攴之省字”。他又说:“而或从卜,在鬼字之右,或从攴,在鬼字之左,或从攴,在鬼头之下,此古文变化之通例,不碍其为一字也。”并认为,鬼字“从攴从戈,皆有击意”。[3]P583-606台湾学者许进雄编《简明中国文字学》认为“畏”字如“巫师戴面具扮鬼且持兵器之象,其威力更高,令人畏怕”。[4]P437这样看来,王国维的分析也不无道理。这不得不让笔者想起在贵州有一句地方话来,即贵州当地人们鄙夷一个遥远的、贫穷落后和人烟稀少的地方为“鬼都打得死人的地方”。“鬼都打得死人的地方”,这不就是“鬼方”吗?实际上,在人们的心里鬼不是以打人使人感到害怕的,鬼是以吓人叫人害怕的。都认为鬼是以打人叫人害怕的,在这一点上王国维先生和贵州人的观点略同,这是不是佐证了贵州曾是历史上的“鬼方”呢?因为这句地方话一定是贵州地域上的人们一代又一代的口口相传流传下来的文化符号,而笔者从小就出生并生活在毗邻贵州的蜀中近二十来年,却从未听过有如此说法。

“鬼”“畏”“甶”字形溯源
其实,王国维的“鬼方”就是“畏方”的论断是值得商榷的。首先,王的研究是基于青铜铭文即金文的,而“鬼”“畏”二字都是有甲骨文的,是甲骨文里不同的两个字。同时,甲骨文也有关于“鬼方”的记载,如前面提到的《库方二氏所藏甲骨文卜词》(237)“贞王勿乎妇好往伐鬼方”、《小屯·殷墟文字乙编》(6684)“己酉卜宾鬼方昜亡祸五月”等。甲骨文主要存在于商代,金文主要存在于周代。准确地说,商代末期也存在金文,商代末期的甲骨文与金文是一致的。商代末期金文是早期的金文,以图像文字为主,写成文章的少,所以金文的字数都比较少。王国维所依据的大盂鼎、小盂鼎、毛公鼎、梁伯戈、者尚盘等青铜器要以大盂鼎、小盂鼎为早,它们是西周前期康王时代的青铜器,其铭文属于早期金文,已具有鲜明的金文书风,距离武丁伐鬼方时期的甲骨时代(董作宾以一定的标准把甲骨文划分为五期,将盘庚至武丁时期作为甲骨文第一期)仍然相去甚远,大约二百年。在这二百年期间,作为字形固定度极低的早期文字甲骨文、金文,其一字多形的情况必无定数。所以,一个“鬼”字出现很多个字形,是完全可能的。而王国维“鬼”即是“畏”的推理虽然很说得通,但未必就是事实真相。但无论怎样,它们都与“甶”字有关。《说文》曰:“甶,鬼头也,象形。凡甶之属皆从甶。”许进雄编《简明中国文字学》称:“甶,扮鬼神所戴的面具形。”[4]P431徐中舒《甲骨文字典》对“甶”字的解释为“所斩获敌国之首也,用为祭品”。[2]P1023因此,“甶”与头部有关,“鬼”“畏”二字与“甶”即头部有关,王国维才将“鬼”与“畏”字联系了起来。王国维“鬼方即是畏方”不成立,就会让王国维的“鬼方”(文字推演)学说关键性断链(如其臆断“隗”字就是“畏”字等),其北方说也就无立锥之地了。
二、“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的“荆”指的就是湖北省南漳县的荆山
《竹书纪年》载“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后人围绕这个“荆”究竟在什么地方争论不休。“鬼方北方说”说“荆”指的是陕西境内的荆山,“鬼方南方说”指的是湖北境内的荆山,为此争论了几百年。我国境内有五座荆山,但最为出名的是湖北省南漳县的荆山。一般来说,没有特别说明,这里的荆山应当指最具代表性的湖北境内的荆山才对。《山海经·山经·中山经》多次提及“荆山”,根据文意判断,书中的“荆山”应当是湖北荆山。古文中的地名但凡说到地名“荆”字,人们的第一反应一定是“荆楚”。《尔雅》说:“汉南曰荆州。”《尚书·禹贡》又说:“荆及衡阳惟荆州。”“荆”,指荆山,在今湖北省南漳县西;“衡”,指衡山,在今湖南衡山县。荆州是大禹时九州(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和雍州)之一,划分的时间是非常久远了。而“荆”,有时又称楚国,它是楚国的别称,也可以连称“荆楚”。楚国建国于周成王时期,晚于商代武丁时期一百多年。所以《诗经·商颂》说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是后代言前代之事,其“荆楚”亦非实指,而是指荆楚方向的地方,那就是除了后来的“荆楚(楚国)”之地,还有“鬼方”。故“鬼方南方说”认为《易经》《竹书纪年》《史记》记载的武丁讨伐“鬼方”跟《诗经》记载武丁讨伐荆楚是同一件事是站得住脚的。
三、“鬼方”活动地带不应在周人或者周朝(西周)的核心势力内
周朝建国前周人主要活动在陕甘一带,在殷武丁时代,周成为商的封国,陕甘一带理所当然成为周人的势力范围。国学大师钱穆在《国史大纲》中也持这样的观点:“若以安阳为中心,安阳至丰镐之距离为半径,画一圆周,约略可以想像殷王室政治势力圈之大概。”[5]P33今甘肃庆阳、陕西延安等地区自认为该地区是远古“鬼方”,庆阳有周先祖不窋的陵墓——周祖陵。如前文提到的武丁伐“鬼方”,岂不是成了武丁讨伐的地点是其封地周吗?还是周人没有肃清“鬼方”之敌而与其混居一地?这显然不符合逻辑,是不可能的事情。
再来说说殷武丁伐鬼方和《小盂鼎》记载的西周盂攻打鬼方的事情。
大盂鼎和小盂鼎都是道光年间在陕西岐山吕村一带先后发现的西周青铜器。大盂鼎的书法艺术价值早已得到书法金石爱好者的顶礼膜拜,而小盂鼎因为其离奇失踪太早而不为人们熟悉,只遗留下一纸由于器身残泐而模糊不清的拓本。但是小盂鼎铭文记载了西周重大的历史事件,其历史价值跟随人们的研究进程而显得尤为重要。
《大盂鼎》记载的是康王对贵族盂的策命与赏赐等方面的事迹,而《小盂鼎》记载了盂率领西周军队与“鬼方”的战争,有西周军攻打胜利取得战利品以及商王对盂赏赐的记载,事件大约发生在康王抑或昭王时期。小盂鼎记载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什么地方呢?这又得牵涉到“鬼方”在什么地方的问题。西周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由武王姬发建立。成王五年,始建东都成周洛邑;公元前770年(平王元年),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这就是说康王抑或昭王时期,西周的都城仍在镐京。大、小盂鼎出土在岐山吕村,周人曾一度迁至渭河流域岐山以南的周原,这也是周字的渊源。岐山离镐京很近,盂征战胜利“班师回朝”铸鼎纪念最后深埋于此地也在情理之中。如果鬼方北方说成立,“鬼方”之敌与镐京近在咫尺,已直接对镐京构成威胁。成王、康王时期,西周的国力空前强盛,史称成康之治。按理说西北一带陕甘地区是西周的“老巢”,是其“核心势力范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不可能有“鬼方”之敌在此嚣张,即使是到了个别学者认为的小盂鼎可能铸造在昭王时代,也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
四、“鬼方易”实为甲骨文“鬼方昜”
“鬼方北方说”认为甲骨卜辞载“鬼方易”是指“鬼方”向远方逃走或迁走之意。不知道“鬼方易”出自哪一片甲骨,但是关于“易”字,根本就没有“逃走、迁走”的义项。倒是《小屯·殷墟文字甲编》(3343)和《小屯村·殷墟文字乙编》(6684)都有“鬼方昜”的相关记载。《说文》言:“易,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徐中舒认为《说文》所说形义皆不确,并说“易”字原字像两酒器倾注之形,故会“赐与”之义,引伸之而有“更易”之义,现在的字形是截取部分而成。[2]P1063《说文》称:“昜,开也。从日、一、勿。一曰飞扬,一曰长也。一曰强者众貌。”“昜”字会意字,许进雄编《简明中国文字学》认为“有太阳高升标杆以上位置”的意思。[4]P304无论怎样,两字有本质上的区别。“鬼方北方说”并说经考古发掘研究,已证明“鬼方”最后迁到了南西伯利亚东起贝加尔湖西至巴尔喀什湖一带。可是考古发掘的大多是为数不多的青铜器和一些城墙,但是没有关键性的文字类文物出土,很难支撑其观点。
五、梁伯戈铭文“鬼方蛮”的“蛮”应指我国南方少数民族
梁伯戈是国学大师王国维最钟爱的四件宝贝(虢季子白盘、梁伯戈 、不期敦、兮甲盘)之一,大约铸造于春秋早期,是梁伯征伐“鬼方”时所作之戈。戈正反两面均有小字,一面为“梁伯作宫行元用”,一面为“抑鬼方蛮□般□”共十四个字。这“鬼方蛮”,指的是哪里的人?《说文》曰:“蛮,南蛮,蛇种。”旧时指称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礼记·王制》说:“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皆列其中。当然,“蛮”古时也泛称我国四方边远少数民族。《尚书·禹贡》云:“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蛮”的两个意思来解读“鬼方蛮”都说得通,前一个意思更加明确,直指所向之敌,后一个意思所指范围就显得宽泛而模糊。基于后一个意思,为什么不说成“鬼方夷”或者“鬼方戎”什么的?难道这是历史的巧合?这值得深思。既然梁伯戈是梁伯征讨“鬼方”所铸造的戈,那么其上铭文所指向的敌人应该是非常明确的,非此即彼,不容含糊。所以,“鬼方蛮”应指荆楚西南面的少数民族才较为合理。实际上,“鬼方蛮”、“荆蛮”都应是殷周时期以来历史上对荆楚及其西南面的“鬼方”这一地域的少数民族的蔑称。
综上所述,“鬼方”这个“鬼地方”究竟在什么地方,还是“鬼方南方说”较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