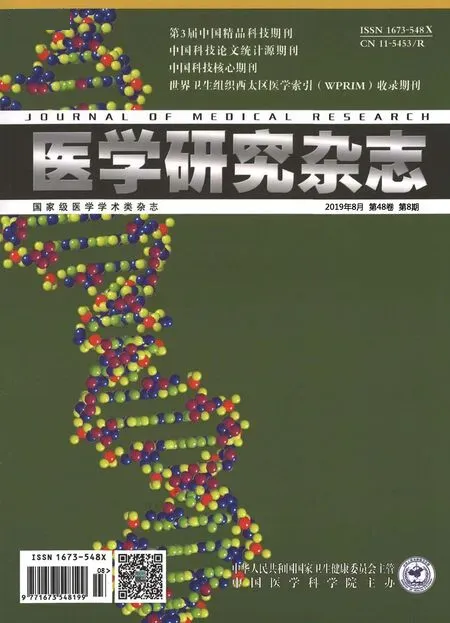中枢PAG区ALLO波动在PMD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刘 坤 张胜男 王玉杰 李亚琼 李自发 魏 盛
经前烦躁症(premenstrual dysphoric disorder, PMDD)是经前期综合征(premenstrual syndrome, PMS)的严重亚型,是指女性在经前1周左右出现的情绪、躯体、社会适应等方面的异常,主要表现为心烦、急躁易怒、情志抑郁、疲劳、小腹坠胀、小腹胀痛及学习能力下降等症状。其症状在经前出现,月经来潮后症状减弱或消失。不同文献报道的各地区发生率存在差异,而严格符合PMDD诊断标准的发生率为3%~8%,并且其发生率在逐渐增加[1]。PMDD的症状严重影响患病女性的身心健康及正常工作和生活。
目前公认PMDD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神经内分泌失调导致的疾病,可能与激素失调及神经递质异常有关。其发病机制与孕激素的代谢产物四氢孕酮 (allopregnanolone, ALLO)的关系尤其密切,有文献报道ALLO在外周血或者脑脊液的水平降低与月经前焦虑障碍相关联[2]。《美国精神病学杂志》于2013年发表《PMDD与脑》一文指出,经前期情感障碍起源于脑已被认知,PMDD的女性患者脑的结构和功能发生改变[3]。在相关脑区的研究中,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periaqueductal gray,PAG)在PMD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被逐渐了解。本文结合国内外文献报道从黄体期孕激素及ALLO的浓度变化引起中枢PAG区GABA能神经元及其受体以及神经环路的变化从而引起行为反应性的改变这一微观机制切入,对PMDD患者的症状病因学做一综述。
一、PMDD的发病机制与孕激素及其代谢产物的相关性
已有文献报道PMDD依赖于女性激素的周期性变化,特别是与黄体期孕激素及其代谢产物四氢孕酮密切相关,其含量变化是PMDD发病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4]。高慧等[5]研究证实,黄体期孕烯醇酮与别孕烯醇酮的降低、脱氢表雄酮的增高、脱氢表雄酮/别孕烯醇酮和脱氢表雄酮/孕烯醇酮比值升高是PMS情绪变化的生物学因素之一。
动物实验方面表明,具备PMDD症状的焦虑及抑郁情绪大鼠的脑中枢内孕激素及其代谢产物含量显著增加,而在动情周期晚期卵巢分泌的孕酮和ALLO会显著降低。在大鼠的行为学测试中也证明孕激素的含量改变会影响其焦虑情绪。动情周期晚期的大鼠对旷场环境更加恐惧,一定量孕激素注射可缩短大鼠强迫游泳累计时间,缓解其焦虑情绪[6,7]。痛觉过敏作为与大鼠焦虑行为增加相关的现象,在动物实验中也得到证实。Devall等[6]研究表明,对动情周期晚期大鼠进行5min温和导致焦虑振动应激可诱导痛觉过敏反应,动情周期的其他时期则不会观察到类似的现象。而孕酮给药模拟大鼠在发情后期自然发生的孕激素下降,表现出与后期发情期动物相似的诱导的痛觉过敏现象。
同时,激素水平变化的速率是PMDD发病的重要影响因素,孕激素及其代谢产物ALLO在黄体期含量增加后的突然撤退是PMDD发病机制的重要方面。有研究指出,自然周期的大鼠处于动情周期晚期时,孕激素分泌急剧下降。 Smith等[8]发现给予大鼠长期超过生理剂量的外源性孕激素随后突然撤退能诱导出突然增加的焦虑行为。Doornbos等[9]也提出对大鼠给予外源性孕酮后突然撤退促使对应激反应源的反应性增加,而逐渐递减的撤退则不会。因此,孕激素及其代谢产物ALLO含量的迅速下降可能是PMDD的关键诱发因素。
临床工作已经表明PMDD依赖于女性激素的周期性变化,其症状出现于黄体晚期,此期孕激素含量增加,在黄体晚期血中孕激素或其合成类似物迅速减少之时其症状出现[10]。正常育龄期女性在黄体期出现血清黄体酮分泌的高峰,PMDD患者体内的ALLO含量较正常高[11]。与动物实验现象相似的是,PMDD患者有更高的电刺激皮肤感觉疼痛评分和更低的缺血阈值,而研究表明女性在黄体期的痛觉过敏与焦虑行为增加有关[6,12]。孕激素减少的速率对PMDD发病的作用在临床研究方面体现为患者的临床症状与黄体期孕酮减少率之间的关联[13]。而在黄体晚期女性卵巢黄体酮分泌迅速下降,可能成为触发对心理反应增强的因素之一。
二、PMDD的发病机制与PAG区的相关性
近年来,国内外研究者从神经机制及相关脑区来揭示PMDD的发病原因。有文献指出杏仁核、下丘脑、隔区、海马、额叶皮质、边缘皮质、前额皮质是情绪调节过程中的重要脑中枢。高明周等[14]在总结了CT脑功能成像、核磁技术等影像学研究的基础上指出PMDD的发病与额叶、海马、杏仁核的关系密切。韩贺云等[15]提出通过事件相关单位(ERPS)技术记录大脑诱发电位来反映认知过程中脑的神经电生理改变。有文献表明,经前时期下丘脑和脑垂体处激素浓度改变会导致中枢神经递质的活性下降,进而导致异常情志和行为的出现。已有研究证实,人类的情绪感知与脑中枢海马关系密切,其脑神经的萎缩会导致抑郁程度明显加重[16]。Gingnell 等[17]研究指出,PMDD患者在月经周期的不同阶段其焦虑情绪和杏仁核反应性会有不同,即PMDD患者的发病机制与杏仁核关系密切。
PAG区是由一群高密度的神经细胞围绕中脑导水管构成的一片扇形区域,是调控恐惧反应的重要脑区。有文献指出,参与调控恐惧反应的中枢也对情绪类的疾病产生调控作用,尤其是PAG区[18]。PMDD作为以焦虑和愤怒行为等情绪异常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综合征,其发病机制与PAG的联系已经得到了证实。Griffiths等的研究显示PMDD的发病机制与PAG区受体亚基的上调有关。已有研究表明,GABA能神经递质系统在PMDD的发病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19]。而Bäckström等研究发现GABA能神经元遍布大鼠的整个PAG区,尤其是背外侧区域。此外,PAG区在大鼠疼痛传导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是痛觉信号传递过程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重要结构,在痛觉调制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20]。这与动情周期晚期诱导大鼠的痛觉过敏反应以及临床工作中的PMDD患者出现更高的电刺激疼痛感觉相一致。
三、PAG区ALLO波动在PMD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
已有研究表明PAG区的孕激素及其代谢产物ALLO波动参与了PMDD的发病机制[21]。Devall等[22]在研究药物氟西汀对PMDD的治疗效果中指出,短期给予低剂量氟西汀可以提高动情间期晚期脑内ALLO浓度,减缓孕酮代谢产物的突然下降。动情周期晚期氟西汀诱导的脑内ALLO浓度提升抵消了生理性下降造成的影响,从而解除了撤退效应致焦虑的触发机制。
PAG内含GABA能神经元及GABA等神经递质,GABA是一种重要的抑制性神经递质,其浓度的降低会导致焦虑情绪的增加。GABA能神经元作为以GABA为主要神经递质的神经细胞在脑内的抑制性反应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有文献指出,黄体晚期孕酮下降与中枢神经系统GABA改变密切相关,而已有研究证明ALLO是GABAA受体的有效正向调节剂。孕酮及其代谢物可通过基因机制调节GABAA亚基受体的表达[23]。
Griffiths等指出在动情周期晚期或外源性孕激素撤退后,脑内孕激素浓度下降通过其代谢产物ALLO引发GABA能神经元的GABAA受体的α4、β1 和δ等亚基上调。而这些转录变化会改变正在进行的GABA能神经元抑制活性水平,从而上调神经元集合的兴奋性。而PAG区神经环路兴奋性的增强在清醒动物中表现为焦虑水平及对应激刺激的行为反应性增加[24]。
其他相关研究也支持这一研究结果。Brack等在大鼠的神经电生理实验中发现动情周期晚期PAG区内输出神经元上的GABA能量值明显减少,这使得环路更易兴奋。有研究表明,动情周期晚期PAG神经环路功能兴奋性增强降低了由直接电刺激PAG区诱发的逃避行为的阈值,对五肽胃泌素(一种已知的给药后可激活PAG神经环路的多肽类物质)的自主神经反应性在动情周期晚期显著增加了[22]。同时,在大鼠动情周期晚期诱发痛觉过敏时的PAG神经环路的功能性激活也发生了改变,表现为即早基因c-fos的区域表达减少,这与应激诱导的GABA能神经元 c-fos 表达降低一致[25]。因此,PAG区对ALLO波动的敏感度所引发的一系列变化可能是PMDD的关键发病机制。
四、展 望
PMDD的发病机制与孕激素、ALLO及PAG区的联系可概括为女性黄体期脑内孕酮含量增加后的迅速降低造成的ALLO生理性回落触发了PAG区GABA能神经元亚群突触外GABAA受体表达的上调,这种转录变化增加了PAG神经环路的兴奋性,而这一神经机制的改变表现为对急性心理应激的行为反应性和焦虑水平的增加。从而表现为在月经前期的焦虑、行为障碍等方面的改变。
目前对PMDD发病机制的研究热点集中在脑区及激素水平,并且已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对于揭示PMDD的发病机制提供了大体的方向但在脑区及激素水平的微观机制及具体的深层联系、各因素之间的相关性等方面却缺乏深入的研究。本文阐释的中枢PAG区在PMDD发病机制中的作用可为研究PMDD的微观发病机制提供新的方向和切入点,如海马、前额叶皮质等情绪调控相关脑区对孕激素及其代谢产物的敏感度程度如何?孕激素及其代谢产物的波动如影响上述脑区又会带来怎样的改变?在细胞水平上不同的神经元类型对GABAA受体表达有何影响?这些科学问题的回答必将使得对PMDD病因及发病机制的研究取得更深入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