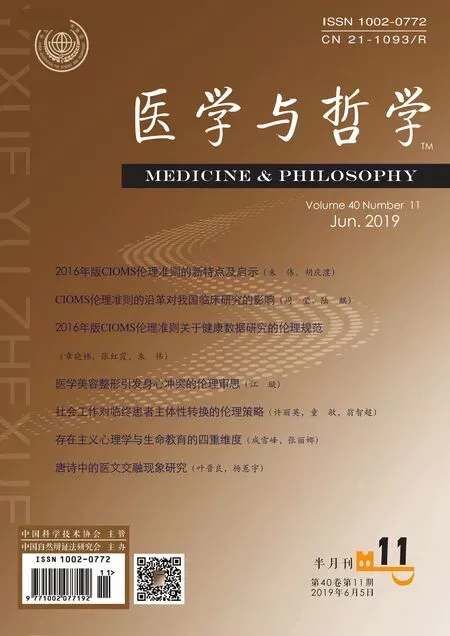临床经验:中医临床理论的核心
钟玮泽 张琼如 蔡鸿泰 郭 华
中医界历来各版本的《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均体现出对中医理论哲学基础的高度重视,并以独立的章节讲述中国古代的某些哲学思想,例如,《中医基础理论》“阴阳五行”一节指出:“古代医家在长期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将阴阳五行学说运用于医疗领域,借以阐明人体的生理功能和病理变化,并用以指导临床的诊断和治疗,成为中医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除中医基础理论教材外,刘长林[2]于《中国象科学观》指出中医学与哲学的密切关系,如“中医学具有很强的哲学性……突出表现在阴阳、五行和气的理论上”。《中医哲学基础》指出:“在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下……中医学形成了独特的思维方式。”[3]可见,中医界普遍认为哲学思想是中医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古代医者的医疗实践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1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贯穿于古代医学理论与医疗活动之中
中国古代医学理论与医疗活动处处渗透着哲学思想。以“人与天地相参”为例,此思想将天地人看作一个相互影响的统一体,在此启发下,《内经》将各种自然现象类比于人体,构建出众多医学理论,如《素问·离合真邪论》云:“天有宿度,地有经水,人有经脉……天寒地冻,则经水凝泣;天暑地热,则经水沸溢;卒风暴起,则经水波涌而陇起。夫邪之入于脉也,寒则血凝泣,暑则经水沸溢,虚邪因而入客,亦如经水之得风也。”经文将气候变化对江河之影响类比于人体以阐述外邪致病之理。阴阳的思想亦贯穿《内经》多篇内容之中,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云:“阴阳者,天地之道也。”《素问·上古天真论》论人体云:“人身有形,不离阴阳。”《素问·保命全形论》论诊法云:“察色按脉,先别阴阳。”《素问·阴阳别论》论治法云:“凡刺之方,必别阴阳。”此外,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即以三阴三阳为框架,并列出相应的提纲证以统摄复杂多变的伤寒病;明代张景岳于《景岳全书·传忠录》云:“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为医道之纲领。阴阳无谬,治焉不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以蔽之者,阴阳而已。”可见,古代医家在哲学思想的影响下,构建了囊括天时变化、天人关系、人之生理病理、藏象、经络、诊法、治则、药物、针灸的庞大医学体系[4]1。
2 中国医学史上并非所有基于哲学思想的联想方式皆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医学理论与医疗活动影响深远,然而哲学思想在医学领域中具有其局限性。古代哲学思想具有极高的自由度而能够产生多种联想方式,但并非所有联想方式皆具有普遍性与必然性,某些哲学联想甚至无法得到中医界自身的广泛认可。下文将从中国医学史举数例以阐明。
2.1 《内经》中有关人体结构、生理现象的某些哲学联想
“人与天地相参”的哲学思想贯穿于《内经》诸篇内容之中。然而“天”、“地”与“人”的内涵十分广泛,基于“人与天地相参”的联想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但并非所有联想皆具有现实意义。如《灵枢·经水》曰:“人之所以参天地而应阴阳也……足少阳外合于渭水……足阳明外合于海水……足太阴外合于湖水。”经文将人体的经脉与自然界之十二水机械地对应,但缺乏临床证据的支持,任应秋对此指出:“把人体的十二经配比为自然界的十二水,这是古人取象比类的一种方法,但此处之比喻具体意义不大,特别是对于临床更是如此。”[5]又如《灵枢·邪客》曰:“人之肢节以应天地……天圆地方,人头圆足方以应之;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辰有十二,人有足十指、茎、垂以应之。”对于《内经》中此类严重偏离现实的“天人相应”推理方式,刘长林[6]于《内经的哲学与中医学的方法》指出:“‘人与天地相参’的理论……既有朴素辨证法的品格,同时又有夸大事物统一性的地方……那时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处于感性直观的阶段……因而常常用主观臆测的联系替代实际存在的联系。”
此外,《内经》经络学说中存在着二十八脉循环的理论,如《灵枢·五十营》曰:“天周二十八宿……人经脉上下、左右、前后二十八脉,周身十六丈二尺,以应二十八宿。”然而,《内经》在构建二十八脉循环的理论时,对人体的阴跷脉与阳跷脉采取了削足适履的处理方法,如《灵枢·脉度》云:“跷脉有阴阳,何脉当其数?岐伯答曰:男子数其阳,女子数其阴,当数者为经,其不当数者为络也。”在男女同时存在阴跷脉与阳跷脉的前提下,分别对男女之跷脉作不对等的处理无疑十分牵强,最终亦无法得到中医界的广泛认可,如黄龙祥[7]于《经脉理论还原与重构大纲》指出:“在《难经》的体系中只承认‘十二经脉’的说法……汉以后乃至现代,提及‘经脉环周’,人们想到的只是‘十二经脉连环’,很少会意识到还有一个‘二十八脉连环’的存在。”
2.2 古代医家和本草文献对药物药性与功效的哲学解释
古代医家和本草文献普遍使用哲学思想以解释药物药性与功效的原因。有以药物生长环境解释药性者,如苏颂《本草图经》载阳起石云:“阳起山,其上常有温暖气,虽盛冬大雪遍境,独此山无积雪,盖石气熏蒸使然也。”汪昂《本草备要》对麻黄药性解释曰:“中牟产麻黄,地冬不积雪,性热。”有以“同性相从”[8]思想解释药物功效者,如《本草纲目》解释白花蛇“通治诸风”的功效云:“风善行数变,蛇亦善行数蜕,而花蛇又食石南,所以能透骨搜风,截惊定搐,为风痹惊搐、癞癣恶疮要药。”陈修园的《医学实在易》解释百合、苏叶治疗不寐的功效云:“其(百合)花朝开暮阖,紫苏之叶朝挺暮垂,俱能引阴阳归阴分。”有以“同形相类”思想解释药物功效者,如吴鞠通《温病条辨》所载“清宫汤”,方由元参心、莲子心、竹叶卷心、连翘心、犀角尖、连心麦冬组成,方论云:“俱用心者,凡心有生生不已之意,心能入心。”然而,上述以哲学思想解释药性、功效诸例无疑具有局限性。以用生长环境解释药性的思想为例,则地理学上有众多地域常年无雪,然而并非所有位于无雪地域的动物、植物和矿物皆属性热。徐灵胎于《神农本草经百种录》已指出以哲学思想解释药物功效的局限性,如“凡药性有专长,此在可解不可解之间,虽圣人亦必试验而后知之……显于形质气味者,可推测而知,其深藏于性中者,不可以常理求也”。
2.3 朱丹溪“阳有余阴不足”的医学思想及其引发的学术争论
朱丹溪《格致余论·阳有余阴不足论》试图以天大地小、天包地外、日实月缺等自然现象类比人体之“阳有余而阴不足”。然而,在《内经》强调阴阳平衡、阴平阳秘为人体健康之准绳的前提下[4]129,“阳有余而阴不足”的观点无疑难以被中医界广泛认可。此外,天、地、日、月等自然现象的内涵十分广阔,而朱丹溪在论述“阳有余阴不足”时仅采纳有利于自己观点的内涵。例如,同样以天、地、日等自然现象类比人体,张景岳于《类经附翼·大宝论》却云:“凡万物之生由乎阳,万物之死亦由乎阳……试以太阳证之可得其象……设无此日,天地虽大,一寒质耳……人之大宝,只此一息真阳。”吴鞠通《医医病书》曰:“天不如是之大,何能包罗万象,化生万物哉……是阳气本该大也,阴质本该小也。何云‘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两者结论与朱丹溪相异。可见,自然现象有多种诠释方式,诠释角度因医家所持医学思想之不同而有差异。《丹溪学研究》亦指出:“类比不能提供必然正确的结论,其结果还有待于证明……丹溪这种推理得出的结论,主要还是由阴易亏阳易动的实践观察资料证明的。”[9]
2.4 古代医家对预防天花的牛痘接种法的哲学解释
预防天花的牛痘接种法自1796年由英国人贞纳试验成功后于1805年传入中国。古代医家为牛痘接种法所取得的显著效果提供了基于哲学思想的解释。如邱熺著《引痘略》云:“痘何以曰牛也?痘之种自牛来也……盖牛土畜也,人之脾属土,以土引土,同气相感,同类相生,故能取效若此。”黄怀安著《西洋种痘论》云:“其用西牛之痘种者何?以牛性属土,毒逢土则解,借牛之土性以解痘之火毒耳。”[10]《引种牛痘方书》云:“盖牛之物,其性属土,其气最厚。敦诚而能信,东之则东,西之则西,百不一失。”古代牛痘接种法的理论在当时曾起到积极的作用,如廖育群[11]认为理论“在客观上起到了宣传牛痘法优于人痘法的作用”。然而,古代的接种理论与技术在现代不再继续发挥作用,现今中医界亦未将接种法纳入中医临床教育体系之中。
3 哲学思想与实际效果之间可能出现巨大反差——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启示
长期以来,研究中医哲学思想的学者更多关注中医界本身。然而哲学思想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普遍方法,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上除医学以外的案例,能够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的局限性,此局限性可能导致哲学思想与实际效果之间出现巨大反差。
3.1 中国古代炼丹术史中的哲学思想
古代炼丹术试图以人工的方法将自然界的矿物制成使人长生的药剂,而哲学思想贯穿古代炼丹活动始终。例如,对于应当选取何种物质以实现长生的目的,古人运用了“假求外物以自坚固”的哲学思想:与古代本草文献解释药物的“同性相从”思想相同,炼丹家认为应选用入火不焦,入水不腐,入地不朽,在自然界中似有无穷之寿的物质。如晋代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云:“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此外,有以阴阳思想解释物质性质者,如唐代张九垓《金石灵砂论》曰:“一阴一阳曰道,圣人法阴阳,夺造化,故阳药有七,金二石五。黄金、白银、雌雄黄、砒黄、曾青、石硫磺,皆属阳药也……阴阳之药各禀其性而服之。”有以《易经》卦象指导炼丹火候者[12]333,如东汉魏伯阳以卦象描述一月三十天中朔晦之间月之盈亏,以喻炼丹时一月火候之进退。然而,以哲学思想为引导的炼丹活动却造成大量中毒死亡[13]336。炼丹活动虽以失败告终,但绝非一无所获,《中国科学技术史:化学卷》指出炼丹术“开阔了人类的视野……提取和精制了很多化学剂,炼出一些黄色和白色的合金,并且找到了不少解决疑难大症的丹药,造福了人类”[12]224。然而,《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指出:“炼丹家的贡献并非炼丹家的本意。相反,这些贡献,或是他们的副产品,或是被他们视为‘祸事’的失误所造成的。”[13]336
3.2 中国古代火药史中的哲学思想
哲学思想引导下的炼丹活动催生出原始火药的发现,如潘吉星[14]137在《中国火药史》中指出:“炼丹术……到唐末,长生的幻想宣告破灭,在它行将落下大幕之前,给人带来的最大礼物是对原始火药混合物的发现。”中国古代火药理论中亦渗透着各种哲学思想。有以“君臣佐使”思想阐述火药配方者[15]305,如明代何汝宾《兵录》云:“火攻之药,硝磺为之君,木炭为之臣,诸药为之佐,诸气药为之使。必知药之宜,斯得火攻之妙。”有以阴阳思想阐述火药燃烧者[14]79,如明代《本草纲目·硝石·发明》云:“硫磺之性暖而利,其性下行;硝石之性暖而散,其性上行……一升一降,一阴一阳,此制方之妙也。今病家造烽火铳机等物,用硝石者,直入云汉,其性升可知矣。”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佳兵》云:“硝性至阴,硫性至阳,阴阳两神物相遇于无隙可容之中。”然而,古人并未在哲学思想的引导下直接推导出火药成分的最佳配比,相反,原始火药配比向最佳配比的发展是一个不断试验与失败的漫长过程,如李约瑟[15]292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云:“几个世纪内经过实验与失误,无疑从最简单的等比配比到缓慢地找到最有效的硝石配比……许多实验必然是失败了,许多是危险的,甚至发生了不幸,实验过程中常遭遇意外。”
4 结语:医家的临床经验(疗效)是构建中医临床理论的核心成分
哲学思想是古人认识世界的普遍方法,在其引导下的古人通过不断探索,加深了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哲学思想对中国古代医学的促进作用表现在:医者在哲学思想的启发下能够联想出各种可能的诊治方法,增加了应对某些疾病的机会,因而哲学思想是医者创造力的源泉。此外,医者在哲学思想的启发下所获得的医疗经验在哲学的框架和语言下得以形成体系。但是,后世必须认识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在应用于现实领域时所暴露出的局限性。医学具有自然科学、人文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性质[16],因而医学是与现实经验领域相关的学科,绝非纯粹的哲学思想。然而,以上中国医学史与中国科学技术史诸例可以充分表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赋予人们以极大的自由联想空间,因而自由联想未必与经验事实相符合。联想的结果自然有优有劣,发挥“优胜劣汰”功能的是经验检验,与经验证据不符的理论难以有立足之地,如李醒民[17]于《科学论:科学的三维世界》指出:“自然科学作为经验科学,其理论必须根源于经验(观察和实验资料的归纳、抽象和启示),而又终结于经验(经验检验)。”《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亦指出:“一种理论的是非,归根到底,要看它的实验效果,人们最终抛弃金丹术,根本原因,还是它的无效。”[13]348因此,单凭哲学思想不足以构建临床医学理论,医者在临床实践中所取得的疗效是筛选哲学联想的工具,因而临床经验才是构建具有实用性的临床医学理论的核心成分。如邢玉瑞等[18]于“临床实践经验与中医理论的建构——经验思维与中医理论建构研究之二”一文指出:“临床实践经验是中医理论建构与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中医学在现代社会的存在、发展,也以临床实践所取得的疗效与经验为根本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