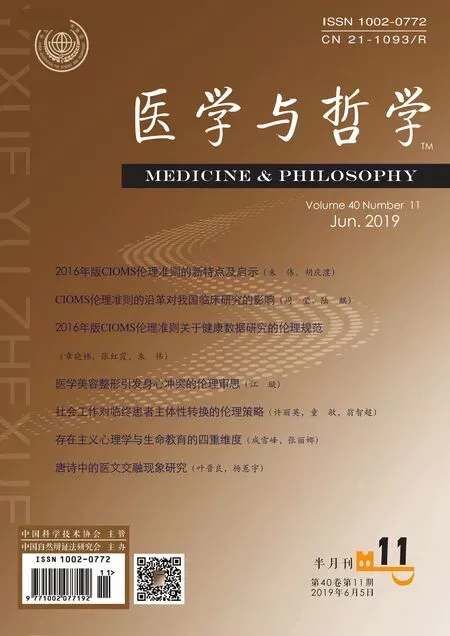痴呆患者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研究进展*
王守碧 陈柳柳 张江辉 缪佳芮 邓仁丽
痴呆是一种以认知功能损害和精神行为异常为核心的渐进性、不可逆的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1]。随着疾病进程的发展,患者将逐渐丧失正常的沟通交流及决策思考能力。如果不协助患者在认知能力尚好时记录未来的生活及规划晚期医疗决策,患者的医疗护理决策将完全由家属和医生决定,这样的医疗决策模式忽略了患者本人的意愿和价值观,违背了患者自主权。而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是以患者本人意愿和价值认同为前提,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沟通共同做出最佳治疗决策的过程[2],符合痴呆患者的需求。目前,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在国外及中国港台地区已逐渐开展成熟,在我国尚处于探索和推广阶段,痴呆患者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尚未见报道,本文综述国外及中国港台地区痴呆患者实施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经验,期望为我国开展痴呆患者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提供依据和指导。
1 相关概念及流行病学
1.1 痴呆的概念及流行病学特点
痴呆(dementia)是大脑病变引起的一种综合征,临床特征为记忆、理解、判断、推理、计算和抽象思维等多种认知功能减退,可伴有幻觉、妄想、行为紊乱和人格改变[3]。痴呆可分为轻度、中度、重度三个阶段[4]。轻度痴呆患者仍可独立生活且保留一定的理解和判断能力。但随着疾病进展到中、晚期,患者将丧失独立生活和自我思考的能力。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有4 700万人患有痴呆症,预计到2030年将增加至7 560万人[5]。随着老龄化的加剧,我国痴呆患者也在迅速增加,预计到2030 年老年期痴呆人数将达1 645.6万人[6]。因此,痴呆已成为全球公共卫生关注的重点问题[7]。
1.2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的概念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dvance care planning,ACP),是支持任何年龄或健康阶段的成年人了解并分享他们的个人价值观、人生目标和未来医疗照护意愿的过程[8]。其目标是帮助并确保人们在疾病终末期或慢性疾病期间接受符合其价值观、目标和意愿的医疗照护。患者以口头或书面形式表达的生命末期医疗照护意愿为预立医疗指示(advance directives,ADs),也称生前预嘱(living will)[9]。ACP更强调以患者为中心,针对患者的个人价值观、需求和意愿进行多次循序渐进的系统化沟通过程,保证患者的治疗意愿真正实现。
2 痴呆患者实施ACP的必要性
目前,世界范围内还没有预防和根治痴呆的方法[10],有大量的资金被用于痴呆患者。2010年,全世界因痴呆产生的总费用约为6 040亿美元[11],给患者家庭和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负担。此外,晚期痴呆患者不仅会逐渐丧失自我意识和决策能力,而且还有多种危及患者生命的并发症存在,肺炎、发热和进食问题是晚期痴呆患者的常见并发症,这些并发症直接影响晚期患者的生活质量,并与6个月的高死亡率直接相关[12]。面临无意义地反复再次入院、过度医疗和不理想的姑息治疗,只会加重患者的痛苦,降低生活质量。此时的治疗手段应该逐渐向姑息治疗目标过渡,提高生存质量,保留人生尊严。ACP是良好的姑息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轻度痴呆期进行积极的ACP沟通可改善痴呆患者的整体护理水平,确保患者在整个疾病过程中保留自主权,接受到符合自己价值观和意愿的治疗手段,从而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及临终关怀质量[13]。由于晚期痴呆患者沟通能力和决策能力面临不可避免的丧失,《痴呆实践指南》也鼓励患者在决策能力不受影响时实施ACP[14]。
3 痴呆患者实施ACP的应用现状
3.1 国外痴呆患者实施ACP的应用现状
自1991年美国率先通过《患者自决法案》(PatientSelf-DeterminationAct,1991),使预立医疗照护计划在美国合法化之后,英国、爱尔兰、澳大利亚等国家都相继颁布了相关法律,支持ACP合法化[13]。在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下,ACP在国外已逐渐开展成熟并在医院或社区等场所广泛使用。同时,痴呆患者开展ACP也愈来愈受重视,如2009年英国卫生部发布的《全国痴呆战略》(NationalDementiaStrategy)等都在呼吁通过促进ACP改善痴呆患者的临终关怀[15]。
3.1.1 研究对象
国外针对痴呆领域的ACP研究大多数是以晚期痴呆患者的照顾者或医护人员的视角探讨痴呆患者实施ACP的经验、ACP在代理决策中的作用及ACP实施的影响因素等[7,16-19],或以符合《国际疾病分类第10版》(InternationalClassificationofDiseases10,ICD-10)诊断标准的具有决策思考能力的轻度痴呆患者为研究对象[20-22],调查其对ACP的意愿及与家属关于生命末期治疗意愿的一致性。但是,对痴呆患者的ACP干预性研究相对较少。
3.1.2 干预者与相关培训
国外痴呆患者的ACP研究大多是在像养老院这样的长期照护机构进行[23],因此干预引导者多为养老院的工作人员或护士。ACP是一个反映文化价值和信仰的复杂过程,沟通内容主要是围绕患者晚期治疗意愿等敏感内容。所以国外发起ACP的干预者必须经过系统的培训,具有良好的沟通技巧和相关知识才能引导ACP沟通。Brazil等[23]研究中的干预护士必须要有至少2年缓和医疗相关领域的工作经验,完成ACP在线课程,并经过当地ACP专家的指导才能进行相关干预。Ampe的研究团队利用Elwyn等[24]提出的共同决策(shared decision-making,SDM)三步模型为框架指导开发了“我们讨论临终选择(we DECide,Discussing End-of-life Choices)”[25],这是一项针对工作人员的教育干预项目,目的是提高养老院工作人员与患者及家属进行ACP沟通的能力,使痴呆患者在ACP沟通过程中更好地表达自我意愿、完成共同决策。
3.1.3 干预策略
国外学者在以患者为中心的干预模式基础上,探索了适合痴呆患者的独特干预模式。Hilgeman等[21]提出了“保持身份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preserving identity and planning for advance care,PIPAC),这是一种以关注轻度痴呆患者情绪为焦点,以患者为中心的干预模式。以对轻度痴呆患者身份及社会角色的维护为起点,逐渐过渡引入ACP部分,完成患者角色的自我调整从而减轻其负面心理感受,达到有效的ACP干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Song等[22]开发了以患者和家属共同为中心的“共享疾病信息,增进信任”的ACP咨询干预(sharing patient's illness representation to increase trust,SPIRIT),这是一种基于患者教育的陈述性方法[26],该方法融合了两种相互补充的理论,即常识模型(common sense model,CSM)和概念转换模型(conceptual change model,CCM)。经过培训的干预者分步骤循序进行,从患者对自我疾病认知陈述开始,干预者帮助患者、照顾者识别认知差距和误解,为患者概念的转变提供机会,最后设定目标和计划。这个过程可帮助照顾者更深入地了解患者的价值观、护理目标以及未来可能的治疗选择。虽然国外对痴呆患者的ACP研究开展较早,但对痴呆患者的干预性研究仍然相对较少,ACP对痴呆患者的效果还需大量的临床实证研究证实。目前,有限的证据表明ACP可降低痴呆患者的住院率及医疗资源的使用[27]。
3.1.4 实施效果
(1)ACP干预的开展有助于患者及照顾者对医疗决策的认知,但生前预嘱签署率不高。Lewis等[28]分三个阶段对轻度痴呆患者及照顾者进行ACP介绍和调查,在回复的48位患者和34位照顾者中,78.6%的患者和63.6%的照顾者都认为患者应该参与到未来的医疗决策中,但只有2位轻度痴呆患者签署了预立医疗指示。(2)ACP干预的开展对轻度痴呆患者的负面情绪具有良好的干预效果,提高患者和照顾者的生活质量。Hilgeman等[21]通过召开4次家庭会议的方式对干预组进行“保持身份的预立医疗照护计划”(ACP名称)干预。结果表明,ACP干预可减少患者的抑郁症状、降低轻度痴呆患者对照顾者的依赖,患者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同时增加了患者在决策过程中的支持,减少了患者和家属的决策冲突。(3)ACP干预的开展可促进医患沟通和医疗决策,提高患者满意度。Brazil等[23]对24家养老院的痴呆患者的照顾者进行以家庭为中心的ACP系统干预。结果表明,ACP干预提高了照顾者的满意度,促进了照顾者与医护人员之间的有效沟通,减少了照顾者在决策中的不确定性。Garden等[29]对参与ACP的80位照顾者进行满意度调查,92%的照顾者都对该服务表示非常满意,一位照顾者说:“我母亲立了一份‘生前预嘱’,这个过程让我有信心知道,即使我母亲不能再进行有效的沟通,我们也了解她的意愿且我们家人终于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
3.2 中国港台地区痴呆患者实施ACP的应用现状
中国台湾在2000年颁布了“安宁缓和医疗法案”,是亚洲第一个赞成“自然死亡”的规定,允许公民根据自己的意愿签署生前预嘱及任命医疗代理人[30]。在中国香港,ACP长期以非立法的形式存在,已经被中国香港公民广泛认可和接受[31]。虽然ACP在中国台湾有立法保护,且在中国港台地区开展较早,但在痴呆领域的ACP研究却相对较少,集中于描述性研究,希望通过开展ACP项目改善痴呆患者的姑息治疗现况[32],或探究痴呆患者参与ACP的影响因素。中国台湾学者Huang等[30]的调查表明,痴呆患者完成预立医疗指示的主要因素有代理人曾经签署过“不复苏”的指示、医护人员告知患者及照顾者ACP的相关信息、养老院有支持ACP的宗教信仰和政策。目前,中国大陆地区还没有针对痴呆患者的ACP研究,这些影响痴呆患者实施ACP的因素对中国大陆开展ACP有借鉴和指导作用。
3.3 我国痴呆患者实施ACP的影响因素
3.3.1 对敏感话题的本能逃避
预立医疗照护计划不可避免地要谈论与临终关怀和死亡相关的一系列敏感话题,但死亡话题在很多国家都是非常忌讳的,患者对ACP常采取本能的逃避和拒绝态度[33]。在我国,由于传统儒家文化和孝亲文化的影响,家属和医生以保护患者的心态拒绝告诉患者真实的病情,剥夺了患者的知情权和自主权[31]。
3.3.2 对疾病的认知
虽然痴呆是一种不可逆的限制性疾病,但公众对痴呆却存在错误认知,认为痴呆是正常衰老的一部分,这是对疾病最常见的误解[34]。甚至部分医务人员对痴呆也存在错误认识,并认为痴呆患者不能从姑息治疗中获益[19]。由于大众对疾病存在不正确的认识,不了解痴呆疾病发展的轨迹及预后等情况,将直接影响患者及其家属对未来的医疗照护规划和参与ACP的自主意识。
3.3.3 缺少支持
痴呆患者对家属的依赖也影响其参与ACP,患者相信即使在自己意识不清或丧失决策能力时,他们的家属仍能为其做出正确的决定,因此愿意把未来的决定权交给家人或命运[33]。但家属却表示在不知患者意愿的情况下做出决策时,仍然面临难以决策的困境[30]。国内有研究发现,由于害怕伤害患者情感,家属不会主动向患者提及ACP话题,但如果患者主动提出,家属愿意支持[35]。患者和家属之间缺乏相互沟通和支持的困境,阻碍了ACP的实施。此外,医务人员是ACP最好的发起者,但大多数医务人员认为ACP对痴呆患者有帮助,实施起来却很困难,并认为ACP已经超出其角色职责范围[19]。且大多数医务人员都缺乏专业的ACP培训和实施技能,不能有效地帮助患者及家属发起ACP。因此,医务人员应加强与ACP相关的知识储备,提升ACP沟通技能,在临床工作中有效促进ACP的开展。
目前中国大陆还没有针对ACP的立法,没有法律法规的支持,ACP在我国很难推进。2012年,《精神卫生法》正式颁布。该法确立了精神障碍患者的自愿治疗原则,说明我国具有确立预立医疗指示权的法律环境[36]。建议我国为ACP制定相关法律和政策,推进我国ACP领域的发展。
3.3.4 痴呆患者实施ACP的时间
通常ACP是在患者生命的最后六个月进行的,但对痴呆患者来说存在挑战和困难[37]。因为随着疾病的发展,患者的沟通能力和自我意识必然会下降,患者将不可能参与自我ACP的讨论。另外,痴呆患者的存活期和疾病进展情况存在个体差异,很难在疾病诊断初期和丧失决策能力之间找到平衡点,因此很难为患者界定明确的ACP实施时间,阻碍了痴呆患者实施ACP[38]。
4 痴呆患者实施ACP的策略
4.1 加强疾病和ACP的知识教育
对疾病的错误认知是限制ACP实施的第一步障碍,应加强对公众的疾病教育力度。有文献报道,对痴呆预后及晚期并发症了解多的代理人比不清楚痴呆疾病进程的代理人更可能为患者选择舒适的姑息治疗[12]。建议通过制作符合中国文化背景的宣传手册或教育视频等手段加强大众对痴呆疾病的发展轨迹、临床问题等信息的知识教育,加强患者及照顾者对疾病的认知,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
Kang等[39]调查了中国15个省份的成年病人及其照顾者对ACP的认知,结果只有38.3%的人听说过ACP。倪平等[40]对养老院老年人进行调查,发现只有4.9%的老年人听说过预立医疗指示。可见,我国公民对ACP欠缺了解,亟需提高公众对ACP的认知。有研究表明,视频辅助决策工具能有效提高患者对ACP的正确认识,推动ACP的开展[41]。通过开发本土化的视频决策等辅助工具加强疾病和ACP的宣教,让更多的人听说ACP的理念并逐渐理解,使其常规化、日常化。
4.2 以家庭为导向、患者为中心的ACP沟通模式
中国文化背景区别于国外,国外推崇个人自主权,认为个体才是医疗决策的第一人[42]。但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沿用的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决策模式,家属不想告知患者病情,害怕其失去生的希望。医生对于患者的病情告知第一人也是家属,而非患者本人[43]。为了找到自主权与家庭式决策模式之间的平衡点,有学者提出了以家庭为导向,以患者为中心的ACP沟通模式[44]。此沟通模式符合中国文化特点,让家属参与共同决策讨论中,而不是一味强调患者的自主决策权,从而减少医患矛盾,更有利于医护人员开展预立医疗照护计划[45]。这对痴呆患者尤其重要,因为患者晚期必然要由代理人代为决策。因此可以借鉴国外开展家庭会议的方法[21],ACP引导者将患者和家属聚集在一起,通过帮助患者回忆生平经历、患病经历及感受,讲述自我价值观和意愿,协助患者及家属共同制定ACP。患者在制定ACP时应给家属留有决策余地,在痴呆患者不能自我决策时,家属可根据先进的医学技术结合患者意愿做出最佳决策。另外,应该鼓励家属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地与患者谈论相关话题,让患者在不敏感和不紧张的心态下,表明自己最真实的意愿。
4.3 探索与痴呆患者讨论ACP的正确时机
由于ACP交流必须在患者有沟通和认知能力时才可进行,因此大多数专家都建议应该尽早与痴呆患者讨论ACP,Poppe等[37]在其质性研究结果中得出可在轻度痴呆患者诊断后不久进行ACP讨论,此时患者有时间考虑其诊断,也有能力为未来的医疗照护做出明确的决定。但具体时间应该具备个性化特征,取决于患者个人的情况以及他们是否准备好讨论ACP。预立医疗照护计划是一个动态变化的沟通过程,从有目的的循序渐进的沟通到鼓励患者表达自我医疗照护意愿的时间进程,都可以根据患者情况随时调整[46]。这就需要相关医务人员和家属协作,个性化地评估患者心理情况及疾病进展,在轻度痴呆期为正确的ACP讨论时机提供合理的个体化建议。
5 结语
痴呆患者作为特殊人群,推进ACP显得尤为重要。同时,随着公民自主意识的增强、国家对姑息治疗相关政策的支持,ACP发展是必然趋势。因此,必须优化公共信息和教育结构,加大痴呆疾病知识及ACP的宣传和教育力度。医务人员应加强ACP领域的知识学习,提高与痴呆患者及其家属进行ACP对话的沟通技巧。通过不断探索适合中国文化背景的ACP的沟通模式,以实现国内痴呆患者的AC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