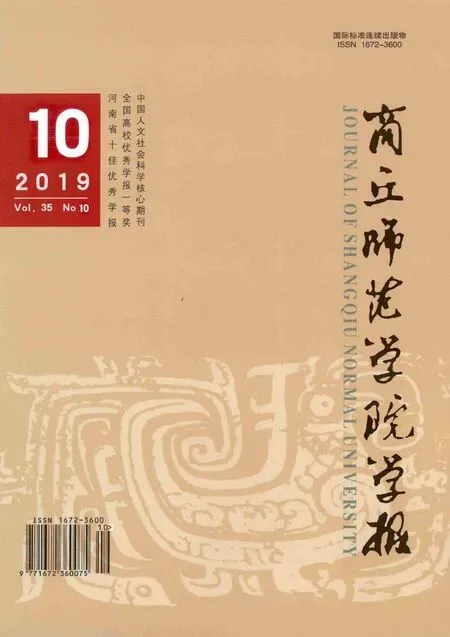皖北工匠编织创新发展可行性探索
张 红 岩
(淮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安徽 淮北 235000)
皖北处于我国南北方交汇处,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温热带植物糅杂生长,自然纤维资源丰富,用于编织的自然纤维材料取之较易,因此,在本地域生活的人们常把它编织成日常生活用具,使用广泛。不仅汇集竹编、柳编、荆编、绳编等小型编织,还包涵屋内隔断、房外篱笆、圊墙、围栏等大型固定型编织,编织形态的多样性产生多元的图式与各异的肌理效果,我们汲取这些图式与肌理并应用到装饰艺术中,补益当代装饰语言。编织材料的原生态自然纤维为人们熟识,用此转换为艺术新媒介材料创作艺术作品会产生对材料的熟悉感与艺术元素的陌生感,欣赏者解码式“揣测”这种熟悉的陌生感艺术作品,对亚媒介主体揣测正是艺术家创作传达欣赏者的意图。不仅如此,皖北工匠编织时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为艺术创作者的必备素养,工匠精神的核心价值体系也是新时代精神文明所倡导。
一、皖北工匠编织肌理与图式补益特征
广义皖北隶属于康熙年间的庐凤道与光绪年间的皖北道,狭义的词义指安徽北部,安徽省唯一的“一带一路”经过地区,地理位置的特殊性,温热带植被生长葳蕤,因此,编织原生态自然纤维材料如竹、柳、荆、麻、草、玉米苞皮等较易获取,加之工匠编织技术南北汇集交流,从而形成工匠编织图式的多样化,有竹编、柳编、荆编、绳编等,由于材质的不同,它们显现的肌理效果各异,这种重复性的编织纹理视觉效果为现代装饰材料提供了新图式,成了传承新时代文化的元素基因。例如,柳编农具簸箕,网状肌理重复规则排列,形成点状、线状、面状视觉冲击。如果提取这些肌理效果用到装饰艺术创作中,正如评论家多拉瓦利埃(Dora Vallier)所述:“线的厚度及其扭动上,甚或引入到经纬的关系上,在这种关系中,编织能够把有规则的和无规则的结合起来,改变浮动与紧连的关系”[1]28,也正是“浮动”与“紧连”的关系,形成了装饰性的设计语言,让欣赏者透过肌理装饰艺术语言产生想象空间,推测亚媒介空间的神秘传达。
从皖北工匠编织的图式视角来看,现代图式元素在其编织中呈现出具有解释性的视觉信息载体,编织工艺所刻画的图形符号在抽象事物的意识形态上建立起一种新式的探索性语言。这种形式语言在编织工艺领域虽然主体相对简单,但是在其所构建的三维空间中既可以视为朴素原始之美,又具有视觉观赏之美。编织工艺结构随着图式元素在艺术客观事物中尽情地发挥,工匠通过对图式的辨认进行主观思维的探索与升华。编织作品的图式不仅仅表现在工匠对于客观事物的形式语言的探索与构架,更体现在工匠认识到不同编织工艺品对其传统文化符号主观上的意识形态的理解与不同图式所构建的心理感知所呈现的特殊的表现形式,“传统文化符号之于设计的运用,则必须符合它的自足性和内在发展逻辑,隔断传统文化符号与现代设计之间的联系,显然是治标不治本的假象”[2],而这种传统文化符号图式视觉元素的表现形式正是构建编织工艺的最主要的特色形式之一。从上述来看,编织图式对装饰艺术语言产生有益补充,皖北独特的地域特点,丰富的编织素材,编织手法汇集了融合南北方工匠技术特色,也正是这种整合补益装饰语言。
总之,以皖北特定地理位置为坐标,从编织原生态材料的广泛性,到南北工匠的技术交流与整合,延伸为本区域视觉文化的不可缺少的元素,我们从中提取皖北工匠编织肌理与图式应用到装饰艺术中,以补益装饰艺术语言。这种装饰艺术语言为人们熟识,易引发潜意识中的联想与情感追忆,情感是观察者欣赏艺术品引起共鸣的原点,我们通常认为,让观察者产生情感的作品就是成功艺术品。
二、皖北工匠编织原生态自然纤维材料转换为艺术新媒介的可能
皖北原生态自然纤维材料最初由工匠进行编织成用具和工艺品,便于日常生活的器物,它的实用功能是首要的,在以功能主义为核心下进行加工处理,形式的美感自然彰显。这种形式感非有意识加强洗练,而是顺从器物功能的结果。例如,捕鱼虾黄鳝用的竹编篓子,用经纬交叉斜织技法编织,口大底窄,能让水迅速进入,漏孔紧密,但尽可能使出水阻力减弱,扣留进入竹篓的鱼虾,起到捕鱼的功效。从功能主义的角度来看,它让水流掉但存留鱼虾,造型随着功能转换,形式附属于功能。如何把这生活用具竹编篓子转换为艺术新媒介载体呢?换言之,需要从一个生活用具转换为艺术作品,用现象学视角透过表象反映事物本质,由形式功能为客体衍变为审美功能为主体。因此,我们认为可以从材料、技术、造型、数量、大小、色彩等方面去研讨。
原生态自然纤维材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高频率物质,将它应用在艺术创作中能让欣赏者产生熟悉感与亲切感,从而调动他们在大脑中储存的潜意识,产生情感共鸣。对熟悉的自然纤维材料作为艺术的新媒介载体,无意识的共频拉近创作者与欣赏者的距离,欣赏者解码亚媒介“揣测”主体传达的意图,避免完全陌生媒介载体与隐藏在暗处的亚媒介主体传达的威胁与危险。正如鲍里斯·格罗伊斯(Boris Groys)所说:“观察者不能去信任一个令他生疑的符号,就像他也不能去信任一个唤起他信任的符号——如果这个符号在它面前显现出是值得信任的、是真诚的。”[3]41不难看出,解读作品的时候熟知信任的符号有多重要,而恰好自然纤维素材提供了真诚符号,编织肌理纹样也提供这种信任符号。从这方面来看,艺术作品继承了传统材料与技法,新时代的艺术创作继承与转换彰显了它的魅力。
艺术新媒介载体应用自然纤维材料,观察者从“信任材料”与艺术符号中解码,揣测亚媒介空间传达的意图,以便引发作品的趣味性,这就需要艺术的另一重要陌生感元素。陌生的艺术符号、造型与熟悉的材料、编织技法共同构建了艺术作品的熟悉的陌生感,对于数量的多少与色彩的调和起到调和剂与中庸作用,平衡了视觉经验,情感也以此释放,“有意味的形式”顺应产生。此外,色彩元素在皖北编织工艺中作为新式创作的最主要的手段之一,不仅仅是要其运用传统手工艺表现其固有的工艺特点,而且创作者本身通过编织工艺品本身要使其引起共鸣与体现。因此,在创作编织工艺品的同时,必须具有丰富的情感与艺术形式语言的感染力,这种色彩元素与编织工艺作品的共鸣需要艺术家在其抽象图式中运用不同的颜色进行混合且有序的排列方式才能呈现出作品本身的面貌与情感。
皖北工匠编织物的制作程序这种非物质文化随着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物质的丰富,以特殊的形态被代替,正在民间趋于消失。如果予以保护,地域广阔非能顾及全面,尚有延续传承需本体转型,从材料的使用功能、医疗保健价值、审美功能为基点,以崭新形态进入信息时代,从而转换成艺术新媒介载体,以博得大众的偏爱。另一方面,吸取皖北区域各工匠编织造物手工制作流程及技术,对编织造物形式的艺术语言进行提炼,转换到高等教育教学实践中,例如用艺术的审美去制作工艺美术品与艺术品,工匠精神的精益求精的技术要求个体拓宽这种非物质文化新媒介,从这方面来看,也是转换为艺术新媒介载体。
三、皖北工匠精神的现代价值
皖北工匠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为精神核心价值,他们精心甄选编织材料,无论竹材获取、荆条收割,还是茅草采集、柳条折获,都是一丝不苟地进行甄选,按照春夏秋冬时令进行,如同采药制药般进行炮制,未尝有丝毫懈怠。比如,在淮北香山庙会见售的清代竹编喜字提篮,售者称自己祖辈采用竹子三年生长期以上,在冬季砍伐做成竹蔑,再经过二十多道工序编织,十几种编织技法,特别是双喜字编织缜密,字形具有现代设计感,最后刷大漆制作而成。历经时间的洗涤,包浆紫金釉色,在自然磨损中诉说它的故事。这种以器物叙事,记忆深刻,视觉感受强,触觉顺畅,不禁令人揣测编织者聚精会神的工作状态,严谨的造型传达自身专业素养,这中职业素养也是我们艺术创作者必备的,也只有这种忘我创作状态才能传达欣赏者,以引起艺术共频。
皖北工匠精修深研、至真至纯的专业精神,创造与编织着皖北的工匠文化。这种敬业精神在其他国家的现代纤维艺术中也得到体现。例如,艺术家YAGI MARIYO的作品《标志》,用自然纤维材料马尼拉绳、铁、白砂石组合完成,马尼拉麻的精致编织与不锈钢形成对比,白砂石作为铺垫衬托,材质的柔嫩与刚硬,肌理的粗犷与顺滑,空间的虚无与真实,是一场视觉的捆绑,情感的倾诉,而这一切都离不开艺术家精修深研的敬业精神。由此观之,艺术家与工匠至臻至纯的工作态度是相通的,他们共同创造着文化。换言之,皖北区域工匠编织文化通过工匠手工创造出来,服务于本区域乃至全人类,同时,在生活、生产与消费中,工匠文化一直担当人们息息相关的生命文化,其核心是工匠精神,载体为工匠造物。从我国传统造物学的视野来看,工匠编织造物是工匠文化体系中的物质再现,工匠编织者手作的器物与器具也是社会发展水平与文明程度的标志,造物形式的艺术语言是工匠的传承与发展根基。反之,如果没有工匠造物形式的艺术语言传承与发展,作为工匠文化的核心工匠精神便虚空与苍白,成为庙堂的拜祭,失去生命文化谱系中的救赎价值。毋庸置疑,皖北的工匠编织文化亦是如此,至真至纯的敬业精神也是艺术创作者所传承与发展的。
四、结语
综上所述,现代人们对于精神追求越来越多,传统区域性工匠编织造物文化的挖掘与发展成为了当代社会重点关注对象,鉴于此,从皖北传统编织造物内涵出发,对皖北工匠编织中的理论进行了分析、整合转换与发展,作为艺术创作的沃土,艺术创作者汲取精益求精、至真至纯的专业精神提供营养,以创作高质量作品。同时,对其工匠编织形式的艺术语言研究在现代社会中占据着不可代替的作用,寄皖北区域现代工匠文化的发展有所理论与事实依据。随着比特时代的到来,全球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现代工匠编织文化正逐步地深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全球日益重视现代的文化与艺术,并将其列入国家经济及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内容,由此观之,对它的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研究具有特定文化价值与社会实践意义。